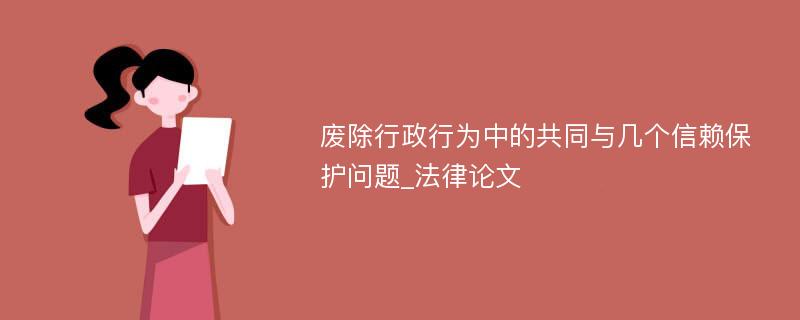
行政行为撤销上的信赖连带保护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行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信赖保护原则亦称保护相信原则,始于德国50年代中期,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根据法律 安定性原则以及民法诚信原则推论而确立,并以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独立的宪法性原则 ,学界及法院判例多从宪法原则高度对此加以研究并推动其发展。1976年联邦德国行政 程序法第48条和49条对此加以了明确规定。继后,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对此问题加以了 研究并得到了发展。信赖保护最初产生于行政行为的撤销问题上。其对象最初也是着眼 于行政相对人,但随着行政活动的复杂化和广泛化,越来越多的行政行为不仅仅涉及相 对人,而且还涉及第三人。那么第三人是否也能得到信赖保护?又应如何进行信赖保护? 这个问题很少有学者涉及,更没有引起有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注。笔者在此试想 来个抛砖引玉之举,讨论一下行政行为撤销上的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现故且称之为信 赖连带保护,要讨论此问题,首先得对行政行为撤销问题以及撤销与无效和废止之间的 区别有足够的了解。
二.行政行为撤销的理论及分析
有关行政行为撤销的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定义,(注:“行政处分之撤销谓将已发 生效力但存有瑕疵之处分,原则上溯及的使其失效。”(台)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 用》,三民书局,1999年增订五版,第367页。“行政处分之撤销,及就已成立之行政 处分,因其有撤销之原因,由有权机关予以撤销,使其不发生效力而回复未为其处分以 前之状态。”(台)管欧:《中国行政法总论》,五南出版社1983年第二十一版修订本, 第463页。“行政行为的撤销,是指由于行政行为而形成、消灭法律关系时,该行政行 为具有瑕疵,因而撤销该行政行为,以使法律关系恢复原来状态。”(日)盐野宏:《行 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行政处理的撤销是指行政机关 取消原来决定,被撤销的决定从其成立起丧失效力,视为自始没有发生效力。”王名扬 :《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行政行为撤销是指有 关国家机关对已成立的行政违法行为的效力事后以违法(或不当)为由予以消灭,从而使 其向前向后均失去法律效力。”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47页。以上概念着眼于撤销原因与效力上,作者在此须指出的是本文行政行为的 撤销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各学者在表述上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是着眼于 撤销的原因和撤销后的效力这两个角度来下定义的。
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为行政行为有瑕疵存在,包括违法与不当。违法与不当是行政行 为撤销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必然条件,也就是说违法与不当不一定会引起行政行为的撤 销,但若是被撤销的行政行为则必定是违法或不当的。这一点上把行政行为的撤销与行 政行为的废止区分开来,行政行为的废止是合法的行政行为由于法定客观情况的出现而 使其从废止起向后失去效力。同时,行政行为撤销的目的在于纠正错误,而行政行为废 止的目的是使行政行为能适应新的情况。德国行政法学家毛雷尔把撤销与废止同作为废 除的下位概念,而废除是一个上位概念,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院通过专门宣示,消除行 政行为法律效果的行为。(注:(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 社2000年版,第270页。)这一点揭示出了行政行为撤销与行政行为废止在法律效果上是 相同的,即使行政行为失效,但何时起失效这个问题上又是不同的。
行政行为的违法与不当后果之一是行政行为的撤销,另一可能的后果是行政行为的无 效,无效与撤销虽都因违法或不当所引起,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无效的行政行 为是根本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对行政机关及相对人或第三人,均不发生效力,任何 机关或个人均不受其拘束,即使其未经确认为无效,换言之,对无效的行政行为,任何 人可以不予理睬。而撤销的行政行为是已生效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效力包括公定力、 执行力和不可变更力,(注:行政行为的效力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台湾学者陈新民 把行政行为的效力归为拘束力(陈新民,《行政法法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修订六 版,第237-238页。)日本学者盐野宏在上述三个效力上再加一个不可争力(盐野宏,《 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12页。))据于公定力,任何行政 行为一旦付诸实施,除无效外,在被有关机关撤销之前,均视为具有效力的行为,任何 机关或个人都必须遵守并服从其效力,所以撤销的行政行为是违法但已生效之行为。值 得注意的是,违法与无效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评价标准,违法相对于合法而言,无效相对 于有效而言,所以违法不一定无效。还有一点,无效行政行为必定已是行政行为,并不 是非行政行为或假象行政行为。(注:所谓假象行政行为是指具有外表上的行政行为假 象,但原则上不具任何实体法或程序法上效力的行为,如:非警察人员着警察制服,行 使警察权所为的行为。)
行政行为的撤销效力是否溯及既往这个问题上,大多学者都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 则应使行政行为恢复原来的法律状态,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视为自始没有发生法律效力, 因为撤销之行为是属违法或不当依法行政的原理,理应自始无效,这也就是说行政行为 撤销效力溯及既往。但也有学者如日本法学家南博方则认为:“除不撤销过去形成的法 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而不能实现撤销目的等情况下,职权撤销的效果不溯既往。”(注:( 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周作彩译,韩大元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 8年版,第48页。)笔者认为,从一般原则上,行政行为撤销之效力应溯及既往,这符合 行政法定原则,不溯及既往当属例外。当所撤销的行政行为能为行政相对人带来利益时 ,则应充分权衡所撤销之利益与相对人之利益,当相对人之利益大于撤销之利益时,则 应保护相对人据于对行政行为的信赖而已得到的利益甚至可能得到的利益。传统理论认 为,“撤销应溯及既往失去效力,废止始往后失去效力。但近来行政法之发展以为违法 行政处分之撤销并不一定要溯及既往,亦得往后失去效力,尤其为保护相对人之信赖与 维护公益,常须排除其应溯及既往失去效力。”(注:翁岳生:《论行政处分》载《法 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此时,撤销的效力应不溯及既往, 这也是法的安定性的要求。
行政行为依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以其对相对人所产生的法律上的效力为依据,主 要可分为授益性行政行为和负担性行政行为两种。所谓授益性行政行为是指以权利或法 律上重大利益的设定和确认为内容的行政行为;所谓负担性行政行为是指干涉相对人的 权利或为不利益的确认或拒绝其受益的请求权的行政行为,也可称为不利益行为或限权 行为。依通说,负担性行政行为应该随时可以撤销,以解脱加于公民身上的违法限制及 负担,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若相对人已为承担不利益之处分而导致既得利益受损或以 另一更不利的行政行为代之时,行政行为的撤销要受一定的限制,这是对相对人利益的 保护,也是体现相对人对国家权威的信任和服从。另外,还有具有双重效力的行政行为 以及混合效力的行政行为,前者指同一行政行为对一人为授益行为,对另一人却为设负 担行为,即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行为,后者是指行政行为对同一相对人既授益又负担 的行为。信赖连带保护问题就产生于具第三人效力的双重效力行政行为撤销之际。
三.信赖连带保护
信赖保护原则亦称保护相信原则,其含义:由于政府以往一贯所采的政策、法制或措 施,使人民对其作为产生信赖观念,认为不致轻易改弦更张,遂就有关自身权益之法律 关系事项,依据此种信赖观念的判断加以处理时,则嗣后政府若无正当理由,即不应对 有关事项采取与人民所信赖观念相抵触之措施,使人民既得权益有所保障,并避免行政 机关对现行行政命令的轻率变更,致使其威信受到损害。(注:张家洋:《行政法》, 三民书局,1993年,第232页。)简言之,“信赖保护原则就是要求保护人民对于国家之 信赖,即不容许国家之行为使人民值得保护之信赖丧失,或是使人民因此无法预估到负 担之增加或丧失利益。”(注:洪家殷:《论违法行政处分——以其概念、原因与法律 效果为中心》,东吴法律学报,1995年第八卷第三期。)即当事人信赖行政机关的决定 合法性持续存在时,则对其据此所作的行为必须予以保护或给予合理的补偿。
信赖保护原则设置的目的是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在许 多公法领域都有适用的余地,(注:日本刑法学家中山敬一对此问题也加以了专门论述 ,可参见中山敬一:《信赖原则》,载中山研一、西原春夫、藤木英雄、宫泽浩一主编 :《现代刑法讲座》(第3卷),成文堂1982年版,第80页。)但于行政行为的撤销最具有 直接关系。授益性行政行为撤销是信赖保护首先也是重点考虑的对象,在各国实践也是 运用最为完善的,但对具第三人效力的双重效力行政行为撤销时对第三人是否也应适用 信赖保护在学者之间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大多学者认为应以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为信 赖保护的前提条件,至于第三人的受益则只是相对方负担或授益所产生的事实上的结果 而已,德国学者Knoke表示原则上行政处分之内容应针对相对人,而且也只有相对人得 藉由该处分确认法律效力……相对人负担之行政处分,可以并非只是偶然地具备第三人 受益之附带效果。另一学者Bverw也认为行政处分之内容并非针对第三人法律上重大利 益之创设,是以,其应不在授益行政处分之法律定义范围内。(注:转引洪家殷:《撤 销行政处分时对其性质为授益或负担之判断》载台湾法学丛刊,第154期,第72页。)由 此可见,具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行为是以对相对人的法律效力为标准的。依上述德国学者 说法,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不能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相提并论,对于第三人受益的负担性 行政行为仍适用负担性行政行为的撤销规定,我国台湾学者一般也接受此观点。(注: 如吴庚在《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关于第三人效力处分撤销的论述中也认同不考虑第 三人保护。(三民书局,1999年增订五版,第370页))
但已有少数学者认识到第三人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信赖保护产生的限制应 当适用,裁量权衡时不仅要考虑公共利益和受益人的利益,也要结合考虑承受负担的第 三人的利益。”(注:(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 版,第308页。)“一个在近期显得十分重要的情况,即对一个具有对第三人效力的行政 行为的撤销和废止。”(注:(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笔者认为在行政行为的撤销上应当也必须考虑第三人的 信赖保护利益,在一个行政行为中,确实,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为主要利益,但这并不意 味着可以以相对人的利益来抵消或忽视第三人的利益,换言之,第三人的权利不能以有 利于相对人的受益的信赖保护而受到损害。在权衡公益与相对人及第三人利益时,不能 从表面来判断该行政行为是授益还是负担,而应从行政行为关系人的实际意义上来衡量 是否受益。德国公法学家毛雷尔说的好,“从关系人的利益立场来看,关键不是待变更 的行政行为是授益还是负担,而是变更本身是授益还是负担”(注:(德)毛雷尔:《行 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因此,考虑信赖保护不应 单纯从授益或负担来考虑,而应从关系人本质上是否受益为考虑信赖是否值得保护的依 据。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一切行政行为的存续性及合法性所形成的合理信赖的社会成员 ,第三人理应也可主张信赖保护。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0条中隐含了对第三人的信赖 保护,在撤销双重效力行政行为时不仅考虑授益人与公益的关系,也要考虑第三人利益 的公允原则。若作为不利方的第三人要求撤销授益的行政行为,并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讼的形式引起法律救济程序时,相对人的授益不再适用信赖保护,这说明已发生法律救 济程序时,偏重于保护不利方的利益。反言之,如果没有引起法律救济程序的情况下, 双重效力行政行为中的任何受益一方利益都得以保护。(注: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0 条规定:“第三人要求撤销授益的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程序中撤销了 行政行为并以此解决了冲突和终结诉讼的,第48条第1款第2句、第2款至第4款以及第 49条第2款至第4款和第6款的规定不再适用。”)
因信赖保护主要涉及受益的保护问题,所以与第三人信赖保护相关的具有第三人效力 行政行为有这样两种:其一是第三人受益的负担性行政行为,这也是最为常见的;其二 是第三人受益的授益性行政行为,这在现实中不太见,但确实是存在的,如经证监会批 准,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发行股票,股民购买此上市公司的股票,此许可行为明显是一 个授益性行政行为,而股民作为该行政行为的第三人也是受益者并非是负担者。这两类 第三人受益的行政行为撤销上则应充分考虑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护,此信赖保护可称之 为信赖连带保护。因相对人的负担而使第三人受益的行政行为,若因负担性行政行为是 违法而予以撤销时,假如第三人因相信自己受益的存在而已作了适当生活上的安排时, 则行政机关在撤销该行政行为时应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已得利益经权衡可以不予返 回,预期可得利益的取消则应给予第三人缓冲的机会,好让第三人作好以后生活的必要 安排。至于第三人受益的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上,考虑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时,也须 考虑第三人的信赖利益,而且,当相对人的利益不符全信赖保护条件时,若第三人对此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应单独予以信赖利益的考虑。第三人的信赖连带保护的构成条件 可以比照信赖保护的一般构成条件,首先,须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基础,即先有一个令人 信赖的行政行为的存在,且此行为与第三人有关,这是第三人信赖保护的前提条件;其 次,信赖表现,第三人有因信赖而作出的一定具体行为,即有一个处理行为(包括不作 为),第三人已经运用财产而产生法律上的变动或用自身的行动产生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效果;最后,第三人信赖是值得保护的(即正当的信赖保护),这是考虑第三人信赖保护 的最重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比较主观又不易衡量的内容,可在实例中又是必须考虑 的问题。依信赖保护一般理论,下列情况下是不予信赖保护的:
1.当事人恶意诈欺、胁迫、行贿或其它不正当的手段而获得;
2.当事人对重要问题或注意事项作不正确或不完整的说明;
3.当事人明知或因为重大过失而不知行政行为违法。
由此可见,这里的值得或正当是指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或法律状态深信不疑,并 在信赖表现中是出于善意亦无过失,信赖保护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并且信赖基础与信赖 表现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存在。(注:参见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 社,第276页;参见吴坤城《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收于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 一般法律原则》(二),三民书局1997年;台湾的行政法裁判百选总论篇第24至27。)(注 :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之际已有保留变更的规定,则当事人应预见到有变更的风险 存在,所以也不应有信赖保护的问题,当然这也可归之于当事人明知之中,但严格来说 明知的是行政行为的违法,而保护变更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所以笔者在此把它另列 ,台湾学者吴坤城所列举的不应值得保护的包括明显错误的行政行为,笔者想可把此放 至于明知这一理由中,因为显然错误,毫无疑问能为当事人所明知的违法或不合理的行 政行为。)
公益是否为信赖保护要件这个问题上,有学者提出当有强烈的公益要求时,则不应考 虑信赖保护,台湾学者林合民和林锡尧持此观点,吴坤城则认为公益不应作为信赖保护 之要件,笔者认同吴坤城学者的观点,若公益少于个人之私利,则无疑可用信赖保护, 那么当公益大于私益时,无非两种选择:维持其存续力或撤销与废止,维持存续力则是 在运用信赖保护;撤销与废止若无补偿产生,则为没有运用信赖保护,若有补偿产生, 则明显是信赖保护运用的结果,事实操作中,信赖保护不在于公益有没有大于私利,而 是有没有产生存续力和补偿的问题,公益大于私利时既可适用信赖保护原则,也可不适 用信赖保护原则,一般而言,当公益大于私利时,应予撤销或废止行政行为,同时,据 于实际情况和信赖保护的三个条件给予公民适当的补偿,所以公益不能成为不适用信赖 保护的理由,总言之,只要具备信赖基础、信赖表现和正当信赖这三个条件,行政机关 都应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第三人信赖连带保护应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即如何实现信赖 保护的效果,当符合信赖保护条件时,若出现行政机关欲变更和消减原为人民所信赖的 法律行为和状态时,如何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依信赖保护通说,采用二种保护方式: 存续保护和财产保护。第三人的信赖保护是否也有这两种方式呢?笔者认为,第三人的 信赖保护方式采用财产保护为较佳,理由因为,虽然具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行为中必须考 虑第三人的利益,但毕竟其效力是处于较次要的地位,若为第三人的信赖利益而存续对 相对人的违法负担行政行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何况作出的行政行为直接所针对的是相 对人而不是第三人,行政行为的效力也是据于相对人而产的法律上的后果。所以对第三 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采取财产补偿的方式是较合理的。
信赖连带保护问题上还须注意一个问题,即第三人的范围应受到限制,而不能无限度 的随意扩大,其实质就是信赖利益不能无限制地扩展至反射利益。如因火车站的搬迁而 导致火车站周围商业的败落,此时作为商业业主能否请求信赖保护?再如,若甲拥有一 土地,与乙合作想成立一个娱乐公司,而后有关行政机关撤销甲对此土地的使用,问乙 能否请求信赖保护?前者的商业业主依火车站优势而得的利益明显属于一种反射利益, 后者的乙从表面上看似乎因行政行为的撤销而直接导致合作利益的受损,而事实上乙权 益的获得是建立在甲对土地有使用权的基础之上,而甲对土地的使用权建立在有关行政 机关的许可基础之上,所以,乙的利益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反射利益,因此乙利益的救济 手段不是用行政法的信赖保护而应用民法合同上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