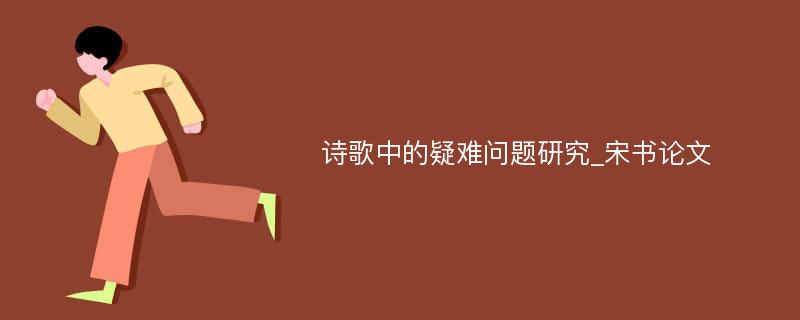
《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难问题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钟嵘身世中的疑点——曾祖父为什么任后魏永安太守?
钟嵘身世有一个疑点:曾祖父钟源任后魏永安太守。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发现。一般研究者以为,钟嵘高祖、曾祖、祖父史无其名,不可考稽。后来,查阅他家谱时发现,钟嵘高祖、曾祖、祖父三代均有其名,不仅有姓名、字号,还有仕宦情况:高祖钟靖,字道寂,为颍川太守;曾祖钟源,字循本,为后魏永安太守;祖父钟挺,字发秀,为襄城太守,封颍川郡公。
又进一步发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也有记载,其世系虽与《钟氏家谱》有出入,但“三祖”的部分完全相同,经比较考察,此世系是可靠的。七世祖钟雅至钟嵘世系为:
钟雅——钟诞——钟靖——钟源——钟挺——钟蹈——钟嵘
发现新材料,对考证钟嵘的身世很有帮助,但钟嵘身世,毕竟有我们完全没有了解的一面。随之产生的疑问是:
为什么高祖钟靖为颍川太守,曾祖钟源却任后魏永安太守?祖父钟挺又为襄城太守、封颍川郡公?我们知道,钟氏历仕汉、晋要职,七世祖钟雅因护元帝过江,为建立东晋王朝作出贡献,封广武将军。此后钟氏便世居建康(今南京),何以高祖钟靖仕颍川?曾祖钟源仕后魏?祖父钟挺又仕襄城?其时,颍川早已沦为北方政权的辖地。是不是根据当时的习惯,人在南朝,官封北地,这些官衔只是空的封号?即使“颍川太守”、“颍川郡公”是,“后魏永安太守”也绝不是,因为它属于北方政权,应是实有其职,实行其权的。那么,这个“后魏永安太守”与前面的“颍川太守”,后面的“颍川郡公”是什么关系?祖孙三代犬牙交错的仕宦经历,显然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疑点。对此应该如何解释?
我的假想是,钟氏的高祖、曾祖、祖父,其仕宦经历会不会与当时的陈伯之有类似之处?陈伯之为齐江刺史,梁武帝起兵讨齐,陈伯之降梁,协助平齐有功,封丰城县公;梁天监元年,他又投降北魏;梁伐魏时,由于丘迟的劝说,陈伯之重新降梁。在钟嵘高祖、曾祖、祖父,包括钟嵘生活的时期,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互相对峙,长期进行拉锯战争。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攻伐,混乱纷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包括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不仅带来城市的残破,万姓的死亡,还使土地归属屡易其主,将帅郡守朝叛夕降成为那一时代特殊的景观。陈伯之降魏时,其亲属、妻妾仍在梁地。梁武帝的政策如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所说的,是“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假如钟源任后魏太守,身居伪官,其家属子女仍在南朝,情况与陈伯之相同,那钟嵘的家庭无疑会受到牵累,并与东晋政权处于某种对立的地位,由此蒙受巨大的政治阴影和生活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钟嵘与父祖辈的关系,钟嵘只提从祖钟宪,列于“下品”,与谢超宗等人同条,并转述:“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传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由此,我们知道二点:
一是,钟嵘写作《诗品》,事实上有家学渊源,先辈指导,这是人们忽视的;第二,说明钟嵘与祖父一辈尚有接触、交流;钟宪能对钟嵘谈诗,钟嵘记住并写进以后的著作,可见钟嵘当时年龄已不在小,由此推断,钟嵘应该有与父亲钟蹈、祖父钟挺,甚至曾祖钟源共同生活的经历,了解在这个家庭内所发生的一切。钟嵘在《诗品》中没有提钟蹈、钟挺、钟源,也许他们不擅五言诗,无法评论?也许有一个钟宪代表就够了,自己的父亲、祖父、高祖,直系亲属应该避嫌疑?
不管怎么说,钟源仕北魏的经历,会使他们家庭处于山川阻隔,政治磨难,亲人思念、分离的痛苦之中;尽管这一变故到钟嵘祖父和父亲时已经结束,但创伤和阴影会重重地压在他们心里。
从祖钟宪在评价诗歌,并对大明、泰始诗风作出批评的同时,会不会把家庭的悲剧,把诗歌的感荡和人生的感荡告诉钟嵘。在解释大明、泰始诗风渐趋华美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向钟嵘表明情性与诗歌的对应,悲剧与情感的发生?不得而知。但是,钟嵘的诗学理论,既有时代风气的影响,前代文论家的遗传,也会与自己的身世有关。从宋都建康,到后魏永安,再到襄城,必定悲欢离合,魂梦飞扬。钟嵘也会由家庭的悲剧,联想“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的历史悲剧,联想屈原的《九章》、《九歌》和《离骚》,领悟人生悲剧和诗歌发生的关系;从家庭个人的艾怨,联想整个社会的怨悱,贯穿汉魏晋宋以来“以悲为美”的传统;理解江淹《别赋》、《恨赋》所蕴涵的社会意义,最后把“怨”与“雅”同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以评判诗歌的优劣高下。
钟嵘论诗歌的作用是“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从钟嵘的身世可知,这并不是简单重复孔子“诗可以群,可以怨”的陈言,而有自己家庭悲剧的“潜台词”。在当时的文论家只把“自然感荡”和“四季感荡”作为诗歌发生的根源时,钟嵘却说:“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把“人际感荡”也作为诗歌发生的重要原因,超越了同时代的批评家。钟嵘天才的创造,正融入了自己的身世?表达了家庭的悲怆?
假如是,我们就能找到隐藏在钟嵘文学观念背后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中国古代论家在构造理论,形成观念,提出自己新见解的时候,一如古代诗人在写他们生命的歌,同样有个人身世和家庭命运的参与。
在新材料进一步证明以前,本文的说法还是个假设。但由此深入,弄清钟嵘身世及其诗学理论的关系,《诗品》研究便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二、《诗品》中诗人的职衔称谓
《诗品》既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的优劣等第,就应该对这些诗人的职衔称谓法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但目前诗人的职衔称谓存在某种程度混乱:一是称名、称字的混乱;二是职衔称法的混乱;三是人名前职衔称谓缺漏的混乱。有的可以解释,有的解释不通。
(一)称名、称字的混乱。最早注意到《诗品》中称名、称字问题的是纪昀。他在《四库提要》中说:《诗品》“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称元长,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台新咏》亦惟融书字。盖齐梁之间避和帝之讳,故以字行,实无他故。”纪昀的说法不对。故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反驳说:“案:见行《诗品》,如汲古阁本、《历代诗话》本、《汉魏丛书》本、严可均辑《全梁文》本,均称“齐宁朔将军王融诗”,不称元长,与《提要》异,不知《提要》所据何本也。‘齐司徒长史张融’亦不称字,知非避和帝讳矣。《提要》误也。”我怀疑纪昀没有看过《诗品》全文,至少没有看仔细。怎么对“王融”、“张融”,标题上两个“融”字都视而不见,致使大学问家犯了低级错误?《诗品》称名、称字确实存在混乱,但王元长没有错,纪昀说错了,纪昀的错误因古直驳正而变得为人关注。
钟嵘大致的体例是:标题中称名,在序或品语中称字或称名,称字可使评的口吻显得更加亲切,语调和缓,古人称谓法如此,《诗品》亦如此。如对王融、刘绘等大多数诗人皆是,混乱来自例外。譬如,《下品·宋记室何长瑜、羊曜璠》条中的“羊曜璠”(羊曜璠名羊璿之,字曜璠)、《下品·晋东阳太守殷仲文》条中的“殷仲文”、“《下品·晋参军毛伯成》中的“毛伯成”(毛伯成名毛玄,字伯成)、《下品·齐高帝》等人条中的“齐太尉王文宪”(王文宪名王俭,字仲宝,谥文宪),共四人。
四人中,三人称字,一人称谥号。为何?我的理解是,四人情况并不一致。其中殷仲文、王文宪比较好解释。
殷仲文以字行;字仲文,故当时或后世皆称殷仲文,如《晋书》本传、《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续晋阳秋》等。《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南齐书·文学传论》说:“仲文玄气,犹不尽除。”《隋书·经籍志》谓有“晋东阳太守殷仲文集七卷”。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才不减班固。”是皆称殷仲文。《诗品》称法相同,当无疑义。
王俭不称名,不称字,而称谥号王文宪,乃是私尊。王俭是钟嵘的老师和恩人。《南史·钟嵘传》说:永明中,钟嵘为国子生时,“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梁书》还说王俭曾荐举钟嵘为“本州秀才”,对钟嵘特别关爱,钟嵘由是感激,故《诗品》中称“文宪”,不直呼其名,品语中亦称“王师文宪”,见其私尊,这也好理解。难解释的是羊曜璠和毛伯成:
毛伯成无缘无故,又不属私尊。我怀疑毛伯成也以字行。《世说新语·言语》篇说“毛伯成自负才气”,《隋书·经籍志》谓有“晋毛伯成一卷,毛伯成诗一卷”,唯《世说新语》注引《征西寮属名》曰:“毛玄,字伯成,颍川人。”钟嵘未见《征西寮属名》?或是从俗称毛伯成?难以断定。
羊曜璠最大的可能是原标题脱漏,后人增补致误。因为通行本《诗品·宋记室何长瑜、羊曜璠》条:“才难,信矣!以康乐与羊、何若此,而二人文辞,殆不足奇”原脱,与“宋詹事范晔”合为一条。今据明刻《吟窗杂录》本补入。明刻《吟窗杂录》本因有大量删节而颇为复杂。会不会整条原文脱漏的同时,羊曜璠的标题也脱漏了?后人因品语中有“以康乐与羊、何若此,而二人文辞,殆不足奇”句,而在标题上增“羊曜璠”三字?
值得怀疑的地方还有,“羊曜璠”名字前脱去职衔称谓。羊曜璠曾任“临川内史”,按《诗品》体例应称之为“宋临川内史羊曜璠”,一如同条何长瑜称“宋记室何长瑜”一样,现标题称谓脱漏未加。又,品语称“羊、何”,羊曜璠在前,何长瑜在后,但标题却是何长瑜在前,羊曜璠在后,是不是脱漏增补留下的痕迹?
(二)职衔称法的混乱。譬如陆机:《上品·晋平原相陆机》条称陆机“平原相”。张锡瑜《钟记室诗平》改“平原相”为“平原内史”。校云:“《晋书·职官志》:‘王国改太守为内史省相’。《地理志》有平原国。则此云‘相’,非也。本传及《隋志》并称‘平原内史’。”《上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称谢灵运为“临川太守”,亦颇有争议。张锡瑜《钟记室诗平》改条中“临川太守”为“临川内史”云:“内史,原作太守。《宋书》本传及《隋志》并云‘临川内史’。考《宋书·州郡志》,作内史是也,今据改。”
张氏改得对不对?今人郑骞《钟嵘诗品·谢灵运条订误》说:“太守与内史,名义不同,实际则一样,这是晋宋时的官制。《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云:郡皆置太守,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亦云:宋用晋制,王国太守称内史。宋时临川郡是王国,撰《世说新语》的刘义庆即是临川王,所以《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江州诸郡长官皆称太守,只有临川称内史。谢灵运的官衔当然是临川内史,《诗品》太守之称,实与当时官制不合。”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说:“郑说是也。当据《宋书》作‘临川内史’为正。”理论上虽然如此,但州郡长官,称名屡变,历代又有反复,故世多混用,实际称法并不那么严格。如谢灵运,《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称“内史”;刘敬叔《异苑》称“太守”,《文选》注引《宋书》亦称“临川(太)守”。
相同的例子还有《中品·晋清河太守陆云》条。《晋书》陆云本传称“清河内史”,《隋书·经籍志》称“清河太守”;《诗品》通行本称“清河守”,《吟窗杂录》一系称“清河太守”。《诗品》标题习称“太守”,也许当时流传两种称法,称“太守”是其中的一种选择。正如当时对王粲、刘桢、潘岳、陆机的评价,江淹说“家有曲直”、“人立矫抗”,而钟嵘选择了刘桢和陆机一样。
唯《下品·晋中书张载》等人条标题“晋司隶傅玄、晋太傅傅咸”,张锡瑜《钟记室诗平》作“晋太傅傅玄、晋司隶傅咸”,傅玄、傅咸前官职颠倒。张校云:“《晋书·傅咸传》:咸以议郎兼司隶校尉而卒,初无为太傅之事,唯咸父玄乃尝拜太傅而后转司隶校尉。仲伟盖以玄、咸父子同官,嫌无识别,故以太傅称玄,司隶称咸。而为后人所乱。”至于错误的原因,张锡瑜以为品语称“长虞(傅咸字)父子”,乃以卑统尊(以子统父),疑此本原作“晋司隶傅咸、晋太傅傅玄”,与品语相合,“后人觉其不顺,又不深考玄、咸历官之详,但互易其名而致此误耳。”今疑不能明也。
《诗品》职衔称法的混乱,也许与钟嵘品诗不喜拘泥的观念有关。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说:
至于诸人历职,多是随便而称,不尽举其所终之官,难以例定
。就其无例之中,细加捡核,略以显近。为重历者,必称显近;若
同则举其最。未据要路,乃称外官;未登王朝,始称府佐。
可见,《诗品》中称谓的标准一是称其显近之职,举其官职之最,这是古之作者遵循的惯例;二是从俗,从实际出发,有时为服从具体的品评内容而改变称谓。譬如《中品·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条:秦嘉最显也最通行的官职是“黄门郎”,《诗品》当称“汉黄门郎秦嘉”才是。《隋书·经籍志》正称“后汉黄门郎秦嘉”。但因与徐淑同条,夫妇同品,品语内容又与夫妇赠答有关。秦嘉后虽任“黄门郎”,但赠答时任“上计掾”,《诗品》遂称之为“汉上计”,而不计其职衔之大小远近。
再是,《下品·齐黄门谢超宗》等人条中亦颇有趣。丘灵鞠曾迁尚书左丞,历通直常侍、正员常侍、车骑长史,终于太中大夫,有很多显赫的官衔,但《诗品》却称其“浔阳太守”,不称其显要之职。是否钟嵘以为丘灵鞠重要的创作在“浔阳太守”时期?但假如是这样的话,谢朓任“宣城太守”时诗歌创作最为辉煌,《诗品》称谢朓“吏部”,不称“谢宣城”,是不是钟嵘和谢有私交,平时就这么称,是遵循他们平时的习惯称法?又,《南齐书·文学本传》称丘灵鞠为“浔阳相”,均未详何义。《诗品》一书,其称谓时有与众不同处,大抵如此。
(三)诗人职衔称谓的缺漏。诗人职衔称谓的缺漏,《诗品》中亦有数例。一是“下品”的“羊曜璠”;二是“中品”的“宋谢世基”。羊曜璠职衔称谓,当为脱漏,前文已有假说。当补为“宋临川内史羊曜璠”。张锡瑜之后,韩国学者车柱环、李徽教亦有论述;但恨无版本根据耳。谢世基名前也仅有一个“宋”字,没有任何职衔称谓。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说:“谢世基上亦当有称谓,传写脱去耳。”韩国李徽教《诗品汇注》说:“‘宋’字下,脱其官名数字。”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疑“世基‘横海’,顾迈‘鸿飞’”下“本有品语,与上文一律。今本盖误脱也。”但杨祖聿《诗品校注》谓:“《宋书》亦未言世基官位,或非误脱。”我赞成误脱说,但证明还有待于将来。
三、《诗品》中的误文
《诗品》中的误文可分三类:
(一)诗人名前时代的错误。《诗品》中,冠诸诗人名前的时代多有错误。如:《中品·宋仆射谢混》条中的“宋仆射”当作“晋仆射”;《下品·晋侍中缪袭》条中的“晋侍中”当作“魏侍中”;《下品·齐高帝》等人条中的“齐征北将军张永”当作“宋征北将军张永”;《下品·齐参军毛伯成》等人条中的“齐参军”当作“晋参军”;同条中,吴迈远的“齐朝请”当作“宋朝请”;《下品·梁秀才陆厥》条中的“梁秀才”当作“齐秀才”等等。这些错误都很明显,因此也不难证明:
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为谢安之孙,谢灵运族兄,历任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因与刘毅关系密切,于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为刘裕所杀,未能入宋。刘裕受禅,谢晦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 《隋书·经籍志》谓有“晋左仆射谢混集三卷”。故当称“晋仆射”,不得称“宋仆射”。缪袭,字熙伯,历事魏四世,累迁至侍中光禄勋;卒于魏正始六年(公元245),未及晋。 事见《三国志·魏书·刘劭传》附。《隋书·经籍志》谓有“魏散骑常侍缪袭集五卷”。故当称“魏侍中”,不得称“晋侍中”。张永,字景云,宋明帝时,为金紫光禄大夫,后都督南、徐、青、冀、益五州诸军事,任征北将军。卒于宋元徽三年(公元475),未及齐世,故当称“宋征北将军”, 不得称“齐征北将军”。毛伯成,名毛玄,字伯成,《世说新语》注引《征西寮属名》谓毛伯成任东晋征西参军;《隋书·经籍志》谓有“晋毛伯成集一卷,毛伯成诗一卷”。可知毛伯成为东晋人,故当称“晋参军”,不得称“齐参军”(错两个时代)。吴迈远,字与籍贯不详,曾任宋奉朝请、江州从事。因参与桂阳王刘休范谋反,兵败,宋元徽二年(公元474 年)被杀,未及齐世。《隋书·经籍志》谓有“宋江州从事吴迈远集一卷”。故当称“宋朝请”,不得称“齐朝请”。陆厥,字韩卿,齐永明九年(公元491)举秀才。因父陆闲被诛,陆厥被系在狱,后遇赦, 感痛而卒于齐永元元年(公元499),未及梁世。 《隋书·经籍志》谓有“齐后军法曹参军陆厥集八卷。”故当称“齐秀才”,不得称“梁秀才”。
这些都是明显的错误。此外,还有不明显或处于两可之间的有:《上品·晋步兵阮籍》条中的“晋步兵”;《中品·晋中散嵇康》条中的“晋中散”;《下品·魏仓曹属阮瑀》等人条中的“魏仓曹属”;《下品·齐惠休上人》等人条的“齐惠休上人”和“齐道猷上人”;《下品·齐鲍令晖》等人条中的“齐鲍令晖”等等。
阮籍、嵇康的卒年相同;均卒于魏景元四年(公元263), 不及晋世,阮籍的步兵尉又属王官,理论上不当称“晋步兵”,而应该称“魏步兵”。嵇康的情况更荒谬,嵇康因为不肯依附司马氏被杀,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说:“冠以‘晋’字,不唯失其实,且乖其意矣。”《隋书·经籍志》称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可证。但《晋书》又为阮籍、嵇康立传。其时虽属魏,而大权已旁落司马氏手中,阮籍、嵇康均与司马氏周旋,或苟存,或被杀,故习惯上把他们划入晋代。同样的情况有阮籍的父亲阮瑀。阮瑀曾任司空曹操的仓曹掾属,为“建安七子”之一,其所任亦为府佐,并非国官。卒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未及魏世。 《隋书·经籍志》称有“后汉丞相曹属阮瑀集”亦可证。但出于同样的习惯,《诗品》仍称他“魏仓曹属”。
惠休、道猷生卒年均不详。惠休本姓汤,字茂远,法名惠休。曾入沙门,宋孝武帝刘骏命使还俗;官至扬州从事。《隋书·经籍志》谓有“宋宛朐令汤惠休集三卷”。张锡瑜、古直均引《宋书·徐湛之传》:“时有沙门释惠休”语,以为当称“宋惠休上人”;但韩国李徽教以为此时距齐受宋禅“不过三十二年”,惠休若与徐湛之同年,活到齐时,也只有七十四岁,“古氏安得断云惠休不能活至七十四岁耶”?“总之,存疑可也”。道猷姓冯,改姓帛,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入沙门后,居若耶山,为吴人生公弟子。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许印芳《诗法萃编》本均校改为“晋道猷上人”,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引《高僧传》谓“宜正曰‘宋道猷上人’。”然各本均作“齐惠休上人”,故可进一步研究。
鲍令晖为鲍照妹,生卒年不详,当称宋,未知是否人齐,亦难遽断。这些都给继续研究留下了空白。
(二)诗人名的错误。《诗品》中还有一些诗人名的错误。如《诗品·序》:“子卿双凫”中的“子卿”;《诗品·序》:“谢客山泉”中的“谢客”;《上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中的“旬日而谢玄亡”中的“谢玄”;《下品·晋中书张载》等人条中的“孝冲”等等。
因为元、明、清各本均是如此,没有异文,故纠正这些错误,意见颇为歧纷。
按照《诗品》的逻辑和品评范围,作“子卿”是明显的错误。这里的“子卿”(苏武)当作“少卿”(李陵)。梁任公以为也许别指六朝的“子卿”,叶长青《诗品集释》反驳说:“梁任公谓:‘乃六朝另一子卿,非汉之子卿。’然《哀江南赋》:‘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六朝另有一苏子卿,六朝另有一李陵乎?《古文苑》载《苏武别李陵诗》云:‘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即本李陵《赠别诗》‘尔行西南游,我独东北翔’及‘双凫相背飞’诸句。”杜天縻注:“《诗品》不列苏武,此云子卿,恐非苏武字也。”日本中沢希男《诗品考》说:“《诗品》不列苏武,然此‘子卿’可疑。恐子卿为少卿(李陵)之讹。《古文苑》卷四载苏武《别李陵诗》一首,中有‘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之句。‘子卿双凫’指此。《古文苑》此诗题为‘苏武’之作,而《初学记》十八引则题为《李陵赠苏武诗》(《初学记》‘双凫’作‘二凫’)。庾信《哀江南赋》曰:‘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此即六朝人以‘双凫’诗为李陵作的一个证据。原文为‘少卿双凫’,‘子卿双凫’当为后人妄改。”日本立命馆大学《诗品》研究班《钟氏诗品疏》云:“或如中沢氏之所言,‘子卿双凫’为后人妄改。然而,若联系此诗‘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句的史实来看,则也许把子卿的苏武设想为作者是合理的。”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云:“《诗品》三品中皆未列子卿。……考‘双凫诗’乃李陵赠苏武之作。《初学记》十八引李陵《赠苏武诗》曰:‘二凫’(《古文苑》作‘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窃疑‘子’、‘我’二字错误,《古文苑》遂列入苏武别李陵之作矣。……幸《初学记》引此为李陵《赠苏武》诗,此文‘子卿’为‘少卿’之误,可得而正。又金王朋寿《类林杂说》七云:‘陵赠武五言诗十六首,其词曰:“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我独留斯馆,子今还故乡。一别秦与胡,会见谁何殃。幸子当努力,言笑莫相忘。”出《临川王集》中。……《初学记》、《古文苑》‘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二句‘我’、‘子’二字之错误,《类林杂说》所引,正可以证其误。则此诗为少卿赠子卿之作,可成定论。而《诗品》此文‘子卿’为‘少卿’之误,亦决无可疑矣。”诸说可参。
“谢客山泉”中的“谢客”,亦颇令人费解。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云:“上文已举灵运之《邺中诗》,则此不得复举其诗,上下文皆单举一人。此谢各疑本作‘谢朓’。谢朓《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诗甚佳,且其中有‘山泉谐所好’之句,《直中书省》诗尤佳,末有‘聊恣山泉赏’之句,可为本作‘谢朓山泉’之证。此作谢客,盖后人仅知谢客长于山水诗而臆改。‘泉’与‘宴’、‘边’为韵,则《诗品》本不作‘山水’明矣。”日本立命馆大学《诗品》研究班《钟氏诗品疏》云:“‘谢客山泉’,当指谢灵运所作众多的山水诗。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亦有《谢临川灵运·游山》的模拟之作。然谢灵运已见于上文的‘灵运邺中’,此重出,故车柱环氏疑‘本作谢朓’。云其诗有‘聊恣山泉赏’之句,故可从之。然此处列举,似皆限于建安以后及宋代诗人之作,中间插入齐代诗人谢朓恐为不妥。而同一诗人重出亦不妥,故‘谢客’或为谢庄之误。‘客’、‘庄’二字,草体相似,可知有讹误可能。”日本清水凯夫教授《诗品研究方法之探讨与五言警策等问题的探究》云:“既然在同组诗人(《中品·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条)中,评价明显居于下位的王微亦被列入‘五言之警策’,而与谢混齐名,在同组诗人中评价最高的谢瞻,则当然更应该列入‘五言之警策’。而且从越石——景纯——王微——谢客——叔源——鲍照的排列顺序及与‘王微风月’对仗方面来看,把谢瞻排列在‘谢客’之处,可以说各方面都最合适。”“谢瞻是谢灵运的从兄,特别赏爱年轻的谢灵运的诗才,倾慕他的诗风。很可能受灵运诗的影响,创作过不少像灵运山水诗那样描写自然的诗。”
由此可知,“谢客山泉”中的“谢客”有四说:谢灵运、谢朓、谢庄、谢瞻,未知孰是。
同在《上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条,有“旬日而谢玄亡”一语。“谢玄亡”,显误。张锡瑜《钟记室诗平》说:“本传云:祖玄,晋车骑将军。父瑍,生而不慧。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哪得生灵运?’考灵运见诛,在宋文帝元嘉十年,年四十九。逆数之,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晋书·谢玄传》:玄以太元十三年卒。则玄之卒,灵运生四岁矣!‘旬日玄亡’之语,近出无稽。则唯灵运生已四岁,渐有知识,玄何由发此语?此盖《异苑》妄谈,仲伟不察而误笔之耳。”
“旬日亡者”非谢玄,则为何人?近有二说:一说为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仲伟殆误其父瑍为祖玄欤!”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说:“‘玄’,应作‘瑍’。”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说:“以常情而论,祖死,不可谓‘子孙难得’。疑本作瑍,由瑍、玄音近,又由联想而误。”日本高松亨明《诗品详解》亦从谢瑍说。二为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据《通鉴》的记载,谢安卒于太元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恰好与钟嵘的说法相合,可证钟嵘记错了人。”郑骞、杨祖聿、清水凯夫、杨勇、吕德申诸氏均从“谢安说”。按,《晋书·谢玄传》云:“子瑍嗣,秘书郎,早卒。”谢玄卒,谢瑍始能嗣而袭封康乐县公,任秘书郎。谢玄卒时,灵运已四岁,可证。“旬日亡”者亦非谢瑍。“玄”当为“安”之形误。
此外,《下品·晋中书张载》等人条:“孝冲虽曰后进,见重安仁。”其中“孝冲”当为“孝若”。孝若“见重安仁”,事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遂作《家风诗》。”夏侯湛字“孝若”,“孝冲”乃夏侯湛弟夏侯淳字。
纠正这类错误不难,但是钟嵘记错了人?还是后世版本错误?没有新材料则很难判断。
(三)品语中的误文。除标题时代,诗人姓名误讹外,品语中也有一些令人头疼的疑难杂症。如:《下品·晋中书张载》等人条“唯以造哀尔”中的“造哀”。“唯以造哀”,语出《诗经·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告”、“造”不同,语义有别。张锡瑜《钟记室诗平》以为:“此致不满之词,当是以其劣,故殿之。”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谓缪袭《挽歌》诗“哀凉独造”,则“造哀”并非贬词。日本高木正一氏释“唯以造哀”为“仅有悲伤的词句,缺少深婉的感情,故虽有哀词,也只能给予较低的评价。”〔1〕意同张锡瑜。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以为:“‘造哀’实为‘告哀’之误。”“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诗之作矣,情以告哀’,亦作‘告哀’。”缪袭《挽歌》诗云:“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朝发高堂上,暮宿黄泉下。白日入虞渊,悬车息驷马;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坠;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此嗟人生袂忽,离乱哀伤,正与作歌告哀意合。故何义门《读书记》说:“缪熙伯《挽歌》诗,词极峭促,亦淡以生悲。”观此条同评五人,各有胜擅,张载虽不及其弟张协,但“近超两傅”;玄、咸父子“繁富可嘉”;夏侯湛见赏于潘岳;均无贬词,知此亦不当贬缪袭。《诗品》“造”字凡六见,唯此“造哀”不词。“告哀”为六朝习见语,故“造”当为“告”之形误。
再如,《下品·宋詹事范晔》条“亦为鲜举矣”中的“鲜举”。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以为:“‘鲜举’当为‘轩举’,形近而讹也。《世说新语·容世篇》曰:‘林公道王长史曰:“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曹植《与杨德祖书》:‘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日本中沢希男《诗品考》说:“此句不顺,恐‘鲜举’二字有误。古直《笺》以为‘鲜举’为‘轩举’之讹。然毋宁说误在‘举’字。‘举’或为‘华’之讹。‘鲜’字则似与《中品·袁宏》条‘鲜明紧健’中‘鲜’字意同。”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谓:“古说疑是。‘轩举’为复语,轩亦举也,故又可分用。颜延之《咏白常侍诗》有云:‘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即其比。”
《诗品》中的文字错误还有很多,弄不清即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如:《上品·古诗》条“陆机所拟十二首”(原作十四首);《上品·阮籍》条“无雕虫之巧”(原作“无雕虫之功”);《中品·张华》条“置之甲科疑弱,抑之中品恨少”)(原文作“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下品·齐鲍令晖》等人条“齐武以为韩公”(原作“齐武谓韩云”);“唯《百韵》淫杂矣”(原作“唯百愿淫矣”)等等。但这是属于通行本的错误,是通行本在流传抄写过程产生的,今有不同版本、类书或宋诗话可以校勘证明,与前所谓“误文”不同。
这些文字上的“疑难杂证”是怎么产生的?是钟嵘理解错误?知识性错误?笔误?属《诗品》本身?还是有其它原因?目前弄不清楚。按理说,钟嵘与其中大多数诗人生活的时代很近,有的还是同代,相互之间有交往,对诗人的时代、姓名、职衔、字号不应该出错。
现在问题是,除张锡瑜、古直、许文雨、吕德申外,不少注家对《诗品》中的“误文”并未重视,有的没有核对版本,以为是通行本的错误;对于误文,有的不注,有的照错的底本注;即如张、古、许、吕,也有部分误文未注,这些任务,都留给了后人。
四、未品诗人研究
钟嵘《诗品》品评自汉迄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什么人该品,什么人不品?什么人置上品?什么人置中品?什么人入下品?可谓殚精竭虑,凝聚了一生的心血。
品总有品的原因,从什么诗人置于何品,可以研究《诗品》的诗歌美学和批评标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循此途。但是,不品的也有不品的道理,如果从未品诗人入手,同样可以研究钟嵘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譬如,只写四言的不品;五言写得不好的不品,成就小的不品。清人许印芳对此不理解,《诗法萃编》有颇多质疑。《上品·汉婕妤班姬》条下说:“两汉能诗妇人,可考者十余人,何仅收班姬及徐淑耶!”《上品·魏侍中王粲》条下说:“仲宣同时诗人,尚有陈孔璋琳,名在七子中,何以遗之?”此外,许氏提出质疑的还有魏代的甄后;晋代的束哲、慧远;宋代的谢道韫等人。末了又作解释说:“汉京作者,既多遗漏;魏、晋、宋、齐,亦未赅括。于魏不录陈琳,为其《饮马长城窟》工乐府也;于晋不录束哲,为其《补亡诗》工四言也。录晋之帛道猷,而不录同时之慧远;录宋之鲍令晖,而不录魏之甄后、晋之谢道韫,殆未见三人五言尔。”
尽管许氏说《诗品》不评乐府诗,说法大谬;所举遗漏的例子也不能说明问题,如西汉诗人,《诗品》只录李陵、班婕妤两家,未录枚乘、苏武,其实只是当时通行的看法,因为作者和作品真伪,都有弄不清的地方,江淹《杂体诗》拟汉诗,也只拟李陵、班婕妤两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世”。但许氏的这番言论,还是启发了对未品诗人的研究,因为确有今天看来是重要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诗品》未予置评的,譬如:《陌上桑》等一些汉乐府五言诗未品;《孔雀东南飞》未品;卓文君的《白头吟》未品;蔡琰的《悲愤诗》未品。为什么评无名氏的《古诗》,不评同为无名氏的《陌上桑》、《相逢狭路间》、《双白鹄》、《艳歌行》和《陇西行》?评班婕妤的《怨歌行》,不评卓文君的《白头吟》?强调作品的怨深文绮,不评《孔雀东南飞》;重视女子的情绪天地,不评蔡琰的《悲愤诗》?这些问题在《诗品》的文本中并不存在,但是,假如深入探讨,这些由历史带来的疑难却存在于我们的研究视野,因而不能不对此作出解释。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徐陵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作者为“无名人”。徐陵没有说明此诗从何处采得。假如此诗在当时并未流传,徐陵直接采自民间,来于里巷,钟嵘没有见过此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又此诗作年尚有争议,假如产生于钟嵘写《诗品》到徐陵编《玉台新咏》的半个世纪内,钟嵘也同样未及一睹。但假如钟嵘看到这首诗,会不会品评?我以为不会。
与《古诗》同时,无名氏的《陌上桑》、辛延年的《羽林郎》,钟嵘是应该看到的。《上品·古诗》条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首”,可见,钟嵘当时看到的这类诗比我们多得多。还有,蔡琰的《悲愤诗》著录于范晔的《后汉书》。《诗品》说范晔诗“不称其才”,可见钟嵘注意到范晔在写《后汉书》时表现出的文学才能,当然也会看到蔡琰的《悲愤诗》,看到那些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场面。诸如:“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这种正面的血淋淋的描写,把悲愤撕碎了给人看:先被董卓乱军所虏,一路受尽凌辱折磨;入番后被迫嫁给胡人,内心痛苦自不必说,已经在番地生儿育女,意想不到的回汉,又使她必须舍弃亲生儿女。儿女渐渐长大,听说母亲离开他们,一去不返。有些似懂非懂——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
常仁侧,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
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这种生离死别,欲行不行的悲痛场面,撕肝裂肺,令人心折骨惊,其情景比江淹的《别赋》更真实、更强烈,也更难忘、更具感染力。而回汉后,自己还将面临改嫁,托命新人的不幸。种种凄凉,种种悲怆,其反映社会历史的深广度,表现个人内心痛若的烈度,比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今天的眼光看,实为建安时代的杰作。钟嵘推尊曹植,将“陈思赠弟”列为五言警策的首篇,但却不提蔡琰的《悲愤诗》。这与未品汉乐府五言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是一致的。妄加推测,也许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诗品》评五言诗,更是评五言诗人。学班固“论人”,刘韶“裁士”,均以诗人为骨架,没有诗人,组不成三品。汉乐府五言诗年代久远,多已不知作者,有的虽标作者,却真伪不辨,难以品评。《白头吟》之类也许就是例子。故许印芳以为《诗品》只评五言诗而不评乐府诗。《诗法萃编》本谓“(钟嵘)自序所录止于五言,而无一语及于乐府。意谓汉人论文,诗、乐分体(自注:如刘子政是也),五言古诗,不宜阑入乐府。”此说虽不确,《诗品》品评,包括许多警策佳篇都属乐府诗。如《诗品·序》列举鲍照的“日中市朝满”、虞炎的“黄鸟度青枝”、刘琨的《扶风歌》(“越石感乱”)、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鲍照戍边”);上品曹植的“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楼”;班婕妤的《怨歌行》(“《团扇》短章”);下品魏侍中缪袭的《挽歌》等等皆是〔2〕。评汉诗不可能不评及汉乐府。 但《诗品》一般不评无名氏的作品,当是撰例。唯《古诗》影响深远〔3〕, 列入上品,是一个例外。
第二,钟嵘的诗学理想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这些汉乐府古辞多来自民间,以当时的审美眼光,不免格调卑俗,少渊雅之致,若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古诗来衡量,则大异其趣。如《陌上桑》中对罗敷美丽的描写: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
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这段文字,尽管我们今天觉得它夸张诙谐,生动有趣,以赋铺陈的手法,从不同人对罗敷的观看,表现罗敷惊人的美丽。但以当时的审美标准,却类近俳优,淫杂不文,不过逗人笑笑而已。刘勰《文心雕龙》斥此类诗为“淫辞”,可见这并不是个别评论家的意见。而钟嵘不评汉乐府古辞,用的仍是“雅”、“怨”两把标尺。
第三,《诗品》基本上不品叙事诗。尽管,钟嵘认为五言诗的特点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写景、状物、抒情之外,也包涵叙事的成分。但从“吟咏情性”诗歌本质论出发,在潜意识里,仍把诗与抒情诗划上等号,以为只有写景状物的才是诗歌。反观《孔雀东南飞》也好,蔡琰的《悲愤诗》也好,尽管抒情意味很浓,但在本质上都是叙事诗。叙事诗当时只在民间流传,见诵闾里,格调卑俗,不在钟嵘的批评范围之内。凡受民歌影响,带有叙事成分的诗人,大多遭到钟嵘的批评。如批评鲍照“险俗”、“颇伤清雅之调”;批评沈约“淫杂”、“见重闾里,诵咏成音”;批驳时人诬蔑陶渊明诗为“田家语”等等;《诗品·序》自谦自己的作品是“农歌辕议”,只能“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均与此相表里。
真伪难以确定;“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学理想;不品叙事诗,也许是《诗品》未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卓文君《白头吟》和蔡琰《悲愤诗》的原因。
如果这些分析成立,则反映了钟嵘重雅,轻俗;重抒情,轻叙事的美学思想。由此可见齐梁时代和我们在诗体和诗歌审美上的差异。
以上系《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的研究。
把疑难问题集中起来引起读者的重视,比单纯研究某个枝节有好处。本文即最大程度地收集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诗品》所存疑难问题归为几类,作出自己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证据还不足,有的只是笔者的假说,有的疑难一时无法解决,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掘,仍可为今后的《诗品》研究提供方向和线索。
注释:
〔1〕高木正一注云:“若‘造哀’作‘告哀’,意亦可通。 只是贬词成为褒词,评价正好相反,拙文暂不采用褒词说。”见《钟嵘的文学观》,文载《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3辑,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笔者译。
〔2〕参考拙文《诗品撰例考之二:嵘今所录,止乎五言》。
〔3〕《古诗》佳丽,人所共识。故魏晋以来,多有拟作。 陆机所拟十二首,为萧统《文选》所录。又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亦称《古诗》为“五言之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