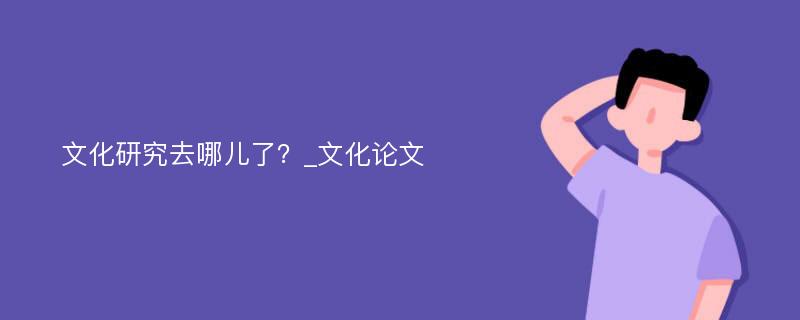
文化研究何处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何处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5)01-0035-03 文化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由精英主义到民粹主义,由欧洲到美洲,影响亚洲和澳洲,20世纪见证了文化研究的兴起、发展、纷争和分歧。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去学科性,一方面给文化研究带来了生命力,但也正是这一特点让文化研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变得过于空泛。精英民粹之争,文学文化之争,再加上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碎片、拼贴、晦涩、多元特征更是把文化研究领进了无孔不入甚至走火入魔的状态。这种混乱和嘈杂使得文化研究逐渐偏离初衷,招来质疑和批判。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批略显狂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讲话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1]甚至有学者认为近三十年来出现在文学系的所有不良表现都打上了文化研究的烙印[2]。当然,对文化研究的批判有学派和学术立场的纷争,不过,文化研究内容的无所不包和标准的支离破碎更使得文化研究大而无当,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无从把握,深感失望。“文化研究正在走向衰落,表现为社会关注度严重下降,刚起步的中国文化研究也陷入了这个怪圈。这与重理论,轻实践的学术传统,权术非学术的研究心态,过于精明的研究方法及特殊的文化语境有关。”[3]175文化和文化现象无处不在,意识形态如影随形,文化研究本可以大有作为,将众多的研究对象纳入到研究视野中,遵循一定的批判原则和研究标准,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作为实践话语,干预、参与和建构我们的生活世界。那么,文化研究究竟要如何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才能重拾生机与活力呢? 一、文化研究应有的话语特点 文化研究话语应该属于公共话语。“文化研究不要有技术学术行话,相反,要发展一种更为宽泛和公共的地方语言。文化研究寻求路径来保留其理论性的同时还要开创公共话语。”[4]227-228在欧洲,文化研究更好地融入了平庸和高雅的文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对待文化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差异很大,但是二者都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带来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从上到下麻痹和操控大众;伯明翰学派确定了与文化生活的公共进程密切相关的文化研究议程,认为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自下而上,对社会具有批判、质疑和改进作用。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民粹立场,日常生活世界都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既然文化研究基于日常生活世界,那么,文化研究的话语就必须属于公共领域的公共话语,而非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的专门领域专业人士独享的专门话语。尽管德里达、巴特和福柯都不书写公共话语,但他们与法国公众生活的融合在英美是无法匹敌的。欧洲知识分子对流行文化和公共问题的参与成了美国人纷纷仿效的事情,在美国,文化研究领军学者本·阿格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继承了法兰克福和伯明翰两个学派的理论遗产,借助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对公共空间里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话语构建和话语批判,试图唤醒沉迷于景观社会的人们去改造当下的日常生活,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调整社会结构,进而改造社会。他的文化研究以参与到公共话语中的方式帮助人们摆脱以往思维和行动习惯,值得文化研究领域学习和借鉴。欧洲知识分子和美国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领域内较好地将研究话语与公共话语进行整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研究者要学习的基本话语方式。文化研究是一条双向道,不仅要努力理解精英文化政治,还要熟知流行文化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的脉络,在精英和流行之间寻找内在联系,探寻二者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影响和作用,为默多克所指出的“有道德的”公共空间贡献公共话语,回归文化研究本质,提升文化研究质量。知识分子要在流行经验和实践中找到立足点,参与到对当下主要问题的重要讨论中来。参与到围绕着文化批评问题的话语讨论之中,这才是文化研究生命所在。 文化研究话语应该平实清晰。既然文化研究离不开文化,文化又无处不在,那么文化研究者的研究话语就应该去学术化,去行话化,以便更多感兴趣的、聪明的但并不专业的读者能够理解。本·阿格在《话语的衰落》中深刻地批判了理论写作的浮夸和晦涩,术语让读者难以理解,从而曲高和寡,达不到文化研究应有的效果。阿格认为“詹姆逊极度技术性的写作实例(我们都想复制他的这种写作,崇拜他深邃的观点和学术的光辉)对批评性文化研究的主流化确实不是一个好兆头。詹姆逊肯定能够以让成千上万的读者,而非只是百来个读者能理解的方式来写作。对他而言,人们也许注意到像他这样的人难以在英美主要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其作品[4]226。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追踪西方理论,热衷于理论研究,涌现了一批“高、大、上”的研究作品,行文冗长,措辞晦涩,不接地气,让读者一头雾水。这种写作风格与文化研究所倡导的风格背道而驰,效果是南辕北辙,研究者们几乎自我孤立,使得冲出学院派围墙的文化研究又开始了新的自我封闭。我们要建立去学术化的文化研究,用朴实的语言,简洁的文风去书写文化研究观点,这样文化研究方能创造新文化,紧扣日常生活世界和日常话语的文化研究必能推陈出新,因为日常生活世界是文化研究源源不断的研究源泉。 二、文化研究应有的批判性立场 文化研究分为肯定性的文化研究和批判性的文化研究。马尔库塞认为肯定性文化研究是批评的毁灭。文化研究者退化的主要原因是将文化研究学术化和方法化[5]。批判性的文化研究拒绝既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将文化文本与所处的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批判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解构和建构。文化研究的目的是要将貌似去作者化的文本进行还原,从而理清文化现象中隐含的霸权本质或者解放潜力。只有还原文化文本作者,才能分析出文化文本的态度和目的,由此开展针对性的批判,所以,在貌似客观的文化研究领域,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态度和立场。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纯粹关注(pure gaze)只是一种假想和虚构[6]。本·阿格认为文化研究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客观的阿基米德姿态[4]67。文化研究必须是批判的,有破有立,有批判才有建树。 “在网络数字时代,人人都是潜在的贡献者,人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受工业操控的价值链上封闭的专家,由等级到网络的变化迫使分析不得不关注流行的创造力……”[7]在多媒体和自媒体网络时代,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学者、研究人员和公众都可以借助媒体和网络发表各自的见解,表达各自的声音。公众就公共问题进行对话、讨论、质疑和批判,如马航事件、雾霾、反腐、政治丑闻、国际关系、《甄寰传》的功过是非等。与此同时,网络也被用来倡导和传播一些群体想要表达的心愿,如微信中流传的好女人标准——漂亮、能干、贤惠、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等。细心的文化研究者不难发现这样的标准是男性目光注视下的理想女人:必要时,女人要有选择性地兼具男人和女人的所有本领和美德。曾于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电影《小时代》系列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为“《小时代》系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恋物癖。恋物癖者心甘情愿地加入生产大军,以为只要循规蹈矩,就能获得体面细腻的生活。同时又以抵抗的神话消弭不公、不满和怨怼情绪,从而更加用心地投入到生产中去,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平衡”[8]。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刘雪松就以参与和实践的态度对郭美美事件的社会效应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就郭美美现象进行了很好的文化研究。他认为理论上要用正确的三观塑造人,但郭美美们的张狂逍遥的生活方式却能将之搅成一团败絮。郭美美们用扭曲三观挑战着社会倡导的三观……这个社会的法治与道德、宣教与喉舌,都应该有勇气照照镜子,照照自己的责任,审视自己的面孔[9]。诸多类似的例证有力地证明了媒体时代催生了众多的文化研究素材,也为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干预性提供了研究平台。 对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批判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但是这种批判不是漫无目的的谩骂、诋毁或纠缠,而是具有批判与改造的实践意义的话语表述,这种表述本身就应该是实践的,是参与的,是建构的。文化研究关注表述接受和表述生产的转型,表述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贡献。流行文化通过表述复制某种世界观,而“不是毫无批判地消费流行文化,似乎这些作品和实践都是从天而降,落入了超市收银台出口、书店、剧院、报纸和电视,我们要质疑这些文化形式编码了的论点的真正内容”[4]234。曾于里对《小时代》的批判就是对其展示的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对拜物教带给消费者的麻痹和麻醉作品的批判,因而追踪文化作品和实践的作者,还原流行文化的作者意图,质疑流行文化隐秘倡导的内容,揭示编码内容,向广大受众解码商品世界人的物化悲剧。 刘雪松对郭美美现象的剖析揭示了拜金主义对传统三观的扭曲和颠覆,呼吁正本清源,回归正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的文化研究是对扭曲错乱三观的拆卸,建构的是一个有价值标准的实践世界。在文化研究领域,对待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我们不是去将自己孤立于日常生活的政治兴衰之外,远离尘嚣,也不是去剑走偏锋,寻奇猎怪,而是要秉持建构和建树的原则,批判性地进行文化分析,以此方式去修复学术批评、知识批评与实践之间的裂痕,修复发展中的日常生活政治,真正地把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立”起来。这样的文化研究才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 三、文化研究应有的参与态度 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事实上,正如马尔库塞所证明的那样,控制、协调和商品化强制措施触及到了所有的私人空间[10]。正因如此,批判理论的未来就在于它作为文化研究与实践意图的结合[11]。这种结合实际上就是文化研究的参与,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实践性。“文化研究直接参与到流行文化的政治功能中。文化研究帮助转换我们经历文化世界的方式,改变我们阅读、观察、聆听和书写的方式。”[4]227-228文化研究的参与功能是批判性文化分析的悠久传统,始于正统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必须以一种强调自身直接参与实践的方式来观照日常生活世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领域中最为政治化的领域,仅仅只对流行文化的形式和功能进行分析是不够的。格雷厄姆·默多克认为文化是争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斗争场所,文化研究要致力于从精英分子的傲慢中讨回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恢复普通人的生活尊严,以毅力和洞见去拷问生活内容,现在是利用文化研究去处理我们时代最急迫问题的时候了。在文化研究的批判和质疑实践中,默多克倡导建立文化公共空间,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资源共享,自由使用,市场靠边站,没有广告和推销,因为很多的时候推销的并不是商品,而是消费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结局就是商品成了我们的延伸物,成为向别人讲述我们是谁的普通符号[7]。 文化研究的参与和实践方式表现在通过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表述和模仿去瓦解日常生活。如美国科幻电影《后天》(2004)和《极乐空间》(2013)借助现代声、光、电科技和视觉艺术给观众带来极具冲击力的效果,两部电影中展现的灾难场景和满目疮痍的生活场所并非完全科幻,现实中的图景几乎如出一辙。电影通过模拟荒原化的生活世界,展现不堪一击的脆弱的生态局面,昭示生态失衡的灾难后果,以期干预现在人类对地球生态的破坏行为,拯救地球。再如我们观看《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结合时代特点,反思当下问题。电影以一种流行文化的形式参与到思想和实践的建构过程中,瓦解脱离群众,铺张浪费的社会风气,倡导厉行节俭,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文化研究的参与和实践方式还表现在对文化的阐释上。对某种文化形式或现象的阐释不是个人日记,而是公开发表的观点。批判性观点的公开就会带来阅读,阅读就是书写,阐释即是参与,因为表述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各个环节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实践内容。文化研究要参与文化批判和媒体分析,要反思具有我们时代、社会、性别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作品和文化实践。所以,阐释是一种实践,是各种力量和立场结合较量的产物,某些力量从某种立场出发,特定性的阐释性断言就变成了普遍观点。文化研究中有影响力的阐释不仅反映社会世界,而且建构世界,帮助我们还原主体性的立场,从阐释中开拓意义,表述主张,瓦解和建构日常生活世界。如对麦当劳食品的霸权性分析,对广告话语中的性别分析,对商品流通的消费主义探究等都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瓦解和建构。参与和实践性的文化研究认识到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内在性,并试图通过参与和实践,从内部而非从外部去转化日常生活的结构和文本。对于生产和接受的日常生活层面,我们根据社会和经济再生产更为广泛的结构性原则再将之理论化。文化研究领域由此同样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理。 伯明翰文化研究为后来的文化研究梳理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尽管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政治实践还不够彻底,但它却为未来的文化研究如何直接参与文化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有学者提出:“中国当下的文化研究应该在不放弃批评的情况下软化批判,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式批判,在如此批判的过程中又要保持独立的研究立场。”[3]179在当下充满悖论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中国文化研究者们处于一种尴尬境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若即若离,欲说还休,文化研究可有中国式的曲径通幽呢? 2014年年初霍加特和霍尔相继去世,虽然他们奠定的文化研究基础和留下的文化研究遗产在当代文化研究中面临挑战,但他们参与和实践的文化研究却是文化研究应该坚持的原则,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不能偏离这些基本路径。文化研究必须基于日常生活世界,带着批判性态度,朝着参与和实践的方向,方能渐行渐远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