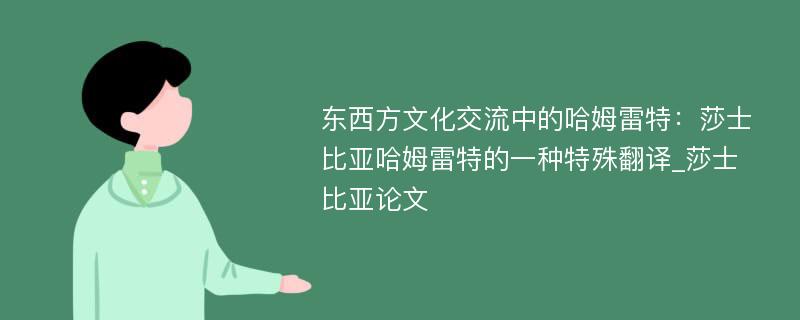
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一个特殊译本《天仇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特论文,莎士比亚论文,哈姆论文,译本论文,东西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最初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都是根据英国散文家查理士·兰姆和他的姐姐玛丽·兰姆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莎氏乐府本事》)以复述的形式翻译过来的。光绪29年(1903),上海达文社首先用文言文翻译出版了名为英国索士比亚著《澥外奇谭》,其中的第十章为《哈姆莱特》,译者翻译为《报大仇韩利德杀叔》。紧接着190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全译本《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其中《哈姆莱特》被译为《鬼沼》。①而第三种用文言文翻译的《哈姆莱特》是商务印书馆在民国13年5月初版(1924)、列为“说部丛书第四集第二十编”的邵挺②译《天仇记》。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在“万有文库”中,出版了邵挺翻译的《天仇记》。③由此,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中,《哈姆莱特》共有三个文言文译本,这“三大文言文译本”是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早期翻译的特殊成果,值得人们特别予以重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早期中国文人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时翻译观的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显然也是翻译史研究中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天仇记》以及其他文言文译本构成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有机链条
林纾翻译外国作品前后,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当时“翻译语言多用古文,甚至是桐城古文”。④但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冲决下,虽然新文学的建设还没有被放到议事日程上,“五四”先贤们已经把眼光投向了外国文学,用大量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国新文学提供借鉴。新文学家们在这种借鉴和接受中对民族传统文学,包括莎士比亚戏剧的文言译本,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这与他们在对待外来文学的态度上显示出的强烈的主体精神、开放气度和宽容心态形成鲜明对照。胡适强调:“萧士比亚和‘伊里沙白时代’的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话’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世界的世界语。”⑤胡适认为:“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⑥他主张:“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林琴南把萧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萧士比亚的大罪人。”⑦陈独秀、胡适认为,用文言文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不但对中国的新文学建设毫无用处,而且是对提倡白话文学的一种反动,对于传播莎士比亚来说,其消极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他们看来,莎士比亚戏剧的文言文译本,全译也好,节译也罢,译述也好,翻译也罢,都是他们一概反对的。只不过林纾等人的主张和译品正好成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靶子,而邵挺在1924年出版文言文的《天仇记》时,新文学运动已近尾声,其译本已经难以引起新文学批评家们的注意了。但是,从新文学家对林纾等人翻译外国小说的批判态度来看,我们不难推测出新文学家对所有以文言文形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对邵挺翻译的《天仇记》的激烈的批判态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对文言文发动了总攻,其中包括对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批判。在这场批判后,以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主导形式,白话文不但取代了文言文在创作领域的地位,而且,白话文也一举取代了文言文在翻译文学领域的地位。但是,即使在这种形式下,我们仍然看到,就是在“五四”运动的十多年后,以文言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莎士比亚作品也没有就此退出文学翻译的历史舞台。这类翻译作品不但受到了当时研习西洋文学的学生的喜爱,而且多年以后,阅读者仍然念念不忘阅读《天仇记》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尽管邵挺“尽力播放传统道地的文体和戏剧形式,不惜歪曲原著的面貌”,⑧但毕竟契合了当时某些语境特点和部分人的阅读习惯。因为“莎氏剧本在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地位应和中国元杂剧和明传奇等量齐观,译本如只是照样译成白话文,便难使沉醉在中国古典文学光芒里的读者和诗人佩服,也降低了《哈姆莱特》自身的崇高文艺地位。”⑨采用《天仇记》而不是用《哈姆莱特》这个译名,“径取《礼记》‘父母之仇,不与共戴天’一句成语作为剧名。这就使得它像中国旧有小说和戏曲同样典雅,很像一本古典作品了。其中文字,译者尽量用古文、旧诗曲词形式翻译,不少地方是有音节的”。⑩不但剧名类似中国古典戏曲、院本的名称,同时在表现戏剧内容的形式上也颇得古典文学作品之妙,甚至在尊重原著内容、形式的基础上,其“归化”的翻译策略也使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在翻译莎剧(诗剧)的过程中的消解减少到最小程度。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就以白话文和完整的剧本形式介绍到中国。田汉1921年在《少年中国》杂志上翻译出版了《哈孟雷特》,一直到30年代,有多种莎士比亚的戏剧被翻译过来,其中既有文言文译本,也有白话译本,但以白话译本为主。这与莎士比亚剧作在世界各国和不同时代都有许多“变体译本”的情况是一致的。这同时也表明莎士比亚戏剧的文言文译本正在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表明旧有的译介观念受到新文学思潮的冲击和消解,新的译介观念至此开始成形并很快成为主导”。(11)到了梁实秋、曹未风、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不断出版的时期,文言文译本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就在出版界绝迹了。
但是,邵挺翻译的《天仇记》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澥外奇谭》和《吟边燕语》中的《哈姆莱特》。前两种译本都是根据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翻译的,所以少了原本的原汁原味,在内容上已经打了不少折扣,在形式上也不是以诗剧的形式来翻译,而是以故事或者是“神怪小说”的形式介绍给国内读者。所以,胡适说:“用古文译小说,也是一样劳而无功的死路,因为能读古文小说的人实在太少了。至于古文不能翻译外国近代文学的复杂文句和细致描写,也是能读外国原书的人都知道的,更不用说了。”(12)同样是用文言文翻译《哈姆莱特》,邵挺翻译的《天仇记》则比前两种翻译前进了一步,虽然仍然采用文言文形式,但是把《哈姆莱特》翻译为剧本,而不是说书性质的“故事”或充满神秘、荒诞、惊险、离奇色彩“神怪小说”,从中我们自然可以看到翻译观的进步。这种情况表明,随着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介绍,人们的认识也不断加深,译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以故事或小说的形式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而需要以更加接近原作的形式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和《哈姆莱特》了。此时,邵挺采用文言文形式翻译的《天仇记》正好应运而生。但是,译者翻译时有意采用旧有的文言文形式,以抗拒五四文学革命之风,在它稍前或稍后出版的白话本莎士比亚戏剧和《哈姆莱特》译本很快取代了它。因此《天仇记》的翻译又成为文言文《哈姆莱特》译本之余绪。
《天仇记》这样的译本出版83年以来,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它,(13)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有兴趣或耐心阅读它,但是《天仇记》的翻译出版却构成了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链条,在研究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的时候是不应该忽视的。例如就有相当多的论者认为,“经历了文言译述莎剧故事梗概”后,接下来就“进入用白话翻译散文译本阶段”,(14)“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直接根据莎剧用白话翻译、保持戏剧形式的散文译本。(15)他们忽视了其中还有用文言文翻译“莎士比亚诗剧”这样一种翻译形式,在已经出版的翻译史、翻译与翻译家词典中,也没有邵挺和《天仇记》辞条,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史特别是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失。显然,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个空白,亟待改变。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用文言文翻译的《天仇记》这样的译本也不是没有读者,阅读这样的译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文言文的语境中了解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的精神,也可谓中西融合,相得益彰,别有一种境界。试想如果在中国有一部全用文言文翻译出来的《莎士比亚全集》,我们对世界文学和莎士比亚的研究所作出的特殊的贡献,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留存到今天,其文化、文学价值自然也是不可估量的。
二、《天仇记》:归化基础上的翻译与评点
1.《天仇记》对《哈姆莱特》原剧本进行了一些删节、合并。由于文言文所特有的涵盖性和信息量,用文言文翻译能够将莎士比亚原文中多词、多句的意思,在一词、一句中表现出来。
2.邵挺的《天仇记》用大量的中国成语、熟语、典故、中国诗歌语言翻译剧文,如凤毛麟角、四面楚歌、险象环生、野老村夫、草莽匹夫、击缶吹笳、杨柳横溪、叶白水镜、泪失荒坟、雨淋漓、雎鸠、窈窕淑女、三军可夺帅也而予志不可夺、埋香葬玉、情真泪雨、碧落、黄泉、蚩蚩者氓、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部史记、衣香鬓影、高悬秦镜、雍容若儒生等等,译文使用四字句泛滥,形成骈文韵味,有“自然的规律和内在节奏”,(16)排偶句,形成整齐的格律形式,体现了用文言文翻译的特点。
3.对人物、剧情分析评论,解释剧中环境,渲染、营造戏剧气氛,帮助读者阅读。例如:开场时两个卫兵在平台上对话时,译者点出:“守卫森严□若细柳营”,(17)“未言鬼。戛然中断。而鬼果见矣。惝恍离奇。凄凉簌悚傈。”“何君既惊奇。鼓勇发问语气故喘促。”当王后劝黑蒙勒时,译者评点:“已不能贞。亦勗子不必孝。”对今王口口声声说痛爱黑蒙勒则说:“口中有蜜。腹里藏刀。”“荒淫之君。但知酒色。”莎士比亚时代用儿童扮演女角,邵挺也加以解释:“索氏时代。英国重童子班戏。女人乃童子所扮装。”(18)“索士比同辈曰William Kemp改隶他帮戏子。与(索)为敌。此段有感而发。非黑太子言也。”当黑蒙勒改了书信则是“当时名人书法皆劣。而佳者皆胥役也。”
4.提醒读者注意,自己也发出感慨,抒发译者感想。例如:对两个卫兵的对话的评点“谈时务,不复说鬼。有虚实相间之妙”。对黑蒙勒评点:“悲哀恻悼之余。能作镇静寻常之语。喜怒忧乐。不形于色。是黑之大过人处。”“仇宜最怨恨。而曰最亲爱。怨恨不能名之意。”“本来何礼初等人告见鬼事。而转由黑蒙勒先告之。行文奇妙。”“黑蒙勒蹇运艰屯。即钟爱一廷臣名媛。尚多磨折可叹。”“黑每有感触。思潮泉。辄发一篇伟论。”对卜诺纳,译者说:“卜诺纳一老奸大滑耳。而又老悖恬言。令人生厌。而戒子一节。转是字字格言。真不可以人废言。”对王后的自语则评曰:“一语道破。良心不昧。”对掘墓人的话则有感而发:“败德者。酒色荒沉。未盖棺而屍已烂。故云。”
5.对自己的翻译方法加以说明。黑蒙勒对鹤飞莱说:“女士。我得居卿裈襠内否。”译者注明“原文得卧君袒服中否”。现代的译文多作“腿上”、“两腿中间”,独邵挺大胆译为“裈襠内”。可见,译者并不一味求“雅”。在第四幕第三景国王和黑蒙勒的对话中,译者注“原文为爱。在华文为敬”。在第五幕第一景中,针对掘墓人的话,译者注:“原文系自戕。系丑夸示渊博。用字转误。兹译其正义。易于索解。”对黑蒙勒的话注:“原文卧与说谎同音。兹以讹译说谎。”“原文无此句。补足其意。”在第一幕第一景何礼初与卫兵的对话中,邵挺告诉读者:“原文无此两句。意味。论者谓有脱漏。故擅补之。以完其义。未知当否。”在译文中征求读者对自己译文的意见,说明补充了两个句子,恐怕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中也是不多见的。
6.对西方风俗、神话、宗教给以解释,使读者不致茫然。例如:点明有些词语是“西方谐语”、“西方古说鬼操拉丁语”、“西俗君父及尊者之名均不讳”、“西妇不言节。每见易思迁。几个有松贞柏操。此语在欧西。故称名言。语文常引用之”、“宗教话”、“欧西婚姻自由。特平民间行之耳。天家儿女婚姻。率皆择定。即今犹然”、“西人言不知两字。即是曰否。特婉言以不触怒耳”、“耶稣之说。开关之夫亚当割肋而成夏娃。故云”。
7.以中国历史事件、中国古典诗词对人物行为、语言进行抨击或赞扬。例如:评点今王:“丹王可比唐太宗。盖太宗元吉而娶其妃。灭理乱伦。正相伯仲……”“即荀子所谓。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郗穴而不偪。”在第三幕第一景黑蒙勒和鹤飞莱对话中,邵挺评曰:“如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第四幕第五景,赖一德提剑冲进屋里,邵挺评曰:“有如陈涉揭竿一呼。响者四应。丹王不获人心可知。”对今王评曰:“俨若王莽所谓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三、形式美的文言魅力能使我们对哈姆莱特形象获得新理解
自莎士比亚创造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形象哈姆莱特以来的几百年,人们对这个人物形象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毋庸讳言的是翻译者的不同,译作的不同,对原作某些关键性的字、词、句或总体认识的差异,是造成人们认识不相同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从邵挺所译《天仇记》的译本中抽出几个关键性的地方,揣摩译者的用心,我们就会对文言文译本《天仇记》那带着镣铐跳舞的优美舞姿有一个新的认识。
身世飘零、命运多舛的哈姆莱特在第一幕第二景中的首次亮相,就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来遭受父死母嫁失掉应得王位打击后的内心世界,并且极力掩饰自己悲哀的心绪。邵挺在翻译的同时,对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的对话以及人物形象进行了评析,并对自己的译文作了说明。黑蒙勒第一次出场,今王和他有一段对话,邵挺译为:
王:“胡为浊云尚医障汝”,黑蒙勒:“否。我主。某光明如太阳。”(19)
黑蒙勒一开口,邵挺就赞美道:“黑极富哲学理想。思虑极灵敏。言多深思奇妙而妥帖。此即一端。案英文太阳与子同音。意本双关。兹仅能译其一。不能译其二。读者谅之。”(20)在这一句中,克劳狄斯主要是在试探哈姆莱特,哈姆莱特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仇恨隐藏起来。邵挺在译文中带给我们的理解是,面色不好,是不是有心事,“浊云”一词使我们体会到“汉语的音象与汉诗词曲本身要求的情韵味之间”的“先天性契合贯通”,(21)何况,莎剧原来就是诗剧,译者采用长于诗歌的文言翻译,形式与形式、形式内容契合,给读者带来了审美的愉悦。而对于黑蒙勒回答我光明正大就像太阳一样,邵挺老实承认,对于双关语只能译出一种意思“太阳”,并请读者原谅。“医”通“翳”,“翳障”即障蔽。《西京杂记》卷四:“茂陵轻薄者化之,皆以杂错厕翳障,以青州芦苇为弩矢……”在此,读者也可悟出,王子是被今王的卑鄙“障蔽”了。
再看克劳狄斯挽着王后在喇叭声中出现在丹麦宫廷上,为了掩盖自己,“先将娶嫂事。掩□一番。大好似信。可惧可怕。”(22)(23)所以,克劳狄斯假惺惺地称哈姆莱特为“侄子”、“儿子”,邵挺提示:“十分亲密。自作多情。”(24)哈姆莱特却自言自语:“亲则有余。仁则不足。”(25)邵挺“谓以姪相称。今吾母嫁汝。吾为半子。(西俗如此)则比姪更亲一层。”“若呼为子。则父子相爱之仁。实属未有。黑憾其母新寡即醮。因并憾其叔。”(26)邵挺用儒家的“仁”来解释“王”的行为,体现了用孔子“仁者爱人”以及孟子的“仁爱”衡量人的行为思想,“不仁者”就是“恶人”,此译文属于早期翻译特有的归化翻译。“情”、“亲人”、“亲情”、“仁慈”、“陌路人”等翻译,都更能使中国读者易于理解,强化了译文的认知功能,但却误导了读者对原作精神的理解。哈姆莱特从心里来说根本不承认这个“亲上加亲”的现实,相反,由于这种残酷的现实,与克劳狄斯离得更远了。大量含有中国古典文化信息的词语被用在《天仇记》的译文中。这样的译本,在莎士比亚译本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在《哈姆莱特》研究中,“生存还是死亡”一句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当多的研究者也对它作出了不同的解释。(27)有的人从这句话中看到了哈姆莱特对充满欺骗、暗杀的封建腐朽社会的绝望;有的人从中看到了哈姆莱特对人和人世的极端厌倦,乐观的人生态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由享受生活的淳酒变成了厌恶人世。(28)这一段邵挺译文为:
[黑蒙勒]噫此躯壳太——太坚“悲愤交集。出辞不相接”不能融化露水也。上帝未尝立法。禁人自戕也。唉、天呼。斯世于予。何其倦惫平淡也。世其无福哉。吁。无福哉。荆天棘地。满目蓬蒿。竟至若斯。“痛其父之死。恨其母之婚。百感萦怀。觉此世之无味。故一切乐观。尽成悲观。然谁可告语者。号泣于旻天而已。” (29)
“汉语言文字它是一种综合性很高的语文……它那个信息量负载量很大。”(30)汉语言文字的诗歌性质,可以淋漓尽致地挥洒在莎氏诗剧译文中,而文言文又把这种信息量、负载量发挥到了极至,邵挺的这段译文在所有译文中是最经济的,从哈姆莱特呼天抢地的呼喊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彻底绝望了。从邵挺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戕”、“自杀”、“自戮”都是一个意思,准确地体现出了哈姆莱特在看透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准备与这个世界同归于尽。邵挺译“倦惫平淡”语气不够强烈,两个“无福哉”的“福”为幸福的意思,对于黑蒙勒来说“无福”就是“没有幸福”。文学语言要充分体现其美学效果,诗歌的语言美在于承载它的言词,尽管是文言文,邵译文不但在审美上达到了一个高度,而且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思。而且,他在译文中的评点也一针见血地点出黑蒙勒由于“悲愤交集”,上句不接下句,面对父死母嫁的现实,已经由一个开朗乐观的王子,变成了一个悲观的厌世者。邵译文的“躯壳太坚”也较好地体现了第一对开本中的这个意思。此外,邵译文在评点中用“旻天”泛指“天”,“帝(舜)出于历山,往于田, 日月号泣于旻天。”(《书·大禹漠》)“尔邀遗多是士,弗韦旻天,大降丧于殷。”(《书·多士》)孔颖达疏:“天有多名,独言旻天者,”又特指秋天,“秋为旻天”。(《尔雅·释天》这是一句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解释,邵挺用中国语言中的特指事物, “悲”秋加深了读者对黑蒙勒呼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局面的理解,真乃别具机杼。
四、译文没有掺入“人文主义者”先入为主的观念
1949年以后的中国哈姆莱特研究由于受到苏联莎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一般都将哈姆莱特的一段所谓赞美人类的话视为他是人文主义者的证据。而且,这种认识根深蒂固,在哈姆莱特研究中有持久的影响,尽管近年受到了相当多的质疑,但直到现在仍然在哈姆莱特研究中占据了很大的地盘。(31)哈姆莱特是不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战士呢?
哈姆莱特颓丧地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32)是继续活下去还是不活了,也成了一个令自己感到极度困惑的问题,邵挺译文为:
黑蒙勒:吾将自戕乎。抑不自戕乎。成一问题矣。脑海烦苦。如矢石交加。将忍忍受之乎。抑将拔剑而起。蹈海而终乎。二者孰为磊落光明。(33)(34)
有人说:“英语——在修饰语的丰富性和排列形式的简洁性方面根本没法跟汉语言文字相比”,(35)浅文言自有其韵味。邵挺译文简洁,修饰味道浓,关键是“自戕”、“不自戕”紧扣了黑蒙勒此时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才有如矢石交加般的烦苦,是拔剑而起呢?还是跳进海里(自杀)呢?哪一样更光明磊落?跳海是躲避耻辱,逃避责任;拔剑而起则是勇敢地挑起了无可回避的重任,相比之下,后者是光明磊落的。邵译简洁、连贯、凝重,审美效果明显、前后照应,“自戕”、“不自戕”较好地传达出黑蒙勒的矛盾心情。据此,我们也可以得出,哈姆莱特是悲观失望的,而绝不能给他戴上一顶人文主义者的大帽子。黑蒙勒宁可避灾而不愿求生,可见他自杀、厌世的情绪已经快要到达顶点,冲破极限了。(36)每当遇到险情恶境的时候,在挫折和困难面前,哈姆莱特毫无例外想到死,透露出他骨子里的懦夫本色,想早点脱身,即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毕竟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哈姆莱特明显地对人生的固有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死亡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种不想摆脱也难以摆脱的诱惑了。历来的研究者将哈姆莱特的这段话视为其为人文主义者的证据,然而,却忽视这段话前后之间的联系。
请看邵挺的译文:
黑蒙勒:夫人何尊。理性何宝。智能何垠。容止何温雅。动作何神明。觉悟何高杳。天地之美也。蜾虫之灵也。然此不可思议之神灵。于我皆尘埃耳。人不能我欢。不能即女人亦不能虽有莞尔。若为其能。(37)
与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林同济、卞之琳、杨烈、方平译本比较,邵译本在翻译这段话时所用文字最少,“天地之美也。蜾虫之灵也”,但“蜾虫”显系译者的用典,即《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毛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蒲卢也。”汉代杨雄《法言·学行》:“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蜾蠃这种绿色的小虫是轻盈的,生命是有灵气的,比较各家的译文,邵挺虽然不自觉地归化了原文,但也比较准确地表达出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意思。联系邵挺的译文,我们就会发现,天地的壮美,蜾虫的性灵都敌不过绝望心境,单取这段话的前面部分,无疑是犯了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任意拼凑的错误。因为,在这段话开始,黑蒙勒可以说是彻底绝望了,他说:“予尔来——然不自知何故。——顿失欢乐。抛弃游戏。甚且大变我性情。”(38)这个世界在他看来“亦无异一团混浊之凝气”,(39)世界和人生在他的眼里顿时都失去了光彩,暗淡了,精彩的世界、曾经眷恋的人生甚至女人,也不能使黑蒙勒发生兴趣了。黑蒙勒已经看不到人生的任何意义了,生命也根本不值得留念了。所以,黑蒙勒说:“(丹麦)是黑狱,”“恰是。世上之监狱多矣(丹麦)其最坏者。”(40)而“我生不辰。脑际紊乱。豈予之生。兹事掌判。‘黑脑筋过敏。一转念。恐鬼非真而生疑惑。行事不断。种种悲剧。即缘之发生。’”(41)黑蒙勒要重整的乾坤,无非是“颠倒、混乱”的局面,是“黑狱”,但“重整”说穿了就是要想尽办法恢复过去的、失去的王位和由于抢班夺权造成的颠倒混乱的秩序,运用的手段是复仇,而根本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具体行动。从邵挺简洁、蕴涵丰富的用典的译文中,我们能够感到一种准确的诗意美、节奏美,同时译文也丝毫没有掺杂“人文主义者”等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莎士比亚塑造哈姆莱特的初衷。
五、《天仇记》对我们的启示
《天仇记》自民国13年5月和民国19年4月作为“说部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到现在已经83年了。虽然《天仇记》缺陷不少,如莎剧味道不浓,译文缺漏,以文以载道思想解释原剧,但它“译文不算草率,谴词方面用了不少心思……利用古文修辞特点……有相当创造力和想象力。”(42)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历经一百多年,其间多种名家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相继出版,而《哈姆莱特》的译本更多,但是,文言文的《天仇记》却是众多莎士比亚中文译本中最特殊的一个译本,它有自己的个性,在译文上有自己的特色,对莎士比亚翻译研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译本,它的意义在于:
1.邵挺翻译的《天仇记》是《哈姆莱特》文言文译本中的最后一个译本,它的出现标志着采用文言文翻译《哈姆莱特》的终结。
2.《天仇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译本,译者在译本中采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评点的方式对《哈姆莱特》中的人物、主题、艺术创作手法、环境、情节、西方文化风俗以及翻译方法、技巧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述、说明,其中蕴涵着译者对《哈姆莱特》及其人物较为简要、清晰、褒贬分明的评价。(43)在这个意义上,《天仇记》是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中不同于其他莎剧译本的一个相当特殊的译本。它既是一个译本,又不完全是一个译本,其特殊之处在于,译者还以一个评论者的身份帮助读者理解,并对《哈姆莱特》一剧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评点和阐释。
3.它又是《哈姆莱特》三大文言文译本中在形式上和译文上最接近原本的译本,它不是译述形式的散文、故事译本,而是真正以戏剧(诗剧)的形式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对它的研究有助于填补翻译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史、中国莎学史研究的空白。
注释:
①戈宝权:《莎士比亚在中国》,载《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34-335页。
②邵挺的身世不详,在所有的翻译类研究论著中几乎没有提到他,即便提到,也只说他以文言文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天仇记》与《罗马大将该撒》。据我所知,作为一个翻译家,邵挺约翻译了11本书,包括:《纽丝伦归程》(出版年代不详,而且标明的是“著”,另外一些译本标明的也是“著”,但显然是邵挺翻译的)、《坎那大中华移民律》(1917)、《嘉士定侵略印度记》(马可尼,1922)、《天仇记》(1924)、《罗马大将该撒》(与许邵珊合译,1925)、《封锁政策》(柏穆著,1927)、《嘉士定》(1930)、《蔡公家训》(英汉对照)(译述,1935)、《中日纠纷与国联》(韦罗贝著,1937)、《南北极探险家勉纯传》(1948)。作为一个翻译家,邵挺译文的数量应该是相当可观了,我们理应在中国翻译史中写上邵挺的名字。
③关于《天仇记》出版的时间,戈宝权先生提到的出版时间是1924年。《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1911-1949)》(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50页上注明:《天仇记》(上、下),莎士比亚著,邵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5月初版,2册(68页,96页),32开(说部丛书第4集第21编)。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仇记》,标明的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初版”,并有1930字样,而且不分上下册,是一卷本,全书共152页。而按上下册页数计算,68页加96页,全书就为164页。出版于1924年的《天仇记》(上、下)较1930年版本字号大(四号字),印刷也比较清晰,由于字号大于1930年版,故上下册页码多出了12页,但经我核对内容完全一样。1924年版《天仇记》封面亦有特色,全书采用红色线条勾勒,封面中间为书名《天仇记》(上、下),右边有一只用红线勾勒的仙鹤单腿站在斜插进来的松树干上并以松针作为点缀,右上部注明“说部”字样,左下为出版者“商务印书馆”。陈汝衡提到的《天仇记》出版时间为1930年,所有的翻译史类书籍也都将《天仇记》初版的时间误为1930年。
④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89页。
⑤⑥⑦(12)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理论建设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132,139,140,4页。
⑧(16)(42)周兆祥:《汉译〈哈姆雷特〉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336-337,225,379-380页。周兆祥认为初版1924年版《天仇记》已不存,见该书19页,实际该版本今天仍存。
⑨⑩陈汝衡:《莎氏悲剧〈哈姆莱特〉及其中译本〈天仇记〉》,载《莎士比亚研究》第4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264,264页。
(11)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3页。
(13)《天仇记》出版以来,仅在出版的最初几年对当时学习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的学生产生了影响。陈汝衡先生在《天仇记》出版64年后的1994年回忆在国立东南大学读书时曾阅读邵挺翻译的《天仇记》,并认为这本书是值得推荐的较好的译本。见陈汝衡:《莎氏悲剧〈哈姆莱特〉及其中译本〈天仇记〉》,载《莎士比亚研究》第4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262-269页。
(14)范伯群、朱栋霖:《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1126页。
(15)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581页。
(17)由于纸质和当时印刷技术的关系,“守卫森严□若细柳营”缺一字,以“□”代替。
(18)邵挺在评点中多次提到“索氏”、“索氏比”,而全书又标明原著的作者为“莎士比亚”,可见,邵挺在评点时,仍然不自觉地受到了《澥外奇谭》译本的影响,因为《澥外奇谭》标明的著者为“索士比亚”。《澥外奇谭》书名,在相当多的翻译学著作中被误为《海外奇谈》或《解外奇谈》等等,如周兆祥:《汉译〈哈姆雷特〉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6页;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增订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416页;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70页;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33页。
(19)(20)(23)(24)(25)(26)(29)(34)(37)(38)(39)(40)(41)莎士比亚:《天仇记》,邵挺译,商务印书馆1924、1930年版,10,10,9,10,10,10,12,66,50,50,50,50,48,33页。
(21)(30)(35)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09,228,179页。
(22)由于纸质和当时印刷技术的关系,“掩□一番”缺一字,以“□”代替。
(27)对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翻译批评几乎成为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中的一大奇观,可参见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载《中国翻译》2004年第5期,52页。
(28)李伟民:《何处是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哈姆莱特形象认识辨析》,载《四川戏剧》2003年第6期,8-11页。
(31)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见李伟民:《俄苏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戏剧·戏曲研究》,1998年第一期,19-24页;李伟民:《阶级、阶级斗争与莎学研究——莎士比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载《四川戏剧》2000年第3期,7-11页;李伟民:《莎士比亚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变脸》,载《国外文学》2004年第3期,35-40页;李伟民:《从人民性到人文主义再到对二者的否定》,载《重庆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75-82页。
(32)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卞之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19页。
(33)我开始怀疑其中的一个“忍”字为衍文,但对照1924和1930的两个版本,这一句中都有两个“忍”字,可能是邵挺在译文中所做的特殊的强调。
(36)蓝仁哲先生认为“自杀”论是由于脱离了情景语境和语言语境而产生的误解,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在思考与即将采取的行动有关的问题。可参见蓝仁哲:《从语境与语篇谈哈姆莱特独白“To be,or not to be...”的理解》,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六期,75-78页。但是,我认为,如此一来就拔高了哈姆莱特,面对强大的对手,特别是有至高威权的国王,他没有理由不想到死和自杀。这样更符合一个普通人的性格。对于哈姆莱特这句名言的梳理,可参见李伟民:《哈姆莱特的一句名言的翻译》,载《书城杂志》1994年第9期,25页。
(43)后来出版的白话译本哈姆莱特一般附有少量的注释。孙大雨先生所译的《罕秣莱德》在每一幕的后面都附了大量的注释,但那主要是以“注释”的形式对罕秣莱德加以解释、说明,和邵挺采用中国文学批评特有的“评点”方式有根本的区别。邵挺在译文中均采用“圆圈”断句,故我在引文中也不加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