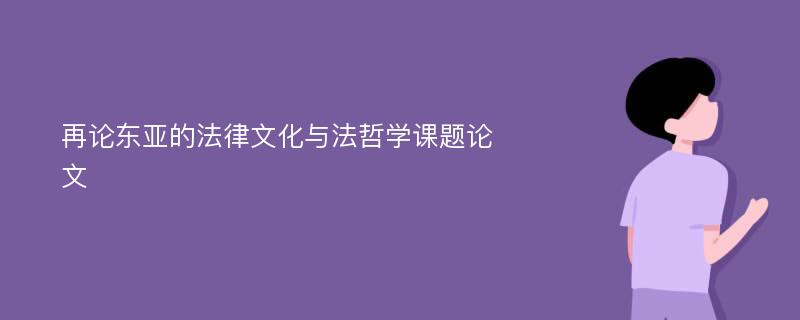
再论东亚的法律文化与法哲学课题
喻 中*
内容摘要 早在1999年,韩国学者崔钟库在《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刊发了《东亚的法律文化与法哲学课题》一文。20年后的今天重读崔钟库的这篇文章,促发我们重新思考东亚的法律文化与法哲学课题,以及东亚法治的现代化问题。法治现代化既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一个世界问题,同时它还是一个东亚问题。“崔钟库之问”,对于思考东亚的法治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重新思考“崔钟库之问”,与崔钟库对话,有助于理解韩国法理学界关于东亚法理学、东亚法治现代化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 法哲学 法治现代化 法律文化 东亚 崔钟库
一、从东亚儒学到东亚法理学
东亚有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处在亚洲东部。东亚既是一个地理单元,但又包含了超越于地理单元的含义。在学术思想界,冠以“东亚”的学问,近年来比较活跃的有“东亚儒学”。针对这个学术主题,当代学者黄俊杰、张昆将、陈来、傅永军、吴震等都有专门的论著,讨论也比较深入。“东亚儒学”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把它看作是“儒学地理学”的一个板块,似乎也是可以的。因为,从地理上看,除了“东亚儒学”,其他地方也有儒学,譬如北美的“波士顿儒学”,(1)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波士顿的儒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就很有特色。
其他地方的儒学暂且不论,关于东亚儒学,复旦大学的吴震认为,“如今‘东亚’作为一种文化概念而非单纯的地理概念,逐渐成为东亚各国学术界关注的对象。近十余年来,在台湾学界的努力下,‘东亚儒学’已足以构成一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已到了对此研究领域的已有成果及将来发展等问题进行总结反省的阶段,特别是对于东亚儒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必要’的问题进行反思显得尤为重要。”(2) 吴震:《关于东亚儒学问题的一些思考》,载《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这就是说,东亚既是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对于“东亚儒学研究”的兴起,台湾地区的学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来的还有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难以遏制的道德溃败的现实:从小地痞到大流氓,从黑社会老大到孱弱的小公安,从形而上的诗性理想到形而下的肉欲狂欢。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急剧变化,各个阶层也在这场浪潮中,面临着重新的洗牌和重塑,曾经由知识分子高呼、推动并为之奋斗的乌托邦豪情与梦想日趋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遮蔽。
在台湾地区,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是东亚儒学研究的重要推动者。在一篇具有总结性质的文章
就在我考上大学的那年暑假,父亲走上了自己的路。祖父去世后留下一大块田地,后来田地被划入住宅建地,父亲因此意外地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他决定带着那笔财富从这个不愉快的家庭里抽身而退。
中,他写道:“所谓‘东亚儒学’指儒家价值理念影响所及的地区所呈现的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这样的一个儒家思想文化圈,并不只是具有地域文化特性的东亚各国的儒学传统的拼图而已,事实上,东亚各国儒学既分享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如‘仁’、‘礼’、‘仁政’、‘王道’等,又通过交流互动而与各地域文化互相影响与渗透,形成一个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共同体’(Christendom)而言的‘儒家共同体’(Confuciandom)。在‘儒家共同体’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说‘东亚儒学’虽然包括各国儒学的‘分殊性’,但更具有‘整体性’。”(3) 黄俊杰:《“东亚儒学”的视野及其方法论问题》,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这段话表明,黄俊杰更愿意强调东亚儒学的整体性。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整体性,而不是东亚各国儒学的特殊性或“分殊性”,才让“东亚儒学”这个概念成为可能。
再次,在东亚法哲学的历史上,应当划分“接受的时代”与“崭新的法哲学”。崔钟库站在20世纪的末叶(1999年),把已经过去的20世纪称为“接受的时代”,意思是,20世纪是东亚“接受”西方法哲学的“时代”。他认为,这样的时代应当结束,应当开启一个崭新的法哲学时代。这个崭新的法哲学当然是东亚自己的法哲学。东亚自己的法哲学应当是与西方法哲学能够适当区分的法哲学。当然不必以“区分”作为唯一的追求,但东亚法哲学具有地域特色(以及历史特色)的因素必须凸显出来。进一步看,在东亚三国中,中日韩对于西方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按照崔钟库的看法,日韩是“单恋着西方”,虽然“单恋”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单恋西方”却是日韩的共性。相比之下,中国对西方是“积累了爱憎”。这是一个韩国人对中国的评论,可以聊备一格。这就是崔钟库关于法哲学的东亚意识。这种法哲学的东亚意识应当得到进一步的辨析。
崔钟库说:“还有一个必需关注的问题是法律为社会的发展起了多大作用的问题。对此东西方都有各种见解,东亚的法哲学家应探索自己的理论与发展模式。”这个问题在东亚与西方都是存在的。东亚法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确实应该体现东亚的地域因素与历史传统。法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取决于如何定义法律。在现代的东亚,从形式上看,对法律的理解已经近似于西方。既然如此,法律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大致就是法律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结论也许只有形式意义。虽然中日韩三国的法律体系,几乎都可以与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对接,西方有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东亚也都有。但是,深入地观察,法律在东亚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还是有差异的。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新波斯人信札》,(14) 参见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此书在形式上模仿孟德斯鸠的名著《波斯人信札》,对东方的法律与社会进行了某些解读,突出了东西方的法律影响社会的不同方式。
崔钟库的《东亚的法律文化与法哲学课题》一文,时至今日依然有讨论的必要,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让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都应当思考的问题。他在文章中提出:“无论我们出生在中国、日本或韩国哪一国,到底东亚是何时学来了西方的法与法哲学理论的?往后是否还要继续学下去?东亚引进西方的法体系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我们是否还要继续模仿,反复下去?我们普遍认可的法哲学是西欧中心主义的哲学,那亚洲法哲学的立足之地呢?是否有人认真做过使东亚法哲学理论化和体系化的研究呢?”这几个问题,相互关联,我把它称之为“崔钟库之问”。东亚法理学上的“崔钟库之问”,其理论意义就在于促成法理学的东亚意识,或者是东亚法理学意识的觉醒。“崔钟库之问”不仅是中日韩三国法理学都应当回答的问题,更是“东亚法理学”应当直面的问题。
从东亚儒学开始,既可以研究东亚的“法家学”,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东亚的法理学。东亚有共同的法理学吗?东亚有一个值得研究的东亚法理学吗?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如果对传统中国的学问进行重新地切割、组装,把传统中国的经史子集之学重新切割,重新组装成为现在的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那么,传统中国也有法学和法理学。这样理解也许更加合理。如果拒绝这样的理解,那么,中国现代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就将彻底失去关联,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如果承认传统中国也有法理学,那么,在传统的东亚,在以孔子、朱子为轴心的学术思想体系中,也可以提炼出东亚的古典法理学。其中,东亚儒学研究需要处理的很多素材,都可以作为东亚法理学研究的素材。还是那些人物,还是那些经典,但经过重新切割,经过重新阐释,可以作为建构东亚古典法理学的材料。
关于人权的法哲学,崔钟库认为:“权利论和人权论在法哲学里占有重要地位,从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的‘争取权利的斗争是道德义务’理论,到霍菲尔德(Hohfeld)、德沃金(R.Dworikn)、魏尔曼(C.Wellmann)等学者的理论,西方的权利哲学体系精密得令人吃惊。但东亚人却不以为然,东亚人具有礼概念在内的独特的权利、义务观念。正确说明并使之理论化便是东亚法哲学的课题。讨论东亚社会的人权问题首先应该正确理解儒教的人权主义,无论权利与人权理论有多精密,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会作出不同的解释。今年初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儒教与人权》一书,详细说明了儒教的人权哲学。铃木敬夫翻译编纂的《中国人权与相对主义》(1997)根据中国杜钢建的相对主义观点,主张民主主义法哲学,把儒教传统与人权联系起来作了系统阐述。在迎接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之际,联合国准备公布世界义务宣言,我们可以用东亚法哲学的观点来关注这一举动。”这段话指出了权利论和人权论在法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这种看法有一个未经反省之处在于:这种思维本身就是从西方传来的,是西方法理学、法哲学的产物。在东亚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有义利之辨,但很难说有权利、义务、人权的理论。譬如,关于“义”,《礼记》的界定是:“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15)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68页。 就是中国传统中的“义”。这样的“义”与西方传统中的义务,显然不能相互解释。如果说,西方传统中的义务与权利相互关联,是一对法学的基本范畴,那么,在传统中国,与义相关联的概念则是利。孟子的话颇有代表性,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6)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7页。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
因此,讨论东亚地区的法理学,既可以讨论东亚的古典法理学,也可以讨论东亚的现代法理学。在这里,不可能讨论东亚法理学的所有问题,即使是一部大书或一套丛书,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主要讨论当下及未来的东亚法理学。就当下来看,作为法律地理学的一个板块,(8) 关于法律地理学的一个简要说明,可以参见喻中:《法的地方性与地方性的法——关于法律地理学的一个导论》,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具有地域性的东亚法理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到底有什么特点?或者说,属于东亚法理学的特定问题是什么?具有东亚属性的法理学到底呈现为一种什么样的学术理论形态?哪些议题是东亚法理学不容回避的核心议题?显然,这都是一些开放性的“东亚法理学问题”,为了使下面的讨论不至于过分散漫与随意,我想把韩国汉城大学(现在的首尔大学)法学院崔钟库的一篇文章作为讨论的材料,有的放矢地梳理东亚法理学、法哲学的主要议题。
1999年,崔钟库在南京出版的《法制现代化研究》这本辑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东亚的法律文化与法哲学课题》,(9) 参见[韩]崔钟库:《东亚的法律文化与法哲学课题》,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401页。为避免烦琐,以下凡引自这篇文章中的文字,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崔钟库在论文中所说的“法哲学课题”,其实都是中国语境下的“法理学问题”,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暂不区分“法理学”与“法哲学”,暂且把两个概念作为同义语来处理。这样处理是有依据的。在一部词典中,关于“Jurisprudence”的解释是“本词含义多有演变”,其中之一是“法理学、法哲学或指概括意义上的法学”。(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潘汉典总审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55页)按照这个说法,“法理学”与“法哲学”可以看作是同义词,都是英文Jurisprudence在汉语中的对应词。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应当区分开来,这个问题暂不展开讨论。 即使经过了20年时光的淘洗,这篇文章的理论意义依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崔钟库是韩国的法学教授,从他的角度来看东亚的法理学、法哲学,也许可以从中国之外的一种角度,来理解东亚法理学的痒痛。
供应链要完整落实并普及应用落地,其成功关键在于平台技术供应商与行业专家之间的充分合作、整合,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软、硬件系统组合产品SRP,SRP再经由系统集成商到用户现场安装并进行后续维护,以成为完整场域解决方案,形成工业物联网的产业链。而研华在迈向此阶段的商业模式,将分别以不同运营模式应对:硬件部分仍将维持利润中心营运;WISE-PaaS软件平台是核心中的核心,但将以分享为目的,透过成本中心为基础进行会员制方式运营;SRP软件开发与DFSI(聚焦细分领域的方案集成商)行业专家公司的合作,则分别以共创或少量合资模式进行。
二、 东亚法理学:崔钟库之问
其他学者关于东亚儒学的论述,还有不少,这里不再引证、讨论。关于东亚儒学的这些研究,无不启发我们,应当从东亚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学术。我自己就做过这样的尝试,我在《法家的现代性》一书中曾经写道:“倘若近代以来的东亚有一个共享的‘东亚儒学’,那么,近代以来的东亚也有一个共同的新法家,新法家也是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因此,有必要“从东亚的角度看法家,以揭示法家的近代性与东亚性。关于法家的近代性,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的新法家以及日本近代的新法家,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但是,把东亚诸国近代以来的新法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似乎还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这就是说,法家的东亚性,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主题,理解法家的东亚性是全面理解法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6) 喻中:《法家的现代性》,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页。 这是我关于东亚法家研究的一点思考。
如果避开了“崔钟库之问”,如果不回答“崔钟库之问”,那么,“我们将成为西方文化的走卒,也有可能成为自我欺瞒的牺牲者。”崔钟库这么说,是基于一百年来持续不断的这种现象“大部分东亚法哲学家单恋着西方的法哲学,在自己还未完全吸收消化的情况下,急于介绍和宣传西方法哲学,可是法哲学与文化、艺术不同,介绍西方法哲学的学者的人格与实存意识是遮在面纱里的,这些人把引进和传播西方最新理论当作了一种使命。当今我们拥有的法律体系是西方的,法学教育亦是西方的,但至少法哲学是可自由思考的,它可超越这些条件的制约,为了‘活着的法哲学’,我们应该结束近一个世纪的接受的时代。21世纪应全面探讨崭新的法哲学,当然我们对待21世纪不应过于兴奋乐观,而应持慎重冷静的态度。长期以来韩、日两国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单恋着西方,中国亦按自己的方式积累了爱憎,作为亚洲人我们应反思过去,为亚细亚的法提供立足之地,应认真探索和讨论东亚法哲学。”崔钟库的这段话提供了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多个侧面。
首先,很多东亚法哲学家的追求,就在于介绍、宣传或引进西方的法哲学。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法学家蔡枢衡就已经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海禁大开以前,中国没有近代式的法学。海禁大开后,变法完成前,只有外国法学著作的翻译、介绍和移植。外国法学的摘拾和祖述,都是变法完成后至于今日的现象。摘拾、祖述和翻译、介绍并移植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依然把它当作外国人的意识看,后者是直截把它当作中国人自己的意识,或中国法的意识看。翻译是非自我的,但有非自我的认识;祖述是自我的,但不是觉醒的自我,结局只能是无我;摘拾算不得体系。”(10)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0页。 蔡枢衡描述的这种现象,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重现于韩国法理学家的笔下,不得不说,这既是中国法理学的状态,也是韩国法理学的状态,同时也是日本法理学的状态,概而言之,它是东亚法理学必须共同面对的状况。
其次,法哲学与其他方面的文化、艺术是不同的。普通的文化与艺术,可以从西方国家引进,引进之后不太会导致明显的负面效应。譬如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尽管在主题、风格诸方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但它丰富了中国的审美趣味,它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人心的幽深与曲折。一个文学翻译家如果把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翻译到中国来,只要翻译质量还过得去,这样的翻译通常不会遭到质疑。但是,法理学或法哲学就不一样。崔钟库说,“介绍西方法哲学的学者的人格与实存意识是遮在面纱里的”,这就指出了西方法哲学的介绍者与西方文学的介绍者之间的差异:前者没有自己的个性与情感,后者有自己的个性与情感。譬如莎士比亚的翻译者,朱生豪的古雅就不同于卞之琳的生动,每个人的美学风格一览无余。但是,法哲学的介绍者就不是这样。他们没有个性,或者说,他们的个性不能显现出来。但是,在价值、功能诸方面,法哲学或法理学方面的作品与普通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一回事吗?显然不是。尽管崔钟库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辨,但我们仍可进一步思考:法哲学或法理学作品归根到底是为了解释行为规范与文明秩序,无论是行为规范还是文明秩序,其实都是有语境的,或者说,都是地方性的。如果“西方法哲学”的介绍者忽略了这一点,那就相当于取消了法的地方属性,那么,他的介绍就是隔靴搔痒。
在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施工中榫卯技术的应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关于榫卯技术的研究可追溯到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便采用了这种连接方式,其稳定性使该技术超越了框架结构、建筑排架等结构,在承受荷载的同时还可减小地震响应。人们通过侧脚、柱子来降低建筑重心,进一步提高了结构的我拿东西,通过构件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系统,增强了构架整体性。
崔钟库认为:“当今英美的法哲学及政治哲学界正热烈讨论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社会与国家,若这是一种世界观问题的话,可以说西方正在进行观念的摸索。迄今为止,许多学者认为东洋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未得到发展的地区,还试图把东洋社会与西方刚刚开始讨论的共同体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说明。但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则主张东洋的新儒学会具有自由主义的力量。我本人认为,无论是儒教还是佛教,不应把东亚传统局限在特定的观念里,应开放地、不断地给予新的解释,东亚文化是超越的观念,它以人为本,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东西方的超观念化发展是与东亚的世界观一致的。我们可以展望一种真正的人本主义法哲学。”
路过的人,走在铺满枯叶的石板路上,感叹村落不可避免的衰败时,忽然看到一树柿果,在转弯处,那么红,心里会为之一动,宁静又柔软。
法哲学可以自由思考的性质,与法律体系、法律教育的循规蹈矩相比,确实有差异。对于这种差异,波兰籍社会学家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有一般性的阐述。根据兹纳涅茨基的划分,我曾经把法律人的社会角色分为三类:“第一,技术专家;第二,既有秩序的辩护者;以及第三,既有秩序的批评者。法律人作为技术专家,主要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同时也是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社会的商业化、‘陌生化’程度进一步加剧,那么,法律人作为技术专家的角色还将进一步凸显——社会公众就会像依赖医生那样依赖作为技术专家的法律人。相比之下,法律人作为既有秩序的辩护者和批评者,尽管立场不同,但都体现了一种超越于专业技术的公共追求。在西方,这种公共追求主要继承了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旨趣;在中国,这种公共追求主要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11) 喻中:《法学方法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27页。 现在看来,法律人的社会角色还可以从三类缩减成为两类:法律技术专家与法哲学家。无论是既有秩序的辩护者还是既有秩序的批判者,其实都可以归属于法哲学家,他们可以在法律体系、法律教育这些硬件设施之外,超越现实的约束条件进行自由的思考。
画稿上的许春花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方格外套,一张好看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下有一个笔挺的鼻梁和两片唇线分明的丰满嘴唇。她侧着头,辫子垂到了胸前。她浅浅地笑着,左嘴角上的小酒窝就在画稿上显现了出来。只是在绘画的时候,许春花一直都微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遮盖住了她的眼睑。
相比之下,台湾师范大学的张昆将却强调东亚儒学的多种指向:一是“与其他文明对话的东亚儒学”,代表人物是杜维明;二是“没有东亚的本国儒学”,这是中国大陆儒学者的观念;三是“自他理解中的东亚儒学”,以陈来为代表;四是“批判方法的东亚儒学”,以日本学者子安宣邦为代表;五是“经典诠释的东亚儒学”,以黄俊杰为代表。以此为基础,张昆将还以“中心—边陲”作为视角,把东亚儒学的立场分为“顺中心”的东亚儒学、“去中心”的东亚儒学、“逆中心”的东亚儒学以及“超中心”的东亚儒学。(4) 参见张昆将:《儒学复兴中知识分子对“东亚儒学”的思考之探讨》,载《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9期。 这里的“中心”其实就是传统中国的儒学,特别是孔子与朱子的儒学。无论如何评价张昆将关于东亚儒学的这些概括与建构,他至少给我们展示了从地理的角度研究儒家学说的可能性,因而在方法论上,是有启示意义的。
三、东亚法理学的主要议题
崔钟库在《东亚的法律文化与法哲学课题》一文中旨在表达的主要内容,还是“东亚法哲学的课题”。他认为,以下讨论的几个方面的问题,是东亚法哲学应当重点考虑的课题。按照这个说法,东亚法哲学这个概念,主要就是由以下这些课题支撑起来的。我们来看一看,崔钟库提出的这些课题,是否构成了东亚法哲学的核心课题;对于东亚法哲学的主要议题,崔钟库的贡献是什么,他还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又是什么。但愿通过这种对话,有助于深化关于东亚法理学的理解。
第一,“法治主义传统的再解释”。
崔钟库说:“过去我们普遍认为儒教传统是否定法律或轻视法律的,这种见解随着中国学、韩国学、日本学的发展在逐步被取代,儒学虽强调仁德,但为维持社会秩序,它也肯定法与刑的必要性。我们知道,西方法律哲学也批判过去强调法和刑的法律万能主义和法实证主义。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具有说服力的‘儒教的法治主义理论’。西方正进行克服和协调自然法论与法实证主义的讨论研究,我们可以基于东亚哲学解释他们的理论研究,1973年发现黄老帛书以后,对中国法律思想开始进行新的解释。”
这段话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建立儒教法治主义。在传统的东亚,儒家学说长期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传统中国自不必说,韩国与日本也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段落中,把儒家学说(特别是朱子学说)作为官方思想。对此前面已经有所交代。这里不再重复。崔钟库认为,儒家学说强调仁德,但也肯定法与刑的必要性。这个观点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对儒学的妥帖的解释。事实上,儒家所说的礼,其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归属于现在所说的法。所谓“非礼勿言”之类的说法,就是把礼作为人的行为规范。如果要说礼与刑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礼是正面设定行为规范的法,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主要由礼来规定。至于刑,则是违反了礼之后的惩罚性规范,这就是所谓的“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2)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5-456页。 所以礼与刑的二元组合,才是传统法的基本结构。
在传统中国,儒家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法家、道家的影响也很大。在传统的朝鲜,特别是在16世纪,由于李退溪等人的贡献,朝鲜几乎可以说是东亚儒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中心,但是,法家、道家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在日本,虽然有一个“近世新法家思潮”,东北师范大学的韩东育还有专门的著作论述这一思潮。(13) 参见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 但是,就我个人所见,中国道家对日本的影响似乎不太大。虽然,中日韩三国都曾经信奉儒家学说,但是,东亚法治的未来能否走向“儒家法治主义”,却是一个难以评估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日本早就“脱亚入欧”了,韩国的西化程度并不逊于日本。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学说能否引领东亚法治的未来?很难给出肯定性的回答。当然,崔钟库的观点也有其相对谦抑的一面:儒家法治主义仅仅是对东亚法治主义的一种解释,而且是侧重于对传统的解释,如果仅止于此,那倒是可能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对东亚的法治传统进行重新的解释,以东亚的法治传统作为参照,解释西方的自然法理论与法律实证主义,这是可以做到的,至少是可以尝试的。这就是说,对东亚法治传统的解释,主要是一种学术层面上的追求,主要是思想史的求索,如果指望它“溢出”学院,去改造现实的法治世界,那恐怕就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人本主义法理学是否可能?
再次,虽然东亚的法律体系、法律教育是西方的,其中,日韩两国尤甚,但法理学、法哲学可以自由思考。这就是说,法哲学与法律体系、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可以区分开来。崔钟库的这个观点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表面上看,他对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体系、法律教育的区分比较平淡,试想,只要是两个事物,都可以区分开来。譬如,虽然法律体系已经是西方的,但是,法律教育的方法也可以自由思考。在法律教育体系中,课程的设置、学制的长短,诸如此类的法律教育问题,不仅可以自由思考,甚至还可以自由选择。然而,如果尊重崔钟库的思路,他的区分还是有价值的。他的区分是关于灵与肉的区分。法律体系、法律教育是法的肉身。你去查阅立法机构创制的法律法规,你去司法机构查阅诉讼档案,你去法学院考察法律教育的各种制度,包括教室的布置,教科书的内容,教师讲授的方式,都是可以“眼见为实”的,都是可以触摸的。这些都是法的肉身。按照崔钟库的观察,东亚法的这些肉身,都已经是西方的。但是,法哲学、法理学却可以自由思考、自由探索。法哲学、法理学是法的灵魂。无论法律体系、法律教育这些“看得见的法”呈现出何种外貌,法的价值问题都是可以重新设定的。这就像一台电脑,它的硬件与软件总是可以相互独立的,相同硬件的电脑完全可以安装不同的软件系统。法哲学、法理学就是法的软件系统。在相同的法律体系、法律教育中,你可以强调自由的价值,但也可以强调民主的价值;你可以强调效率,也可以强调公平。当然,这些价值可以兼容、兼顾,但在一些关键的环节上,各种价值要素之间的差异是不容回避的,而且确实也是可以选择的。你优先选择、支持了这种价值,就必然暂时遮蔽了其他的价值。在很多时候,确实可以追求“双赢”的效果,但在对抗性的“决赛”时,怎么可能实现“双赢”呢?
英美的法理学主要强调自由主义。崔钟库所说的共同体主义,也许是指社群主义,当然影响也很大,但较之于自由主义,毕竟是一种次要的声音。正是在模仿、追随西方法理学的过程中,东亚的学者才主张,应当进一步发展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新儒学是否蕴含了自由主义的因素?只要去挖掘,只要对新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肯定是有的。毕竟,无论是新儒学还是自由主义,都存在着巨大的解释空间。崔钟库提出的观点是: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法哲学相比,东亚的法哲学可以是人本主义法哲学。人本主义的口号是“以人为本”。现在,众口一词说“人本”。那么,“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简而言之,就是把人作为根本,作为起点。在西方,“以人为本”的对立面,也许是“以神为本”,欧洲的中世纪也许流行过“以神为本”的主义,从中世纪的欧洲到近现代的欧洲,也许出现了一种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向。不过,如此描述欧洲的历史,也许是欧洲近现代人的某种自得心态的反映。
欧洲历史上有一个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转变,但东亚的情况又另当别论。相对于欧洲的中世纪,“以人为本”也许可以当作东亚的一个传统。但是,法哲学上的“以人为本”也包含了各种指向。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还是“全国人民”?最近几十年里,在中国的法理学界,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著也是比较多的。韩国学者也有这样的观点。由此看来,“人本主义法理学”也许有机会成为东亚法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当然,由于“以人为本”中的“人”与“本”,都面临着相当大的解释空间,这就意味着,“人本主义法理学”也包含了多种不同的走向。
子宫切口憩室在妇产科存在有极高的发生率,对产妇产后健康造成较为严重影响,促使其生活质量持续下滑。手术治疗已成为该症最为主要的临床处理方式。
第三,法律的作用及其他方面的课题。
陈来关于东亚儒学的研究,侧重于对中国、韩国、日本历史上的朱子学所展开的研究。因而,陈来关注的东亚儒学,主要是东亚朱子学,在他的《近世东亚儒学研究》一书中,分别论述了中国的朱子学,朝鲜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李牧隐的朱子学,以及日本林罗山的朱子学,在此基础上,陈来归纳了“中日韩三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他说,“如果用两个字,我们中国是‘仁恕’。韩国凸显‘义节’。”相比之下,“日本凸显‘忠勇’。这种不同反映了各自的价值体系的差异,也可以说反映了三个国家文化原理的不同,就是文化里可能有很多原理,但是有一个支配性的原理。”(5) 陈来:《近世东亚儒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7页。 显然,这是从辨异的角度,分析了东亚儒学内部的三种风格。
基于三维激光扫描和全景摄影技术的数字校园景观建设……………………………………… 叶瑞锋,赵培,胡玉龙(9-269)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在东亚地区,同样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为东亚法理学的思想与学术,较之于东亚古典法理学,可以称之为东亚现代法理学。东亚现代法理学出现的背景是:东亚各国先后都兴起了一种“学习西方”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起步较早,明治维新是这股潮流的政治表达,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可以视为这股潮流的理论表达。(7) 参见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引入了西方的法理学。这种法理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从日本传到了中国,代表性的人物是梁启超。当然,中国也从西方直接引进法理学,代表性的人物是严复。严复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方面的专业知识、专业技术,但却引进了西方法理学的一些核心著作,譬如《法意》(现在译为《论法的精神》)、《群己权界论》(现在译为《论自由》)等,这些“严译名著”既是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基础,其实也是东亚现代法理学的基础。韩国的情况要特殊一些,韩国学习西方的时间可能稍迟一些,但由于20世纪中期以后韩国的实际情况,韩国对西方的学习也是极其深入的。由此可见,在古代,孔子与朱子是东亚地区共同仰慕的思想家;近代以来,密尔、孟德斯鸠等西方思想家成为东亚地区共同关注的对象。这就是说,共同的“东亚法理学”,不仅可以见之于古代,也可以见之于近现代。
关于法律理念,崔钟库说:“法哲学中最主要的是法律理念。一般来讲西方强调法哲学的正义,最近女性主义法哲学反对男性为主的虚伪的正义,而主张‘照顾的法哲学’。西方法哲学理念的潮流,让东亚法哲学家们不禁想起在追求‘良法美意’的东亚法传统里,义和善以及美三者之间的关系。东亚法哲学理念里不存在与真、善、美无关的严格独立的正义。正义不是单纯的观念和论理,它是在与文化的接触中形成的。于是便不可排除‘正法’与‘善法’的理念。现代法哲学开始重视实践理性,而东亚很早就已强调实践理性。法哲学的实践性问题不只停留在法哲学家们思、辨的领域,它是给民众和法律家提供力量的学问。它需要建立符合东亚人心理的善法的法哲学。”崔钟库的这段话,名义上是在讲法律理念,但它实际讨论的内容,却是东亚的“善法”与西方的“正义”之间的差异。用当代中国常用的法学术语来说,其实是关于法的概念论或本质论。把法的本质理解为正义,这是一种西方的观念。那么,在东亚的传统中,法的本质又是什么?崔钟库对此语焉不详。在传统东亚,特别是在传统中国,“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17)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这里的“刑”与“兵”同义,显然跟正义没有直接的关联。先秦法家所说的法,虽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但是,这样的法同样偏离了正义,因为,“一断于法”的后果是,“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18) 《史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59页。 这样的法,由于“不可长用”,显然也是远离“良善”的。那么,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兵刑同义”,由于习惯于把法理解为“刀把子”,基于这种固有的法观念,是否有一个追求“良法美意”的传统,可能还是一个疑问。
关于法伦理学与法美学,崔钟库说:“法伦理学与法美学的方向是体现东亚法哲学特点的两大要素。东亚法哲学应树立更贴近法伦理,具有丰富内容和形式的法哲学,可以与西方法美学、法象征学、法记号学相互对话的理论体系。西田几多郎主张‘正的善是一种美’,吴经熊的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正义论值得关注。最近韩国、日本也已开始研究法美学。”这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东亚法理学的主题,拓展的空间很大,东亚各国的资源都很丰富。中国的伦理学与美学一向很发达,日本独特的伦理观念与美学传统也很丰富,“韩剧”“韩潮”的影响也很大。这些资源都可以支撑东亚的法伦理学与法美学。应当在东亚的传统中研究法伦理学、法美学。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吴经熊的《法律哲学研究》,都属于融汇了东西方的研究,正如吴经熊的自传所标示的,他的愿望就在于“超越东西方”。(19)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四川省安岳县是国内柠檬主要种植区,当地柠檬种植面积占当地耕地面积的35%。目前主要是2014年-2015年新种植的柠檬,到2019年到达盛果期。现阶段,柠檬种植户刚开始见到收益,故用肥积极性比去年略高。有经销商反映,当地零售商多销售常规肥料,很少销售有机肥,这便给部分销售有机肥的忽悠团以可乘之机。忽悠团销售的有机肥价格比正规有机肥低很多,但农民不会识别有机肥的品质,在忽悠团忽悠下就会购买,但这种有机肥水分控制得不好,盐分也超标,农民施用过后会出现果树黄化现象。农民发现上当后,早已不见忽悠团的身影,农民无处投诉,忽悠团正是看到这一点,故能一直逍遥法外。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东亚式民主主义的问题,崔钟库说:“我们的民主主义应建立在东亚式民主主义法哲学基础上。‘东亚民主主义’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的‘王冠民主主义’和韩国朴正熙的‘民族的民主主义’。但真正的民主主义是不需加任何修饰语的,应该是仅以亚洲式思维方式和语言便可扎根于社会的民主主义。它应成为随时可与西方法哲学对话的法哲学。例如,拉德布鲁赫(G.Radruch)的法哲学在韩国、日本都引起共鸣,最近中国也开始介绍他的民主主义法哲学。”民主的观念源出于西方,但近代以来,民主的观念在东亚得到了广泛而普遍的承认。中日韩各国都形成了自己的民主道路,但是,要提炼出东亚各国都能够普通接受的“东亚民主主义”,可能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
四、 东亚法理学:方法及其他
在提出了东亚法哲学包含的主要课题的基础上,崔钟库还在《东亚的法律文化与法哲学课题》一文中,讨论了东亚法理学或东亚法哲学的方法。东亚法理学研究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方法吗?对于这个问题,崔钟库主要谈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他说:“我们应该考虑法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考夫曼(Arthur Kaufmann)指出,法哲学不受民族的制约,是普遍性学问。同时,他也通过比较中国唐律思想和西方的自然法论来强调法哲学的相似性。但任何文化、文明若只强调普遍性,就会变得空虚无味,相反如过分强调特殊性会变得闭锁、独断。千叶正士就指出应尊重个别的法文化,并使它走向世界化。‘第三世界法哲学’很好地反映在新加坡1984年出版的《第三世界法哲学论文集》里。马拉辛赫(M.L.Marashinghe)教授认为第三世界法哲学‘需要新的接触’。千叶正士教授讨论了‘文化的普遍性与法哲学的特殊性’。印度德里大学的乌蓬德拉·巴克西(Upendra Baxi)教授目前主导着‘非西欧社会的法与道德、宗教’研究,但整个东亚应重视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儒教、佛教、神道传统的东亚三国,研究课题应该是非常丰富的。1987年首次在东亚召开的世界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IVR)大会以‘法·文化·科学·技术:追求异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为大会主题,它再一次强调了法文化的多元主义。1996年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法哲学研讨会也进一步加深了对东亚法文化的认识。”
崔钟库的这段话主要概括了20世纪晚期以来与东亚法理学有关的一些学术进展。其中,考夫曼侧重于强调法哲学的一般性与普遍性,他认为,法哲学应当与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割裂开来。在这种追求的背后,可能有一个德国式的传统: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是普遍性的学问,是世界观、方法论,法哲学也应当是这样。也许是德国传统的法哲学比较偏好这种“一般性”的方法。考夫曼作为德国人,认为法哲学是“普遍性学问”,并不令人意外。在德国法哲学的框架下,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从表面上看,是运用“一般性”的方法形成的法哲学作品。但是,黑格尔的法哲学难道没有民族传统的影响?黑格尔法哲学对国家的推崇,难道没有体现德意志民族的某种期待?再说,如果一味强调法哲学研究的一般性,那么,东亚法哲学这个概念还能存在吗?
透过两千多年的沧桑时空,从这些大多数至今也没有生锈,仍然满盈铜色斑驳的餐具,我似乎看到了在“天下膏腴之地,莫盛于齐者”的沃土之地,一个个名君贤相、英帅良将的身影,一场场承载着历史,寄托着情怀,更演绎着政治色彩的宴席——
因此,适度注意作为法理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可能是一个更加合理的选择。特殊性可以是民族性,但是,对东亚法理学研究来说,特殊性其实就是区域性、地方性。东亚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这个区域在历史上曾经共享了一套文化体系、价值体系、概念体系,因而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法理学、法哲学。比较而言,研究“第三世界法哲学”或“非西欧社会”的法哲学,较之于研究东亚法哲学,难度系数还会更大。就前者来看,无论是“第三世界法哲学”还是“非西欧社会”的法哲学,都旨在把西欧(以及北美)之外的所有地方作为一个研究的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多元化、多样性,远远超过了东亚内部的多样性。东亚法理学存在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经典作家、经典著作。但是,“非西欧社会”的共性,可能就仅仅在于它们的“非西欧性”。
在此基础上,崔钟库还谈到了他自己努力的方向:“本人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去年在夏威夷大学期间仔细观察了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现状。以五十年代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菲尔姆·诺思罗普(Filmer Northrop)等的哲学展望为背景,一直都在进行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东西中心(East-Weste Center)’,现在试图把‘命题中心的西洋’与‘直观中心的东洋’哲学综合起来,从中会发现许多多元要素。此中心1967年已出版《中国的精神》与《日本的精神》,还没有《韩国的精神》一书。与那里的研究东亚哲学的学者们交谈会发现他们似乎比东亚学者更重视和爱护东亚哲学,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基于这些观察,我认为东亚法哲学的发展方向是比较法哲学或综合法哲学。”
最后一句话表达了崔钟库的基本观点:东亚法哲学应当是比较法哲学或综合法哲学。这个结论意味着,东亚法哲学无论如何都要以西方的法哲学作为参照。这样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把法理学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那么,法哲学或法理学其实是“东亚在世界”的产物。着眼于古今之变,东亚的历史其实可以分为两段:首先是“东亚在东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东亚各国之间相互交往,孔子、孟子与朱子成为东亚文明的最高象征。后来,西方人来到东亚,东亚进入世界,是为“东亚在世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西方的法理学逐渐传入东亚,东亚法理学开始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置身于21世纪,东亚法理学需要有一个清醒的东亚意识。但是,这个东亚意识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东亚法理学只有与西方的法理学保持某种对话,才可能在对话中不断成就自己。
崔钟库关于东亚法哲学、东亚法理学的诸多观点,已经引用他的原文作出了逐一的评析。评析也是对话,也是讨论。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发现,东亚法理学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法理学主题。东亚法理学在21世纪的展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也许是必要的。
[7]陈宝生:《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http://news.cslg.edu.cn/index/read/id/77521.
首先,寻找东亚法理学的共同性。东亚法理学的共同性既有历史之维,也有现实之维。在历史上,正如前面已经反复强调的,儒家学说以及佛家学说,多多少少都是东亚法理学共同的文化背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东亚法理学可以分享很多共同的人物与著作,譬如孔子与朱子,譬如法家与道家,等。就现实的需要来看,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既需要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其实也需要地缘法理学的研究,地缘法理学其实就是法律地理学。立足于现实政治研究东亚法理学,其实是把法理思维、法治思维引入东亚地缘政治的研究中,其现实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其次,在东亚内部开展比较法理学研究。中国的法理学、日本的法理学、韩国的法理学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即使是对西方法理学的借鉴,各国的路径和期待也是不一样的,借鉴过来的西方法理学在中日韩各个国家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比较中日韩法理学的异同,寻找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无论是求同还是辨异,都是具有理论意义的活动。从最低限度来说,东亚内部的比较法理学研究,至少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促成东亚内部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
最后,促进东亚法理学与“东亚之外”的其他地方的法理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崔钟库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把东亚的法理学作为一个单元,以之与西欧或北美的法理学进行比较,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东亚之外的世界并不仅仅止于西欧与北美。进一步拓展东亚法理学与西亚、南亚法理学的比较,比较东亚法与非洲法的法理基础,比较东亚法与拉美各国法的异同,都可以作为东亚法理学研究的主题。从根本上说,法理学或法哲学乃是关于文明秩序原理的一套学说。东亚法理学的终极使命,还在于从学术思想的层面上,探索东亚内外的文明秩序,只要是与东亚文明秩序有关的学与思,都可以纳入到东亚法理学的视野中,经过处理,都可以成为东亚法理学的组成部分。
五、结 语
以上主要是以韩国学者崔钟库的一篇论文作为材料,剖析了东亚法理学研究过程中需要处理的若干问题。在评述他的观点的过程中,我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如果拔高一点,以上的学术对话也可以当作中韩法理学比较研究的一个尝试。
二要加大治理投入。首先,中央应尽量保持投资稳定,项目实施方案一经审批就应严格执行,按时足额下达投资,确保治理工作能够按计划有序顺利实施。其次是国家应及时根据市场化运作及规范管理的要求,紧密结合当前市场建材、人工及税费价格情况,根据定额尽快对石漠化投资标准和工程单价进行科学核定,适当提高补助标准和投资强度,确保投资概算能够满足实际工作需要,提高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第三是建议取消地方配套,在进一步加大相关项目整合力度的同时,在人工种草措施中适当考虑一定数量的牲畜配套,解决种草户养不起畜禽的困难,提高其发展种、养业及保护现有人工草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东亚法理学是一个学术问题,需要建构,需要发现。讲东亚法理学的发现,还有必要提到新近出版的一本著作——旅美学者宋念申的《发现东亚》。此书开篇即指出:“在殖民现代语境中,‘东亚’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概念,而带有强烈的时间和种族性。我试图梳理出一个不以欧洲殖民现代观为参照的‘东亚现代’,并把这个现代的起点,定为16世纪。不以欧洲为参照的意思,是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弃;反思欧洲中心主义,但也不塑造一个东亚(或中国)中心主义。也就是说,欧洲、亚洲、美洲乃至非洲的多元的现代历史,都可被看作是整体历史的地方性部分,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人既不共享一套时间观念,也不遵循同一种发展逻辑。同时,这些观念和逻辑又不是各自孤立的,人类的现代状况是它们相互影响、吸纳、对抗、对话的结果。”(20) 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以这样的理念作为前提与预计,宋念申的著作论及“朝鲜之战”“满洲崛起”“新天下秩序”“欧亚的现代相遇”“早期全球化”“东亚现代思想的兴起”直至“二战”之后的“冷战”。这部以东亚史为主题的著作,既有助于发现东亚,发现在东亚的现代性,同时,也有助于发现在东亚的法理学。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表明,东亚的法理学是世界法理学的地方性部分,亦即东亚部分。立足于东亚,对于西方的法理学,既不必全盘接受,也不必全盘否弃;既要反思法理学上的欧洲中心主义,但也不必提倡东亚中心主义的法理学。说到底,东亚的法理学毕竟是在东亚的历史进程中兴起的。东亚法理学的未来,必然是东亚传统的延伸,同时也是与其他地方的法理学进行交融对话之后的产物。
Abstract: As early as in 1999, the Korean legal researcher Choi Chongko published his article East Asian Legal Culture and Jurisprudence in the journal Modernization of Legal System , volume V. After two decades, a re-reading of this article promoted us to revisit the legal culture and jurisprudence in East Asia and think about the issu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rule of law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Rule of law modernization is a problem facing not only China but als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in particular an issue confronting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question raised by Choi in his article provides us with a valuable access to addressing the issue concern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le of law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Revisiting Choi’s question and carrying out a dialogue with him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Korean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jurisprudence and rule of law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Key words: jurisprudence; rule of law modernization; legal culture; East Asia; Choi Chongko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学科编辑:倪 斐 责任编辑:李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