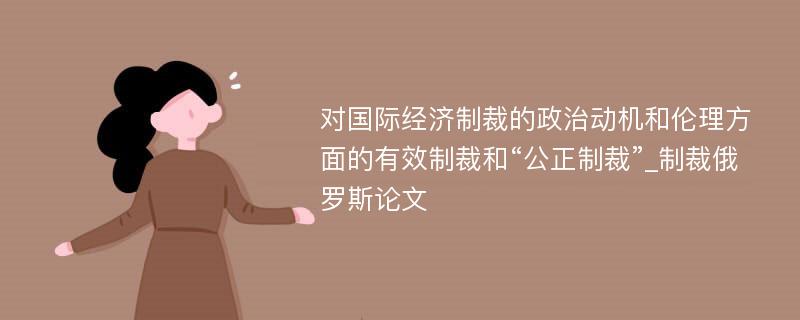
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维度论文,伦理论文,正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8-0024-24
在国际关系中,利用经济手段追求政治与安全目标是极为常见的现象,经济武器也是仅次于军事力量的一种强制手段,因此经济制裁一直是一种重要的对外政策工具。① 战后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制裁的使用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其实施主体、动因、目标和性质等也日趋复杂化。但经济制裁的效果实际上很不稳定,有时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与人道危机,其有效性与合理性均缺乏可靠的保证,因而成为当代最有争议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本文试图在简要梳理经济制裁的历史演进并界定其内涵与类型的基础上,着重对其政治动因以及在经济、政治与道德等方面的实际效果或影响进行分析与评判,并就国际社会如何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国际规范以保证制裁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提出一点看法。
一 经济制裁作为外交工具的历史沉浮
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戒手段在东西方世界都由来已久。例如在中国,《尚书·吕刑》中所谓“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就是以处罚犯罪者一定数量的财物以示惩儆。② 在公元前432年的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也曾以本城邦三名妇女被劫持为由颁布法令,宣布切断通往麦加那地区的粮食供给,并禁止麦加那利用雅典帝国的港口和市场。③ 不过,由于古代时期国家间经济交往较少,经济制裁的价值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形式也比较简单。
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尤其是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后,国家之间有时既要解决冲突,但出于成本与收益等考虑又不想诉诸战争,于是经济制裁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外交工具。其中19世纪中叶英国通过《航海条例》对荷兰实施经济封锁便是一个标志性事件。④ 英国的制裁不仅给荷兰造成了巨大打击,还强化了英国对英属殖民地的控制。
在一战期间,经济制裁对于协约国打败德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备受青睐。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就竭力推崇这一策略,经济制裁的理念甚至被纳入国际联盟宪章。在实践中,国联对某些小国的制裁取得了较佳的效果,例如在1925年成功迫使希腊撤出保加利亚领土。然而,1935年国联的经济制裁却未能促使意大利军队撤出埃塞俄比亚,因此声誉大跌。
二战期间,盟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措施同样有效地遏制了德、意、日的军事潜能,使经济制裁的声誉有所回升。战后以来,拥有超强经济实力的美国频繁使用经济制裁,并以此作为推行冷战遏制战略,维护美国利益甚至推广其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工具。美国不仅对东方阵营国家实施了长期制裁,为贯彻其冷战战略,甚至不惜对其盟国进行经济恐吓。例如,通过施加经济压力,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迫使荷兰放弃阻止印度尼西亚独立的企图,在1956年迫使英、法从苏伊士地区撤军,在60年代初使埃及从也门和刚果地区撤出。但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制裁同样得失参半。例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并未达到预期目的,⑤ 60年代旨在颠覆古巴政权的全面经济制裁以失败告终,1979年以后对苏联的禁运也未能奏效。在冷战后期,随着失败案例的增多,人们对制裁的热情又大为消退。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制裁被空前频繁地使用,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在冷战后最初四年就实施了八起制裁,而在整个冷战时期只有两起。⑥ 不仅如此,经济制裁的动因、目的、形式等都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除了诸如制裁南非等少数例外,冷战时期的经济制裁主要是某些国家的单边行为,并主要为军事安全等传统政治目标服务。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成为实施制裁的重要角色,开始体现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而反恐、防扩散、反毒品交易乃至政权改造、保护环境、促进民主与人权等也成为经济制裁的动因。⑦ 这类制裁行为实际上大多具有国际干涉的性质,因为制裁的发起者或实施者并非国际冲突的当事国,而是在无关自身直接利益的情况下采用制裁手段介入或影响他国事务。“干涉性制裁”虽然并非新现象,但从未像冷战后这样盛行,并且目标如此广泛。尤其明显的是,冷战后,人权危机被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成为一些国家甚至联合国频繁使用经济制裁的重要理由。由于传统政治动因与人道主义动因之间关系的变化,国际制裁发生了重要转型。
但在冷战后这个所谓“制裁的时代”,⑧ 经济制裁的效果依然不佳。例如,美国及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就防止核扩散的主要目标而言,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⑨ 经济制裁甚至被称为当代美国外交“最大的悖论”。⑩ 从联合国对伊拉克、南联盟、海地等国的制裁实践来看,制裁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有时并不亚于战乱所带来的后果,而这些灾难主要发生在目标国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老人和儿童身上。经济制裁的倡导者所强调的“针对性”和“正义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由于冷战后的经济制裁屡遭挫折,人们的态度又趋于谨慎。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焦点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自2006年年底以来,为解决伊朗核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已通过了三份含有制裁内容的决议;2010年6月又通过第1929号决议,决定进行第四轮制裁。但制裁前景尚难预料。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希望加大制裁力度,但中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都强调,制裁措施应主要针对核扩散问题,不应扩大化,以避免造成政治与人道危机。中国主张“对有关制裁进行严格的限定”,不能影响各国正常经贸往来和伊朗人民的正常生活。(11) 这种立场无疑非常审慎,也很有代表性。
总之,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运用经济制裁,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二 经济制裁的内涵与类型
对于“经济制裁”这个由来已久的概念,当代人非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而且还存在着许多颇为严重的分歧。
要理解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制裁,也许还得从“制裁”的一般意义谈起。英文“制裁(sanction)”一词,其词源来自拉丁语“sanctio”,意指对违背神意或法令特别是教令的一种特定惩罚。这意味着“制裁”不仅是对某种违反法令行为的惩罚,也是对某种有悖道德共识或侵犯整个共同体利益的行为的惩罚,也就是说,制裁不仅包含惩罚的意图,也意味着道德谴责。同样,国际关系中的“制裁”行为,一般也是因为目标国侵害了发起国的利益,或触犯了其所珍视的道德价值。
当今国际关系中,国际制裁一般指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为了防止目标国违反国际法准则或因其不遵守国际法准则而采取的非武力威胁措施或惩罚行为。(12) 制裁是发起国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制裁的类型与其效果密切相关。制裁类型不同,所引起的政治和道德后果往往大不相同。
如果按照制裁的主体(发起者或实施者)来区分,国际制裁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所谓“普遍制裁(universal sanction)”,(13) 即由全球性国际组织(如国联或联合国)发动的制裁,如国联对意大利的制裁,战后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这类制裁通常得到国际法认同或全球性国际组织授权,因此具有较强的国际合法性。二是多边制裁(multilateral sanction)。其实施主体可以是多个国家、国家集团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如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或者北约、美洲国家组织、东盟对某一成员国的制裁。由于国家集团或区域组织的代表性远不如全球性组织广泛,加之其制裁行为还常常忽视更普遍的国际规范,因此其合法性往往有争议。三是单边制裁(unilateral sanction)。一般指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比如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单边制裁的发起国如果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也可能会动用多边关系来增强制裁效果,或者寻求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的支持以使制裁“合法化”。但只要该国始终占据主动与主导地位,并主要为该国的利益服务,本质上仍是单边行为。
上述分类法有助于判断制裁的合法性来源,但对探讨其政治和道德后果却意义不大。因为从政治效果上说,多边制裁并不能确保避免单边制裁中的具体利益追求问题,其较为明显的经济功效也不一定能转换成相应的政治功效;(14) 从伦理角度看,无法断定普遍制裁或多边制裁造成的伦理困境一定比单边制裁小,或者说无法证实单边制裁一定是不道德的(甚至肯定是违法的),或者多边制裁以及普遍制裁就不存在消极的道德后果。出于反侵略目的的单边制裁显然具有正义性,为了维护国际秩序或避免大规模人权伤害的制裁往往也具有合理性。例如,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美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的全面制裁法案就较少引起原则性的争议。
如果按照制裁的内容或者说按照制裁对象国被剥夺的价值类型来划分,国际制裁至少有三大类型:外交制裁、交流制裁(communication sanction)以及经济制裁。(15) 其中,经济制裁的使用日趋频繁,影响也最大。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决策者认为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既可以是某种象征性措施,也可以是实质性的甚至非常严厉的惩罚手段;既可以保留较多的经济成分,也可以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经济制裁的推崇者们认为,经济手段与武力手段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它们的威胁或破坏程度,而是所使用的工具本身的性质。后者试图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直接暴力来影响别国,而前者则采用相对较为“温和”、就目的而言更为间接的手段,即经济工具,其道德成本低廉,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所谓国际经济制裁,一般是指一个或多个国际行为体(通常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公开地对某个或某些国际行为体施加各种经济压力,或与其断绝经济交往或与经济有关的其他交往。(16)
但经济制裁也有广义与狭义之争。狭义的经济制裁只是国家“经济方略”的一个部分,主要指通过经济压力手段来达到某种政治与安全目的,尤其是影响目标国的某种政策行为;广义的经济制裁则几乎等同于所谓“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即治国方略的整个经济方面,对外经济战略、经济外交以及“经济战”、“贸易战”、“经济强制”(即狭义的经济制裁)等概念都被囊括在内。其主要目的虽然也是影响目标国的行为,但“行为”的含义还包括信念、态度、观点、期望、情感与行动偏好等。此外,制裁动机可能还包括争取国内政治支持。有的学者甚至将解决贸易争端、改变目标国对外经济政策等非政治目标也纳入制裁目标的范围。(17)
过于狭窄的定义固然可能忽视了经济工具在外交实践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但过于模糊、宽泛的概念则会导致理论分析的困难。例如,人们往往将“制裁”与“抵制(boycott)”和“禁运(embargo)”等概念等同起来,这就忽视了它们在实施主体、法律效应、威慑程度等方面的区别。(18) 再如,战争期间为赢得军事胜利而采取的诸如经济封锁、贸易禁运等措施,实际上是军事对抗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作为战争和战略之组成部分的“经济战”或经济战略,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制裁,因为削弱对手经济能力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其军事潜能。冷战时期西方在战略物资方面对苏东的贸易管制以及美国所谓对华“经济制裁”,都是冷战战略的一部分,与“制裁”的本义也相距甚远。
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制裁与国际经济中的制裁区分开来:第一,在国际政治中,经济制裁是为了实现某种外交目标,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改变别国内外经济政策等非政治目标。第二,国际政治意义上的经济制裁,其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或国际组织,同时也包括一些直接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行为体,但一般不包括可能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国内“院外集团”、个人或跨国公司。经济制裁的对象或客体也是民族国家或具有政府行为能力的实体,而非个人等次国家行为体。第三,为了明确表达某种政治立场或政治目的,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制裁一般有必要公开宣布,而国际经济中的制裁则不一定都要公开。第四,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制裁形式更为多样,诸如限制或中断与被制裁国的经贸往来、冻结账户存款和其他资产、中断或减少金融往来与外援、取消贸易优惠条件,而国际经济中的制裁往往集中在进口配额与反倾销这两个领域。(19)
同样,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经济制裁也有若干类型。从制裁的参与程度看,可分为多边制裁和单边制裁;从制裁的内容来看,可分为金融制裁、贸易制裁等局部制裁和全面制裁。金融制裁是指剥夺目标国获取外国资本或者进入外国金融市场的制裁行为;贸易制裁不仅包括对从目标国进口的商品进行禁运以使目标国出现外汇短缺、出口行业工人失业或削弱其工业能力,还包括对重要商品进行禁运;全面制裁就是两者兼而有之,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改变被制裁国的政策行为。
从制裁的手段来看,可分为说服性制裁/积极制裁与强制性制裁/消极制裁。说服性制裁强调在施压的同时运用所谓“胡萝卜”,以诱导或奖赏所期望的行为。其支持者认为,对别国行为施加影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提供经济利诱,诸如增加贷款数额、减免贷款利息或给予最惠国待遇;而强制性制裁就是直接运用“大棒”。其支持者认为,要遏制或改变非法或令人厌恶的行为,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经济惩罚,例如提高关税、限制货物进口、中止贷款乃至冻结外国资产、停止外国投资、全面经济封锁等更为极端的手段。尽管理论上似乎说服性手段更有利于引导行为的改变,但在实践中各国却更倾向于使用强制手段。
在冷战后,还有人根据制裁的效果,将经济制裁分为导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全面制裁(comprehensive sanctions)/“愚蠢制裁(dumb sanctions)”与“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针对性制裁(targeted sanctions)”。许多人认为,传统的全面制裁不仅达不到目的,还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使制裁的正义性受到置疑,可谓得不偿失,因此是“愚蠢制裁”;而具体对象和手段都有所选择,“更有针对性、更人道、更有效”的制裁则被称为“聪明制裁”。在其倡导者看来,所谓“聪明制裁”就是尽量针对政治责任人及其支持者以最大限度影响决策,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普通民众或无辜者(包括邻国)造成伤害。(20)
如前所言,在冷战后时期,经济制裁正在由一种传统国家间对抗工具演变为一种国际干涉手段。因此也许还可以根据制裁的动因、目的以及发起者和参与者的不同,将经济制裁分成两大类:传统“竞争性经济制裁”与“干涉性经济制裁”。
三、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
经济制裁从根本上讲是发起者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标而采用的一种外交工具。在较抽象的层面,人们一般将制裁的动机概括为四大类型:惩戒、威慑、强制或胁迫、显示决心。(21)
其一,惩戒。这是与制裁概念的历史起源相一致的常见目的。其出发点是为了制止对国际法规的违反或破坏,并以适量的痛苦来惩罚违法者。正如金·诺萨尔(Kim Nossal)所言,国家将经济惩罚作为一种对别国先前伤害或敌意行为的报复,目的是矫正过去的不公正以及遏制未来的敌意行为。(22) 不难想见,如果只是为了给对方造成损失,惩戒总能取得一定效果。不过,只有当违法者受到有效惩罚,发起国认可或珍视的价值或规范得到再次肯定或加强,惩罚性制裁才算真正成功。
其二,威慑。即遏阻目标国可能采取的某种行为,同时也警示其他潜在的侵犯国,达到以做效尤的效果。经济制裁不仅仅是为了惩罚某种行为,也是为了阻止可能发生的行为,为此必须使对手充分理解它将面临的经济灾难或痛苦。比如,在冷战期间,苏联对其他不屈从其霸权政策或试图摆脱其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制裁,既是一种惩罚,也是想通过显示其政治意向以及决心和能力,震慑和警告其他可能的效仿者。例如,苏联曾先后全面中断或部分限制同南斯拉夫(1948年)、阿尔巴尼亚(1960年)、罗马尼亚(1962年)等国的经贸往来。一般而言,以威慑为目的的制裁要取得成功,必须目标明确、手段可靠、结果可信。除非遏阻的是一项明确、具体的行为,否则很难衡量经济制裁的威慑作用。(23)
其三,强制(coercion)或胁迫(compellance)。即迫使目标国放弃或取消某项侵害或不受欢迎的行为。例如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对日本的制裁措施,目的是试图扭转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扩张步伐(然而美国最后采取石油全面禁运这一最严厉的措施,结果不过是使日本决心孤注一掷)。(24) 强制与威慑有时被研究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强制旨在扭转对手已经采取的行动,而威慑旨在遏阻某项尚未开始的行动。
制裁国希望强制改变的行为种类繁多,目标可大可小,从一项具体的行动(如恢复谈判或释放人质)到较大的政策变化(如撤出军队或停止敌对状态),直至寻求政权变更。同样,实施强制的国家必须使目标国确信,制裁对后者造成的损失将超过其从现行政策中获得的收益。但由于扭转一种行为(特别是放弃已到手的利益)比阻止一种行为难度更大,历史上此类案例的成功率较低。强制的目标越大,成功率越低,而且一旦失败便只有三种选择:放弃制裁、勉强维持无效的制裁以及诉诸战争。(25) 如果目标国实力雄厚或者能够自给自足,要迫使它放弃核心利益,或者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是完全不现实的。
其四,显示决心。即向目标国、国际社会或国内选民发出坚决维护某种利益或原则的信号。首先,制裁可以用来向目标国显示决心,即为了惩罚违反国际规范或破坏国际安全的行为,制裁国愿意承担制裁的经济代价。其次,发起国通过制裁某些受到国际舆论广泛谴责或抵制的国家,还有助于维护或提高其国际地位与声誉。最后,通过制裁来展示某种道德和心理优势,还可以塑造和主导国际舆论,使其他国家不敢轻易与被制裁国合作,以免形象受损。例如,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威望和“领导”地位,经常感到“有义务”动用制裁手段去纠正别国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发起国主要考虑的不是自身或目标国的经济损失程度,而是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此外,制裁还可以带有国内政治目的,如通过满足公众要求有所作为的呼声,争取选民或者缓解民众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批评。例如,20世纪30代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之时,正值英国大选前夕,面对公众舆论压力,英国政府不得不决定对意实施制裁。正如当时英国反对党领袖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所言,就拯救阿比西尼亚而言,英国的制裁其实已为时过晚,但是对挽救英国政府来说却恰逢其时。(26)
上述经济制裁的一般目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实际上,一项制裁政策往往包含多重动机。例如,“惩戒”本身就意味着警告潜在的效尤者,这就包含了“威慑”的意图。再如,1979年美国对苏联的经济制裁,既有胁迫苏联改变政策的目的,又有惩罚与威慑的意图。(27)
制裁的具体目标则可以多种多样。例如,美国在1993-1996年期间,曾60次通过立法对35个国家进行过制裁,制裁的主要动因包括:促进人权和民主(22次)、打击或者威慑恐怖主义(14次)、限制和阻止核扩散(9次)、制止毒品交易(8次)、维护政治稳定(8次)以及改善工人劳动权益(6次)。(28) 而且,有时候那些公开宣布的目的未必就是真正的或唯一的目的。例如,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期间,除了使人质获释这个公开、直接的目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恢复公众对卡特总统执政能力的信任。
经济制裁的动因在冷战后正日趋复杂化。在全球化不断深入、战争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的情况下,经济制裁作为替代手段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其中既有直接、近期目标,如制止侵略、解决地区或国内冲突、结束军人统治、恢复被剥夺的权利、中止武器计划、应对人道危机;也有许多中长期目标,如减缓武器扩散的步伐、反对恐怖主义、削弱敌对国家的影响力或改变其政策方向,乃至推广自身意识形态与价值标准,塑造或维护国际秩序与规则。(29) 这也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对经济制裁情有独钟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制裁的一个常见但未必总是公开的意图,是颠覆目标国政权或改变目标国现行体制,即通过制裁使目标国领导集团内部分裂、发生内乱或政变,最终导致该国政权垮台或社会转型。例如,苏联希望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制裁迫使铁托下台;美国对古巴、伊拉克、海地、塞尔维亚乃至朝鲜的制裁,都包含着诱发政权变更的意图。这类制裁的逻辑是,如果目标国政府的执政基础脆弱,让民众遭受巨大痛苦,就有可能使他们在绝望中起而推翻现政权,或者为反对派提供政变或改革的理由。然而,单靠制裁实现此类目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民族国家在面对诸如经济制裁等外来压力时,政府很容易获得道义优势,加上政府控制的舆论机器的强大影响,反对势力不仅很少能对该政权构成致命威胁,相反却可能被描绘为国外敌对势力的傀儡,而反抗制裁的领导人则可能被塑造为“民族英雄”,从而形成举国一致抵抗制裁的局面。
如前所言,“制裁”一词在产生之初,即具有明显的伦理内涵,反映了制裁发起者自信拥有的道德优势。当制裁成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之后,政治动因无疑占据了首要地位。惩罚、威慑、强制等制裁目的或制裁动机,就其实质而言,仍然不过是为了达到某种现实政治目的的手段。但政治目的(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本身不仅主观上仍然需要寻找道德支撑,客观上也不得不面临道德评判。不仅如此,在冷战后还出现了一类直接以道德目标为理由的制裁,即与“人道主义干涉”有关的制裁。当然,此类目的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
很明显,制裁的目的与手段和效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一项制裁行为的分析与评判,既要分析主观动机,也要考虑客观结果,此外,手段的选择也不可忽视,而不能仅仅将结果作为成功与否及合理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样,对于制裁的结果或功效的评判,不仅要考虑其经济与政治后果,也要考虑其道德后果。
四、经济制裁的政治功效与道德后果
经济制裁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效的外交工具?对此主要有两种意见。虽然很少有人无条件地肯定制裁的功效,但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制裁总的来说是富有成效的,或者说其失败并不是必然的。(30) 例如,加里·赫夫鲍尔(Garry Hufbauer)等人对经济制裁做过一项著名的实证研究,他们分析了1914—1990年间的116次经济制裁案例,认为其中有40次是成功的,约占34%;但另一派学者则认为,经济制裁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外交手段,多数制裁过程旷日持久,效果与期望值相距甚远,对目标国精英阶层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许多制裁都是“无果而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就是持此类观点的代表之一。他对赫夫鲍尔等人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认为在这40项所谓成功案例中,能经得起严格审查的只有5例,还有3例不确定。换言之,其成功率只有4.3%。(31) 如此高的“失败率”,意味着所谓“经济影响力”大部分时候不起作用,根本无法用来有效处理和解决国际争端。
造成上述分歧的一个原因是对经济制裁的定义不同,一个较狭窄,一个较宽泛,成功的标准因此也不同。(32) 正如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所指出的,佩普的定义过于狭窄,因而把成功的标准限定为目标国对制裁国的主要要求做出重大让步,这样成功就只有两种可能的值:1(成功)或0(失败),没有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效果类型或层次。(33)
但双方评判制裁功效的眼光其实都很狭窄,即仅仅从制裁国的立场和功利的角度看问题。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制裁这一外交工具的实际价值,至少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如果从制裁国的立场以及功利的角度看,成败与否当然要看制裁国所追求的主要政治目的是否得到实现;而如果制裁包含多重目的,结果当然就可能有完全成功(失败)与局部成功(失败)之别;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或者站在国际社会的立场上看,则必须对制裁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无论制裁国有意还是无意造成)以及制裁本身的性质做全面的分析。这就不仅要考察其经济、政治后果,还要评判其伦理后果;不仅需要借助工具理性,也需要价值理性。道理很简单:即使制裁国达到了它自己预期的目的,也可能同时还造成了其他严重后果,或者国际社会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经济制裁的基本逻辑是:经济压力—经济困难—社会压力或政治动荡—政策行为改变。(34) 这种因果逻辑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忽视了民族国家这一制裁对象的一些重要特点,例如民族主义对外来压力强有力和近乎本能的抵制、现代国家管理体制化解内外困难的能力以及统治精英转移矛盾、转嫁危机与负担的巨大空间。(35)
尽管研究者们对经济制裁褒贬不一,但一般都承认,经济制裁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若干条件。(36) 这些条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第一,与制裁国相比,被制裁国一般在经济上要更为脆弱,政治上更缺乏稳定性。成功的案例表明,制裁国(通常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往往比目标国大得多。在80%的成功案例中,其国民生产总值是被制裁国的10倍以上,在半数以上的案例中超过100倍。(37) 尽管这并不表明制裁国的经济实力与成功率是成正比的,但不难发现,对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实行制裁的成功率是很低的。
第二,被制裁国与制裁国在经济上处于高度依存甚至依附关系。一般来说,双边贸易关系越密切,制裁的影响就越大。在有效的制裁案例中,目标国大多在贸易上对制裁国有依赖。(38) 通常,最容易受影响的是依附经济大国的经济“卫星国”,其大部分进出口贸易都是与大国进行的,但这种交易量却只占大国总交易量的极小部分。
第三,制裁的施加必须迅速、果断,才能提高政治可信度与经济损伤力,否则目标国可能通过有效调整或采取反制措施来适应或化解困难。许多人以为,经济制裁与政治动荡之间有某种因果联系,受制裁的范围越大,政治上就越发不稳定。但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指出,这种“幼稚的”观点忽视了“适应性”这个简单的道理,即目标国会逐步适应困难,随着时间的延长,制裁效果将逐渐接近某种极点或“上限”,一旦达到这个上限,制裁目标将越来越不容易实现。(39) 古巴、利比亚、伊拉克等案例表明,长期制裁还会造成“制裁疲劳症”,使国内外的支持热情消退。(40)
第四,制裁对目标国造成的经济破坏必须足够巨大。有人认为损失通常要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41) 按照制裁的基本逻辑,如果不能造成任何损失,也就谈不上影响目标国的任何政策。一般而言,制裁造成的损失越大,可能带来的政治收益也越大。
此外,制裁的成效还与多边(包括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内)参与的程度有关。当事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参与,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制约目标国寻求替代资源的能力,还可以对其造成更大的政治与心理压力。例如,在国际社会为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对南非实施全面制裁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大国众多公司纷纷从南非撤资,从而增强了制裁的效果。(42) 相反,如果制裁缺乏第三方的合作,甚至面临第三方的抵制,例如向被制裁国提供经济援助,则制裁效果将大打折扣,乃至归于无效。
经济制裁的成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上述条件只是其中较突出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涉及制裁的经济效果。更重要的是,即使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并不等于制裁就是成功的,还要看政治目标是否实现,即是否导致了制裁国所预期的政策调整或行为改变。然而,尽管经济“大棒”可能对目标国造成某种损害,这种后果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预期的政治效果。从经济效应向政治效应的转化通常还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目标国国内社会的开放程度、制裁国所提要求的范围和重要性以及多边参与的程度。(43)
首先,相对而言,民主、开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比社会开放度较低、经济集中、政治集权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制裁的影响。(44) 例如,军人政府和独裁政权很少受民意影响,经济制裁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再如,美国对伊拉克的全面经济制裁尽管对该国民众造成了巨大灾难,但不仅对萨达姆及其复兴党高层的生活影响不大,也未能通过制造社会压力迫使萨达姆下台。
其次,经济制裁一般只能在非核心利益上使目标国屈服。(45) 制裁一旦威胁到目标国的生存与安全等核心利益,往往会遭到殊死抵抗。此时,强大的国内凝聚力和顽强的抵抗意志将弥补目标国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和不对称性。例如,美国的制裁无法搞垮古巴卡斯特罗政权,无法阻止巴基斯坦的核计划,甚至无法使利比亚在洛克比空难问题上屈服。(46)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尼加拉瓜的制裁之所以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该国认为其主权受到了严重危害。
最后,与经济上的成功类似,政治成功同样有赖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支持或参与。国际社会的支持不仅可以提高制裁的可信度,还将增强其合法性,从而使目标国统治精英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相反,如果缺乏国际社会的合作,不仅会降低制裁的效率,甚至可能削弱制裁国的信心。例如,美国对古巴的制裁不仅得不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还遭到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谴责甚至抵制,其效果可想而知。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制裁很少成功。(47)
衡量经济制裁的成败得失,如果仅仅着眼于直接的经济与政治目标,显然过于狭窄和短视。因为这不仅忽视了制裁所产生的各种副作用,也忽视了制裁的后续效应及其对国家间关系的长远影响。实际上,经济制裁特别是理由不充分或措施失当因而其正当性引起争议的制裁,有时不仅徒劳无功,还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例如对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导致各方军力失衡、冲突加剧,对巴基斯坦核问题的制裁反而增加了其安全担忧。不仅如此,制裁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使大量普通民众成为牺牲品,例如,在伊拉克导致的人道灾难举世震惊,在海地还引发了困扰美国的难民潮。(48) 因此,经济制裁的道德后果同样不可忽视。近期经济与政治目标的实现并不足以证明制裁就是成功或值得的,更无法证明制裁就是正当、合理的。
在国际竞争中,有关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对相关各方的动员能力、道德自信心或情感认同往往有巨大影响。在冷战后时期,无论是当事双方还是国际社会,都越来越重视经济制裁的道德后果。制裁国试图通过避免或妥善解决经济制裁可能造成的道德危机,来保证制裁的效果,目标国则充分利用制裁所导致的道德后果来争取同情,抵制制裁。例如,1988年美国对巴拿马独裁政权的全面制裁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裁所带来的痛苦被统治者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使民众苦不堪言,从而使美国陷入道德困境。在制裁无效的情况下,老布什政府于1989年12月发起所谓“正义行动”,推翻了诺列加政府。
事实证明,经济制裁的道德影响几乎都是消极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49)
第一,制裁可能加重目标国民众的苦难,甚至导致严重的人道灾难。冷战后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伊拉克。对伊长期、全面制裁,使伊拉克民不聊生、社会状况急剧恶化。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这种境况与伊拉克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两伊战争的创伤以及盟军对伊打击等因素有关,但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制裁是直接导致严重人道灾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制裁也在塞尔维亚、海地等地造成了类似的惨剧。虽然在南非、海地有部分民众对制裁持欢迎态度,从而增加了制裁的道德“合法性”,但是在更多时候,目标国民众对制裁非常反感,他们对制裁的后果也毫无准备,更无法靠自身力量克服这些灾难。
经济制裁的支持者往往争辩说,制裁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并非实施者的主观故意,也在所难免。然而,无论那些难以确认的动机多么“良善”,毕竟无法取代客观事实。随着制裁事例的增多,对不断出现的类似灾难视而不见,在道德上显然越来越站不住脚。经济制裁的支持者还有一种“替代合法论”,即认为得到联合国授权的经济制裁是军事行动的一种更加“温和”的替代手段,与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相比,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制裁所造成的人道困境在伦理层面是可以接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以伊拉克为例,海湾战争期间的军民死亡人数大约为45 000人,而仅战后最初几年因为经济制裁而死亡的儿童就高达50余万。(50)
第二,制裁给国际人道主义救援造成了困难。全面的经济制裁要求阻碍所有货物的流动和运输,从而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为了避免惨剧再次发生,国际社会设计出“人道主义豁免(humanitarian exemption)”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道德困境。所谓“人道主义豁免”,就是将人道主义物资排除在制裁物资的清单之外。其设计者们希望,这样可以将制裁的政治目标与保护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权利两者兼顾起来,从而使制裁的道德基石更为稳固。
问题在于,何种物资属于“人道主义豁免”的范畴?给大众的食物,给婴儿、孕妇和老人的食品供给显然符合这一标准,而奢侈品、酒精或香烟大概不在“豁免”之列。但是,种子、农用工具、化肥、杀虫剂等这些食物生产的必要工具呢?至关重要的药品,比如对婴儿接种的疫苗、医院给肾病病人做透析的仪器以及手术必需的血浆呢?救援组织提供的那些“军民两用”的仪器呢?大桥、发电厂、水电站以及教育设施等人们赖以维持生存、健康和发展的基础性设施是否也应该“豁免”?在实践中,这些东西往往都在制裁国的目录之中,因为控制这些物资有助于保证制裁的效果。联合国或国际社会都没有制定出一套公认的人道主义物资清单。出于政治利益考虑,制定出的豁免物资条款往往种类单一、数量有限,而人道主义救援需要的是一套范围更广泛的条目。联合国管理上的弊端也非常突出。安理会每次制裁时都会建立一个制裁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会制定出一套制裁标准和程序,结果让国际社会和救援组织无所适从。总之,“人道主义豁免”问题的提出,有时不仅没有缓解人道危机,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国际社会亟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豁免机制,以保证救援工作的有效展开。
第三,制裁可能使人道主义活动政治化。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不仅受到体制能力的限制,还面临着救援被政治化的障碍。“人道主义豁免”问题就常常因为政治化而背离人道主义的目标。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制裁委员会内部的利益分歧,都使得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举步维艰。例如,联合国安理会曾试图通过“石油换食品”计划来缓解伊拉克境内的人道灾难。(51) 但是,由于担心削弱制裁的功效,美、英对该计划限定了严格的附加条件,使得伊石油出口所得绝大部分被美、英控制的制裁委员会截留,伊拉克仅获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道主义物资。
实际上,如果制裁发起国为救援组织提供更好的条件并给予信任,支持它们救助那些因为制裁而濒临死亡、饥饿以及被疾病困扰的人民,不仅可以减少目标国民众的痛苦,也有助于缓和他们的敌视情绪,这也许比一意孤行地全面制裁,以至于成为目标国“全民公敌”,结果要好得多。然而,国际救援活动常常处在制裁发起国与目标国的两面夹击之中。制裁国常常将救援活动视为破坏经济制裁功效的一种不合作行为;目标国民众则可能将愤怒与不满转移到救援工作上。比如,在塞尔维亚的救援工作就丧失了民众的信任,人道主义组织被认为是站在敌对方一边。救援活动的政治化也削弱了那些协助发起国进行制裁的盟国的人道义务。由于救援活动并非权责分明的义务,参与制裁的国家既要考虑目标国民众的苦难,又要兼顾与制裁发起国的关系,在权力政治的支配下,自然都是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再决定是否及如何给予援助,从而导致救援工作效率低下。
毋庸讳言,经济制裁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与一再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经济制裁低下的效率和严重的道德后果使人们在质疑其有效性的同时,也开始怀疑其作为外交工具的合理性。显然,不加分辨地认可一切制裁,可能导致制裁被滥用或误用;简单化地摒弃一切制裁,则又可能使一些极端的不正义现象得不到匡正,或者使武力成为唯一的选择。(52) 面对种种困境,国际社会不仅应该努力探明成功的制裁必须具备的条件,还应该就正当、合理的制裁确立相应的原则与规范。
五、国际“正义制裁”的原则与规范
迄今为止,有关经济制裁的理论模式或政策建言大多仍着眼于如何提高其政治功效,对于冷战后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和广泛争议的经济制裁的道德后果与正义性问题,不是避而不谈,便是解释乏力。然而,国际规范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正当性,制裁本身的有效性也常常取决于其合理性。与所有政治行为一样,无论经济制裁的政治理由如何充分,其在目的、手段和效果等方面的正当性都不可避免地还要面临伦理道德层面的评判。对于经济制裁,不仅要从功利的层面关注其有效性,即何种条件下经济制裁会取得成功,还要从价值的层面思考其合理性,即何种条件下实施制裁才是正当的,对于具有国际干涉性质的制裁而言,尤其如此。
对国际政治的伦理分析,通常需要借助某种伦理传统来进行。经济制裁实际上是战争的一种替代手段,或者说是诉诸战争与采用非强制性手段之间的一种折中选择。显然,经济制裁与战争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手段,发动战争的前提与运用经济制裁的前提可能大不相同,战争与和平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因此,有关“正义制裁”的思考,不能简单套用“正义战争”的原则。不过,就它们的政治从属性以及人类道德评判的根本尺度而言,制裁与战争又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两者都是国家行为,都是政策工具,都是对抗活动,都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其目的、手段和后果都将面临道德审视。由于制裁是仅次于战争的对抗手段,决策环境也具有相似性,因此,“正义战争”的分析框架与基本原则可以作为探讨“正义制裁”问题的一个起点和参照。
“正义战争论”主要围绕“开战正义(jus ad bellum)”和“交战正义(jus in bello)”这两大传统范畴来展开道德分析和论辩。(53) 前者主要通过考察战争的理由来判定战争本身是否正义;后者主要通过考察遵守或违反战争惯例或规则的情况,来判定战争是否正义地进行。(54) 按照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看法,两者在逻辑上是独立的,彼此不构成充要条件,正义的战争也可能不正义地进行,反之亦然。(55) 参照这一分析框架,“正义制裁”理论至少也包括两大内容:诉诸制裁的正义(正义的制裁)与实施制裁的正义(制裁中的正义)。
首先,关于“诉诸制裁的正义”。在正义战争论的相关原则中,值得参考的主要有六项:合法权威、正当理由、正当目的、相称性、成功可能性和最后手段原则。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竞争性经济制裁”,合法权威同样只能是主权国家,尽管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可能参与。然而,具有国际干涉性质的经济制裁,必须是基于国际社会共同意志并出于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目的。在实践中,这种制裁的合法性来源只能是联合国的授权,而不是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以对南非的制裁为例,虽然众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参与了制裁活动,但是联合国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个国际社会唯一“合法权威”的存在,不仅协调了各方的制裁行为,保障了制裁的有效性,而且确保了制裁始终围绕取消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正义目标进行。
正当目的和正当理由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正当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称为正当理由的主观方面,但正当理由的存在不一定意味着正当目的的存在或实现,反之亦然,因此有必要将它们视为各自独立的道德原则。(56) 以“正当理由”而论,至少“自卫”可以构成战争的一项较少争议的理由,甚至可以说,只有自卫才能证明战争的正义性。同样,如果制裁是出于自卫的目的,比如,捍卫本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便具有正义性。如果发起国是为了实现某种私利,只因战争时机不成熟才采用经济制裁手段,这种目的便无正义可言。
但经济制裁的理由或目的在实践中远非如此简单。根据正义战争原则,理由或目的是否正当,还与“相称性”有关。例如,A国侵犯了B国领土,B国就有夺回土地的正当理由,但根据相称性原则,B国的目标应限于收复失地,而不是无限制的报复。该原则的意义在于对拥有正当理由一方的战争动机或目的提出道德限制,以防止因为“得理”而追求不正义的目标。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济制裁,例如以反恐、防扩散、人权等为理由的干涉性制裁,如果追求目标国政权变更的目的,其正当性就很可疑,也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在当代,如果制裁是为了惩罚破坏国际秩序与稳定的行为,或者为了制止肆意践踏人权等国际社会珍视的共同价值,一般也被视为正义的行为。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多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可以构成制裁的理由?如何对待多重制裁目标交织的“动机不纯”现象?总之,在当代,最有争议的是那些具有国际干涉性质的制裁。
“成功的可能性”显然与制裁目标的大小和性质有关。无疑,只有当政治目标有可能借此得以实现时,制裁才有意义,但这种可能性还取决于政治目标的性质。例如,以威慑或强制为目标的制裁,其成功标准是有效遏阻或改变了目标国的政策或行为。如前所言,如果制裁国的要求危及目标国的国家安全、政权稳定等核心利益,就很难成功。
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制裁成功率不高,必须慎用的话,那么“最后手段”原则(尽管词不达意)在此仍有参考价值。只有在除军事手段之外的其他外交工具都尝试过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种“倒数第二”的经济威慑手段,也只有这样才可以降低制裁的道德成本。如果经济制裁还不如发出外交照会、撤回驻该国大使等其他手段管用的话,那么使用制裁就是不合理的。
其次,关于“实施制裁的正义”。正义战争论关于“交战正义”的两条核心原则在此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区别原则(discrimination)和相称性原则(proportionality)。正如战争伦理所强调的,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必须正义地作战,“相称性”和“区别”原则同样是制裁是否“正义地进行”的关键,也是关于制裁伦理最为复杂和棘手的问题。
“相称性”在此意味着手段与目标必须相称,制裁带来的善必须大于所造成的恶,以避免极端的伤害。这一原则实际上也适用于“诉诸制裁”阶段,即在制裁前需要对代价与收益进行权衡,只有当预期普遍利益符合正当理由,且大于预期普遍代价时,才具有正当性。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取消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与道德价值大于制裁给南非民众造成的痛苦。何况国际社会还努力运用了“区别原则”,即将制裁矛头直指白人统治者。
“区别”原则要求将“肇事者”或统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使制裁在有效惩罚“违法者”或责任人的同时,尽量避免伤及无辜。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性,这种区分在实践中相当困难,构成了制裁中最大的道德两难问题:从道义上看,某些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犯下的错误不应由全体国民来承担后果,应该承担痛苦的是那些对国家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统治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但从作用机制上看,制裁很难对统治者或政治精英产生直接作用,而主要通过给民众造成痛苦来培育社会压力从而影响政府行为,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不仅如此,即使在战争问题上,“区分原则”本身也曾遭到非议。一些人认为,国家公民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公民对国家负有责任和义务,应该分担国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57) 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决策精英与普通民众在政治能力与政治责任上的重大差异。进一步推论,“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的民众各自所负的责任似乎也应该有所不同,但事实上,遭受最大痛苦的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他们对政策几乎毫无影响力。总之,当代经济制裁的倡导者所设想的“针对性”在实践中很难贯彻。
“区分原则”的贯彻尽管相当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例如,为了将制裁对普通民众的伤害降至最低限度,或者避免统治者转嫁灾难,使民众成为“替罪羊”,制裁措施可以有所选择,例如,将贸易、商品禁运的范围限定在军事、战略物资以及与上层、权贵有关的奢侈品方面,而不是盲目进行全面制裁。即使是全面制裁,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人道主义物资也应该得到“豁免”。例如,在对伊拉克的制裁中,联合国安理会第661号决议就规定,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物资和食品应严格实行进口豁免。虽然人们对“人道主义豁免”的内容有不同看法,但对于食物、药品等维持基本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并无异议,即便是对萨达姆政权恨之入骨的美国政府也规定这类物品可以豁免。人道主义物资的禁运与武器禁运、金融制裁、交往制裁等属于不同的道德范畴。后三者在实行时,人民的基本生活仍可以维持,但对食物、药品等基本生存物资的禁运无异于“向妇产科医院释放毒气”。(58) 例如,因为缺少医药和食品,伊拉克儿童成了制裁的最大受害者,每年死于饥饿和疾病的儿童多达数十万人。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也不难证明,豁免范围还可包括公共卫生、公共服务系统的设施等。以伊拉克为例,由于电厂、医院等在战争中大量受损,又因制裁的影响而无法修复,导致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下降,结果造成死亡和营养不良的人数急剧增加,而这一后果对于实现制裁的政治目的而言毫无意义。
以上说明,“正义战争”理论可以为思考“正义制裁”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如果比较一下南非和伊拉克这两个制裁案例,不难发现,前者更符合“正义制裁”的基本原则与规范,而后者却最终背离了这些原则,因而成为冷战后历时最长(1990-2003年)、范围最广、人道灾难最严重的经济制裁。最初由联合国主导的对伊制裁是为了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其目的具有正义性,并得到了普遍支持。1990年联合国安理会第661号决议还包含了区分原则,即对人道主义物资实行“豁免”。因此该阶段的制裁是合理、有效的,也没有引发严重人道危机。但战争结束后美、英仍想以经济制裁为手段迫使萨达姆下台,并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口实维系制裁,结果酿成重大灾难,战争手段的最终使用也意味着制裁的完全失败。
但制裁与战争毕竟有很大区别。传统正义战争理论并不能解决经济制裁所面临的许多特殊难题。首先,关于经济制裁还存在着许多似是而非的流行观点。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目标国民众和社会各阶层均支持现政权,且对引发制裁的政策负有一定责任的话,那么制裁及其所造成的痛苦就具有合理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战争造成的直接伤亡不同,如果将制裁范围限定在特定阶层之内,并通过相应的人道主义救援将消极后果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那么制裁在道德上也是允许的。这类观点不仅具有片面性,在实践中也很难准确把握。
其次,经济制裁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即制裁对非目标国造成的连带经济影响。如果说通过“正义战争”来矫正触犯国际法的行为,其惩罚范围原则上只限于目标国本身,战争后果的外溢效应既非主观故意,也不具有必然性,经济制裁则不然,贸易禁运一旦实施,与目标国有密切贸易关系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经济损失,而要保证制裁的成功,这类损失似乎又是必要的代价。这就难免会导致利益分歧。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就曾表示,制裁的代价应由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而不应完全由邻国或与目标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承担。(59) 《联合国宪章》第50款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但目前尚无任何固定机制和程序来妥善解决。
减少对第三方的伤害对于提高制裁的效率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目标国的邻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支持,制裁无法奏效。以对伊拉克的制裁为例,约旦、土耳其作为伊拉克的贸易伙伴国,为了维护制裁令不得不中断与伊拉克的贸易来往,一些对伊出口企业因此停产,在伊拉克打工的约旦、埃及和叙利亚公民也不得不撤回国内,造成本国就业压力陡增,导致这些国家对制裁令怨声载道。此外,制裁还影响了世界能源供应。因此,对于配合制裁行动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应该设法给予适当的补偿。(60) 至于美国那种为了强迫第三方国家支持制裁而使用或威胁使用“次级制裁”的蛮横做法,只能激化反美情绪。(61) 总之,制裁的外溢效应不可低估,这不仅事关制裁的合理性,也影响其有效性。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日益盛行的干涉性制裁,其复杂性并不亚于干涉性战争。传统的经济制裁主要是出于国际权势斗争与利益角逐的需要,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战略性、政治性举措。在无政府国际体系内,这类制裁行为尽管很难约束,其性质相对而言却不难判断。然而,干涉性制裁特别是所谓“人道主义制裁”(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吊诡”。由于国家这一制裁对象的复杂性,伤及无辜几乎在所难免,而剥夺无辜者的权利很难被称为是“人道的”),一方面主要由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倡导或发起,具有大国权力政治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被罩上了维护国际稳定、捍卫普世价值的耀眼光环,因此性质更加复杂,争议也最大。人道主义动因与政治动因往往难以平衡甚至难以区分。人道主义目标常常不得不让位于政治目标,甚或成为后者的道德外衣。因此,国际社会在确立有关“正义制裁”的原则时,必须将约束和规范干涉性制裁行为作为一个重点。否则,就像美国对伊拉克、波斯尼亚、海地的制裁所表明的那样,经济制裁不仅有可能失败,而且这种失败可能成为战争的借口,或者制裁本身不过是想为武力解决扫除舆论障碍,如此一来,制裁就成了战争的前奏而非替代。(62)
由于经济制裁的概念、类型、性质特别是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等问题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国际社会相关法理与伦理规范很不健全,在实践中还导致许多认知错误。例如,2010年2月,针对美国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中国政府宣布将对参与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一举措就遭到一些海外舆论的误解甚至指责。有人认为,中国一向主张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不主张采用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强制手段,而这回却打算启用制裁手段。言下之意是有奉行“双重标准”之嫌。这不仅颠倒了是非,也混淆了制裁的性质。中国并非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制裁,只是强调要严格界定其实施条件,特别是要谨慎使用干涉性制裁,尤其反对将经济制裁作为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手段。美国对台军售恰恰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是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当事国,采用制裁手段的目的是反干涉,无论成效如何,其性质不容扭曲。
总之,在确立经济制裁特别是干涉性制裁的国际规范及其实践等问题上,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主要体现,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六、结论
对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制裁问题,可以得出几点基本结论。首先,由于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深,各国的经济脆弱程度也越来越大,因此,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工具,被赋予越来越大的价值,其使用也更加频繁。但事实上,就实现政治目标而言,经济制裁即使不是完全无用,其成效也是相当有限、很不确定和有条件的。其次,经济制裁在冷战后已经由一种传统国家间对抗工具演变为一种国际干涉手段,其政治动因和伦理原则都日趋复杂化。但恰恰是这种“干涉性制裁”,其有效性与合理性却更难保证。众多事例表明,经济制裁不仅较少达到预期目的,还时常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与人道危机。最后,面对经济制裁的局限性,特别是其中的政治与伦理冲突等两难困境,国际社会亟待确立和完善有关“正义制裁”的国际规范,明确区分经济制裁的不同类型与性质,严格界定其实施前提、执行主体以及手段和目标,以保证其合理性与有效性,避免制裁手段的滥用或误用。
判断经济制裁是否正当、合理,除了考察伦理判断通常关注的三大要素,即制裁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的基本性质,还可以参照“正义战争”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基本原则,从经济制裁的启用、实施过程(以及后续措施)等几个阶段来加以具体分析并建立相应的国际规范。制裁本身的有效性就常常取决于其合理性。国际规范的有效性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正当性。在当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背景下,关于“正义制裁”的国际规范至少应坚持两项基本原则:一是首要价值标准。除了当事国和实际影响都完全限于双边关系等少数例外,对于具有国际干涉性质的制裁行为,其价值尺度是必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人类和平发展的目标,而不是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的价值观、政治目的或利益需要。二是主要合法性来源。同样,除了当事国反对侵略或避免直接、重大伤害等少数例外,必须坚持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主义原则,体现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在此前提下,国际社会还需要逐步完善联合国制裁机制,使经济制裁真正成为政治上可取、经济上可行、道德上正当的一种外交工具。
[收稿日期:2010-05-07]
[修回日期:2010-07-05]
注释:
①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冷战后时期。其中,自1985年初版以来引起广泛争议的一项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成果参见Gary Clyde Hufbauer,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Washington,D.C.:IIE,2007;关于美国制裁中国、古巴和伊朗的案例研究参见 Hossein Askari,et al.,Case Studies of U.S.Economic Sanctions,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3;通过研究冷战后美国对八个国家的制裁案例并得出若干经验教训的一项重要成果参见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8;案例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并就经济制裁的成效、困境等提出许多独特见解的佳作参见Daniel Drezner,The Sanction Parado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对改良联合国制裁机制的探讨参见 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Lopez,Sanc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Security:Challenges to UN Action,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2;对所谓“灵巧制裁”模式的集中探讨参见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Lopez,eds.,Smart Sanctions:Targeting Economic Statecraft,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2002;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运用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进行分析的一项尝试参见 Robert Eyler,Economic San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中国学者有的是从美国冷战战略的角度入手,如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曙光的《经济制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主要内容也是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制裁,但也有许多理论思考。有的则将经济制裁视为“负面的经济外交”纳入“经济外交”的框架内讨论,如周永生:《经济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总的来说,国内外绝大部分论著都是对战后以来美国和联合国各种制裁案例的经验性分析,理论性、综合性的研究较少,而且主要关注经济制裁的政治绩效而非伦理后果,这一特点在国内尤其突出。
② 张铭新:《(秦律)中的经济制裁——兼谈秦的赎刑》,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5页。
③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页;Gary Hufbauer,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pp.9-10.
④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⑤ 详见张曙光:《美国关于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对华禁运决策(1949-1953)》,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105-113页。
⑥ Robert Pa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2,1997,p.90.
⑦ 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Lopez,The Sanctions Decade:Assessing UN Strategies in the 1990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p.2;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1.
⑧ 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Lopez,Sanc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Security:Challenges to UN Action,p.1.
⑨ Suk Hi Kim and Semoon Chang,eds.,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a Nuclear North Korea,Jefferson:MeFarland & Company,2007,pp.104-114.
⑩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1.
(11) 《安理会制裁伊朗草案成型》,新浪网,2010年5月20日,http://news.sina.com.cn/w/2010-05-20/080117538228s.shtml.
(12) Margaret Doxey,International Sanctions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7,p.4; M.S.Daoudi and M.S.Dajani,Economic Sanctions:Ideals and Experienc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8.
(13) David Leyton-Brown,ed.,The Utili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7,p.7.
(14) William Kaempfer and Anton Lowenberg,“Unilateral versus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Sanctions:A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1,1999,p.55.
(15) Johan Galtung,“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 World Politics,Vol.19,No.3,1967,p.383.外交制裁包括:不承认受制裁的国家、中断与受制裁国的外交关系、断绝政治领导人的往来、停止与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等;交流制裁包括:中断电讯、邮件、交通以及人员交往(如旅行、访学、考察)等。
(16) David Baldwin,Economic Statecraf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20-40,90-114; Robert Pa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p.93.
(17) David Baldwin and Robert Pape,“Evaluating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2,1998,p.190.
(18) David Leyton-Brown,ed.,The Utili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p.11; M.S.Daoudi and M.S.Dajani,Economic Sanctions:Ideals and Experience,pp.4-5.
(19) David Baldwin and Robert Pape,“Evaluating Economic Sanctions,” p.190;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1.例如,2009年1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存在政府补贴为由,决定对其进口的中国钢管征收约10%-16%的关税,这项迄今最大的一起对华贸易制裁案就主要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20) 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Lopez,eds.,Smart Sanctions:Targeting Economic Statecraft,pp.1-2.
(21) James Lindsay,“Trade Sanctions as International Punish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No.30,1986,pp.155-156; M.S.Daoudi and M.S.Dajani,Economic Sanctions:Ideals and Experience,pp.161-162; Gary Hufbauer,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pp.5-7; David Leyton-Brown,ed.,The Utili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pp.298-306.
(22) Kim Nossal,“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s International Punish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2,1989,pp.301-322.
(23)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199.
(24) 详见何晨青、石斌:《错觉与战争的起因——兼论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的错觉因素》,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07-121页。
(25)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199.
(26) Gary Hufbauer,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Washington,D.C.:IIE,1990,p.3.
(27) Kim Nossal,“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s International Punishment,” p.316.
(28)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A Catalog of New U.S.Un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for Foreign Policy Purposes,1993-96,Washington,D.C.: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1997,pp.1-4.
(29) Gary Hut'bauer,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pp.9-19; 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Lopez,Economic Sanctions Panacea or Peacebuilding in a Post-Cold War World,Boulder:Westview,1995,pp.3-6; 张曙光:《经济制裁研究》,第10-12页。
(30) M.S.Daoudi and M.S.Dajani,Economic Sanctions:Ideals and Experience,pp.12-13; Daniel Drezner,The Sanction Paradox,p.321.
(31) Robert Pa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pp.90-136; David Baldwin and Robert Pape,“Evaluating Economic Sanctions,” p.195.
(32) 还有人指出,赫夫鲍尔等人的统计结论有两个缺陷:一是没有区分单边、双边和多边制裁;二是只关注公开宣称的政策目标。参见 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Lopez,The Sanction Decade:Assessing UN Strategies in the 1990s,pp.14-17.
(33) David Baldwin and Robert Pape,“Evaluating Economic Sanctions,”pp.191-192.
(34) Johan Galtung,“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pp.378-416; David Baldwin and Robert Pape,“Evaluating Economic Sanctions,”pp.193,197.
(35) Robert Pa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pp.93,106.
(36) Gary Hufbauer,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pp.55-63;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p.197-210.
(37) Gary Hufbauer,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pp.89-90.
(38) Robert Pa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p.109; Gary Hufbauer,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pp.90-91.
(39) Johan Galtung,“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p.388.
(40)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205.
(41) Gary Hufbauer,et al.,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pp.49-73.
(42) Mark Amstutz,International Ethics,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p.192.
(43) Mark Amstutz,International Ethics,p.178.
(44)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203.
(45) Robert Pa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p.109.
(46)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198.
(47)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200.
(48)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201.
(49) 详细的讨论可参见 Larry Minear,“The Morality of Sanctions,”in Jonathan Moore,ed.,Hard Choices:Moral Dilemmas i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8,p.235.
(50) Robert Po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p.110.
(51)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Iraq Programme,Weekly Update,August 22,2003,http://www.un.org/depts/oip/background/latest/wu030822,html.
(52) Thomas Weiss,“Sanctions as a Foreign Policy Tool:Weighting Humanitarian Impulse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6,No.5,1999,p.506.
(53) 在不同语境下也可表述为“诉诸战争权”与“合理交战权”,或“战争的正义”与“正义的战争”。此外,尽管“战后正义(jus post bellum)”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领域,但严格说来涉及的已不是战争本身,而主要是一些后续性相关问题,如战后秩序安排、对遗留问题的处理及其伦理标准。
(54) 参见张书元、石斌:《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述评》,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6-127页。
(55) 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New York:Basic Books,1992,pp.21,231.
(56) 参见张书元、石斌:《沃尔泽的正义战争论述评》,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6-127页。
(57) Michael Howard,“Can War Be Controlled?”in Jean Elshtain,ed.,Just War Theor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I992,p.30.
(58) Evans Clark,ed.,Boycotts and Peace:A Report by the Committee in Economic Sanctions,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33,p.257.
(59) David Cortright and George Lopez,The Sanctions Decade:Assessing UN Strategies in the 1990s,p.229.
(60)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201.
(61) Richard Haass,ed.,Economic Sanct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p.201.
(62) Robert Pa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p.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