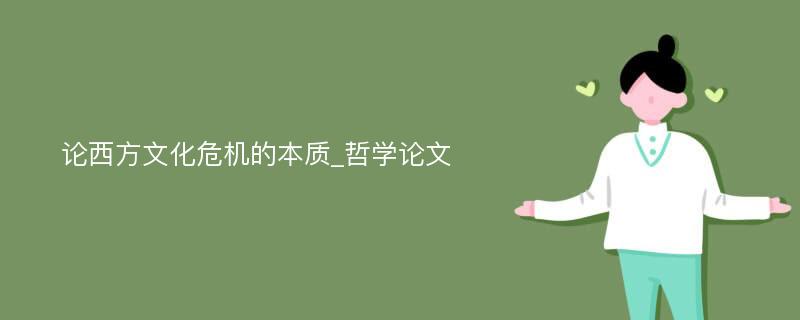
论西方文化危机的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质论文,西方文化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东、西方同时出现的文化“危机”有着复杂的表征和深厚的历史根源,理性失落、人的地位的下降、哲学的终结既为原因又是结果,这场危机实为人类文化转型时期的心理激荡,成功与灾难俱在。区域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文化的要求是危机导致的结果。
【关键词】 危机 实质 文化转型 多元化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东、西方同时出现了文化系统的混乱和反常,百家诸说纷然杂呈。尤其是西方,各种“主义”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最为本质的是“危机”感的日渐加强,反传统方法的视角逐渐拓宽深入,各种拯救方案交互缠结,成为人类文化史上十分奇特的人文景观。人类何去何从,如何对待历史,什么叫“后现代”,几千年的文化发展道路在何种程度上启示着未来,在批判性审查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所有这一切一经表现,就在浅层次上以各式各样的“危机”面貌出现。本文将透过这些过激的理论寻找人类文化尤其是近百年来的发展脉络,从而给下个世纪或更远的未来讨个可能的分晓,揭开这层历史的面纱。
一
西方思想家早就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尤其是作为文化基石的哲学危机的存在。胡塞尔说:“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①]科学(die wissenschaft)危机即是认知(wissen)的危机,即文化危机和它的核心——哲学危机,包括人类所有的知识,以及作为知识之超验依据的一切方面。
具体地说,就是哲学旨趣由理性到非理性的转变,在有识之士(或称守成主义者)看来,这意味着理性的“失落”,甚至“毁灭”,意味着西方人对自己数千年追求目标的怀疑、对理性的信仰崩溃。这种怀疑波及到了文化的每一个领域。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用理性的方法营建人类文化,披荆斩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泰勒斯到柏拉图,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儿,再到康德的开创性进展,最后至黑格尔而集大成。但是突然之间,这些成就都成了昔日黄花,理性坍塌了,从中分裂成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
现代哲学的开端就是哲学危机的开始,尼采最具代表性,他倡导“一切价值之重估”,高扬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精神),反对阿波罗精神(理性精神)。他斥传统为虚妄,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宣称上帝死了。传统哲学在尼采这里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喻示着整个20世纪的发展及各种“危机”的出现。
此后理性及传统哲学一再受到现代思想家的诟难。此前认为牢不可破因而精心营造的价值体系成了废墟,光荣的整体化时代被湮没在了激烈的批判之中,非理性主义通过各种主张——如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的以及后现代的思潮而泛滥成灾。用卢卡奇的话说,理性毁灭了,这种毁灭一再受到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的加剧,最终走向了毁灭一切、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本世纪残酷的现实和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复杂的文化矛盾给人们一种受骗上当的情绪,“愤怒的青年”受到愤怒的思想的感染,肆意、盲目、狂热地反抗着传统。人们不再相信理念、本质、普遍性、崇高理想,摆在人们面前的是空无、孤独、死亡、异化、技术的漫天统治。人们呐喊、绝望、歇斯底里、无所适从,这时各种短命的济世良方走马灯似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接着又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大幕之后,让人们更加不知所措。于是反传统成为时尚,危机与出路成为百年时髦的话题,这些莫衷一是的理论更加深了危机的感受。
二
西方哲学的危机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溯本求源方知其真意。概括起来,西方哲学危机的表现和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理性的绝对化 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可靠的途径(比如严密的逻辑推论)找到世界的最后原因和终极本质,水火土气、原子、理念、绝对精神就是它的初期表征。在这种思辨的追寻中的确曾经取得过重大的成就,因此人们把理性看作是终极的、绝对的、永恒的。一切都建立在理性之上,就连人的本质也由理性来界定,而被称为“理性的动物”。现代人认为,人们一直在围绕理性建立着虽不可能存在但仍为之努力不懈的理性世界。这是一种高贵的、超越性的目标,企图把一切都包容进去,力求一劳永逸地建立人类文化的万年基业。
这样一种理性的热望甚至是理性的迷狂,在文艺复兴及以后的历史的催化下变本加厉地发展。理性这种关于最高和最终的科学,享受着文化王国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它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活跃起来的哲学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它甚至相信,它已经发现了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方法,通过运用这种方法,一种在形而上学中达到顶点的系统哲学能够被构造出来,从而真正建成哲学的千年王国。”[②]这种思想可以在18世纪人们高昂的时代热诚中,在席勒——贝多芬辉煌的“欢乐颂”中,在黑格尔宏伟的思辨大厦的完成中找到不朽精神的充足论据。理性绝对化了,因而也异化了,它越出了自己的有效范围,离开了有所能为的土壤,走向无所不能的神话,走向僭越,也就走向了悲剧。理性因此倍受攻击,千孔百疮,开始了被西方思想家看作是孤魂野鬼式的飘荡,到今天仍还未能回到恰当的定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的失落。”
遗憾的是,理性无所不能的神话只是一种假定。从外在方面看,实证科学在理论上、实践上不断获得的巨大成功同理性的一再失败形成鲜明的反差,引起了普遍的深思和反叛。从内在方面看,理性过分的拔高使得它离真实的现实越来越远,也使人们对这种虚幻设计和概念游戏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厌倦、抗议甚至逆反情绪。现代哲学与相对应的主旨就是返古和归真——寻求真实,不加任何掩饰的真实。胡塞尔提出Lebenswelt(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Lebensform(生活形式)和the way of Living以及海德格尔对本真世界的追求,表明哲学只有在真实之中面对本真的存在体会真实存在(佛说真如)的意义。
现代哲学认为,人类在理性这个透明的玻璃瓶内走了几千年弯路,似乎看到了光明,却永远找不到出路。其原因就在于,首先,理性意味着对世界的总体把握,要求统一性、整体性。但这种冠冕堂皇的要求却是一种虚伪的专制,它淡化了人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同时,这种大一统容忍并且鼓励由一种虚幻假定向另一种虚幻假定无休止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它鼓励了对众多以差异为标志的存在理由的无情而“合理”的剥夺,成为理性专制、思想禁锢的文化暴政的崇高借口。尼采首先对此开战,他认为几千年来凡经传统哲学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他对西方一切价值之重估成了西方哲学危机的前奏和定音鼓。胡塞尔把实证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哲学危机直接划归理性的僭越。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理性核心的逻辑和以逻辑为支撑的科学主义,虽然曾一度被捧为价值的典范,但它的力量其实非常有限,真实世界远非逻辑能够包容。
经海德格尔考证,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是西方由古希腊向古罗马文化转变过程中的一场灾难性的误解,因为ratio一词其本意是“计算”,“ratio原本只是古罗马商业用语中的一个词汇,早在希腊思想向罗马认识转换时就已经被西塞罗所采用”[③]。这样,人的本质就被降为计算思维(caculating thinking),远离了反思(reflecting thinking)这一真正的本质。科学技术这种计算体系随之膨胀成评判一切的标准,包括人的意志、自由、灵魂。
西方哲学的危机首先就产生于对理性和科学的盲从与迷信。科学以纯粹的客观性为目标,也以此自高于其它文化形式,这本身没有什么可诟病之处。但科学主义或纯客观主义把这一点极端化、终极化,使科学乃至以科学为坐标的现实文化丧失了生活的意义。胡塞尔对此看得十分真切:“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④]科学主义排斥了主观方面的价值问题、意义问题。正如大物理学家海森堡所说,现代物理学家正在加深一种危险,使人们接受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却不知道这种看法只是物理学家的世界。不幸的是,人们对一元化思维方式的弊端全然不察,由此最终产生了现代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
2.人的价值和地位的下降 从古希腊的哲学觉醒时,人就被看作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把人们的视线从天上拉回到地上的自我以及自我的德性、灵魂,弘扬“认识你自己”的主体理性精神,唤起人的自我主体意识。至此,人被看作世间奇特的存在物。到文艺复兴这一以人道反神道、以人权代替神权的特定历史时期,人的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人被视为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人成了自然界的主人,乃至一切存在物的拥有者。这一成果被理性主义以哲学的形式固定下来,到德国唯心主义而功德圆满。从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先验论,经费希特“自我设定”的绝对主体学说,到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集大成,人的地位和价值被一步步拔高,几乎成了哲学本身,那么人的地位和价值的危机自然成了或至少带出了哲学的危机。
人的地位和价值最先与神的地位面临了共同的挑战。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在毁坏世俗神权的同时,也破坏以地球和地球上的人为中心的无上尊严,人以及人所在的位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众多星球、众多存在物中的一种而已,只是在哥白尼时代尚未得出这个仅隔一步之遥的结论。尔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边将自然神论驱逐到目的论的最后堡垒中,一边把人的优越意识撕个粉碎,人并不是直接由神造出来体现神的大全的高级存在物,而只是与虫子鸟兽同宗同源的“某物”。“太阳中心说”与“生物进化论”剥去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尊崇的外衣,使之逐渐下降。
上世纪末,从叔本华、尼采开始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多角度多层次地动摇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弗洛伊德通过对潜意识的精神分析,从内部揭示了人的存在不过是受“原欲”(Libido)支配的,处在冲动与压抑中的自然人格被分裂的可怜虫。存在主义认为,人被莫名其妙地抛入了这个世界,因此人的存在是非决定论的、荒唐的、无意义的;人的本真存在不是堂皇的理智状态,而是处于新旧意欲交替、烦恼、畏惧以及死亡的阴影之中的。以“解构”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更把上述种种彻底化以至虚无化。其相应理论(如果还剩下什么理论的话)就是反中心论(decentrism),反对男权中心、理性中心以及人类中心。继“上帝死了”之后甚至在文艺作品中发现“人死了”。按照德里达所说“中心不在现存在(present-being)的形式之中,”[⑤]那么“人”这个传统的文化中心(所以称作“人文”)这时彻底成了“空场”。
3.哲学的终结 面对分歧日益加深的各种人类共同的话题,面对各种绝对而有“理”的庞大体系,面对越来越多与温情的陶然自得的理论不相一致的穷途末路,人们预感到了文化分裂将在所难免。有的人开始以全面的反叛来代替反思,有的人以温和的改良来结束哲学史上的论战,有的人还以摆正传统为良方来重新设置文化的基准。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到哲学的地位与作用这个既外在又直接关涉到诸如本体论、知识论之类的核心问题上来。
自启蒙时代以来,特别是从康德以来,自然科学一直被看作是知识的范型,文化的其它领域必须依照这个范型加以衡量,“哲学受到如果不是科学就会失去威望与效准的恐惧之驱迫”[⑥],因此,经验论者以科学主义的纯客观主义为剃刀,砍掉了“由笛卡尔创始的、与牛顿力学同时被发展的一种哲学范式”(库恩语),接着进一步宣告哲学命题,尤其是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经验论者对哲学的传统进行盘点后,断然认定经营了数千年的哲学已经破产。
人本主义者大都是文化多元论者,一方面否定哲学的文化之王地位,如前所述,这只能产生一元的专制与暴政;另一方面也同经验论者一样,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传统哲学(主要是形而上学)的内在成分,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相继宣布形而上学或哲学的终结,其目的主要在于为新的思想开辟道路,海德格尔终生对这个“道路”青睐有加,它的起点就是形而上学终止的地方。德里达更把哲学的终结当作文艺理论的解放。
对哲学终结问题最为热心者莫过于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他从分析哲学阵营中超越出来,试图调解并融汇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他既不完全赞成哲学根本上是无意义的“胡说”因而“怎么都行”,又拒绝像德里达那样把形而上学与暴力相提并论,既反对涅盘一切、无节制解构一切的“后现代”操作,又审慎地看待似古实左的文化保守主义。他推行自创的“后哲学文化”主张,所谓“后哲学文化”,就如同文艺复兴以理性哲学代替经院神学而产生的“后神学文化”一样,是文化类型的历史鼎承,所不同的在于后哲学文化系统中没有像哲学在后神学文化中那样的文化法官,而是处于平等、多元对话状态下的新型文化。其原因就在于近代后神学文化中哲学的地位被过分拔高而失去了本来的定位。在罗蒂等现代反传统主义者看来,哲学本是对“智慧”之“爱”,但现在却僭越成了“智慧”本身。所以后哲学文化要求哲学“逊位”,还政于民主化的新文化系统。哲学不再有特权,甚至不再有方法与专业,它本来是、也只能是小写的哲学,而不再是以前大写的哲学,哲学家只“是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乐于对任何一个事物提供一个观点,希望这个事物能与所有其它事物关联”,因为“一个自由的文化必须尽可能让所有成员以其很不相同的声音表达其很不相同的愿望和目的”[⑦]。当然,哲学的归位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消亡,一如神学在后神学文化中的情形。这时哲学的功能不再是教训,而是教化。罗蒂接受了后期海德格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教化哲学”的思想,主张教化就是批判性、建设性的文化图景的重构,它拒绝构造思辨哲学意义上的体系,反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主张诗化的哲思,寻求开放的对话。教化哲学终止的是哲学的扩张,不会终止哲学的发展,但能防止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
西方哲学危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它的种种表现给人一种似乎无法捉摸的感受。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三种最直接最重要的方面外,二元对立也是很受研究界重视的一个因素,它既是危机的一个方面,又是危机的根源。二元对立不仅产生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现代人大多对此不遗余力地攻击),也由此产生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很多人不仅把它看作文化危机的渊薮,而且视之为生态生存危机的“潘多拉”。
科学基础的变更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的变化恐怕也是哲学危机的深层动因。经典科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遭受了全面的根本性考验,并在“危机”之上建立起了新方法、新观念,尤其是思维方式由绝对观走向了相对观,必然会带动文化的总体变化,许多现代科学的词汇涌入大范围的文化系统,那么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哲学自然要受到冲击,并且必须对此作出反应,结果就以“危机”和“重建”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自然科学的转型看相应的文化转型,我们更能明察秋毫。
三
正如罗蒂认为后哲学文化对大写的哲学终结不会产生文化上的危险一样,本文所论述的危机也并不意味着某种直接可见的灾难,也不是对现实“信息过量式”的坐立不安。危机不是危险,而是对数千年文化发展的反思,它真正表达的是“人类整个文化转型时期我们怎么办”这样一种焦虑、期望与思索。
这是一场巨大的变革,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传统的沉淀之中面对人类的发展所肩负起的神圣使命感。不可否认,在这种思潮迭起的“天下大乱”(维特根斯坦语)的时代,难免泥沙俱下、玉石俱毁,但也许只有过正的矫枉才能拓出生存与前进的新境界。从方法论来说,历史的前进必须、也只能依托在反思之上,这一点早已被事实确证过了,可以说古已有之。那么面对这场程度上或许类似于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件,我们不会也不必惊慌迷惘。冷静的思索比大声疾呼之于当今的现实当更有裨益。
危机的表现以及原因的本身就是其实质所在,前文对此已有浅释。总的说来,这场“危机”挖掘出了哲学上的一些“假”问题,即似是而非、貌似高尚实则无理无用的东西,击中了传统的弊端,暴露了传统的某些偏差与不足。尤为重要的是,这场危机带来了东西方文化内部结构的突破,为文化的融合进而转型以产生新的文化形态起到了开路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这场旨在“破”的危机仍在进行之中,它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理性的僵化与狂热,攻击近代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基石,主张一切价值之重估,宣扬文化上的革命,多角度多层次地对传统纠偏和补漏。根本上说它的实质之核心在于多元化的基调,是作为西方哲学基本精神——“自由”理想的延续,也是对此更为认真切实的贯彻。
另一方面,现代化使个体的生存空间之间产生了更紧密的交互关系,那么作为调和滋润它的文化也必将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这场危机的实质还在于它是因区域文化交锋、碰撞、对话以及企求认同而走向新的、松散的、一体化文化历史目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古希腊发端的西方文化虽然随同军事与经济而遍布全球,但它根本上只是一种区域文化,从对形而上学乐观追求的开始就注定了要最终走向某种形式上的衰亡。作为一种形式,它必定是处于时间中的有限存在,也会经历有限存在物富于旺盛生命力的开始和极度辉煌灿烂的历程,在各种区域文化真正相互面对之时也会走向形式的终结或转轨,而各自独特的智慧成果将以另外的形式公正而完整地融入新的文化形态之中,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在深层意义上得以保存下来,并在新的土壤上重新开花结果。这不仅是“复兴”,也非简单的“创造性转化”,而是进一步理解之后的继续发展。人类的智慧——对生命以及生活的理解、对存在的体认,虽表述各异,但却具有永恒的价值,任何以危机为表象的反思或转化必依于是,又归于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运伟大之思者犯非常之错”(海德格尔语),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危机之中,人们受一种不正常(非贬义)心态的驱使,在传统的反思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许多本来不是问题或至少不是大问题的问题被扭曲夸大后使文化变得混乱不堪,各种“剃刀”良莠不分。具体地说,最严重的恶果就在于牺牲了我们对理想、对未来、对生存的超验承诺,使得现实泛滥,当今各种“主义”横流,让人无所适从,也让历史在各种短命的思潮热浪中颠簸摇摆,危机及其拯救的意图被这些浪头逐级推送得更为遥远,未来和现实也就变得愈加虚无与苍白。[⑧]
所幸的是,在今天对近代的理性主义、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倍感眩晕难解的西方思想界,已经有人部分地走出了这片必经的被偏激、愤怒和迷惘所笼罩的地带,清醒地检讨了得失及原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新形态文化在遥远的未来给现在正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我们一次小小的电击,这点微弱的火花虽还不能照耀我们走出迷雾识得庐山真面目,但至少已给我们指明了一个不难捉摸的方向。
首先,要从多元化出发,承认多元并立,公平相处、互相尊重、深入对话以求共同发展,同时要防止以多元化为借口的文化沙文主义,多元化不是相对主义,更不为抱残守缺提供庇护地。然后在多元化的基础上端正心态,以开放的、创造性的、也是冷静的心态对待传统,并对百余年的反思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以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去“广博精微、综罗百代”。
其次摆正传统的位置,承认历史的合理性,在前人文化的或智慧的道路上继续迈进。哲学终结的提法并不表示智慧的结束,理性的价值本身具有永恒性,一如真理绝对性之说。只要摆正理性的位置,经非理性的矫正补充之后的现代“新理性”将是传统赐予的福荫,也是未来的指北针。胡塞尔说得好:“‘危机’能够变得同‘理性主义表面上的崩溃’一样可以得到清晰的理解”,“理性文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不在理性的本质之中,而仅仅在其外部形式之中。”[⑨]理性本身无罪,罪在人们不正确的态度上;科学本身也无罪,罪在无度地对待它,所以胡塞尔的理想就是要把真正的理性建立在真正的科学精神之上。伽达默尔的《科学时代的理性》更乃这种智慧意义上的新理性张本。当代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坚持启蒙运动精神,反对保守立场,反对对传统随心所欲的破坏,他提出以社会交往理论的交互理性为新理性的建设作可能的方案。
凡此种种,无不应和着胡塞尔那段名言:
从那势必焚毁万物的无信念的大火之中,从对西方对于人类负有的使命的绝望的洪流之中,从严重的困倦造成的废墟之中,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不死的。[⑩]
注释:
① ② ④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3、10、5—6页。
③Heidegger,Principle of Reas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129.
⑤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Routledge & Kegan Pall,Ltd.,London,1978,P.280.
⑥Heidegger,Letters on Humanism,Quoted from philosophy——THE POWER OF IDEAS,p.117.
⑦参阅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3—22页。
⑧参阅拙文《论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的现代意义》,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⑨ ⑩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祥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74、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