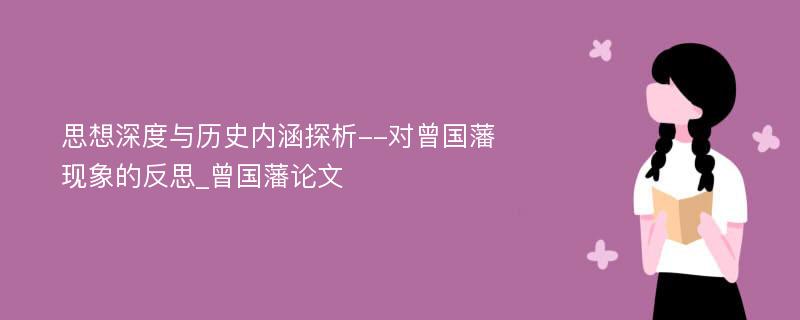
向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开掘——《曾国藩》现象引起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曾国藩论文,深度论文,现象论文,思想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在较短的时间内;分别由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四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在大中华文化圈内是颇为罕见的现象。除台版和港版之外,湖南文艺出版社从1990年底到1994年底连印10次,书店还经常脱销。当文学在九十年代受到影视、歌舞、体育等多种文化娱乐样式强烈冲击而面临困境时,一部三大卷、120万字的名副其实的严肃文学作品居然成了畅销书,而且所刻画的主人公是一个在不同地区有着天地之差评价的历史人物,竟然能够深受海峡两岸读者的青睐,这一文学现象很值得深入探讨。
它是不是新闻界“炒”起来的?不是。是不是评论界“吹”起来的?不是。是不是影视再创造后才“火”起来的?也不是。据笔者所知,它在大陆出版以来,除湖南省内有少数报刊作过一些简单评介之外,到1994年底止,省外较有影响的文章,只有《文学评论》1993年底和《文艺报》1994年初分别发表的作者本人的《创作琐谈》和蔡葵的《救赎与重塑》等几篇。素以搜集资料最全、以推荐佳作著称的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也在1994年底之前未转载过任何完整的有关评介。这与陕军东征时的浩大声势相比,只能算作“大地微微暖气吹”。
搞市场经济,对商品进行适当“包装”,是应该的,必须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商品属性,同样需要进行一定的广告宣传。但是,商品本身首先得是优质特产,作品本身首先得是精品佳作。粗制滥造、质次价高的伪劣产品,即使包装新奇怪异,广告铺天盖地,暂时获得一些经济效益,终将被消费者唾弃。因为《曾国藩》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因为作者对曾国藩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出来的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大人物,没有单纯地在政治上定位和从道德上评判,而是努力置于文化系统中进行考察和描绘,从而刻画出了中国封建末世理学名臣的悲剧典型,所以才能在出版商没有大肆叫卖的情况下,仍然流传甚广。但我不准备对小说本身的艺术成就进行详细分析,只是想从更广泛的范围谈谈这部作品之所以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的原因,以及由此引起的思考。
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出版,首先当然是因为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有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有“双百”方针的全面贯彻等必备的社会条件。然而,这一大好的历史环境,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是完全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的。唐浩明较为成功的创作,自有他本人所独具,又可供其他作家所借鉴的东西。姚雪垠认为历史小说家应该同时是历史学家。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大师,哪一位不同时是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杰出学者。唐浩明还必须奋力攀登,但已在崎岖的道路上作了艰苦的跋涉,则是不争的事实。他少时在父母离开大陆,自己寄养穷家的困难条件下,曾用捡废铜烂铁换来的钱去购买《三国》、《说唐》等书。大学虽然攻读工科,但新时期伊始,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华中师大中文系录取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不仅圆了多年想进文科大学的梦,而且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学基础。毕业后被分配到岳麓书社工作,不久即担任了《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这样他就有条件阅读和整理曾国藩留下的1500万字的家书、诗文、日记、奏稿等尘封百余年的历史资料,并有机会访问海峡两岸的曾国藩后裔和调查曾国藩活动过的历史遗迹。同时,他还钻研了解放前后和海峡两岸出版的多种近代史著,阅读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以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文集,并旁及各种笔记杂谈、稗官野史。如果说这类艰苦的准备工作,其他一些稍有成就的历史小说家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过的话,可贵的是,唐浩明在创作之前还对曾国藩的生平交游及政治、学术、人才和文学思想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十来万字的学术论文。这就为他突破单纯地强调史料真实性而作浅层次追求和狭隘地理解古为今用原则而作机械比附的窠臼,能从大文化的广度和高度认识和描写曾国藩这一艺术形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想理论准备。
我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自从姚雪垠填补了“五四”以来的空白之后,在新时期,农民运动领袖、民主革命志士、封建明君贤相和历代文人学者相继跻身于文学画廊,各类历史小说可谓层出不穷、空前繁荣。为什么除《李自成》、《金瓯缺》、《少年天子》等为数不多的作品尚在读者中流传外,其他大量作品,甚至包括某些初版时喧腾过一阵的作品,今天已经逐渐被读者淡忘了呢?究其原因,仍然是恩格斯所说,看其是否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一般说来,那些被时间逐渐筛掉的长篇历史小说,在“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方面都有可取之处,然而在“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方面相对薄弱。唐浩明的《曾国藩》与其他一些较好的作品无不都是作者经过长期酝酿和构思,才在这方面找到独特的视角,并揭示出较深的文化底蕴,甚至提升到一定的哲学层次。
其实,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是如此,以现实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何尝不应该如此呢?现在走进书店一看,某些稍有名气的作家的作品,就像魔方组合般摆满书架,如精选、自选、分类选、文丛、文萃、文集,就差一步要出全集了。实际上能够在读者中造成一定影响,过了几年尚能被读者提到的,只有那么一两部,或者两三篇。我国古代五大长篇名著的作者,除罗贯中尚有其他长篇之外,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都是终其一生,仅以一部长篇传世,曹雪芹的《红楼梦》还只完成三分之二。像俄国托尔斯泰有三部巨著藏于世界文学宝库的现象并不多见。而且他的《战争与和平》在壮年花了七个春秋,《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年费了五个寒暑,《复活》在老年耗了十个岁月,三部作品的间距是五年和十年。“板凳需坐十年冷”虽不一定是必须遵循的规律,但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严肃态度,托尔斯泰“在墨水瓶里留下自己的血肉”的刻苦精神,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长篇小说被称为描绘历史的巨幅画卷,是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标志。只有摒弃虚荣心态、浮躁情绪,树立精品意识、夺标思想,经过反复琢磨、精心锤炼,才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挖得更深、写得更美,既不重复别人,又能超越自己,克服某些作家后部不如前部,甚至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处女作的不良现象。一部优秀作品胜过成千上万部平庸作品,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现在我国每年出版长篇小说高达四百余部,不是数量太少,而是精品不多。德高望重的巴金于1980年在日本说过:“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最近在作协主席团会议期间,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人生要有理想,我写作七十年,就是靠理想。”并且强调:“我就是对拜金主义很反对。”遵循耄耋老人的教导,中国当代作家一定能够创作出与社会主义伟大时代相适应的史诗,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相匹配的瑰宝,与世界各个艺术高峰相媲美的精品。
《曾国藩》之所以流传甚广,除了作者在内容上能够不拘于“三立完人”和“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的定见而有自己的卓识之外,是否象先锋小说那样在艺术形式上也有不少探索和突破呢?显然不是。蔡葵认为“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是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对史料的运用也很严谨,在艺术手法上并没有很多创新”。这是完全符合作品实际的评价。就情节结构而言,除插叙家乡求学和京城为官之外,主要按曾国藩墨经出山到寿终正寝的经历安排,没有时间的跳跃交错,没有空间的切割拼贴。至于变形、隐喻、荒诞、魔幻等手法,都难于在作品中找到突出实例。那么它是否采用了某些通俗文学中的“戏说”、“新编”等方法,或大肆渲染“怪”(怪诞)、“力”(暴力)、“乱”(淫乱)、“神”(鬼神),以招徕读者呢?更加不是。作者自己说,这部作品“可以说真实与虚构之间是七三开”。从金戈铁马的战场来看,确实描写很多,因为曾国藩的最后二十年,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但与在它之前问世的《李自成》、《金瓯缺》、《星星草》等长篇历史小说相比,并没有更多的出色之处。就风花雪月的情场来看,描写得更少,有点像《三国演义》,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整部作品,可以说主要遵循了恩格斯所提倡的方法,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至多是运用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一文学现象也很引人深思。
唐浩明创作《曾国藩》,构思于八十年代中期,完稿于九十年代初期。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在短短的十年之内将西方现代主义在一百多年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流派全部演示了一遍。这对于我国作家开阔眼界、活跃思维、吸收方法等方面,功不可没。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激情的快速转移,创作界又“新”军蜂起,“新”旗林立。什么新文化、新状态、新写实、新历史、新感觉、新笔记、新都市、新乡土、新实验、新体验、新言情、新武打和新闻小说等等,不可尽数。与之相配合,评论界也进行了“后”字竞赛、“后”名展览。什么后新时期、后现代、后解构、后文化、后殖民、后人道、后乌托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新”,是否能推陈出新,这些“后”是否能后来居上,尚难论断。因为它们或者刚刚呱呱坠地,或者还才牙牙学语,或者正在蹒跚迈步。当现代主义浪涛汹涌澎湃,当“新”兴潮流奔腾翻滚之时,唐浩明仍然固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革命现实主义阵地,并以其艺术实绩显示出革命现实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实为难能可贵。西方现代主义这个庞杂体系,像多股激流,前呼后拥,此起彼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冲击,最终还是没有冲散现实主义的主流,甚至部门溶入了这股主流。中国文坛在八十年代掀起的现代主义浪潮,也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复了这一过程。现在涌起的“新”潮“后”浪的命运将会怎样?鉴古而知今,结局是不言而喻的。时间是最有效的沉淀剂,读者是最权威的裁判员。《曾国藩》从面世到流传,还只有五年时间,它将继续经受时间的筛选和读者的取舍。但仅就作者所高扬的革命现实主义这面旗帜来看,时间的流水不会使它褪色,读者的眼光也不会对它冷淡。
《曾国藩》虽然从一个侧面给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部回顾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形象历史,具有一定的古为今用的功能,然而,我又不能不遗憾地说,它究竟不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题材决定”论固然必须否定,“题材无差别”论也未必正确。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由于需要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就必须“鼓励创作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昨天,广大读者因文坛“先锋”们只顾“超前”而逐渐疏离了高雅文学;今天,广大读者也并不热衷于跟着文坛追“新”逐“后”,而是热切盼望作家们提供更多的革命现实主义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