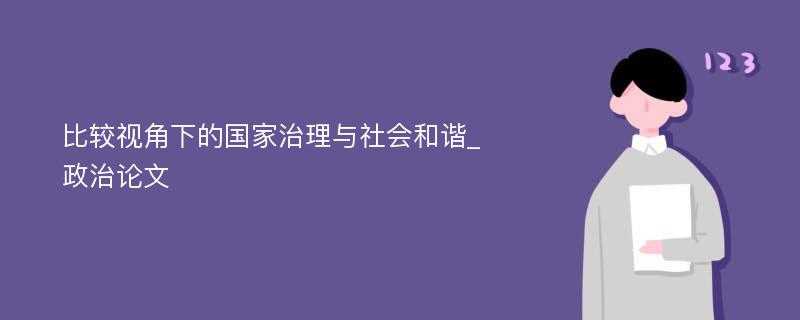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和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和谐论文,视野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4527(2007)02-0140-03
一、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
所谓制度变迁,指的是社会制度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处在变化之中。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因此,生产方式的变更,必然导致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谐社会是自古以来人类所孜孜追求的理想的社会模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历代大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为人类的同一向往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看,社会的和谐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密不可分。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国家和社会是融为一体的,城邦就是一个公民生活的全部内容,它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政治体制,社会生活就等同于政治生活。同时,它也反映了一种伦理规范,人的本质是政治人,人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城邦的各种事务——辩论、投票、选举和担任公职等。所以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城邦的动物。”在当时生产方式单一的小国寡民时代,国家与社会基本上是和谐的。
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由于各国社会经济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差别又分成了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和国家主义的法德模式。前者强调个人自由,主张最大限度限制国家作用,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肯定家庭和一切小共同体努力的价值,“自愿组成的联合团体通常会比国家用强迫力量来做的更好。”[1] (P22)法德模式强调在落后而混乱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必须强化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的扶持力,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控制和高度整合,社会不享有任何独立于或者对立于国家的利益。这种模式发展到极端就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模式,即国家充斥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模式。上述两种模式各有弊病又各有千秋。前者崇尚民主而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繁荣,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没有发生过一次政变;后者因强调国家的“保护神”作用而成就了“福利国家”。二者都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温和控制,社会与国家的纽带是选民的选票。
“东方社会”的情形如何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东方社会包括中国、印度、俄国和土耳其等亚洲国家,列宁沿用了“东方”这个概念来概括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迟滞,受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经济上落后,政治上高度集权。进入20世纪中期,“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和东欧、东亚地区影响很大。这种模式强调国家对经济和政治乃至个人生活的垄断,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国家政权逐渐吞噬了民主的活力,社会生活被集中到政府手下,政府权力又集中到党委手下,而党委权力又集中到领袖的个人手下,形成了等级森严、形式单一的僵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它几乎不受社会的任何约束,“整个社会僵化停滞,绝大多数民众除了被动地听从政府的命令之外,基本上游离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2] (P92)
二、和谐社会的历史憧憬
早在两千年前的中国,便有人喊出人本主义的理念:“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孟轲的“民贵君轻”之说,敢于为民立言,锋芒直剌至尊,这在当时是极有胆识之为。“和谐”的思想在社会学的视野中被称之为“秩序”或“均衡”。[3] (P9-12)自古以来“和”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更是历代政治家秉持的治国理念。中国是一个以追求和谐为完美的国度,在传统的道德伦理中有“和为贵”、“和衷共济”、“和气生财”、“求同存异”等思想观念,为历代先贤所推崇。孔子所言“致中和”、道家主张的“和异以为同”、《春秋繁露》所载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及张载所表述的“天人合一”等,都表明和谐观念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理想国》里提出,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个人是缩小的国家。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大家傅立叶于1803年写了《全世界和谐》一书,他预言“不合理的不公正的现存制度”将被崭新的“和谐制度”,或称“和谐社会”所代替。1842年空想社会主义学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就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和谐作为社会状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的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把共产主义称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 (P603)
三、社会失调的原因与演化周期
斯大林模式因缺乏充分的民主与法制制衡而受到人们的反对,最终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社会混乱,一直到现在,制度问题、民族问题、腐败问题、福利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都没有处理好。东方国家还存在社会与国家的冲突,表现为1956年的波匈事件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现在的俄罗斯表现为车臣等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和60年代开始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
与东欧相比,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欧美及拉美大行其道,但结果也不容乐观。拉丁美洲的国家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停滞和贫富差距,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冲突,失业率高涨、贫富差距拉大,政局动荡。拉美国家的社会失调,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规律:
第一,宪政是规范社会冲突,调整社会矛盾的利器。英国的宪政框架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不受王权的任意侵犯,这一方面规范了王权与民权的冲突,使得以前人格化的流血冲突变成了非人格化的规则冲突。而拉丁美洲从独立以来一直未能建立起宪政基础上的产权保护制度,因而也就始终没有摆脱政权循环的命运。
第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民富国强的活力之源。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后由于政局动荡导致政策多变,一直未能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竞争体制。
第三,中产阶级是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主体。追求市场经济的片面发展虽能保证生产效率,但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宪政体制虽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不能保证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作,作为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和对政府职能的补充,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和谐的反义是冲突。从冲突到和谐,或从和谐到冲突是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从乱到治,或从治到乱的周期。历史上的“治”(或曰太平盛世)正是一种社会安定和谐的情状,其特点是:内外矛盾得到缓解,休养生息之后,生产得以恢复发展,社会整体而言,较为安详和谐。但是必须指出,此种和谐乃孕育并产生于冲突,犹如风暴之后的雨过天晴。况且,社会的和谐也决非人们的一厢情愿,它自有演变的规律,和谐的旋律中也潜伏种种隐患,犹如平静水面下湍急的潜流。和谐——冲突——和谐,如此周而复始,曲折地推动着社会进步,这也就是各种矛盾酝酿作用所产生的演变周期。此种历史现象(或曰历史规律),已在中外古今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屡屡得到印证:国家治,则社会安定和谐,民众安居乐业;国家不治,则社会分裂动乱,民众流离失所!对于社会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四、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
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是一个人均收入位于1000-3000美元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长期以来潜伏的社会矛盾处于临界点和进入高发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使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农业的工业化、农村的城市化、计划经济的市场化和传统政治的现代化转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然而,高度集中的领导并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社会运动一次连着一次。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衰退,中国经济损失5000亿,相当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5] (P386)
邓小平复出后,中国走上了循序渐进改革开放的道路,其基本路径是先经济后政治。经济改革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报告,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指导性纲领。但是,因为国家正致力于经济恢复,所以政治改革始终没有深入展开。由于现代化过程中只注重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只注重经济而忽视了其他行业、只注重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只注重经济改革而忽视了政治改革的同步进行,发展中长期潜伏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腐败现象盛行和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加剧,保持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成了当务之急。
(一)政权与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一直在追求政权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国家在社会中获得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权威正当性的资格和权力。”[6] 西方执政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选民选票,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则来自于“代议民主”,属于“利益代表型”,立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巩固和扩大。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全能型的政府不会导致社会和谐,这是因为:第一,“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迄今为止,随着文明的发展,个人行动受成规束缚的范围在不断地缩减。”[7] (P60)因此采用单一的共同的伦理标准,将意味着与这种趋势背道而驰。第二,由于个人和群体的地域性、民族性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政府必然不能保证绝对的正确性,政府也就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和自身的工具理性,政府的缺陷在所难免。第三,政府主导的共同价值观具有排他性,导致社会成员的身份的不平等。符合共同价值的成员将以集团成员的身份受到褒扬和尊重而处于强势地位,而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则会受到冷落甚至排挤,这就是说不是任何种姓意义上的人都会受到“人”性的待遇。比如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在中国成为打击对象的是地、富、反、坏、右,在前苏联则是富农。第四,由于国家经济领域的垄断性和对资源分配的决定权,确定了同类实体的不同地位。同样的企业,一个姓“国”一个姓“资”,前者是亲生子,备受呵护,后者是“私生子”,命运多桀。
(二)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
王沪宁认为,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都有双重目标:“一是谋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二是谋求政治生活的稳定化。”[8] (P370)要达到二者的平衡,首先,应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9] (P284)邓小平的两段话告诉我们,我们的政策是一要稳定,二要改革开放。其次,一个国家的民主的具体形态和运作方式不能脱离该国的实际。国家制度的设计不能过于理性主义和神圣化,因为民众多是非理性的、感情化的、追求现世利益的和民族主义的“凡人”,过于完美的制度设计由于脱离了实际而显得虚无缥缈,最后以非理性的社会动乱结束。同时,只有把个人的自由和福利置于国家追求的目标之上,才能造就“以人为本”的社会,这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0] (P273)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可以天马行空,因为自由是和责任义务对等的。卢梭在1756年写成的《社会契约论》中指出:“社会是自由人组成的,国家代表公益”。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只有通过公约加入整体,才能获得自由。人在集体中的自由大于个人自由。
(三)社会和谐与国家治理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迁,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但不会引起根本政治制度的变化,因而和世界上的其他变迁类型相比,中国既不是原生型的,也不会是革命型的,而应当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型的。中国现阶段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的矛盾,且阶级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而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11] (P61)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尽享太平。从财富分配角度看,过去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的,在我国经济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应重新考虑二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点,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今天,应该把公平放到首位,至少两者不应有主次之分。公平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也是分配的最重要的原则,它体现在同等条件下的人应该得到同等的机会和同等的选择权和被选择权,不应有排他性和优先权。从法治角度看,依法治国是保障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关键。应当处理好党纪和国法的关系,把党和国家的活动也纳入到法制的轨道,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是我党在长时期革命和建设中总结的执政规律。
结语:马克思曾在《六月革命》一文中指出:“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12] (P303)我国实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是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体现。“和谐社会”乃是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社会没有绝对的和谐,只有比较地和谐。国家能否有效治理,社会能否安定和谐?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够妥善化解主要矛盾。对于社会问题,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治本之道,须反省得失成败,并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须找准积弊之所在,深究其内在原因和根治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