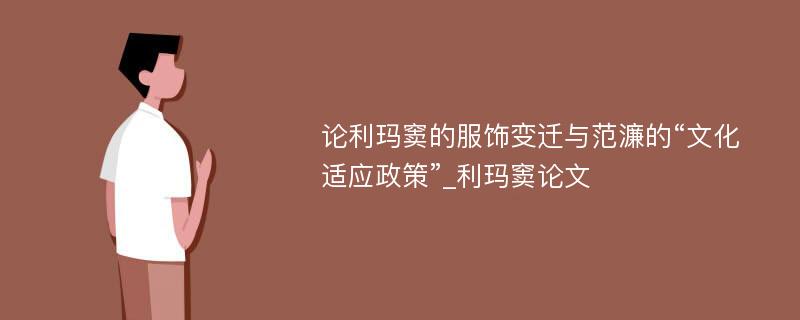
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文化论文,利玛窦论文,范礼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2.24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2-09-05
在许多相关研究中,1595年5月利玛窦(Matthoeus Ricci)在江西樟树改换儒服被视为传教史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之一①。作为这个传奇的始作俑者,金尼阁神父在1610年的信中声称,利玛窦采用了儒生装束,使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一切都开始发展,几乎到了繁花盛开的地步”[1]600。而出于世界大同、文化交流的美好理想,徐光启当年别具深意的“驱佛补儒”之说又逐渐在今人的想象中演绎成“合儒、补儒”的既定模式,而利玛窦头戴儒冠、身着长袍的标准像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广泛共识的绝妙写照。但是,利玛窦在其回忆录的卷首意味深长地告诉读者:
这样的事并不是常常发生的:大规模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壮举,年深日久趋于成熟,但其创始时的情况,对于生活在这些事件以后很久的人们,却完全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获得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之微不足道,以致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情。[1]1
利玛窦没有阐明有哪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何在“年深日久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变成“巨大规模的事件”,但从他易服行为的历史情境中不难发现以下细节:其一,从更广的范围看,易服并非利玛窦首创,在印度、日本以及利玛窦入华之前的中国,易服都是传教士们不约而同的策略行为;其二,从严格意义上说,利玛窦在华期间的易服行为至少发生过两次,他首次易服应该是在他入华之初,将象征清贫和圣洁的黑色修道服改换成中国僧人的异教服装;其三,1595年利玛窦易换儒服,是在他身着僧服、以番僧模样示人的12年之后。根据其“每过佛堂,并不顶礼膜拜”的自白,利玛窦早就对其宗教对手的服饰标志及含义有足够的认识。因此,最终的易服决定不应是戏剧性的突发事件,而期间一言难尽的种种隐情也是“一本未曾打开(细读)的书”。
一
根据利玛窦本人的记载,罗明坚(Michel Ruggiere)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易换服装的第一人。利玛窦在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写道:“从他们(按:罗明坚等人)入境时起,他们就穿中国的普通外衣,那有点像他们自己的道袍;袍子长达脚跟,袖子肥大,中国人很喜欢穿。”[1]168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见到中国官员之后,这些福音的传播者便爽快地接受了官员的建议,欣欣然地准备改穿“偶像崇拜者”的服装。在1583年2月7日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Beao P.Rudoifo Acquiviva)神父的信中,罗明坚坦陈道:“(位于肇庆的两广总督)愿我们穿中国和尚的服装,这与我们神职的衣冠略有分别,如今我们正在做僧衣,不久我们将化为中国人,‘以便为基督能赚得中国人’(Ut Christo Sinas Iusrifaciamus)”②[2]451。在几天后(2月12日)寄回澳门的另一封信中,罗明坚又提到了另一位中国官员的相同愿望及慷慨解囊。信中说:“……两天前我们去见他(广州都司),他对待我们很和气,赠银一两作为布施;我们谈及服装,他当即自己画了个帽子,说总督和所有的官员都希望我们穿北京‘神父’的服装……”[4]82综合以上记录,耶稣会士在进入中国之后的极短时间内迅速进行了第二次易服,即从普通中式常服改换为佛教僧侣的服装。出人意料的是,神父不仅没有对中国官员建议的异教服装表示反感和厌恶,反而认为:“要在中国获得社会地位,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于是,他们就让人把头和脸都剃得净光,穿上非常得体的袈裟——是大襟式样的”[4]82。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在澳门的利玛窦也对中国官员的建议表达了赞许之意。他在1583年2月13日于澳门写给罗马总会长的信中同样欣喜地说:“……他们应该更换衣服,神父们以为这样很好,于是他(两广总督)把北京和尚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是他所能恩赐最体面的服饰了。”[2]40众所周知,在写下此信约半年后的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随罗明坚来到广东肇庆,由此开始了中国内地传教的漫长岁月。
关于利玛窦初入中国时的服饰打扮,清人张尔岐《嵩庵闲话》卷一说:“利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5]9。对照前引罗明坚等人的信件,文中“髡首袒肩”一语或有细究的余地:首先,所谓“髡首”,或可证明利玛窦已与罗明坚一样,“让人把头和脸都剃得净光”;而随后“袒肩”一词的含义虽然与前述“非常得体的袈裟——是大襟式样的”僧服略有些差异,但无论如何,绝不会是耶稣会士的传统黑色修道服。
正如方济各会修士腰中的麻绳,耶稣会士标准服装的黑色修道服也有其特定的含义,它被视为入会三大誓中“清贫”和“贞洁”的外在标志。而在向来以准军事化组织闻名、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耶稣会中,罗明坚与利玛窦毫无顾忌、“自作主张”的易服行为显然是极为大胆的。对此,裴化行神父的解释是,他们是仿照诺比利神父(Robert de Nobili)在印度已有的先例。为此,裴化行还援引诺比利在1610年所写辩解词作为证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诺比利在辩词中声称:“在日本和中国的耶稣会士穿和尚服,是一个先例……我一向深感诧异,因为,首先在中国,而后在其他地方,我们的神父采取同样的做法,并没有人指责他们令人骇异。”[4]83-86从时间的角度看,诺比利在二十多年后的辩解不会是对利玛窦易服事件的直接回应,但他却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耶稣会士们“入乡随俗”的形象改变始于日本的传教先驱。
二
对照史料,诺比利所说的“日本耶稣会士”是指1549年8月15日进入日本传教、1552年12月3日客死于广东沿海的上川岛上、后来被封为传教圣徒的沙勿略(Francisco Xavisr)神父。关于沙勿略在日本传教初期穿着的服装,文献中大多语焉不详,只是含糊地声称:神父“穿着古老的法衣,上面套着古老的长袍”[6]422。然而,参照文献记载中的街头传教方式以及因此受到的各种侮辱,沙勿略应当身着传统的黑布修道服无疑。或许缘于一再受挫的现实,沙勿略开始改变衣着习惯,在重返山口时,他身着华丽祭服去拜访领主,并获得出人意料的效果。“看到他身穿与最初来访时不同的服装,(大内义隆)部下诸将都对他待以上宾。大内义隆拍手赞道:‘这位神父简直就是我们信仰的众神的生动写照’。”[7]101关于这次亦可称之为易服的策略调整,陆若汉(Joam Rodriguez Tcuzu)神父论述道:“(沙勿略)从最初在山口遭到人们虐待以及京都之旅的经验可以明白,由于他们(传教士)身着粗糙的破衣,对这世上的东西采取完全轻视的态度,所以日本人轻视他们,就像躲避来往乞食的乞丐那样躲避他们……因为日本人对作为他们教师的僧侣极为崇敬,他们只注意到装饰在外观上的东西,而且被僧侣们举行的仪式和外观所迷惑……因为这个原因,神父(沙勿略)决定今后与以往不同,穿着更为合适、清洁的服装,为了对我主的爱,在不至于犯罪的限度内尽可能地依从日本人的习惯。”[6]447-448由于环境的不同,沙勿略以及此后日本耶稣会士的形象包装不是改易僧服或者文人的服装,而是使用当地上流社会喜好的丝绸服装,但对比罗明坚等人所作所为,两者间的异曲同工仍一目了然:正如沙勿略易服是“决心为基督获得所有人的心”,罗明坚改装也是“以便为基督能赚得中国人”;正如罗明坚等人的易服是源于中国官员的建议,沙勿略在日本的服装改变也是迫于社会习俗——日本人轻视那些“身着粗糙的破衣”,如同轻视乞丐一般的传教者。
考虑到沙勿略作为该修会创始人之一以及后来被封为“东洋传教圣徒”的特殊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穿着更为合适、清洁的服装”,不仅意味着新的服饰标准,而且还表明新的策略原则的建立,即“在不至于犯罪的限度内尽可能地依从日本人的习惯”的行为准则,而这一原则的形成与确立,当然会对利玛窦等同会晚辈产生深刻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易服还是其他入乡随俗的行为改变,从来都不是出于文化交流或其他超越宗教派别的自愿行为,而是迫于生存需要,无论是沙勿略还是后来的利玛窦,在力量对比中始终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耶稣会士通常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屈从于现实。但另一方面,这种强大的外力压迫也必然导致反弹,从而酿成新的危机与冲突。根据记载,关于服装问题的激烈争议爆发于第三任教区上长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1570年8月来到日本之后在当年于志岐召开的全体传教士会议,会上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如何解决“在日耶稣会士身着丝绸、过于奢侈”的问题。由于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反对卡布拉尔的提议,恼羞成怒的新任教区长干脆下令属下的所有传教士重新换上象征清贫的传统修道服③。
许多史料表明,卡布拉尔的独断专行几乎引起日本教会的分裂,赞成者与反对者的争议甚至从教会内部扩散到日本信徒之中④,这一危机直到范礼安1579年对日本教区首次视察才宣告结束。在1582年写给总会长的报告中,这位擅长公关事务和行政协调的视察员声称:
日本人如此地爱好清洁,而佛教僧侣又尤其重视这一点,所以关于清洁的问题决不可疏忽大意。因此,为了与日本人亲近,我们最初穿用丝绸衣服。但后来全部停止,现在是穿用长修道服和斗蓬,即一种罩衫。这种服装与日本的风俗相同,是全黑的、带袖子的上衣,所以完全不用丝绸。所有这些服装都必须是清洁而得体的……[10]121
关于范礼安偷梁换柱、文过饰非的诸多内幕和话外之意暂且不论,可以确定的是,“所有这些服装都必须是清洁而得体的”的结论,不仅与沙勿略易服创举的真意遥相呼应,而且意味着由视察员再次确定了服饰原则以及更深含义上的行为准则。
与日本耶稣会士关于服装问题的激烈争议和再三反复相比,罗明坚和利玛窦的前两次易服算得上风平浪静,他们的形象转换一方面缘于有可以参照或仿效的先例,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压力远甚于日本同行。从范礼安“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打开”的著名感叹可知,自沙勿略客死上川岛到罗明坚入居肇庆的近三十年间,耶稣会士一直在为合法进入并定居中国内地而努力,而此前的多次碰壁和失败也早已使他们明白,能否实现梦想的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中国官员的认可。因此,好不容易才看到希望的罗明坚等人当然无法拒绝两广总督和广州都司的建议。对于跪拜于案前阶下、唯唯诺诺的传教士们而言,这些“很和气的”老爷(曼达琳)的建议实际上就如同命令一般,更何况他们还“赠银一两作为布施”,并且亲自绘图以作说明。
三
然而,另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在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利玛窦等人未必清楚那些“最体面的服饰”是多么荒谬,但随着对于中国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他们迟早会发现身传佛僧的外衣是多么不可思议,进而不可避免地再次易服。
从时间来看,最早提出此议的恰恰是那位要求“废除丝绸与华美装饰”,并强令日本耶稣会士重新“穿黑布修道服”的卡布拉尔神父。他在1584年12月5日于澳门写给范礼安神父的信中提到了利玛窦如何用世界地图和三棱镜获得中国官员与文人的青睐,随后转弯抹角地称:“神父您知道,他们僧侣才是官员们所轻视的,因为佛教人即不讲来世,也不谈灵魂不灭的道理,不善于管理庙宇,也不尊重他们的方丈。因此,开始重视与尊敬我们。”[2]469在这封信的最后,卡布拉尔提出了这个建议,即“神父都该穿中国式的长袍,头戴高方帽”[2]471。必须加以补充的是,卡布拉尔写此信时是在他因传教策略的分歧于1582年被迫辞去日本教区上长,又在1583年被“放逐”到中国教区后不久。鉴于他在日本耶稣会士服饰问题上的顽固立场,我们有理由相信,卡布拉尔在此建议“神父都该穿中国式的长袍,头戴高方帽”,并非是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境,而是基于他对佛僧一贯的极端仇视,甚至意有所指地影射利玛窦等人刚刚易换的“最体面的服饰”。也正因如此,他的这一建议才如同石沉大海,无人问津。直到十年后,才由利玛窦重提此事。
在1592年11月15日于韶州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利玛窦首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与知府大人及当地绅士之间的密切关系:“往往一天数席,应酬不暇,餐餐佳肴美酒。因此只能到一家坐下,吃一点,再到别家应酬”。然后转弯抹角地指出:“这种荣誉为我们十分重要,否则在教外人中传教便无效力了。洋人、和尚和道士在中国并不受尊重,因此我们不能以和尚、道士之流出现……”[2]123-124在随后返回澳门治疗脚伤期间,利玛窦第一次向当时远东教会的最高上长范礼安神父当面提出了易服的明确要求,也得到了同意:
因此利玛窦神父对视察员神父说,他认为如果他们留胡子并蓄长发,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他解释说,那些人按规定要剃得光光的,头发要剪干净。他还说,经验告诉他,神父们应当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视察员神父认为这些请求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一一予以批准,并且亲自负责把每项请求都详细报告给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神父,也报告给圣父教皇。[1]276
《札记》的这段记述非常重要,也非常著名,许多研究著述都将它视为利玛窦易服甚至是耶稣会士改变在华传教策略的转折点。由于缺乏材料,我们不清楚范礼安如何向罗马总会陈情汇报,但在他撰写的《写给澳门神学院院长的训诫》中,我们找到了视察员神父对此请求的明确指示:
中国的佛僧极受人鄙视,曼达琳对他们的评价很坏,所以我们的伙伴由于这些佛僧而使信用与名声受到很大损失。为此,我觉得在不长的时间中,与其说使用佛僧的名号,还不如采用文人的名号为好。为此,我觉得像佛僧那样剃发是不好而且并不恰当的。正如以前葡萄牙人通常所做的那样,以及今天我们在印度的伙伴所做的那样,(中国)国内的人还是蓄起胡子、将头发留到耳际为好。同样,他们在每日访问时还是穿着规定的外套为好。关于其他事情,应像访问曼达琳和其他重要人物时所奉行的那样,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作相应的打扮就行了。[11]270-271
对范礼安的上述指示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确定的、由远东耶稣会最高上长对传教士合适服装作出的明确指示;正是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利玛窦等人才有可能再次易服,以儒士的全新面目示人。
需要补充的是,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范礼安的《写给澳门神学院院长的训诫》被认为写作时间不明,但考虑范礼安在1594年创建澳门神学院即著名的圣保禄学院,并在1595年前往印度述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份《训诫》应当完成于上述时期,而且极有可能是在他离开澳门之前交给首任学院院长孟三德神父,然后经当时主管中国教区的神学院院长转达于利玛窦本人;正因如此,利玛窦才得以在同年即1595年5月于江西樟树正式换上中国儒服。
四
可能是由于漫长的等待,最终如愿以偿的利玛窦显得兴奋异常,在1595年8月到11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利玛窦在写给上级与各方朋友的六封信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他的漂亮新装,而11月4日致总会长的信中的记录最为详尽。他说:
离开韶州前,已经做好一套漂亮的绸质服装,准备在特殊场合穿用,另有几套为平日使用。所谓漂亮讲究的,即儒者、官吏、显贵者所用,是深紫色近乎墨色绸质长衣,袖宽大敞开,即袖口不缩紧,在下方镶浅蓝色半掌宽的边,袖口与衣领也镶同样的边,而衣领为僧式,几乎直到腰部。腰带前中央有两条并用的同样宽(的)飘带,下垂至脚,类似我们的寡妇们所用的。鞋子也是绸质,手工很细。头带学者所用之帽,有点像主教用的三角帽。[1]202
相较于《利玛窦书信集》中的其他年份,利玛窦上述时期的书信密度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而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不同寻常的文宣造势,利玛窦高冠博带、美髯垂胸的新形象广为人知,它不仅在当时就引起欧洲同事的误会,以为“在中国的耶稣会神父极力想得到中国授予的科举学位”,而且被许多不明底细且又自以为是的中国文人视为同道,甚至有人宣称,利玛窦偷梁换柱、似是而非的道德说教与中国古代圣贤的教导并无二致[1]277。
但另一方面,与中国文人的无知相比,终日与之周旋的利玛窦却没有自我陶醉到忘乎所以。如果说他首次易服还有些仓促、更多出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那么他第二次易服则更像是处心积虑的公关策划和形象包装。事实上,在易服之前,利玛窦就已经开始展开对中国文化及儒学经典的认真研究。在1593年12月10日于韶州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利玛窦声称他正在将四书译为拉丁文,此外,还在编写一本新的、用中文撰写的要理问答。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我们还不清楚利玛窦如何翻译儒家经典四书,但通过他信中所说的那本教义书即此后声名卓著的《天主实义》,不难了解他对中国儒家及其学说的基本看法。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天主实义》对中国儒家的基本态度可以用“容古儒”、“斥新儒”之说来概括,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看来,中国传统儒家尤其是先秦古儒,与基督教神学体系的自然理性颇有吻合或相通之处,而宋明以来的新儒则是背忘古训、步入歧途了。在利玛窦晚年所作的《札记》中,他一方面称赞古儒的理性之光,声称古代中国人因此得到拯救,但同时又毫不留情地将儒学归于“迷信”之列,即“三种崇拜或宗教信仰体系”之一。他说:“儒教目前最普遍信奉的学说,据我看似乎是来自大约五个世纪以前开始流行的那种崇拜偶像的教派。”[1]101“……因为他们既不禁止也不规定人们对于来世应该信仰什么,所以属于这一社会等级的很多人都把另两种教派和他们自己的教派合而为一。他们确实相信,如果他们容忍谬误并且不公开摒弃或非难虚伪的话,他们所信奉的就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宗教了。”[1]105
鉴于本文的主题,这里不能对基督教神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冲突进行详细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玛窦在易换儒服之后,对于身穿同样服饰的中国文人普遍信奉的哲学理念并不认同,即便他们时常酬答往返,甚至在一起把酒言欢。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我们注意到利玛窦在1595年10月28日于南昌写给高斯塔神父的信中记述的灵异经验:
我如今要谈我的梦,是到南昌后最初几天睡觉中所有的。当时我正因南京之行的不成功而忧忧不乐,又因旅途劳累而进入梦乡。看见迎面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对我说:“你就是在这里要消灭古传的宗教而宣传天主的宗教吗?”我听后非常惊讶,这人怎会知道我心内的事?便问他道:“你是魔鬼?或是神明?”他回答说:“我不是魔鬼,我是天主。”我闻声跪地叩拜,流泪痛哭谓:“主啊,您既然知道我的心事,为什么不帮助我啊?”他回答说:“你可以到那座城里去!”当时我懂是指北京而言——“在那里我要帮助你”。[2]185-186
很显然,由于长期戴着面具生活,身心俱疲的利玛窦才会在梦中出现幻觉。但另一方面,这个神秘梦境也透露出利玛窦深藏不露的真正用意:易换儒服等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计划中的北京之行,其最终目的不是渡化身边身穿同样儒服的文人,而是渡化号令天下的皇帝,因为这才是改变清王朝的唯一希望。
在许多相关著述中,耶稣会士习惯结交社会上层的行为策略被批评为“上层路线”,但换一个角度看,在专制制度高度发达的远东尤其是日本与中国,势单力薄、得不到强力后援的耶稣会士们别无选择,如果违逆统治阶级的意愿,不仅宣教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会立即丧失本已岌岌可危的生存空间,日本将军或中国皇帝一声令下就足以毁掉他们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可怜成就。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最初的僧衣还是后来的儒服,耶稣会士朝三暮四的形象包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获得统治阶级(包括构成其社会基础的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无论这一外在标志有怎样的内在含义,在利玛窦等人眼里都不过是升级版的通行证和护身符。
五
利玛窦两次易服的本质并无根本差异,其着眼点都在于它的社会效应,即为了获取或拓展生存、发展的政治空间;两次易服显然不是自愿,而是迫于生存压力的无奈之举,是向社会上层和主流意识的屈从,传教士们一再更换的新衣就是他们的通行证与护身符。我们甚至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如果得到清王朝的传教许可,或许有更多传教士不会介意像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那样再次易服,改穿清朝官员的皇袍马褂。
另一方面,身穿儒服并不能使利玛窦成为真正的儒者,也不意味着他对儒学的认同,更不能说他已接受儒家的政治理念。所谓“容古儒、批新儒”的选择性策略,其实质是阉割儒家忠孝伦理的道德前提,为上帝信仰的传播开辟一条通道。作为排他性极强的一神论基督教神学及其传播者,利玛窦们不可能容忍凌驾于教权(教会)甚至神权(天主)之上的皇权(天子)。也正因如此,耶稣会士在士大夫中间的传道远不如他们宣扬的那样成就辉煌,而且,最终还不可避免地触发长达数百年的“礼仪之争”。所谓“合儒、补儒”或“驱佛补儒”,既不是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它可能缘自徐光启等人为消除士大夫戒备心理所做的文过饰非的行为,但后来却在某些现代理想主义者的想象中逐渐沉淀为诱人的乌托邦。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易服这一形象的改变是耶稣会士们在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东方普遍采用的策略,而在幕后导演这一出出精彩剧目的关键人物,即文化适应政策的真正确定者,则无疑是当时东印度教区的最高上长、耶稣会视察员神父范礼安。就像巨网中心的蜘蛛,这位被利玛窦称作“中国教区之父”[2]319-320、被教会历史学家誉为“集亚历山大雄心和汉尼拔铁腕于一身”[12]61-62的重要人物,是研究并破解许多历史迷局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关于利玛窦易服的时间与地点有不同说法,鉴于易服时间和地点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取计翔翔先生的考定结论,参看计翔翔《关于利玛窦戴儒冠穿儒服的考析》,见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此外,相关研究著述还可参见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未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林仁川、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萧濬华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法]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于硕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法]安田朴、[法]谢和耐等《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耿昇译,(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等等。
②另据夏伯嘉摘引的意大利文版利玛窦著作集,罗明坚在1583年2月7日的信中明言,“两位耶稣会士脱下了黑色短褂,穿上了棕褐色或蓝灰色的中国僧袍”。转引自[美]夏伯嘉《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向红艳、李春园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③卡布拉尔在1593年12月15日写给总会长的信中愤愤不平道:“……当时耶稣会士们身着丝绸,装饰华丽……耶稣会士这样考虑,如果废除丝绸与华美装饰,身穿黑布的修道服,遵循我们的规则在谦逊与清贫中生活,那就会成为推进(改宗)的障碍,不仅无法进行改宗,而且还会使已有的成果减少,领主们也许会不再注意我们。他们顽固地坚信这一点,在我向他们提出反驳、对他们全体以及某些个人进行说教时,虽然在这一生活态度方面,我宣称这是管区长命令我实施的,但结果除了洛佩斯(Baltasar Lopes)神父之外,全体(修道士)都反对我。”高瀬弘一郎編『イエズス會と日本』,高瀬弘一郎訳注,见『大航海時代叢書』第Ⅱ期,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第124-125页。
④据考证,当卡布拉尔巡视京都教区时,一位教督徒武士曾鼓励他说:“传教士应当穿着上等服装,虽然一开始看起来有些别扭,但不久就会习惯了。”而河内的另一位教督徒武士却表示了不同看法:“应该让人们知道,神父们放弃了丝绸(衣服)而改穿朴素的棉布服装,这不会引起异教徒的嘲笑。”他甚至鼓励卡布拉尔说:“您是我们的榜样。神父们不应该拒绝穿着特别的服装,它可以让神父们显得与众不同。不必担心脱下丝绸衣服而丧失人们的尊敬,或者妨碍神的教义的传播。”见松田毅一『南蛮史料の発見:よみがえる信長時代』,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64年,第88-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