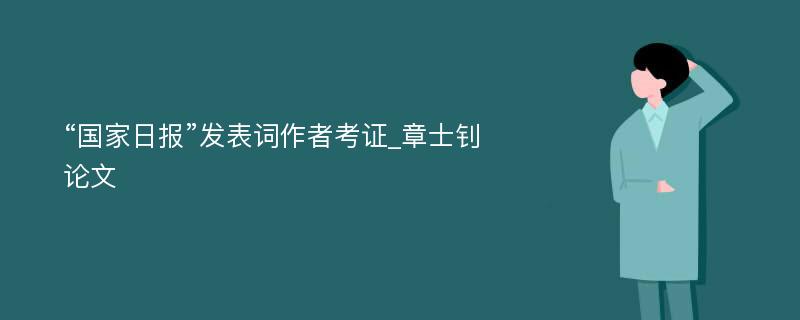
《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作者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刊词论文,国民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创办于1903年8月7日的《国民日日报》,是继《苏报》之后又一份革命报刊,继承了《苏报》宣传革命的宗旨,创刊号刊发的《发刊词》不仅是指导办报的纲领方针,也反映出报刊编辑的办报理念。考证《发刊词》的作者究竟为谁,不仅可以还原史实,也可以理清彼时陈独秀、章士钊二人的新闻理念,更可以为研究陈独秀早期的新闻理念提供“可靠”的文献。 关于《发刊词》的作者,多数观点认为是章士钊,持此观点者包括白吉庵、张之华、李开军等。[1]沈寂则认为《发刊词》应为陈独秀、章士钊合撰[2]。前一种观点建立在章士钊作为报纸创办人,《发刊词》理应由章撰写的基础上;后一种观点则建立在陈独秀与章士钊一起创办《国民日日报》的基础上。上述观点虽然不同,但都不是建立在细致的文本比较的基础上,猜想成分居多。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相关文本,认为《发刊词》应为陈、章合撰。 一、《发刊词》对松本、梁启超二人新闻观念的引述 (一)《发刊词》表达的新闻理念及对报界现状的描述[3] 《发刊词》作为指导办报活动的方针,反映了作者的新闻理念,文中必然运用相关新闻理论作为论据,也必然对报界现状进行描述。《发刊词》中涉及的新闻理念及对报界现状的描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之母的舆论观 文中有三处类似的表述:“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如林肯为记者,而后有释黑奴之战争,格兰斯顿为记者,而后有爱尔兰自治案之通过。言论为一切事实之母,是岂不然。”“虽然,言论者必立于民党之一点而发者也。有足为事实之母之言论,必先有为言论之母之观念。” 以上表述时用“舆论”,时用“言论”,虽然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即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之母,但“舆论”与“言论”的混用,表明这篇发刊词应由报刊同人合作完成。 2.“第四种族”说 《发刊词》对“第四种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对“第四种族”做了界定,“第四种族者”是“对于贵族、教徒、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另成一绝大种族者”,亦即“由平民之趋势,逶迤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的所谓“新闻记者”。在此基础上,《发刊词》论述了“第四种族”与“舆论”的关系,“第四种族”为“一切言论之出发地”,“舆论”由“第四种族”“尸之”,“自十九世纪欧洲有所谓第四种族之新产儿出世,而舆论乃大定。” 《发刊词》还论述了“第四种族”的产生条件及其与“平民种族”的关系。“第四种族”必待“贵族与平民之界既分”,“平民得与于三大种族之列”,然后依“平民多数之志望”,“并合发表”,于是平民也得“足以抵抗贵族教会而立于平等之地位”。关于第四种族与平民种族的关系,文中作了这样的论述:“新闻学之与国民之关切为何如,故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此处把“新闻学”与“国民”的关系等同于“第四种族”与“平民”的关系,表明作者认为“第四种族”与“新闻学(实指新闻界——笔者注)相同”,“平民”与“国民”相同。 《发刊词》还批评了中国第三种族与第四种族的现状,“中国民族之历史,言之实可丑也……至于今日……号称数万万,宁可当欧洲第三种族之一指趾哉?第三种族于沉沦,至于此极;而望第四种族之间起而勃兴,胡可也!然第三种族之沉沦,至于此极,而不升高以望第四种族之间起而勃兴,又胡可也!”上述批评性表述,其目的在于阐述报纸的宗旨,“愿作彼公仆,为警钟适铎,日聒于吾主人之侧……” 3.“国民向导”说 《发刊词》还表达了“向导国民”的志向,“呜呼!中国报业之沿革如是,国民之程度如是,而欲蔚成一种族,吸取民族之暗潮,改造全国之现势,其殆不能乎?其殆不能乎?故以吾《国民日日报》区区之组织,詹詹之小言,而谓将解脱‘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则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颂新闻记者),诚未之敢望。……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作者认为,以区区《国民日日报》之詹詹小言,虽然努力解脱“国民”、向导“国民”,但不敢奢望做到松本君平称赞记者像裁判官,如救世主的地步。 4.对中国报业沿革的批评性表述 《发刊词》还对中国此前30年报业发展做了批评性回顾。“中国之业新闻者,亦既三十年,其于社会有一毫之影响与否,比可验之今日而知之者也。有取媚权贵焉者!有求悦市人焉者;甚有混淆种界,折辱同胞焉者。求一注定宗旨,大声疾呼,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者,概乎无闻。有之,则又玉碎而不能瓦全也。”这种批评性的回顾,是为了表明中国报业不尽如人意,其目的在于表明该报的坚定宗旨。 (二)松本君平、梁启超二人相关新闻理念的论述 此处主要对松本的《新闻学》以及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馆之经历》(简称《祝辞》)、《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简称《舆论》)、《敬告我同业诸君》(简称《敬告》)等三篇文章进行分析。依据在于,上文举列的《发刊词》中相关新闻理念与上述两人的著述关系密切,部分内容甚至为直接引用。[4] 1.《新闻学》对“第四等级”及相关论述 松本在《新闻学》第一章“第四种族之发生”中,专门论述了第四等级的发生,原文如下: 第四种族者何谓也?贵族、僧侣(欧西之教徒)、平民,为构成国家之三大种族。而其称第四种族者,发生于近世纪,而为社会之一大现象,一大革命家。其职任既非如贵族之夸耀人爵,又非如教徒之祈福未来,且非如平民之行尸走血,隶马奴牛。彼盖以明敏之才干,灵秀之神经,握区区一管,以指挥三大种族之趋向,即构成国民之三大阶级,而有天赋与使命之大种族也。其种族为何?即指新闻记者之一种族而已。英之普鲁古氏,曾在英国下议院指新闻记者而喟然叹曰:是英国组织议会之三大种族之力(贵族、僧侣、平民),而有最伟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今者,无论贵族也、僧侣也、平民也,皆不得不听命于此种族之手。彼若预言,则可以征国民之运命;彼若裁判,则可以断国民之疑狱;彼若为立法家,可以制定律令;彼若为哲学家,可以教育国民;彼若为大圣人,可以弹劾国民之罪恶;彼若为救世主,可以听国民无告之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其视力所及,皆有无穷之感化,此新闻记者之活动范围也。[5] 近世新闻纸,所以有此大力者,盖以新闻为舆论之引火线,而又为舆论之制造器也。故国民之意见,常随有卓识之新闻记者为转移。以是其一抑一扬,足以决彼等运命之浮沉;其一毁一誉,即可为最后舆论之宣告也。[6] 该书《叙论》“近世文明与新闻之德泽”中,还有如下论述: 若夫乘此潮流,涨进之,充足之,唤发人类思想之自由,益助此文运进步者,则惟近世之新闻事业也。然新闻之于社会,所以有此猛大势力者,全在创立近世文明之基础与发达思想之自由,而使之永进化而不止。是则新闻之与社会,相为因缘。社会之进运日益强大,而新闻之发达,已从可知也。[7] 此外,该书《原序》[8]中,还有相关文字论述此点: ……今也新闻纸,至能夺此能力。……此果何故耶?曰:在平民时代,不外代表国民中最聪强、最高尚之思想感情而已。盖平民时代者,非谓以多数人民之意见为国政之标准,乃以国民中之最聪强、最高尚之思想感情,为多数国民之向导,且由其力而可疏通国政也。……曰言之,则新闻纸即国民之本身也。[9] 由上可知,松本的《新闻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第四等级”(新闻记者)的定义、产生时间及作用,《序论》则阐释了近世文明与新闻业之关系,认为两者相互因缘,互为涨进。该书所附《原序》则特别强调了“平民时代”记者可为多数国民之向导的重要性。 2.《祝辞》有关“第四阶级”的论述 梁氏的三篇文章只有此文论述了“第四阶级”,内容如下: 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英国议员以贵族、教徒、平民三阶级组织而成,该英国全国民实不外此三大种族而已。)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歌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预言者,讴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最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为一切文明之母。 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10] 比较该文与《新闻学》的论述,可知梁文关于“第四阶级”的论点来源于松本,但梁文对“第四等级”的论述则非常简单,且用“报馆”代替“新闻记者”,把《新闻学》中对“新闻记者”的称赞改为对“报馆”的称赞,这种替代反映了在梁的意识中,“新闻记者”与“报馆”为同一指称。梁文又以林肯、格兰斯顿为例论证欧美报馆言论的重要性,这两个事例是《新闻学》所没有的。[11]值得注意的是,梁文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实为一切文明之母”的观点。 3.《舆论》对“舆论之母”的论述 梁氏在该文中,论述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辩证关系,内容如下: 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爱存也。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惟其尽为仆之义务,故能享为母之利权。……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12] 这段文字辨析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关系,但此处的“舆论之母”概念与上段“‘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实为一切文明之母”的观点是不同的,“舆论之母”指向豪杰(或进步报馆);“文明之母”则指向“三大自由”。 4.《敬告》对报馆“两大天职”的论述 梁氏在本文论述了报馆具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两大天职的观点: 所谓监督政府者何也?……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拿破仑尝言:“有一反对报馆,则其势力之可畏,视四千枝毛瑟枪殆加甚焉。”……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而岂以主文谲谏毕乃事也。…… 所谓向导国民者何也?……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义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大抵报馆之对政府,当如严父之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几谏,委曲焉,迁就焉,而务所以喻亲于道,此孝子之事也。[13] (三)《发刊词》与松本、梁氏相关论述的比较 对比《发刊词》与松本、梁氏的相关表述,可知《发刊词》的相关表述来自松本与梁氏。因此,可以做这样的推论:上述两人的论述为《发刊词》提供了理论来源,《发刊词》作者应该读过上述两人的著述。当然,《发刊词》的相关表述与松本、梁氏仍存有一些不同。 1.《发刊词》对松本“第四阶级”说进行了“发挥” 《新闻学》虽然论述了“第四等级”(新闻记者)的定义、产生时间及作用,但没有交代“第四种族”产生的原因。该书所附《原序》对“平民时代”的强调虽可理解为平民时代是新闻记者(第四阶级)产生的重要背景,但通观《新闻学》,松本没有对“第四种族”的产生作阐释。[14]《发刊词》则指出,“第四种族”即所谓“新闻记者”,“第四种族”是由“平民之趋势,逶迤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其职业志向为监督贵族、代表平民。《发刊词》还认为,第四种族的产生必待“贵族与平民之界既分”,“平民得与于三大种族之列”,然后依“平民多数之志望”,“并合发表”而为“第四种族”,于是平民也得“足以抵抗贵族教会而立于平等之地位”。 应该说,这种关于“第四等级”形成的解释是不科学的,但反映出作者尝试运用域外新闻理论观照中国现实问题的努力。如果考虑到清末社会语境下“国民”与“平民”的同构性,这种解释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民族危亡时期,“第四种族”与“平民”关系确实很密切,清末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发刊词》虽引用了松本“第四等级”的理论,却多有发挥。 2.舆论(言论)之母的论说与松本、梁氏论述的差异 上述松、梁二人的著述均对舆论的强大力量表示了膺服,如松本“故国民之意见,常随有卓识之新闻记者为转移”的表述,梁氏“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以及报馆通过舆论手段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两大“天职”说等表述。两人也都论述了新闻与文明的关系,松本认为近世文明与新闻业互为因缘,相互涨进;梁启超则进一步认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实为一切文明之母”。可以说,梁氏的观点是从松本的观点发展而来,但两人均没有明确提出“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之母”的观点。 梁氏与《发刊词》均使用了林肯、格兰斯顿的例证,但两者论证的观点是不同的。梁氏的目的在于阐述“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的原因;《发刊词》则是为了得出“言论为一切事实之母”的结论。因此,《发刊词》“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事实)之母”的观点,虽源自松本与梁氏的相关著述,但内涵却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发刊词》的观点还比较模糊,比如“舆论”与“言论”不分、“事业”与“事实”混用,但这一观点本身蕴涵的含义已经超出上述二人的相关论述。 由上述分析可知,《发刊词》作者不仅读过上述松本、梁氏的相关著述,而且进行了深入地思考。 二、创办《国民日日报》前,陈独秀与章士钊各自的新闻理念 创办《国民日日报》前,陈独秀与章士钊均发表过能反映其新闻理念的文字,这为比较两人的新闻理念提供了可能。[15] (一)陈独秀创办《国民日日报》前的相关新闻理念 陈独秀在参与创办、编辑《国民日日报》之前,虽未曾办报,但却留有相关报刊言论文字。如第二次演说会期间,发表于《苏报》、署名为“皖城爱国会同人”的《开会之启》中即有“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文字[16],这八字与《发刊词》中“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有足为事实之母之言论,必先有为言论之母之观念”暗合。此外,在陈独秀拟定的《安徽爱国社拟章》中“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17]的论述与《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21日所刊《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18]一文对《清议报》、《新民丛报》所使用“揭”、“攻”、“诋”、“骂”、“嗤”、“聒聒”等词所持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第一点表明了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之前即有“思想言论,事实之母”的观点,后一点表明陈独秀对《清议报》、《新民丛报》作了批判性的阅读。 (二)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日报》前的相关新闻理念 章士钊在创办《国民日日报》之前,曾任《苏报》主笔。作为《苏报》主笔,以下三篇论说极有可能是章士钊所写,即便不是其所写,文章观点也为其赞同,反映了他的新闻理念[19],具体如下: 论湖南官报之腐败(5月26日) 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此报馆之天职也……吾为此言,非谓官场人人与国民反对,事事与国民反对也,若以报馆而论,则官场视之当如神圣不可侵犯,而业报馆者之应付官场,当如严父之教训其劣子,丝毫不肯放过,则岂有官场与报馆合而为一者哉,以泰西宪法之精美权限之确立,而□报馆犹视为绝大之监督,拿破仑日,有一反对报馆其势力之可畏,比四千枝毛瑟枪尤甚焉…… 报也者,文明之现象也,报归官办,文明国之所绝无者也,文明国之所无,野蛮国或有之。今吾国既出此野蛮之报,然则报尚得谓之文明之现象耶,呜呼…… 论报界(6月4日) ……夫报馆者,与社会为转移者也……虽然以社会之进步为报馆之进步,非报馆之性质也。报馆之性质,乃移人,而非移于人者也,乃监督人而非监督于人者也。唯有此性质是必出其强硬之手段,运其灵敏之思想,无所曲循,无所胆顾,对于政府为唯一之政监,对于国民为惟一之鄉道,然后可以少博其价值,而有国会议院之倾向。 吾国报馆之无价值久矣,迁就于官场,迁就于商贾,迁就于新旧党之间,下至迁就于荡子狎客,而稍有不用其迁就者,必生出种种之反对,反对尤甚,莫如官场,以其性质本不伦,而今日又报界黑暗官场婪戾之时代…… 读新闻报自箴篇(6月30日) 今者若朝若野均有其捕拿革命之好名词。以图升迁,以谋異赏。而为此时代之交通机关者,实惟报章与新旧有直接之关系者。……吾于是净瞩中国有名之报章,察其宗旨之果坚定与否。□论之果足助长风潮与否,而不得不放声为报业哭…… 细读上述三篇论说,可以发现,章氏的持论与梁氏的论点有胶合之处,而且主要来源于梁氏的《敬告》,其对报刊监督政府的观点以及所引拿破仑的言论,均表明《敬告》—文对章氏的影响。章氏对其时报业现状的批评也源自于梁文,当然章文对报业现状的批评显然比梁文有所发展,而且与《发刊词》中对报界现状的批评相合。但是就《发刊词》中最为重要的“第四等级”与“舆论(言论)为一切事业之母”的论点,则无一笔。这说明章士钊此时(1903年6月)只受到了梁氏《敬告》一文的影响,似乎他只阅读了《新民丛报》,而没有阅读过《清议报》与《新闻学》。 由上可知,章士钊肯定参与了写作,而《发刊词》部分内容也暗合陈独秀的理念。 三、相较章士钊,陈独秀接触松本、梁启超相关著述的可能性更大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发刊词》的作者应该阅读过松本、梁氏的相关著述。第二部分则从理论上证明陈独秀参与写作《发刊词》是可能的,而章士钊则肯定参与了《发刊词》的写作。然而,这还不能排除章士钊独撰的可能性。如果章士钊在《苏报》停刊至《国民日日报》创刊的短短一个月内,阅读了松本、梁氏的新闻著述,就有可能排除陈独秀参与写作的可能性。以下即对陈、章二人接触松本、梁氏著述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以此论证陈独秀参写的可能性。 (一)两次留日让陈独秀具备了阅读松本、梁氏著述的可能性 陈独秀第一次留学日本是在1901年11月,到东京后,陈独秀就参加了当时留学生中唯一的团体“励志会”,而“励志会”即有专门的“译书汇编社”,出版《译书汇编》月刊。[20]该刊第七期(1901年7月30日)所载“已译待刊书目录”中,第23种即为松本的《新闻学》。然而《新闻学》一书最终未刊载,陈独秀也因政见不一退出了“励志会”。因此,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独秀在日本读过《新闻学》。然而相较于章士钊,陈独秀毕竟近水楼台,而且陈独秀对西学有着浓厚的阅读兴趣。1902年3月在安庆发起藏书楼,该藏书楼被安庆官方及保守派称为“西学藏书楼”,所藏书籍也是陈独秀第一次留日期间收集的西学书籍[21]。不仅如此,陈独秀此时办报愿望强烈,1902年曾拟办《爱国新报》,1903年再次表达了创办报纸的愿望。因此,留日期间阅读《新闻学》是极有可能的事。 梁启超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先觉者、启蒙者,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均在日本发行,且在留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上述梁氏的三篇论述刊发时间分别为,《祝辞》(《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12月),《舆论》(《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敬告》(《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上述文章发表时,陈独秀恰在日本留学。因此,陈独秀阅读《清议报》、《新民丛报》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章士钊接触松本《新闻学》、梁启超《清议报》的可能性较小 由前述章士钊在《苏报》上发表的论说可知,章氏接受了梁启超在《敬告》中提出的新闻观点。然而章氏是否在此之前接触过梁氏其它两篇论说呢?是否阅读过松本的《新闻学》呢?又是否可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接受了松本、梁氏的新闻观点并有所创造发挥呢? 松本的《新闻学》虽由商务印刷馆于1903年印行,但大范围的发行、形成影响则应在1904年[22],而章氏的办报活动则主要集中于1903年。因此,理论上章氏是有可能看到《新闻学》,但是如果考虑到在短短一个月内,阅读、接受《新闻学》,进而有所创造发挥,实现思想资源的转变,这种可能性则是微小的。 《苏报》案的发生,章士钊义兄章炳麟、义弟邹容作为主犯牵涉其中,章氏必须出手营救,《国民日日报》对“沈荩案”的高度关注即是章氏出于营救章、邹二人的考虑。不仅如此,按照白吉庵在《章士钊传》中的论述,《苏报》被封后,章即从事“实际工作,又开始与黄兴加强联系,计划如何开展革命工作”。他是在送走黄兴后,才刊行《国民日日报》。而且即使在编辑《国民日日报》期间,章士钊还“抽出时间,去推行他与黄兴议定好在南京方面的工作”[23]。可以说,《国民日日报》创刊前后章士钊都在从事“实际工作”。这种情况下,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思想资源的转换,由关注报馆转向关注记者,是有困难的,况且《新闻学》的大范围传布则是在1904年。因此,章士钊在创办《国民日日报》前,阅读松本的《新闻学》并进而有所发挥是有困难的。 那么,章士钊是否阅读过《祝辞》、《舆论》两篇文章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微弱的。如前所述,上述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和《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敬告》一文则发表于1902年10月第17期。需要指出的是,《敬告》与《舆论》发表时间相隔八个月,而且《新民丛报》一经创刊旋即取代《清议报》成为新型知识分子阅读的主要刊物。 章士钊则于1902年3月才东下南京,同年夏入读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4月退学赴上海参加爱国学社,5月任《苏报》馆主笔[24]。东下南京前,章主要忙于生计,因而读到《清议报》的机会非常微小。1901年12月《清议报》即因火灾而关张,新刊的《新民丛报》旋即取代了《清议报》的地位。入读南京陆师学堂期间,章士钊是有可能阅读《新民丛报》的[25],但读过《新民丛报》并不意味着也看过《清议报》,甚至也不意味着读过《新民丛报》创刊号。事实上,章士钊刊发于《苏报》的论说在显示梁氏《敬告》一文影响的同时,也透露出他没有读过《祝辞》一文。《苏报》论说中用拿破仑的话作为例证与《发刊词》中用格兰斯顿、林肯作为例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更何况,退学去沪后的章士钊全力投入书报宣传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章氏能否重翻已经落伍的《清议报》是大可怀疑的。 由上可知,相较于章士钊,陈独秀不仅有可能接触松本、梁氏的相关著述,而且也有“充裕”的时间“改造”松本、梁氏的论点。 尽管没有确切“史实”来“坐实”陈独秀与章士钊合撰了《发刊词》,但是通过对相关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认为陈独秀参与了《发刊词》的写作。这种讨论是必要的,既有利于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有利于辨清陈、章二人的报刊主张,更有利于研究陈独秀早年的报刊实践及新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