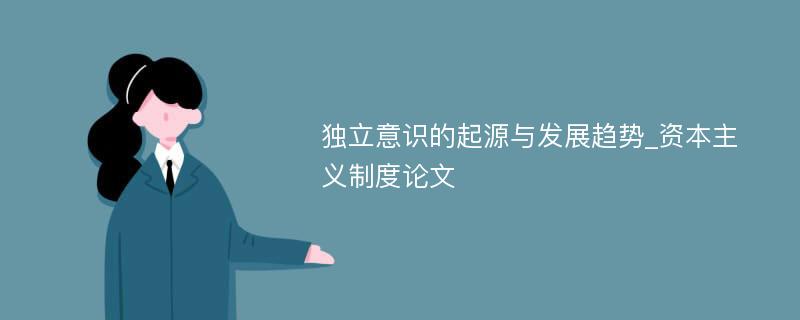
自主意识的由来与必然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由来论文,自主论文,意识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自主意识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的产生与成熟同文艺复兴的文化批判有着不解的文化渊源关系。自主意识是现代人必备的意识品格,也是创造现代生产力与建构民主政体必备的心理素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必须大力提倡自主意识,批判非自主意识,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输入必备的心理条件。但个体本位的自主意识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它必然被集体本位的自主意识所代替,这是自主意识发展的必然趋势。
商品经济建构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革新了人的内部世界,也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与人的解放,其中模塑了具有自主意识的人是它所创造的辉煌的文化成果。党的十四大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自主意识与发展商品经济有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它的命运与发展的趋势怎样?这个问题应该是理论界重视和研究的课题。
一、自主意识的由来
自主意识是一种充分意识到个体的存在、价值、意义,并依据个人的目的去设计人生,依靠个人的奋争去实现自我价值的明确的意识;是一种有主体归属,由自我主持的独立意识;是一种张扬个性,突出新奇、表现独特的异质意识;是一种讲究人性、捍卫人权、追求人道的为人的意识。
自主意识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然的平等物”,商品交换的双方都以自己的需要为目的,遵循价值原则、平等原则,换取对方的劳动或产品。交换中的任何一方都必须尊重对方的商品所有权或劳动,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这种互相认同、彼此独立、自由自愿、平等交换、等价原则等以及它只认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格,不问及商品所有者的身份、地位、背景的特点,使得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为了生存、发展,必须追求独特的创造和高效益的劳动。从而使人们的目光从瞄着别人而转向盯着自己。它唤起了每个人跃跃欲试与奋争、搏击的冲动,使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为自己而搏动的灵魂。可以说,自主的意识正是萌发、成长于商品经济这片沃土上的。
自主意识的萌发、成熟还与文化的批判有关。开始于16世纪而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自主意识萌发、形成的催化剂。启蒙运动的主旨是什么?哲学巨匠康德的一段话深刻地指出启蒙运动的主旨。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译注)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①a]黑暗漫长的中世纪是神喻的文化,基督教把人的存在归结到灵魂,又以外在的人格化的神主宰人的灵魂。内在无自我的灵魂宣判了鲜活生命的死亡,外在教皇、教会的专制统治又无情地剥夺了人极其可怜的肉欲享受,人以“高洁”的灵魂控制着“罪恶”的欲念;不仅如此,人还要受到教会的监视、鞭挞、训斥乃至酷刑的惩罚。文艺复兴正是在人受了千余年的压抑后爆发的,宗教的虚伪、罪恶成为它怒斥的中心,呼喊人性的苏醒成为它主要的宗旨。文艺复兴运动一手抓住人的理性,一手牢握人的自然权利,将理性注入灵魂,将自然权利复归肉体,给人以平等、自由、理性。文艺复兴运动推翻了神学、经院哲学的权威与教义,第一次以人的尺度取代了神的地位,不仅唤醒了被封建意识、宗教教义压抑、泯灭了的人的天性,也净化了社会的文化氛围。自主的意识逐渐扎根于人心的深处,并成为社会的共识。
最初的自主意识以张扬个人的权利为基调,呼唤各异的、新奇的个体意识。这是因为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残酷无情地剥夺人性、人权,横征暴敛的剥夺在人内心积聚了反抗的欲念,在这片憎恨人、无视人的土地上掀起的文化批判,其锋芒必然首先指向人性、人权。人文运动对人的弘扬程度正是中世纪对人的剥夺程度的测量器。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发动的启蒙运动以及它对人性、人权的论述都不尽科学。但不管怎样,在反对封建宗法的意识与制度,在批判宗教的伪善与罪恶的斗争中,它都曾发挥过巨大的积极的作用,它是一次伟大的人的解放运动,它第一次使人由他人摆布的盲目力量上升为自主的、独立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璀璨夺目的文化成果,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
二、对自主意识的认识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主意识与商品经济互为因果。商品经济是自主意识产生的源头,但它一旦发育成熟又成为发展、推动商品经济的文化动力。
自主意识是个体的意识、独立的意识,有着强烈的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欲望,这正是启动创造、施展创造的最深刻的内在根源,也是创造千姿百态、殊相万千世界的心态源头。这与商品经济所提倡的卓越、新奇、独特,以优取胜、以新取胜、以质取胜是吻合的。在商品交换的市场上,只有敢于出新、创优,才能独占鳌头。
商品经济是法制的经济,这就要求具有强烈法律意识的人与之相呼应。实践证明,只有具备了自主意识的人才能遵纪守法。从表面看来,自主意识的价值取向是利己的,因为无论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还是商品的消费者都要千方百计地实现商品交换利润的最大化,或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最大化,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但从深层去分析,正因为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市场交换才实现的,这就决定了进入市场的人,其行为不再是孤立的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性的行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市场不再是卖方市场,而是买方市场,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商品,获取利润,必须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市场也要制定相应的保护商品的生产者、所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害的法规法律,规范市场行为,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公开,使市场正常运转。双向的需求与相互的认同,使得利他的价值取向逐渐渗透其中,并积淀于每一个进入市场、参与市场行为的人的内心,形成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人所特有的价值取向。自主意识的人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要维护个人的尊严,实现自我的价值,也必须想方设法得到他人对自己的尊重与认同。这样,就不能不关心他人的需求与利益,无论自我情愿不情愿,他人的需求、利益都会以反馈、折光的形式渗入自我意识之中,成为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重要参照。同时,自我要保护自己,维护自身的权利,必须关心社会环境的净化与完善,投身到社会环境的治理与建设之中,这样,民主、法制、文明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建起来。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自主意识的欠缺带来的问题是严重的。欠缺自主意识的人没有自立的、自主的意识,更没有法律、契约的观念,也缺乏现代人所应具备的人格和自尊意识。这样的人,在强权政治与小生产的模式下,俯着贴耳、唯唯诺诺、麻木不仁;一旦跨入政治约束力相对弱化并充满各种利益诱惑的经济模式中,便会失去理智,胡作非为,以一孔之见、一己私利来曲解社会的规范,伺机钻法律、法规、政策的空子。他们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义务,不知道合理合法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协调好人际关系,他们不会为自己在社会中定位,更不能以合法的手段去谋求合理的利益,捍卫合理的权利。许多时候,即便是侵犯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也茫然无知,毫无感觉。因此,文化批判与文化建构要想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当务之急是大力弘扬自主意识。
当前,我国民众自主意识的欠缺是有深刻根源的,主要有:
1.生产力的落后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限制和阻碍了人的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及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必须看到,我国国民经济中农业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村的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模式从总体上讲依然是小生产的规模和粗放型的经营,科技含量很小,大多数农民沿用的依然是世代相传的耕作方法。生产模式、生存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依旧保留着小生产的思维方式及心理素质,拖着小生产的尾巴涌入商品经济的大潮。
2.文化批判没有找准突破口。经济不能直接作用于人、改造人,它要通过文化层面——即通过对人的心理、意识的作用后才能改变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掀起了几次文化热潮,文化批判、文化建构的活动空前活跃,但遗憾的是它没有真正抓住人的素质欠缺的关键点。我国自近代以来,文化批判多是出于理想,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根源”触及不够。
本世纪最有力量的文化批判当属“五四”运动,它亮出“赛先生”、“德先生”的旗帜,给古老、愚昧、专制的中国吹来一股强劲的清新之风,统治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偶像被推翻,律条被批判。城市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在民族工业发展的推动下,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农村中受尽地主压榨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揭竿而起,对封建制度发出了强有力的抗争。应该讲,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所受到的最猛烈的讨伐和冲击,历史意义非同凡响。但70多年后的今天,封建思想依旧有不小的市场,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新文化运动批判的重点不够准确和深刻。拿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做比较,由于历史条件、人文传统的不同,两者之间有很多的差异,但主攻方向是一致的,两者的任务、攻击的矛头都是针对封建制度。可从文化效果来看,文艺复兴开展的启蒙运动的效果大大超过新文化运动。欧洲正是借助这一成果,肃清了封建文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民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人文基础。这不能不归功于启蒙运动批判封建文化的核心找得准确。它以人的自然权利的复归作为突破口,而这正击中了西方封建文化的要害。以血缘宗亲维系的封建世袭制就是以人的先天不平等为依据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紧紧抓住这一点,大力宣传“人生而平等自由”,“人人生来平等”,“自由、平等、博爱”,这就击中了封建制度的关键,使人从先天的血缘、门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击碎了迷信、奴性的精神枷锁和专制政体的要害。而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却没有击中我国封建文化的要害,它宣扬的“赛先生”、“德先生”是人解放后的“果”,而不是“因”,即只有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生来和别人是一样的,他才会重视理性,自主、自立,要求民主政体。我们开始打出的口号原是思想解放后的结果,所以有着极大的感召力、诱惑力,人们期待着依靠科学和民主来拯救中国。但何以能够让“赛先生”、“德先生”在中国扎根,安家落户,我们的文化批判在这点上的火力却远远不够。对造成非自主意识的根源一直触动不深,文章停留在表面,因而得到的成果就不扎实,封建的东西一有机会就得以滋生、蔓延。
资产阶级发动的文化批判不能不受到阶级的局限,它能要求人的自然权利的平等,但不可能提倡和要求人的社会权利的平等。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回自然权利后,它就止步不前了。无产阶级在这点上远比它先进、彻底。无产阶级不仅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平等,而且致力于人的社会权利的平等,积极创造条件为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过渡到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而努力实践。但人的社会权利的平等不是沙丘建塔,它的根基应该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平等。我国在这方面的欠缺在于对人的自然权利复归的呼喊、批判的工作做得太少,以致很多人以为人的平等不必也不应强调什么自然权利上的平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使劳动人民一下子在社会权利上获得了平等。与此同时,又认为人的血统有贵贱之分,于是认同门第、认为人在自然权利上的不平等的思想就大量存在。试想,在这样的人文前提下,社会权利的平等观何以能建立、巩固呢?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跨越”式革命带来的成果,制度可以跨越,但人的素质的跃升是个渐进的过程,为了使制度更巩固、完善,必须在提高人的素质上下功夫,这已是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搞得不好,改革之舟将停滞不前。
这样讲不是说形成于西方的自主意识是十全十美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个体为本位的自主意识的不足已日见端倪。正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延续、重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老路一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主意识的走向也应与西方的自主意识有所不同。
三、自主意识的必然走向
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熔铸了自主意识,而资本主义制度又束缚、限制了它,甚至把它引向了歧途。
1.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它公开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意志至上等等,使社会总体的价值取向都围绕着“钱”字、“私”字运转。这一价值取向就把人的发展逐步引向歧途,人成为疯狂的拜金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社会机体中难以生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社会日显病态。恩格斯说过:“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①b]这瓦解了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拉大了社会的不平等。个人无节制的行为,势必损耗社会整体继续前进所需要的能量,使社会放慢、甚或停止了前进的步伐。显然这与个人企盼的社会进步、个性解放的要求相悖。对病态社会的不满情绪反过来又消磨了个人的积极性,于是无奈、愤懑、烦燥、堕落之风弥漫社会,带来一系列毁灭个体的社会悲剧与社会问题。这一现象几乎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
2.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所有者与商品生产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分离的,广大的生产者和劳动人民与自己的创造物是“异化”的,商品生产者在商品所有者面前只能被动地、被驱使地干活,为了养家糊口,屈从于分工,片面地发展自己,淹没了潜质,成为畸形发展的人,自主意识所提倡的“张扬个性”、“关注人”的初衷被严重扭曲,逐渐沦为“为他”的意识,“为物”的意识。
3.自主意识萌发、成熟于文艺复兴的人文运动。人文运动以人的自然权利为武器,彻底粉碎了封建宗法及神权笼罩在人的血统、出身上的神秘性与先天的不平等性,在反封建的革命中曾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它忽视甚或否认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认为靠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就是绝对平等、自由的社会制度,由此暴露出人文运动开创者的局限性。虽然先天自然权利的平等复归到人的身上,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后天的不平等同样拉大了人与人的距离,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虽说商品经济造就了机会的均等,但成功的几率是多种参数的综合,其中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和社会地位是重要的指数,直接影响成功与否。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形式和收入分配形式,可以促进生产力要素的最佳组合,带来效益和利润。但它只是一种经济的调节手段,并非万能。何况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认同财产不平等的合理性,这必然拉大资源配置及分配上的不平等,进一步分化、扩大了人后天的不平等性。对两手空空的穷人来讲,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演绎“灰姑娘”的故事,也如同神话传奇一样少而又少、罕而又罕。可以肯定地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不是解放所有人的理想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的劳动人民第一次由被剥削者上升为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为在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权利的基础上讲求集体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创造了可能,劳动者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的时代才真正开始。以个体为轴心的自主意识走向以群体利益为中心的自主意识的帷幕拉开了。
自主意识由个体中心向群体中心的发展有着历史的必然。我们不妨先看看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提供的佐证。二战后资本主义获得发展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进行改革有关。它们不断地调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之尽可能地减少摩擦而趋于和谐。在这一系列的改革中,资本主义普遍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有报道说,二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没变,但其表现形式已由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变,资本的结合主要是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结合,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成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国家是国有资本的“人格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干预经济作用的加强意味着离社会主义更近了。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保留私有制的基础上推行“混合经济”,实行“经济计划化”,在国内采取强制主义,增加福利事业的项目、幅度,完善医疗、人身保险,改进就业、住房、养老等制度,运用社会有机体消除贫富的尖锐对立。另外,许多垄断资本为了自身的发展,不得不更紧密地依靠其雇员,积极地改善劳资关系,加强劳资合作,吸收员工直接参与管理,进行决策。这些措施虽然没有触动私有制和垄断资本的根基,却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抗性矛盾,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正是这些以社会主义为模本的“抄袭”和改革,延长了它的寿命,缓和了社会基本矛盾。但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使它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个人本位和自主意识的恶性发展。
个人本位的自主意识将个人的利益无限扩大推至极端,这就造成了从本质上对集体主义的否认与排斥,而没有集体主义约束的自主意识极可能成为瓦解现代社会的破坏力量,因而,呼唤集体意识,向往和谐宁静的社会已成为世界的潮流。自主意识以其符合商品经济所要求的独立、自主、创新等品质,以其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合理性取代了非自主的意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要让位于更高级、更先进的新事物。个人本位的自主意识让位于崇尚整体利益的自主意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趋势。商品经济的初期,为了发展生产,冲破自然经济的封闭、狭隘、趋同、单调的经济模式必须培育出伸张个性、发展个性的主体,以个体为本位的自主意识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要求生产资料的逐步社会化,而且要求社会的个体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奋斗目标,以保证社会财富的合理利用、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为以集体为本位的自主意识的产生、形成提供了深刻的根源。这一观点就连西方许多的有识之士也承认,从儒学的兴起、对人文运动的反思、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批判中,都可以看出、听到他们对个人本位的自主意识的怀疑和企图超越的努力与呐喊。
以集体为本位的自主意识的形成、巩固从社会制度上讲只能依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为全体劳动人民谋利益和幸福的政治制度,它不仅认同人自然权利上的平等,而且为造就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它把集体主义、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既尊重每一个成员的权利,又寻找保障集体、社会利益的机制与方法,确定全社会都可接纳、遵守的共同的价值观。将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有机地融合,在发展个人、健全社会的双重价值取向下,使个人、社会都得到发展。这里要注意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认为社会主义否认、排斥自主意识的论点是错误的,一些西方国家以人权作为借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毫无道理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可以跨越,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跨越。没有自主意识,商品经济很难发展,更不会有民主的政体。社会主义从来不讳忌人权,但它是从群体利益出发来讲个人的权利、地位,这是它高于资产阶级人文运动之处。它为自主意识的发展展示了最广阔的空间,指出了最正确的道路。
纵观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意识的发展经历了正、反、合的过程。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中,研究自主意识的作用、走向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漫漫路程后,才确定发展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得失成败,社会主义运动的起伏跌宕都是我们前进的参照,我们不必去重复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而应更快、更好地前行。因此,片面地否认张扬个体的自主意识与极力地鼓吹、宣扬它都是不对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自主意识,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它,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文条件。同时也一定要看到个体极度膨胀的自主意识在现代也是有害的,我们不必去重蹈“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①c],“只有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②c]。而是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将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结合起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用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去引导、教育、规范每一个人,将集体的、社会的利益灌输给他们,加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向心力,在促进个体健全、自由发展的同时,建设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
注释:
①a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①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3页。
①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0页。
②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