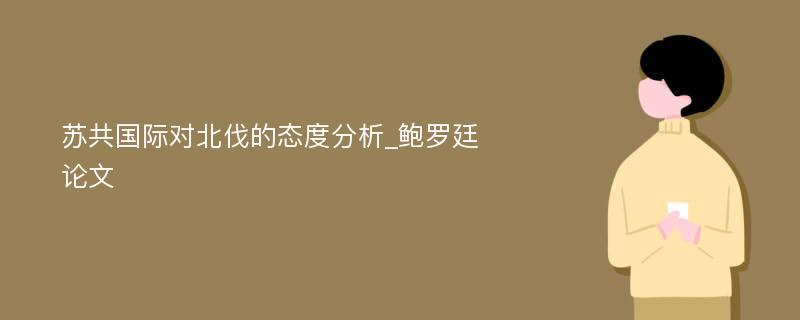
试析苏联、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共产国际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3)05-0026-08
1926年的北伐是国共合作浴血奋战的一场革命战争。在半年多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长江流域,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赢得了辉煌战绩,极大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和国民革命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和军阀独裁倾向。在北伐进程中,苏联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北伐的态度如何?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往史学界了解的不多且少有论述,直到近几年翻译出版苏联解密的档案材料,才获得了许多新知与真知。
一、苏联、共产国际对北伐态度的变化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松动再到密切关注的较大变化过程,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苏联和共产国际出于多种考虑,不主张北伐,对北伐持谴责态度。
北伐是孙中山多年的夙愿,他曾作过几次尝试,均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夭折。1924年下半年,孙中山将其注意力再次集中于酝酿已久的反对直系军阀的北伐,但时任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反对立即出师北伐,他指出:“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这两个条件目前一个也不具备”(注:加伦:《军事政治形势》,载[苏]Α.Ν.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1925年五卅运动风暴席卷全国,掀起了革命新高潮,加伦认为举行北伐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于是月制定了《今后南方工作展望与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正式提出北伐的计划,拟定了军事部署,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北伐,将政治工作中心从广东移到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
到1926年初,国共两党不约而同地将北伐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因为,在“五卅”革命浪潮冲击下,国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一,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经过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胜利,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给北伐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第二,尽管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和国民军趁势占领直隶全境,把反奉运动推向了高潮,但直军吴佩孚和奉军张作霖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反赤”战线,联合进攻革命,致使郭松龄倒奉失败和冯五祥被迫通电下野,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旨在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遂流产,直奉军阀准备进攻广东革命政权。北方政局的急剧逆转,对国民政府构成严重威胁。第三,受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刚统一不久的广西政府宣布接受国民政府领导,派代表与国民政府商谈,正式成立了两广统一委员会。两广的统一为举行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上可见,北伐实际上是在五卅运动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国民政府需要寻求向外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群众斗争的基础。这是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和统一全中国的根本出路,也是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举措。这时,渴望早日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的全国广大群众,亦越来越把希望寄于国民政府的北伐。
虽然如此,苏联和共产国际起初对国民革命军是否能取得北伐的胜利存在疑虑,对北伐持否定态度,而主张广州国民政府应以集中巩固广东根据地为主要任务。1925年12月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斯大林的指示,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纪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42页。)从此在俄共(布)高层领导内部,加强了对北伐的谴责。俄共(布)领导人之所以采取反对北伐的立场,主要出于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形势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其一,西方列强奉行孤立苏俄的政策,1925年12月,英、法、比、德等7国正式签订了《洛迦诺公约》,推动德国走向反苏道路;西方还掀起反苏反共的宣传活动,苏俄与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苏俄的处境愈加艰难。其二,中国北方政局继续恶化。1926年春,接连发生了俄日在中东铁路冲突,日军掩护奉军炮击大沽口,段祺瑞执政府屠杀北京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国民军在奉军进攻下被迫撤离北京退守南门等严重事件,使莫斯科对华政策新重点转移到冯玉祥的计划受到挫折。其三,莫斯科担心北伐行动将导致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存在失去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危险。而北方国民军的失利,保卫广东根据地更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上述时局,俄共(布)领导人对日本在中国北方和远东地区的扩张野心甚为担忧,它们所关切的是如何稳定广州局势及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所以决定调整对华政策,采取分化帝国主义反苏联盟和中立日本、集中对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敌人——英帝国主义的策略,也就是说,由1925年的进攻路线转为暂时退却的“喘息”政策。在莫斯科看来,只有赢得和延长“喘息”时间,才能维护周边地区的安全和中东铁路的利益,而目前进行北伐,显然不符合“喘息”政策。
第二阶段:中山舰事件后至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苏联和共产国际仍根本上反对北伐,但一度出现某些松动迹象。
鉴于中山舰事件后的不利形势,联共(布)中央重申:“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尽管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急电苏联政府,阐明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必要性,批评莫斯科的决定不适用于广州的具体情况,但丝毫未能改变莫斯科的态度。1926年4月15日,根据斯大林的旨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告诫加拉罕:“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0号(特字第14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02~203页。)
蒋介石为巩固中山舰事件的成果,篡夺国民党领导权,急于进行北伐。有鉴于此,4月下旬,莫斯科领导内部有人较早提出准备北伐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政治顾问穆辛提出:“广州政府的主要任务,除在自己的地区进行革命改造外,则是准备以后在广东之外为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注:《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12页。)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拉兹贡也认为:“必须扩大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因此准备进行北伐的工作应当提上我们军政工作的日程。”(注:拉兹贡:《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25页。)可是,莫斯科高层领导仍坚持反对立即北伐的立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建议:“应发出指示不允许广州政府在目前进行‘北伐’”,并决定“关于‘北伐’问题,应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27、228页。)
到1926年4月底,北伐已基本准备就绪。这时湖南的政局变化,给广州国民政府举兵北伐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驱逐湖南督军赵恒惕后,表示倾向国民政府,并吁请国民政府出兵援湘。事态的发展,迫使莫斯科领导人容忍北伐这一事实。5月上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一方面强调“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决定“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3号(特字第17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41页。)可以看出,莫斯科反对北伐的态度虽然仍很坚决,但出现了某些松动的迹象,说明它们已开始考虑北伐问题了。
但当北伐先遣队已进入湖南境地,北伐事实上已经进行时,莫斯科仍担心北伐可能引起英日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以及促使蒋介石的权力膨胀而走向军事独裁,所以不到半个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回到了原有立场,于5月20日作出决定:“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68页。)。
第三阶段: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至占领长江流域,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开始关注北伐事态的发展,认真考虑北伐问题。
从1926年夏开始,有两件事促使莫斯科开始认真对待北伐问题。一是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同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主流派的斗争趋于尖锐化,而中国革命事态的发展成为他们争论的主要焦点。二是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正式出师北伐,其势锐不可挡,革命浪潮再度掀起。迫于无奈,莫斯科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开始关注北伐的事态发展,慎重权衡在北伐问题上的利弊得失。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所谓北伐问题,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责成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在军事方面和一般政治方面的情况通报,并请国民党中央阐述其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动机和想法。”(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5号(特字第33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67页。)
8月末国民革命军准备进攻武汉时,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顾及到继续北进会作出巨大的牺牲和今后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于是提出一些军事策略的设想,指出中立孙传芳和张作霖以及冯玉祥国民军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重要性。9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广州同孙传芳达成协议,以便取得他的支持或保持中立,并试探同张作霖达成不侵犯协议”(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0号(特字第38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429页。)。11月中旬北伐军肃清江西孙传芳部队的第一阶段结束时,革命面临新的困难和危险:一是蒋介石和唐生智的权力斗争及其他军队将领之间的斗争加剧。二是孙传芳失败后国民革命军直接面对着奉系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南方需要“喘息”时间,必须调整军阀之间、国民革命军领袖之间相互关系,决定:“广州目前向北挺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加剧奉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建议鲍罗廷同志和加伦同志劝告国民政府占领浙江并继续谨慎地向安徽推进,但不要同张宗昌发生武装冲突。”同时“极有必要把阎锡山吸引到南方人这边来或者使他保持中立。”(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特字第51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527页。)随后还提出:“必须劝告国民党中央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来消除或者哪怕是缓和蒋介石、唐生智和其他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注:《联共(布)中央会议第7l号(特字第53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635页。)
二、苏联、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北伐问题上的分歧
莫斯科驻华代表对北伐问题的认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大相径庭,有的积极赞成,有的犹豫不决,有的明确反对,其中布勃诺夫、鲍罗廷和维经斯基是这三种不同态度的代表人物。
(1)布勃诺夫使团积极赞成北伐
为了解苏联顾问在华工作情况和研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问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6年2月派遣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使团来华考察。布勃诺夫征询了华南的几乎所有军长的意见,发现整个军队和全体指挥人员都确信北伐是必要的。布勃诺夫赞成北伐,确信北伐是迟早要进行的,认为“北伐问题是时间和行动方式问题”(注:《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87页。)。他认为现在就要开始促使广州对吴佩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华南的国民革命不能停滞不前,不能躲在华南,等待北方自己来解决所有的矛盾和问题。”强调应做好各方面的北伐准备工作,但不提出明确口号进行北伐,特别要将北伐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他说:“想不‘牵涉’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这就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注:《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68页。)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正在广州的布勃诺夫使团,为缓和华南俄国军事顾问组组长季山嘉与蒋介石的矛盾,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当即解除了主张北伐“从缓”的季山嘉等人的职务,迅速平息了事件,从而为北伐的准备和进行赢得了时间。为北伐营造有利的条件,使团尤其提出要把苏联顾问的全部工作同北伐前景联系起来,应当毫不迟疑地为北伐作准备。鉴于国民革命军比较弱小,使团提出要把“与广东相邻省份和长江流域省份的军阀,特别是孙传芳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或者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同时要积蓄力量,建立一支能够进行北伐的军队。”(注:《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56页。)
(2)鲍罗廷对北伐的认识含混不清,自相矛盾
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治总顾问的鲍罗廷是北伐的最早鼓吹者之一。他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期间就强调向北发展的必要性。2月,他在北京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工作时,更明确提出北伐已“刻不容缓”;我们“不能坐守广东,建立模范省,不扩大自己的战略范围。而应该北上”(注:《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22页。)。但鲍罗廷不同意重复孙中山的单纯军事讨伐,而提出北伐应着眼于两点:一是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北伐应有明确的要求和土地纲领;二是必须与北方革命联系起来,北伐还要着眼于援助北方革命。这就赋予北伐新的革命内涵。
但是,鲍罗廷对北伐的思想是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预见到北伐将使工农群众运动高涨,同时认为北伐只是为蒋介石军事独裁开辟道路。于是正确提出了两种北伐观:“一种是同人民大众的革命压力相联系的北伐;另一种是3月20日以后蒋介石组织的纯军阀性质的北伐。”(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91页。)并且强调要用人民革命的北伐去战胜蒋介石军阀的北伐。另一方面,鲍罗廷又认为中山舰事件后,不能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北伐,反蒋是危险的,那将是中山舰事件在更大范围的重演。主张要给蒋介石以一切可能的支持,要使蒋在北伐前线作战完全放心。他说:“我们在一般政治问题上和特别是在北伐问题上都不能充当蒋介石的反对派,因为蒋介石本人在他对北伐问题的非革命的解释中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自信地解释说:“如果我们由于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那么我们就只有等待和面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结束时等待着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北伐的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注:《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69~370页。)。出于对革命实力不足和斗争策略的考虑,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中共不去大力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及工农革命武装,如果没有坚强的实力为后盾,那么,想利用蒋介石北伐,指望蒋介石在北伐中失败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灭亡,岂不是一种投机的幻想?正因为鲍罗廷对北伐的态度犹豫不决,所以从未制定如何配合北伐军事的政治保证措施。人们也很难领会鲍罗廷的立场。
(3)维经斯基和以他为首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北伐持反对态度
呆在中国时间最长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直反对北伐,因为他“不了解北代的客观意义,不懂得利用北伐来争取群众,从而与群众共同对付国民党。”(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所以指责鲍罗廷支持蒋介石北伐的政策,会使“蒋介石的进攻野心越来越大”,在蒋介石已经控制国民党的情况下,“北伐必然遭到失败”(注:《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09页。)。指出:“把我们的政治同北伐联系起来是极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广州应当采取防御立场,“工作的重点口号不是进行北伐,而应当是提高工农群众的经济福利,巩固革命政府的基地”(注:《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22页。)。1926年6月下旬,在上海成立的以维经斯基为主席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样认为,“举行北伐是有害的”(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2号纪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07页。)。
不过,在策略上,维经斯基也同意鲍罗廷的观点,他说:“我们决不应该公开地进行反对北伐的鼓动宣传并在我们的敌人强加于我们的一些问题上接受挑战。如果我们想采取坚定的反蒋方针,那么我们确实应该展开反对北伐的广泛战线。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对蒋介石采取这种方针。”(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92~393页。)
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维经斯基和远东局一方面清楚地看到广大工农群众热情地为北伐而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意识到,北伐战争的胜利将会大大助长反革命势力的活动。因此,当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时,远东局建议: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停止继续向华北推进。11月下旬进而指出:“在打败吴佩孚和孙传芳之后南方以不主动与奉军开战为好”,“北伐军应采取防御态势——保卫江西和湖北,当然要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好准备。”(注:《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5页。)
三、苏联、共产国际的北伐态度对中共的影响
1925年初以前,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原则上赞成进行北伐,但认为尚不具备消灭北洋军阀的条件,存在矛盾心理,态度一度摇摆不定。因担心广州国民政府的政治地位不稳固,军队不够强大,所以对立即北伐持否定态度。
鉴于“五卅”后国内革命高潮迭起,从1925年秋起,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改变了立场,认为举行北伐是适宜的,这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1925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从战略高度强调北伐的重要性,认为“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会议作出了支持北伐的决定,指出:“党的现时政治上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的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注:《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陈独秀虽然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也不知道会议的决定,但他对北伐是支持的,曾拍电报给汪精卫和蒋介石,力促开始北伐。可是共产国际代表指责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国民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注:《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38页。)会后,中共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推动和准备北伐。
中山舰事件后,尽管莫斯科三令五申,但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支持不改初衷。5月上旬,在中共领导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均决议请愿政府出师北伐。维经斯基在6月11日的一封信中谈到:“关于北伐问题,尽管莫斯科作了各种指示,但在这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还不能确切地说,中央的情绪怎样,但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03页。)显然,中共支持立即北伐的态度有悖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主张,维经斯基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共中央认真地谈一谈,希望能与中共达成共识。6月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北伐问题。与会者一致赞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就北伐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个电报,“指出现在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第2号纪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17页。)。
然而,维经斯基和远东局对中共北伐立场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鉴于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接连发生,以及北方革命形势的低落,陈独秀和中央部分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野心和军事独裁倾向感到忧虑。在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维经斯基的劝说下,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于7月初改变了支持立即北伐的态度,提出了对北伐的共同看法:“采取了广州的防御立场而不是北上以使全国革命化的立场”,“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切实动员群众的问题上,而不是提出广州向北方军阀进军的冲锋口号”(注:《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26~327页。)。陈独秀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长时间交谈后,于7月7日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这篇文章的基调是由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共同拟定的,其中心思想是不支持立即北伐。文章指出: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强调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须防止投机军人政客利用北伐扩充个人的实力,不能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实践证明,陈独秀对蒋介石通过北伐扩张个人独裁势力的忧虑不无道理,从文章的本意中很难得出反对北伐的结论。但文章发表在北伐实际上已经开始之时,是不合时宜的,因而遭到党内外许多人士的非议。对北伐的这种消极态度,也使中共在政治上陷入极大的被动。
为了澄清对陈独秀文章的指责,中共中央于7月31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重申陈独秀文章的思想,批评那种对北伐希望过高,把北伐看作革命的唯一出路的错误认识,指出:“我们并不是反对北伐而是赞成北伐,尤其是现时广东北伐更为必要。”但应当“提出我们独立的政治主张,而不可笼统的宣传北伐。”(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04页。)
此时,围绕陈独秀的文章,鲍罗廷与维经斯基之间关于对北伐的态度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鲍罗廷反对陈独秀的文章,指出:“陈独秀的文章现在已经在群众中造成麻烦,因为人们的注意力从北伐被转移到这篇文章的内容上来了。”“现在我们支持北伐,甚至广泛宣传北伐,但同时又对它采取批评态度。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而只是批评北伐。”中共的这种“行动不能不给国民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反对北伐。我认为,这种方针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冲突,因此应该防止这种冲突的很快到来。”(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89、388页。)维经斯基则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对北伐的唯一正确的立场。但策略性地运用这一政治上正确的方针问题要复杂得多。”(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92页。)远东局认为陈独秀的文章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在北伐问题上它使党的注意力转到内部反革命的危险上,并决定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要宣传陈独秀文章的立场,制止军队继续向北推进。
以上不难看出,本来,中共中央在北伐问题上的态度摇摆不定,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北伐的消极态度,影响中共中央在北伐问题上一波三折,说明维经斯基和远东局对北伐的消极态度,直接影响到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北伐的立场。由于中共中央对北伐问题的态度是听命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致使中共对北伐始终采取一种有限度的支持态度,正如陈独秀所说:中共“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也就是说,“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注:《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承认,1926年6至8月这段时间,“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中共中央最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远东局“加强了对北伐的否定态度,无疑也防碍了中国党更好地武装自己,加强自己的影响”(注:《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31、32页。)。这是由于:其一,极度夸大了中国反对派的力量,尤其是夸大了孙传芳集团的力量;其二,夸大了广东内部反对派的危险;其三,既不愿支持孙中山关于通过北伐拯救中国的思想,又不愿意表示拥护蒋介石;其四,不懂得在反动派阵营已经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北伐应具有的巨大革命意义;其五,远东局内部对北伐的态度不一致。
实践证明,不管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如何消极以及它们驻中国的代表分歧有多么大,都不是根本上否定北伐,本质上是“急进”和“缓进”之分歧;其争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整个政治形势的评估不同和着眼于全中国的政治关系而对蒋介石本人以及整个右派统治集团的评估不同引起的。一般说来,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更多地顾及应尽量避免同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相碰撞,顾及应尽量避免同蒋介石集团利益相磨擦,顾及应尽量维护中共在广东的统战合法地位。这是他们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症结所在。而布勃诺夫和鲍罗廷等人在北伐态度上之所以不同于莫斯科领导人,主要是多从眼前和局部考虑问题,而不象莫斯科那样更多地着眼于长远和全局。同时,远离广州的莫斯科领导人对广州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与身临广州其境的驻华代表,对北伐的现实感受也大不一样。但总体上看,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北伐战争给予不少的指导与援助,比如,开展以工农运动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在反帝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军阀集团间的矛盾来削弱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加强和组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等。不言而喻,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北伐的胜利功不可没。
标签:鲍罗廷论文; 陈独秀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革命委员会论文; 历史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蒋介石论文; 远东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北伐论文; 莫斯科论文; 中共中央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