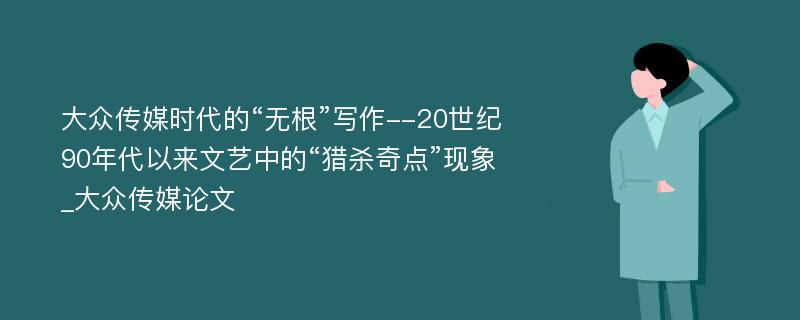
大众传媒时代的“无根”写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中的“猎奇化”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艺术论文,大众传媒论文,现象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7—0004—08
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使得许多年前的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成为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媒介文化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手机、电视、互联网诸种传媒已经成为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伴侣。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艺术一方面以批量化的生产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又以“丰收的荒凉”态势呈现在我们眼前。与此同时,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文学艺术正在泛化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铺天盖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刺激着我们的神经;电视新闻栏目的各种节目也非常讲究叙述技巧,海湾战争期间,香港凤凰卫视的战地新闻节目就是利用说书的方式进行播报。近年来,我国内地的电视新闻节目,也十分注意叙述技巧,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道德观察”、“生活”栏目的“危机时刻”等等都概莫能外;江西卫视的“传奇故事”、“人间写真”等都以讲述的生动传神而收视率一路攀升。当然不仅仅是叙述技巧,更重要的还是取材的奇巧与刺激。至于各级晚报都市报及各级娱乐小报则更是把新闻栏目娱乐化了①。新闻节目尚且如此,那些电视剧、娱乐节目更是不言而喻。文学艺术本身以网络写作、博客写作、电脑写作汇入这股时代大潮中,共同塑造着大众传媒时代的风貌。当我观察和思考这一时代风貌的时候,“猎奇化”一词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20世纪90年代以来,猎奇化一直是我们时代文学艺术写作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实际上,猎奇化也成为我们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甚至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结构,渗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认真剖析猎奇化这一现象的表现形态、运作机制以及背后的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猎奇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诸种表现
1.“身体写作”:性展览与“隐私秀”
曾几何时,“身体写作”成为文学中的关键词和热门话题不断被人提及。身体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实际上古已有之。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在《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一书中,就对自卢梭、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以来的文学以及马奈、高更等西方现代绘画中的身体写作进行了很有意思的分析。身体写作主要还不是对身体的一般描述,而是特指书写身体的隐秘部位及涉及性的欲望描写。我这里说到的“身体写作”,特指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写作潮流。身体写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身体写作,又叫“私人化写作”,主要指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描写自己身体,表现女性隐秘性心理的一些作品。这类作品以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为代表。实际上,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具有反抗男权文化的宗旨,因此,她们的私人化写作或身体写作,具有一种“解放”的性质。解放身体就意味着反抗,不仅反主流,也反男权文化。在她们看来,主流文化与男权文化正是一种共谋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文学与文化中的“宏大叙事”,因此,她们的写作就是以个人体验和经验的私密性来对抗90年代以前文化和文学创作中的“宏大叙事”。宏大叙事在利奥塔尔那里是与基础主义和普遍主义一元化文化霸权相联系的。其中包括现代理性、启蒙话语、总体化思想和历史哲学等话语范式。利奥塔尔宣称,现代话语为了使其观点合法化而“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大叙事”②。在利奥塔尔看来,现代性的元叙事倾向于排他,并且倾向于欲求普遍的元律令。如此一来,“宏大叙事”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某种代言的性质,因此,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坚持倡扬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等因素。显然,针对“宏大叙事”的私人化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利奥塔尔的影响。不过,这里所针对的“宏大叙事”更侧重于对一种“公共性群体意识”,一种代言性的“大我”乃至“非我”的叙事。这种叙事排斥多元和差异因素,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由此看来,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正是要以“个我”的独特体验颠覆这种“大我”乃至“非我”的公共性经验,因而,具有所谓的“革命性”意义。
身体写作的第二阶段主要指卫慧、棉棉等所谓“美女作家”或“新新人类”的写作,以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为代表。“美女作家”的称谓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消费社会对“美丽”的消费需求,也说明了女性被看的命运在商品社会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陈染、林白们反抗男权文化的吁求在强大的消费时代顷刻化为泡影。“新新人类”的说法,主要是指她们的写作在题材上是全新的,“综观她们的多数作品,性是其描写的主要内容,欲望是其基本主题,酒吧是其重要意象,自虐与自恋是其最具特征的心理过程”③。这些作品标志着一种新的后殖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方式。它是圈子化的产物,而决不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它的新奇带有强烈的性展览和“隐私秀”的味道。倪可在马克的身体下,幻想着被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的法西斯所强暴,一种被占领、被虐待的快感与林白、陈染笔下的女性意识实在不沾边。这正是欲望一代的身影。由此可见,卫慧、棉棉们的身体写作基本上是一种猎奇化的产物。到了九丹的《乌鸦》则直接被称为“妓女文学”,春树的《北京娃娃》则被认为是“用身体写作,十七岁少女疯狂赶超九丹卫慧”,直到木子美的《遗情书》、“芙蓉姐姐”的S型身体,已经成为纯粹的性展览和隐私表演秀了。
实际上这种展览性事、出卖隐私的身体写作并不只是女性作家的专利,在许多男性作家身上也非常突出地存在着,我们且不说贾平凹《废都》中那欲盖弥彰的“□□□”,也不说陈忠实《白鹿原》开头那大段的对白家轩娶妻七房的大肆渲染,单就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号性有关这一事实就颇值得我们深思。陈晓明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道:“现在,苦难动机已经遗忘了,爱欲变成叙事的中心。作为苦难根源的爱欲其实是充满快乐的,苦难的本质已经失踪了,不幸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寻欢作乐的气息。”④ 这种寻欢作乐的气息就是一种猎奇。我不是道德家,也不反对文学作品写身体和性,但这种身体与性应该是作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不可或缺的肌质,否则,它就成为一种招徕和吸引读者眼球的招贴,它的别有用心的企图昭然若揭。而实际上,当隐私失去了历史的参与,它必然成为浅薄的公共性。浅薄的公共性历来都是艺术的敌人⑤。
2.“大话”与“戏说”:“无厘头”与搞笑秀
“大话”与“戏说”无疑是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中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前者以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为代表,后者则见于《戏说乾隆》、《戏说慈禧》、《铁齿铜牙纪晓岚》、《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有关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小说中。这两类作品基本都以拼贴、并置、戏仿等后现代手法来结构作品,使作品始终处在娱乐化、猎奇化的状态中。
周星驰的电影是典型的后现代文本,它的颠覆意义与反讽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周星驰的电影也无疑是香港商业消费主义社会的产物,它的彻底搞笑化、全面娱乐化也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从中得到的是纯粹的笑料,它消解了一切,颠覆了一切,它把自己置于无根状态。
“戏说”类的影视剧与小说在90年代的盛行,显然也是时代的产物。“戏说”有意识地把历史戏谑化、庸俗化了,这种对历史各取所需的虚无主义态度,显然也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时尚。“戏说”掏空了历史的内在本质,填充的是大众传媒时代商业主义的欲望内核,历史被猎奇化、娱乐化了,历史的根被商业主义的斧钺无情斩断,历史悬空在天边,漂浮在今人歌舞升平、娱乐至死的缕缕烟岚中⑥。
3.玄幻小说:狂想游戏秀
当70年代作家把隐私变成公开的秘密的时候,80年代的一批小字辈写手则被各种媒体推上了时代的前台,这些被冠之于“80后”的少年才俊,在不经意间已经占领了各级媒体的热炒版,尤其是网络。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沧月、萧鼎、步飞烟等等,我们几乎可以列出一长串他们的名字,这一串稚气但却与印数和大量“粉丝”联系着的名字,已经不能不引起文学界的注意,而近几年中年评论家与他们之间的龃龉,比如“韩白之争”、“陶萧之战”等,都说明传统文学价值观与大众传媒时代文学价值观的尖锐冲突。在这里,我无意对他们的创作进行全面的评论,只是对他们写作中的玄幻小说在运思方式上的猎奇化现象进行一些勾勒。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像郭敬明的《幻城》、萧鼎的《诛仙》、沈璎璎的《逝雪》、沧月的《七夜雪》、林千羽的《逍遥·圣战传说》等都具有出奇的想象力。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建立在游戏的基础上,是一种狂想游戏秀。这种想象失去了生活与价值的依托,只能是一种无根的游戏。我赞同陶东风教授的观点,“80后”的玄幻小说的确在装神弄鬼⑦,他们与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可同日而语,金庸武侠小说是建立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想象,是有根的写作,而“80后”的玄幻小说基本上是在猎奇。
4.媒体批评:热炒秀
媒体批评在90年代以来的文坛上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非凡能量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媒体批评是指以媒体为主体的批评。相对于传统批评而言,媒体批评具有通俗、浅显快捷、尖锐等特点。它是大众传媒时代文学艺术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特有的一种现象。麦克卢汉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强调了媒介的技术作用。实际上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的作用愈来愈具有主导性意义,媒介不仅参与作品的流通传播,甚至也参与作品的生产。媒介实际上也在制造事件、造就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就是作品,作品就是媒介。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阅读和观看趣味的多元化,一部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消费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是不可思议的,再好的作品也需要媒介的推销。如此说来,媒体批评,主要是一种广告,一种推销术。加上利益的驱动,媒体批评建立了自己的话语霸权。众多的读者在当今时代对作品的了解主要就是通过媒体来实现的。作品讨论会,是媒体批评的发布方式。通过作品讨论会,媒体收买了传统批评家,作品从此走向大众。“酷评”是媒体批评的极致。一骂就灵,一骂就火。媒体批评趁机加以热炒,一个事端被制造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的媒体批评就是在制造事端,通过制造事端,引发大众的猎奇心理。
二、全面猎奇化:大众传媒时代的社会心理结构与资本运作机制
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全面猎奇化并非危言耸听,全面猎奇化意味着猎奇化不仅仅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大众传媒时代的普遍的社会心理结构,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症候。猎奇化是一种时代病,它和人类为了求知的好奇心不是一回事;猎奇化也和陌生化、追求艺术的新奇化不是一回事,追求艺术的新奇化与陌生化是艺术创新的必由之路,这种追求是在正常的心态下对艺术之美的发现与创造。猎奇化则不然,猎奇化是为了猎奇而猎奇,是从一个新奇到另一个新奇,正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自由空闲的好奇操劳于看,却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着所见之事的存在,而仅止为了看。它贪新骛奇,仅止为了从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新奇上去。这种看之操心不是为了把捉,不是为了有所知地在真相中存在,而只是为了放纵自己于世界。所以好奇的特征恰恰是不逗留于切近的事物。所以,好奇也不寻求闲暇以便有所逗留考察,而是通过不断翻新的东西、通过照面者的变异寻求着不安和激动。”⑧ 我觉得,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好奇”,实际上就是中文的“猎奇”。猎奇到处都在而无一处在,它和“闲言”一起都是一种无根的存在。无根的存在意谓这种猎奇是一种漂浮的状态,大众传媒(比如一些娱乐小报、互联网等)以一种道听途说、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方式即海德格尔的“闲言”方式制造事端,进而吸引大众的猎奇心理。而这种心理正是以不断的遗忘方式促使传媒不断制造富有刺激的事端,以唤醒已经愈来愈麻木的神经。大众传媒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批量生产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这样一个悖论:资本权力生产的信息越多,它就愈没有能力控制处于社会特定地位的各主体对信息的各种各样的阐释,主体不仅分散信息,同时也在信息的狂轰滥炸中麻木不仁。制造事端、寻求新奇成为刺激之源。任何时代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喜新厌旧,所有的事件都只能热闹一时,而且所有的事件都几近无聊,从“美女写作”到“妓女文学”,从“木子美”到“芙蓉姐姐”,从“韩白之争”到“陶萧之战”,从“下半身写作”到“梨花体事件”,哪一件事不是被制造事端的媒体弄得如此呢?猎奇是为了寻求刺激,这种刺激决不会涉及心灵,它是肉体的、感官的、肤浅的,因而也是无根的。
全面猎奇化不仅是普遍的社会心理结构,实际上也是消费社会资本运作的机制。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⑨ 因此,我们对猎奇化现象的分析也应当从生产方式出发。我们时代的生产方式就是消费社会资本的运作方式。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一定是对商品的实用性消费,而主要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仿像”文化消费。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突出了消费的符号性质。资本要想从大众手中掏出更多的钱,则必然要采取各种手法。将消费符号化、审美化是消费时代资本运作的基本机制。周小仪在梳理凡勃伦“代理消费”与拉康“剩余快感”的理论资源后提出的“代理审美”的概念⑩ 颇富启发意义。“生活的艺术化和审美的资本化这两个在表面上似乎完全不相干的社会过程,以‘代理审美’的方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资本世界已经占据了我们的位置,填补了我们作为主体的空白,并慷慨地为我们留下美感”(11)。资本营造了我们生存的幻像,娱乐文化、休闲文化、广告文化、名居文化等以艺术的方式满足了我们的虚拟享乐的欲求,资本成为我们的审美代理。然而,资本在营造消费审美语境的时候,往往诉诸感性的肉欲层面,只有在肉欲层面,消费者才有可能不惜血本。因此,猎奇化成为我们时代最有吸引力的方式,猎奇化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业已麻木的神经,刺激我们的感官,引起我们持久的兴趣。资本总是不断地制造消费时尚,制造热点,代理我们进行审美,在这种审美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虚拟的享乐,正像柯林·坎贝尔所认为的那样,在消费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新奇事物渴望的内在动力,主要是一种自我陶醉的享乐主义。“自我陶醉的享乐主义代表了一种寻求快感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虚构的刺激物和刺激物带来的隐秘的快感上,而且更多地依靠于情感而不是直接的感觉。换句话说,提供快感的刺激物源于个体想象的虚构情境所产生的情感影响,源于一种正好可以被描绘为白日梦的实践”(12)。资本正是将它所传达的信息直接指向了这个隐蔽的内心世界,“怂恿消费者去相信它所描绘的新奇产品确实可以使他们的美梦成真”(13)。
当我们消费文学艺术产品的时候,我们作为被代理的主体,感受到的是文学艺术中那些最具享乐意义的情节。身体写作之所以被大众所消费,主要是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后殖民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宝贝》中,倪可与马克的性爱方式、那种异国情调、那种酒吧的感官的颓废的享乐场景,已经成为艳羡的对象,在这种艳羡中,我们得到了虚拟的享乐满足。
三、全面猎奇化与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
全面猎奇化归根到底是一个价值问题,它在20世纪90年代大面积泛滥主要是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所导致的。
在西方,虚无主义被尼采的“上帝之死”裸露在前台,“上帝之死”意味着最高价值的不在场,尼采说:“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14) 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标志着西方人信仰的缺失,失去了信仰的西方人,在虚无主义的围困中不知所措,“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成为现代西方人的普遍的价值规则。实际上,尼采对虚无主义也做了区分,他所反对的是消极虚无主义,而极力倡扬积极虚无主义,这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是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在颠覆、轰毁和重估一切价值的同时,从废墟上建立起“强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最后大厦。然而,尼采的一厢情愿在西方两次大战的血腥中化为梦呓,虚无主义所向披靡,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萨特的“绝对自由”种种,只是虚无主义时代的强心剂而已,当历史无可阻挡地进入消费主义时代,无可救药的享乐主义成为虚无主义的新的顽疾。
在我国,虚无主义的来临与其说完全源自西方,毋宁说根植于我们自己的社会肌体内部。当十年“文革”结束,中国也面临着一个“上帝之死”的危机。“重估一切价值”也是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思想文化界最响亮的口号。一时间颠覆、解构、调侃、狂欢成为时代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王朔诸人的“文学痞子运动”、先锋小说的文体革命与文学“新历史主义”实验,刘震云等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原生态”,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的身份觉醒等,都可以看作我们这个上帝缺席、诸神退位时代的价值“清障”。虚无主义正是在此时乘虚而入的。旧价值已经无可挽回地坍塌消匿,新价值却无力建基。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价值真空。众所周知,90年代大众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谁能预料到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城市中就普及了电话,电视机、手机、电脑也算不上奢侈品了,上因特网、逛超市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行为,再加上汽车进入家庭,技术主义以它的实际行动抢占了文化霸权地位。技术主义的高度扩张,加剧了欲望及享乐主义的快速疯长。资本借技术之手代理了一切,人们可以轻松地不加思考地沉入其中,浑浑噩噩地娱乐至死。这是一个无聊的时代,一个他人引导的时代,没有思想、缺少敬畏、不负责任、人云亦云,金钱就是一切,享乐就是一切,新奇刺激就是一切,不要道德只要肉欲,不要理性只要感官,不要深度只要浅俗,不要历史、不要未来只要当下与瞬时。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在虚无主义之风的强劲吹拂面前,先前的文学艺术的“革命”、“解放”诸意义也消逝殆尽,正像丹尼尔·贝尔所说的:“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地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众’加以制度化了。它的实验形式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它作为文化象征扮演起时尚的角色,使得文化大众能一面享受奢侈的‘自由’生活方式,一面又在工作动机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占有舒适的职位。”(15) 贝尔在三十多年前所说的这段话仿佛就是针对我们今天来说的,90年代以来,我们的所谓现代派先锋文学艺术不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吗?苏童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从而变成了时尚符码;余华在新世纪出版的《兄弟》一开头就用了三十多页的篇幅大谈特谈女人的屁股,池莉干脆开始大写特写所谓的电视剧了;海岩的一些为影视剧写就的小说,基本上就是按照大众的消费趣味“勾兑”而成的,比如《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其中有纯洁的爱情线索,女主人公既传统又现代,还有凶杀线索,这一线索往往是情杀,还有侦探故事,这些都是迎合观众的东西;“后新潮小说”几乎就是欲望主义的歌者,如朱文的《我爱美元》。可以这样说,在90年代,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举行了入俗仪式,他们都被收编在市场话语霸权的麾下,在金钱美色的盛宴中洋洋自得。
大众传媒时代的虚无主义价值观,使得许多作品丧失了真正具有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度感。比如在身体写作一族中,隐私的公共化是由于隐私被作为消费的缘故,这种消费只能在欲望的层面上进行,因此是无根的,它没有根植在作家深刻的思想信仰之中,而是漂浮在身体的肉感层面,只能成为浅俗的公共性。
同样,“大话”与“戏说”诸文学作品,它们寄生在传统与历史中,通过戏仿、颠覆、嬉戏,消解了深度,它们像青藤缠树一样,借用的是传统和历史的外壳,在貌似深度的阐释中消费化了。特别在戏说历史的作品中这种现象尤其明显。虚无主义疯狂挺进历史,正是资本看上了历史这一具有相当隐蔽性的市场,从90年代到现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作品经久不衰且愈来愈强劲,充分说明历史作为消费的广阔前景。戏说历史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的怎么都行的饕餮式抢掳(16)。
玄幻小说是真正市场化的产物,是随着网络传媒的发达而发达的。虚无主义同样在他们的作品中起着作用。陶东风在对这些作品的批评中认为:“装神弄鬼是以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为内核的一种想象力的畸形发挥,是人类的创造能量在现实中不可能得到实现、同时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的情况下的一种疯疯癫癫状态。这种想象力的最大特点就是非道德化,无价值性,不问是非,不管善恶,只求绚烂,只求痛快。在一个现实溃烂、未来渺茫的时候,在人们因为长期失望而干脆不抱希望的时候,犬儒主义就会以一种装神弄鬼的方式表现出来。”(17) 玄幻小说的这种畸形的想象力,是我们这个大众传媒时代欲望主义与技术主义联姻的产物,它的无根性、无深度性同样令人担忧。
长期以来,我们对“深度”似乎已经不屑一顾,仿佛一提“深度”就与本质主义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了理论界在价值观上也是相当混乱的。我们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引进与推崇,导致了张口“反本质主义”,闭口“削平深度”。我不禁要问,我们有过深度吗?如果有,那我们的深度又是什么?我们的深度与西方所说的深度一样吗?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深度,也没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我们的“反本质主义”与“削平深度”岂不太过盲目?在我看来,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削平深度的问题,而是重建深度的问题。这里的深度指的是文学艺术作品所应该具有的人文价值深度,包括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勘查,对生命意义的深层体验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尊重等。大众传媒时代的作家,不应该只是一个写作者,而应该是一个有责任心、有道德感、有良知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大写的人。大众传媒时代是一个精神贫困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诗人何为?”对此,海德格尔如是说:“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18)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写作中的猎奇化现象,已经成为我们这一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艺术写作的痼疾。猎奇化使文学成为无根的写作。写作既缺乏现实的支撑,也缺乏历史的支撑。它飘浮在空中,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化快餐。精神价值的缺失,灵魂的苍白,使文学艺术变得肤浅。我们仍然要问,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削平,究竟是否适合我们?实际上我们从来都没有深度,大众传媒时代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更是浅俗不堪,因此,重铸历史深度,重新确认精神价值的优先地位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 中新网2005年9月8日电:来自《中国妇女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由于猎奇心态作祟,部分媒体在报道女性新闻时紧盯他人隐私,由此所呈现出来的庸俗化倾向让人忧心。文章以最近媒体上报道的两条新闻为例:其一是广西的林小姐天生丽质,但一直不敢交男友,因为其被“难言之隐”困扰着,她有三个乳房,其中左胸竟然一上一下有两个完整的乳房,最后医院为其做了“并乳术”;二是广东21岁的周太太在生了小孩后,她的乳房由于激素的影响,急剧发育,竟然像米袋一样硕大!后来同样是医生为其进行了手术。文章说,多家媒体对这两件事进行了报道,不仅将当事者身体出现异常情况的经历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述,还图文并茂,用特写图片展示了当事者的隐私部位。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媒体并未将这两条新闻放在卫生健康版面,有的放在了社会新闻版,有的更是将其置于所谓的“趣闻”版,不仅占的版面大,用的是特别醒目的标题,还有不少在头版做了导读。
②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③⑤ 参见拙文《个人化写作与公共性》,载《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
④ 陈晓明:《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⑥ 有关历史题材作品热现象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历史亡灵复活的意味及其批判——近年历史题材作品热现象思考》,载《文艺评论》1995年第6期。
⑦(17) 参见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6月21日。
⑧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0页。
⑨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
⑩(11) 周小仪:《消费文化与生存美学——试论美感作为资本世界的剩余快感》,载《国外文学》2006年第2期。
(12)(13) 柯林·坎贝尔:《求新的渴望》,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14)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0页。
(15)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龙、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页。
(16) 参见拙文《历史亡灵复活的意味及其批判——近年历史题材作品热现象思考》。
(18)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10页。
标签:大众传媒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文艺论文; 猎奇心理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猎奇论文; 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