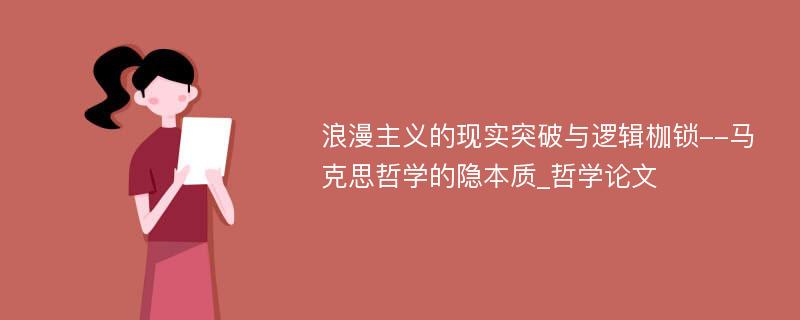
浪漫主义的现实突破和逻辑桎梏——马克思哲学的隐秘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桎梏论文,浪漫主义论文,隐秘论文,实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5-0012-07
马克思和浪漫主义的渊源在维塞尔的《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一书中有非常清楚的阐述。书中维塞尔以异样的视角解读了马克思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框架,认为浪漫主义神话诗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隐秘的本源。刘森林主编译介的这本书应该说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的走向应该起到振聋发聩的影响。可以说始于此如若不认真对待维塞尔的观点,则很难说其研究是负责任的;同样,不参照浪漫主义的因素研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难说其评价会是中肯的;甚或不区分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主义成分而执意为之,则必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在历史、当下和未来之中)。这后果的严重程度可以套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表达:“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我想马克思说这话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其他人严重误解了马克思。重视维塞尔的观点,寻找隐秘的浪漫主义痕迹,也许是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清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被误解的历史迷雾的钥匙。
一、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梦魇
浪漫主义的起源既有针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理性的反抗因素,也有克服有限性、通达无限性的救赎因素。启蒙运动所坚持的科学和理性遭到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相对主义和休谟(Hume)的怀疑主义的首轮进攻,唯理主义的理想被打破。始于真正浪漫主义之源——虔敬运动的精神生活,启动了反叛启蒙主义理念的,以精神、激情、神圣、个性、活力为特征的浪漫派的真正进程。作为浪漫主义真正父执的赫尔德(Herder)以表白主义、归属感、理想的互不兼容性,强调生命的表达性、多样性、个性,此观念犹如可怕的利刃巨创欧洲理性主义的肌体而几近颠覆了影响西方两千多年的“永恒的哲学”②。痛恨浪漫派放纵和幻想的康德(Kant)以彻底反对决定论的、人是自己选择结果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反权威和无拘无束意志的自由观,为浪漫主义埋下了极具革命性和颠覆性后果的种子。席勒(Schiller)以游戏冲动调和感性和理性的学说,同费希特(Fichte)以生命源于行动的理念一道,开启了浪漫主义的“人必须坚持不懈地生成和创造才能臻于完满”③的解放观念。接下来的费希特自我的主格宾格之分、谢林(Schelling)自身内的无意识力量观点,把走出浪漫主义荒蛮森林的任务,托付给了诗人的意志和情绪,从而开启了奔放的浪漫主义历程。奔放的浪漫主义在浪漫主义者的艺术理论和生活中,表现为思乡情结和某种类型的偏执狂两类思想情感。思乡情结是有限性、经验自我、个我对无限性、本我、自我即一和全的永恒追求——世界精神化——诗化世界,这也是区别于启蒙运动所追求的完美、封闭生活范式的无止境的向往和永恒的运动。偏执狂情结则认为世界存在某种神秘的狄奥尼索斯力量,在冥冥之中决定人和世界的命运,既可以摧毁一切障碍解放人类,也可以给无辜的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毁灭。纵观浪漫主义的实质是变相的形而上学,在反对科学、理性、理念的完满天国救赎道路中,踏入了反讽、精神、意志的无限性救赎歧路。歌德(Goethe)和席勒都反对无根的浪漫主义,认为浪漫主义不过是空洞想象的狂放表达“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古典主义是健康的”④是歌德对其最终的断言。
维塞尔对马克思哲学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即其神话诗学本源解读的切入点,是马克思的浪漫诗。他从马克思140多首诗中选择了17首,来说明马克思思想和浪漫主义的渊源,并把这些诗分为“整体之诗”、“异化之诗”、“反抗之诗”⑤,来说明马克思从浪漫主义脱逃与转向的思想脉络。如果维塞尔的发现是正确的,那么对浪漫主义的认识和批判,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移植到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和评价之中,成为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极具参考价值的路径。
维塞尔非常重视马克思文学旨趣对此问题的论证价值,从而强调其传记中的重要迹象,即“马克思终其一生对美学和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⑥。青年马克思曾听过浪漫主义首倡者之一施勒格尔(Schlegel)的两门课,并得到“勤勉与用心”⑦的评价,应肯定深受其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也试图通过浪漫主义的诗歌梦想来征服死亡,建立永恒的上帝王国,这有维塞尔列举的通信与诗歌为证。但是马克思此举遭受的挫败,维塞尔认为在他与他父亲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来:“在1833年和1837年之间,马克思对浪漫派的渴望的态度多次犹豫不定。然而,反抗和愤怒的心情却最终获胜。”⑧马克思这种对浪漫主义从沉迷到绝望的态度,在他的浪漫诗中有着直接的明晰显现。诸如诗作《苍白的姑娘》就表达了其对精神本源、诗化宇宙的绝望及对世界荒凉、生命有限的全新认识:“我心中燃烧的热望,到头来竟是梦幻一场,失去了上天的保佑,从此我完全绝望,我的心信仰过上帝,如今却堕入地狱的苦海汪洋……枝头没有掉下绿叶,向她表示哀泣悲伤,天地一片沉寂,无法唤醒这位姑娘。”⑨这首诗不仅表达了马克思曾经对无限精神的渴望、对自然神性的信赖,也表达了现在他对自然精神已死、人无法永恒的无情现实痛苦而逐渐觉醒的认识。马克思对此转变的评价是:“最近的诗是毁灭性的一击……如遥远的天宫一样真正的诗歌王国……以前的创作全都化为灰烬。”⑩在后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我们也得见马克思的表达明确显露了其哲学思考如诗歌一样的此种转向。他说:“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思想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一句话,你们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1)应该说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中延续的对精神、神圣、虚幻世界的批判。在这里马克思对脑壳中的东西表示了蔑视,开始转向现实的变革救赎,强调用现实活动否定旧制度,并且只有现实的“哲学”才是哲学,才能消灭脑壳中的哲学。而浪漫主义不过就是脑壳中的哲学,不具有反抗现有制度的真正否定力量。可见,浪漫主义确是马克思思想路径的一次迷失,尽管马克思不会承认他年轻时这种稚嫩的梦游经历,而是把对真正的抽象哲学的批判作为他哲学建立的基础,但是浪漫主义的价值理想一直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他的哲学的转向恰好在路径上是对浪漫主义虚妄的克服。而在他不能以哲学转向克服的无限性、世界精神、意志动力领域,他还是会回到他青年时的梦境,借助浪漫主义在记忆中留下的印痕,构思他的哲学体系。
二、马克思哲学是对浪漫主义救赎的现实突破
作为对现代性的第一次批判的浪漫主义,试图遵循意志、精神动力原则,由有限趋向无限,克服启蒙精神的理性、冰冷与虚无,实现人类与世界诗化的神圣救赎。可是浪漫主义所鼓吹的无意义、无目的的狄奥尼索斯的非理性,以及宇宙冷酷无情的客观性,使马克思认识到浪漫派抒情主义的救赎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他用诗作《小提琴手》的愤怒和悔悟的语言说“上帝对艺术一窍不通,毫不尊重,艺术是从阴暗的地狱跃入我的心中,它使我心荡神迷、如醉如痴,把这生机勃勃的艺术卖给我的是魔鬼”(12),从而否认了艺术——诗化世界——也即浪漫主义对人实现拯救的可能性,认为浪漫主义的救赎不过是魔鬼给予的美妙的幻影,它不会通向天堂而是走向地狱。
在经历由渴望、相信到挫败、失望、绝望的痛苦之后,马克思开始寻找新的救赎方向,他的哲学思想因此可以说是必然保留着浪漫主义基因的浪漫主义的转向。
1.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救赎的现实突破表现在其对精神解放彻底批判的态度中
马克思由浪漫向现实转换的核心突破,表现在其对感性的发现,及由之而对浪漫主义所追求的精神解放和感情的内在丰富性的批判上。马克思这一转换的灵感应该来自费尔巴哈(Feuerbach)的感性理论。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了两句既是费尔巴哈的发现、也是见证他灵感到来(感性转向)的真诚而严肃的判断:“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13)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如此高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推见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精神丰富而肉体僵硬的悖谬救赎困境所进行的长期苦闷的思索,以及发现解决途径的释然与凝重。只有在寻找替代那破灭的浪漫主义精神解放理想的合理之物长期未果的隐痛心境下,才会对一个引发顿悟的发现有如此深切的感慨。所以,尽管马克思的思想建基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Hegel),但潜隐着的、真正的出发点,却是浪漫主义的精神救赎破灭而遗留的心病。
浪漫主义无疑是追求精神解放的。其一是认为人是精神的完整存在物而不是科学、秩序和理性的碎片存在物。神秘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为此反对启蒙运动造成人活力的窒息,认为“由于人类的堕落,由于毫无想象力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人类灵魂杀手的邪恶工作,人类精神已经石化”(14)。其二是认为世界真正的主体是精神,是本我,是一与全,因此世界必须被浪漫化、被诗化,以解放凝固于其中的精神内容,从而通达由有限到无限的救赎之路。施勒格尔说“一块石头肯定也有意识和精神,只是石头死死锁住了意识和精神”(15),并用“有限性的表象终将被消灭”(16)表达了浪漫主义的精神解放的追求。维塞尔对浪漫主义的这一追求也从历史现实的判断中证实为:“面对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那一代德国人,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人和自然、本质和存在、客观化与自我现实化之间,一句话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敌对情绪”(17)
马克思从这种浪漫主义精神解放的抽身,是由其在1843年到1847年创作中对精神的反驳中透露出来的。本来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立没有必要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只要立论阐述即能够完成,但是在这五年期间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哲学的贫困》全部持批判的态度,而对精神的批判一直贯穿其中。在著作中他说过鲜明的反精神话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结论)“法的关系……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18)。这段话清楚表明其曾有的“善良的‘前进’愿望”(19)的浪漫主义“苦恼”与“人类精神”的关系,以及与“人类精神”决裂的事实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看清了他曾坚信的精神的“非存在”性质,认为“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20)。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非对象性的感性客体的局限性,否定了精神,认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21),这时的马克思已经自觉地抛弃了精神主体的任何学说而转向人的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建立了具有现实根基的、以“感性主体自我意识”为实质的精神学说,从而否认了精神主体(本我)和“摆脱客观性符咒的自由行动”(22)的自我意识,以及“人类意识是利用普遍本我要认识到自身即认识自己的精神活动所使用的手段”(23)的浪漫主义理论假说。马克思指出了精神的现实基础是“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24),并强调要“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25)。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分析了精神的来源,从而进一步对这种颠倒无用的纯粹哲学的“贫困”现象予以嘲讽:“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26)这样浓墨重彩、长篇累牍的批判已不能说明批判的偶然性和客观性,而是表明马克思潜意识中自身曾对精神的信仰以及现在对精神的自觉拒斥。应该说没有年轻时的浪漫主义思想印痕,则精神在哲学中的“在场”不会让马克思如此敏感与反对。
2.马克思的现实救赎之路是从精神解放和感情的内在丰富性转向感性的丰富性和人的全面发展
否定了世界精神,否定了诗化世界的可能性,马克思要寻找另一条救赎途径,那就是感性的丰富性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条救赎途径具体是通过把反理性转向反贫困和反资本逻辑、把非理性转向感性的确定性、把精神转换成肉体、把精神的生成转化成人的生成、把无限性转化为感性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把全和一转化为类、把精神自认转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把有限无限悖谬的动力转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动力而构建起来的。
浪漫主义反对理性与科学对人的抽象和僵化,把人变成没有精神的物质,使世界呈现为无神的荒凉。马克思却认为不是理性和科学僵化了人,而是理性和科学的现实运动,也即私有财产运动(资本)和工业(机器)使人异化为“商品”和“牲畜”资本和工业在马克思看来是抽象的生产,是剥削的真正秘密,是现实中奴役的根由,即“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27)。从马克思嘲笑浪漫主义者不懂得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运动的本质区别是造成的“家园失落”的现实原因而空自感伤——“浪漫主义者为此留下的感伤的眼泪,我们可没有”(28)——的揶揄中,得见马克思抛弃浪漫思想和反资本逻辑的此一转向。
浪漫主义认为诗化世界借助狄奥尼索斯的非理性力量,马克思则强调依靠“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29)的感觉,要运用内在的尺度去“构造”世界。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人本身都是自己劳动的产物,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0)。而这种劳动就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自然的过程,也即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的生成过程,亦即“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31)。马克思坚持费尔巴哈的观点“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32),认为“感性确定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33)的对象化实践,是确证和实现人个性的途径和真正现实力量。马克思为此直接否定了精神是灵魂自我的欢愉,以及是渴望和生成无限的自因谋划,而认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34)。至此,浪漫主义的精神及精神内部由有限向无限的追求,就变成了马克思的感性身体及其向感性个体——人——自身生成的追求。
浪漫主义基于人的碎裂、孤单、有限与虚无而要追求无限、一与全,追求永恒与圆满,并把反讽作为手段,把诗意世界作为目标,这显然是马克思蔑视的由“头脑的激情”建立的、只具有幻想现实性的“真理的彼岸世界”,相反马克思要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35)。马克思这一转向的迹象,在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由他自己提到过。在序言中,他说明了他对人的进步救赎观念由纯哲学(包括浪漫主义)转向现实的事实过程:“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36)马克思这一转向首先就把浪漫主义描述的机械、碎裂的身体,变为由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造成的异化而产生的畸形和贫乏的肉体,而解放的途径和方向就是通过“消灭私有制”(37),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38)。这一转变是基于现实的、感性的人,并且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中的人,并不是“脑壳”中解放,因而无论在解放途径和解放目标方面都具有现实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会坚定地指出浪漫主义的虚妄性,即“浪漫主义是对工业革命恐怖的逃避”(39)。
随着马克思把精神与现实的贫乏与单调转变为人感性的丰富与发展,他也把无限性、一和全归结为类和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人是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的类存在物,而不是纯个体存在物。恰似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强调的“诗歌是真正的、绝对的真实”(40),马克思也坚持只有作为类存在物人才能是“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41)。也恰似浪漫主义强调的“人有意识的个我、有限的自身不过是人真正的神圣自身的一部分”(42)一样,马克思也强调“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43),而“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44)。当浪漫主义强调诗化世界以达到永恒与无限,去弥合“诗与经验、理想与现实、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分歧”(45)时,马克思也用“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46)来表述共产主义的这种“诗化”特征,其表达方式在形式和意义上都与浪漫主义基本一致,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7)。而当浪漫主义把这种有限与无限、个我与本我的沟通力量,描述为一种不断生成的对无限渴望的、“有限自我与无限整体之间的狄奥尼索斯亲缘的心情,是对宇宙意义的认识,是对存在之诗的认识”(48)的反讽力量时,马克思则用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出生壮大的无产阶级力量(“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49))——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历史隐形力量的产物、“奴隶”和“掘墓人”——去消灭自身,实现共产主义。对此,马克思有这样类似浪漫主义表达的语言,即“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50),又有如“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51)。还有,当浪漫主义用“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52)表达其理念为生成着的无限增长的完美远景,马克思同样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3)来说明人的丰富的解放前景。更为相像的是,如浪漫主义所言“一切为我的事情皆是借助于我”,马克思也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对自身使命的自觉,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54)。
通常认为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体系建立了变革世界的新哲学,但黑格尔辩证法和理念实现自身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革命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无限性,而似乎浪漫主义的反讽和生成及无限的概念更能够切合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以上的分析很难说是牵强的歪曲。
三、浪漫主义的定式思维形成马克思哲学的逻辑桎梏
如果马克思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是确实的,那么马克思哲学当中的一些观念的逻辑根由就会被发现并被破解,并且是否具有现实性和合法性就会得到指认。有理由认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无产阶级、类、共产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等方面,马克思没有脱离浪漫主义的话语逻辑而形成其哲学思维突破的桎梏。
马克思在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决定力量(55)的论断,并不是与生俱来或不证自明的,它来自马克思苦闷求索的顿悟。尽管马克思予以详尽的阐述和严密的论证,但这种从天而降的超验的力量总有些浪漫主义所鼓吹的狄奥尼索斯力量的影子。而这一历史动力力量的设定,以极其抽象的方式被马克思延伸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并几乎左右了马克思哲学的一切判断,不能不说已经成为一种哲学思维的逻辑枷锁。即便人类社会真的存在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我们还应该在康德的“人以自身为目的”,以及阿克顿的“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56)的明见中,去寻求人类超越必然性的自为力量,从而在马克思所说的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自我决定中“自由活动”。这个判断应该是不证自明的:一种能看清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系矛盾的“自我意识”存在物——人——自然也能看得出走出这种困境的途径,而未必非要等到暴力革命的到来。这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以自由立国”(57)的革命力量,它是不同于必然性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导致的革命)的替代途径。显然马克思的神秘力量学说拒斥了这个途径的逻辑推演的可能。
浪漫主义由有限向无限、由个体向一全、由个我向本我的自因谋划是反讽,而马克思也把无产阶级作为人的解放的力量,即“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58)。在这里浪漫主义那个通达无限的反讽手段,变成了哲学的头脑(共产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心脏(解放的力量)这一逻辑挪移就把无产阶级看成是消灭私有制的唯一和有效的力量,以及把产生无产阶级的私有制看成是必须被消灭的、无限生成过程中必死的、不真实的阶段,从而彻底否定了私有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失去了探求私有制在其自身中可能克服的变交换价值生产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可能性。交换价值的生产是无止境的,它决定于对金钱的贪婪,而使用价值的生产是具体的,以身体的享受为限。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生产的对立端,会在人们的生产实践中趋于动态的平衡,从而使私有制的无限运动终止于人在实践中确定的尺度中。在洛克的财产“享用”为限、获得以“共有”为度的原则里,在亚当·斯密的以“体面生活”为必需品的概念中,都表明了私有制可以合理存在而不必必然被消灭的可能性。但是,一旦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按照反讽的逻辑设定,则无产阶级灵活的现实性就变成僵硬彻底的革命武器,而不再具有阿伦特所说的“契约立国”的可能性。同样在浪漫精神中,反讽的虚幻有效性就变成了真实而致命的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和残酷性。孰知生产从来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这种革掉资本家命的、生生断裂生产关系的生产,是否也会中断历史通向目标的生成过程?
浪漫主义逻辑对马克思思维的最高桎梏,在于形成了马克思所言的类及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浪漫主义的思想中无限、一、全、本我、诗化的世界才是真实和有价值的,有限、个我不过是通向无限的碎片,是非我。但很难说存在无限、本我之类的永恒物,其实真正真实的就是有限的、必死的经验个我。但马克思显然更相信无限(类及共产主义)而轻视真正存在的有限的生命。他说“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59)个体的死其实和所谓类的存在并没有具体关系,海德格尔明确指出“死本质上不可代理地是我的死,然而被扭曲为摆到公众眼前的、对常人照面的事件了”(60),所以不能因为所谓的类而伤害个体。没有超个体的类实体,正如没有超个我的本我、超有限的无限一样。把某类个体排除在外的如“无限”一样完美的“类”不过是人类的幻觉,其最终现实表现不过是一种具有乌托邦精神的普通个人组成的群体罢了——卡尔·波普尔所言的“乌托邦工程师”,不可能具有统一的精神,更不会具有完美的精神。可是,马克思却对这种“类”的观念深信不疑,此事实表现在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领导者的信仰中。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用大量篇幅表达了对公社和中央委员会的绝对信任和高度评价。诸如说“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61),还引用说“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洁、狂热”(62)。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论证为什么由常人组成的公社会成为超社会的完善政体形式,而中央委员为什么会成为超人。我们所能解释的只能是马克思认为他们是无限性、是本我的化身,因而才会具有这种完美和全面性,但其实它们更像是马克思浪漫思维中那真正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63)。孰知无论是公社还是中央委员,都不具有浪漫主义所标榜的完善性,因此这种信仰不过是又一个浪漫主义的逻辑移植而已。
马克思的感性和实践的思想,是真正具有活力和变革价值的。但是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思想印痕,却让马克思的哲学思索超出感性的限度,以类似反讽、无限性、本我、一、全的思想论说无产阶级、类及共产主义,而成了制约其思想价值的逻辑桎梏。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对待马克思的思想,抛开浪漫主义的因素,回到本真的马克思。历史不能改写,但人类的未来却能被筹划,因此我们责无旁贷。
①[德]恩格斯《恩格斯致保·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②[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62—71页。
③同上书,第93页。
④[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⑤[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刘森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⑥同上书,第15页。
⑦见《波恩大学肄业证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7页。
⑧[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刘森林编,第14页。
⑨[德]马克思《苍白的姑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5—497页。
⑩[德]马克思《致父亲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4页。
(11)[德]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5—206页。
(12)[德]卡尔·马克思《小提琴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78页。
(1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4—315页。
(14)[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第54页。
(15)[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刘森林编,第59页。
(16)同上书,第55页。
(17)同上书,第81页。
(18)[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32页。
(19)同上书,第32页。
(20)[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页。
(21)[德]马克思《马克思论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
(22)[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刘森林编,第47页。
(23)上书,第47页。
(24)[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
(25)同上书,第75页。
(26)[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9页。
(2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页。
(28)同上书,第260页。
(29)同上书,第304页。
(30)同上书,第310页。
(3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5页。
(32)同上书,第308页。
(33)同上书,第315页。
(34)同上书,第305页。
(35)[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9—202页。
(36)[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页。
(37)[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
(3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4—303页。
(39)[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第54页。
(40)[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刘森林编,第31页。
(4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2页。
(42)[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刘森林编,第33页。
(4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2页。
(44)同上书,第302页。
(45)[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刘森林编,第35页。
(46)[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4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7页。
(48)[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刘森林编,第31页。
(49)[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50)[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4页。
(51)[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52)[德]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72页。
(5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6页。
(54)同上书,第297页。
(55)[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56)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4页。
(57)[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02页。
(58)[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页。
(5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2页。
(60)[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王庆节、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91页。
(61)[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页。
(62)同上书,第80页。
(63)[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
标签:哲学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