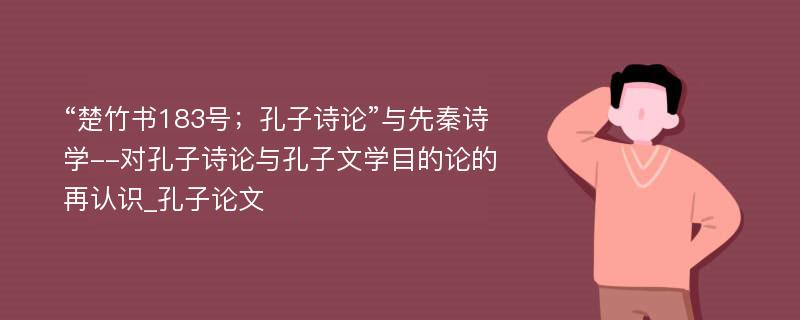
《战国楚竹书#183;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目的论论文,再认论文,诗学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出版,是2001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而其中的《孔子诗论》,对于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的研究来说,其意义更是重大。根据马承源先生的分类与统计,《孔子诗论》的29支竹简大体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类是诗序言性质的竹简,第二类是讨论诗篇具体内容的竹简,第三类是专门讨论邦风(即国风)的竹简,第四类是邦风与大夏(即大雅)、邦风与少夏(即小雅)并存的。《孔子诗论》的内容所涉及的诗篇包括讼(即颂)、大夏、少夏、邦风59篇,其中包含7篇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马承源主编《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附录一《竹书本与今本诗篇名对照表》。)。
《孔子诗论》的出版,因为收集有孔子及其后学关于诗乐文及数十篇传世《诗经》及佚诗的批评,证明了孔子与《诗经》的密切关系,及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以动摇的地位。同时,在学理上也为我们全面认识孔子的诗学理论提供了新材料和新眼界。
首先,《孔子诗论》对我们认识《诗序》问题,提供了支持。《诗序》问题是讨论《诗经》主题、诗人的创作目的,以及讨论孔子与《诗经》关系的核心问题。成伯玙《毛诗指说》云:“序者,……申其述作之意也。”王安石云:“《诗序》,诗人所自制。”(注:朱彝尊《经义考》卷九十九《诗一》引。)程颐曰:“《诗大序》国史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注:《二程遗书》卷二十四《伊川先生语十》。)这些观点,虽然难免为推测之言,但却并不与汉儒所论抵牾,又极尽逻辑情理。所以,我相信“《诗序》应该是诗人或者采诗官所记,太师所传,至孔子删诗,有所删正,子夏传之,毛公加以申说”(注:参见拙文《诗序与诗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建立》,中国诗经学会编《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今天《孔子诗论》的发现并公布,为《诗序》的权威性又加上了一个新佐证。我们虽然不能通过《孔子诗论》直接证明《诗序》的确经过孔子整理,以及由此探究孔子如何整理《诗序》,以及如何删诗的问题,但是,《孔子诗论》的内容再次雄辩地证明《诗序》绝不会是汉儒凭空杜撰,而是在孔子之前就存在的,是经过孔子传承下来的。
《孔子诗论》所阐发的诗论观点,与《诗序》极为一致,而且,由于论述语境和方式的差异,《孔子诗论》和《诗序》还可以互相发明。《孔子诗论》第1简与大序的一致性,是大家都肯定的。我们以第8简和第9简为例,第8简曰:“《十月》善諀言,《雨无政》、《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疑言不忠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小有仁焉;《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伐木》[弗]……”第9简曰:“实咎于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祈父》之刺,亦有以也;《黄鸟》则困,而欲返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则以人益也;《棠棠者华》则……”(注:本文涉及《孔子诗论》的引文,用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见《中国哲学史》2002年1期。廖名春之校释,吸取了马承源隶定本的成果,改正了马承源隶定本的混乱,有较大参考价值。)
按《诗序》云《十月之交》、《雨无政》,大夫刺幽王也,《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諀言,即訾恶讽刺之言,幽王政治之衰,国事日非,“非所以为政也”(注:《诗经·雨无政序》。),所以王公耻之,有讥刺之言;《诗序》云《小旻》亦大夫刺幽王也,《诗集传》以为“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廖名春认为“《小旻》多疑,疑言不忠志者也”的意思是“人臣对君上的倒行逆施多有怀疑,因而离心离德”。《诗序》云《小宛》刺宣王也,宛,小貌,所以《毛诗正义》云,毛以作《小宛》诗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为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狭小宛然。经云“宛彼鸣鸠”,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鸟然。传曰“小鸟”,是也。所以,《孔子诗论》云“其言不恶,小有仁焉”。《诗序》云《小弁》、《巧言》皆刺幽王也,而《巧言》则是“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孔子诗论》之言谗人之害也,正是指此。《诗序》曰《伐木》宴朋友故旧也,其中有“宁适不来,微我弗顾”,“宁适不来,微我有咎”之句。《诗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孔子诗论》之言“《伐木》[弗]……实咎于其也”(注:此处是简8与简9合文。),其,己也,正是《诗序》之旨。
《诗序》云《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君能礼下,臣能敬上,君臣和美,所以《孔子诗论》说“《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蔑疆,无疆也,巽,具也,寡德,此处指君德也。《诗序》曰《祈父》刺宣王也,《毛传》云祈父为司马官,职掌封圻之甲兵,《祈父》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颤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毛诗正义》云:时爪牙之士呼司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职有常,不应迁易。汝何为移我于所忧之地,使我无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称,故陈之以刺王。所以,《孔子诗论》曰《祈父》之刺,亦有以也。《诗序》云《黄鸟》刺宣王也,诗曰:“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孔子诗论》云《黄鸟》则困,而欲返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与《诗序》一致。《诗序》云《菁菁者莪》乐育才也,“君子能长育人才,则天下喜乐之矣”。《孔子诗论》曰《菁菁者莪》则以人益也,人益是言益人,此正是乐于育人之特点。《诗序》曰《棠棠者华》刺幽王也,虽然《孔子诗论》之《棠棠者华》失辞,相信与《诗序》必然相表里。
因为《孔子诗论》可能是孔子教授学生时讨论《诗经》话语的集结,所以,比之《论语》中孔子关于《诗经》的有关论说,则更见具体而贴近诗意。但是,它不是对《诗经》某一篇主题的全面阐释,所以,比之《诗序》,则见简洁间接。因此上,就《孔子诗论》的语境而言,其谈话场合和对象更接近于《论语》,其阐释诗旨又与《诗序》有一定联系,所以,这种解释体例存在差异,以及话语方式和语境上的差别,使《孔子诗论》和《论语》论诗,《诗序》解诗,在论述角度和方式上都不可能成为一个重合的文本。马承源先生说:“以上孔子授诗内容,除指出《雨亡政》、《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以外,其他都没有发现如《毛诗》小序所言那样许多‘刺’、‘美’对象的实有其人。”因此马先生断言“小序中的美、刺之所指,可能多数并非如此,之所以写得这么明确,可能相当部分是汉儒的臆测”(注:见《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之《篇后记》。)。
实际上,马承源先生的说法是对《孔子诗论》的误读,《孔子诗论》既不是《诗序》的另一版本,也不是孔子所创作的第二部《诗序》,我们要了解《诗序》的价值,是要看《孔子诗论》是不是与《诗序》关于《诗经》各篇主旨相矛盾,如果矛盾,说明孔子没有阅读过《诗序》,《诗序》的价值就可能大打折扣,如果相反,则说明《诗序》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通过对《孔子诗论》与《诗经》的对比研究,实际的情况是,《孔子诗论》对《诗经》主旨的评论,是在《诗序》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因此可以说,《诗序》肯定是在孔子之前就存在的。
《孔子诗论》与《诗序》的一致性,为我们重新认识孔子的文学目的论提供了新证据。《孔子诗论》第1简:“诗无泯志,乐无泯情,文无泯意。”(注:廖名春对这句话的隶定,参考曹锋、李学勤先生的意见,似比马承源的隶定准确。)我们可以看作是孔子对文学创作根本目的的阐述,而其基本精神,正是《尚书·尧典》所谓“诗言志”,孔子论诗、乐、文,抓住了志与情与意,就是强调文学从根本的目的意义上说,应该体现对人的关怀(注:参看拙文《古代文学存在的价值与研究的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6期;《从出土文献诗与志的关系看文学的价值》,《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4期。)。《诗序》曰:“诗者,志之所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说明诗之“志”是有关人生与人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感触和评价的,诗是体现以人为根本的价值观的,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创作出来的,是人文精神的直接体现,所以,《诗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序》立足于以《诗经》各诗篇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来解说诗意,其立论在于“美刺”、“兴寄”,即以文学关心人生,关心人类的生存状态。而《孔子诗论》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多少“美刺”问题,但是在字里行间,都隐藏着对美刺的肯定。
在传世文献中,孔子所谓“兴于诗”的说法,最准确地反映了《孔子诗论》关于文学终极目的的思想,《孔子诗论》第10简曰:“《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11简曰:“《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诸……”第16简曰:“[父母也。《甘棠》之报,敬]召公也;《绿衣》之忧,思故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孔子曰:吾以《葛覃》得祗初之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返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孔子评论诗,不离为人之根本,所以,孔子对文学的认识,是把文学与人格的修养紧紧地扣在一起。《论语·泰伯》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之兴人,为的是立人,成人,所以,诗的内容的纯正就显得格外重要。《论语,为政》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对内容的基本要求。《论语·子路》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阳货》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些都是强调诗为兴人、立人、成人的手段。孔子把诗纳入为人的存在服务的大系统之中,诗是为人类的福祉服务的;诗歌不仅仅是体现个人之哀乐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个人哀乐的表现,成为培养人格、实现美好政治理想的媒介。即文学必须体现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文学应该关心人,关心人的成长和生活,反映人的喜怒哀乐。所以,《诗序》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书·艺文志》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大学》之言“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治国平天下应始于修身齐家,修身齐家则应从正心诚意开始,正心诚意又依赖于格物致知。“兴于诗”,从读诗开始,无疑正是孔子格物致知的意思所在。
了解孔子此目的,我们反回来再看今天所谓的文学独立论者,难免就显得肤浅。文学的独立如果说就其学科独立的意义而言,似乎有一定道理,如果把它看成是追求艺术的华丽,而丧失为人的根本,则文学本身也就没有价值了。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幸福的,这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当然也是文学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