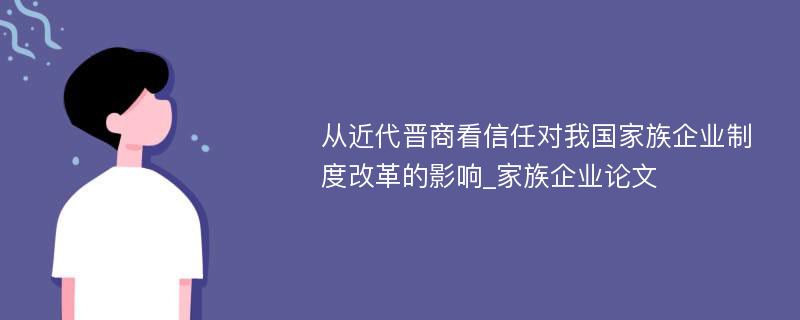
从近代晋商看信任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变革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晋商论文,家族企业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2006)05—0245—03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已表现出强大活力,支撑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中有90%以上是家族企业,绝大部分实行家族式管理。但是,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制约。一方面我国家族企业的寿命很短,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五年,大企业的平均寿命也不到十年。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很难再长大,失去了创业时的生机和活力,成为长不大的“小老树”。
针对目前我国家族企业发展中的困境,有学者提出要实现更大的发展,必须摒弃家族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不少企业主也在打破家族制,实行两权分离方面作了很多尝试,但很多都失败了,如兰州黄河集团,它在吸取失败的教训后,重新又回到了家族所有家族经营的形式。重庆力帆集团老板尹明善声称家族企业50年不变。西安海星科技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荣海说:“在1993年的时候,我在公司里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包括亲戚、同学、朋友,但是后来发现,家族式管理在中国有它的道理。”
所有这些表明,目前中国很多家族企业向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演变的条件还不成熟。本文认为,影响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革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信任资源。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而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分工合作,没有信用制度的支持是不可能扩展到家族或血缘关系的支撑范围以外的(汪丁丁,1997)。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家族企业一方面受到传统伦理信任资源匮乏的制约,难以像近代晋商那样获得传统的泛家族信任资源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受到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的制约。信任资源的双重残缺使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采取了家族治理模式,难以从家族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一、信任的内涵、分类和特征
信任(trust)、诚信(honesty,trust)、信用(trustworthiness,credit)、信誉(credit,prestige)等一些相近的概念,学术界对此没有准确的区分,本文主要将其理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
信任是组织控制的机制,具体地说,是在价格和权威之外的另一种组织控制机制(Bradach & Eccles,1989),信任由于具有有限理性以及专用性的特点,因而是一种有价值的无形资产(Mark Lorenzen,1998),信任的出现能降低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减少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信任的出现常常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Kreps,1986; Fbdenberg & Tirole,1992; Williamson,2001)。
家族企业的信任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家族信任。即基于血缘、亲缘、姻缘基础上的信任。家族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私人信任,它是华人社会信任结构中的基石。第二,泛家族信任。即基于地缘、业缘、学缘和朋友缘等私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信任。此类信任主要是源于习俗、道德规范和礼尚往来所产生,这是华人社会中最复杂的信任。其产生不仅与人们之间的交往次数、频率和回报预期感受相关,而且与华人社会长期形成的一些社会交往的文化规则相关,这些文化规则对信任的产生有一种先验性的奠基作用。泛家族信任既包含有亲情的信任又包含有算计性的工具信任。第三,社会信任,即主要靠法律、法规制度维系的普遍主义信任。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制度对信任的广泛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支持,使得更进一步的风险承受能力与信任行为成为可能。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华人社会的信任度很低。德国学者韦伯(M.Weber)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信任关系有两类: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后者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大多建立在亲缘或类亲缘的私人关系基础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所以中国人对圈内有“特殊的信任”,对“外人”却非常不信任。福山(F·Fukuyama)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经济的繁荣》一书中认为,经济深植于社会生活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通常是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他在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认为,美国、日本、德国属于高信任度国家,而法国、意大利和中国属于低信任度国家,中国社会的信任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家族基础之上,中国社会的本质和信任关系的基础是家族主义,对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任,是一种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
目前,中国处于转轨时期,社会信任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家族信任和泛家族信任是基石,而制度化的社会信任度很低或有限,社会信用缺失(G.Hamxilton,1991; 郑也夫,2003)。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张,并影响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影响古典式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二、信任资源与近代晋商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民间私营企业曾经有很好的发展,并且不乏规模相当大的企业,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商和晋商。晋商是当时国内实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一大商帮。从明初到清末,他们在商界活跃了5个多世纪,活动范围遍及国内各地,并涉足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晋商的经营项目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尤其在清代创立票号之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相结合,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有人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仑到北京铺一条路。北京至今还存在的著名老字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晋商首创和经营的。明清晋商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是罕见的(张正明,1995)。
近代晋商的发展与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的诚信密不可分。“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是晋商称雄中国500年的奥秘之所在。晋商视商业信誉高于一切,这可以从他们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的格言中看出:“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出言必顾行”。晋商首创的票号,是信用制度的产物。1824年,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家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这就是山西境内平遥城里的日升昌票号。此后的一二十年间,山西票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到极盛时,山西票号发展到28家,票号在国内设立分号的城镇增加到80个,并在朝鲜仁川,日本神户、东京等也设立了分号。票号重信用,轻抵押,这与意大利金钱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票号依靠诚信制度的创新而“汇通天下”。晋商在对待同行与合作伙伴的经营活动中也很重诚信,被美誉为“虽未经国家法律之规定,而守范围、重信用、敦品行,此其所长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晋商的很多商号(特别是驻各地的分号)普遍采用了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的制度。晋商在商号经理聘用方面很有特色,财东(投资人)物色到合适的经理(掌柜)之后,便向掌柜授予全权,并签订契约,规定若干资本由掌柜自主经营,不干预掌柜的一切经营活动,让其大胆放手经营,连日常盈亏也不过问,只是静候账期决算(一般为四年)。由于财东充分信任经理,所以经理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可见,在晋商的发展过程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已达到相当程度的分离,财东对经理的信任程度之高,是西方国家难以比拟的。在晋商兴盛的几百年间,极少有掌柜和伙计坑害企业、欺骗财东的记载。这一方面是晋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财务、业务信函往来、报告、休假、日常管理等制度,另一方面是形成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诚信文化。晋商发育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其用人基本局限于本县和邻近地区,一旦某人因为违规被商号开除,意味着其他所有商号都会知道,而且没有人会再用他,代价极其惨重。
近代晋商的发展,没有良好的信任资源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种信任主要是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家族信任和在地缘、业缘、学缘和朋友缘等私人关系基础之上的泛家族信任,即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伦理规则及泛家族规则为核心内容的道义信用规则。
三、信任对家族企业制度变革的影响
家族信任是家族企业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并且家族信任对于两权合一的古典式家族企业而言,具有生产性,因为它提供了家族企业家创业所必需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且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家族信任有助于克服一次性博弈中的“囚徒困境”的局面,降低组织合作的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效率。这种生产性源于家族信任所具有的利他主义动机和合作的可能性,为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便利。但是,建立在家族信任基础上的家族企业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融合社会人力资本,引入非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从而使古典式家族企业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泛家族信任和社会信任显得尤其重要。具体地说,信任对家族企业制度变革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企业内的委托——代理链条越长,雇佣关系越发达,企业的平均规模越大。也就是说,随着信任由家族信任、泛家族信任向制度化的社会信任方向发展,企业规模将趋于扩大。福山(见表1)Rafale La 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Andrei Shleifer(1997b)① 以及张维迎(2002)等人的研究都证实了上述论点。社会信任有利于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从古典式家族企业向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发展,而过强的家族信任则不利于大型家族企业的发展及两权分离治理结构的完善。
表1 信任与企业规模
国家主要企业的平均雇员人数
前10大企业前20大企业
韩国54416 不详
法国11604981381
德国177173114542
美国310554219748
资料来源:(美)福山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63页。
2.社会信任结构对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企业所有权多元化的风险相对较小,取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越强,这将为企业实现所有权的多元化、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创造条件;相反,社会信任度低的国家或地区,企业更倾向于个人占有全部资产,企业取得金融机构贷款的成本相对较高,所有权难以多元化,或所有权只能在家族成员内部实现多元化。对此,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Luigi Zingales(2000)等人对意大利南北地区的相关实证分析证明了上述观点。
3.信任资源影响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对家族企业而言,企业的持续成长主要表现为要不断突破家族资本的封闭性,去吸纳、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引进职业经理人,就得对他们授让部分经营管理控制权,而授权的过程是一个家族企业机密资源和机密信息与外人分享的问题。由于社会信任资源的缺失,中国家族企业主更倾向于个人集中垄断企业机密信息和资源(储小平,2003),如不少企业主对相关客户、营销、竞争、原料采购、价格等商业秘密不会轻易地让非家族成员的经理了解掌握。于是,就出现两种情形:一方面,职业经理人,特别是非家族成员的经理由于没有得到职位工作所必需的信息和资源,难以有效地完成工作,使家族企业主认为他无能,这些经理就会跳槽。另一方面,一部分非家族成员的职业经理获得了一些机密资源和信息,特别是一些客户资料,并与客户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便另立门户,带走重要的商业机密,和自己原来的老板同业竞争。所以,对家族企业来讲,真正稀缺的不是管理资源,而是“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家族企业制度变革要么抓住控制权不放,但使企业成长受到限制,不能从封闭式家族企业走向开放式的家族企业,更谈不上发展成为现代企业制度。要么部分或全部让渡控制权,但有可能导致控制权旁落他家。正如张维迎所讲的,中国并不缺乏有管理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同时需要融和外部管理资源的企业也大量存在,目前真正缺乏的是社会信任资源。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家族企业处于创业和成长阶段(张厚义等,2002),在双重信任资源残缺的社会环境下,两权合一的古典家族企业制度能节约交易费用,是一种有效率的适应性制度安排。但是,“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② 对有规模的民营企业来说,走向委托代理制,走向现代公众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必经之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需要构建信任文化,完善法律制度,为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革创造良好的信任环境。
收稿日期:2005—11—21
注释:
① Rafale La 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Andrei Shleifer等人将新人划分为社会信任和家族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规模与这两种信任的关系。分别用调查对象信任陌生人的比重和信任家人的比重来表示社会信任和家族信任,结果表明,前20家企业的销售额与信任陌生人(社会信任)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54(t=4.1),而前20家企业的销售额与信任家人(家族信任)之间的相关系数则是-0.563(t=-3.1)。
② 卢元镇:《体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