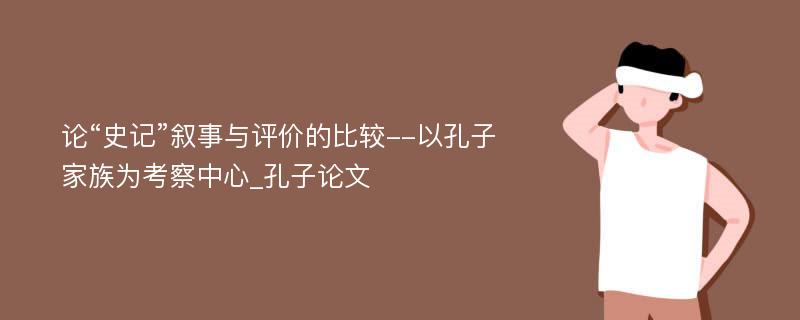
论《史记》叙评对比——以《孔子世家》为考察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孔子论文,世家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3)03-0393-09
一、前言
司马迁叙史写人,蕴含史笔文心,具有“成一家之言”①的用心。以传纪体的方式记述历史、表达史观,承继《左传》“君子曰”的传统,以“太史公曰”的论赞方式阐述司马迁自身的看法。然而《史记》中却有着许多传文与论赞之间,甚至与自序中所论著作之意,相歧异或相矛盾的地方,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司马迁特意为之,藉此表达个人的思想与情感,或将深意隐含于其中。《史记》诸多人物中,当属孔子最为司马迁所敬佩与称颂,孔子一生为礼乐教化付出无悔的努力,周游列国十余年,许多的挫败与折难,暮年返国之后,专心在《春秋》的编纂之上。除了孔门弟子编纂的《论语》保存孔子的言行之外,司马迁在《史记》中替孔子写下第一篇个人传记。事实上,《孔子世家》考订上有着许多疏漏与错误,但这却不伤其价值,因为司马迁在传文中试图贴近孔子之心,比起后世许多的校订,《史记》的叙述更能呈现孔子的人格。翻阅《孔子世家》,可以看到孔子奔走各国的沧桑与行道的艰难,才能无所发挥,始终不得志;但司马迁于论赞中却极力颂扬孔子的文化事业,使得圣人形象又跃然纸上。这其中有何差异?太史公何以如此叙写孔子?是为本文所欲探究之要旨,试图就传文与论赞的相异或是对比中,考察司马迁心中的孔子形象,以及两者心灵上的贴合。
对于《史记》的传文记述与史公论赞相异之说,韩兆琦于《史记博议》论其矛盾性,认为主要由刻意为之、思想观点以及情感与理性三种因素所造成,这些传主又以汉代人物居多,是以因政治因素而晦言之或披露隐情,抑或在思想及情感有所冲突时候,所采用的一种著述笔法,使之不失实录,又能为一家之言。关于《孔子世家》一文,针对入世家的考究之外,对司马迁如何揭示政治命运与遭遇多作剖析。是故,本文以《孔子世家》为论述焦点,并旁及《史记》相关孔子之论,以太史公对孔子的刻画,以及如何透过孔子表达自身理念,为开展的主轴。
二、挫败的叙事
《孔子世家》集中记述孔子对礼乐的努力与明君的追寻,然而“天下无道”构成屡屡的挫败,孔子丝毫不减对“道”的坚持,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宛如一叶扁舟,欲挽狂澜于既倒,无畏迎面而来的惊涛巨浪。
(一)圣人的凡相。
司马迁在五帝、三王的本传之中,都强调他们拥有先祖神圣的血统,或是承天降生的异事,如殷、周先祖是“吞玄鸟卵”与“践巨人迹”②,即便是屏周的诸侯世家,也多为古圣先王的后裔血脉,近如汉高祖刘邦,亦有着神异的诞生现象③。但《史记》对孔子的记载却是:“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其为宋微子之后人也仅论“其先宋人也”(《史记·孔子世家》,第1905页),并未凸显孔子的先祖血统或是特意神化出生的不凡。所谓的“野合”,是指父母非合礼仪而婚,郑玄于《礼记·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条下注曰:“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1]又《史记正义》曰:“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史记·孔子世家》,第1906页)因此,孔子出生是不合于礼仪,但亦非今日的“野合”之意,乃是时代的推移所造成的词义变迁。司马迁录圣人事迹并不予以隐讳,若以此论孔子之生是接续下文“祷于尼丘得孔子”为感天而生④,那么言叔梁纥与颜氏女祷祝而生即可,提及非礼仪之事,并非特意地褒贬孔子,应是司马迁欲显孔子亦为平凡人,非遥不可及的圣人,同时也展现史家的核查录实的精神。
在《孔子世家》中又述孔子幼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第1906页)孩童嬉戏为正常之事,孔子陈俎豆、设礼容是效仿成人行为,其后的孟子亦如此,刘向《列女传·母仪传》:“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衒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2]此一叙事见微知著,钱穆论之:“为士者必习礼。孔子儿时,耳濡目染,以礼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儿童。”(《孔子传》,第7页)不论孔子幼时是否仍为士族之家庭,即便出身贵族之家者,也非人人均以礼为嬉戏内容,故孔子以礼容作为游戏,必然与家庭教育有关,可睹日后孔子追寻礼乐理想世界的初萌。
另外,司马迁所描绘的孔子并没有所谓的清高形象,如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欲召孔子为用,其后周游列国途中,晋国佛肸也欲召孔子,这两次孔子都显得心动欲往,却均受到子路以君子的立场批评,遂止。在鲁国之时,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孔子面露喜色,亦被学生提醒(《史记·孔子世家》,第1914、1917、1924页)。这些记载固然不符后世对夫子圣人形象的想象,却使孔子形容更为贴近一般人,也表露其从政用世之心的迫切。
由上可见,司马迁没有将孔子神化,而是从最平凡之处暗示未来的可能成就,同时说明圣人是平易近人而非高高在上,在传文中有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史记·孔子世家》,第1909页)由细微之事,见孔子不以职小而怠忽,呈现一位青年兢兢业业的模样,表达出孔子在文化史上绽放光芒的必然。
(二)挫败的政治生命。
《孔子世家》载:“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孟厘子曰)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史记·孔子世家》,第1908、1910-1911页)然《索隐》引《左传·昭公七年》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召大夫’云云。按:谓病者,不能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云‘仲尼时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误也。”(《史记·孔子世家》,第1908页)说明太史公记载之误,此系于孔子少时,对比传文记载俎豆礼容,可见司马迁的心中,孔子是少时即知礼之人,人生的颠沛也是从对礼的坚持开始。传载:
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第1915页)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史记·孔子世家》,第1917页)
鲁国在孔子治理下,呈现着国泰民安的气象,表现出孔子并非只是空言理论的思想家,而是能够付诸实现的政治家,其理想完全有被实现的可能。但才干特出之人,往往会遭遇他人的畏惧或嫉妒,以上两则孔子为政之绩的记述,后面都接着敌国对孔子的忌惮,甚至以计谋使孔子失位。《史记》:
孔子为中都宰……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史记·孔子世家》,第1915-1916页)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黎鉏曰:“请先尝沮之!”……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第1917-1918页)
孔子真正的从政及掌有实权仅在鲁定公时期的短短数年,先有夹谷之会,让鲁国以小国获取外交上的胜利,及至桓子受女乐,内部的腐化,造成在位者不行道,使得孔子不得不自我放逐。然而,孔子从政最为挫败当属“堕三都”一事,《孔子世家》曰: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史记·孔子世家》,第1916-1917页)
《左传》将此事系在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且并无“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一语,当时季氏执政,堕三子之都的实质受益者也非鲁定公。司马迁基本因袭《左传》之说,先论孔子言于定公,以显孔子欲压抑权臣,以彰国君之意。由于公山不狃与叔孙不服,使鲁君与采邑之臣兵戎相见,让百姓无辜受害。从另一角度而论,孔子的用心,是惧采邑之臣坐大而叛乱,造成国内动荡不安。⑥孔子此举最终无功而返,虽然力抗春秋“陪臣执国政”的僭越现象,失败以终也预示着封建礼乐时代将一去不返,孔子的政治理想将不为当世所用。
(三)世道不遇的必然。
《史记》以年系孔子一生行事,孔子不遇的命运,使淑世愿望无法具体落实,却又是当时必然的结果。长达半个世纪的行道岁月中,孔子真正参与政事的日子并不长久,更多的时光是在教授学生,或是四处奔走,以期明君为用。
孔子年三十适齐(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的应对受到赏识,景公欲重用之,司马迁记载此时晏婴沮之、齐大夫害之(《史记·孔子世家》,第1911页),使孔子失去展露长才的机会。但这段叙事是有问题,因为《左传》中未载晏婴沮孔子之言,而且当时孔子方为青年,晏子已是年逾七十、名显诸侯的国之重臣,基本上晏婴并没有排挤孔子的理由,而孔子面对齐景公,《左传》载:
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3]
景公田猎之时,招虞人以弓,是件违礼之事,孔子听闻后也只是称赞虞人“守道不如守官”,未见对景公有所评论,故孔子对于齐君应未有所期待,而司马迁写道:
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闲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史记·孔子世家》,第1911页)
欲凸显的是“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2817页),也点出春秋之时,在陪臣执政下,国君无法任贤用能的状况。
孔子为政时,因桓子受齐人女乐,有感政治上的挫败,黯然离开鲁国,踏上十余年周游列国的旅程(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已过“知天命”年纪的孔子,远离故国,去找寻道的落土之处,所遭遇却是“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闲”(《史记·孔子世家》,第1909页)。孔子受到谗言、围困,几经波折,最后又回到卫国,然而卫灵公却是“老,怠于政,不用孔子”,致使孔子又一度离卫,但再度折返的结果是:
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鴈,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史记·孔子世家》,第1926页)
卫灵公一心想扬威军旅,亦非孔子心中的行道之君,是年(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又离卫去陈,周游列国的前半段,孔子就在卫、陈之间徘徊,然而始终未能找寻到可事奉行道的君主。
周游列国期间,季桓子卒(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遗言季康子召用孔子,孔子曾有回到鲁国的机会,却因为公之鱼所沮,仅召回冉求,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史记·孔子世家》,第1927页)未能回国再度为政,但传己之道的弟子已能返鲁致用,孔子的心境可能非常复杂。其后绝粮陈、蔡之际,楚昭王兴师以迎,虽欲封地予孔子,也因子西的进言而止。《孔子世家》中,可以看到孔子数度受沮,面对君无道而多谗臣的世道,那种天下莫己知的悲凉孤寂之感可见一斑。⑦
综上所述,孔子之不遇,是因为政在家门,这些权臣为一己之利,对于人才有所妒忌,进而横挡仕进。《论语》载孔子之言: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⑧
世道的衰微,造成处士横议,礼乐的价值终究一去不回,即使行道坚定,也难挡与人间的扞格。与其说是周“游”列国,不如说是在浪迹天涯,期盼找到可以依托的天地,但寻寻觅觅的结果,只能自我解嘲为“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第1922页)或者临河感叹“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第1926页)这并非孔子的理想脱离现实,当各国畏惧孔子受到重用,就显示孔子企图以礼乐再造旧邦新命,仍具有一定的治国价值。只因遭谗畏讥,才会凄凄惶惶十余年,最后回到母国故土,亦为“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第1935页)。世道的衰微,注定孔子的努力无法成功,无人问津,也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正义·宪问》,第十五页上),同时也映照出孔子一往无悔的精神。
三、至圣的尊崇
孔子生前奔走各国未获重用,死后有赖门人与再传弟子的努力,遂能将儒家学说保存及发扬,《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第3116页)依凭这些学生门人的传布,孔门思想学说在战国纷争、处士横议的年代,面对其他思想家的挑战,依然不绝如缕地传播下去。及至汉一统天下,陆贾建议汉高祖刘邦以六艺治国,同时叔孙通也为汉廷起朝仪⑨,虽未能够为儒学争取官方的高度重视,从正面的意义而论,也让儒家思想于战火后的世界,找寻到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
(一)折中夫子。
《孔子世家》叙写孔子积极用世,企望在政治上能有作为,然而司马迁于论赞之中却高度称扬孔子在文化与教育上的事业成就。鲁大夫孟厘子即称之:“圣人之后”(《史记·孔子世家》,第1907页),而孟子更论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②在先秦,甚至孔子当代,已有“圣”之名,太史公在论赞之中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在圣之前冠上“至”,又论言六艺者以孔子为最高标准,即是司马迁给予孔子最高的敬意。
司马迁对孔子的礼赞不仅见于《孔子世家》,《史记》里有许多考其是非与评论人物多引自于孔子。如《吴太伯世家》赞引孔子曰:“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史记·吴太伯世家》,第1475页),《宋微子世家》赞亦引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史记·宋微子世家》,第1633页),《酷吏列传》序引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酷吏列传》,第3131页),等等,显示司马迁将孔子之言视为论史的绳准之一,《伯夷列传》载: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蓺……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史记·伯夷列传》,第2121页)又论: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史记·伯夷列传》,第2122页)
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事迹让司马迁感叹天道报施失准,但传首先言考信六艺,表示司马迁处理“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第46页)的材料以“六艺”为标准,又称睹“轶诗”可异,在六艺与轶诗之间,太史公必然以六艺为依归。但太史公是否真惑于天道不公?又引孔子之言: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史记·伯夷列传》,第2126页)
表明伯夷、叔齐乃求仁得仁,对于恢恢天道,不应拘执在生命的存在,而是超越看待精神的展现,所以司马迁仍是肯定孔子之意,藉孔子为一己之身与往哲先贤的联结作出生命的超越。《自序》中太史公亦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司马迁克绍箕裘,也有承继孔子作《春秋》的宏大志向。显而易见,圣人笔削,是史家的典范,而且孔子的至圣形象是贯乎《史记》,圣哲之言,见重于史家之笔。
(二)行道与广道的抉择。
司马迁赞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在礼器文物与儒生面前,司马迁对孔子的孺慕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虽然本传所呈现的是孔子行道不成的故事,然而却是太史公在赞中所论的真正的道之所在,否则孔子政治的失败,又怎能衬托出淑世之志的伟大,而这种对比,在弟子们与孔子政治生命的反差上可以略窥一二。
孔子的理想可以说在具体的现实世界中无法落实,而弟子们却能够在鲁国政坛上有着一定的地位,但他们从政却逐渐背离孔子的理想之道。从其他的记载来看,《国语》:
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茍而赋,又何访焉!”[4]
对于季康子想要扩大征兵的政策,孔子是持反对意见的,不仅批评这项政令的举措之失,对于为季康子服务冉有不假辞色,显示孔子认为冉有身为臣子理当对季康子加以规劝,但冉有却没有这么做,显然是帮着季氏为恶。又《论语》载: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注疏·季氏》,第三页下)
孔子因冉有无法阻止季氏僭礼行为,责备他不知礼,这是很严重的话语,表示孔子对冉有的为政之道感到已经是背道而驰,在理念上渐行渐远。《雍也》篇载:“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注疏·雍也》,第五页上)若是冉有如孔子般的坚持在行道的路上,那么季氏是否依然会重用冉有?现实与理想之间依然有着距离⑩,对此种情形,孔子应该也是有所体悟,而又有着无法言语的感受。
而在陈、蔡绝粮之际,孔子引《诗》比况问弟子,其中子贡的对答很有深意: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史记·孔子世家》,第1931页)
子贡认为孔子理想高远,为当世之人不能接受与兼容,建议孔子作出些许让步,使得理想可以让众人接受,这样才能够将道付诸实现,然而孔子却对此言大感不悦。更深一层而论,“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正是孔子坚持道的理想所必然的遭遇,虽不免困顿挫折,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注疏·卫灵公》,第八页下)的信念是未曾衰减。子贡之言也显示他知道在乱世之中,就是存在理想行道与现实政治的扞格,孔子亦深知“道不行”的缘由,不免感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注疏·宪问》,第十四页上)。然而对子贡有所斥责,更可见夫子守道的信念,才能让司马迁“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产生斯文在兹的想望。
(三)学问与人格。
儒学在汉代逐渐兴盛,有着许多内外因素,但汉代儒者一反孔子命运,许多人入学致仕,甚至位居高位。战国的纷争,无法提供儒学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而汉代一统的政局,却让孔门思想传承数百年后,有跃上政治舞台的机会。这些汉代儒者以干王侯,借着神化孔子,加上素王的桂冠,使儒术有着加持的光芒。然而学者宗奉儒家信念,在一统政权之下,无有政治抉择的士人,当理念不合于统治者时,内心的郁闷可见一斑,如:“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史记·儒林列传》,第3123页)又《史记》载:“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第3128页)仅能遵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论语注疏·宪问》,第一页下)的夫子之教,可见在统一的帝国下,儒学是受到张扬,但士人的精神却受到打压。反之,孔子虽道之不行,依然可以坚持择木而栖,是时代因素,使得孔子的人格精神无法完全地传续下去。
另外,贱儒多而大儒寡是古今皆然,辕固生、董仲舒固然有战国处士之风,更多的汉儒却非真心欲广孔子之道,也无淑世的理想,与孔子的精神有所违离。《史记》载:
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2-2724页)
汉初叔孙通为高祖刘邦起朝仪,合以时务之变,以迎刘邦之意,让战后儒学有萌起的机会,但他所召共事者,见有赏赐便喜形于色,如同孔子所论“斗筲之人”(11)的鄙儒。武帝之时的公孙弘以儒术致卿相,公孙弘起于布衣,卒为朝廷三公,他成功的因素除了“遇时”之外,更重要的是:“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0页)显得曲学阿世的样貌,使得“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第3118页)。当然汉儒并非皆如此模样,只因环境已是大一统的帝制时代,外在政治的现实,造成面谀者众,无怪乎司马迁会引《诗》赞颂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所以《世家》叙写孔子的政治挫败与行道坚持,论赞予以高度称颂,正代表着司马迁对于孔子的人格有着无限的追思。
四、伤怀的超越
太史公叙写孔子的失败,也论赞孔子的伟大,失败与伟大看似相歧,实则由失败中见其伟大。另一个角度而论,更是司马迁试图贴近孔子的心灵,即便《孔子世家》的记载有疏漏错误之处,但却真实呈现孔子的人格(12),同时也联结到史家的书写之心。
(一)异代士君子的联结。
《孔子世家》的传文中,孔子是不遇而困顿,不仅政治上无所建树,晚年时,一些先进学生与儿子也早他逝去,孔子去世之前,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记·孔子世家》,第1944页)这时的孔子对世道已经不再有所期待。《十二诸侯年表》序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
孔子晚年深感道之不行,退而作《春秋》,期望以微言大义,使己道能够传之后世,所以《春秋》可以说是孔子最后付出的心血,传曰: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第1943-1944页)
孔子据鲁史修《春秋》,重点不在文字之增删,而是在于笔削之时的“义”之表达,如孟子所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注疏·离娄下》,第八页上)故《春秋》蕴含是非褒贬之精神,能够“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司马迁对于天下“莫能宗予”的孔子却论“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这不仅是礼敬孔子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对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当的共鸣,认为《春秋》包含“万物之聚散”为“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7、3298页),且有继《春秋》之志,才道出“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之语,称言《史记》乃是继《春秋》之作。当壶遂质疑司马迁作《史记》与《春秋》之间在时代背景上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对此,司马迁论道:
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9-3300页)
这段只是较为片面的说法,《史记》之作固然有整齐故事,使贤人志士功业不灭的用意,但以思想情感而论,其后遭遇的李陵之祸,让司马迁从《春秋》转移到著述者的身上: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30页)
所谓的“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云云并非史实,然太史公如此而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更显示他对于孔子怀道不行、天下莫宗的不遇有着更强烈感受,所以“述往事,思来者”之《史记》,不仅是《春秋》“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7、3299页)的另一种文化继承,更是“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的使命,太史公自道: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蓺之统纪于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0页)
说明作《孔子世家》乃因孔子为达王道之治而制仪法,并整理六艺,使学术生命不致中断,而司马迁“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9-3320页),即是对孔子事业的继承,可知异代得士君子不仅有志业的先后传承,在心灵上更有着贴近的感受。
(二)超越命运的精神。
孔子无法行道当代,但“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史记·刺客列传》,第2538页)是太史公所能够体悟,司马迁对孔子不仅在政治命运上的不遇感悟甚深,两者对自身遭遇所作出的回应,更是试图作出突破。《论语》: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注疏·微子》,第三页下—第四页上)
孔子与隐者都知道现下世衰道微,但如何面对却是两者不同生命情调与抉择,所以当隐者不愿与孔子交谈,所谓的“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正是展现一种坚毅的心志,虽然问津未果,孔子也很清楚真正通往大道的渡津之处,是遍寻不着,所以《论语》又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注疏·宪问》,第十五页上)“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可作为孔子一往无悔精神的最佳注脚。
坚持理想,却无法避免现实的困境,当困厄于陈、蔡之间,孔子对子路、子贡、颜回问了同样的问题,唯有颜回深得孔子之意:
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第1932页)
颜回所论,正是弘道者在现实世界的挫败中,对于自我信念的升华与超越,使得生命价值不随世浮沉,更能够坚定行道之心,所以孔子说:“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因此,孔子虽然一生积极追求,在心中却有“择木之鸟”①的情绪,也为司马迁所称道。晚年归鲁之后,“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也让孔子专注在教育后进弟子与著述《春秋》,反而“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成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的至圣,生命化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断地灌溉后代的心灵。
司马迁身遭刑戮,将存活的信仰系之于《史记》的著作,无论世道湛暗,司马迁都希望以史笔“述往事”,让贤人志士“不令已失时”,如同孔子著述教育以传己道,太史公希冀透过对史事的斧钺,即便“虽万被戮,岂有悔哉!”[5]让真正的世道价值传之后世。对于孔子,太史公是心灵贴合,同样的,面对自身命运,亦秉持自我的理念,在困顿之际,可以作出对生命的超越,绽放价值的光芒。
五、结语
太史公作《孔子世家》点出圣人与常人相同,没有所谓的遥不可及的圣人神话,传文记载夫子一生行道的艰辛与困顿,这种挫败来自战乱的人间,价值崩落的社会,所以孔子周游列国,除了国君的不能行道,更有着孔子对自我理念的坚持与不退让,进而导致不遇的必然。太史公以孔子政治上的屡屡挫败,衬托出其对于士人精神与理想的坚持;与此相对,在《孔子世家》的论赞之中,司马迁不仅吐露对孔子的企慕之情,表达对夫子的追思之外,更道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态度极为崇敬,在《史记》之中,处处可见“折中夫子”的评判。而这并非毫无来由,因为在政坛上有所成就的先进弟子,已稍损孔子之道,更遑论汉代因为政治上的压迫,守道的士人仅能“危行言逊”,更多数的儒生缘饰以儒术,以求功名的心态,相对比下,孔子坚持于道的信念,就显得可贵与可敬。所以,失败的叙事正映照出论赞的高度评价,而太史公曰的礼赞,也是因为孔子一生行道困顿而不堕其志,这两者都要归之于孔子一以贯之的人格。
面对孔子的遭遇,司马迁感到伤怀,因为“不合时宜”,所以孔子只能退而教育弟子,以及著述《春秋》。而在《史记》的著述中,对于这些“心有郁结”以及不遇的议题都极度关怀,这可以联结到司马迁为李陵执言获罪而左右莫救的世情感受,“莫己知”是孔子与太史公共同的呐喊,在志业行道上,二位异代士君子在此有了共鸣。同样的,面对困境与折难,孔子坚持理想,择木而栖,不因世俗而一改初衷,即便道已不行,仍退而论著,化育英才,让生命有了超越的价值;太史公亦感受世道的黑暗,面临人生的转折,忍辱负重而完成藏之名山的《史记》巨著,不仅不负父亲所托,也展现自己史笔斧正人间的意念,对横遭的不幸作出突破的努力,也成就继《春秋》的生命目标。
注释:
①[汉]司马迁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3319页。以下引文皆此版本,不再详注。
②见《史记·殷本纪》,第91页,与《史记·周本纪》,第111页。
③《史记·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见《史记·高祖本纪》,第341页。
④钱穆认为:“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见钱穆《孔子传》,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4页。以下引文皆此版本,不再详注。周先民也论之:“‘野合’即不合正规礼仪的结合,司马迁认为这一传闻可信,即组织进传记之中,其主观意图不大可能是‘欲神其事’,倒很可能意在强调其出身微贱。”见周先民《司马迁的史传文学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
⑤杜正胜以为:“一旦采邑家臣叛变,在国都的贵族必然联合起来,兴师动众,派兵敉平叛乱,‘国’军与采邑军兵戎相见,受害的还是人民。”参见杜正胜《流浪者之歌》,收录于杜正胜《古典与现实之间》,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第110页。以下引文皆此版本,不再详注。
⑥王健文认为:“公之鱼所沮之事,是后世儒者虚构出来的‘孔子神话’。齐景公欲用孔子,为晏婴所沮;楚昭王欲用孔子,为令尹子西所沮;就是同样的‘神话’主题的反复。孔子的一生,恐怕‘莫己知’才是真正的主调,而不是‘知’而后受‘沮’。”见王健文《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第32页。以下引文皆此版本,不再详注。
⑦[魏]何晏注《论语注疏·季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四页上—第四页下。以下引文皆此版本,不再详注。
⑧传载:“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从这段纪录,虽然刘邦仅仅称善而未依其实施治国之方,但基本上并未排斥六艺。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2699页。又太史公曰:“叔孙通稀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6页。
⑨[汉]赵岐注《孟子注疏·万章下》,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2页上—第2页下。以下引文皆此版本,不再详注。
⑩王健文对此论曰:“当冉有说‘不足’时,他的意思是指自己的能力不足呢?还是对孔子之道在现实世界中已没有实践的条件的委婉说法呢?”见《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第95页。
(11)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见《论语注疏·子路》,第七页下—第八页上。
(12)杜正胜认为,崔述《洙泗考信录》与钱穆《孔子传》虽然考证孔子事迹极为精详,但离孔子的心灵世界还是很远,远不如考订孔子事迹极为粗疏的司马迁,能够体会到孔子的心境。见《古典与现实之间》,第89页。
(13)卫孔文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见《史记·孔子世家》,第19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