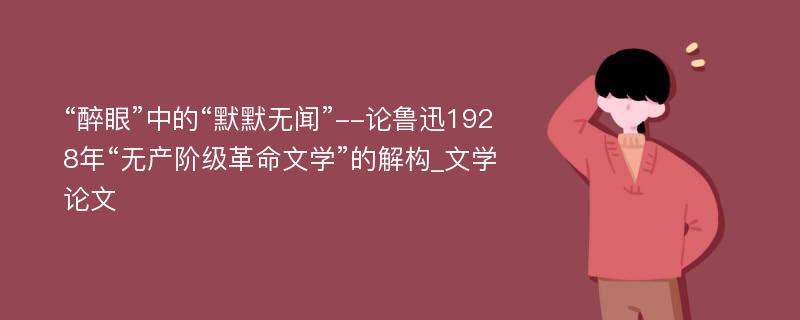
“醉眼”中的“朦胧”——论鲁迅对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醉眼论文,朦胧论文,无产阶级革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杂文书写所展示的是此在生存论的视野,即从自身生存将其直面到的世界打开,其中贯穿着一种日益深入的生存之思;如此的生存论视野亦是历史一时间性的,基于自身存在境域而绽露出历史性民族的演进历程,乃是一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鲜活的此在生存史。这样,在鲁迅不同的生存时段即表现出对不同历史内涵的把捉,不同存在之思重心的置放。“五四”以后,鲁迅深感“周围的空气太寒冽”,因将其论断为“君政复古时代”;①1927年在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一段静观默察之后,他断言革命的策源地也可蜕化为反革命的策源地,而血腥的“清党运动”则更使鲁迅看清了这场革命的本质,从而预言了一种新的专制统治模式——“以党治国”——的降临。②那么,从1928年始,鲁迅在上海际遇了另一种政党政治,即无产阶级革命及作为其理论表述的“革命文学”,从此,展示了鲁迅对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及其文学思潮长达近十年的观察思考,面对新的生存提问,他以最后的生命做出了回应。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于1928年的上海,在此之前,鲁迅对这一文学思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几乎没有什么了解。鲁迅曾在追忆1927年“清党运动”的《怎么写——夜记之一》中谈及,当时有分属共产党和国民党阵营的两个刊物《这样做》和《做什么》,都声称因他的“南来”而“先后创办”。为什么这么生死相对的刊物都要说因他来而创办呢?固然是想借助他的声望,然而更证明了鲁迅对这场革命所持的中间立场,他自嘲为“因为我新来而且灰色”③。所谓“灰色”,介于红白两色之间也;也就是说,他既没有投到青天白日旗下去,也没有想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在写于当时的沉思之作《答有恒先生》中,他自幸“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有人想以他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上做过文章来证成他是共产党,但被推翻了,因那时陈独秀还未讲共产。是“亲共派”吗?也不是,事变后他并没有投到“反革命”的据点汉口去。这些皆表明鲁迅当时所持的中间立场,他坚执的仍是“五四”以来的“思想革命”,即针对整个社会、面向民族生存观念的革命,这与国民革命抑或共产革命都是相冲突的。鲁迅甚至认为,后两者只可以当作“废话”存留,当时作为国民党喉舌的吴稚晖不也奉行一种主义么,但要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而共产党实行的主义也要等到二十年之后,“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社会的闲情逸致”,“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④这即是鲁迅1927年前后的思想状况,尽管对这场空前的血腥杀戮深恶痛绝,斥之为“先天性的遗传”的复活,极度同情被杀戮的青年,但确实对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缺乏了解。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上海的勃兴却是以鲁迅作为革命对象的。后期创造社的冯乃超首起讨伐,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以极度嘲讽的笔墨写道:“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⑤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称鲁迅等的创作“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呼吁用“十万两无烟火药”将他们的“乌烟瘴气”炸开。⑥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以郭沫若、成仿吾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者,继三个“闲暇”之后称鲁迅等的创作为“趣味文学”,“趣味文学”即是“文学的法西谛主义”。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之时,“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因而声色俱厉地质问“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我们的时代’,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⑦无异是说,鲁迅是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代表。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宣告了鲁迅及其文学的终结与死亡,鲁迅以阿Q形象为代表的创作“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我们早就应该把阿Q埋葬起来!我们是永不需要阿Q时代了!”因而摆在鲁迅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就死亡,要就新生。”鲁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若不彻底悔悟,转换新的方向,他结果仍旧只有死亡”。⑧杜荃(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说得更为刻毒,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⑨。等等。
这就是1928年鲁迅在上海所遭遇到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作为回敬,鲁迅引成仿吾的“三个有闲”将这时期的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虽然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⑩,但事实却并非这样,自后来的50年代以至80年代,这样的“大批判”或“口诛笔伐”曾一再演历,这或许是当时的鲁迅所始料未及的,也许到后来才明了这一点。《三闲集》的主体内容即是对如此“围剿”的一种回应,亦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次思考,对呈现于鲁迅生存的新的历史提问的首度沉思。
《“醉眼”中的朦胧》是一篇标志性作品,标志着鲁迅的生存之思朝向了一个新的境域。“醉眼”借冯乃超的嘲讽之语“醉眼陶然”以自况,表达的正是基于自身生存的观看。“醉”与“醒”相对,虽说是醉眼,其实却看得格外真切,乃是最清醒的看,似乎仅用“醉眼”就把对象看得一清二楚了。因而在此反讽中,包含一种甚深的解构。从“醉眼”所看到的即是“朦胧”。鲁迅将192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现象表述为“朦胧”,朦胧的意义显然是多面的:不清晰、令人质疑、不确定性、多样性,等等。正是透过对朦胧现象的多面观看,鲁迅不仅表达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深度质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它,并在解构中包含了对朦胧中所潜在的本质的揭示,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的预见,显示了鲁迅观看的历史深刻性。
朦胧导源于就近生存:“旧历和新历的今年(1928)”为什么“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不仅各种期刊纷纷面世,且“显出拼命的挣扎和突变”来呢?在鲁迅看来却是其来有自,来自对1927年大革命中赢得权力的官僚和军阀的不同的爱憎:对其示爱者,“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者,则显“笑眯眯”的脸色,但“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因而“留着一点朦胧”,乃是知识追逐权力的起始阶段;而“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者,欲“走向大众去的”,即使笔下“雄赳赳的,对大家显英雄”脸色,但他们不久前亦曾追随新军阀的指挥刀,使人难以忘怀,“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露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这是鲁迅对当时文学现象在上海的突然勃发的整体观看,虽然令人颇感困惑,但隐含的其实是不同的中国知识者追逐权利的本性。
鲁迅将思考投向了“朦胧”的后一种,即“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者。鲁迅认为,处在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是不免带些朦胧的,但关键在革命者必须不怕批判自己,有正视黑暗的勇气。倘若面对中国“目前的情状”,“连他的‘剥出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这样的革命者怎么能不令人感到朦胧(疑惑)呢?鲁迅在此直指高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旗的创造社,他们先前曾一再宣称“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与任何政治团体无任何关系”;后又投身国民革命纷纷南下,与政治合二为一了;今年复又突然倡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投向了另一种政治。顷刻之间,数度变异,这是否太过于善变了呢?其“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曾以守护“艺术之宫”为职掌;而今却要去“获得大众”,并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这“飞跃”是否又太突兀了呢?鲁迅从中看到的“消息”实在是中国知识者的“两副面孔”,用对方的理论来表述则是:“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而这“向……去”乃是至为关键的,是中国知识者最重要的人生选择,鲁迅看得十分清楚:“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者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但问题在于,“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鲁迅深度质疑他们骨子里的动机仍然是知识对一种新兴权力的追逐,与前一种“朦胧”是并无本质区别的。
由此,鲁迅从根本上质疑他们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据说,“无产阶级文学”并“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就是’”。这无异是说,无产阶级意识决定无产阶级的存在,亦因此决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但这与鲁迅所坚执的存在之思是恰相反对的。我们知道,鲁迅在论及书写“沉默的国人灵魂”阿Q时曾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11)。鲁迅认为他与他的书写对象“阿Q”之间是存在隔膜的,他只能“孤寂地姑且”将之写出。当论及“平民文学”时鲁迅一再强调:“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12)因此鲁迅断定:“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3)实际上,鲁迅所执守的正是唯物辩证法最基础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但亦与其不同,乃是此在存在之间(主体间性)的差异,本己生存与他者(工人农民)生存之间确乎存在差异,且是一种源自民族—历史生存处境的差异,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鲁迅就一再感叹他与“国人魂灵”之间的这种生存隔膜的难以逾越,甚至都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却宣称一经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就摇身一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上,从他们“翻云覆雨”的自身演历来看,他们是否属一个“革命人”尚值得怀疑,更遑论其“无产阶级”的身份了,充其量只是一种新的表演姿态罢了。
鲁迅更进一层看到这种文学上的新的表演姿态所潜在的生存实质,乃是中国智识者的生存奥秘:“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说穿了,这不就是对似乎可以预见的新的权力的追逐吗?自己本身的存在可以不发生任何变化,关键在于首先占据某种话语权,以新的面目出现,这样便可以号令天下,使反对者望风披靡。这样的“革命”(飞跃)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实确实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号不就成了倡导者们排斥、抨击、讨伐他人的锐利武器吗?从一开始鲁迅就从倡导者们的“英雄”脸色上感觉到,所有的人(“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他们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实绩”做了全面的批判否定,当时的主要作家叶圣陶、郁达夫、周作人、鲁迅、茅盾,甚至包括同样倡导革命文学的蒋光慈等都在批判扫荡之列,尤其对被称为“有闲阶级”的“语丝派”的“趣味文学”,更要用“十万两无烟火药”将其炸开,因为有闲即有钱,这类文学定属资产阶级无疑。鲁迅创作不就被宣判为已经“死亡”与“终结”了吗?鲁迅的阶级属性不就由资产阶级而晋级为“封建余孽”的“二重反革命”吗?质问作家的阶级属性不就成了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吗?利剑所到之处,敌手无不登时毙命。自己的阶级身份(自我批判)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通过“否定之否定”已经“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对他人却丝毫不会放过,就鲁迅而言,先是要将他“挤进”资产阶级去,后来又说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似乎又给人以一线希望;但却还要询问你参加的“动机”,是否系“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这就令人完全绝望了。这正是中国知识者一旦权力(“旗号”)在手便即刻施之敌对的生存本性。对这样一种唯独自己得了革命的真传,动辄斥他人为反革命的手段,鲁迅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认为“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乃是中国式流氓历史变迁的现代表现。
毋庸置疑,权力在此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时尚只是一种“旗号”,但旗号或许有转变为真正的权力的一天。这正是“朦胧”的不确定性的最终确定性,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即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艺术的武器”不过是目前的权宜之计,“因为那边(新军阀和官僚)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他们所期待的,是“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这就“保障了最后的胜利”。鲁迅预言,倘若“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这正是鲁迅在《失掉的好地狱》中对以“人”的名义建立的那个更加严厉的“新地狱”的再次预见,所执守的仍然是“历史同一性的现代轮回”的生存观念,只是这次并非体现在“有雄辩和辣手”者身上,而是从革命文学家“英雄”的气势上所看到的。惟此,鲁迅断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无论“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的革命文学家,还是“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他们都是不会相信手里的“艺术的武器”的,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14)历史确乎证实了鲁迅的预见。
继此,鲁迅那一时期的杂文多是从“‘醉眼’中的‘朦胧’”所展开的。既然朦胧源于不敢正视当时的黑暗现实,所以“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15)。在鲁迅看来,当时的现实并非革命文学家所鼓吹的那样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仍处铁血专制之中,即便经历了民元革命和国民革命,黑暗程度也不曾稍减,只是不断变换了旗号罢了。在《太平歌诀》中,鲁迅引述《申报》上的一段记事:南京近日发现谣传,谓总理(孙中山)墓行将工峻,欲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魂叫不去,再叫自承当。”鲁迅认为,此歌诀“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而革命文学家却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仍然是这样的市民,如此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16)小巧机灵的歌诀所戳破的是革命文学家畏惧黑暗、掩藏黑暗,欢迎喜鹊、憎厌枭鸣的卑劣心理。《铲共大观》中鲁迅更引《申报》上湖南共产党领袖郭亮“伏诛”悬首示众和三位女性被处决的场面,来说明新的专制杀戮的残酷和民众往观的盛况:“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无论谁的都有人看”。鲁迅以残酷的生存现实强有力地驳斥了钱杏邨那个“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的超时代的论断。倘若无视这一现实,“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17)
因此,在鲁迅看来,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革命文学”,只是一个心造的无抵抗的超时代的幻影,是要“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的。鲁迅对此做了尖锐的嘲讽,乡间有一个笑话,说两位近视眼要比视力,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天新挂的匾额。他们事先从漆匠处探得字句,但一个仅知大字,一个仅知小字,便又争执起来。质之于过路人,那人说:“匾还没有挂呢?”这无异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就是一块尚未挂起的匾额,“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18)在《路》中鲁迅说得更为直白:“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19)鲁迅从此所表述的,无异是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更遑论其“文学使者”了。鲁迅仅仅承认:“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20)但这是国外的情形,“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21),所挂出的仅仅是一块“招牌”,说的刻薄一点,甚至连“招牌”都尚未挂出。
虽然,鲁迅并非没有看到,1928年之际出现的革命文学家确乎有“一大串”,阵营也颇为壮观:“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蒋光慈拜帅的《太阳》,王独清领头的《我们》,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和《战线》;再加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22)但是,从如此壮观的阵营和众多的刊物是否就可以证明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生呢?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刊物或“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呢,还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他们都把鲁迅当作革命的对象“这口吻却大家大略一致的”。(23)更为奇怪的是,他们的论战却并不涉及是非,只在鲁迅的“态度”、“气量”、“年纪”等方面做文章。这不禁使鲁迅想到他先前与陈西滢、高长虹等的论战,如化名“弱水”的潘梓年明明与创造社同一阵线,却偏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来论是非,以示其公允,这与陈西滢的战法如出一辙:“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又一再攻击鲁迅的“老”与“不行”,而高长虹也确曾“指出我这一条大错处,此外还嘲笑我的生病”。更有甚者是将鲁迅与“五四”时期暮年景象的林琴南相类比,势欲将之置诸死地而后快。然而无论怎样花样翻新,鲁迅看到的只是中国文人排除异己的惯用手法,“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某某思想或主义往往被他们用来当作打倒、攻击他人的利器。因此,“无论是怎样炮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这种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方向正确——无产阶级方向)的创造社也在所不免的。”(24)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不过在新的旗号下以旧的手法向对手施行攻击罢了。
惟其如此,鲁迅敏锐看到,革命文学家们是善变的,他们才刚大张旗鼓地张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由于现实的压力,“两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广告,来吓唬别人了。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25)鲁迅甚至不无刻薄地说,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都藏身于“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除掉)了”(26)。鲁迅尤其将笔墨指向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帅之一的成仿吾,在这位“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点粉”:说他“做了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珰鲁迅’之后,……就又走在修善寺温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没有),并且在那边被尊为‘可尊敬的普罗塔利亚特作家’,‘从支那的劳动者农民所选出的他们的艺术家’了”(27)。鲁迅以尖锐的言辞解构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身份,伪饰一经剥去,他们实在与先前的文人并无什么两样。
因此,倘若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并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只是一个伪饰的身份,那么,怎么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生呢?鲁迅固然认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但这番话是鲁迅就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而言的,在一个连诸如此类的革命都并不存在的国度,怎么谈得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鲁迅断言:“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历来的论者,几乎都遗漏了鲁迅这后一句话,他们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存在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以此来论述革命与文艺的关系,认为革命文学倡导者只是未足够注重其文学的特质罢了。而鲁迅对此前提实在是否定的,“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应该“又作别论”。无异是说,探讨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仅仅在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国度才有可能,但中国不在其列,应该“又作别论”。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惟此,鲁迅进而解构了当时的所谓“革命文学”:“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28)如上面所引述的虽为报章记事的“太平歌诀”,是“虽有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恐怕也难有做到这么简明深切的了”(29);至于《铲共大观》中的那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长沙通信》,在鲁迅“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这百余字实在抵得上小说一大堆,何况又是事实。”(30)而革命文学家的创作呢?鲁迅引冯乃超独幕话剧结尾的警句为例:
野雉:我再也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31)
确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的。
鲁迅无异表述了文学生命的一个本质真理,文学家只有敢于面对现实黑暗,敢于“睁了眼看”,其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才会处在真的境域,也才会有真理的发生。惟其中国现实自民元革命以来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仍处铁血专制生存之中,民众依然是那样的民众,而人们偏要超越现实去倡导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其作品怎么可能成真,怎么可能具有生命力呢?其结果只能是一个“心造的无抵抗的超时代的幻影”,是要“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的;是要像自己用手提着自己的耳朵离开地球者一样地自欺欺人的。这一“自我提升的悖论”确乎击中“革命文学”的死穴,因为它造成了双重的遮蔽:不仅遮蔽了革命文学家的眼睛;而且遮蔽了文学本身。第一层遮蔽使革命文学家看不见当前的黑暗现实,沉溺于心造的“幻影”,坠入了纸战斗的“新梦”。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文学家其实并非“不愿”正视现实,而是心造的意识形态的“幻影”阻碍了他们,迫使他们“无法”或“不能”去正视现实,因为一旦直面现实,那个心造的“幻影”便会宣告破灭,这是由后来的事实所一再证明了的。而第二层遮蔽则使文学丧失了存在的根基,要么只能强行书写革命的“超时代的幻影”(所谓时代的“主旋律”),要么陷入“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的“瞒和骗”的境地。更有甚者,如此的遮蔽后来一再得到强化,主宰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文学书写的历史,使人们陷于“革命与文学”的两难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正是鲁迅深度解析“朦胧”的意义,他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肇始之际就看破了其中的隐秘,我们不能不说鲁迅具有预言家的眼力。
1929年鲁迅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是一篇关于“革命文学”的总结之作。鲁迅重申了先前的观点:“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鲁迅所指的“环境”即生存环境,有怎样的生存,便会有怎样的文学,而不是恰相反对。因此,“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唯其真正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发生,所以中国就不可能有相应的革命文学产生,而只是一种“舶来品”。“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所以鲁迅嘲讽说要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使者”,只能到“大屋子里”、“客店里”、“洋人家里”、“书铺子里”、“咖啡馆里”去寻。进一步言,决定生存环境的更是权力的政治,“政治先行,文艺后变”,中国的文艺总是依附于权力政治的,一切操持“艺术的武器”者所景仰期待的,都是“武器的艺术”的到来。然而这到来的“武器的艺术”(革命)究竟是什么呢?往往超出文学家们的“豫想”,使他们碰碎或破灭在理想的墙上。虽然,“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这之中有种种复杂情形:有仅仅憎恶旧社会而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者;有大呼改造社会而其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者;有寻求刺激者;且有“更下的”“旧式人物”,他们“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对此,是有历史作为见证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将他们的理想破碎了。这是第一种。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原是欢迎十月革命的,愿受革命风暴试炼的,但真实的革命一来,就将其空想击碎了,活不下去而自杀了。这是第二种。鲁迅以为中国眼下的革命文学家似乎是第三种甚至“更下”者。因为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眼下的中国不仅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存在,甚至连小资产阶级的文学都没有,不过一个“题目”或“旗号”罢了。鲁迅说:“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
既然中国的“革命文学”只是一个“题目”或一种“旗号”,那么其内容的悖谬是可以想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鲁迅清楚看到这些称其为“革命文学”的作品其实是全无内容的,王独清鼓吹广州暴动的诗志在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但“无其力和才”,因为他所书写的是从安全的租界里所遥望到的“革命”,自己毫无体验,怎么可能有其力和才呢?所以只是为电影的字幕或上海酱园的招牌所感动罢了。从《苦闷的象征》和苏联的旗帜上拼构起来的那把带铁锤的钢叉,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拙劣模仿,只能当作“革命文艺家”的徽章。也就是说它恰好成了革命文学家虚空本质的象征,倒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至于郭沫若的名作《一只手》,却实在“未免失得太巧”,鲁迅认为,“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止这一点”,为什么不是失去一只脚甚至一颗头呢?仅仅失去一只手而另一只还能与爱人握手,其实“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是颇有些中了才子+流氓的毒的。鲁迅从这些革命文学创作不仅看到其内容的虚空,真正的革命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而且看到了革命文学家的本真面目,他们骨子里仍然是“更下的”“旧式人物”,“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所谓革命或革命文学不过一种新的包裹罢了。
鉴此,鲁迅径直勾画出他们的形象:“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了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用以排斥扫荡他人的利器,他们藉此可从“艺术的武器”走向“武器的艺术”。但其面目却不幸被鲁迅戳破了:“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32)只不过此时他们所奉的并非皇上的圣旨,而是“无产阶级”的号令。成仿吾不就是一位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出的“可尊敬的普罗塔利亚特作家”吗?(尽管鲁迅质疑“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他对鲁迅之类作家不就进行了这样的“奉旨申斥”吗?
这就是鲁迅在中国所遭遇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笔尖的“围剿”,他从“醉眼”中所看到的“朦胧”,对这类革命之应“又作别论”的深度质疑,于质疑中对其不确定性的最终确定性的论断,乃是中国智识阶级对似乎到来的新的权力的追逐。
由此可见,身处1928年的鲁迅的思想并没有实质性变化,所执守的仍然是“历史同一性的现代轮回”的生存论思想,他曾用之于“君政复古时代”,亦用之于“国民革命”时代,只不过这次却是用之于以极端的革命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出现的又一新的时代,并以此解构了新的“旗号”包裹下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其实仍然是中国智识阶级对新的权力的占有与追逐,正所谓“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当然,其间的不同之处在于,鲁迅并未否定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也没有否定作为其“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出现,仅仅以为在当下中国应“又作别论”。这就潜在着一种生存的可能性,鲁迅可能接近或接纳这一革命,事实上鲁迅的生存思考点——书写“沉默的”国人魂灵——是十分接近这一革命的,而新的严酷的专制政治的宰制也迫使他靠近这一革命,这就有可能使鲁迅与他曾严厉地予以解构的“革命文学家”们结成某种暂时的统一战线,以对抗新的专制。实际上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虽然对革命文学家与革命文学做了严厉的解构,但末尾的结语却是颇为温和的,认为“倘要比较地明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倘要打破创造社批评家所故弄玄虚的“这包围的圈子”,便是多译多看几本“较为切实可靠”的“关于新兴文学”(33)论著。鲁迅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也因此预示着后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出现。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鲁迅完全转变了立场,放弃了历来所执守的历史同一性的现代轮回的生存论思想呢?放弃了他对中国智识阶级追逐权力的本质的质疑与解构呢?事实并非如此。面对一种新的权力,一种新的权势话语,鲁迅正处在观看思考的途中,而后者也正处形成之中。存在之思的预见只能相应于生存而生。
注释:
①参见拙作《历史同一性的现代轮回:君政复古时代——鲁迅杂文研究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9期。
②参见拙作《历史同一性的现代轮回:革命与反革命——鲁迅杂文研究之二》,《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③《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④《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57页。
⑤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转引自《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⑥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转引自《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20页。
⑦李初梨:《怎样的建设革命文学》,1928年2月15日《文化批判》第2号,转引自《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33-40页。
⑧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57-65页。
⑨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126页。
⑩《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4-6页。
(11)《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2页。
(12)《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22页。
(13)《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544页。
(14)以上引文见《“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第61-66页。
(15)(20)(28)(31)《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3、82-83、84、84页。
(16)(29)《三闲集·太平歌诀》,《鲁迅全集》第4卷,第103、103页。
(17)(30)《三闲集·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06、106页。
(18)《三闲集·扁》,《鲁迅全集》第4卷,第87页。
(19)《三闲集·路》,《鲁迅全集》第4卷,第89页。
(21)(22)(25)(27)《三闲集·文坛的掌故》,《鲁迅全集》第4卷,第122、122、122-123、123页。
(23)(26)《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98、98页。
(24)《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全集》第4卷,第109-112页。
(32)以上引文见《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3-136页。
(33)《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7页。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革命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