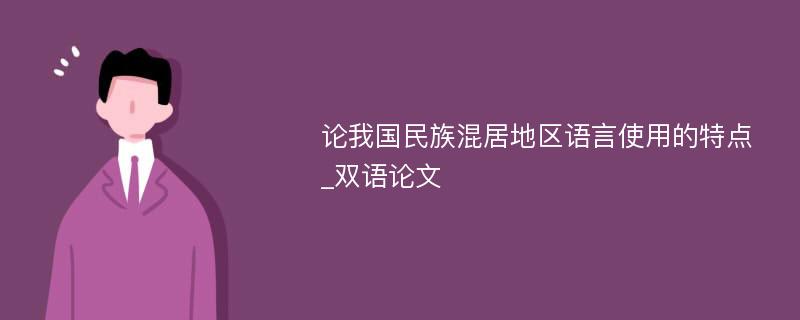
论我国民族杂居区的语言使用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语言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在一个特定的民族聚居区内,常常杂居或聚居着其他民族。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杂居中有聚居、聚居中有杂居的分布特点,民族杂居区和聚居区只能是相对的概念。在一个特定范围内,不同民族交错聚居或相互杂处,形成民族杂居区,而在这同一范围的不同区域里,不同民族又多以单一民族或单一民族为主的聚居形式分布。因此,无论是民族的杂居还是聚居都与所指地域涵盖的范围有关:地域涵盖范围越大,民族分布的杂居特点就越突出,反之亦然。我们只能一般地认为,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同一个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是民族聚居区,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交错聚居的是民族杂居区。由于杂居区和聚居区民族分布特点上的差异,其语言使用特点自然有所不同。
一 双语现象的普遍性和双语使用的不对等性
我国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有的民族内部不同群体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在一个特定的民族杂居区,不同民族的杂居为各民族兼通语言提供了条件,而杂居区内单一民族的小聚居又为不同民族保留自己的语言提供了方便。杂居区内各民族在使用本族语言的同时兼用其他民族语言,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双语或多语现象,因此,民族杂居区内的语言使用情况常常比民族聚居区更加复杂。由于民族杂居区往往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因此,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语言的兼用、转用现象不仅自古有之,而且较之民族聚居区更加普遍。
从我国民族分布的总体特点看,与西北、东北、华北“三北地区”相比,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杂居程度更高,因此,双语或多语现象也就更加普遍。西南地区的壮、彝、苗、布依等四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双语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6—1988年)已经占全国少数民族双语人口总数的65.4%,而“三北地区”的蒙古、朝鲜、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东乡、土族、达斡尔、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鄂温克、保安、裕固、塔塔尔、鄂伦春、满、赫哲等十九个少数民族的双语人口仅占全国少数民族双语总人口的13.6%。上述所列西南地区和“三北地区”的民族人口基数虽然不同,但从所比较的民族的双语人口比例看,仍然能够说明西南地区双语或多语现象更为普遍。从较小的民族杂居区看,双语或多语现象的普遍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县,各民族基本上都以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形式分布。从民族分布上看,全县所辖的三个镇十五个乡都是多民族杂居区。汉族是禄劝县人口最多的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69.73%, 交叉分布在全县各个乡镇,而且各个乡镇中人口最多的也是汉族。汉族不仅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彼此和睦相处,而且不同民族耕种的土地、管理的山林、经营的牧场相互交叉,这就为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依赖提供了条件,为不同民族互学语言尤其是少数民族学习和掌握汉语提供了有利条件。禄劝县人口最多的三个少数民族即彝族、苗族、傈僳族的分布状况也是大杂居小聚居。总的看来,禄劝县人口较多的民族都以典型的层级形式分布,即行政区划单位越大,包括的地域范围越广,民族分布就越复杂;地域范围最小的村民委员会和自然村则以单一民族为主。这种分布特点形成了境内少数民族在完整地保留本族语言的同时普遍兼用汉语即“民—汉型”双语人比较普遍的语言使用格局。
在民族杂居区复杂的语言使用“场”中,民族人口和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诸如语言的法律地位、文字的使用情况、传媒用语、学校教学用语等方面的差别,导致了不同语言群体在双语使用的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等性。也就是说,民族杂居区内普遍存在的双语或多语现象对不同的语言群体而言并不是对等的,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非相互的双语或多语现象。比如在多民族杂居的新疆伊宁市,人口较少的锡伯族、俄罗斯族、蒙古族、塔塔尔族居民在全部或部分人使用本族语言的同时,普遍兼通汉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而人口较多的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居民却几乎不通或很少有人兼通上述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民族人口和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语言群体双语或多语使用方向上的不对等性,是造成民族杂居区语言使用具有层次性特点的重要因素。
二 语言使用的层次性和功能互补性
与民族杂居区双语或多语现象的普遍性和语言使用的不对等性密切相关的是不同语言在使用上的层次性。民族杂居区语言使用的层次性也主要是由于民族人口和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上的差异造成的。
在民族杂居区,不同民族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各民族的人口数量有多有少,各民族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有强有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使用层次上的差异。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汉语是全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际语。在民族杂居区,汉族人口也常常不在少数,加之汉语强势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几乎所有的民族杂居区,以汉语作为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用语或地区交际语也就成了不同民族的必然选择。从语言功能上看,杂居区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某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多,社会文化功能强,这种语言就可能成为该地区的区域优势语;一种情况是当地的各种少数民族语言都不具备使用人数和社会文化功能上的优势,难以形成区域优势语。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杂居区各民族语言的功能大致有3个层次:(1)族际通用语;(2)区域优势语;(3)族内交际语。
在不同类型的民族杂居区,由于地域范围的大小、民族分布特点、人口比例、文化发展等条件的不同,各民族语言的功能、不同语言群体互通语言的程度不尽相同,因而语言使用的层次性也有一定差异。我们分别以比较典型的民族杂居县(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市(新疆伊宁市)和地区级行政区划单位(新疆哈密地区)为例,从是否形成区域优势语的角度,分析说明民族杂居区语言使用的层次性特点。
1.形成区域优势语的民族杂居区 由于某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和社会文化功能上的优势,形成了以这种语言为交际语的区域优势语,即在少数民族普遍兼通汉语的同时,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也多兼通这种优势语言。新疆伊宁市和哈密地区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新疆西北边陲的伊宁市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人口占多数的多民族杂居城市,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8%,其中维吾尔族占总人口的52%。伊宁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工厂、每一个机关,都是由不同民族成分的人组成的。长期以来,生活在这里的每个民族中都有不少人既掌握本族母语,又能熟练使用另外一两种甚至三四种、四五种民族语言,双语或多语现象非常普遍。伊宁市各民族语言使用的状况可分为4个层次:(1)族际通用语。汉族人口虽然只占伊宁市人口比例的第二位,但由于汉语不仅是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而且在伊宁市的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大部分商人和一部分普通群众中也是不同民族间最重要的交际用语,同时还是绝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语言,因此在伊宁市,汉语处于族际通用语的地位。( 2)区域优势语。维吾尔语是新疆主体民族使用的语言,伊宁市的维吾尔族人口又占各民族人口之首,维吾尔语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比较通用,甚至在一些场合或一定交际对象中比汉语更为通用,因此,维吾尔语是伊宁市的区域优势语。(3)亚区域优势语。 哈萨克语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主体民族哈萨克族的民族语言,也是自治州内的法定语言,各类行政公文等均用汉、哈两种文字。然而,在州府所在地伊宁市,由于哈萨克族人口较少,而且多是近几十年从州内各地迁来的,因此,哈萨克语在伊宁市处于亚区域优势语的地位。(4 )族内及家庭交际语。伊宁市使用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像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内部差异不大,族内交际语一般都是本族语;而人口较少的民族如锡伯、俄罗斯、蒙古、塔塔尔族或在族内、家庭中使用本族语言,或本族语言只保留在部分人群中,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而且很少为其他民族的人兼用。
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也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杂居区。汉族占总人口的65.66%,维吾尔族占20.70%,哈萨克族占9.54%,其他25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1%。哈密自古以来就是民族杂居区, 语言使用情况复杂多样,双语现象不仅自古有之,而且相当普遍。境内各民族语言使用状况可分为3个层次:(1)地区通用语。汉语既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也是新疆各民族的族际交际语,加之哈密地区汉族人口占多数,因此,汉语是哈密地区的通用语。维吾尔语既是新疆主体民族维吾尔族的母语,也是自治区内的法定语言,各类行政公文等均用汉、维两种文字,加之维吾尔族分布在哈密地区的各县、市以及绝大多数乡、镇,因此,维吾尔语也是全地区的通用语。哈密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或兼通汉语,或兼通维吾尔语。(2)县、乡级区域优势语。 哈密地区有一个自治县即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三个民族乡即哈密市乌拉台、德外里都如克、伊吾县前山哈萨克民族乡。在哈萨克族自治地方,哈萨克语文是法定语文,行政公文等使用汉、哈两种文字,加之自治县和民族乡中的哈萨克族人口占相当比例,因此,哈萨克语是这些地方的区域优势语。(3)乡、村(行政村、自然村)或族内及家庭交际语。聚居在部分乡、村的人口较少的民族如蒙古族,除在乡、村或本族及家庭内部使用本族语外,普遍兼通更大范围内通用的民族语,有的甚至兼通三四种民族语。
2.没有形成区域优势语的民族杂居区 在一些民族杂居区,即使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在当地的人口比例中也不占多数,或由于各少数民族之间人口比例的悬殊不大,因此,各种少数民族语言都很难成为当地各民族的族际交际语或通用语,即很难形成区域优势语。在这类杂居区,由于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主要分布片区,少数民族语言除主要通行于本族聚居的村寨之外,还能形成少数民族的片区交际语。广西龙胜县和甘肃肃南县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位于广西东北部的龙胜县境内居住着侗、汉、壮、瑶、苗五个世居民族,各民族之间的人口比例悬殊不大,其中侗族43707人(占26.20%),汉族38665人(占23.17%),壮族33308人(占19.96%) ,瑶族27586人(占16.53%),苗族23534人(占14.11%)。境内民族成分虽然不算多,语言使用情况却非常复杂,不仅各民族语言使用特点不同,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语言使用特点有别,而且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不同地域的人语言使用特点也不尽相同。境内各民族语言使用的状况可分为4个层次:(1)族际通用语。龙胜境内各民族的族际通用语是汉语西南官话桂柳片区的桂林话。桂林话不仅是龙胜境内操不同土语的汉族族内交际语,在四个主要少数民族中,除本民族聚居区内的极个别老年人和一部分学龄前儿童之外,几乎全民兼通桂林话,桂林话也是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共同交际语。也就是说,桂林话是龙胜境内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语言功能最强的族际通用语。 (2)族内交际语。桂林话不仅是龙胜各民族的族际通用语,也是以不同汉语土语为母语的汉族之间的族内交际语。瑶族内部语言差异大,不同支系、不同地区使用不同语言变体的瑶族也都以桂林话作为族内交际语。苗族内部不同地区的人分别以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变体和桂林话为内部交际语,而使用不同语言变体的苗族之间则以桂林话为族内交际语。也就是说,在汉族、瑶族、苗族内部,操不同语言变体的人之间也都以桂林话作为族内交际语。侗族和壮族本民族内部交际主要使用本族语和桂林话。(3)片区交际语。龙胜虽然是多民族杂居区, 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主要分布片区。在各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片区,除通用桂林话之外,另有不同民族的片区交际语。比如北部的侗语,南部和西部的壮语,福平包山麓四周以及北部、南部的红瑶话(桂北平话)、勉语、巴哼话、优诺话,东北部苗族使用的特殊汉语方言变体等等。因此,生活在某一少数民族相对聚居地区的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也多兼通这种片区交际语。(4)村寨及家庭内部交际语。龙胜境内的绝大部分自然村寨、 村民小组以姓氏或家族聚族而居,或单一民族聚居,村寨和家庭内部以本族语言或本地方言土语为交际语,对外则视交际对象的不同,或使用片区交际语、族内交际语,或使用族际通用语。
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的肃南县是由九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杂居区,汉族占总人口的47.84%, 两个主要少数民族即裕固族(占总人口的24.85%)和藏族(23.64%)占全县总人口的48.49%。 境内各民族基本呈插花分布,其中汉族分布在全县各个区、乡,裕固族和藏族分别有自己比较聚居的区、乡。 境内各民族语言使用的状况主要有3种类型:( 1 )以一个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样的区域里,杂居着少量其他民族成员,聚居民族的人口占绝对多数,本民族语言得以保留,形成“民—汉”双语区。比如明花区明海乡、莲花乡是典型的西部裕固语和汉语双语区;康乐区杨哥乡、红石窝乡是典型的东部裕固语和汉语双语区;皇城区泱翔乡,祁丰区祁青、祁文乡是典型的藏语和汉语双语区;康乐区白银蒙古族乡东牛毛村、西牛毛村是典型的蒙古语和汉语双语区。(2)使用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聚居区。在这样的区域里,裕固族人口虽占多数,但因内部分别使用两种差别较大的裕固语,一部分使用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通东部裕固语,一部分使用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通西部裕固语,加之裕固族都兼通汉语,从而形成多语区。如国营大岔牧场、大河区韭菜沟乡、皇城区马营乡等地属于这种类型。(3)多民族杂居区。在这样的区域里,民族成分复杂, 不同民族通婚家庭比较普遍,少数民族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族际交际语,只能选择汉语。久而久之,多数人不懂本族语,转用汉语,这类地区也就随之成为汉语单语区。比如红湾寺镇、皇城区铧尖乡、马蹄区大泉沟乡等地属于这种类型。可见,肃南县各民族的分布类型与不同民族的语言使用状况有明显的对应规律:第一种类型即以一个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是“民—汉”双语区;第二种类型即使用东、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聚居区一般是“民—汉”多语区;第三种类型即多民族杂居区一般是汉语单语区。与此同时可以看出,汉语既是肃南县各民族的族际通用语,也是各个民族内部的族内交际语之一,同时还是杂居区少数民族的惟一用语;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片区交际语和家庭内部的交际语之一。
无论在哪种类型的民族杂居区中,处于不同层次的语言在其功能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总的来说,处在第一个层次的语言,社会功能最强,使用人数包括兼用这种语言的人数最多,使用场合也最普遍,依此类推。相反,只是处于第一个层次的人语库最为简单,掌握或使用双语、多语的现象最不普遍;处于第三或第四个层次的人,语库最为复杂,掌握或使用双语、多语的现象最为普遍。也就是说在复杂的语言使用“场”中,语言功能的层次越低,以这种语言为母语或掌握了这种语言的人,语库最为复杂,语言使用能力最强,反之亦然。
汉语不仅是民族杂居区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用语,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汉语文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民族杂居区,与少数民族语言一样,汉语的使用也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在汉语不能发挥作用或汉语的交际功能不如少数民族语言的层面,比如在本民族之间和家庭内部,少数民族语言仍然是主要交际工具;在一些地区,少数民族语言还处于片区交际语甚至区域优势语的地位。除上文列举的例证之外,还可以更大的民族杂居区贵州省为例。在贵州省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3 个民族自治州、11个自治县、254个民族乡中,仍有800多万人以本族语为第一交际语,其中不懂汉语的就占一半,约有400多万人, 半通汉语的300多万人,本族语和汉语双语人只有100多万。因此,在民族杂居区,少数民族的本族语言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定范围内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家庭内部发挥着汉语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民族杂居区,由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各有自己的功能,它们在不同层次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因此,在对少数民族语文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在制定民族语文政策和教育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的功能互补性。
三 语言使用的类型转化
民族杂居区双语或多语现象的普遍性是各民族在彼此杂处、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因此,双语或多语现象不仅具有较长的历史,而且随着社会环境、民族关系、民族人口比例、不同民族间的通婚、语言态度等因素的变化,双语或多语的类型也会发生变化。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人口流动量的不断增加,汉语文教育的不断普及,少数民族掌握汉语的程度普遍提高,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从而导致了语言使用类型的转化。
从总体上看,民族杂居区双语类型的转化主要有3 种表现形式:(1)“民—民型”双语人向“民—汉型”双语人转化。 比如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的蒙古族,哈密市的哈萨克族,伊宁市的各少数民族,甘肃肃南县的蒙古族,广西龙胜县的少数民族,云南禄劝县的少数民族,几十年前的双语人多是本族语和当地少数民族优势语或片区交际语的双语人;几十年后的今天,本族语和汉语双语人迅速增加。(2 )“民—汉型”双语人向“汉—民型”双语人转化。比如肃南县的裕固族,河西走廊及其周边地区的一部分藏族,四川攀枝花市盐边县的彝族、苗族,几十年前的双语人多是本族语和汉语双语人;几十年后的今天,汉语和本族语双语人迅速增加。也就是说,在少数民族双语人中,不少人的第一语言即最常用的语言不是本族语,而是汉语。(3)在青少年中, 出现了“汉—民型”双语人向汉语单语人(或是汉语方言,或是普通话)、汉语双语码人(汉语方言与普通话)转化的趋势。这种转化趋势在民族杂居区的城镇地区更为显著。
具体而言,由于民族杂居区民族分布特点上的差异,语言使用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在通行某种少数民族优势语的民族杂居区,优势语是本族母语的少数民族多是“民—汉型”双语人,比如新疆乌鲁木齐市、伊宁市的维吾尔族双语人;而优势语不是本族母语的其他少数民族则多是本族母语和当地少数民族优势语的“民—民型”双语人,比如新疆伊犁地区的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多是本族母语和哈萨克语双语人,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前山哈萨克民族乡的哈萨克族多是本族母语和维吾尔语双语人。在这种类型的民族杂居区里,无论双语人的语库特点以及语言使用能力如何,近几十年来都出现了双语类型转化的趋势,其中本族语是当地少数民族优势语的“民—汉型”双语人有向“汉—民型”双语人转化的趋势;而本族语不是当地少数民族优势语的“民—民型”双语人有向“民—汉型”双语人转化的趋势。
在没有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能够成为区域优势语的民族杂居区,由于居住环境比如是城镇还是农村、交通便利与否等外在条件以及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语言态度等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差异,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民—汉型”和“汉—民型”两种类型的双语人。在这样的区域里,农村、交通不便地区以及文化程度较低、中老年语言人一般以“民—汉型”双语人为主;而城镇、交通便利地区以及文化程度较高、青少年语言人一般以“汉—民型”双语人为主。在这种类型的民族杂居区里,无论双语人的语库特点以及语言使用能力如何,近几十年来,也出现了双语类型的转化趋势,其中“民—汉型”双语人有向“汉—民型”双语人转化的趋势;而“汉—民型”双语人有向“汉语方言—普通话”单语双语码人转化的趋势。一些地方的部分青少年则成为“普通话—汉语方言”单语双语码人。广西龙胜县和甘肃肃南县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特点及其类型转化特点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近几十年来,龙胜和肃南境内各民族在语言使用方面出现了这样几个趋势:(1)双语、多语人的数量呈下降趋势;(2)部分双语人的语库特点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去的“民—民型”双语转变为“民—汉型”双语;(3)在部分“民—汉型”双语区内, 语言使用特点出现了年龄上的分化。解放前,青少年和中老年在语言使用上没有明显差别。解放后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汉语文教育的普及,年轻一代文化水平的提高,本族语水平逐渐降低。有些年轻人虽能用本族语交际,但仅停留在一般的日常用语上,有些人则只能听懂本族语,不会说。于是,中老年之间交际一般使用本族语,青少年之间交际一般使用汉语。与之相应的是,中老年和青少年之间的交际,或是转用汉语,这种现象多出现在社交场合;或是中老年一方使用本族语,青少年一方使用汉语,这种现象多出现在家庭内部,从而出现了家庭“半双语”交际现象。
于是,龙胜和肃南各少数民族就面临着如何保留和保护本族语言和文化的问题。在这类民族杂居区的其他一些地方,特别是杂居区内某一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不同民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语教学。具体而言,学校特别是小学低年级阶段采用以汉语文为主、少数民族语言为辅的“辅助型”双语教学模式。由于没有形成少数民族优势语的民族杂居区,特别是南方民族杂成区的语言使用特点和教育状况的制约,多数小学采用的少数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只是作为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汉语文的一种手段,即学校教育的目的语文主要是汉语文,而不是少数民族语文。这是我国不少民族杂居区实施的一种传统的教学模式。
怎样看待这种教学模式呢?我们认为,不能脱离历史来看现状,更不能脱离现实去预测未来。从理论上讲,没有形成少数民族优势语的民族杂居区在教学模式上可以有4种选择:(1)继续沿用单一的汉语文教学模式;(2)采用本族语单语教学;(3)采用“辅助型”双语教学模式;(4)采用“民汉并举型”双语文教学模式。 由于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当地的教学传统和条件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有不少地区长期以来实施的是汉语文教学,即采用的是第一种教学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模式存在不少弊端,尤其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广大农村,其弊端更是显而易见。因为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农村地区是少数民族语言发挥作用的主要层面。少数民族儿童从小习得的语言是本族语,在社交场合也主要使用本族语。面对这种语言背景的学生,采用单一的汉语文教学显然不利于汉语文的学习和掌握,同样不利于本族语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选择第二种模式,必然会受到一系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比如本族语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否有本族文字、本族文字在当地的通行情况、教材和师资条件,以及本民族广大群众的意愿等等。如果条件许可,采用第四种教学模式最为理想;如果条件不具备,采用“辅助型”双语教学模式,无疑是符合当地实际的、合理的选择。它不仅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文水平,而且对于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至于如何进一步发挥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如果有文字的话)的功能和作用,只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不断地创造各种条件,而不能脱离历史与现状凭主观愿望行事,更不能无视少数民族的实际需要和长远利益采用强制的、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处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