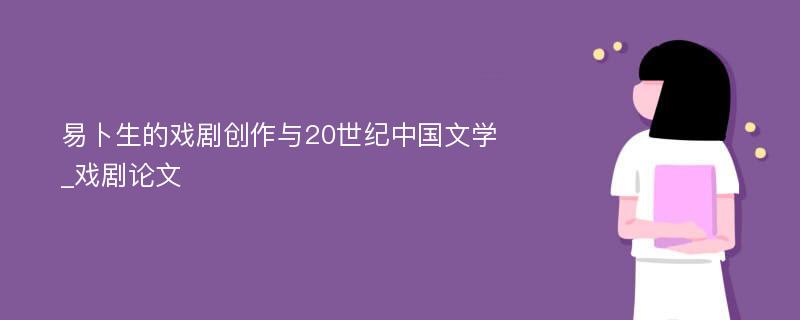
易卜生戏剧创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戏剧论文,世纪论文,易卜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一位使挪威人、斯堪底纳维亚人乃至全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文化巨人。他从“抒情诗人”到“现代喜剧之父”,为世界文库留下25部戏剧以及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论文。这些文学创作和论著组合成一部翔实而生动的“巨人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他的超前意识与超前技艺,为后世各流派戏剧家所赞赏和借鉴。与莎士比亚一样,易卜生不属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和全世界。中国人民了解易卜生,需要这个“伟大的问号”。易卜生的剧作在中国介绍很早,上演很多,影响很大。广大读者极其重视这位戏剧家的创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演出、评论的历史。他的各种类型的戏剧,尤其是“社会问题剧”,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有深远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易卜生的戏剧文学创作,与我国现当代小说、戏剧的关系,还有独特复杂的“易卜生主义”在我国的传播〔1〕, 都已成为许多研究者进行比较探索的饶有兴味的课题。
1922年,胡适曾在《英文泰西文学》(Western Literature)序文中说他首先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这显然是不确切的。从戏剧创作来看,早在清末民初,易卜生及其戏剧《群鬼》便传到了中国。《群鬼》由译述家林纾根据别人的口译改写成为小说并予以发表,当时的译名是《梅孽》(一说是1921年正式出版)。阿英的《易卜生在中国》一文认为陈虾译的《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戏剧中译本最早的一种。不过,这个译本直到1918年10月才发表。就评论而言,最早评论易卜生的是鲁迅。1907年,鲁迅在《河南》月刊第二、三、七号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论及易卜生。他告诉读者,近世挪威易卜生“瑰才卓识”,其所描写的,“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摄之强者也。”(《文化偏至论》)他还认为,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于是作剧《社会之敌》(《人民公敌》),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剧中斯托克曼(斯托克芒)医生宣传科学,为民请命,“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摩罗诗力说》)对易卜生崇信个性解放,维护生活真理,勇于斗争顽敌这一方面,鲁迅大致赞同。1908年,仲瑶的《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学报》杂志第十期)一文,称赞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反映了社会真实。从艺术的角度考虑,1914年,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成就卓著的春柳社上演了《娜拉》(即《玩偶之家》),这是易卜生的剧本在我国首次演出。就在这一年,话剧界的先辈陆镜若在《俳优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专论《伊蒲生之剧》,称易卜生为“莎翁之劲敌”,并介绍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群鬼》、《海上夫人》等11部戏剧。易卜生的戏剧,随着欧洲剧被引进中国而来到中国。从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易卜生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重视,在群众当中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不能说不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痛恶清朝末年的腐败社会,而且不满1911年(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后果,深感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革命必须坚持下去。就文艺领域来讲,不少人为了唤醒民众的觉醒,为了打破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往往从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文学中吸取力量。富有挪威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个性与独创精神的易卜生,就成为他们引进的对象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的时代要求,使易卜生及其戏剧更加深入广泛地在中国流传。1918年6 月号《新青年》杂志刊出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国内第一篇全面系统地评析剧作家的专论),袁振英的《易卜生传》(第一篇中国人写的剧作家传记)。稍后,从“五四”爆发的1919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又有周瘦鹃,潘家询等人译成易卜生戏剧多种出版。还有许多论述易卜生的文章发表。潘家询的《易卜生集》(一、二集)于1921年和1922年问世,并附有易卜生传记与译者前言。从此,他孜孜不倦地从事易卜生评介工作,他的译笔严谨流畅,评论较有系统,卓有劳绩。在“五四”期间,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都在我国上演过。《五四》前后,娜拉、斯多克芒的形象活在中国青年的心上,易卜生的名字传于青年之口。茅盾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新青年》宣传易卜生时代,这位北欧文豪的名字传述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列宁”。这是历史的真实。有些作家把易卜生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道德,提倡民主科学等新运动的象征,因此,他们的作品也染上了易卜生的色彩,充满了诘难社会的一连串“?”(易卜生就是“伟大的问号”)。那时候,人们如此重视易卜生,既有学习欧洲近代剧“写实主义”艺术技巧的根由,又有从民主精神中吸取精神营养的原因。后来,鲁迅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是确当的。但我想,还因为Ibsen 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介绍者,恐怕是颇有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奔流》编后记)。这虽然是指《新青年》的“易卜生的专号”讲的,却也包括“五四”前后几年的情况在内。“五四”运动以后的三十年间,特别是20年代和30年代,易卜生戏剧在我国戏剧创作和演出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易卜生的戏剧的翻译和评价也越来越多。我国优秀的剧作家洪深在《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时了吗?》一文中,讲过一则有趣的事:1922年从美国回来时,有人问他,是想做“红戏子”还是想做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他的回答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做一个易卜生。”据他看来,易卜生的戏剧比莎士比亚更切合中国反封建专制与反帝国主义的实际。鲁迅一生,曾在许多文章中论及易卜生和易卜生的戏剧,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重要的还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娜拉走后怎样》(1923)、《再论雷锋塔的倒掉》(1925),《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忆韦素园君》(1934)等。鲁迅非常重视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影响,并且使这种影响与中国人民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融合起来。易卜生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批判精神,在鲁迅的一部分短篇小说和杂文中有所感应。文学理论家瞿秋白曾对鲁迅介绍易卜生的积极作用,包括他对易卜生个人反抗的称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32年,瞿秋白还发表了恩格斯论易卜生的信的译文,为中国的易卜生的研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五四”前后到40年代末,易卜生的剧本在中国的译本最多、评介最多、演出最多,争论也最多,引起争论最多的是《玩偶之家》。1935年,上海的左翼剧社大规模的地上演此剧,全国各地也先后上演这出戏,盛况空前,因此有人称这一年是“娜拉年”。这是《玩偶之家》在中国演出的高潮,扩大了娜拉的影响。觉醒后娜拉要求过真正人的生活,不做丈夫的傀儡,离开了“玩偶之家”。娜拉走后怎样?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在较长的时间里,不少中国的娜拉“砰”的一声,随手带上了专制的封建家庭的大门或以男权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大门,走向社会。
在这三十多年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可以明确地看到易卜生戏剧(主要是社会问题)的启迪作用,象《玩偶之家》、《社会支柱》等剧作,在胡适的《终身大事》(1919)、欧阳予倩的《泼妇》(1922)、蒲伯英的《道义之交》(1922)等早期话剧中,都有直接的反映。这种反映证实,接受易卜生影响的作家的创作,也走上了社会问题剧的道路。胡适的《终身大事》显然与他的《易卜生主义》有血缘关系。这里对《易卜生主义》的有关问题,略予评论很有必要。胡适于1918年发表此文,对于中国话剧创作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一方面提倡“写实主义”,主张戏剧成为宣传反封建的“宣传工具”,称赞娜拉、斯多克芒的反抗精神,这在当时无疑地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另一方面又曲解了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把这位剧作家强调人格独立、“自强”“自救”的人道主义说成是“纯粹的个人主义”,极端的“为我主义”。不过《易卜生主义》在当时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就表现了这一点。它是典型的摹仿《玩偶之家》的作品,虽然其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不能和易卜生的剧作比拟,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突出了妇女问题和婚姻问题,而这又是当时反封建斗争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剧中女主人公田亚梅可以说是中国的娜拉,她反对父母利用封建迷信,风俗祠规干涉她的婚姻自由,离家时留下一张字条,表明自己的“终身大事”,“应由自己决断”。然而,胡适并没有真正提倡中国的娜拉走出玩偶之家,他只重视精神上的反叛,所以不主张“女学堂”上演这出戏。难怪他这个新派人物维护旧式包办婚姻。他和他的夫人江冬秀本无爱情可言,却主张白首相依,谁也不会弃家出走。欧阳予倩也塑造了一个中国的娜拉形象,她就是《泼妇》里的于素心。她反对男人借故纳妾,欺侮女性,反对封建市侩家庭对女子进行欺骗教育的一番议论,她理直气壮地离开家庭的具体行动,颇有易卜生式的特色。于素心带着儿子出走,娜拉扔下儿子出走都能表明她们要摆脱牢笼,寻求妇女独立生活的道路的决心。蒲伯英为揭发中国社会的多种黑幕而创作《道义之交》。它的思想意义与易卜生的《社会支柱》差不多,康节甫就是易卜生笔下博尼克式的伪君子。尽管这出戏还比较粗糙,可是其中提出的社会问题却是值得人深思的。此外,熊佛西的《青春底悲哀》、侯耀的《弃妇》、陈大悲的《幽兰女士》、白薇的《琳丽》和濮舜卿的剧本集《人间乐园》,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汲取了易卜生的思想营养和编剧技巧。象田汉、曹禺等杰出的剧作家,也都接受过易卜生的影响,曹禺自认为易卜生是他的启蒙老师(《我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象田汉的《获虎之夜》、曹禺的《雷雨》、《北京人》以及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甚至包括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易卜生的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精华,他们将它溶化于自己的创作中,提出了种种社会问题。比如,曹禺写作《雷雨》接受过易卜生《群鬼》的影响,他不仅积极学习易卜生的编剧艺术技巧,而且努力扩展他那干预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群鬼》的启示下,《雷雨》也描写了父子两代人与使女的情感纠葛,并通过封锁式(团块式)结构从鲁贵与四凤(父女)“谈鬼”开场,交代出全剧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一部分剧前发生的“情节”。虽然如此,《雷雨》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又有其独创性。其“社会问题剧”的特征在于“宏观性”,社会主题较《群鬼》更为深远。它并不局限于血缘性爱的矛盾与复杂的家庭悲剧,而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家庭丑史,揭露资产阶级虚伪、残暴而怯弱的实质,与此同时还表现出贫困劳动者的惨境与抗争。《雷雨》的封锁式框架中,也结合着开放式结构部件,并运用多层次的“回溯法”,使剧情更加跌宕多姿,戏剧性更加强烈。又比如,从现代文学时期到当代文学时期,郭沫若通过历史题材塑造了叛逆的女性即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不仅对古代人物作了现代的观照,而且她们的身心都有易卜生笔下娜拉的印记。卓文君“出走”之前与海尔茂(丈夫)“辩论”。郭沫若认为他的卓文君就是一个“古代的娜拉”。无可讳言,三个叛逆的女性形象都有现代的、当代的独立自主意识,反映了现代的、当代的中国女性的觉醒。从艺术视点考察,中国当代地方戏曲中的一些表现技巧,也可与易卜生戏剧技艺作比拟对照。桂剧《泥马泪》是中西方多种艺术手段的结合。其中,悲愤的李马撞马而亡,台上出现了一大群似马的白衣人,这场戏令人自然想起易卜生的《罗士莫庄》,当“白马”出现时,牧师罗士莫和他所爱恋的女人吕贝克搂在一块儿投水自杀。不过,《泥马泪》里的“似马的白衣人”,并没有《罗士莫庄》中“白马”那样象征死亡的神秘主义,前者显然运用象征手法使“造神反而被神害”的主题得到深化。
易卜生对“五四”以来我国小说创作的影响,虽然往往是潜在的,却又是可以理解的。这方面的创作,除了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庐隐的《灵魂可以卖么》、叶绍钧的《隔膜》和《一生》,还有茅盾的《虹》、巴金的《家》、《春》、《秋》等长篇小说。鲁迅于1926年发表于《彷徨》小说集的《伤逝》,多次讲及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女主人公子君也是当时中国的娜拉,不过这一形象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比娜拉更深邃。子君和涓生都很崇拜易卜生等资产阶级民主作家,对于娜拉出走予以赞同,那是不用说的。子君争取婚姻自由,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与涓生生活在一起,自然是好样的。但是小家庭平庸的生活,婚后与涓生之间的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竟迫使她不得不返回她所厌恶的那个家,直至毁灭。在这里,鲁迅并不是反对“出走”,而是形象地表明他过去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宣传的主张,妇女解放必须以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为保障,妇女不愿做傀儡,“经济权就是最要紧的了”。如果不这样,娜拉走后还可能回来,甚至“饿死”或“堕落”。子君就是出走之后又回来的娜拉。郭沫若的《娜拉的答案》可以说是“五四”以来关于“娜拉走后怎样”争论的继续。郭沫若认为,清末女革命家秋瑾就是中国不折不扣的“娜拉”。秋瑾确实经历过一段玩偶家庭生活,但终于摆脱了丈夫的羁绊,逃离了家庭后参加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杀身成仁”,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郭沫若说得很透彻,出走的娜拉往何去?应求得独立谋生的学识与技能,必须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郭沫若的答案,完全符合清末以来,直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扩而大之,“娜拉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即使在当代的中国也有其现实意义。据吴雪先生撰文(《“娜拉”演出所想到的》)记载,1956年,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娜拉》的某晚,一对青年夫妇观剧后,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女:“你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了!”
男:“我考虑什么呀!”
女:“考虑什么?这还不明白。我看你就有点象那个海尔茂!”
男:“别胡扯,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根本不会有海尔茂那样的人!”
女:“我才不胡扯呢?我完全有根据。我说的是你意识中也还有象海尔茂一样对待妇女的观点和态度。”这则似乎并非杜撰的“故事”以及类似的争论,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有两点:一是易卜生的戏剧在社会主义中国深受欢迎,还在发挥作用;而且它的影响与作用,决不止于上面引出的“故事”。二是易卜生的戏剧还会引起争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与理解,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文学是人学。中国当代小说中反映妇女的命运、出路以及独立自主意识的作品也不少,令人注目的有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回黄转绿》等。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中国的娜拉一再出现,并随着时代的步伐,逐渐从个性解放的小圈子走上改革社会的广阔的革命道路。已经提到的茅盾的《虹》,就描写了梅女士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而冲进社会,经过新思潮的教育,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的过程。胡也频的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里的素裳女士,是一个“未来社会新女性的典型”。她厌恶庸俗而凶残的丈夫,决然抛弃资产阶级家庭,到象征革命的莫斯科去。关于这方面的人物形象,在戏剧创作方面,也不乏其例。比如,白薇笔下的肖森(《打出幽灵塔》)终于发出了革命的呼声,于伶笔下的沙霞(《女子公寓》)勇敢地奔向民族解放斗争前线。在当代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梁信)和《李双双》(李准)中,表现了中国女性的社会主义觉醒。吴琼花的“出走”,从女奴——女兵——女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革命过程,李双双不屈从“夫权”安排(呆在家里做鞋烧饭),坚决承担妇女队长任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都感人至深!当然,易卜生戏剧人物与当代中国文学形象之间可作平行或影响比较的不只是娜拉,还有其他。比如,王蒙笔下的林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与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颇似易卜生笔下的斯多克芒“死守真理,以拒庸愚”。不过,林震并无斯多克芒那种无政府主义思想。象这些中国的娜拉、中国斯多克芒,确曾走过北欧娜拉、斯多克芒的争取个性解放的道路,然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早已超过了易卜生的戏剧人物。这种超越所形成的差异,当然不能标志作家技艺的高低,它只能表明时代的需要不同,社会条件不同。还必须指出,上面列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杰出的作品,虽曾接受过易卜生的影响(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但它们是以继承与发展中国文学传统和民族独创精神为主导的。
鲁迅、茅盾、郭沫若、曹禺、王蒙等现当代作家借鉴易卜生文学创作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必须把努力借鉴域外文学的精华,与积极弘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
注释:
〔1〕参阅拙文:《易卜生和他的文学创作》(代序), 载《易卜生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标签:戏剧论文; 玩偶之家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雷雨论文; 鲁迅论文; 人民公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