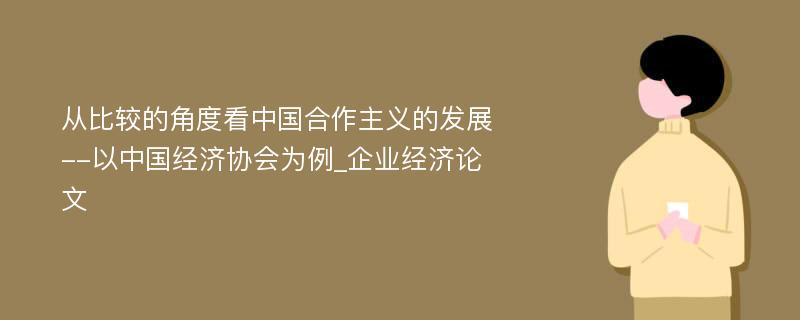
比较视角下中国合作主义的发展:以经济社团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社团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社团,包括行业协会(行会)、专业协会,商会等,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发展起来的一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也是方兴未艾的社团崛起中的一支生力军。从1977年到1990年代中期,至少有304个全国性经济社团建立起来了,① 到21世纪初,全国性专业协会和行会已达500家(《经济日报》2001年6月6日)。根据民政部2004年统计,当年全国范围内各级行会及专业协会总数超过了82047家。② 经济社团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的学者们的广泛兴趣。研究此类社团的发展以及政府在其崛起中的角色,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一般状况及特点,也将启发我们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自上而下类经济社团,在关注国家—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试图回答两种类型的问题。首先,从社团研究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经济领域内的社团,特别是通过自上而下途径发展起来的,比其他社团发展要快?它们出现的主要背景、特点和作用是什么?而政府推动这类社团的目的和方法又是什么?其次,从理论研究上讲,二战后西方政治学家在研究欧洲以及非西方文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广泛采取了合作主义概念来解释国家与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并强调行会协会在权力安排中的关键作用。这种框架能否用来描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管理结构的变化及经济类社团的兴起?更进一步说,它是否有益于我们理解当前经济领域中政府与各种利益团体的关系?而如果我们选择用合作主义思路来研究这些问题,那么中国的合作主义又有什么自己的特点?
一、比较视角下的合作主义模式
与其他类型的中国民间组织相同,经济领域社团的发展亦呈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些组织的成立方式、决策过程和管理机制。前者表现为政府在协会行会成立中起主导作用,且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给予这些组织以各种资助并对其进行控制。后者以私人企业家发起、组织并运作的民间行会商会为代表,尤以沿海地区民营商会最为典型。经济社团发展中的两种模式,反映了中国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新特点。政府在推行改革时,将许多原属政府的权力让还于企业与社会,同时起用了各种民间组织形式来承担责权以满足市场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而自发性社团的兴起则代表了社会利益集团、非政府力量和个人保护其利益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合作主义与公民社会是当今政治学中解释国家与社会及与社会利益集团关系的两种流行理论概念。中国社团发展中的两种途径表明了公民社会与合作主义在中国的同时出现以及国家与社会各自对改革后新形势所做的反应。限于篇幅,本文集中以合作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自上而下经济社团的大量兴起和政府在社团发展中的作用。
合作主义(corporatism),又译为法团主义,其原义来自拉丁词汇corpus,也就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部分和机能组成的有机体社会,与阶级冲突理论相对。③ 像公民社会概念一样,理论界至今对其内涵争论不已。如菲利浦·施密特所形容,人们“用很多不同的方式界定这一概念,对其付诸实行亦常常有争议”。④ 而他本人对合作主义概念的表述在政治学界影响很大。施密特认为,“合作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利益代表体系,在此成员团体被纳入单一的,强制性的,无竞争的,等级制的,按其功能划分的一个个组织范畴,‘这些组织’是由国家认可的,发以执照的(如果不是由其操办的),并授之以权的各自部门中的垄断性代表。作为交换,它们得在选择领导人,表达要求和支持等事务中听从‘国家的’某种控制”。⑤ 在此基础上,他将合作主义进一步分为两个模式:第一,自由主义型或社会型,社团的领导人向其成员而不是政府负责,同时政府不直接指定不同部门之间协议的条件。第二,极权型或国家型,国家对社团行使自上而下的权力。两种模式的共性在于组织上的一致与合作,“在合作主义体系中,口号是和谐。不论和谐是真的一致还是由上边强加的”,⑥ 其后,豪沃德·维阿达将合作主义简化为:(1)强有力的指导性的国家;(2)对利益集团自由和活动的限制;(3)把利益集团纳入或者作为政府机制的一部分,使其在政府中代表其成员的利益并帮助政府推行政策。⑦ 在合作主义中,国家和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结合为一种协作而又互利的关系。在此无论是国家的积极干预或者是经济社团在本行业的垄断地位都是关键性的。国家承认有执照的行会在其行业中的权威性,而这种保护使垄断性行会得以行使其职权。而行会作为在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中介机构,既代表成员利益,又协助国家减少竞争中的冲突。
目前已有不少中国学者注目经济类社团的发展,但尚无以合作主义来分析行会商会等组织的研究。使用这样一种源于西方的理论概念来研究中国经济社团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主义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跨越文化和地域的政治实践和研究框架。自19世纪末以来,合作主义作为一种国家与利益团体的权力安排已经在欧洲广泛流行,此后更流行于东亚、北非和南美。而长期以来政治学界采用的基于自由主义的多元化发展理论越来越不适合于解释很多非自由主义民主制国家的发展途径。这是合作主义后来被比较政治学广泛采用的主要原因。基于这一概念而对不同历史文化下发展途径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在发展中会遇到相同的问题,而它们在面临国内外挑战时所采取的对策也有相同之处。其一就是政府在这些国家经济起飞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利益集团与国家形成的合作主义关系。同时,合作主义在欧亚的经历也证明,不同的政治结构、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导致了合作主义模式的变异。合作主义研究途径要求我们在分析一个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注意形成的背景、目的及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变化。对他国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照物,因其不仅提出新的角度和关注点,也为交流创造了共同话语和理论平台。
合作主义不仅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西方政治学概念,也是一种付诸实践的利益团体行为。⑧ 有研究认为,合作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政治理念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和圣经时代。例如在圣经中,圣保罗曾说,社会与政治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篇》中国家与社会的区别是不存在的。他强调国家应力图成为整体的,统一的甚至是铁板一块的,而其整合应沿着自然的社会功能划分。⑨ 经中世纪,这种意识形态不断演变而延续了下来。到19世纪中后期,强调阶级调和及国家统一的现代合作主义不但在天主教国家而且在新教国家开始被接受。由于工业化带来了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包括产业工人阶级的出现,合作主义作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另一种政治选择,即第三条道路,得到了欧洲政治家们的青睐。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系列的经济危机以及一战后的政治冲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合作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实用性的政治管理模式当时风靡了欧洲。⑩
然而,合作主义在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盛行使这一政治理论在二战后很长时期内被政治学家所回避,虽然它实质上从未真正从欧洲政治中消失。到了70年代,合作主义不但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而再度兴起,也开始被政治学家们所再次讨论。究其原因,一方面,当时欧洲经济的不景气导致了人们对自由主义制度的反思和对国家作用的认可,很多利益团体开始采用与国家合作来应付经济困境。(11) 另一方面,以多元主义为主导的发展理论难以解释很多东亚和南美非民主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路径,因此于70年代让位于合作主义和依赖说。(12) 在欧洲,合作主义方法主要用来分析政府与社会或经济利益集团如工会、雇主协会及行会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安排。(13)
大量研究表明,由于欧洲与亚洲和南美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不同,虽然都经历了合作主义,但它们的特点显然不同。潘佩尔指出了欧洲合作主义的四个特点:1.欧洲的合作主义是从很强的自治社会组织中发展出来的;2.其出现的背景是政治党派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民主制度;3.无论在企业或在全国层次上,有实力有组织的劳工在决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4.其发展包含了一个提供社会福利的昂贵的政府机构的扩张。(14) 这类合作主义被界定为自由合作主义或者社会合作主义。查尔斯·泰勒形容其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统一,如瑞典,荷兰和德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在此,“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盘根错节已经到达这样一种程度,使它们之间在权力与决策力上的区别失去了重要意义。政府和社会两者都取之于并尽责于同一个公众”。(15) 由于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无论是在国家与利益集团谈判时,还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利益团体,特别是劳工组织,以及政党的参与和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北欧国家的经验还证明,合作程度越高,劳工冲突和公民骚动率越低。(16) 而东欧合作主义的出现与西欧又不同,虽然前者试图模仿后者。在东欧90年代政治转型时期,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解体后的俄罗斯、乌克兰等,都进行了合作主义的试验。但在那些国家中合作主义的出现更多有赖于政府的倡导,而其生存也多与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信任有关。(17)
亚洲的合作主义与西欧的形成鲜明对比而与东欧的有类似之处。亚洲国家不具备西欧历史上的对国际市场开放的小企业,强大的劳工组织和左翼政党,以及长期以来国家作用的弱化。因此其合作主义的形成不可能与欧洲相同。以日本和韩国为例,合作主义在那里的出现“往往不是由利益团体发起而是政府倡导的结果。在此民主机构和政党常常尚未牢固确立。在整个亚洲经济成功的例子中,有组织的劳工在重要决策中的作用往往被边缘化了”。在日本,其关键工业中均设有合作主义的组织形式,每个工业都被紧紧地纳入到最高层行会(peak association)中。二战前,为了在不利的世界市场中竞争,日本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与大企业、小企业和农业中的最高行会紧密合作来推进国家经济利益。同时却将试图促进各自利益的工会和左翼政党作为政府和企业体系的压制对象。潘佩尔认为,日本30年代为建立自给自足帝国所作的努力部分是囿于对正在关闭的世界市场的反弹。战后这种传统延续了下来。大部分日本的重要工业都由日本经济联盟(Keidanren)代表,而每个工业的最高协会不但对其成员有真正的影响力或控制权,并且在国家决策机构中代表该工业的利益。例如农业和小企业,它们的最高层协会,例如囊括了99%个体农场主的日本唯一的农业合作协会(Nokyo),对战后日本经济政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与此对照,日本工会50年代的摩擦导致了几大工会群雄并立。其结果,不但工会和代表工人的政党几乎被完全从治理中排挤出去,而且主流意识形态还鼓励工人将其利益与公司而非本阶级认同。(18) 日本并非特例。在亚洲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劳工或者代表劳工利益的政党在决策和利益表达中往往缺位。(19) 这样的合作主义常被称为“劳工缺位式合作主义”(corporatism without labour)。亚洲合作主义的这种特点将其与几乎是完全集中于公司与劳工关系的西欧式社会合作主义区分开来。
再看战后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在其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一种将支柱工业利益和国家维系在一起的国家合作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基于此,不仅国家处于经济的中心,而且大工业、利益团体与官僚国家建立起了紧密的相互影响和依赖关系。(20) 对韩国战后几十年的国家与利益团体关系演变的研究表明,在六七十年代形成的国家合作主义目前正在向社会合作主义过渡,有组织的利益正在得到更多的影响力。
合作主义在欧亚的不同特点证明,特定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进程必将导致合作主义模式的变异。它们之间的不同是很关键的。然而,毕竟是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相似之处导致了合作主义在不同背景的国家中形成。换言之,也正是因为不同国家在经济协调和管理权力安排上的一些共同特点使得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合作主义来“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合作主义的出现常常与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面临的竞争形势有关。虽然不同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决策过程各异,然而当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国际市场的挑战时,无论是国家或利益集团双方或利益集团之间,或劳资之间,均力图以协调和妥协来减少内部竞争,以求对外有更强的竞争力。以亚洲经验而言,在明治日本和当代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经济起飞时期,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软弱地位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使集体的、合作主义的、乃至于内部强制性的政治经济结构在这些地方,特别是在他们的主导工业中形成了,而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则未能发展为主流意识形态。(21)
以欧洲而论,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美,较晚工业化的国家面临着更固定的世界市场和由于更复杂的制造技术而产生的更高成本以及由之而来的各种管理和政治问题。例如,二战前的德国和南欧国家,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软弱地位迫使国家和利益集团联手采取集体的、合作主义的及其他国内强制性的政治经济结构,特别是在它们的主导工业中。皮特·卡泽斯廷的研究表明,70年代以来,合作主义在北欧的一些工业化小国的形成有助于这些国家适应变化了的已成为对它们不利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些国家既无法左右国际经济又难以有效地抵制外部对其经济形成的经久而巨大的压力,因此只有依靠内部的经济和权力调整来对付外部挑战。(22) 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和经济精英都认为只有通过合作主义来解决内部冲突,加强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别无选择。(23) 简言之,在不同背景下形成的合作主义殊途同归。只不过,在权威主义时代的韩国,是国家扮演了控制和安排经济利益的角色,而在民主制的北欧,则是经过政府与利益团体的谈判达到了内部的合作。然而,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合作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以及通过内部协调来加强对外竞争力。
二、经济领域中自上而下的协会行会
为了以经济社团为例来分析合作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必要先对改革开放后自上而下的经济社团的发展状况做扼要的描述。在中国,国家拨款和事业编制是表现一个社团与政府关系的两个显性指标。虽然获得这些指标的社团往往被统称为半官半民,但它们的成立背景、经费来源、组织结构、运作及与政府的关系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转型深入,这些组织的自治程度和与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有时是实质性的变化。本文将这些经济组织粗分为三类。
第一种类型:以社团名义存在却承担明确的政府职能并仍然生存于政府体制内的经济社团。这一类组织分改革前已有的和改革后新建的两种,虽然出现时期不同但两者共性很多。清末民初工商民间组织十分活跃,但到50年代,大部分已不复存在。根据《中国社会团体大词典》不完全统计,至文革前,全国性社团,包括解放前建立的,仅有108个,其中将近1/3是经济社团。改革前这些组织虽然仍挂着社团牌子,却已基本上行政化了。它们承担各种行政责任,其工作人员同政府部门干部享有同等待遇。改革后,很多体制内生存的社团逐步走出体制。但仍有少数重要社团留在了体制内。在这类经济社团中,工商联是最有影响的一个。与此同时,改革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经济力量,也带来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管理机制显然无法满足需要。为此,政府建立了一些新的管理机构。在很多情况下,或由于新情况的自身特点,或出于与国际接轨的目的,政府认为非政府组织这一形式更适应新形势和新问题。于是消费者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企业家协会等应运而生。
为取代解放前大量存在的民间商会行会,而又“代表”私有经济的利益,政府于1951年就开始组织地方工商联,中华全国工商联成立于1953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工商联的作用被形容为“帮助政府拉住私有企业家,改造私有企业家”。(24) 到“文革”前,从全国到地方县级的工商联体系已完全行政化,由于私有经济成分日益下降,工商联当时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这一情况到80年代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商联的性质被明确定位为经济性、统战性、民间性。首先看工商联的经济作用。政府需要工商联在推动非国有企业经济发展中为私有企业提供有关市场、资金信息以及各种专业服务,同时要求工商联引导私有企业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服从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此,政府在积极支持工商联和鼓励私有企业家入会的同时扩大了工商联的工作范围,特别是经济工作任务。到2002年,全国各级工商联已发展到2800个,吸纳了160万个团体和个人会员(《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3日)。工商联的另一项任务是将私有资金引导到公益事业中来。在工商联的直接组织下,1994—2002年吸引了近9000私人企业家和229亿人民币投资于光彩事业中,这些项目给一百多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人民日报》2002年4月14日)。其次,新政策明确了工商联的民间性质。工商联作为人民团体和著名的八大社团之一,与政府有紧密的关系,而且多年来享有政治上的某些特殊待遇。至今,工商联仍直接受各级政府和统战部门的领导,不必在民政部门登记,且得到行政开支,其工作人员福利参照公务员,而各级领导享受同级行政干部的待遇。例如全国工商联相当于部级,北京市工商联相当于局级。因此说工商联是民间组织显然是不合适的。然而,为吸引私有经济力量,特别自90年代以来,政府有意强调工商联的民间性。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工商联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代表民间商会。1994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参观全国工商联时,特地为之题词“民间商会”。在工商联2002年第九届代表大会上,全国工商联执委会412名成员中56%是私有企业家(《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3日)。从工商联的态度看,有研究表明,全国工商联中有影响人士不断呼吁给工商联以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市、区级工商联的基调实际上“更多是代表它们成员的而非政府的利益”。(25) 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和自下而上组织的成长,工商联更实质性地为其成员服务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与此同时,政府在现阶段将继续强调它的统战性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立的经济社团中,有一些承担着重要的行政职能。以中国消费者协会为例,1984年政府建立中消协是为了加入国际消费者联盟这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然而由于在中国政府中没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构,消协从建立初始就承担了很多政府职能(采访中消协,1996年,2000年)。个体劳动者协会又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50年代初全国有700多万非农业个体劳动者。经过多次经济改造和政治运动,到文革结束时,这一数目降到最低点,仅存15万。北京解放时有15000家饭馆,而到1976年全市仅剩六百家。改革开放之后,为解决城镇待业青年和社会过剩劳动力,政策开始对城镇个体经济开口子,到80年代中后期,政府不但进一步放宽城镇人口从事个体经济,更明确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个体经济人口迅速增长,到1988年,全国城乡个体户发展到2300万人。(26)
虽然个体经济给整个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可是如此庞大、散漫、流动性极强的劳动大军使政府难以管理。个协的成立就是为了管理这部分劳动人口。在一份个协编写的教育材料中,这种目的被直白地表达出来:“个体工商户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队伍庞大,人员复杂,文化知识水平较低,整体素质较差,组织纪律松散,在行动上有很大的随意性等特点,在当前没有专门的业务主管部门的情况下,特别需要通过协会这种组织形式将他们团结在一起,进行有必要的教育和管理。”(27)
在80年代初,部分个体劳动者自发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到1986年,全国27个省出现了两万多自下而上的个体劳动者协会性质的组织。然而,政府很快介入了这一发展,并开始组织个协。1986年,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由政府高级干部担任全国个协主要领导,改变了自下而上的形势。至2004年,全国个协的主席仍然由全国工商局副局长担任;在地方,大量个协领导职务由同级工商局干部兼任,而个协的工作人员属于事业编制。由于个体户没有单位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贯彻政府文件,并对其经营进行指导,个协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显得分外重要。在全国个协之下,一个自上而下的个协系统建立起来。从省区市到地州盟,到县,再到基层协会和会员小组,力图将每个个体户都组织起来。以北京朝阳区为例,那里的个协被分为28个分会,而这些分会又进一步被分为1000个会员小组,每个小组大约有20个会员。(28) 到1993年,全国建立起30个省个协,2881个县个协,包括了29136分会和306993个会员小组。(29) 在所有改革后新成立的自上而下型的社团中,个协系统是最完备的。
虽然原则上个协会员入会是自愿的,但是每一个个体户在领取开业执照时,就会自动成为个协会员。澳大利亚学者马克·雷昂在讨论第三部门的志愿性时指出,虽然有些第三部门组织成功地使其职业或行业中每个工作人员都成为它们的会员,并不能因此就说它们不完全算是第三部门性质的。因为活跃地领导这些组织的人是志愿者。(30) 个协的志愿性显然不是雷昂描述的情况。个协成立的最主要目的是协助政府监督指导个体户。这样的入会谈不上是自愿的,而这种情况即使在官办色彩浓厚的社团中也是不多见的。从政治意义上可以说个协是个体户的“单位”,政府通过个协对分散而无组织的个体劳动人口进行基本的控制、教育和管理。
第二种类型:各行业中成立的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成员的专业性协会。目前在各个工商业部门中,专业协会是相当普遍的。协会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政策、交流信息及沟通企业与政府。大量协会是八九十年代中期自上而下组织的,当时这些协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协会的领导班子一般是经主管单位推荐和内部选举的,活动由协会自主,而经费则以会费和活动收入为主。政府的补助一般是免费办公室,会议资助,和有限的研究经费。这类协会数量很大,而其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则与组织者和会长单位的投入和协会的经费数额有关(采访机械、建筑部门协会,1996年)。
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下称中促会)是此类协会中很成功的一个。(31) 中促会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组织,因为它是由包括宝钢、一汽、东风汽车制造厂等几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于1987年倡议发起的。由于这些企业都是协会的团体会员,所以也可以说是会员自行成立的。一般某个特定的协会只存在于一个或几个相关的行业,可是中促会的成员几乎囊括了全国主要的工商行业。这些会员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大型国有企业。在120多个国家试点的企业集团中,有110家是中促会会员。从与政府的关系看,这些老总都是政府高层干部。而由于会员都是国有企业,会费和企业赞助的活动经费也是国家的钱。
中促会当时成立的主要动因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解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了帮助国有企业面临市场经济的挑战,中促会定期发行三种刊物,向会员企业提供有关政策和市场方面的动态和信息,以及有助于企业决策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更重要的是,中促会代表其会员向政府反映这些大企业的意见和要求,并组织有关政策研究来影响决策机构。其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组织专题研讨,自90年代以来,每年中促会就有关重要政策或问题邀请专家、企业代表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调研,然后将研究报告提供给政府决策机构。例如,1995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提出逐步取消行业主管部门后,一些管理部门想成为行业控股公司,而使企业成为它们的子公司。很多企业集团担心这些控股公司将成为婆婆+老板,改革十几年得到的自主权又被拿回去。但是囿于上下级关系,企业不敢说话。于是中促会牵头,其成员自愿参加,委托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聘请专家研究,经过多次讨论和大型评审会,于1996年写出报告,提出行业管理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政企分开,行业管理部门改组为控股公司应慎行,而建议授权大型集团公司为投资机构。最后报告上达到国务院,朱镕基明确批示中促会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举对全国的控股公司政策以及中促会在会员和政府有关部门中的地位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1998年到2000年,他们上报了16个专题报告,其中有7件得到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批示。
中促会的成长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下情上达和企业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和机制。它的影响力无疑与其会员单位的经济政治实力有关,然而国有企业经济改革和转型对这种中介服务和表达渠道的需求是它成功的关键。由于这些集团公司都是国有企业(中促会目前已经向私有集团公司开放),而中促会的领导均由在位或退休的干部担任,因此它与政府的关系并不能真正代表独立的经济实体,特别是中小型和私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企业都有自己的利益,它们的目的是赚钱。而政府的决策则涉及多层次多方面,不可能针对所有企业的状况或代表它们的利益。但是单一企业无力为自身利益来影响决策过程,也没有条件对有关政策进行研讨。而这正是协会的职能和所长。中促会一方面沟通企业和政府,另一方面代表一种集合的力量来影响决策。这种中介作用是个别企业与政府组织所无法取代的。
第三种类型:由政府工业管理部门转型而成的协会、行会。行业协会是改革以来政府大力支持和促进,因而也是数量最多、发展最快的一类经济社团。(32) 首先,随着经济改革深化,政府逐渐认识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政府的管理角色必须有实质性的调整。90年代中,政府从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的改革强调政府对经济部门从控制改为宏观管理,放权于企业,依靠行业协会为中介对企业提供必要的监督和服务。为此,自90年代以来政府有目的有系统地以社团性的行业协会逐步取代了各行业中原有的政府管理部门。这一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以行会来取代政府管理机构并填补市场经济中急需的中介机构,另一个目的则是以此来精简政府机构。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行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精简机构的收容队,而且一些协会实际就是为了安排很多下来的干部而设立的。
简单地说,以管理机制改革而论,由于市场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一方面国有企业被管得死死的,另一方面只面向国有企业的管理机构也不能满足非国有经济的需求。以上海为例,1995年上海纺织局的管理覆盖面不到全行业的22%,而在塑料行业只有1%。(33) 民营企业不但需要各种信息和服务,它们的经营也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管理。不同于原有的工业局,行会不但向全行业开放,而且它们和企业也不是婆婆和儿媳的关系。行会是服务、协调、监督,而不是控制、命令和干涉。这样的管理体制使企业有自主权,而又不是放任自流。就精简政府机构目的而言,自80年代以来,国务院系统进了四次重大机构改革(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如下所示,这些改革,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的机构改革与行会的发展有直接关系。(34)
行会的发展代表了政府自上而下地改造经济管理体制的努力,也反映出政府对非政府行为的认可。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正、监督作用”。(35) 自上而下行会的发展首先是80年代以来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组建,在政府授权或委托下承担部分管理职能的行会。随着行会发展的深化,自90年代起开始转为直接撤销政府工商管理部门而以行会取而代之。在1993年的行业管理试点中,纺织部和轻工部首先被改组为纺织总会和轻工总会。这也是同年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其结果,纺织总会的工作人员减少了一半(采访纺织总会,1996年)。随之而来的是1997年在上海、广州、温州和深圳对23个行业进行的深度行业改革试点。而更大规模的行会发展是在1998年之后,当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精简同步大刀阔斧。首先,国务院的10个工业部先被改组缩减为3年过渡的工业局(委管国家局,政府机构),而大至六七百人小至二三百人的工业部在改组为工业局时均缩减为100人左右。2001年初,9个委管局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综合性行业协会,由经贸委直管。(36) 当2003年经贸委撤销而国资委成立后,这些综合性行业协会又转由国资委直管。到2004年,此类直管协会达到15家。同时,原工业部门之下的协会则成为直管协会之下的代管协会。一个直管协会下少的代管3个协会,而多的则达49个。目前,经济领域国字头的协会大大小小已有362家,聘用专职工作人员近3500人,其中规模大的协会可有30—50人,而小的仅1—2个人。(37)
行会在数量上的发展主要是政府的推动,而在行会协会发展过程中,对其使命的界定也始终是政府行为。经贸委明确将协会职能分为三大类:为企业服务;自律、协调、监督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协助政府部门加强行业管理。从1997年的行会6条职能的规定到目前通行的17条职能,都直接出自国家经贸委文件。(38) 政府干预已经存在于政府体制之外的行会的运作使行会改革在很多地方不能到位。政府并未将在理论上已属于行会的权力完全交给行会。其结果,一方面,使后者仍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受制于政府;另一方面,大部分此类行会由于先天不足而不能真正为其成员服务。
三、合作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施密特认为,在所有对合作主义的研究中,最有用处的看法是把它理解为某些种类型的安排。在这些安排中,利益组织可以在它们的成员(个人、家庭、公司、社区、集团)和国家机构或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协调过程中,正式的、稳定的和有全职工作人员的专门化协会和社团是中心角色,它们通过施加影响和辩论来确认、倡导并保护成员的利益。(39) 也就是说,在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对利益组织譬如行会协会的分析十分重要。那么,中国的这类利益组织与国家是否形成了一种合作主义的关系呢?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工会、共青团、妇联与政府的关系就代表了一种合作主义安排。我以为,1949年以后至改革前这些群众组织完全行政化了,它们实际上是生存于政府体制内,成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因此谈不上与政府是合作主义的关系。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法律上确立了社团法人,政府认可登记的社团为合法组织,鼓励社团自立并逐步推动原在体制内的社团走出体制。因此社团与政府的关系与改革前社团的情况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它们至少在法律上已经是民间团体了。
早在90年代初西方一些学者就开始用多元主义或合作主义来讨论中国改革以来的社团发展了。最早用此来研究中国社团的是美国学者苏珊·怀廷。她认为与多元主义相比,合作主义框架更适合用于解释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强调国家可以限制或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影响力。(40) 之后,玛格里特·皮尔森在研究经济类社团时用社会主义的合作主义来形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此来区别其与极权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权力安排。(41) 乔纳森·安格尔和安妮塔·陈是用合作主义来研究部分亚洲国家社团与政府关系的有影响的学者。在其90年代对中国社团的研究中,他们不同意用公民社会来描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认为这一框架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社团假设了过多的独立。他们强调中国政府在社团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因为“是由政府决定承认哪个组织为合法组织,并建立与这些组织的不平等的关系”。他们指出,即使这些中国社团得以进入决策渠道,它们也是帮助政府来推行政府的政策。(42) 因此,这两位学者认为国家合作主义模式对八九十年代正在中国发生的转变给予了更准确的描述。
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在社团发展中的战略与决策是国家合作主义在经济领域形成的基本前提。在中国工业市场化的过程中,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政府日益认识到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合经济发展,因此力图通过建立中介性的行会来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政府构建的新型工业管理模式中,行会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同时实现政府对经济宏观控制的关键,因为它们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代表非政府的、非行政的机制,而另一方面却继续处于政府的监督甚至控制之下。行会只有与国家建立合作主义关系才可以达到此双重作用。因此可见,政府对建立经济社团有明确的目的,而且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也只有政府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规模的机构转型。比较行会与其他类型社团的发展就可看出政府对行会的积极推动。从1996年至2003年,由于社团整顿和再登记,以及社团登记规定的严格化,无论是全国性社团还是全国各级社团总数都经历了明显下降阶段,前者至今还没有超过1996年的水平。相比之下,行会的发展却一直呈快速上升趋势,全国性行会从1988年的100家增长到1999年480家,全国行会总数则从1992年的10000家跃为2001年的44240家。社团发展的不同趋势明显地反映出政府对不同类型社团在政策上的差别,同时证明了政府在中国社团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社团已走过20年的历程。无疑,这些社团的成立背景与生存环境与欧亚行会协会相当不同。那么,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主义模式相比,它们与政府的合作主义关系表现出了哪些独特之处呢?相同的地方又是什么呢?对合作主义研究颇有影响的艾伦·考森曾总结说,无论在北欧或者亚洲工业国,合作主义均表现出了以下特点。首先是合作主义团体的垄断性作用;其次是它们在国家政策制定与执行之间的连接作用;最后是国家在颁发这些团体的执照和制定合作政策过程中的无形影响。(43) 以下就依据考森的结论来比较一下中国合作主义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垄断性。根据中国社团条例,在同一行政区域、同一或相近的业务领域内,不得重复建立相同或相似的社团。这种一业一会的规定防止了同类组织竞争的可能性,从而保证了政府承认的社团之垄断性和权威性。近10年来政府有系统地自上而下地成立了很多行会协会,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阻止了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组织的建立。在个体经济发达地区或者新兴行业(采访温州工商联,2001年),民办企业希望成立自己的组织却因有官方组织的协会已经存在而不能获批准的例子已经出现。民间率先成立协会而后政府又力图以官办协会兼并的情况也已见报。(44) 对韩国和日本的研究已证明,组织上的垄断性是国家合作主义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在北欧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由于合作主义的建立,行业组织的数量也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中国的行会发展表现出了国家合作主义中组织垄断性这一普遍特点。
然而,与欧亚工业国相比,中国社团垄断性的不同之处是,这一规定的初衷不在于协调内部冲突以加强对外的市场竞争力,而在于对自发性组织的政治控制。政府不允许重复成立社团的规定始自改革后的第一个社团登记管理条例(1989)。当时无论市场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利益分化都不充分。反之,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与中国学运的出现却是当时政府高度重视的政治事件。社团垄断性的规定表明了政府对自发群众组织的忧虑。9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和利益冲突加剧,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对工人、待业人口或其他经济弱势群体的自发组织以及任何自发性群众组织极为敏感,认为它们是不稳定因素。因此,继续控制自发的利益组织就成为政府必然的政策选择。
尽管中国的行会实行一业一会,这些组织却并不具备像日本、韩国的垄断性行会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国家合作主义采取垄断性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减少行业内部协会的数量来加强垄断性行会参加决策时的权威及其在帮助政府推行政策时的力度。就中国情况而论,中国行会不具备以上功能。影响其权威和实质性工作能力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两点。第一,包括由政府机构转型的行会在内,目前中国行会从未被赋予过代表其成员利益参与政府有关决策和进行集体谈判等重要职能。这一点在经贸委对行会职能的几次修改中看得很清楚。而且从本文上节分析的几种主要类型的经济组织看,中国任何行会协会都还不具备就政策问题彼此之间或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实力。然而,如中促会的出现所表明的,利益多元化使利益集团寻求通过集体行动参与决策和影响政策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在有效益的行会,其成员的意见也日益受到重视。有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在决策时也开始听取相关协会的建议和反馈。然而,这些只是分散的个案,往往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异。现在中国的行会尚不能成为企业、利益团体与政府的正式沟通的组织机制。包括行会在内,中国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常规性的利益团体参与决策的渠道。第二,中国自上而下行会的会员覆盖率过低,有的协会其成员不及该行业企业总数的1%。究其原因,是此类行会对非国有企业开放不久,而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力、资源和领导能力,因而对企业缺少吸引力。不具备对决策的影响力而又未能吸纳大部分本行业的企业,使得这些行会无论在服务于其成员或与政府打交道时都不能代表本行业的权威和根本利益。
中国合作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些社团负有由政府指定的明确使命。合作主义通常是由国家精英设计的有明确目的的机构性安排。(45) 在合作主义中,国家决不只是经济利益之间的裁判,一个积极的国家有自己的目标和选择。(46) 如上所述,政府大力推动行会的目的是为了及时建立一个市场经济急需的中介管理机制。而且,行会应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事情也由国家规定地很仔细。与此同时,一些自上而下的组织还被授予某些行政职能或特殊使命。如工商联的统战任务,个协的控制个体户作用以及消协处理消费者投诉和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政权力。
然而在这一方面中国亦有它的特点。以日本经济联盟和韩国全国农业合作联盟为例,它们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强政府对经济、市场和利益集团的控制或干预,这些与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合作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虽然给政府提供了通过行会干预经济的新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目的是强化它对经济的控制。反之,行会协会应经济转型需求而诞生,它们是政府下放的权力的承接机构。将原有的政府机构转型为行会,使原属于体制内的人事和办公资源划到体制外,这是一种扩大非政府部门的行为。进一步说,现在政府对协会行会的拨款或完全停止或越来越少,他们的收入主要靠会员会费和活动收入。因此为会员服务已成为协会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例如,协会跟任何组织一样,有责任将上级或同级政府的文件或宣传资料下达。现在,当政府不再给它们日常经费时,这些组织提出问题:谁付邮费?(采访温州工商联和商会,2001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它反映出政府和行会的关系正在变化,后者从依赖政府拨款从而必须听命于从属于政府的行政机构逐渐变为自主自立的民间组织。到政府需要委托行会协会提供服务而必须对这种服务拨款时,政府与它们的关系就变成为合作伙伴。同时,近年来自下而上的行会商会的发展对自上而下的组织无疑是一种挑战,前者的经验促使后者更重视与会员的关系并寻求更多的自治。(47)
中国合作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政府对社团的管理和干预。考森指出,在合作主义中政府通过发放执照来实行无形干预。中国的特点在于,准许或不准许社团登记实际上是政府控制社团发展的主要的和公开的手段。政府通过愈来愈严格的登记条例和每隔一段时间的重新登记强化了这种管理形式。其他管理方式的发展,如对民间组织实行税收部门的审计,加强这些组织的自律机制和透明度,以及提倡公众舆论对社团的监督等都滞后。一方面现行登记规定要求的条件很高,自发的草根组织要登记为法人社团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一个没有执照的组织完全不能合法运作。因此中国现行的登记管理也成为保证社团垄断性的一种手段。而在自上而下经济社团运作中,政府通过两种方式对它们干预。其一是对领导班子选举的介入,有些是在代表大会选举前内部圈定主要职务人选,有些则是选举后上报审批。其二,政府可以通过项目或运作拨款左右这些组织的活动,由于大量协会经费十分拮据,这类拨款显然十分重要。虽然政府与社团在人事或项目方面并不一定意见相左,但这些干预渠道的存在表明自上而下组织自治的程度与限度。
以上对比显示,中国自上而下经济社团与政府的关系的确具备国家合作主义的基本特征。然而其发生的特定政治历史条件决定了它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模式。此类经济社团的出现基本上是政府行为,而且是首先在体制内生成的。虽然从理论上说,行会代表本行业所有企业的利益,但现在企业对行会的介入和影响却微乎其微。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经济力量,包括工人、个体户、私有企业家和消费者,这些利益团体虽已有代表它们的经济社团,却还未能在决策机构和决策过程中成为常规化和机构化的力量。这种利益集团在参与决策中的总体弱势状况是中国合作主义模式的主要特点,这在国家型合作主义中也是不多见的。更进一步来说,行会的发展与政府机构改革和权力重新安排紧密联系在一起,行会不但承担精简机构的分流而减弱了它们的领导能力,且由于各种原因而得不到应该下放给它们的责权。这就更加削弱了它们的力量。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中国经贸委对全国工商领域的行会的研究结论中说,只有五分之一的行会工作有特色有成效,另有五分之一实际则名存实亡,其他大部分只是运作而已。(48) 因此,从目前情况看,行会实际上即不能满足企业对中介组织的需要,也未能实现政府发展此类社团的初衷。
总之,改革开放后社团的迅速兴起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事件。合作主义型社团的出现和发展是政府适应改革需要与利益集团开始认识到自身权益的混合产物。对这些社团成立和使命的研究表明,国家不仅在合作主义关系的确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其政策对利益团体的影响也是明确而有力的。与合作主义在欧亚其他国家的经历不同,至少在现阶段中国合作主义首先不是为了强化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市场竞争的控制。以自上而下经济社团为代表的合作主义安排提供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管理机制。这些民间组织既是下放的政府权力的载体,又是政府延续权力的一种渠道。它使政府在让权于企业的同时,仍然能够通过这些非政府的中介机构来控制和干预经济。然而,中国行会协会的发展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在策划这一改革时所设计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正在出现的变化。仅从中促会的例子就可看到,协会为分散的经济实体提供了集合的声音和表达意见甚至影响决策的渠道。它表明当利益团体的势力达到一定分量时,它们的声音也就有了更大的影响。自上而下的经济组织日益重视其会员的利益,表明了形式上的民间组织正在向实质上的民间组织过渡。随着行会协会的自立水平的提高,它们代表会员利益的能力也必然加强。如果将自下而上的利益团体考虑进来,我们就能看到更实质性的变化。
注释:
① 马秋莎:Classification,Regulation,and Managerial Structure:A Preliminary Inquire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ese NGOs,in S.Hasan and M.Lyons.Social Capital in Asi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Examples and Lessons,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04,p.23。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③ D.L.McNamara.Comparative Corporatism,in D.L.McNamara ed.,Corporatism and Korean Capitalism,London:Routledge.1999,p.9.
④ P.C.Schmitter.Corporatism as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and Political Theory,in W.M.Lafferty and E.Rosenstein,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327.
⑤ P.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F.B.Pike and T.Stritch(eds.),The New Corporatism: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Iberian World,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4,pp.93—94.
⑥ 转引自J.Unger and A.Chan,China,Corporatism,and the East Asian Model,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Sffairs,vol.33.1995,pp.31—32。
⑦ H.J.Wiarda.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Other Great “Ism”,Armonk,NY:M.E.Sharp.1997.
⑧ Schmitt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ations,p.327.
⑨ H.J.Wiarda.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Other Great “Ism”,Armonk,pp.27—46.
⑩ P.S.Adams.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s There A New Century of Corparitism,in H.J.Wiarda ed.,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oulder,CO:Westview Press.2002,pp.21—24.
(11) 参见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8—133页。
(12) H.J.Wiarda.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ambridge:Westview.2002,p.12.
(13) Adam.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s There A New Century of Corparitism,pp.17—19.
(14) T.J.Pempel.The Enticement of Corporatism:Appeals of the“Japanese Model”in Developing Asia,in D.L.McNamara ed.Corporatism and Korean Capitalism,New York:Routledge.1999,pp.28—29.
(15) C.Taylor.Civil Society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in E.Groffier and M.Paradis (eds.)The Notion of Tolerance and Human Rights:Essays in Honour of Raymond Klibansky,Ottawa: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118.
(16) Schmitt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ations,p.335.
(17) Schmitter,P.C.and Grote,J.R.The Fate of the Corporatism: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Summer Issue.1997。该文已被译为中文,参见张静:《法团主义》,第179—180页。
(18) Pempel.The Enticement of Corporatism:Appeals of the “Japanese Model”in Developing Asia,pp.29—44.
(19)(20) McNanara.Comparative Corporatism,p.11,pp.69—70.
(21)(23) Pempel.The Enticement of Corporatism:Appeals of the “Japanese Model”in Developing Asia,p.31,33.
(22) P.Katzestein.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32.
(24) 采访中华全国工商联和北京市工商联,1996年。
(25) J.Unger.“Bridges”:Private Business,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No.147,1996,p.815.
(26)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个体经济与个体劳动者协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22页。
(27)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个体经济与个体劳动者协会》,第68—69页。
(28) Unger.“Bridges”:Private Business,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p.799.
(29)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个体经济与个体劳动者协会》,第52页。
(30) M.Lyons.Third Sector:The Contribution of Nonprofit and Cooperative Enterprise in Australia,Crows Nest:Allen & Unwin.2001,p.2.
(31) 这一个案研究主要根据1996年、2002年采访中促会和收集的中促会刊物及未发表的工作报告。
(32) 以下讨论是基于作者1996—2005年期间对国资委、上海工经联合会及大量各类行会协会采访及收集的文字资料。
(33) 陈宪、徐中振:《体制转型与行业协会》,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34) 一份对政府精简机构和社团发展的关系的研究认为社团发展与政府精简人员的数额增加成正比。王明、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3—89页。
(35) 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中国行业协会改革与探索》,未刊稿,1999年,第2—3页。
(36) 《人民日报》2001年2月2日、3月5日。这部分可参考冷明权、张智勇:《经济社团的理论与案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3—127页。
(37) 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行业协会工作手册》,第420页。
(38) 参见国家经贸委:《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1997),《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工商领域协会的若干意见》(1999),载于《中国行业协会改革与探索》及《行业协会工作手册》。
(39) Schmitter.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ations,pp.327—328.
(40) S.H.Whiting.The Politics of NGO Development in China,Voluntas,2,No.2.1991,p.20.
(41) M.M.Pearson.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4,30:pp.25—46.参见张静:《法团主义》,第147—166页。该书曾经介绍了西方学者以法团主义(合作主义)对中国改革以来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
(42) Unger,J and Chan,A.Corporatism in China,A Developmental State in An East Asian Context,in B.L.McCormick and J.Unger (eds.).China After Socialism:In the Footsteps of Eastern Europe or East Asia? Armonk:M.E.Sharpe.1996,p.106,pp.95—96.
(43) A.Cawson.Corporatism,in W.Outhwaite and T.Bottomore,eds.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Twentieth-Century Social Thought,New York:Blackwell.1993,pp.114—116.
(44)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4月7日,第7页。
(45) G.White,J.Howell,and X.Shang.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212.
(46) Adam.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s There A New Century of Corparitism,p.33.
(47) 关于自下而上的商会行会,参见马秋莎: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Paving the Way to Civi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48) 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行业协会工作手册》,第4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