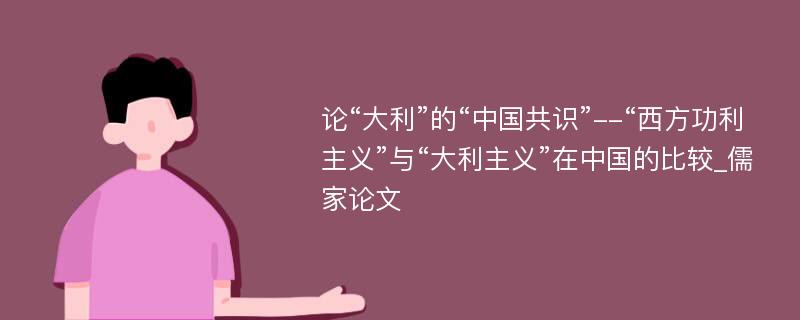
论“大利”之作为“中华共识”——兼及“西式功利主义”与中国“大利主义”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利论文,功利主义论文,中华论文,中国论文,共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利”是相对于“小利”而言的。何谓“大利”?相对于个人之利而言,家庭家族之利是“大利”;相对于家庭家族之利而言,民族国家之利是“大利”;相对于民族国家之利而言,人类全体之利是“大利”;相对于人类全体之利而言,天地万物之利是“大利”。“大利主义”是指“大利优先”,“大利”与“小利”不能兼得时,舍“小利”而就“大利”。
设若个人为“己”,个人之外之家庭家族、民族国家、人类全体乃至天地万物均为“他”或“人”,则“利己主义”就是“小利优先”,“小利”与“大利”不能兼得时,舍“大利”而就“小利”。“利己主义”又分两种:利己不损人,是谓“合理利己主义”;利己损人,是谓“极端利己主义”。相应地,“利他主义”亦分两种:利他不损己,是谓“合理利他主义”;利他损己,是谓“极端利他主义”。“大利主义”是一种“利他主义”,故也有“合理”与“极端”之分。
中国传统功利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大利主义”思想体系,换言之,是一种典型的“利他主义”思想体系。既有“合理利他主义”,亦有“极端利他主义”,更有根本超越功利之“忘利主义”。唯独没有“利己主义”,这是中西功利思想之根本不同。
中国有“义利之辨”,论者常判为“道德与功利之辨”,实则“义”有道德义,但更重要的是功利义。义者,大利也。“义利之辨”中的“利”仅指“私利”、“小利”;“义”不过就是与之相对应的“公利”、“大利”而已。换言之,“义利之辨”者,“公利私利之辨”也,“大利小利”之辨也。
《大戴礼记·四代》云:“义,利之本也。”《墨子·经上》云:“义,利也。”《墨经·大取》又云:“义,利;不义,害。”义就是利,不过特指公利、大利。《大学》云:“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不以利为利”就是不以私利、小利为利,“以义为利”就是以公利、大利为利。张载《正蒙·大易》云:“义,公天下之利。”义的含义就是公利、大利。程伊川《语录》卷一七云:“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语录》卷一九又云:“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程氏易传·益卦》云:“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云:“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之分。”王夫之《尚书引义·禹贡》云:“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有利也。”颜元《四书正误》卷一云:“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又云:“利者,义之和也。”均以“义”指公利、大利,以“利”指私利、小利。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云:“义即当然,亦即行为的制裁。然义之标准何在?何者为应当,何者为不应当?关于此点,有对立的两说。一说认为应当之表准即人民之大利或人群之公利。凡有利于大多数人民之行为,即应当的;反之即不应当的……一说认为应当之表准在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凡表现或发挥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行为,即应当的;反之即不应当的。”① 此处似认“义”有两义:一指公利、大利;一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并认为前者为墨家所有,后者为儒家所有。实则儒家同样以“义”为公利、大利,认为公利、大利即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公利、大利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一、儒家讲“大利”
儒家讲“大利”,表现为“合理利他主义”与“极端利他主义”。前者兼顾“利己”与“利他”,后者不讲“利己”,只讲“利他”。
“合理利他主义”之代表,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诸人。《论语·子罕》讲“子罕言利”,此“利”即私利、小利也。孔子罕言私利,但并非罕言公利,其“富之”、“教之”等言,就是公利。其“罕”字又与“不”字不同,罕言私利,不是不言私利,只是少言而已。这是一个以公利为归依而又不废私利、以大利为归依而又不废小利的“合理利他主义”立场。《论语·里仁》又有“放于利而行多怨”之言,此利指私利、小利。《论语·里仁》又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言,指君子持“合理利他主义”之立场,小人持“合理利己主义”之立场。
《论语·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比“仁”更高的一个境界是“圣”,它要求在“博施于民”之上还加上一个“济众”的层次,这个层次似是超越人类全体的。类似于《孟子·尽心上》所谓的“物”:“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孔子之“济众”与孟子之“爱物”应属同一层次,讲的都是“利万物”之“大利”。
《孟子·告子下》云:“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此处孟子是反私利、小利。孟子见梁惠王,斥责梁惠王“利吾国”之言论,常被学者判为“反功利”。实则孟子只是反私利、小利,并非全盘反功利。
《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利吾身”相对于“利吾家”而言,是私利、小利;“利吾家”相对于“利吾国”而言,是私利、小利;“利吾国”相对于“利天下”而言,是私利、小利。孟子一方面批评梁惠王以“利吾国”为最高追求之立场;另一方面批评当时社会上“后义而先利”之潮流,倡导“先义而后利”。
“后义而先利”之立场是把“利吾身”置于“利吾家”之上,把“利吾家”置于“利吾国”之上,把“利吾国”置于“利天下”之上,总之一句话,是把私利、小利置于公利、大利之上。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夺不餍”,亦即不以私利侵公利、不以小利侵大利便不得满足。而相反的是“先义而后利”之立场,这个立场要求“利吾身”服从于“利吾家”,“利吾家”服从于“利吾国”,“利吾国”服从于“利天下”,总之一句话,私利服从于公利、小利服从于大利。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可能“遗其亲”,就不可能“后其君”,更不可能“弑其君”。所以孟子斥责梁惠王,并非反对功利,只是反对梁惠王及当时社会上讲功利的立场。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是要求梁惠王“先义而后利”,不是要求他舍弃利;“何必曰利”实即“何必曰私利”、“何必曰小利”之略称。孟子在同一篇中,讲“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讲“鸡豚狗彘之畜”,讲“谨庠序之教”,讲“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讲“无恒产因无恒心”,讲“明君制民之产”,更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都表明孟子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而只是反对“后义而先利”之立场。孟子以大利为先,但并不舍弃小利,故其立场乃是一种“合理利他主义”。但《孟子·离娄下》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之言,似乎表明孟子有“极端利他主义”之倾向。但这只是对“大人”的要求,不具有“普适性”。对广大民众而言,有“合理利他主义”就足够了。
荀子对待功利,也持“合理利他主义”之立场。《荀子·王霸》云:“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攒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在荀子的理论系统中,国家是调节功利的一部机器,《荀子·王霸》开篇一句就是“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制”就是调节。国家调节功利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是“先义而后利”,一是“先利而后义”,前者是“合理利他主义”,后者是“合理利己主义”。“合理利他主义”,荀子称为“巨用之”,就是讲原则、共分享;“合理利己主义”,荀子称为“小用之”,就是不讲原则、不讲是非曲直,只知唯利是图。“小巨分流”,实即“合理利己主义”与“合理利他主义”之分流。荀子以为只有“合理利他主义”才能成就一个伟大国家,故曰“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又以为“合理利己主义”最终会导致国家灭亡,故曰“綦大而王,綦小而亡”。
《荀子·荣辱》云:“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这是“极端利己主义”与“极端利他主义”之对举,“唯利之见”代表“极端利己主义”,“不顾其利”代表“极端利他主义”。《荀子·大略》云:“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乱世。”此处亦为“合理利他主义”与“合理利己主义”之对举,“欲利不克其好义”代表“合理利他主义”,“欲利克其好义”代表“合理利己主义”,“义胜利”代表“合理利他主义”,“利克义”代表“合理利己主义”。荀子以为,一个国家若是倡导“合理利己主义”,则为“乱世”;只有倡导“合理利他主义”,才是“治世”。
荀子对于“利己主义”有严厉之批评,《荀子·荣辱》云:“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正论》云:“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这是对“合理利己主义”之批评。《荀子·儒效》云:“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不苟》云:“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儒效》云:“先义而后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这是对“极端利己主义”之批评。
董仲舒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似乎表明他是“反功利”的。实则这不是他的原话,这句话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的原话载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不谋其利”,似有反功利之嫌;“不急其功”,则不宜速断为反功利。“不急”只是不把功利视为当务之急,不把功利视为优先考虑的目标,并非全盘反功利。
就算他确有反功利之言论,其所反者亦只是私利、小利,而非公利、大利。《春秋繁露·考功名》云:“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是以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为天下兴利”、“为天下除害”,讲的就是“天下之功利”,董仲舒并不反对“天下之功利”。他要反对的是在乎“多少”的那种“兴利”、在乎“南北”的那种“除害”,此等功利乃是私利、小利。
《春秋繁露·诸侯》云:“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兼利”是兼利己与利他,兼一世之利与万世之利,兼国家之利与人民之利,兼君王之利与百姓之利。故其立场应是“合理利他主义”。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云:“唯人道为可以参天: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爱利天下”就是“爱天下”与“利天下”,“变化成功”亦是言功利,故董仲舒的立场是“利天下”,并非反功利。
宋明道学中,“合理利他主义”之立场依然存在,但同时发展出一种“极端利他主义”思潮。如张载《正蒙·大易》讲“义,公天下之利”,是在不否定私利、小利的前提下讲公利、大利,是“合理利他主义”的。但其《语录》亦论及“极端利他主义”之立场:“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饥,亦不恤:惟义所在。”为了公利、大利之实现,不仅可以舍弃富贵,而且可以舍弃生命,这就把私利、小利置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境地,趋于“极端”。这个“极端”,蔚为宋明之一大思潮。
程伊川《语录》卷一六云:“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凡有利心便不可”,是对私利、小利的“极端否定”立场。“以义为利”是以公利、大利替代私利、小利,也是对私利、小利的“极端否定”立场。《语录》卷一七云:“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就是对于私利、小利的“极端否定”。
宋明儒“存天理,灭人欲”或“存天理,去人欲”之说,也常被学者判为反功利。实则仍只是一个“极端利他主义”之立场:以为实现公利、大利必以铲除私利、小利为前提,私利与公利完全对立,小利与大利完全对立,要么取“小利主义”立场,要么取“大利主义”立场,两者无法兼容。这只是一个“极端”立场,不存在全盘否定功利的问题。换言之,宋明儒讲“灭人欲”,只是讲“灭私欲”,目标是实现“公利”、“公欲”;讲“去人欲”,只是讲“去私欲”,目标在实现“公利”、“公欲”。“人欲”不过就是“私欲”、“小欲”之代名词;“天理”不过就是“公欲”、“大欲”之代名词。不兼顾私利、小利,只讲公利、大利,这就是“极端利他主义”之立场。
二程《遗书》就把公心与私心、公利与私利对立起来。《遗书》卷五云:“虽公天下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不仅“私行”不能有,连“私意”也不能有,这是很“极端”的。《遗书》卷一五云:“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天理”之实现,必以“无人欲”为前提,这个立场也很“极端”。《遗书》卷二四又云:“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消灭私利是实现公利之前提,同样是“极端”立场。
南宋胡宏《知言》云:“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无谋”是“极端利他主义”的。南宋朱熹也持此种“极端利他主义”立场。朱子《语类》卷一二云:“圣贤千言万语,只教人明天理,灭人欲。”“灭”就是“极端”。《朱子文集》卷三二《答张敬夫问目》云:“夫营为谋虑,非皆不善也,便谓之私欲者,只一毫发不从天理上自然发出,便是私欲。”不允许“一毫发”私欲,就是“极端”。陆九渊有时也持此立场,如《象山全集》卷一四《与包敏道》云:“私意与公理,利欲与道义,其势不两立,从其大体与其小体,亦在人耳。”“势不两立”就是一种“极端”言论。
明代王阳明也曾有这样的“极端”立场,如《传习录上》讲:“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又讲:“须是平时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无复纤毫留滞”,无疑是太过“极端”。恰如陈确《鼙言一》所批评的“天理人欲分别太严,使人欲无躲闪处”。然此种“极端利他主义”之立场,直到明末王夫之还有遗留,如其《思问录》内篇讲:“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其《读四书大全说》卷五更有“大公无私”之论:“奉此大公无私之天理以自治,则私己之心,净尽无余。”“大公无私”就是“极端利他主义”之典型表述。
宋明时期儒家发展出来的“极端利他主义”思潮,同时受到儒家内部“合理利他主义”之批判。北宋李觏《文集·富国策》云:“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反对“贵义而贱利”,就是反对脱离私利、小利,而讲公利、大利。其《文集·原文》又云:“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激也”,就是“极端”,李觏斥责孟子为“极端利他主义”诚然不准确,但他在此处批评了根本不言私利、小利之“极端利他主义”,却是肯定的。
叶适也以“合理”斥“极端”,其《习学记言》云:“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离开私利讲公利,是虚;离开小利讲大利,同样是虚。正确的做法是兼顾私利、小利而讲公利、大利,这被颜元称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颜元《四书正误》云:“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正其谊”、“明其道”就是讲公利、大利,“谋其利”、“计其功”就是讲私利、小利。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以”与“而”的关系,两者是可以兼顾的。这被学者称为“义利双行”,实则就是一种“合理利他主义”。
颜元《言行录》又云:“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讲公利不是不可以讲私利,只是要注重一个“后”字;讲大利不是不可以讲小利,只是要注意一个“后”字。先公利后私利,这就对了;先大利后小利,这就对了。简言之,“先义后利”这就对了。要特别注意,这里完全是以“合理利他主义”批评“极端利他主义”,而不是以“利己主义”或“合理利己主义”(“西式功利主义”只是一种“合理利己主义”)批评“极端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在中式思想系统中是不存在的,不仅“极端利己主义”不存在,就连“合理利己主义”也不存在。
总之儒家功利思想可分两派:一派是“合理利他主义”;一派是“极端利他主义”。要之都统属“大利主义”:认定“利天下”高于“利吾国”,“利吾国”高于“利吾家”,“利吾家”高于“利吾身”。
二、墨家讲“大利”
与儒家相比,墨家功利思想有两点不同:一是它只讲“极端利他主义”,不讲或少讲“合理利他主义”;二是它把“利他”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之外,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天下”之外。墨家对于儒家之诸多批评,实即是以“极端利他主义”批评“合理利他主义”。
《墨子·兼爱上》云:“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父子之间有父之“自利”与子之“自利”,兄弟之间有兄之“自利”与弟之“自利”,君臣之间有君之“自利”与臣之“自利”,所有这些“自利”都被视为“乱”,都是墨子所反对的。在墨子的理论系统中,“自利”是不能有的,“自利”固然不是目的,亦不可为手段。
墨子强调一个“兼”字,这个“兼”不是兼顾利己与利他,而只是指“利他”;不是兼顾私利与公利,而只是指“公利”;不是兼顾小利与大利,而只是指“大利”。“兼”不过就是“利他”之代名词,不过就是“公利”与“大利”之代名词。与之相对应的“别”,当然就不过只是“利己”、“私利”、“小利”之代名词。比如,“兼士”是“爱人利人”,“别士”是“恶人贼人”;“兼士”是关心他人重于关心自己,“别士”是关心自己重于关心他人;“兼士”是视人如己,“别士”是人我有别。再比如,“兼君”是“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别君”是“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兼君”倡导人重于己,“别君”倡导己重于人。
墨家功利思想完全建立在“他人中心”之上,而非“自我中心”之上。对墨家而言,“利他”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牺牲”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最大多数”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利他”与“牺牲”能够给自身带来好处当然好,不能带来好处也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墨家讲功利,遵循一条“绝对命令”:一行为是善的,当且仅当它有利于人类,同时有利于天地万物;一行为是善的,当且仅当它先有利于天地万物,然后有利于人类。我们读《墨子》一书,就知它贯彻此项“绝对命令”是非常彻底的。《墨子·兼爱中》云:“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兼爱下》云:“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又云:“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又云:“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又云:“兼者,圣王之道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节葬下》云:“且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天志中》云:“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墨子》全书始终是以“天下之利”、“大利”为落脚点,是一种典型的“大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极端利他主义”。
然则此“天下”、此“大”,究竟涵盖怎样的范围呢?其最大范围是国家吗?非也!其最大范围是人类全体吗?非也!墨子此处所谓“天下之利”之“天下”,大于儒家之所谓“天下”,是超越人类全体,超越“人类中心论”的。墨子讲功利,总是“三利”并举,人类之功利只是其中之一。如《天志上》云:“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与之相反的情形是:“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一行为仅“利于人”,还不能称为善;仅“利于鬼”,亦还不能称为善;仅“利于天”,亦不能称为善。只有“三利无所不利”,方得称为善。且顺序不能颠倒:只有先利于天,次利于鬼,最后利于人,方得称为善。
此种思维格局遍见于《墨子》,如《天志上》云:“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与之相反的情形是:“其事上诟天,中诟鬼,下贼人。”《天志中》云:“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与之相反的情形是:“观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无所利,是谓天贼。”《天志下》亦有“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之说,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之说。在“人”之上放置“鬼”这个层次,在“鬼”之上放置“天”这个层次,表明墨子之立场已完全超越“人类中心论”。
其功利思想也完全是对“人类中心论”之超越:它强调的是“三利”,而不只是人类这“一利”。“利天”就是有利于天地万物,“利鬼”就是有利于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灵,只有最后一利“利人”才是针对人类而言的。只有“三利无所不利”才是善,“三不利无所利”才是恶;不能说对人类不利的就是恶的,亦不能说对人类有利的就是善的。要以“利天”为背景讨论“利鬼”的问题,这就是“大利主义”;要以“利天”、“利鬼”为背景来讨论“利人”的问题,这就是“大利主义”。
《墨子·兼爱上》云:“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第一步是“贼人以利其身”,第二步是“乱异家以利其家”,第三步是“攻异国以利其国”,至此还没有完,还有一个“贼物以利其人”的问题。此处“乱物”即是“贼物”,就是康德所谓的以“万物”为手段,就是西式功利主义所谓的以“万物”为手段。只承认人是唯一的目的,其他均是手段,就叫“贼物以利其人”,或“乱物以利其人”。
《兼爱中》记反对“兼利”之言论云:“然乃若兼利,则善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此言论反对把“利”的范围扩大到人之外的“万物”。对此墨子反驳:“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有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墨子以为以“挈太山而越河济”来比喻扩“利”至“万物”,是不恰当的:“挈太山而越河济”,是“能不能”的问题;扩“利”至“万物”,是“为不为”的问题。《兼爱下》论及同一问题,墨子同样反对“兼者直愿之也,夫岂可为之物哉”之论。
这表示墨子始终是把“功利”问题放到大于人类的“宇宙背景”上来考量的,《天志篇》可说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专门探讨。《天志上》开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只讲“利于人”,是“知小”;不讲“利于鬼”、“利于天”,是“不知大”。只讲人类之“独利”、“别利”,不讲天地万物之“大利”、“兼利”,就是“知小而不知大”。《天志上》对“不知大”的解释是:“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不敬畏天地万物,不关照天地万物,以“万物”为手段、为工具,就是“知小而不知大。”
《天志中》又云:“今夫天兼天下以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也,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然独无报乎天,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明细而不明大”,就是“知小而不知大”。“撽遂万物以利之”,就是“大利”,就是“天下之利”,反之就是“不仁不祥”。当时“君子”不明此理,就是“不明大”。《天志下》亦云:“天下之所以乱者,其说将何哉?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何以知其明于小不明于大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得罪于天,将无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极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则不知者也。”不知“大物”,就是不知扩“利”于天地万物。
墨家之立场是强调“天下之利”,强调“大利”,强调“宇宙背景”,反对以“万物”为手段,反对只讲一人、一家、一国、一类之“小利”。“利吾身”当服从于“利吾家”,“利吾家”当服从于“利吾国”,“利吾国”当服从于“利天下”,“利天下”当服从于“利万物”。总之,墨家之功利立场是“极端利他主义”的。
三、道家讲“大利”
道家讲“大利”也是“极端利他主义”的。《老子》第49章讲“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实即强调“常无私心”。《庄子·应帝王》讲“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无容私”实即“无容私心”、“无容私利”。道家以为不讲私利、小利,才能实现公利、大利,才能实现“天下治”。
讲“常无私心”、讲“无容私”,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墨家就是这样讲的,儒家中的“极端利他主义者”也是这样讲的。道家功利思想所以能成一家言,不在于它能突破儒家的“利天下”而上达“利万物”之视野,这个视野墨家已经达到了;而在于它要完全颠覆以儒、墨两家为代表的“常人”的功利观、世俗的功利观。
它以为关键不在舍私利而就公利,关键是要弄清楚何为私利、何为公利;关键不在舍小利而就大利,关键是要弄清楚何为小利、何为大利。世俗以为络马首、穿牛鼻是利,道家以为是不利;世俗以为拦河筑坝是利,道家以为是不利;世俗以为喝牛奶是利,道家以为是不利(牛奶只对小牛有利)。《老子》第18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9章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都是针对儒家而发言,认为儒家所谓善并非善,儒家所谓利并非利,儒家所谓大利其实只是小利。
《庄子·逍遥游》曾举出三个实例,说明世俗所谓“用”其实并非“用”、世俗所谓“无用”其实正是“大用”。这三个实例是“大瓠无用论”、“不龟手之药无用论”、“大树无用论”。魏王送给惠施大瓠之种,惠施种出五石之瓠,却以为无用:“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惠施的此种做法,被庄子斥为“拙于用大”。一个东西有不有用,关键看我们如何用,而不在这个东西本身。庄子云:“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就是长满杂草的“世俗之心”,“世俗之心”以为大瓠无用,那只是因为它们“拙于用大”。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同样是“拙于用大”。他掌握了这个药方,只是用于世世代代帮人漂洗丝絮。有人发现了这个药方之“大用”,“请买其方以百金”,买断之后就去游说吴王攻越,吴王以此人为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用在甲处,它只是“小用”;用在乙处,它就有“大用”。有不有用,不在东西本身,而在用之者;有大用还是小用,更不在东西本身,更在用之者。
惠施又跟庄子讲“大树无用论”:“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就“大而无用”反驳惠施:狸狌小不小,是很小,却常常“中于机辟,死于罔罟”;斄牛大不大,是很大,“大若垂天之云”,却常常抓不住一只老鼠。小有小之用,大有大之用,小有小之无用,大有大之无用,东西本身无所谓有用无用,关键看用之者。“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三个实例之共同目标,是要颠覆世俗之“功用”观:世俗认为“无用”的,不必以为无用;世俗认为“无功”的,不必以为无功;世俗认为“不利”的,不必以为不利。道家讲功利,其最特出之处就在这里。《老子》第2章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世俗认为美的,不必以为美;世俗认为善的,不必以为善。第3章云:“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世俗以为“尚贤”是利,其实是不利;世俗以为“贵难得之货”是利,其实是不利;世俗以为“见可欲”是利,其实是不利。道家要求人们站到一个比世俗更高的平台,去审视“功利”问题,不要被私利、小利所困扰。
公利、大利之终极指向,是以“利万物”为究竟,不能仅停留于“利人”、仅停留于“人类之功利”。《老子》第8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强调“利万物”。第13章云:“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强调“利天下”。第16章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强调“公利”与“长久之利”。第22章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强调“宇宙背景”。第27章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明确认定“救人”之上还有一个“救物”的层次。第54章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明确“邦”之上还有“天下”这个层次。
《庄子·天地》亦强调“爱人利物”:“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又强调“不拘一世之利”:“藏金于山,沉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私利之上有大利,“一世之利”之上有万世之利。圣人当以公利、大利、万世之利为目标。
实现公利之办法是什么?是从私利做起吗?道家以为不是。实现大利之办法是什么?是从小利做起吗?道家以为不是。世俗认定的功利是私利,实现公利就当从私利之反面开始;世俗认定的功利是小利,实现大利就当从小利之反面开始。《老子》第2章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无为”即不为世俗之所为,“不言”即不言世俗之所言,“弗居”即不居世俗之所居。第3章云:“为无为,则无不治。”第9章云:“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含义同上。第8章云:“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先讲公利然后才能得私利,先讲大利然后才能得小利,此为典型“极端利他主义”之立场。
第13章云:“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欲完全根除“利吾身”的可能性。第34章云:“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付出还只是“小”,不占有才是“大”,此又为“极端利他主义”之论。第63章云:“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思路同上。第81章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为人己愈有”、“与人己愈多”两句,可视为道家功利思想之总结:愈讲公利则私利愈多,愈讲大利则小利愈厚;不讲公利者其私利不至,不讲大利者其小利不得。道家所以颠覆世俗功利观者,在此;道家所以成“极端利他主义”者,亦在此。
汉代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以“事少而功多”概括道家功利思想,切合道家根本精神。《淮南子》被视为汉代道家重要典籍,其功利思想是对老、庄思想之延续。《淮南子·修务训》云:“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迫而不动者。”不是不讲功利,只是不基于“私志”而讲“公道”,不基于“嗜欲”而讲“正术”,不基于私利而讲公利。这当然是“极端利他主义”的。《淮南子·精神训》又反对以世俗之功利为功利,云:“视珍珠宝玉犹石砾也,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颠丑也。”又云:“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害也。”世俗以为病的,实是利;世俗以为利的,实是害。“或欲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欲利之而反害之,欲害之而反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这就是道家所以要超越世俗功利之的理由:私利其实不是利,小利其实不是利。
四、释家讲“大利”
释家讲“大利”,最典型的表述是“自利利他”(或“自益益他”、“自利利人”、“自行化他”、“自利他利”、“自他二利”、“自他利”等)。自利者,利己也,为自身之功德而努力修行,以此所产生之善果而自得其利;利他者,利益他人也,非为己利,而为救济诸有情而致力行善。自利与利他合称二利,通于世间与出世间。小乘佛教偏重自利,大乘佛教则兼顾自利与利他,然以利他为目的。故其称佛之世界为“自利利他圆满”。②
《发菩提心经论》卷上就六度之行一一解释自、他二利之意义:(1)修行布施,能流布善名,随所生之处而财宝丰盈,此为自利;能令众生得心满足,教化调伏其悭吝,此为利他。(2)修行持戒,能远离一切诸恶过患,常生善处,此为自利;能教化众生不犯恶业,此为利他。(3)修行忍辱,能远离众恶,达于身心安乐之境,此为自利;能化导众生趋于和顺,此为利他。(4)修行精进,能得世间、出世间之上妙善法,此为自利;能教化众生勤修正法,此为利他。(5)修行禅定,能不受众恶而心常悦乐,此为自利;能教化众生修习正念,此为利他。(6)修行智慧,能远离无明,断除烦恼障、智慧障,此为自利;能教化众生皆得调伏,此为利他(第2522—2523页)。
释家讲的“利益”,实际涉及自利、利他、利生三个层次。自利称为功德;利他则特称利益,分现世所获之利益(称“现益”)与后世所得之利益(称“当益”)两种;利生则指佛、菩萨之济度利益众生,又称“利物”(以一切众生为物)。在释家之理论框架中,真正能称为利益的只有利他与利生两个层次:利他当服从于利生;自利当服从于利他。这看上去是一种“合理利他主义”之立场,实则依然是“极端利他主义”。
《坛经·疑问品》(宗宝本)记韦刺史与六祖慧能之对话云:“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各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梁武帝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是一种“利他”之行为,按理说是有功德的。但达摩大师却为何断定其“实无功德”?六祖慧能的解释是:因为这种“利他”之行为是出于“利己”之心。“武帝心邪”、“各为求福”、“心常轻人”,这就是从“利己”出发去“利他”。从“利己”出发去“利他”,“利他”只是手段,“利己”是目的,这就是无功德;从“利他”出发去“利他”,“利他”本身就是目的,这就是有功德。这表示释家是讲求“极端利他主义”的。
小乘佛教偏重于“自利”,但并非完全拒绝“利他”,其为“自利”而修行的同时,客观上也包含着“利他”之一面。小乘佛教基本方法有“五戒”、“八正道”等。五戒为: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语戒、不饮酒戒。八正道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这些方法是“自利”的,主观上是为了使自己去恶增善,利益自身;但客观上也对他人和社会有利,客观上能起到“利他”之作用。且小乘佛教之基本经典《阿含经》已从理论上提出“四摄法”、“四无量心”等“利他”思想。可以说小乘佛教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主观“自利”,客观“利他”。“自利”是目的,“利他”是手段。
大乘佛教相反,是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主观“利他”,客观“自利”,“利他”是目的,“自利”是手段。大乘佛教一方面遵循“五戒”、“八正道”之修行方法,同时对修行者提出更高要求:能为社会做点什么,能为他人做点什么。换言之,一方面讲“自利”,同时又要求修行者去“利他”;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求修行者以“利他”为出发点,以“利他”为目的。在“合理利他主义”之基础上,最好能达到“极端利他主义”之理想。于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自度度他”之菩萨行,便成为大乘佛教修行之宗旨。于是慈悲为怀、普度众生、闻声救苦之行为(观世音),“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以及大慈大悲、救度众生、利乐有情之誓愿,就成为中土佛教追求之理想。
中土佛教把布施者之动机与目的分为两类:“不净施”与“净施”。“不净施”者,为求财或畏失财而布施也,为心中有愧于人而布施也,怕死而布施也,为显示富有而布施也,为与他人争胜而布施也,为名而布施也,为位而布施也,总之为一己之私心杂念而布施也。“净施”者,纯粹出于慈悲心而布施也,不求任何报答而布施也,忘掉自我而布施也,总之毫无私心杂念而布施也。《大智度论》卷一一云:“为道故施,清净心生,无诸结使,不求今世后世报,恭敬怜愍故,是为净施。净施是趣涅槃道之资粮。”③“不净施”为凡夫布施,不应提倡;“净施”为菩萨布施,当以之为理想。中土佛教承认“合理利他主义”之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主张以“极端利他主义”为追求目标。
“自利利他”思想要求修行者“利他”时要有“慈无量心”,以无量慈爱待众生;要有“悲无量心”,以无量悲悯待众生;要有“喜无量心”,以无量喜悦待众生;要有“舍无量心”,以无量平等待众生。“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被称为“四无量”。“无量”者有三义:以无量之众生为此四心之所缘;此四心能牵引无量之福;此四心能招感无量之果。“四无量”中以慈悲为最根本。
“自利利他”思想讲到“利他”之方法,也有四种,叫“四摄法”或“四摄事”。一曰“布施摄”,以无所施之心施受真理(法施),以无所施之心施舍财物(财施),令众生起亲爱之心而依附菩萨受道。二曰“爱语摄”,依众生之根性而善言慰喻,令众生起亲爱之心而依附菩萨受道。三曰“利行摄”,行身口意善行,利益众生,令其生亲爱之心而受道。四曰“同事摄”,亲近众生,同其苦乐,并以法眼见众生根性,而随其所乐分形示现,令其同沾利益,因而入道(第1853页)。“四摄法”中以布施为最重要。
“自利利他”思想讲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视万灵为兄弟姐妹,不分亲疏、不讲条件、不计得失地去“利他”,认定利人就是利己,害人就是害己,只有在众生度尽中才能最终度己,只有先解放万灵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个人通过成就整体而实现,人类通过成就天地万物而实现,私利、小利通过成就公利、大利而实现。《优婆塞戒经》云:“自利益者,不名为实,利益他者,乃名自利……利益他者,即是自利。”④“自利”是虚的,只有“利他”是唯一的真实。中土佛教讲“大善大恶”,“损己利人”就是“大善”;“损人利己”就是“大恶”。相应地,“善”就是“利己利人”,“恶”就是“损己损人”。
换言之,在释家功利思想框架中,“合理利他主义”是“善”,“极端利他主义”是“大善”,“合理利己主义”是“恶”,“极端利己主义”是“大恶”。“大善”者,以最大之力为之;“大恶”者,以最大之力避之。要之中土佛教之理想,总以“极端利他主义”为依归。
五、超越功利的一派思想
儒、墨、道、释诸家,或强调“合理利他主义”,或强调“极端利他主义”,主体上总未脱出一个“利”字。然其中并非没有脱出“利”字之思想火花,高居于“功利”思想之上。
后期墨家之“周爱人”思想就已脱出“利”字,既不讲“利己”,也不讲“利他”,只讲“爱”。《墨子·小取》云:“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因为不爱人矣。”只有爱遍万灵,才能真正爱他人;只有爱遍他人,才能真正爱自己。“周爱人”是一种脱出“利”字的“极端爱他主义”思想。
《老子》第56章也出现过这样的思想火花。其言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玄同”是最高层次的“同”,是最大外延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视野之下,亲疏没有分别、利害没有分别、贵贱没有分别。上达利害无分别的境界,当然已脱出“利”字。
杨朱有“不以一毫利物”之思想,是“超越功利”的,却常被学者判为“极端功利”。《孟子·滕文公下》斥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是“无君”,《孟子·尽心上》又斥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为我”,《韩非子·显学》斥其“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为“轻物重生”。近世学者更斥其为“极端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实则乃是断章取义,不明杨朱思想之整体。
《列子·杨朱》载杨朱之言云:“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孟孙阳因顾与其徒说他事。”
一方面我们不能“自利”;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利物”。讲“自利”固然有问题,讲“利物”同样有问题,因为我们始终没有脱离一个“利”字。只要“利”字还存在,极小之利有问题,极大之利同样有问题。极小者“一毫”而已,极大者“天下”而已,取“天下”是利,取“一毫”又何尚不是利?从“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一句去看,我们判杨朱“极端利己主义”;从“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一句去看,我们又得判杨朱“极端利他主义”;结合两句话去看,我们就只能以“超越功利”之格式去判断他。只有一个不讲“利”的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只有一个人无需我利、我无需人利、人人自主、人人自足的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极小之利不讲,极大之利亦不讲,总之完全不讲“利”,才能真正实现“天下治”。总之杨朱之思路只是:讲利则天下不治,不管是讲“自利”,还是讲“利物”,不管是讲“利己主义”,还是讲“利他主义”,不管是讲“极端利己主义”,还是讲“极端利他主义”。放到中式思想之整体脉络去看,杨朱似乎已经大致形成一个“超越功利”的思想系统。
《吕氏春秋·重己》“利而勿利”之思想,似乎也是“超越功利”的。学者释为“务在利民,勿自利也”,总觉力度不够。如果只是“利民”而反对“自利”的意思,它为何不讲“义而勿利也”,而要讲“利而勿利也”呢?故其“微言大义”应为:即便是讲极大之利,也不如不讲利。《吕氏春秋·重己》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不长”、“不私”、“不阿”,就是不讲“利”。又云:“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得其利而莫知”同样是不讲“利”。《吕氏春秋·贵公》云:“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行其德”同样是反对讲利。
儒家内部之邵雍也曾发展出“义利兼忘”之“超功利”思想。《皇极经世书·心学》云:“君子喻于义,贤人也。小人喻于利而已。义利兼忘者,唯圣人能之。君子畏义而有所不为,小人直不畏耳。圣人则动不逾矩,何义之畏乎?”“小人”讲“合理利己主义”,不是最高层次;“贤人”讲“合理利他主义”,不是最高层次;“圣人”讲“极端利他主义”,依然不是最高层次。最高层次是“义利兼忘”,既不讲私利,也不讲公利,既不讲小利,也不讲大利,既不讲利己,也不讲利他,总之一句话,是不讲“利”。“忘利”才是最高境界。
中式思想有讲“合理利他主义”者,如儒家;有讲“极端利他主义”者,如墨、道、释诸家;有讲“超越功利”、“义利兼忘”者,如后期墨家、杨朱、邵雍诸人。唯独没有讲“利己主义”者,不讲“合理利己主义”,更不讲“极端利己主义”,这就和西式思想形成鲜明之对照。
六、以“西式功利主义”为背景的分析
近代以降西洋思想之种种努力,不过在为“利己”之行为“找理由”,为“利己”之行为“提供学理支持”。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更是如此。学者判其为“合理利己主义”,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它试图在不损害“利他”的情况下讲“利己”。但判其为“最大幸福主义”,却有不妥,因为它并不以“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为归依、为目的,而只以“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为工具、为手段。讲求“最大多数最大幸福”,只是为了增进个人幸福、保证个人利益。犹如垂钓者给鱼撒食,不为鱼本身,只为垂钓者一样,功利主义讲“最大多数最大幸福”,只为“利己”,不为“利他”,“利己”是唯一的“实”,“利他”是真正的“虚”。功利主义只在为“利己”找理由,只在为“利己”提供学理支持,所以判其为“最大幸福主义”乃是不妥的。
西式功利主义力图为“利己”找理由,为“利己”提供学理支持;而中式思想几千年下来,始终在为“利他”找理由,为“利他”提供学理支持。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系统,我们怎么可以像梁启超、冯友兰、韦政通、朱伯崑、田浩诸大家那样,拿“西式功利主义”去释读“中式大利主义”呢?就算“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可以并存,我们至少得为中式思想确立一个与西式思想“并肩”的地位,不可以自我矮化的。
亚当·斯密《国富论》之“经济人”的设定,就是力图从经济学角度为“利己”找理由,为“利己”提供学理支持。其言曰:“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⑤ 既人人自利,则利他又如何解决呢?只能通过“主观利己,客观利他”去解决:“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⑥“利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主观利己,客观利他”,就是西洋近代以降的基本理论设定。亚当·斯密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这一点,泰罗之“科学管理理论”则从所谓现代管理学的角度论证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这一点,以边沁、穆勒等为代表的“西式功利主义”则更从哲学的高度证明这一点。
“主观利己,客观利他”,是一种“合理利己主义”,西式功利思想以主张“合理利己主义”为主流,也有主张“极端利己主义”者。“主观利他,客观利己”,是一种“合理利他主义”,中式功利思想以主张“合理利他主义”为主流,也有主张“极端利他主义”甚至“超越功利”者。兹以边沁、穆勒等人之“西式功利主义”为背景,分析中西功利思想之差异与得失。其差异至少有如下方面:
第一,“西式功利主义”主张“义”对于“利”的工具地位,中式功利思想则反其道而行之。对边沁、穆勒等人而言,道义乃是谋利之工具,日常道德准则能带来利益者则遵守之,不能带来利益者则可以不遵守。⑦ 中式功利思想于“义”、“利”关系,大体上有三派主张:一曰以“义”为目的,不以“利”为手段;二曰以“义”为目的,可以“义”为手段;三曰以“义”为目的,必以“利”为手段。孔子、孟子、朱子等人代表第一派的主张,荀子、张载、程伊川等人代表第二派的主张,李觏、陈亮、叶适、颜元等人代表第三派的主张。要之中式功利思想只讨论“利”可否为手段的问题,决不讨论“义”可否为手段的问题,无一人主张以“义”为求“利”之手段,无一人主张只以“利”为目的。因为中式功利思想认定“义为目的”乃是当然,不需要讨论的,也没有讨论之余地;一如“西式功利主义”认定“利为目的”乃是当然,不需要讨论,也没有讨论之余地。
第二,“西式功利主义”主张“动机”对于“结果”的工具地位,中式功利思想则反其道而行之。对边沁、穆勒等人而言,行为之善恶只凭“结果”,不凭“动机”,若有杀人动机其结果反有益于人,则其动机非为不道德,可置而不论。⑧ 可知“西式功利主义”是一种“结果主义”,“特殊结果主义”、“利益结果主义”。中式功利思想相反,是“动机主义”、“特殊动机主义”、“道义动机主义”。“动机主义”乃是中式功利思想之主流框架。《盐铁论·刑德》云:“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此就法律方面而倡“动机主义”,且是一种“极端动机主义”。朱熹《答陈同甫》云:“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帝则和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此乃就史学方面而论“动机主义”,且以“动机主义”鄙薄汉唐。要之中式功利思想之主流是“动机主义”的与“极端动机主义”的,与“西式功利主义”之“结果主义”甚或“极端结果主义”,完全背道而驰。
第三,“西式功利主义”主张“利他”对于“利己”的工具地位,中式功利思想则反其道而行之。对边沁、穆勒等人而言,利他若损害到利己,则应放弃;讲利他,承认利他,只因不利他便无以实现利己。⑨ 关注私利优先于关注公利,关注利己优先于关注利他;公利乃实现私利之工具,利他乃实现利己之工具。私利、利己乃是“唯一的目的”、“唯一的标准”。这是“西式功利主义”对于“利己”与“利他”之关系的表达。就连号称最高理想的“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之说,在边沁、穆勒等人的理论框架中,依然是处于工具与手段之地位。⑩ 中式功利思想则反之,以利己为手段,以利他为目的,以私利为手段,以公利为目的,以小利为手段,以大利为目的。利己、私利、小利在“极端利他主义”看来,甚至连手段之地位也没有,甚至连工具之地位也没有,甚至连提都不能提。个人价值通过为家庭家族牺牲来实现,家庭家族价值通过为民族国家牺牲来实现,民族国家价值通过为人类全体牺牲来实现,人类全体价值通过为天地万物牺牲来实现。这个完全彻底的“利他主义”思想系统,不以“大圈”为手段,只以“小圈”为手段。
第四,“西式功利主义”主张“利物”对于“利人”的工具地位,中式功利思想则反其道而行之。边沁、穆勒等人几乎完全不讲“利物”,只讲“利人”,属于典型之“人类中心论”。他们有“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之设定,连人类全体都不能覆盖,何谈“利物”?何谈天地万物?“人类这一整体”、“人类整体利益”,这就是边沁、穆勒等人“理论上的最大视野”,这等视野不承认人类为“利物”而牺牲是一种美德,不承认“利人”之上还有“利物”这一更高的层次。(11)
越不出“人类中心”,乃是西洋思想家似乎永远逃脱不了的“原罪”与“宿命”。就连号称“人类最大哲学家”的康德,也无法越出“人类中心”之宿命。他撰《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提出“人是目的”这一“绝对命令”,认定宇宙中人所希望和控制的一切东西都只是手段,唯有人是“自在的目的”;人在行动时不可以视自己为手段,同时亦不可以视他人为手段,但却可以视“万物”为手段。这就把全部西洋哲学之视野规定下来:万物之存在与不存在,人是尺度;现象世界之有秩序与无秩序,人是立法者;“万物”之有用与无用,之有价值与无价值,人说了算。边沁、穆勒等人不过是从“功利”、“快乐”、“幸福”之一方面,贯彻此种“人类中心论”而已:有利于人的就是好的,就是善的;不利于人的就是坏的,就是恶的;其他动物、生物乃至天地万物,均只是人类求乐之工具。
中式功利思想却遵循着另一条“绝对命令”:利他高于利己,利物高于利人。墨子所谓“利天”、“利鬼”、“利人”之“三利”,要求“三利无所不利”,不能只讲“利人”。在理论的一个极端,是“三利无所不利”,是“三利”并举;在理论的另一极端,是“三不利无所利”,是“三利”并废。中间则有可能有一利或二利,然其中轻重必是“利鬼”高于“利人”,“利天”高于“利鬼”。天地万物不是手段,人不可以天地万物为手段;否则就是“贼物以利其人”、“乱物以利其人”。“利物”是中式功利思想之底线,是中土思想家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郡雍语)。中土思想家把仅局限于“人类中心”之学问,不称为学问,以西洋哲学术语言之,它们只是一些“意见”而已。
“际天人”而讲功利,就是立于“宇宙背景”而讲功利。这样的功利就是所谓“大利”。“大利”之作为“中华共识”,告诉我们,人类思考功利问题,不止西洋一路;人类解决功利问题,不止西洋一系。西洋一路是一条路,但也许并非最好之路;西洋一系是一种方案,但也许并非最佳方案。因为人类已来到这样的十字路口:不解决“利物”的问题,“利人”已成为“死穴”;不破除“人类中心论”,人类已走上“绝路”。“西式功利主义”把我们带到这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它已经哑口无言;幸好中国早就有一个“大利主义”,可以给人类指示一个方向,可以点这个“死穴”,通这条“绝路”。这或许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有比没有好!
“大利”之作为“中华共识”,告诉我们要善待“中式思想”,要善待“中华文明”,要善待“华夏祖先”。他们指示给我们的路,也许译不成英文,也许不时髦,但却实实在在,为我们往后的生存提供一种“可能性”。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各民族都有其特别的生存之道,“西洋之道”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唯一正确的。“大利”之作为“中华共识”,就是要破除此种“西洋唯一论”,就是要破除国人对于“中式思想”的“自我矮化”。就是要告诉世人,“利己”之上有“利他”,“利他”之上有“利物”,“利物”之上有“忘利”。“西式功利主义”未能实现功利思想的“最后一着”与“桶底脱落”,未能达至功利思想之“究竟真理”。
注释: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86页。
② 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台北:佛光山出版社,1989年,第2522页。下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③ 《大正藏》第25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2005年,第140—141页。
④ 《大正藏》第24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2005年,第1043页。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3—14页。
⑥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页。
⑦ 参见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1页;穆勒:《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页;穆勒:《功利主义》,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81、83页。
⑧ 参见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80、144页;穆勒:《功利主义》,第43—45页。
⑨ 参见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58、81页;穆勒:《论自由》,第125页;穆勒:《功利主义》,第45—47页。
⑩ 参见张东荪:《道德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第99、102页。
(11) 参见穆勒:《功利主义》,第41、121—131页。
标签: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荀子论文; 利己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