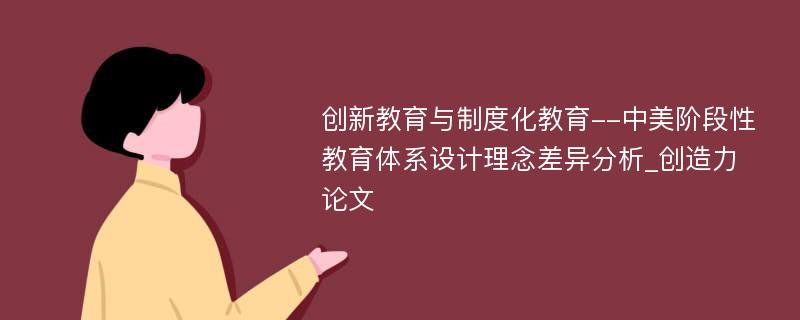
关于创造力、创新与体制化的教育——兼析中美阶段性教育制度设计理念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创造力论文,设计理念论文,性教育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1-0015-06
在20世纪90年代后,因为全球经济竞争更趋激烈,诸如“创造力”(creativity)、“创新”(innovation)等概念,不仅在教育界、企业界极为流行,就是在各国政府部门的官方话语和文本中也频繁出现。然而,究竟什么是“创造力”和“创新”?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其概念的所指究竟是什么?迄今人们似乎并无共识可言。本文在此并无意纠缠于两个概念在学理层面上的复杂解释,而是试图从常识以及当前特定语境分析角度,给予必要的澄清和说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美阶段性教育体系与体制间的比较,就教育对人的创造潜能开发以及它对整个社会创新活力培育所发挥的功能差异,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分析。最终目的是为我们反思创新人才匮乏、创新活力不足与教育体制所存在痼疾间的关联,提供一个观察和分析的视角。
一、关于“创造”或“创造力”的内涵
关于“创造”,用英文更为准确的表达是"creativity",转换为汉语表达,它涵盖“创造力”、“创造性”和“创意”等多种解释;我们常提到的“创新”,有时也与“创造”的概念间存在混淆,而在英文中多采用的是"innovation"概念。因此,两者间在概念内涵上应该有所不同。关于"creativity",阿比农(Joseph Abinun)曾就教育界的各种界定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如果它是“产出某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新事物的能力”,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知道“此前未有”?如果它指的是“一种不期然的、令人感到神奇和好奇的认识和理解”,即带有心理学倾向的“灵感”概念,问题在于这种“灵感”往往与现实和实践间存在非常弱的联系;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人们不遵从某种已知或预期的规律”的习惯,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如“癫狂”、“任性”、“心不在焉”和“错觉”等不合常理的思维是否也属于“创造”特质?还有人认为,它是在自由状态下的一种自我表现,如所谓的创意,但问题在于这种表现或创意是否有价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1]总之,以阿比农较真的方式来理解“创造”,几乎它就是一个不可界定的概念。
的确,无论是从规范性、描述性以及可操作性的角度,要给出"creativity"一个严格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何心理学界如吉尔福德(J.P.Guilford)、托兰斯(E.P.Torrance)等关于创造力的评价和测试,曾经风行一时但后来其影响逐渐式微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么不妨让我们回到常识或者日常经验。在现实中,为何人们相互之间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譬如有人“点子多”,新招和奇招迭出,而有人则更拘泥于惯例;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之间,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彼此间思维上存在的众多差异,譬如已经有众多研究表明,中美学生在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角度、想象力、批判意识间就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对各种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间思维差异暂且不做价值判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无论是个体还是不同国家国民间各种差异存在,的确表明有一种关联到人的个性、想象力和思维方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创造力”的潜质存在,它是内隐的甚至是不可名状的,但是可以通过人们的言行得以表现出来。而且,不独于此,它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性(或国民性)差异,又表明创造力并非先赋之物,而与文化、制度尤其是教育等后天环境间存在高度关联。即使认为"creativity"太过于复杂、以至于成为一个不知所指的心理学行话(jargon)的阿比农,在消解了"creativity"的规范性定义时又认为,对教育者而言,应该关注一些可替代"creativity"的概念,譬如“精神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思考”、“想象力”、“激情”和“审美情趣”等。[1]而在此,如果他所提到的这些替代性概念成立,是否我们又不妨把上述概念统统归于“创造力”所应具备的潜质甚至等同于创造力?抑或把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名状和界定的创造力的基本构成因素。
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创造或创造力本身所存在的个体差异。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潜质,它其实存在于所有正常个体之中,并往往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得以体现,通常表现为人们应付或适应日常生活中困惑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但是在一般人的创造力之外,还有一种非凡创造力(extraordinary creativity)。克拉夫特(Anna Craft)对此进行了区分,她认为:“非凡创造力是那些能够改变知识或者我们世界观的、并为人们所称道的特殊类型。”对于这种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或创造力,她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概括为如下方面:“取决于人的素养、特性,人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特定环境,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类型,以及创造性行为发生的社会制度。”[2]非凡创造力的极端典范,如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科学家。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创造力与非凡创造力之间未必存在一个清晰的界限,而是一个连续体。[2]甚至,两者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日常生活中总是因循守旧、恪守陈见的人,在思想、文化和知识上能够有卓越的创见。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创新力还是非凡创新力的获得,其实都无法超越于个体所置身的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当然更与体制化教育,包括上述阿比农所提起的教育者所应关注的概念(价值取向)间存在关联,后文将对此展开专门论述。
二、关于“创新”的内涵
关于“创新”(innovation)与“创造”(creativity)的区别,创建了"Creativity at Work"网站的奈曼(Linda Naiman)女士认为:“‘创造’涉及两个过程:思考(thinking)与创作(producing)。”而“‘创新’则是产品和理念的落在实处。”她进一步指出:“如果你仅有理念,而不去行动,则只具有想象力而不是创造力。”[3]与之观点基本相似,达特茅斯商学院的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教授认为,“创造”主要是指一种理念,而“创新”是这种理念的得以实施后的产品。[4]由此,不难理解,创造与创新虽然不同,但是两者间却须臾不可分,创造或者创造力其实是一种能力或倾向,其产品是精神性的诸如思想、知识、理念、方法、风格和品位等等,这种能力以及由其形成的精神产品是创新的前提。创新可以是物质性的、技术性或制度性的,它带有应用和实践特征。一个人如果仅有创造力而无创新,他充其量是一个空想家或者理论家,而一个社会若如此,则未免会失之空疏和浮泛。因此,创造力最终必须转化为创新才有价值,而反过来,如果仅高调地提创新而漠视甚至抑制创造力,创新就失去了它得以发生的前提。
与对创造力的理解一样,关于创新,也存在一个一般日常生活中的与具有更为广泛社会影响的差别问题,日常生活中的小制作、小发明与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甚至文明的变革性创新间可能存在影响力的差异,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却也未必存在质的不同。小发明往往孕育了大型创新的胚芽,人们赋予创新型社会的标志往往是一些显赫人物和相关重大领域的成果,岂不知这些重大领域的成就,有可能就是来自不知多少无名者在前赴后继的大胆想象、试错过程中所累积的知识、教训和经验。回顾20世纪初以来整个人类科技进步过程,我们也不难发现,为我们今天人类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技术创新,相当部分都来自我们可能并不熟稔的人物和小企业。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曾理出了一份20世纪来自美国小企业的众多重要创新清单,阅读这份清单,对于创新我们也许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空调、航空客运服务、飞机、胶膜人造皮肤、装配流水线、磁带录音机、人造树胶、生物磁性成像、生物合成胰岛素、电脑化血压控制器、连铸、采棉机、DNA图谱识别、便携式计算机、大型计算机、超型计算机、个人电脑、静电复印术、偏振光照相机、直升飞机、CAT扫描器、核磁共振、起搏器、口服避孕药、光扫描器、集成电路、肾结石激光术、X射线显微镜、高清CAT扫描仪……”[5]
鲍莫尔(William J.Baumol)在解读这份清单时,提出了他对创新的独特理解。他认为,这些小企业大多是由独立的革新家(发明家)所创建的,而正是这些革新家发起并担当了众多具有革命意义上的创新。所谓革命意义上的创新就是多少有一点惊世骇俗、戏剧性或者让人不可思议的味道,如莱特兄弟早期的飞机设计和发明,它开创了一个足以改变人类生活甚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产业。而与这种创新不同的另外一种类型,在他看来则是常规性(routine)或者渐进性(incremental)创新,相对而言,这种创新活动更为普遍,它多由大型企业中拥有众多接受过学院教育、有高学位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工业试验室所承担并完成的。尽管常规性创新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但是相对于前者,它们多少失却了些“梦幻”和“引人入胜”的效果。[5]不过,无论是常规性的创新还是革命性的创新,在鲍莫尔看来,都与教育存在关联。
三、创造力、创新与体制化的教育
无论是创造力还是创新都是非常复杂的心理和社会活动,因为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实在太多,其中包括个体先赋性的、后天的以及社会性的,等等。如上所述,既然对于创造或创造力几乎无法界定,我们不妨抛开各种复杂的学理解释和因素分析,回到常识,仅仅从阿比农所提及的几个可替代性议题角度来阐释创造与教育间的关系。首先,阿比农所关注的“想象力”、“激情”和“审美情趣”等关于创造力的义项,究竟与教育存在什么关系?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周遭世界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就一般情形而言,人对外在于其自身的世界越无知或困惑,他就越会充满着好奇和想象,并焕发出去努力摆脱这种无知的激情。因此,在关于原创精神上,人的成长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个悖论,即他越“有知”,尤其是对事实性(fact)的知识掌握越多,他的想象力和发自好奇的激情,就越有可能受到牵制。而吊诡的是,体制化的或正规的教育过程往往所特别关注的就是事实性的“科学”知识,对于这种正规教育,正如有人评价到:“究竟之于学生的创造力培养有多大贡献,迄今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很难否认,由于受强大的同质化和水平测试影响,学校教育往往趋向于妨碍人的诸如好奇心、原创力、想象力和独创精神的养成。”[6]如果再辅之以刻板性的规训、强制性的灌输以及各种或潜隐(如区隔、贴标签)或公开的惩罚,我们不难想象,这种集体性的教育生活之于人的激情和想象力所带来的可能是何等巨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即使深谙这种体制化教育的负面影响,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无可选择。人的成长不可能超越于他所置身的社会条件、文化和文明以及既有的知识传统,完全信马由缰、不着边际的想象力大多时候不过是臆想和妄念,而总是停留在常识层面上的好奇和求知激情难免有幼稚之嫌。所以,为缓解既有知识传统之于人的创造力所带来的桎梏,“精神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思维”又是必不可少的解毒剂。所谓精神独立,其实主要是指涉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独立思考,反思或反省则是主体对自我认知和实践的检讨,而批判性思维或意识则表现为个体的一种质疑倾向、态度和能力。上述所有议题其实都关联到教育过程中人与知识间的关系内涵,即人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去主动介入到知识活动和教育过程之中,还是为既有知识所牵制,成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和教育的施受者。精神独立、质疑和批判赋予人以对既有知识的审慎态度,避免了盲信和盲从,不过,由于理性与事实、逻辑性的知识或者说学术性的科目间存在天然的渊源关系,它又很可能消解了人所与生俱来、不受羁绊的想象力和无知无畏的激情。没有想象力和激情的理性求知,即使带有批判和质疑取向,其是否带有创造性是存疑的,至少也是大打折扣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在科学中,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7]
正因为如此,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对于所谓带有“科学”标识的学科性知识,过早地让学生形成一种书本知识就是真理,甚至以标准化、刚性的测试和刻板的训练来强迫学生就范,这对创造力之培养无疑是一个灾难。著名的科学家邦迪(Hermann Bondi)所言:“关于科学,有个认识非常重要,它根本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毋宁说是一个谁的更有效、谁的更能让人欢欣鼓舞、谁的有助于对事物认识的进展问题。众多的证据表明理论都是临时性的。”[7]始终带着理性的审慎、怀疑和批判,同时又借助丰富想象力来另辟蹊径,这其实就是一种所谓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创造力。而在此如果要避免“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和激情不被“脚踏实地”的理性所扼杀,人的审美情趣养成又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无论是对纯粹艺术还是科学,如果没有审美所带来的持续性愉悦和对习以为常的事实和常识的超越,想象力和激情就会枯竭,理性就成为人自由意志和精神的冷酷牢笼。即使被视为理性的科学,没有“可爱”所激发出来的求索动力,恐怕它也永远难以抵达“可靠”的彼岸,因此王国维先生的“可爱”与“可靠”间未必一定存在矛盾。
总之,由上所述,想象力、激情、自由独立精神、反思和批判精神和审美情趣等等不同义项,在人的创造力开发过程中可谓缺一不可,它甚至是一个社会思想、精神、观念、文化、知识和风尚嬗变或转变的动力源泉。但是,更多局限于精神层面的创造力激发和维系,或者说创造力要真正能够转化为创新并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却离不开一个更为关键的环节,这就是特定的环境和氛围支持。克拉夫特认为,教育过程中激发创造力所必要的组织氛围包括:“新想法能够得到鼓励和支持;能够获得相关的信息;能够与他人间形成互动;能够容忍不确定性并鼓励冒险。”[2]概括而言,学生创造力潜质的挖掘不仅需要教育过程学校能够给予学生以精神激励,更需要创设一种宽容的、设疑的互动情境和提供实践所必要的信息和物质支持。一种仅仅关注于书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而不是允许学生通过实践去质疑、检验和发现有可能书本外新知识的学校环境和教育体制,在现代高风险社会可谓是最没有希望的。正如欧洲大学协会在倡导创造力和创新应该成为大学教学和研究核心时指出:“未来复杂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书本知识’得以解决,而是需要创造性的、向前看的个体和群体,他们不惧于质疑既有的思想和知识,如此才能摆脱未来社会的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8]
四、比较与反思:中美阶段性教育制度设计理念的差异
我国学生的创造力究竟如何,一个最近被媒体广泛传播关于我国学生在国际上想象力垫底的报道,因为出处不详我们无法得到确证。但是,如果以在当今世界最具创新活力的美国为参照,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创造与创新能力上与之相比,差距实在太远。对此,多年来,人们往往把问题或归咎于高考制度或高等教育,甚至是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这些归因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诉诸环境与文化传统带有典型的宿命论色彩,一味指责高等教育或者仅在高等教育阶段频繁强调创新型人才培养,却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如果在基础教育阶段人的创造力已经被抑制和扼杀,高等教育的亡羊补牢又有多大功效?刚性的高考制度固然难脱其咎,然而,美国社会虽然没有官方主导的统一考试制度,民间考试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竞争性的选拔、筛选和“指挥棒”功能。因此,上述各种归因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并没有触及到体制化教育的痼疾,更无法为我们解决这一痼疾提供一套手术方案。
审视美国整个教育体系,其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由幼儿园、中小学到高等学校,美国的教育经过了一个由“松”到“紧”、由“放任”到“收敛”、由关注所有人权利的平等到强调优质资源分享过程中激烈竞争的渐进过程。在初等教育时期,尤为关注儿童与创造力有关的想象力、好奇、激情和兴趣的呵护、激发和引导,而淡化刚性的规训和考试。在此,以纽约一所名校——实行幼儿园到12年级一贯制的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附属学校为例,透过其不同阶段的课程设置内容和目标,也许我们自有一番体会。
在幼儿园和小学教育阶段,该校课程就分为核心(core)课程和专门课程(specials)。幼儿园阶段教育的核心课程强调幼儿对事物联系的分类和识别,并引入问题解决观念;小学1-3年级强调区分不同学生的才艺,给予个别化指导,并开发语言能力;4-6年级开发学生的研究和动手实验能力,使之能够成为独立的研究者。最能体现其教育价值取向的是专门课程,包括:视觉艺术、工作室艺术、外语、数学实验室、音乐、体育、科学、图书馆、棋艺、文化(多元)艺术、计算机与技术等,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艺术”范畴,工作室艺术提供各种泥塑、木工等各种材料,常年供学生自由制作和创作。换言之,想象力、审美情趣和兴趣培养为该阶段教育的重要特色,与此同时,也尤为关注孩子的问题自我探究和解决能力、自己动手设计能力。
从8年级开始,实行学分制。除了必修课如艺术、科学、社会研究、英语、体育卫生、数学、外语以外,开设大量选修课程。仅以高中11年级和12年级为例,艺术和音乐选修课多达22门,英语类选修课23门,社会研究20门,外语33门,数学与计算机20门,科学24门。累计142门,如此之多的课程对于我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此期间,除了依旧重视艺术对人的想象力和审美情趣培养之外,开始根据个人偏好、兴趣和天赋给予不同的选择,一些课程甚至在我国属于大学层次,譬如为有数学天分的学生提供的微积分课程便有6门,科学课程中甚至有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9]
作为一所每年向美国常春藤大学输送大量毕业生,并拥有大批知名校友的亨特学院附属学校(公立),相对于其他一般中小学,学术色彩要浓厚得多。然而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我们可以理解美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早期相对宽松(其他一般学校更为宽松),充分尊重个体选择和发展,然后到高中后期逐渐强化高等学校入学竞争的阶段性教育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凸显了人在不同成长时期的创造、创新能力与品质开发和培养的特点,譬如幼儿园到初中,尤为关注想象力和审美情趣;高中晚期和大学,重视与知识有关的理性反思与批判、精神自由和独立。而尊重个体选择、提供广泛的课程内容、强调问题解决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基本贯穿于个体的整个正规教育生涯。
相对于美国的基础教育,在我国,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大班开始,刻板性、规范化的语言训练、数学演算(而不是应用)、寥寥可数的几门主干课本知识的掌握就几乎构成学生学习的全部。熟记课本知识并获得高分数成为学生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在美国中小学中主要指个体首创和创造力的表现)的唯一形式。譬如,不久前,笔者的一位同事曾参加一面向全上海优秀小学生的英语口语竞赛,竞赛中出现的一个场面却不得不让我们震惊。当问及“如果让你送给妈妈一份心爱的礼物,你会送什么”时,高达2/3的人回答是“考试高分数”。难以想象,在一个校长迎合教育主管部门、教师迎合校长、学生讨好教师和家长的链条中,在一个一以贯之的分数主义持续高压下,学生的想象力、激情和兴趣其实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已经枯萎,更遑论精神自由和独立、理性地质疑和批判精神,甚至过早地出现了厌学倾向。一位家长曾对笔者感叹到,她的儿子一直非常叛逆,高考结束之后,他恨不得把所有以前的课本和考试材料付之一炬。
上述来自学生的极端反应其实印证了我们当前体制化教育的痼疾,从小学便开始的高强度、刻板性学术化规训、技术性训练,虽然不能说一无是处,譬如相对于美国,我国中小学生在基本知识和读写技能、甚至艰深的奥数训练方面,平均水准的确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为这种学业成绩平均优势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优胜者不优,能够鼎立国际学术界的卓越人才寥寥,大多所谓优秀人才也不过担当了国际科技走向的追随者、仿制者角色,或者充其量是鲍莫尔所提到的在大企业中从事带有“打工”性质工作的高学历常规创新者。对于这种中小学时期国家间学业成就差异,鲍莫尔曾予以了颇意味深长的推断性分析。他发现,与欧洲和亚洲等国家相比,美国中小学生在数学、物理和其他科学或技术学科方面国际测评成绩的确始终处于落后位置。然而,美国在Ph.D训练上的优势却举世瞩目。尽管美国招揽了不少其他国家最好的学生,但不可思议的是,似乎原创性和有价值的论文也多出自美国毕业生之手。究其原因,在他看来就是过于关注现有知识掌握的正统教育,妨害了学生的异端思想生成和突破性方法路径的采用。他甚至认为,正是非刚性化和强制性的教育体制,为美国社会注入了创造的活力,也为美国培养了大批独立的创新型企业家和发明家。[5]
当前,人们在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吁求中,更多把焦点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高等教育。的确,在教育理念、跨学科或通识教育、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教育管理制度等等方面,高校在学生批判性思考和质疑精神养成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我国国家创造力水平低下和创新人才匮乏的源头还需要追溯到早期教育尤其是中小学阶段教育,如果不在根本上变革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理念、校长办学理念和教师教学理念,如果不在根本上变革目前僵化、刻板的以书本知识为主,强调基本功训练的教育模式,从幼儿时期就开始呵护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激情、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我们的学生很可能在未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时,其创造力就已经被抑制甚至扼杀,所谓对创新型人才的企盼则更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美基础教育制度设计理念的根本性差异就在于:以升学为指向的我国教育制度,从一开始就把每个人定位于学术人才(诸如科学家、文学家)来培养,但在重知识传输的过程中却忽略了学术人才所应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更忽略了人的个性和品质多样化的丰富生动样态,其结果是尽管也培养了一批训练有素但原创精神明显不足的学术人才,但绝大部分人却极有可能为这种早期刻板的学术训练付出了创造之花凋谢的代价;美国的教育制度设计理念则遵从了由培养个性化的、懂得生活的普通社会公民到允许学生根据各自偏好各取所需,并逐渐分流注重自我发展的线路,虽然在阅读、科学、运算等基本训练上表现一般,但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刚性的、规范训练所导致的人的创造力和创新实践能力被抑制的后果。因此,正如我们现实中所看到的情形,这种分流不仅让少数学术人才脱颖而出,也培育了大批敢冒风险的发明家和创新型企业家,而更多的则成为日常生活中不乏创意和动手实践能力的常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创造力和创新活力,其实不仅仅端赖于少数精英,而更要依靠普罗大众的创造性和睿智,尤其在一个知识获取越来越容易、自主性学习越来越普遍的当今世界,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比既有知识掌握远为重要得多。
因此,面对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势,笔者以为,人们虽然意识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开发上的不足,但是,如果不回头全面检视时下我国基础教育所存在的缺陷(可怕之处在于,很多人还依旧认为我国基础教育是成功的),未来的情形或许会让我们更为忧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