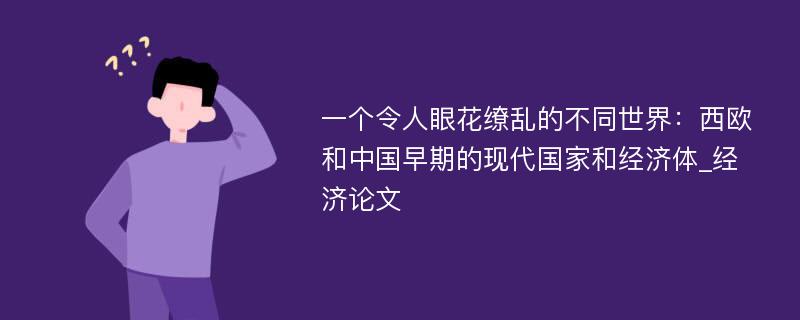
令人瞠目的不同世界:西欧与中国近代早期的国家与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N00 N10 N40 057
“…商业体制…是资本主义学会走路的拐杖。”
——E·诺曼·郝伯特,《日本以现代化国家的姿态出现——美济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纽约, 1946,第10页)。
“重商主义是所有成功的资本主义的根源,这一事实常被忽略。”
——埃瑞克·S·瑞耐特,《富国如何致富》,《经济政策历史论文汇编》,2004年第1期(萨姆环境与发展中心,奥斯陆大学,2004,第13页)。
引言
在西方历史的记载中,中国在19世纪的后10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早期阶段大约从15世纪晚期到19世纪头10年。在本人从事的经济史研究中,发现许多作者都不再把中国描述成为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样子,即清朝鼎盛时期的落后与贫穷。相反,他们现在把中国和西方看作是惊人的相似①。这一所谓的欧亚发展相似观,借用彼得·C·皮杜对其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②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杰克·古德斯通甚至给其定义为“加州流派”,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处在两个极端的欧亚在近代早期的发展和财富状况上非常相似,曾一度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独有的特性,现在看来只是持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们的臆想而已③。
对于中国明清时代经济历史的学术关注早已在西方的历史史料中被尘封起来。很久以来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数不胜数。在全球经济历史的新领域中,中国不仅值得认真研究也应恢复其本来面貌。特别是那些不了解中国帝王时代的人们不断地简单复制着有关中国的负面说法和早已过去的历史,这种观点理应得到及时的修正。但我还是害怕那种学术界的惯性思维会导致其将错就错。正如现在所做的那样,打破传统做法中只把目光排他性地并几乎带有强迫症意味地集中在(处于匮乏状态的)“东方”和“西方”的比较研究上,这种良好的期望必定不会让我们漠视确实存在的那些主要差异。只埋头于机械地研究中、西方的相似性的学者们将不得不用“偶然”、“巧合”等字眼来敷衍不容否认的19世纪东、西方历史演进轨迹的巨大差异,确实有许多人也在这样做。④从个人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并不是解释历史上中、西方演化轨迹出现显著差异性的好方法。虽然偶然性在历史上通常起着不容置疑的作用,但解释重大的转折则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就这些演化轨迹的重大差异性而言,它意味着最初条件中的主要区别。本文将要探讨的这一“差异”或许是“大分岔”的重要根源。
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及功能
我认为中、西方经济中真正的区别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在本篇文章中我将阐明中、西方在这些方面的本质区别。本文将就国家对欧亚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展开探讨,重点是放在它惊人的不同点而不是相同点上。
在这样两个巨大的实体之间进行系统的比较并非易事。为条理清晰,我按地域和时间以及相关的话题,进行切分。地理的划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洲或者西欧不象在其他领域,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相当重要,因此把整个欧洲或西欧作为研究对象没有太大的必要。也因此,我将把英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因其在许多方面具有某种普遍性或典型性,尽管在某些方面它也有其特殊性或极端性,但在其他方面却是例外。同时我也会推及到其他欧洲国家以便扩大(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我的研究将表明,虽然欧洲诸国之间的区别较大,但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中国进行比较意义依旧重大。基于上述原因,我还是把西欧当作我的主研究对象。然而,如果读者简单地把其理解为“西欧国家”,那就真是误入歧途了。
从时间上,我将把中心放在“漫长的18世纪”。它指1688年以后的英国,那时恰逢英国大革命之时,英国的许多重要体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直到1849年,那时“航海法”刚被撤销,英国新的经济政策业已启动。显然,中国的清朝将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始于17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刚刚平息“三藩之乱”,清廷开始有效地治理中国。19世纪40年代,中、英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历史时期开始了。本文将从两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方面将主要关注国家的“硬件”和“基础设施”,重点研究中央政府的收入、开支和人员、市民以及军队;第二方面研究对经济决策产生影响的国家政策。
本文以描述为主,并尝试精确的量化方法,来解释中国和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区别究竟有多大和有多重要。我确信分析“大分岔”的重要原因一定会立足于研究这些不同点。换句话说,这些不同国家历史路径“分岔”的演化所带来的或可能产生的影响将会是我的另外一个研究主题。当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把某一问题阐述详尽时,他肯定会付诸努力的。除了一些个别情况外,我将大量引用英国的出版物,并尽量展现本研究主题的西方学术前沿。研究中国内部国情将会对我的专业知识带来很大的挑战,然而我乐此不疲。
传统观点:一个开放、自由贸易经济条件下的英国
许多读者或许惊讶于我对中西差距之大所给予的关注,特别当我谈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时更会“放大”他们的这种惊讶程度。关于近代早期“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的研究中,是不是会有许多学者乐于把清廉和精于政务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和“东方暴政”的代表国家中国进行比较呢?为了找寻答案,我将结合传统观点,从历史角度出发,用日趋发展的视角来研究东、西方的历史演化路径的分岔。
早在1723-1790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指出,“除了和平、低税和一个可以让人平和地生活下去的公正制度,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或力量可以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带到最高程度的富裕文明。”⑤不幸的是,不仅有许多学者深信斯密的学说,还有很多人加入到接受他的观点或思想的行列。事实上,许多人一直认为,作为西方崛起的工业化代表英国,其崛起得益于它的统治者认真采纳了斯密对过多的政府干预和重商主义予以抨击的意见,这隐含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解决一切的。⑥依“斯密派”的观点,英国在西欧获得其特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工业化所带来的骄人成绩,总的来说,来源于其长期以来奉行并实践自由的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阿诺德曾给19世纪80年代的“工业革命”作过高度概括,他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中世纪的那种曾经统治过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制度被自由市场的竞争体制所替代。”⑦这种观点,即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作为能够积极发展时期的一个特殊案例,最好的解释就是“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公众的市场意识。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帝王时代之所以没有实现工业化的疑问就似乎迎刃而解了。他们只需要承认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东方暴政”的典型。这一论点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马可·波罗时代。⑧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过精心和系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欠发达是“高压(极权)政府”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果,这已经成为专家一致认可的解释。⑨
关于“西方如何致富”的问题在很多出版物上都可以看到“斯密派”的观点。当然,我们会发现,这些文章之间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文章,最后都要涉及到一个“强而有力”的结论,那就是,导致西方经济世界之所以发达而强大的主因,就是它无一例外地实行了自由的市场机制,这种观点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了。⑩这一系列原因的背后可以到戴维·兰德斯的《国家的贫穷与富有》、《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之大》来找寻答案。(11)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他的论著毫无疑问是西方崛起的最好注脚。关于西欧或者西欧新教派尤其是英国新教派的工业化以及为什么(英国)比想象的更加富有,戴维的解释是多方面的。但在此过程中他强调国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命题体现在他的英国如何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广泛论述中。根据他的研究,工业化只有在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市场机制才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其作用。(12)他认为,市场的作用是欧洲“个别化”、“特殊化”的核心。政府的功能就是创制市场经济体制并为市场运行提供必要的制度条件。当他想得知欧洲创建文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时,欧洲的独有特色及工业化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为他提供了圆满的答案,他在文章中总结到,“最后…我还是要强调市场的作用。在欧洲,企业享有充分的自由。政府鼓励革新,政府及相关团体对市场的干预活动和对革新的消极态度得到了抑制。”(13)我敢肯定,他的论述和威廉·易斯特里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富国拥有市场的自由,穷国拥有官僚的专制。”(14)
这一经典论述经常被持有古典或新古典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所拥趸:自由和完全竞争这只无形的手是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保证。几十年前,所谓的“新体制经济”对西欧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让我们重拾经济发展的历史,虽然经济史学家比一些“冥顽不化”的经济学家更能意识到体制或制度的重要作用,而后者只能靠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同行们的提醒才能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道格拉斯·诺斯,作为一名主张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和其他经济史学家一样,发表了大量关于西方崛起和英国经济发展方面的论文。(15)他的研究预示着改造或革新经济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虽然这样说起来有些夸张,但诺斯与他的同行们在推进新古典经济学并扩大其理论的解释基础方面一直默默耕耘。在国家作用的论述上,他比“斯密派”的那些学者走得更远,其观点更加详尽和精炼。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诺思与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们在论述或理论阐释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他们的分析逻辑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6)
传统的观点:一个帝国时代主张暴政和“东方化”的中国
在对中国帝国时代的经济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观点依旧在干扰我们的视线。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出版物把中国的清朝描述成一个充满“暴政”和“落后”的时代。在兰德斯描述西方如何崛起和东方如何落后的论述中也持有同样的传统观点。在他的作品中,中国的清朝是一个充满暴政甚至极权主义肆虐的国度。他认为,在中国的清朝或帝国时代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都是被反对发明和革新的统治者左右,企业的发展受到压制,对外国的影响持消极态度。他认为整个帝国在各个方面都无法和西欧相提并论。(17)兰德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学家爱丁·波兰兹的影响。(18)爱丁的论断对20世纪在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佛纳德·博拉戴尔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在佛纳德的著作中,无一例外地也把中国清朝描绘成“没有变化”且“不求变化”的一个朝代,它更象是一个高度集权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密封容器。(19)在他的同事阿兰·皮睿菲特发表于1989年的一本畅销书中,同样把中国看作是“不思进取的帝国”。这本书还提及了1792年到1794年英国使者出使中国所看到的“两个文明的冲撞”。(20)这样类似的观点举不胜举。埃里克·琼斯(EricL Jones)关于欧洲奇迹的著名著作中 (1987,165),作者引用了温武德·雷迪(Winwood Reade)写下的一句话:“财产是没有保障的。这个阶段是亚洲全部历史的充分写照。”(1925,108)(21)
关于中国近代早期的发展,在西方史料中,无论是马克思学派还是斯密学派,就此问题所展开的论述分歧越来越小。正象19世纪那样,持两种政治观点的学者始终认为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政府是暴政和极权主义的代表,并坚信无论它做什么,都不会带来发展,更枉谈在这样一个社会与经济体内部会产生出一个资本主义来了。然而,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西方学者对此类观点不以为然。马克思学派的历史学家如黑尔·盖茨、苏切塔·马祖达、罗伯特·布莱尼和克利斯特法·伊斯特,当他们谈论起中、英之间的差别时,会从诸如生产方式、财产关系、土地所有权、等级制度和政府在维持或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诸多方面,来观察这两种迥乎不同的社会在历史演进路径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性。(22)新马克思学派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他颇具影响力的关于现代世界体制的著述中对这些老生常谈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帝国时代确实没有象16世纪的西方那样使资本主义得以动态发展:“一个帝国如以政治为中心必有其利弊。利在于通过强权(贡物和税收)可以保证经济的流向从边缘向中心汇聚,并且获得贸易上的垄断优势。弊在于官僚会使更多的利润流向政府,特别是压迫和剥削导致的民变会增加政府的军费开支。”(23)文章的后一部分当提及中国清朝时,几乎每一个观点都和上述观点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英国的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比任何人都付出得更多,以期望改变人们的传统看法,特别地,当他考察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时,受到了历史上拜金主义的影响,指责中国科技的发展受到的抑制应该归咎于它的封建官僚体制。(24)自从马克思针对中国著书立说以后,这一观点始终没有改变。
非同寻常的视角:英国军国主义的财政策略和中国悲天悯人的家长式的农业制度
根据最新的一项有关英国和中国的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献的调查,我们发现,来源于19世纪的许多陈词滥调继续被不厌其烦地如法炮制。至少部分解释来源于我上文提到的那些老生常谈:它们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就何为“有效治理”和“高效经济”的认同一拍即合。没有任何流派的社会科学家们能够脱离这类传统观点的影响。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国家会极大程度地使竞争更加自由和公正,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平稳运行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就象一只“无形之手”,会使价格更加公平。毫无疑问,人们在这些文献中一定会注意到“新自由”或者目前的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即“华盛顿共识”。(25)如果出现了什么差错,国家就会为破坏这种规则而难辞其咎;如果经济发展顺利,那肯定就是清正廉洁的国家的功劳了,国家的标准角色就是“守夜人”,不干预市场,但要为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制定政策。勿须调查,对这么明显的问题还用得着持怀疑的态度吗?
“斯密派”学者一直把重心放在市场机制、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上,但解释西方崛起的问题并没有在西方学者中产生什么巨大的影响。它与马克思学派的观点一直分庭抗礼,后者对“原始积累”和(国家权力的)“强制原则”的论述反倒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对(国家的)“有形之手”,即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学者们一直把它作为探寻西方财富本质和根源的重要依据。象埃里克·威廉姆斯这样的学者,他本人认为谈论英国资本主义就是要涉及到奴隶制,(26)有些学者借用沃勒斯坦的论点解释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应和其他“边缘”地区的欠发达对应来看。(27)并非巧合,埃里克·霍布斯曼把其著述冠名为《工业和帝国》,(28)这本书讨论的是1750年到1968年间英国的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帕特里克·奥伯兰近期提到英国历史时也认为,贸易、经济、国家财政和帝国的扩张密切相关,他的这一观点被很多人认同并不断被更多人接受。他同时阐明持有上述观点的人并非是马克思的忠实信徒或极端左翼分子。(29)特别地,在约翰·布鲁弗在其所著的《力量的来源:战争、金钱和英国》(30)一书中就明确说过,对“漫长的18世纪”中的英国经济来讲,那种“国家的作用相当微弱”的观点一经面世即遭到广泛质疑。相反,对布鲁弗所说的,“英国是一个繁荣的而且十分重视军事财政策略并极力发挥国家的重要作用”的论点,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许多研究近代西欧演进史的学者们不再低估西欧经济历史中国家的作用。在许多研究中国清朝的历史学家中,我们也能发现他们在观点上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与“主流见解”持相反意见的新论述的产生与发展。例如,在描述清朝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些学者不再简单地把清廷说成是暴君,是抑制经济增长的刽子手,是经济发展的反对者了。 过去那种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极具“东方化”的国家,暴君的统治一直干扰着社会的发展的观点也已经越来越过时了。许多学者不再相信中国一直有一个清一色的、前后一致的并且总是反对贸易和反对通商的政府在操纵一切,而且也不再简单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集权经济”的国家。通过阅读诸多研究文献,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学术界的这一重大变化。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是一个集权经济的国度,无如把它恰当地描述为奉行了“家长式农业制度”的国家更具有说服力。(31)根据这一观点,与那些主流学者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中国的经济演化反而是沿着斯密派路线走的,它的国家反而没有象西方国家,如英国那样,在工业革命时期,政府的作用巨大,军事集权的色彩十分浓厚,中央政府保持强而有力的财政汲取权,以便为它的军事征服和海外贸易提供必要的条件。然而,对于中国来讲,其拥有众多的小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及众多的具有相当规模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在漫长的18世纪,中国被认为是商业化市场经济时代——或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一个商业社会”——政府只在人们的生活面临危机时才对市场机制予以干预。(32)王洛宾在论及中国的经济生活时认为,政府并非被游移不定的暴政所控制,而是(相对)“仁慈的”和高效的。中国政府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优势,特别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财富和安全的追求甚于对个人自由的期望。当然,政府毫无疑问想对公众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控制,至少对其进行操控和管理。当国家和人民的主要利益都没有受到威胁时,你有理由相信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绝对受到拥戴。这一观点的拥护者承认这基本上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即政府和人民都在维持原状而并非求变求发展,用威尔的话来说,这完全有可能导致“量的增长”而非“质的发展”。再者,西欧政府是否真正把重心放在为人们创造财富上?只要我们没有误入时代错误的陷阱,我们就会把中国清朝看作是一个“福利国家”,而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以后我会更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
西方对于中国帝国时代的经济生活中的政府作用的普遍看法,其中部分论断坚信中国政府是以抵御外国货和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士,来保护中国经济的。当然,没人否认中国和其他国家有着广泛的经济往来。但这种解释只能说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往来仅限于物物交换,而这不能算作正常的“贸易”,这种物物交换更象是“进贡”。现在有关这二者如何区分的争议依旧很大。我们现在读到的许多出版物都简单地把“进贡”解释为贸易,因为有许多贸易紧随“进贡”之后或在“进贡”掩护之下进行。(33)现在,关于中国帝国政府对外贸的不断干预的观点也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排斥。在西方学术界,这种观点越来越认为,帝国政府对外贸的干预是因为要阻止中、西方的实际上的不断在加深着的接触。确实存在着干涉、监督甚至于控制着这些接触的因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个词之间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即官方的政策和现实的存在是有区别的。更为关键的是,中、西方贸易只是中国贸易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并且这一部分贸易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预。修正主义者在此情况下渐行渐远。根据王洛宾的解释,“中国政府(和西欧各国相比)在内、外贸方面的干涉”并不多。(34)他还认为,“…中国在长期的内、外贸上的国家政策方面更鼓励走‘斯密派’的路线,有时甚至超越了欧洲当时的惯例而寻求贸易的发展。”他甚至认为,“西方的商人比中国的贸易伙伴被课以更重的税收并更易被敲诈。”(35)
在主要的一些历史资料中,中国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以来被简单地认为是政府排外情绪的延伸,独裁和中央集权成为对外政策的标志。针对这个话题的一些西方文献中,几乎都会看到乾隆皇帝的标志性文字,它是在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后写给乔治三世的一段话。这些文字被认为是对外贸进行抵制的一个缩影:“我们的大清帝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国土的资源享用不尽。没有必要用我们的特产和从外国蛮夷那里进口的产品进行交换…我们从来都不稀罕你们的玩艺,我们一点也不需要你们的洋货。”(36)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许多类似的字眼。例如兰德斯和皮睿菲特曾多次提到这次出使的失败,看起来这并非偶然。如今许多研究中国清朝的西方历史学家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和封闭的国家,甚至在谈到西方人和其观念时也并非一味持排斥的态度。乔娜·威利科恩曾经在文中写道,“从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中国对欧洲兴趣颇大,尽全力与西方沟通。”(37)正象约翰·霍布森说的那样,中国近代早期并非是“封闭的”和拒绝向优越的欧洲学习,相反当时落后的欧洲却向“优越”的中国取经,而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向欧洲文明“讨要”。(38)这意味着(学术)观念上的巨大转折!
进一步的修正:中国和西方是否在近代早期非常相似?
在许多研究专家中盛行的说法已经出现了,即对中、英两国在近代早期的样子已经有了重新的认识,虽然并未完全颠覆原有的论断。至少有两种关于欧洲的不同版本:一个说法是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崇尚自由放任的状态,另一个说法则强调其财政和军事的扩张政策以及重商主义的盛行。当谈到中国时,虽然对于中国当时的暴政依旧有所描述,但学者们倾向认为,“家长式的土地共享(制度)”已经在中国渐渐盛行,虽然它还未占据主导地位。王洛宾在用“家长式的土地分配制度”来诠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时,毫无疑问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者,他非常赞同“加州学派”的观点,即西欧和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差甚微,这使他在致力于研究西欧和中国国家形成的“主题”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如果你相信上述论断的话,你当然就会折服于西欧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差距这样的说法。许多学者都已“纷纷下马”,臣服于这种“有力的论断”。
伊薇琳·罗斯基在谈到国家形成和建立时指出,她看到了中西方的相似性:在近代早期,西方诸国在国家收入、巩固领土、行政集权和文化融合方面加快了步伐。(39)彼德·C·皮杜在《中国向西进发》一书中写道,如果象过去那样把中国当作一个封闭的帝国,把欧洲视做一个扩展而又开放的国家体系,这种极力夸大两者差距的做法已经非常不明智了。让我从这本有趣的书中引用一些句子,例如,“清朝的早期并非是封闭的、平稳的、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调动一切军事力量向外扩张的国家组织。”(40)根据他的观点,再一味地认为“…欧洲的国家体制是充满多元化的竞争或者倡导地域核心论的组织”并且“简单地把西欧和欧亚其他地方参照对比,这已经是错误的看法了”。(41)他认为,直到18世纪中期,整个欧亚地区在商业交流和军事力量上已经势均力敌。可是他不认为从那时起中、西方的发展确实开始产生了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然而,自18世纪中期起,由于和俄罗斯划定疆界并且平息了内蒙准葛尔的叛乱,中国的统治者就自认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国家大业,因为整个帝国不再受到来自欧亚中部草原的威胁了,从此帝国也失去了活力和生气。(42)
有些学者甚至想在这“惊人的相似”中找到帝国主义的影子。罗斯基就毫不讳言地宣称,中国清朝和西方国家的相似点证明了“帝国主义者”是最好的注解。她认为,“在近代早期的历史资料中经常忽略后起的一些帝国,如东欧的哈普斯堡、俄罗斯帝国和清朝帝国,表明了西欧中心论的固执偏见。”(43)她甚至抱怨说“这些历史的古怪偏见把西欧冠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把中国、祖鲁人和其他地方称作“帝国建筑”即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这就把欧洲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一种局面,“因为人们认定能够形成世界力量的殖民主义是近代帝国的最佳解释,虽然在工业化和高科技时代这种国家的扩展方式被认为是一种时代的错误。”(44)罗斯基在解释麦克·阿达斯的论述时写道,“清代满洲帝国和英、法、荷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45),“清朝帝国主义以及满、汉和其他清朝子民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得到世人的瞩目。”(46)阿达斯在他的著作中强调,在中国清朝和西欧各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确信罗斯基也会认同他的观点。问题是人们都把目光聚焦在这些相似性上。(47)
许多其他的观点,没有过多的数据支撑
“重现国家的本来面貌”此时在社会科学领域非常受宠。(48)因为我们并不缺乏近代早期中、西对比上对“国家”这一概念进行详实讨论的相关资料。可是在关于“大分岔”这一问题的争论中,这些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详尽说明已经不象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只了解“资本主义”的英国,因此注定要比“暴政”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更具备成功的条件。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些现存的区别并没有在最终产生多大的在历史演化路径上的“分岔”,仔细看来确实没有那么大。以我所见,甘德·弗兰克的见解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他简单笼统地认为,国家或任何其他体制并非是解释历史演化路径出现“分岔”的唯一的原因。依他的意见,其他因素也象国家一样,在解释制度变迁的“大分岔”方面没有什么新意。(49)彭慕兰却认为,在中、西方演化分岔的差异上,国家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特别是当他象布劳德尔和沃勒斯坦那样来阐明现代早期的中国缺乏“资本主义”时,他更是强调国家的重要作用。 (50)当他们在解释现代早期资本主义时,他们故意把其描述成“重商的资本主义”,在此情况下资本得以从长期贸易中累积起来,市场并非是自由的和完美的,相反,却始终处在被垄断和被操纵的状态。这样的体制如果没有国家这只“有形之手”的干预和支持,是不可能存在的。(51)但许多研究“大分岔”的作者们并没有详细解释西欧各国和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在宏观调控机制得以形成并有效运行中是如何发挥其特有的作用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详述政府在政策上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并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
在王洛宾的《中国变革》这本书中,最为系统的中、西方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国家形成上。正如上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洛宾阐明的立场非常明确,他认为,只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讨论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历史演化路径上出现的差异性并且只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家形成是极不明智的。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论述中没有使用量化和实证的方法,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框架分析。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中、西方国家形成的过程以及所出现的演化路径的差异进行逻辑分析。他认为,这个差异在工业化之前并没有影响到经济,而且也没给工业化带来什么。(52)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欧洲”所下的定义也是含糊其辞的。(53)
皮杜在他最新著作中论及“重现国家的本来面貌”时,强调了国家的重要性,并阐明国家在历史演化的“大分岔”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但遗憾的是他同样没有用量化的方法来为这种国与国之间及中、西方之间所出现的历史演化“分岔”提供一种系统性的解释框架。或许他可以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关于18世纪后半叶之前的中、西方差别并不大。实际上,照我看来,说那时中、西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这种说法依旧是令人怀疑的,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54)伊薇琳·罗斯基在关于中、西方发展过程中的相似性也有类似的深入探讨,并指出这些地区都可以被统称为“近代早期”。(55)我的论述类似于霍布森和韦斯,因为我只把视角放在中、英这两国比较上,而且我的研究集中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因此我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更详细和更有深度的分析。(56)
为了给实证性的学术研究提供永久性的基本要素,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能够运用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如果可能的话,有必要运用量化的和比较的方法来判断争议和分歧颇大的这些观点。我希望通过本文来阐明这些要素。我将会就中、英两国国家的重要性、功能和作用的差异展开讨论,并就这些方面给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重要性和深刻意义进行详细的论述。
焦点:我不会做的和我不能做的
我会尽我所能在两国的比较研究方面做到更多的量化(数据化)、结构化且系统化。我将首先描述正在探讨中的所谓国家的“硬件”:即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以及人口方面。接下来我将把重心放在经济政策和体制上。为保证文章的可操纵性,我将放弃法律和产权方面的探讨,因为在其他文章中会有对此问题的详尽论述。我曾在一些文献中读到关于中国私有财产的正常化,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规则,虽然中、西方会有很多重要区别。对我来说,似乎在中国私有和国家的产权上不象西欧那样正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是最重要的产权方式,也不象西欧那样绝对化和个人化,而是更具局限性和集体性,而其“有条件的销售”这一概念依旧重要。(57)当谈及法律,很多专家认为书面合同在现代早期的中国非常普遍,而且它们在“法律上”的地位和西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58)关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争论现在更多是集中在产权方面,但人们对所谓“法律条例”的重要性的解释也相当宽泛。在马克斯·韦伯所有关于“西方个人主义”的出版物中,他在发现法律系统的功能和其是否理性、正常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并非偶然。(59)在他的论述中,“法律秩序的可预见性、持久性、诚信度和客观性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保证。”(60)我将不再触及这一有趣的题目,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看现有的文献。
在我做的这些比较中,我将不怕由于“详细解释所带来的错误”,会尽我所能来使提供的信息更加精确和可靠。我想强调的是我的论述顺序会按照“很大程度上”、“据估计”,甚至是“大概估计”来进行,因为我们探讨的是缺乏数据的时代。我们有时甚至连最重要的问题,如人口、税收、政府其他收入、工资和价格、就业人数等等,也缺乏最基本的统计数据。我们仅有的数据也是不精确的、不可靠的或者是很难比较的。例如,我们就没有如今系统的、可比较的、规范的人口普查,即使我们能够得到,也要意识到地域的随时变更从而使诸多数据缺乏一个统一的口径这样的现实问题。政府根本没有我们索要的“预算”数据。虽然听起来有些令人惊讶,但在中央管理机制下,只知道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此外,还有定义问题:哪些可以算作税收,哪些不可以?如何区分政府的税收和其他收入?如何处理征收的税金并把它用在地方性投资上?官方的数据、定额还有金额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差距?腐败、欺诈、挪用公款和泄露机密所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还有很多难题摆在我们面前,例如,有多少人在为政府工作,又有多少人在军队服役,他们得到了多少补偿,以及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实际上,所有这些数据是难以进行精确计算的。
在这方面,历史学家也要尽量审慎地使那些搜集来的数据及其相关的统计更加精确、一致。我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是“很大程度上”,以期在比较分析上更加严谨,特别是关于中、西方政府在推动和阻碍总体发展上的力度,尤其是在“大分岔”上它所起的作用。收集并建立基本的实证数据是本文的中心目标。(61)
焦点:关于货币
政府的收入和开支在本文的分析中将起到核心作用。它是用不同国家的货币单位表示的,英国是英镑,中国是银两。为使数据在文章中派上用场,我们必须了解两种货币的相对价值。我们把括号内的在术语上被称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如英镑和银两看作是“记账单位”,也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将根据所包含的一定数量和一定纯度的金属银表现出来,但是,它们并非真正的(银)铸币。中国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官方发行的银币。英镑和官(库平)银(62)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度量”手段。(63)关于英镑和官银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答,至少我们可以把官(库平)银作为我们(计算汇兑率)的出发点,再考虑一单位银量中包含了多少金属银,又代表了多少的英镑。在我们的论文所涉及到的年代中,1英镑相当于111克纯银和3两银子。我们由此可以推算出官银相当于37克纯银。(64)我将在本文中系统地采用这种兑换率以便把英镑兑换成银子,或把银子兑换成英镑。当我们谈到其他货币时,如荷兰盾、法国里弗(一种古老的货币)等等,我将根据它们所代表的一定数量的金属银来给出它们对中国的银两,或其他货币的兑换率(汇率)。此种方法正象我们今天用美元来表示许多货币一样,我希望在我所拥有的所有数据之间建立起某种(不同货币间)可比性(即兑换率)。这些(货币间的)兑换率并非学者的臆测。银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易:基于它的价值,在近代早期市场上它是一种重要的商品。19世纪30年代以前,曾有大量的银子从西方流入中国。实际上它在世界各个角落都作为货币使用。在中国,那时候银子还不是铸币,但毫无疑问,银子在功能上却起着“货币”的作用,人们还是不得不用它来支付并用它来体现货物的价值。(65)在英国,货币通常是要与银子进行兑换的,每1英镑大约可以兑换111克银。这样,我们这里就可以用银子作为兑付手段,用银子来表示其他货币的内在价值。因此当1797年它被暂缓作为兑换其他货币的“计账手段”的时候,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其本有的可兑换其他一切货币的特殊地位,但直到1821年才完全恢复银子在历史上充当“货币的货币”的重要角色。
当然我们在用货币兑换银子和用银子兑换其他货币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官方可以更改货币的纯银含量,如可以降低含量,可以随意改动它的价值,而银子本身也会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被反复磨损而改变其成色,造成银子不足斤两从而降低了其本有的价值。我曾经系统地使用过由官方规定含银量的各种货币。西欧和美元的含银量在85%和90%之间。俄国卢布和日本的含银量大大地少于85%。这可以方便我对其及时调整。中国的官银据说是接近100%的纯度。有时计量和测算不能按照标准来进行:所谓的纯银并非纯度达到了100%的标准,只是一种称谓罢了。帝国政府或许只认可含量在95%到100%的银币。(66)如果我们把这些碎银子打成银锭,在此过程中就会丢失一些金属。中央政府在征税时,会收纳税者的“锻造费”,因为每年收上来的税银都会损失由于重新打造、重新冶炼和旧币回炉的一些费用。在清朝,这个费率上升到3%。(67)在此我想重申的是英镑和银子之间的兑换率(如1镑相当于3单位银两)是基于当时的实际费率和它们所代表的含量。可是也有许多实例表明一些货币相对另一些货币或金条有“溢价”的存在。如来自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人们使用的美元就是以更高的含银量和纯度来“裁定”与中国某种货币的比值的。用清朝皇帝的话来说,“那时,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人们只用重量来衡量美元的价值,货币所含的金属量是主要的参考标准;然而在其他地区或在其他朝代中国人只考虑货币的表面价值,而忽略其本身的价值。”(68)很明显,美元被认为是可信度较高,特别是和其他相同含量的货币相比较易使用的一种货币,因此它的价值就应该定的较高。据史料记载,本世纪末它的币值已经溢价50%。这或许有些太高,但较高溢价的存在却是事实。(69)我们还可以在中国发现这样的实例,如“金锭”经过证实,比金条还要值钱,就象金币比非货币金条值钱一样。(70)
不同国家使用他们彼此(流通)的货币,即使用官方汇率,或者利用象银子这样的“记账货币”来计算各自的(政府)收入和支出的价值,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需要慎重对待的过程,因为你并不清楚这种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有多大。基于此,我想尝试用实际的经济量或比率,例如,考虑用价格水平,或者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并进一步采用人均基数(量)来表示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都是用来测量(表示)数字所代表的经济意义的。
焦点:关于人口和政体
如想尝试度量宏观经济政策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当然需要了解我们涉及到的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近代早期历史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数字并非准确无误。对于我们随口一说的“英格兰”或“大不列颠”来说,必须区分不同时期它是由哪些不同的地区构成的。1801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宣告成立。它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自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是一个共同体了。对威尔士来说,在17世纪的(几乎)全部地区和18世纪的大部分地区,其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人口数据非常缺乏。但我们知道19世纪20年代它的人口还不到100万。英格兰1680年的人口不到500万,1800年几乎达到900万,1850年则超过了1,600万。因此,我们不难判断17世纪8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合计还不到600万。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一数字就一跃而为1,300万,1850年则将近1,800万。1707年苏格兰又加盟到英格兰和威尔士所结成的联合王国,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大不列颠。但直到19世纪早期,苏格兰人纳的税也没有落入伦敦的腰包。所以针对那个时期,我列举的税收数字只能涉及到英格兰和威尔士。19世纪早期,苏格兰的人口有200万,18世纪中叶人口只有150万,19世纪50年代人口也只有300万。1801年爱尔兰的加盟形成了最后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不列颠王国。爱尔兰人口众多,1801年逾500万,1841年超过了800万。(71)它人口的大幅度下滑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大瘟疫”。总的来说,对“英国”这种简单的称谓,我的重心是放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上。因为苏格兰在 19世纪才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爱尔兰到了很晚才历尽艰辛成为大不列颠的一部分,因此在论及诸多的金融问题时,我们可以对它忽略不计。正象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英国”是一个“大熔炉”,是一个“君主制的大熔炉”。(72)1707年苏格兰成为大不列颠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共同拥有一位新教统治者,有着统一的立法和唯一的自由贸易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在政治上是高度统一的。(73)许多爱尔兰人认为他们联合王国所处的地位更象是一个半殖民地而非联邦国家的一员。(74)至于税收、国家收入的用途以及对国债的义务,英格兰和威尔士一直和苏格兰及爱尔兰享有不同的待遇。令人关注的是,通过研究,我发现“航海法”最初是属于英国人的。这一立法明显对英吉利海峡诸多岛屿和苏格兰,特别是爱尔兰非常不利,甚至把他们排除在最惠国待遇之外。
在本文所作的比较中,我认为了解国家领土的规模也非常重要。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将给出西欧一些国家当时的规模,他们的国土面积肯定会小于目前的规模,在此我们会涉及到德国、意大利、偶尔涉及到比利时,还有奥地利,当时它只能算作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区域,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他国家因其现有国土面积和近代早期差距不大而忽略不计。英格兰和威尔士总的面积是150,000平方公里;苏格兰是76,000多平方公里,爱尔兰,包括北爱尔兰大约有80,000平方公里(75)。法国是544,000平方公里;荷兰或称荷兰共和国是41,000平方公里;比利时30,000平方公里;卢森堡2,500平方公里;现在的德国是357,000平方公里;西班牙是504,000平方公里;葡萄牙是92,000平方公里;瑞士是41,000平方公里;奥地利是83,000平方公里;意大利是301,000平方公里。(76)如果我们把这些国家作为整个西欧合在一起,包括大不列颠和整个爱尔兰,是230万平方公里。1700年这些国家大约有7500万人口,1820年大约达到10,000万人。(77)特殊的数据应在特定的情况下给出,这样才对我们的分析有所帮助。关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帝国时代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我会在帝国主义那一章里详细列举。(78)只需粗略地一看,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得知,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我们只能大概统计一下中国的人口。明清转折时期,即17世纪80年代,在文献中我们遇到的数字就有很大的不同:从邓肯统计的5000万到其他一些人统计的14,000万,马丁统计的至少有2,300万。(79)清朝末期即19世纪30年代,人口大约有40,000万。(80)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国清朝,作为一个大国,它在不断地征服和吞并其他地区的过程中不断壮大。
那时的清朝拥有9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81)“真正意义上”,有18个省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腹地”,人口以汉人居多,面积大约不到400万平方公里。(82)现代早期的中国经常被视为“一个帝国”。在强调18世纪中国扩张前更象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帝国上,皮埃尔·威尔虽然很有说服力,但为了简便起见,我还是愿意把它称为帝国。(83)可是我还要进一步解释威尔的主张。首先,我们要了解这18个省包括西南部的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云南,因此援引马德琳·泽林的话说 “18世纪20年代以前,大部分地区由非汉人占据,在此政府只发挥有限的作用,社会处于无序状态。”(84)再者,清朝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包括蒙古,特别是满洲,当时它们都有特殊的地位。直到19世纪50年代,俄罗斯从中国掠走了大部分满洲以后,“他们的”满洲拥有逾12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最后,直到17世纪80年代,拥有36000平方公里的台湾才回到清朝的怀抱。
然而,清朝“帝国大厦”最风光的时候始于17世纪末期,那时除了内蒙,后来的“外蒙”也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个地区非常广阔。仅内蒙的面积就达到120万平方公里。现在的蒙古共和国,即原来的外蒙,面积为150万平方公里。18世纪被称作“青海”的地区也被清朝占领。面积为720,000平方公里。巨大的“新疆域”即新疆在18世纪也被收归清朝,虽然国土面积有些变化,但也有160万平方公里。同一时期清朝在西藏的影响和权威也在不断增长,其现在的面积逾120万平方公里。(85)
18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据邓肯记载,1812年它拥有1,1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凡纳甚至认为19世纪上半叶清帝国的国土面积已经达到了顶峰,几乎有1350万平方公里。(86)即使我们把一些很小的地区忽略不计,它也是一个综合实体,许多地区都是在清朝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之下,但它们有各自的行政管辖权。对此,我在以后探讨中、英帝国主义时再详细论述。关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腹地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口规模,我还要在以后进一步探讨。因为在此之前这些数据还没有记载下来。乐观一点说,1800年的最高人口数字统计也还是比清帝国(实际)所拥有人口少上十分之一。
不同国家的实际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差别,我会在后面继续探讨,这样我就可以解答一个问题,即帝国治下的人口、规模究竟能给“(行政)治理”带来多大的便利,又能给“(行政)治理”带来多大的难度。或者笼统地说,按每一平方公里或人均计算治理成本来衡量的话,究竟是小国高(低)还是大国高(低)?就我所知,并无确切答案。即使有,有关现代早期中、英两国对比上我们也缺乏必要的、精确的数据。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和邻国进行战争时,只需动用庞大人口的一小部分就可以把对方打败。然而,即使一个大国出动再多的军队,与那些需要征服的广大边界比较的话也会显得微不足道。治理一个大国肯定要比小国付出更多的成本和精力。按每平方公里和人均来计算建设成本的方式比较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国和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国,前者的成本肯定要低于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小的岛屿肯定要比广袤的大陆更易治理。当然这里面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们很难得到统一的答案。再者,解释各式各样的国家其政府的统治功能究竟是强是弱并非本文的主要目标。
注释:
①Kenneth Pomeranz,《大分岔》,《中国和欧洲现代经济的形成》,普林斯顿,2000。
②Peter C.Perdue,《中国向西进发,清朝占领欧亚中部》,剑桥和伦敦,2005:536-542。
③参看Jack A.Goldstone,《西方是崛起还是衰落?对社会经济历史的修正》,《社会理论汇编》,1998(18):157-194。“加州学派”代表人物有Kenneth Pomeranz,Roy Bin Wong,Andre Gunder Frank,Peter C.Perdue,Evelyn Rawski,Jack Goldstone。
④参看Kenneth Pomeranz,《大分岔》,《中国和欧洲现代经济的形成》,普林斯顿,2000:12、16、68、241; Peter C.Perdue,《中国向西进发,清朝占领欧亚中部》,剑桥和伦敦,2005:536-539; Roy Bin Wong,《中国变革》,《英国的历史变革和经验的局限性》,伊萨卡和伦敦,1997:278-279; Robert B Marks,《近代世界的起源》,《关于全球性和生态性》,拉纳姆,2002; John M.Hobson,《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剑桥,2004:313-316。
⑤出自Adam Smith的朋友Dugald Stewart。参看John A.Hall,《国家和经济发展:亚当·斯密观点的反映》,《历史上的国家》,牛津,1986:154-176。
⑥参看Adam Smith,《国富论》,牛津和克拉伦登,1979:463-465。
⑦参看《Toynbee的工业革命:关于工业革命的演讲系列》,纽约和纽顿艾伯特,1969(最初1884):58。
⑧参看Joan Pao-Rubies,《东方的暴政和欧洲的东方主义:Botero给Montesquieu》,《近代早期历史期刊》,2005年第 9卷第2期:109-189; Gregory Blue,《近代中西社会思潮》,Timothy Brook和Gregory Blue编,《中国和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家谱》,剑桥,1999:57-109。
⑨参看Gregory Blue,《近代中西社会思潮》,Timothy Brook和Gregory Blue编,《中国和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家谱》,剑桥1999:57-109; Timothy Brook,《中国的亚洲生产模式》,纽约,2001; Karl A.Wittfogel,《东方暴政》,《权威下的比较研究》,纽黑文和伦敦,1957。
⑩Jean Baechler,John A Hall,Michael Mann编,《欧洲和资本主义的崛起》,牛津,1988; Ernest Gellner,《犁、剑还是书》,《人类历史的结构》,伦敦,1988; John A Hall,《权力和自由》,《西方崛起的原因和结果》,牛津,1985; Peter Jay,《通向财富之路》,伦敦,2000; Eric L.Jones,《欧洲的奇迹》,《欧亚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第三版),剑桥,2003;Eric L.Jones,《成长的重现》,《世界史上的经济变迁》,剑桥,1988;David S.Landes,《国家的贫穷与富有》,《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纽约和伦敦,1998;Alan Macfarlane,《现代之谜》,《自由、财富和公平》,贝辛斯托克,2000;John P.Powelson,《数个世纪的经济奋争》,《欧洲和日本的相同之路以及和第三世界的比较》,安阿伯,1994;Nathan Rosenberg和Luther E.Birdzell,《西方如何变富:工业世界的经济革新》,纽约,1986;Sir John Hicks,《京津史》,牛津,1969。
(11)David S.Landes,《国家的贫穷与富有》,《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纽约和伦敦,1998。
(12)David S.Landes,《国家的贫穷与富有》,《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纽约和伦敦,1998:119-217。
(13)David S.Landes,《国家的贫穷与富有》,《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纽约和伦敦,1998:59。
(14)William Easterly,《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努力总是适得其反》,纽约,2006:165。
(15)Douglass C.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化》,纽约,1981;《体制、体制变革和经济绩效》,剑桥,1990;《如何理解经济变化的历程》,普林斯顿2005,Douglass C.North和Robert P.Thomas,《西方的崛起》,《新经济史》,剑桥,1973; Douglass C.North和Barry Weingast,《宪法和责任:17世纪英国政府体制的革新》,《经济史期刊》,1989,(9):803-832。
(16)Hernando de Soto,《资本的秘密》,《为什么资本主义东方不亮西方亮》,伦敦,2000。
(17)David S.Landes,《国家的贫穷与富有》,《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纽约和伦敦,1998:56-57。
(18)Etienne Balazs,《作为永久性官僚社会的中国,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中国人的文明和官僚》,《主旋律的改变》,纽黑文和伦敦,1964:13-27、34-54。
(19)Fernand Braudel,《文明史》,哈默德斯沃斯,1995,第三部分,第二章;同上,《15到18世纪的文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视角》,伦敦,1984:520。
(20)Alain Peyrefitte,《没有变化的帝国》,纽约,1992;《两种文明的冲突:英国1792-1794年第一次中国之征》,纽约, 1991。
(21)Eric L.Jones,《欧洲的奇迹》,《欧亚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第二版),剑桥,1987:165; Winwood Reade,《人类的殉道》,伦敦,1925:108。
(22)参看Hill Gates,《中国的动力》,《一千年的资本主义微式》,伊萨卡和伦敦,1996; Sucheta Mazumdar,《中国社会和糖产业》,《农民、科技和世界市场》,剑桥和伦敦,1998; Robert Brenner和Christopher Isett,《英国和中国三角洲的巨大差异:产权关系、微观经济和发展模式》,《亚洲研究》,2002,(16):609-662。
(23)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制》,《16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纽约,1974:15。
(24)Joseph Needham,《巨大的转变: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伦敦,1969:197。
(25)参看Wikipedia,网络百科,Joseph Stiglitz,《全球化和它的抱怨之声》,伦敦,2004;Robert Wade,《市场的管理》,《东南亚工业化的经济理论和政府作用》(第二版),普林斯顿,2004:11-14。
(26)Eric Williams,《资本主义和奴隶制》,查佩尔西尔,1944; Rene Barendse,《阿拉伯海:17世纪的印度洋世界》,纽约,2002:495、500、注解17; Robin Blackburn,《新世界奴隶制的形成》,《从野蛮到现代,1492-1800年》,伦敦和纽约,1998:第十二章;Jim Blaut,《殖民者的世界格局》,《地理差异和欧洲中心论历史》,纽约,1993; P.J.Cain和 A.J.Hobkins,《英国的的帝国主义:1688-2000年》(第二版),伦敦,2002; Javier Cuenca Esteban,《殖民贸易方式的比较:英国和其竞争者》,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编,《杰出主义和工业化》,《英国和欧洲竞争者1688-1815年》,剑桥,2004:35-68; Richard Drayton,《劳动中的协同:大西洋世界的奴隶、帝国和全球化:1688-1850年》:A.G.Hopkins编,《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伦敦,2002:98-114; Andre Gunder Frank,《亚洲时期的全球经济》,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1998; Joseph E.Inikori,《非洲任何英国工业革命》,《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研究》,剑桥,2002; Kenneth Morgan,《奴隶制、太平洋贸易和英国经济,1660-1800年》,剑桥,2000,Kenneth Pomeranz,《大分岔》,《中国和欧洲现代经济的形成》,普林斯顿,2000; John M.Hobson,《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剑桥,2004:第三和第四部分;Robert Marks,《近代世界的起源》,《关于全球性和生态性》,拉纳姆,2002:第四章;Clive Ponting,《世界历史》,《新的视角》,伦敦,2001:第二十和第七章。
(27)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制》,《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纽约,1974;同上,《现代世界体制》(第二卷),《重商主义和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1600-1750年》,纽约,1980;同上,《现代世界体制》第三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展的第二个阶段,1730-1840年》,圣迭戈,1989。
(28)Eric J.Hobsbawm,《工业和帝国》(第一版),伦敦,1968。
(29)Patrick Karl O" Brien,《不容分割的联系:贸易、经济、财政和帝国的扩张:1688-1815年》,P.J.Marshall编,《英帝国剑桥历史》第二卷,《18世纪》,剑桥和纽约,1998:53-77。
(30)John Brewer,《力量的来源》,《战争、金钱和英国国家,1688-1783年》,伦敦,1989。
(31)Susan Mann,《当地的商人和中国的管理体制,1750-1950年》,斯坦福,1987; Pierre-Etienne Will和Roy Bin Wong,《给人民给养:中国的粮仓制度,1650-1850年》,安阿伯,1991; Jane K.Leonard和John R.Watt编,《如何获得安全和财富》,《清朝的国家和经济,1644-1911年》,伊萨卡和纽约,1992; Gang Deng,《近代前的中国经济》,《结构平衡和资本主义的荒芜》,伦敦和纽约,1999; Helen Dunstan,《建议的冲突使时代混乱》,《中国清朝政治经济文献研究,1644-1840年》,安阿伯,1996; Roy Bin Wong,《中国变革,英国的历史变革和经验的局限性》,伊萨卡和伦敦, 1997;同上,《帝国的土地政治经济和近代遗产》,Timothy Brook和Gregory Blue编,《中国和历史帝国主义》,《汉学知识家谱》,剑桥,1999:210-245;同上,《探寻欧洲各国区别及近代早期的统治地位:亚洲的视角》,《美国历史评论》,第107期,2002:447-469;Robert J.Antony和Jane Kate Leonard编,《龙、虎和狗》,《清朝的危机管理和晚晴的国家势力范围》,伊萨卡和纽约,2001;William T Rowe,《拯救世界》,《陈宏谋和18世纪中国的主流意识》,斯坦福,2001。
(32)参看Smith,《近代世界之谜》,《自由、财富和平等》,郝德米尔斯,2000:第二部分。
(33)Takeshi Hamashita,《贸易体制的性质和近代亚洲》,A.J.H.Latham Heita和Kawakatsu编,《日本工业化和亚洲经济》,伦敦和纽约,1994:91-107; Giovanni Arrighi,Takeshi Hamashita和Mark Selden,《东亚地区崛起和世界历史观》, Giovanni Arrighi,Takeshi Hamashita和Mark Selden编,《从50年、150年、500年来看东亚的再次崛起》,伦敦和纽约,2003:3-16; Gang Deng,《近代早期前中国的主要贸易》,《国际历史评论》,1977,(19):253-304。
(34)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GEHN/GEHNPDF/WorkingPaper05RBW.pdf.P20。
(35)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GEHN/GEHNPDF/WorkingPaper05RBW.pdf.P18。
(36)Eleen H.Tamura和其他人,《中国,了解它的过去》,火奴鲁鲁,1997:88; Jonathan D.Spence,《追寻现代中国》,纽约和伦敦,1990:122; James L.Hevia,《追忆过去的人们》,《清朝的礼仪和1793年的马卡特尼大使》,达勒姆和伦敦,1995。
(37)Joanna Waley-Cohen,《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的全球浪潮》,纽约,1999:128; Joanna Waley-Cohen,《18世纪晚期的中西科技》,《美国历史评述》,1993,(98):1525-1544。
(38)John M.Hobson,《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剑桥,2004。
(39)Evelyn S.Rawski,《近代早期清朝的形成》,Lynn A.Struve编,《世界历史上的清朝形成》,剑桥和伦敦,2004:207-240。
(40)Peter C.Perdue,《中国向西进发》,《清朝占领欧亚中部》,剑桥和伦敦,2005:第十五、十六章、527。
(41)Peter C.Perdue,《中国向西进发》,《清朝占领欧亚中部》,剑桥和伦敦,2005:527。
(42)Evelyn S.Rawski,《清朝的形成和近代早期》,Lynn A.Struve编,《世界历史上的清朝形成》,剑桥和伦敦,2004:207-240。
(43)Evelyn S.Rawski,《清朝的形成和近代早期》,Lynn A.Struve编,《世界历史上的清朝形成》,剑桥和伦敦,2004:207-240。
(44)Evelyn S.Rawski,《清朝的形成和近代早期》,Lynn A.Struve编,《世界历史上的清朝形成》,剑桥和伦敦,2004:207-240。
(45)Evelyn S.Rawski,《清朝的形成和近代早期》,Lynn A.Struve编,《世界历史上的清朝形成》,剑桥和伦敦,2004:207-240。
(46)Pamela Kyle Crossley,Helen Siu和Donald Sutton编,《边缘的帝国:近代早期中国的文化、种族和边界》,伯克利,2006; Laura Hostetler,《清朝的殖民企业》,《近代早期中国的人种学和制图学》,芝加哥和伦敦,2001; J.A.Millward,《超越困难》,《清朝在中亚的经济、民族和帝国,1759-1864年》,John.F.Richards,《永无休止的边界》,《近代早期世界环境历史》,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2003:第三、四章;R.Kent Guy,谁是满洲人?《亚洲研究期刊》,2002,(61):151-177; Sudipta Sen,《中国满洲的新疆土和亚洲帝国历史》,《亚洲研究》,2002,(61):151-177;Pamela Kyle Crossley,《半透明的窗户:清朝帝国的历史和意识形态》,Mark C.Elliott,《满洲的方式:晚清中国的八旗和种族意识》,Evelyn Rawski,《最后一个皇帝:清朝帝国制度社会史》,E.J.Rhoads,《满人和汉人:晚清中国和共和早期的种族关系和政治权力, 1681-1828年》,《国际历史评述》,1988,20(2):253-388; Lynn A.Struve编,《世界历史时期的中国形成》,剑桥和伦敦,2004。
(47)Michael Adas,《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比较》,《国际历史评述》,1998,(2):371-388。
(48)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kpol编,《回顾国家》,剑桥,1985。
(49)Andre Gunder Frank,《亚洲时期的全球经济》,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1998:206。
(50)Kenneth Pomeranz,《大分岔》,《中国和欧洲现代经济的形成》,普林斯顿,2000:第二、四章。
(51)Braudel和Wallerstein,《文明和资本主义,15世纪到18世纪》(三卷),伦敦,1979-1984;《近代世界体制》(三卷),纽约,最后一卷,圣迭戈,1979-1989。
(52)Roy Bin Wong,《中国变革》,《英国的历史变革和经验的局限性》,伊萨卡和伦敦,1997:第六章,142-151。
(53)Roy Bin Wong,《中国变革》,《英国的历史变革和经验的局限性》,伊萨卡和伦敦,1997:详见各节。
(54)参看Peter C.Perdue,《中国向西进发》,《清朝占领欧亚中部》,剑桥和伦敦,2005:第15章。
(55)Evelyn S.Rawski,《清朝的形成和近代早期》,Lynn A.Struve编,《世界历史上的清朝形成》,剑桥和伦敦,2004:207-240。
(56)Linda Weiss和John M.Hobson,《国家和经济发展》,《历史分析比较》,剑桥,1995:第二、三、四章;John M.Hobson,《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剑桥,2004:第三、四部分。
(57)参看Hill Gates,《中国的动力》,《一千年的资本主义微式》,伊萨卡和伦敦,1996; Philip.C.C.Huang,《三角洲地带的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斯坦福,1990:第六章;M.Macauley,《世界越来越简单:奥特曼和中国帝国的法律和产权》,《近代早期史》,2001:331-352;Sucheta Mazumdar,《中国社会和糖产业》,《农民、科技和世界市场》,剑桥和伦敦,1998;F.H.Schurman,《中国的传统产权意识》,《远东》,1956,(15):507-516; D.Wakefield,Fenjia,《清朝和共和时期中国家产的分割和继承》,火奴鲁鲁,1998; Kenneth Pomeranz,《大分岔》,《中国和欧洲现代经济的形成》,斯坦福,2000:69-107; Martin Daunton,《进步和贫穷》,《英国经济社会史,1700-1850》,牛津,1995:第三、四章;Thomas M.Buoye,《屠杀、市场和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产权的激烈争论》,剑桥,2000。
(58)Madeleine Zelin,Jonathan K.Ocko和Robert Gardella编,《近代早期中国的合同和产权》,斯坦福,2004。
(59)Derek Bodde和Clarence Morris,《法律和中国帝国:190个清朝案例:历史、社会和司法评论》,Hsing-an hui-lan译,剑桥,1967; W.J.F.Jenner,《暴政的历史》,《中国危机的根源》,伦敦,1992:法律一章;Madeleine Zein,Kathryn Bernhardt和Philip.C.C.Huang编,《清朝和共和时期的民法》,斯坦福,1994; Philip.C.C.Huang,《中国的民法公正》,《清朝的法律陈述和惯例》,斯坦福,1998; Philip.C.C.Huang,《社会习俗和法律惯例:清朝和共和时期的比较》,斯坦福,2001。
(60)Max Weber,《经济和社会》,伯克利,1978:1095。
(61)Peer Vries,《我们是否应重新定位?》,《海外历史欧洲版》,1998,(3):19-38; Andre Gunder Frank,《重新定位》,《亚洲时期的全球经济》,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1998;David Landes,《文化、时钟和比较成本》,《海外历史》(欧洲版),1998,(4):67-89; David S.Landes,《国家的贫穷与富有》,《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大》,纽约和伦敦,1998; Kenneth Pomeranz,《煤和殖民地就那么重要?》,《世界史》,12期,2001,(12):407-446。http://www.lse.ac.uk/ 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GEHN/GEHNWorkshops.htm,《政府的力量》,《世界史》,2002,(13):67-138;《由北京回到曼彻斯特》,《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中国》,雷顿,2003; Richardo Duchesne,《加州是衡量世界的尺码吗?》,《世界史》, 2005,(5)。
(62)清代虚银的一种。为政府征收赋税和国库其他收支活动中称量银两的标准。中央库平一两为37.31256克,即575.82英厘。
(63)Frank H.K.King,《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1845-1895年》,剑桥,1965; Peng Xinwei,《中国的货币历史》,华盛顿贝林哈姆,1994:注解64。
(64)1两=1.333盎司=1.2金盎司=37.3克白银(纯度99%),约合三分之一英镑=111.35808克纯银。
(65)Frank H.K.King,《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1845-1895年》,剑桥,1965。
(66)Frank H.K.King,《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1845-1895年》,剑桥,1965:78。
(67)Kent Deng,《作为银子来储备的消费品和作为消费品储备的银子,明清时的国际贸易和物质生活》,伦敦政治经济科学院,2004; Ray Huang,《明朝的货币管理》,Denis Twitchett和Frederick W.Mote编,《剑桥中国历史》,第八卷,《明朝,1368-1644年》,剑桥,1998:106-171、161。
(68)参看Frank H.K.King,《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1845-1895年》,剑桥,1965:46、86、255; Peng Xinwei,《中国的货币历史》,华盛顿贝林哈姆,1994:672;Yen-p" ing Hao,《19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中西重商主义的兴起》,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1986:35-44; Richard von Glahn,《外国的银币和中国19世纪的市场文化》,《十六届赫尔辛基国际经济历史会议汇编》,2006,(8):21-25。
(69)Eduard Kahn,《中国的货币:困扰中国的金银币调查,铜的一章》,S.J.Durst出版,1978:129。
(70)Frank H.K.King,《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1845-1895年》,剑桥,1965:31、73。
(71)E.A.Wrigley,《漫长18世纪的英国人口,1680-1840》,Roderick Floud和Paul Johnson编,《剑桥英国经济近代史》,《工业史,1780-1860》(卷一),剑桥,2004:57-95。
(72)参看Helmut G.Koenigsberger编,《政治家和艺术大师》,《近代早期历史文章汇编》,伦敦,1986:1-25; John H.Elliott,《君主集团下的欧洲》,《过去和现在》,1992:48-71。
(73)参看Linda Colley,《英国如何锻造国家,1707-1837年》,纽黑文和伦敦,1992:12-13。
(74)参看David Fitzpatrick,《爱尔兰和帝国》,Andrew Porter编,《剑桥英国帝国史》,《19世纪》,剑桥和纽约,1999:421-495。
(75)Roderick Floud和Deirdre McCloskey编,《1700年以后的经济历史》(第二版),剑桥,1994:429。
(76)数字来自于《欧洲经济家手册》,《今日欧洲的形象、事实和数据》,伦敦,1992。
(77)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新千年的视角》,巴黎,2001:232。
(78)正如前述,本文只是傅瑞斯先生十几万字论文的一个“概述”,文内所提到的“帝国主义”一章,将与全文一并另行出版。——译者注。
(79)Kent Deng,《事实还是虚构?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前的数据》,《经济历史系论文汇编》,68期,伦敦政治经济学学院, 2003; Kent G.Deng,《揭开中国近代官方人口统计的真实面纱》,《人口评述》,2004,43(2):1-38; Martin Heijdra,《明朝中国乡村的经济发展》,第九章,Denis Twitchette和Frederick Mote编,《剑桥中国历史》,《明朝,1368-1644年》第八卷,William Lavely和Roy Bin Wong,《对马尔萨斯的更正:中国晚期帝国时代的人口动态比较》,《亚洲研究期刊》,57期,1998:714-748; James Lee和Wang Feng,《人性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学和中国现实,1700-2000年》,Frederick W.Mote,《中国帝国,900-1800年》,剑桥1999:743-747。
(80)参看前文注解。
(81)Robert Benewick和Stephanie Donald,《中国国家地图》,哈蒙德斯沃斯,1999:102。
(82)参看Frederick W.Mote,《中国帝国,900-1800年》,剑桥和伦敦,1999:944-945; Benewick和Donald,《政府历史》 (第三卷),牛津,1997:1130。
(83)参看Pierre-Etienne Will,《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科学社会期刊》,1994,(49):7-26。
(84)Madeleine Zelin,《雍正统治》,Willard J.Peterson编,《剑桥中国历史》,第九卷,第一部分,《清朝到1800年》,剑桥, 2002:183-229; Alexander Woodside,《乾隆统治》,《剑桥中国历史》,230-309、注解46。
(85)Robert Benewick和Stephanie Donald,《中国国家地图》,哈蒙德斯沃斯,1999:94; Joseph Fletcher,《亚洲的清朝, 1800年,清朝的鼎盛时期:蒙古、新疆和西藏》,John K.Fairbank编,《剑桥中国历史》,第十卷,《晚清,1800-1911年》,第一部分,剑桥,1978:35-106、351-408; Susan Naquin和Evelyn S.Rawski,《18世纪中国社会》,纽黑文和伦敦,1987:213。
(86)Deng,《五味杂陈的儒教》,《第十届全球经济历史会议》,华盛顿,2006,(9):16; S.E.Finer,《政府历史》(第三卷),剑桥,1997:1130;Geoffrey Barraclough编,《世界历史不同年代地图》,伦敦,1979:174-175; Patricia Buckley Ebrey,《剑桥中国历史插图》,剑桥,1996:223、141; Albert Herrmann《中国历史地图》,阿姆斯特丹,1996:51;J.V.Beckette和M.Turner,《18世纪英国的税收和经济增长》,《经济历史评述》,第二个系列,XLIII,1990:377-402; John Brewer,《权威的支柱》,《战争、金钱和英国国家,1688-1783年》,伦敦,1989; Martin Daunton,《进步和贫穷》,《英国经济社会史,1700-1850年》,牛津,1995:十九章;Martin Daunton,《请相信这个庞然大物:英国的税收政治,1799-1914》,剑桥,2001; Philip Harling和Peter Mardler,《“军事财政”国家到自由主义国家,1760-1850》,《英国研究》,1993,(32):44-70; Allen Horstman,Zenith,《税收:英国税收和社会阶层,1816-1842》,《欧洲经济历史》, 2003,(32):111-137; R.V.Jackson,《18世纪英国政府开支和经济发展:度量衡上的一些问题》,《经济历史评述》,第二系列XLIII,1990,(32):217-235; Robert M.Kozub,《英国的税收改革,1700-1850》,《战争和工业化的时代》,《欧洲经济历史》,2003,(32):363-387; Peter Mathias和Patrick K.O" Brien,《英法税制,1715-1810》,《中央政府社会和经济税收比较》,《欧洲经济历史》,1976,(5):601-650; Patrick K.O" Brien,《英国税制的政治经济, 1660-1815》,《经济历史评述》,1998,(41):1-32; Patrick K.O" Brien和,Philip A.Hunt,《1485-1815时的英国》,Richard Bonny,《经济历史评述编》,《欧洲财政国家的崛起,1200-1815》,牛津,1999:53-100; D.Eckart.Schremmer,《税制和公共财政:英法德》,Peter Mathias和Sidney Pollard编,《剑桥欧洲经济历史》(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发展》,剑桥,1969:314-494; Linda Weiss和John M.Hobson,《国家和经济发展》,《历史分析比较》,剑桥和牛津,1995:第四章,112-130。
标签:经济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