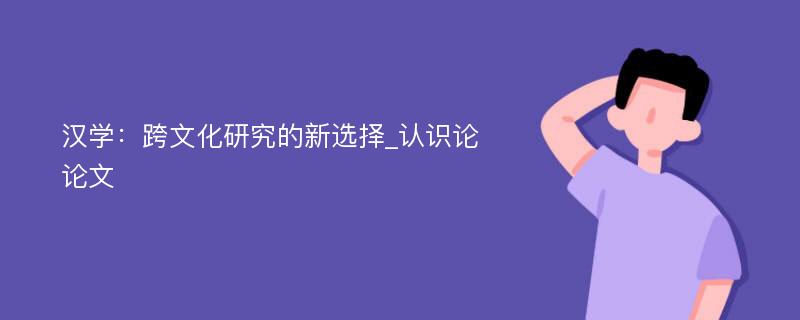
“汉学主义”: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新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跨文化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4-0015-08
若干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和描绘总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前者是把中国描绘成理想国,君主贤明仁德,人民安定富足,而后者则把中国描绘成人间地狱,君王暴虐无道,人民苦不堪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自相矛盾的描绘和对中国文明所持观点的前后相左,促成了中西研究领域当下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中国形象学”。该研究的对象是西方人笔下纷纭复杂的中国形象。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的学术成果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①在中国学术界,不少人对历史悠久的中国学术及其在西方的对应学科——汉学,亦怀有同样矛盾的情感。这一现象再次因中国学者两大阵营的形成而复杂化:一派是保守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坚决维护传统学术的价值,坚持严格遵循中国学术规范,另一派是激进的西化学者,他们不断攻击中式学术及其生成方式,将其贬为一文不值的垃圾,并不加选择地拥抱西方的一切思想、概念、理论、范式和学术研究方法。两大阵营的分歧集中在对待汉学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价值和态度上。一方盲目崇信汉学的效力和价值,热情效法,另一方则应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慷慨激昂地批评汉学是殖民主义的话语,是一门像东方学一样充满偏见的学科而将其摒弃。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识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误读并非仅仅源于信息不灵、偏见歧视和政治干预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源于一种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深层逻辑,而这种逻辑业已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无意识。这种无意识进一步衍生为一系列的次无意识,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知性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和评价相互矛盾,就是这种文化无意识的必然产物。这种文化无意识是导致误读中国的核心因素,并已构成了一种涵盖广泛的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汉学主义”。
寻找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探讨东西方在认识上的内在逻辑,自然绕不开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但据之对中国材料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套用“东方主义”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这也难怪,赛义德多次重申,他的理论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而得出的。正是赛义德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西方人(殖民者和学者)对中东文化的认识、观念和评价中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他的“东方主义”著述并没有关于被殖民者的只言片语。此外,赛义德的批评理论没有探讨被殖民者自身对于殖民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因此,有些学者诟病赛义德在其批评研究中让被殖民者缺席的不足是不无道理的。阿里夫·德里克就是对“东方主义”的这一缺陷提出质疑的代表性批评家:
我认为,赛义德所论述的“东方主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其疏忽了“东方人”参与有关东方话语阐释的地位,这一点会引起话语的地域问题,也因此意味着会引发有关权力的问题。我在上文提到,虽然“东方主义”在其根源和历史上与欧洲中心主义有紧密的关系,但在根本上,如果想要获得合法性,东方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实践方面,“东方主义”从其产生伊始就是以一种形象和表述的交流而出现,与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的流通遥相呼应,一开始是欧洲人在亚洲的流通,逐渐地产生了一种反向趋势,亚洲人开始在欧美流通。②
德里克正确指出了赛义德“东方主义”的一大缺陷:即它极少关注被殖民者在殖民心态和自我殖民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少关注葛娅特丽·查克拉芙替·斯皮瓦克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在同化他者过程中的同谋角色”③。这一缺陷同样受到了其他后殖民批评家的质疑,其中包括霍米·巴巴④、罗伯特·杨⑤、齐亚乌丁·萨达尔⑥、阿贾兹·阿赫迈德⑦和其他的后殖民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对赛义德的理论进行了大量修改、补正和重新概念化的工作。后殖民研究也因此而超越了赛义德理论中东方和西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关系,同时也拓宽了赛义德的视野。但是,后殖民话语同样有其局限和缺陷。很明显的一点是:中国从未被西方完全殖民过。这一历史前提肯定会影响西方人和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社会的认知和看法。普通人和知识分子都会受到这一影响,同时他们的学术研究方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一点与第一点相关:“东方主义”的母体(东方学)与“汉学主义”的母体(汉学)因历史原因在本质和功能上有所不同。如今,多数学者视“东方学”为一种“殖民话语”,但很少有从事汉学研究和国学研究的人会把“汉学”视为一种殖民话语。其原因很明显:它们是两种研究动机不同的学术活动。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对殖民话语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描述:
殖民话语的目的就是把被殖民者视为一种因其种族根源而落后的人群,其目的是为征服正名,为统治和教导体系的建立铺路。⑧
由此看来,“汉学”肯定不是一种殖民话语。因此,运用一种在完全被西方殖民的文化研究中推衍出来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知识生产中的问题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
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研究模式套用到中西研究还有一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这两种理论的研究方法都是以政治为导向、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因而极易引发文化战争。文化战争对于解决学术问题无能为力,并总是无视知识和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因此,这需要一种新的不同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概念范式。这一新的概念范式能够对如何进行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如何在尽可能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有关中国知识生产等问题进行自觉的思考。
在许多中西文化研究者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知性心态和学术习惯:即不管西方目的论模式和概念框架是否适用于中国资料,也不管研究资料所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研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照单全收。李泽厚曾多次批评自1919年以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趋势——很多人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把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用来研究中国的资料,结果丢失了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把握,他指出:“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从胡适、冯友兰到牟宗三,这些中国思想家都用西方的概念框架来谈论中国。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也不无成果:在阐明中国如道、气、太极、性、理等难以诠释的概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方法同时也抹杀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性。”⑨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在为汪晖的英文新作《想象亚洲的政治学》所写的序言中也提到,他在汪晖的书中发现了同样的对于方法论的关注:“这些文章的真正主题是对西方舶来话语的深切不满,过去一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就是用这种话语来评析中国的。”⑩与李泽厚、汪晖一样,笔者一直也觉得强行套用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框架和范式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材料和数据无异于削足适履。但笔者与汪晖在内容上,特别是研究方法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汪晖的著作记录了他“提出一种不同的中国历史观的不断努力,这种历史观跳出了一直统治多数西方人和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及其遗产所做思考的西方概念框架的窠臼”,同时他“不断努力发展一种不同的现代性的可能性”。(11)而笔者试图在中西研究纷纭复杂的表象之下和之后进行观察、希望能揭示一种导致中西研究误识和误读现象发生的内在逻辑。当然,两者都对机械地挪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资料的做法持批判、怀疑态度。在举例说明套用西方概念模式来解读古代中国的资料时,汪晖谈到:“很多受过现代欧洲哲学熏陶的学者,直接从本体论、现实主义和认识论的框架出发对宋代思想进行哲学分析。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基于欧洲哲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的分析方式本身就与宋代思想相去太远。”(12)汪晖的论述含有一种认识论的信念,笔者也正是带着这种信念从事对中西研究问题探讨的,并找到了中西研究问题内在逻辑的一些洞见。这就是中西知识生产中的意识形态无意识。可以用“汉学主义”这一广泛知识体系的核心来涵括。
“汉学主义”虽然也涉及了“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或“族群中心主义”的方方面面,但绝非它们的翻版。“汉学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可以指称西方的中国知识生产和中国的西方知识生产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现象。它与“汉学”这一集中研究中国的领域相关但却不同。它是汉学和知识生产的一种异化形式,是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涵盖中西学术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并探索中西研究、跨文化研究中隐性的知识生产范式。
“汉学主义”的新解读
“汉学主义”既是一个新词,也是一个新的理论范畴。(13)毫无疑问,“汉学主义”的提出受到了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启示。最早使用该词的德国学者夏瑞春(Adrian Hsia)在解释他所用的新词“Sinism”时,就说该词也可被称为“Sinologism”,因为“Sinologism看起来与赛义德的Orientalism类似……并且,在研究欧洲对中国的构建时,这个词比赛义德所描述的Orientalism更为精确”(14)。现有中西方少数提及该词的论述都视其为“东方主义”在汉学研究中的一种形式。(15)的确,“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虽然人们对“东方主义”的解读大相径庭,但赛义德的初衷应是揭示西方为了推进殖民主义而对东方进行的单向构建。与“东方主义”一样,“汉学主义”也是一种西方对中国的构建,但这仅仅是其诸多维度之一。“汉学主义”是一种远为复杂宽泛的知识生产体系。其动机有善有恶,其特征有雅有俗,其结果有正有反。从根本上讲,“东方主义”论及或隐或显的为殖民铺路的观点、思想、信仰、意识形态和学术行为,而“汉学主义”却是一种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认识论、方法论和西方视角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并因中国人和非西方人的参与而异常错综复杂。其中不仅有西方人通过西方视角对中国文明的观察,更有中国人通过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世界、对自己的文化,以及对于自身的观察。它几乎控制了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方面面。因此,“汉学主义”是一种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参与的双边构建。正因为如此,在对“汉学主义”的材料、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时,“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就不再是称职的理论范式。
在世界语境中,“汉学主义”并非仅仅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双边构建,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多边构建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由来自全球各地,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知性产业。由于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汉学主义”已经构成一种以中国为原材料,而生产商是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消费者却是世界各地的人们的知性产业链。因此,“汉学主义”不仅是由西方的中国通和华裔汉学家向世界表述的中国形象,而且是以出口的中国知识资源为原材料,由西方的和非西方的知识分子所操纵的知性机器根据西方人和非西方人的文化消费要求、习惯、趣味加工制造而成的知性商品,之后为了迎合中国大众对西方知识产品的狂烈追求,有些热门的知性商品又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引进知识产权并在中国重新包装推销兜售。(16)从迎合不同国别、地区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来看,“汉学主义”也是一种受制于全球化和商品化逻辑的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
“汉学主义”既与“东方主义”相关,也与汉学这一聚焦中国研究的学术领域不可分割,但它既非“东方主义”的一种形式,亦非汉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这一点笔者在已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17)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主义”呢?
“汉学主义”大致上是西方人在与中国交往中处理各种中国事物并理解纷繁复杂的中国文明时所构思并使用的一种隐性系统,其中包含观点、概念、理论、方法、范式。由于西方一直主宰着世界的政治和知识视域,整个世界必须通过西方的眼光观察和消费中国知识。“汉学主义”也因非西方人(包括中国人)对于中国文明的观察、认知和评价而更加错综复杂、丰富多彩。对中国的观察、中国知识的生产以及对中国的学术研究都受控于一种内在逻辑,它常常以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而运作。因此,“汉学主义”在理论上是一种在中西方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中深藏不露的文化无意识,在实践上是受文化无意识的内在逻辑制约而产生的有关中国和中华文明知识体系。
“汉学主义”有一个在“东方主义”中不存在的层面。这一层面有两个对立冲突的侧面。一方面是非西方人(包括中国人自己)对西方认识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吸收,并在处理中国资料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被强加的西方范式,自发地采用西方标准来评价中西方事物,以及或隐秘或直白地承认西方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这个方面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进行自虐式的诋毁和攻击。另一方面恰好相反,周蕾曾一针见血地批评其极端形式:“我们所遇到的是一种文化本质主义,在此就是一种中国中心主义。这种文化本质主义在中国与外界之间画上了一道想象分界线。根据其逻辑,中国的一切都被想象成为高人一筹——中国文明的历史更长、更有智慧、更为科学、更有价值,简直无与伦比。”(18)
“汉学主义”理论的概念性基础
“汉学主义”理论的概念性基础既非“东方主义”,亦非后殖民主义,而是由另外两个概念相结合而形成的概念性基础。其一是“文化无意识”。它包含一系列次无意识:“智性无意识”,“学术无意识”,“认识论无意识”,“方法论无意识”,“种族无意识”,“政治无意识”,“语言无意识”以及“诗性无意识”等。这诸多无意识组合而成的大范畴构成了“汉学主义”研究的概念性基础,它广泛涉及“汉学主义”的所有问题,并将对“汉学主义”的认知与“东方主义”及“后殖民主义”区分开来。其二是“知识的异化”。就异化的知识而言,“汉学主义”可视为汉学和中西知识的异化形式。“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这两大概念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的理论核心。根据这一概念核心,人们可以用大量的个案分析对文化无意识进行理论探索,并可探讨“汉学主义”是如何演化成为中西方研究中的异化知识的。总之,文化无意识是“汉学主义”之源泉、动力,而汉学和中西方研究的异化知识则是“汉学主义”之结果。
基于以上的概念性基础,首先应当对“汉学主义”的主旨内容进行理论性处理,其次探讨其逻辑根据和多元维度。借助这种组织结构,可以提出一种中西方研究的新范式。这种潜在范式基于如下认识:“汉学主义”是一种在学术领域(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具有多元维度的知识产业,它受控于一种无意识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通常生产异化的知识。“汉学主义”成为一种新范式的可能性,一方面在于它能为不同领域和学科的学者们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使他们得以探索“汉学主义”在他们研究中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于它能把学者们从中西研究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桎梏中解放出来。据上述概念基础,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要把“汉学主义”当做一种批判理论提出来,并用个案研究来探讨其原理和逻辑,而是要把它构建成一种自觉反思的批评理论。
基于这种理论取向,“汉学主义”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揭示对中国的偏见歧视,亦非为了纠正对中国文明的歪曲表述以及驳斥对中国材料的误解误读,而是在这些问题的表象之下和之后揭示其产生的动机、精神框架、态度和原因。其基本目标是寻找有关中国和西方学术研究中问题产生的内在逻辑。从概念上来讲,首先是揭示在“汉学主义”这一标题下产生的形形色色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次是提高人们对文化无意识的认识,正是这种文化无意识导致了知识生产中问题的产生;也要揭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无意识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其中包括阻碍跨文化交流、导致认识论的惰性以及造成非西方民族原创力的萎缩等。再次是帮助厘清在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中应用赛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一些学术问题。最后是希望发起涉及已有中国研究范式的可行变革,因为已有范式是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和伪科学目的论的基础之上的;也希望能给读者以灵感而找到中国知识生产的真正科学的方法。其最终的目的是鼓励和促进相对中正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应远离任何形式的歧视、偏见、主观性和政治干扰。当然,这一目标似乎有乌托邦之嫌,因为大家普遍认为知识是建构的结果,而真理,即便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也难逃主观性的干扰。但是,即使真的没有绝对客观的知识,人们也需坚守知识的相对客观公正性;否则,知识生产将退化为话语战争、文化战争,甚或意识形态战争,这将危及知识传播,恶化文化偏执,阻碍文化间的理解。更为严重的是,这会给萨缪尔·亨廷顿在他那著名论断中警告过的文明冲突火上浇油。(19)
“汉学主义”研究的范围
“汉学主义”是知识生产的研究而非知识的研究。也就是说,“汉学主义”是对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知识生产、对西方和世界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的批判性研究。中国知识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中国知识就是有关中国的一切知识;狭义上的中国知识则是汉学或中国学。作为一种批判性审视,“汉学主义”研究首要关注的是中西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其次关注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自身,在生产中国知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中西知识生产中的问题和揭示问题之下的内在逻辑,从中获得启示和洞见,提出更科学、更客观、更可取的中西知识生产方法。
具体而言,“汉学主义”的研究意在探讨“汉学主义”的根源、兴起、历史发展、特征、现状及其内在逻辑;同时也要观察在历史、思想、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不同领域里“汉学主义”在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表现。它也企图解决一系列理论问题,其中包括:“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研究中已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批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把“汉学主义”作为一种概念范畴提出来在学术上是否有理有据?如果合乎理据,那么“汉学主义”具体是指什么?“汉学主义”何以有别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其他理论?如果“汉学主义”是一个有理据的概念范畴,其涵盖的范围应有多大?有多复杂?“汉学主义”是不是中国知识生产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影响是什么?我们如何抵制不同领域中的“汉学主义”化倾向?我们能否把“汉学主义”从一种解构性的批评话语转化成为一种建构性的范式?这种建构性的范式将有利于产生真正科学的观察中国和进行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并将激励、催生具有真正普世价值的知识生产。最终的核心问题是:“汉学主义”的理论探索应当产生植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还是应当产生如何生产不偏不倚的知识和学术的自觉反思理论呢?
“汉学主义”的研究范围涵盖很广,人们可以从跨文化、跨国别、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入手。但为了使研究有相对集中的范围,目前似应从如下十个方面入手。
第一,探讨提出“汉学主义”的理论问题,论证把“汉学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研究的概念范畴提出来的合理性。无论是“东方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都无法满足中西研究的需求,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取代它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文化无意识理论。具体地说,这种理论可被用作批判分析中西研究问题的指导原则,亦可广泛应用于跨文化研究之中。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应探讨与“汉学主义”有关的概念问题及其可能的涵盖范围。
第二,探究“汉学主义”与“汉学”之间的关系,找出“汉学”与“汉学主义”,以及“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之间的主要差异,进而厘清“汉学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和“西方主义”等其他意识形态观念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应探讨“汉学主义”与非领土殖民之间的关系,并研究“汉学主义”的最终形式:即“汉学主义”化。
第三,对“汉学主义”从产生到成熟再到现代形式的发展过程进行历史表述,通过批判分析西方历史上一些重要思想家和学者的思想,抓住“汉学主义”成为一种中国知识生产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而完成对“汉学主义”进行历史批判。
第四,在概念上关注“汉学主义”的认识论。通过对一些思想家的历史批评中所获得的理论洞见进行反思,从概念上对“汉学主义”问题进行研究,形成能够描述和批判中国和中国文明知识生产中形形色色的问题的概念框架,同时尝试揭示导致“汉学主义”这一标题下林林总总现象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工作逻辑。“汉学主义”基于一种微妙的意识形态,或可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意识形态本质上并不是真实政治性的,而是由一种有问题的认识论衍生而来的,这种认识论使观察中国的方法转变成为一种认识论意识形态。找出“汉学主义”的内在逻辑就可对其进行定义,并探讨其本质和内容。
第五,关注“汉学主义”的方法论。“汉学主义”的方法论意识形态性是基于某些惯用的研究中国文明的学术方法为逻辑依据的。“汉学主义”虽然声称致力于客观、科学和无偏见的学术研究,但其种种方法恰恰暴露了为学术政治、话语霸权和族群身份所左右的意识形态性和主观性。由于方法论问题通常是人们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内在偏见、歧视的情况下发生的,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就成了一种方法论无意识,引起了对中国文明的误识、误解和扭曲。
第六,探讨“汉学主义”与政治、族群和身份等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相关的一些问题,并研究这些问题如何塑造了学者学术研究的心态、如何导致学术研究的政治化、如何阻碍了不同族群和国籍的学者之间有意义的交流。甚至还可以通过个案研究探讨族裔身份的差异所引起的学术政治,考察对学者族裔身份的关注何以演化成了学术研究中的身份政治问题、何以对学术研究的观念和范式产生不良的影响。由于置身于身份政治之中的学者很少有人能清醒认识或愿意承认族群身份的影响,因此有一种对学术研究产生负面影响的心态,可被称为“族群无意识”,由此而生的学术研究心态和习惯又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知性无意识”。
第七,探讨中西研究中的学术政治和学术政治化。虽然中西学术研究中的政治维度要比“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研究中的政治维度轻微得多,也没那么常见,但其的确存在。自从中国从一个封建帝国转变成了民族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现实政治一直是中国知识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期间中国被视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这使得中西研究有了一种明显的取向,并逐渐演化成了一种中国知识生产的政治无意识。
第八,“汉学主义”的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也比比皆是,“汉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造成中国人原创力的萎缩,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健康发展。这一方面尚未见研究,是一个大有可为、且意义十分重大的研究领域。
第九,对西方的和非西方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华裔人士)为了迎合受制于全球化和商品化大趋势的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追求个人成功成名的欲望而故意歪曲中国材料、制造异化的中国知识的现象予以研究。
第十,对“汉学主义”进行反思,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在中西研究中避免“汉学主义”化?如何超越“汉学主义”?如何使“汉学主义”从一种解构性的批评理论转化成为建设性的知识生产理论?如何使“汉学主义”成为一种自觉反思的理论?
自觉反思的理论
“汉学主义”不应该是一种批判理论,而应该是一种自觉反思的理论。因为,学术研究虽然无法回避政治与意识形态,但是可以呼吁学术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摆脱学术研究中文化战争困境的途径。学术研究首要关注的是学术问题,而非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立场或个人恩怨。学术就是学术;知识就是知识,两者都应是不偏不倚的,最起码从原则上来讲是如此。公正无偏的学术研究应当远离意识形态的、个人的、社会的、学术的等等非学术的种种考量。非功利性的学术研究特别应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自从英国思想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19世纪后期提出将不偏不倚的文化批评作为一种原则之后(20),“非功利性”这一概念就一直受到无情的拷问和强烈的批评。但我们应分清文化批评和学术/知识生产之间的差异。批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批评者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而知识和学术具有相对中立性,我们不仅要接受和尊重,还应视其为一种追求的理想目标。在现代之前,汉学研究很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但自从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以后,“汉学”和“中国学”研究就与国际政治、族群政治、个人政治及学术政治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因此,需要超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研究的政治取向,把中西知识生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中解放出来。而对“汉学主义”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批评分析,也不应被误解为是在套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政治路数。
作为一种反思的理论,笔者对未来“汉学主义”研究的进展有如下一些心愿:首先,希望这种理论能有助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而目前的趋势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有演变成为各种形式的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风险。很多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都对此表示关切。其次,希望有助于提高学者们对“汉学主义”负面影响的认识,让他们警惕“汉学主义”化的潜在危险,并鼓励非西方民族的原创性活动。再次,希望能帮助参与东西研究的学者们跨越“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并为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开辟新的路径。最后,希望有助于构建一种研究范式来替代由赛义德首创、以政治为中心、充满意识形态的现有范式。该范式被当今后殖民研究进一步发展,并被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所热情拥抱。如果“汉学主义”能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外提供一种新的理论选择,我们也许就能在跨文化研究方面开辟新的领域,促成学术研究的跨文化超越。
注释:
①中国形象学研究的重要著述有:雷蒙德·S.道森(Raymond s.Dawson)的《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963);史蒂芬·莫什(Steven W.Mosher)的《误解的中国:美国臆想与中国现实》(1990);辛建飞(Xin Jianfei)的《世界看中国:近两千年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1991);朱莉清(Julie Ching)、威拉德·奥克托比(Willard Oxtoby)合编的《发现中国:启蒙时期的欧洲观》(1992);夏瑞春(Adrian Hsia)的《欧洲17、18世纪文学作品中构建的中国》(1998);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大汗之国:西人看中国》(1998);马克林(Colin Mackerras)的《西方的中国形象》(2000);鲁珀特·霍德(Rupert Hodder)的《中国形象:西方思潮中的华人自我认知》(2000);大卫·马丁·琼斯(David Martin Jones)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中的中国形象》(2001);周宁的《想象中国》(2004);汪晖(Wang Hui)的《亚洲形象政治学》(英文版,2011),等等。
②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in 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4.(1996),p.112.
③Gayatri C.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Vincent Leitch et al,eds.,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second edition(New York:Norton,2010),p.2114.
④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pp.71—75.
⑤Robert Young,White Mythologies: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London:Routledge,1990),pp.127—140.
⑥Ziauddin Sardar,Orientalism(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9),pp.54—76.
⑦Aijaz Ahmad,In Theory:Classes,Nations,Literatures(London:Verso Books 1994),159—220.
⑧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p.70.
⑨李泽厚:《实践美学发言摘要》,见《李泽厚近年答问录》,第44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⑩Theodore Huters,"Introduction" to Wang Hui's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
(11)Huters,"Introduction" to Wang Hui's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pp.2—3.
(12)Wang Hui,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67.
(13)顾明栋:《什么是“汉学主义”?——探索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载《南京大学学报》,2011(3)。
(14)Adrian Hsia,China:The European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98),p.7.
(15)“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新词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其含义完全相同,被定义为“汉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参见Bob Hodge and Kam Loui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The Art of Reading Dragons,pp.12-17;周宁:《汉学或“汉学主义”》,载《厦门大学学报》,2004(1)。
(16)我用“热门的知识商品”一词来指一个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所观察到的奇怪的现象:当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被引入中国以后,它们立刻大受欢迎,甚至被奉为研究之典范;经常有一些研究成果不尽如人意的西方汉学家被捧为学术明星。
(17)顾明栋:《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载《学术月刊》,2010(12)。
(18)Rey Chow,Preface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Reimagining a Field(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5.
(19)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NY:Simon and Schuster,1996).
(20)Matthew Arnold,"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in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p.703.
标签:认识论论文; 跨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