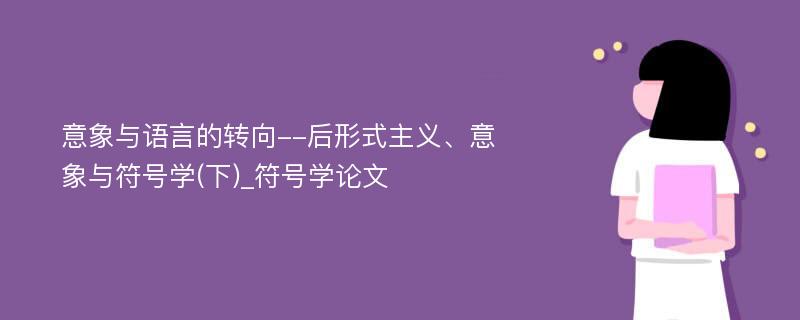
图像与语言的转向——后形式主义、图像学与符号学(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像论文,符号学论文,形式主义论文,之二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图像学与符号学符号学与视觉图像
符号学是一门现代学科,(注:符号学[semiotics],顾名思义,是一种关于符号[signs]的理论,而符号则是此物指代彼物的标志。例如,窗外的一棵树,可有许多符号表示这个物体。首先是文字“树”,而“树”这个字又是由“木”、“又”、“寸”三个符号组成的符号。画中的一棵“树”是另一种符号,而塑料盆景中的“树”也是一种“树”的符号。符号不但以语言、声音、图像、物象的形式出现,而且也以姿态、甚至观念的形式表示。在哑剧字谜游戏中,参与者如高举双臂,做V形姿势,就可被同伴辨认为“树”的符号,而人们看到窗外的树,在头脑中产生的“树”的思想也是一种符号。虽然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符号,但惟当某物被解释为符号时,才能起符号的作用。)但自古代以来,它就以不同的形式而存在了。现代符号学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前者认为符号即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符号呈现的形式,例如画中的一株树,这称为“能指”[signifier];二是符号再现的观念,如在纸上写出的“树”这个字,这称为“被指”[signified]。“能指”和“被指”的关系是一个表意的过程,“树”这个字可使人联想到真实的树,而见到真实的树,可使人在心目中想到“树”这个字。(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一般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London,1983年。)
皮尔斯提出了与索绪尔相异的符号构成理论,他认为符号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符号采纳的形式(不一定是物质的形式),被称为“再现”[representation];二是由符号组成的感觉或意义[sense],被称为“解释”[intepretant];三是符号所指的事物,被称为“物象”[object]。(注: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皮尔斯哲学文集精粹》[The Essential Peirce: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1867-1893)],Bloomington,1992年。)
在皮尔斯的符号模式中,马路上的一组红绿交通灯,一旦红灯被视为停车的观念符号,这个符号就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交叉路口的红灯即再现[the representamen],其次是停止的车(物象),最后是红灯表示必须刹车的观念(解释)。皮尔斯认识到,解释符号的过程往往激发更多的符号,如驾驶员见到红灯,形成必须停车的观念,即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解释。皮尔斯的符号系统的基本结构是一种三角关系,车的符号和被指的关系表明两者之间没有自动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必须加以建构。
皮尔斯的符号系统比索绪尔复杂得多,艺术史家运用的大凡是他的体系。皮尔斯提出了59000种以上的符号分类,而对艺术史家最有用处的是他对三种基本的符号的辨认系统:象征[symbol]、图像[icon]、索引[index]。“象征”即“能指”,如字母表、数字和交通灯等,“能指”全然是随意的,约定俗成的,它并不类似“所指”之物。“图像”也是“能指”系统,这个“能指”模仿或类似“所指”,或者说,它与“所指”的某些物质相似,如肖像画、汽车模型等。“索引”也是“能指”,但它不是随意的,而是在某些方面与“所指”直接相关联,例如病症、烟雾、脚印、摄影和电影等。当然,符号系统并不仅仅属于一个类型,符号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总是相互作用的,交替产生更多的符号。例如一个人的照片,它不仅是“图像”也是“索引”,因为它是一个人的物质存在的影像,同时又与这个人相似。
皮尔斯认为,符号是一个过程,而索绪尔则认为符号是一种结构。但皮尔斯符号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再现、解释、对象的无穷生发能力也令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其指号过程何处结束?假如解释一个符号的过程总是激发另一个符号,那么指号过程就可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意大利符号学家和小说家埃科[Umberto Eco]就认为,这种可以无限的方式读解符号文本的观念,与其说是真实可行的,不如说纯然是假说而已。在皮尔斯的基础上,埃科进一步指出,一个符号所产生的可能意义,虽然从理论上说可以是无限的,但在现实中,这些意义受社会和文化上下文的制约。(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1984年。)
在符号学中,代码[code]是最基本的东西。代码是在任何社会中流传的符号的复杂体,因此当代符号学家都强调不应孤立地看待符号,应将之视为“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亦即将符号相互之间联系起来加以解释。美裔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强调指出,符号的产生与解释有赖于代码的存在,有赖于交流的惯例。(注:《结论:语言学与诗学》" 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homas Sebeok,ed.《语言的风格》[Style in Language],Cambridge,MA,1960年。)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所处某种情境的代码所决定的,亦即代码提供参照系,而符号在这参照系之中产生意义。从符号学的角度解释一个文本,读解一个图像,涉及到将之与相关的代码联系起来的过程。
雅各布森的符号学理论对文学批评和艺术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送者、讲话者把一条信息(文本、言语或图像)传发给接收者、读者、听者或观者。为使这条信息可以理解,它必须指涉发送者和接收者共同理解的现实。这一现实就被称为“情境”或“上下文”。这条信息必须通过接收者可以接收的媒介传送,而又必须化为接收者可以理解、可以运用的代码。因此,交流由下述几个步骤组成:传送→信息→接收→参照系→代码。雅各布森的符号学理论说明,符号关乎交流,而交流则是一个特定的文化过程。当然,交流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发送者或接收者有时并不擅长使用代码,或者说,代码有时并不适合于表达信息。
符号学家在代码理论上精益求精,有时运用复杂的代码类型学区别代码发生作用的各种不同的方式。雅各布森的交流理论对接受论产生了影响。
皮尔斯和索绪尔先于艺术史家就认识到,符号学可以成为解释艺术的卓有成效的方法。1934年,捷克语言学家穆卡罗夫斯基[Jan Mukarovsky]发表了“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一文,指出“艺术作品具有符号的特征”。他运用索绪尔的方法,分析视觉艺术。然而,索绪尔将“能指”与“被指”区别开来,穆卡罗夫斯基在“感官可感知的有效事物”与“存在于整个集体意识中的审美对象”之间划了分界。1960年,法国哲学家梅洛-蓬蒂[Maurice Merleau-Ponty]发表了《符号》一书,将索绪尔的模式运用于知觉现象学研究。由于绘画是由符号(依据语言般的“句法或逻辑”组合而成的符号)构成,所以梅洛-蓬蒂把绘画与语言相联系。巴特的《符号学的成分》[Elements of Semiology](1964年)影响巨大,使用索绪尔方法研究广告之类的通俗图像。
新图像学与符号学
正是由于符号学的这种灵活机制,克劳斯相信它可以激活艺术史研究。1977年,她就运用皮尔斯的模式,研究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艺术。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艺术实践品种多样,呈现出她所谓的“任性的折衷主义”,折衷了从影像到表演艺术,从大地艺术到抽象绘画等一切艺术媒体,尽管如此,克劳斯认为,所有这些风格都背离了传统的风格和媒介观念,统摄于“索引”这个符号系统的大旗之下。例如奥本海姆[Dennis Oppenheim]的《认同的延绵》[Identity Stretch](1975年),艺术家将大拇指印放大,转印于大地,并用沥青勾画其轮廓。克劳斯对此评论道,这件作品“以索引的方法聚焦于纯粹的装置(艺术)”。
克劳斯和其他新艺术史家一样,攻击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认为符号学乃是驱动艺术史的新能源。然而,符号学其实是图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哲学基础同出一源,卡西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即为其重要基础。卡西尔认为,图像代表一个特定文化的基本原理与观念即象征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看作艺术家、宗教、哲学,甚至整个文明的“文献”。(注:卡西尔[Ernst Cassirer],《象征形式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New Haven,1953-1996年。)卡西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与贝尔等形式主义者的“有意味的形式”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充满了文化意义,后者彻底剥离了艺术作品的内容,认为形式是艺术作品至高无上的成分。(注: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艺术》[Art],1914年。)图像学和符号学都旨在破译艺术作品所包含的意义。
如果说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理论,那么图像学和图像志就是对图像的主题、内容与意义的辨识。Iconography和Iconology两个术语通常交替使用,其实却表示两种不同程度的读解视觉图像的过程。前者重在辨认图像、确定其象征寓意,后者则更进一步,力图根据更广阔的制像文化背景阐明特定图像的制作原因与目的,并说明人们为何要将这个图像视作某个文化的征兆或特征。
德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的导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图像学和图像志的研究方法与区别。他把整个研究过程分成三个步骤。首先是“前图像学分析”。在这个阶段,研究者仅仅观察所面对的视觉物象,毫不顾及其他文献,就作品本身的视觉品质而分析图像。这其实是基本的形式分析。第二个阶段是图像学分析,研究者将某个图像断定为某个已知的故事或可以辨认的角色。第三个阶段是图像志分析,其任务是破译图像的含义,亦即它的政治、社会、文化的意义,为此,研究者必须考虑这个图像制作的时间和地点,当时的文化时尚与艺术家的风格,以及赞助人的愿望等因素。
潘诺夫斯基虽然为研究文艺复兴艺术发展了图像学和图像志研究方法,但这种方法在20世纪中期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艺术史领域的研究,产生丰富的学术成果。1996年,斯坦伯格[Leo Steinberg]发表了他著名但遭争议的书《基督的性》[The Sexuality of Christ]。在此书中,作者充满想象力地运用了图像学和图像志分析的方法,断定基督的阴茎是一个被忽视的图像[an overlooked icon]。斯坦伯格力图说明,在许多文艺复兴图像中,基督的阴茎不但明显可见,而且是有意展示的:圣母玛利亚也许向东方三博士展示了初生基督的生殖器,死亡的基督的手落在生殖器上微妙地强调了这一点。斯坦伯格把这个图像学与强调基督人性化的神学联系起来。道成肉身,基督以有性器官的凡人现世,将上帝与人子合为一体。
波兰艺术史家比亚沃斯托茨基[Jan Bialostocki]为图像学和图像志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创造了“图像学引力”[iconographic gravity]的术语,描述图像与母题产生新意义的方式。在西方艺术中,善胜恶、献身、英雄、母与子、神圣灵感、哀悼被爱戴者之死等母题,犹如文学中的惯用语句[topoi],作为重要的主题,持续出现在希腊、罗马、早期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之中,出现于各种历史和文化情境之中。比亚沃斯托茨基认为“图像学引力”尤其弥漫于他所谓的“包围性主题”[rahmenthemen]。
随着“新艺术史”的兴起,人们开始怀疑图像学方法的有效性。艺术作品并非是艺术家向观者传送的信息包裹,而是一种可以无数方式读解或误读的复杂文本。由此,他们强调观者和社会情境在塑造艺术作品上的作用。图像学分析与形式分析一起,成为新艺术史家攻击的首要对象,他们认为这类分析不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拘泥于描述性。此处,必须指出的是,新艺术史家批评的不是潘诺夫斯基本人,而是那些缺乏技巧的追随者;他们滥用潘氏的方法,随意地从图像中读出象征含义。T.J.克拉克将这些人戏称为“主题追猎者”[theme chasers]。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公开否定图像学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假说,认为视觉象征符号并非必然具有含义,并非一定表达意义。即便如此,1999年她亲口对我说,她重读了潘诺夫斯基的《视觉艺术的含义》,从中获得了新的启示。
新艺术史家对艺术史的理论假说、方法和目的进行了重新思考。在这个批评范围内,阿尔珀斯和其他一些学者觉得,潘诺夫斯基的方法是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也是最适合于文艺复兴艺术研究的方法。但如果不加区分地使用这种方法,就会使人误解文艺复兴艺术为制像提供了一个普遍有效的模式。有些尼德兰艺术史家曾错误地运用图像学方法,从描绘日常生活的风俗画中读解充满象征意义的寓意。阿尔珀斯在《描绘的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中提出,荷兰艺术有别于意大利艺术,它并不注重叙述与象征。荷兰画家是尼德兰特有的视觉文化的参与者,将对日常生活的详细描绘视为了解世界的方式,而非传达隐含其中的道德信息的手段。她认为,绘画和其他视觉材料产物诸如地图、镜片和镜子一样,属于独特的荷兰视觉文化的表现形式。
艺术史与符号学
阿尔珀斯表明为读解意大利艺术而发明的图像学并无助于解释荷兰艺术的独特形式。荷兰文学批评家巴尔[Mieke Bal]则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了图像学,她指出,艺术史中既有的图像学分析强调的是图像的共性,如类型史,而不注重探究特定图像在特定观者身上所引起的特定反应。图像学虽可宣称是为分析图像而发展起来的独特方法,但自相矛盾的是,它实际上却忽视了图像的特质。
巴尔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即是一个“事件”,观者与图像相遇,事件便发生了。由此,艺术作品是动因[agent],是观者的经验、观者的主观反应的积极生产者。符号学艺术史的终极任务是在分析图像的同时解释图像,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究为何以这种方式解释这个或那个主题,并将图像固定于解释,将解释凝固于图像。她认为,这样就能诉诸图像的特质。
夏皮罗[Meyer Schapiro]是艺术史领域中第一个运用符号学分析探究视觉艺术的学者。1969年,他发表了“论视觉艺术的符号学问题:场所、艺术家和社会”。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对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与考察其社会文化史相结合。尤其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所看的图像与图像所在的表面(基底)与图像的多种架构方式问题之间的关系。夏皮罗的论述范围极广,从洞窟绘画到埃及艺术,直到20世纪艺术,探究不同的架构手段是如何使艺术家驾驭图像符号的。为了创造意义,人物可以各种方式加以摆布,如神的右侧依据画框的关系而加以安排、扩大、提高或放低。
这篇论文虽引起极大的争议,但不能说是系统地运用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只有“新艺术史家”才开始较系统地运用符号学。布赖森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词语与图像:法国旧王朝的绘画》中,他探索了语言般的艺术特质,艺术与实际书写语言的关系,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他意在考察艺术作品的开放性。对他而言,一个图像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符号,而是开放的、在图像与文化环境中产生多层重叠效应的符号系统。对他而言,符号学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使之认识到艺术乃是社会中的动力,而符号视觉通过图像、观者和文化进行“传播”。此处,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的“交织性观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克里斯特瓦强调符号的相互联系性,符号不是“封闭的”,互不连接的微小的意义单元,而是更大的上下文的组成部分。她发展了符号交织的观念,以探究文本或符号互相指涉的方式。她将文本放在两条轴线上:横轴线把文本与另外的文本联系起来。共享的代码把两个轴线合成一体,因为,按照克里斯特瓦,“每一个文本从一开始就处于将宇宙强加于文本的其他话语的权限之内。”它有赖于符号的创造者和解释者去激活这种联系。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思想中,“交织性”成为极端重要的观念。(注:《语言的欲望:文学与艺术的符号学取向》[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New York,1980年。)
法国艺术史家马兰[Louis Marin]在《阿卡迪亚牧羊人》[The Arcadian Shepherds]中论述了使用符号学理论必然面对的挑战。如何将主要发展于语言的符号学恰当地用于解释视觉艺术,他集中关注“直证”或“直指”的问题。
每一言语存在于空间与时间之中:它在一个将之带到一起的特定的上下文中,由说者(发送者)发出,发送给听者(收者)。一个言语的直指特征,包括个人发声、动向和关于时间、地点的副词之类的东西。其难点在于:我们如何将之转译到艺术作品上去,尤其是普桑之类的历史画上去,因为这类历史画并不向某人诉说。
马兰指出,除了这幅画的物质存在,除了我们正在观看这幅作品这一事实之外,图像本身丝毫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它的传递和接收方面的情况。画中虽有一个人物的视线射向画外,但全画并非诉诸观者,作为观者,我们仅仅看到画中人物各行其是,他们仿佛并不需要我们而演绎其故事。此画以如此方式掩盖了其“发音”结构,然而,奇妙的是,掩饰其发音结构及其作为再现的外观恰恰是该画的主题。牧羊人在墓碑上辨认“我也在阿卡迪亚”[Et in Arcadia ego]的字样,辨认以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方式诉诸牧羊人的字句,因为句中缺少动词,I too in Arcadia是拉丁原文的字面翻译。(注:《走向视觉艺术的读解理论:普桑的“阿卡迪亚牧羊人”》[Towards a Theory of Reading in the Visual Arts:Poussin' s' The Arcadian Shepherds' ]。)马兰的读解,涉及到微妙的文本与视觉分析,显示了雅各布森模式即传达作为绘画主题的威力,在此,画家或观者取代了建构这一模式的语言学家的位置。马兰的论文在两个方面提示我们:理论并非是简单的,理论不但可以用于解释艺术,而且对艺术的解释能改变我们对理论的理解。
四、图像与语词
后形式主义、图像学和符号学,都将艺术的核心问题阐释为“语言与图像”的问题。在形式主义那里,虽然“语言”是一个隐喻,用以突出“形式”成分的重要性与自主性,但在新艺术史家眼里,这种形式等同于符号,将之看作“文本”的构成部分。克劳斯即希望借助符号学解释“形式”。因此,“语言与图像”的问题包含下述几个子问题:什么是图像与文本的关系?视觉图像是否仅仅是文本的图解?图像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对话形式吗?当艺术史家运用文字解释图像时,这意味着什么?
图像与文本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论述诗歌与绘画的平行关系。荷拉斯的名言“诗如画”更是建立了它们的姊妹关系。在西方历史上,关于图像与语言的关系的争论,可谓是一场“符号之战”。所以,米切尔[W.J.T.Mitchell]将图像与语词喻作说不同语言的两个国度,但它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漫长的交流与接触的关系。他的意思是既不要打破它们的国界,也不要加强它们的区分,而是保持它们之间的交流永不中断。因为作为解释的过程,视觉再现与言词表达有其各自的形式特性,即使它们通过先前的艺术实践和社会、政治上下文而相互关联,情形也是如此。
然而,艺术史家是以文字为媒介来探究图像的,以此为论,图像产生文本。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学科越来越觉得自己面临“图像与语词”之间的固有困难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布赖森和巴尔等文学批评家带着符号学的武器跨进了图像世界,而在图像世界里的艺术史家也指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启示,更好地缓解图像与语词的紧张关系。但是,由于布赖森等“新艺术史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图像读解训练,他们力所能及的是用既定的符号学理论套用到图像解释上去,或搜寻可以运用他们的理论解释的图像,而他们的大胆推测,虽有时给专业艺术史家带来某些理论上的启示,但就理解艺术史本身而言,经常显得比较幼稚,反而加剧了“符号之战”,造成两个对立阵营:新艺术史家谴责专业艺术史家轻视言词与理论,而专业艺术史家指责新艺术史家忽视图像。米切尔和布赖森、巴尔一样,来自文学研究领域,他承认自己的介入,加剧了紧张气氛,仿佛使艺术史领域被“文学帝国殖民化了”。(注:《图像志:图像、文本、意识形态》[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Chicago,1986年,p48。)
处于艺术史学科心脏的“图像与文本”问题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正是这个学科的魅力所在。从歌德到肯尼思·克拉克,直到当代的艺术史家,都感到艺术史的言语在某种层面上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有些视觉特质是难以用言词表达的。巴克森德尔不但同意这一点,而且还怀疑艺术史家究竟能否做到把“视觉”因素放在其研究的首要地位。他在《意图的模式》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不是对图画本身作出说明:我们是对关于图画的评论作出说明——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我们只有在某种言辞描述或详细叙述之下考虑图画之后,才能对它们作出说明。”(注:《意图的模式:论图画的历史说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p1。)如果艺术史家以为自己直接针对的是视觉图像的本体,那么他或她不仅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读者。克劳斯也深知此理,感到难以直接描述视觉形式本身,因而指望借助符号学来克服这个难以逾越的困难,事实上,她并没有具体指明究竟在哪些方面符号学可以帮助艺术史家走出困境,这表明她实际借用符号学回避了问题。美国艺术史家萨默森认为,符号学和其他新理论都无法改变艺术史的本质:即艺术史是根据风格序列将艺术作品置于特定时间和地点进行考察。由此,他认为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把形式分析与图像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综合的方法,他称之为“后形式主义”。(注:萨默森[David Summers],《真实空间》[Real Space],Phaidon,2003年。)可见,欧美当代艺术史学始终是在“语言转向”与“图像转向”的张力之间摸索一套一套化解“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对立、解决“文本”与“情境”的复杂关系的方法与理论,力图更理性地探究视觉艺术的永恒品质及其与使之产生的历史文化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