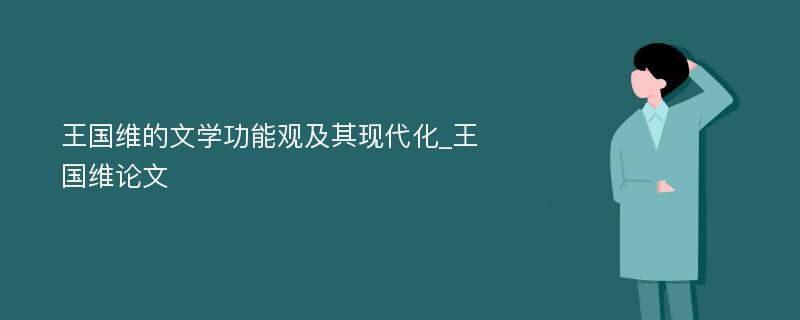
王国维的文学功能观及其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王国维论文,功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化进程,已有很多人把起点定在王国维那里。对王氏的价值重估,是带着对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和重建的自觉的。王国维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堪与传统划清界限的新质,以至于可以把他算作文学现代性的起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几千年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挞伐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对文学独立价值的强调。如果说梁启超只是掀开了现代性文学观念帷幕的一角,那么到了王国维,这个帷幕便开始在徐徐地拉开了。梁启超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虽然涉及到了汉语现代性和体裁的现代性问题,但还限于局部,并带有新旧杂陈的特点。而王国维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和文学的独立价值,则找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关键。
王国维略成体系的美学思想大致有以下基本构件:无用说(美的性质论)、慰藉说(文艺价值论)、天才说(创作主体论)、古雅说(审美范畴论)、意境说(文艺理想论)。“非功利”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核心,并且是他整个美学思想的基础。他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是其“非功利”美学思想的自然的逻辑延伸。
王氏没有对“非功利”问题进行专门、集中的论述,但从其不同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对此的论证和理解。其有关的思想基本上没有什么创见,主要来自三个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叔本华。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注: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以下所引王氏文章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该书。)一文里,王国维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
他首先用康德的“美在形式”的观点加以论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一章里认为,美只涉及表现形式,不涉及对对象的存在,与概念、利害、欲念无关。这种形式之所以能引起美的快感,是因为它适合人的认识功能——想象力和知解力,使这些功能可以自由活动并和谐合作。王国维说,西方把美分为优美与壮美两种,不同的哲学系统对二者的解释不同;但要而言之,优美“由一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壮美则“由一对象之形式,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至于壮美的对象,康德虽然说它无形式,然而这种无形式的形式能唤起壮美之情,所以可以视之为形式的一种。那么,怎么解释艺术作品的内容性的因素呢?王国维解释道:“就美术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于形式固不俟论,即图画诗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焉。”他把小说、戏剧中的人物都看作“材质”。王氏对形式与材质关系的辩析与席勒的观点很相近:“美只是一种形式的形式。我们称它的素材的东西,只能是赋予了形式的素材。”(注:席勒:《论美书简》,《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9月。)所以王氏的解释也可能受到了席勒的启示。他们的观点虽然在逻辑上能够说通,但不免牵强。康德提出过“纯粹美”和“依存美”的分别,前者是有符合目的性而无目的的纯然形式的美,后者即依存于概念、利害计较和目的之类内容意义。康德的“美在形式”主要是就纯粹美而言的,而他在“美的分析”里根本没有提到的诗和一般文学则不能不涉及内容意义,这样就要归到依存美。(注:参阅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2版,下卷,365—368页。)显然,王国维和席勒要把“美在形式”的逻辑贯彻到所有的艺术作品中去。
他又从审美作为一种认识方式的特性的角度来阐明美的非功利性。他这方面的思想主要来自叔本华。叔本华在自己的哲学体系里展开了这个被康德系统论证过的美学命题,使之成为其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叔本华的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重直观而贬理性,认为只有从直观出发,才能认识到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的本质。王国维介绍说:“至叔氏哲学全体之特质,亦有可言者。其最重要者,叔氏之出发点在直观(即知觉),而不在概念是也。……彼之美学、伦理学中,亦重直观的知识,而谓于此二学中,概念的知识无效也。”(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在叔本华看来,审美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所具有的最基本的规定性是对理念的纯粹直观。他说,审美“突然把我们从欲求的无尽之流中托出来,在认识甩掉了为意志服务的枷锁时,在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欲求的动机,而是离开事物对意志的关系而把握事物时,所以也即是不关利害,没有主观性,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版,274页。)。在《红楼梦评论》中,王氏具体运用了叔本华的审美直观理论。他用“欲者不观,观者不欲”来概括审美直观的主观条件。美中的优美、壮美都能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不过它们的产生有着不同的心理方式。“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观其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面对优美的对象,直觉是自然地发生的,而壮美的对象之于人情况就复杂得多了。王氏的解说远非清晰,不过把这里的话与《红楼梦评论》里对壮美的解说联系起来,可以大致理解他的意思:壮美的对象对人们的“生活之意志”构成了威胁,但“意志”又无法克服这种威胁,于是“意志为之破裂”;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唤来了理性的帮助,认识到壮美的对象对自己的威胁并不真实,这样经过一番斗争,终于能“达观其对象之形式”。与优美、壮美相反对的是眩惑,王举了例子:“如炬籹蜜饵,《招魂》、《七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昉、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亭》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赝《秘辛》”。“眩惑”使人执着于“生活之欲”,直接妨碍了审美直观。
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胜任审美直观的,这往往是天才的专利。作为审美创造物的艺术则是天才的游戏的事业。王国维说:“‘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康德——引者)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注:《文学小言》。)他在别处说过的几句话可以看作“游戏的事业”的解释:“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注:《人间词话删稿》,徐调孚注,《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版。)康德认为艺术是天才的创造物,而与游戏相通的自由是艺术的特征。不过,王氏的命题更多的是叔本华的天才论和席勒的“游戏冲动”说的结合。叔本华说艺术是为天才所掌握的认识方式:“天才的性能就是立于纯粹直观地位的本领,在直观中遗忘自己,而使原来服务于意志的认识现在摆脱这种劳役,即是说完全不在自己的兴趣、意欲和目的上着眼,从而一时完全撤销了自己的人格,以便(在撤销人格后)剩了为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明亮的世界眼。”(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259—260页。)所以正如王氏所转述的:“美者,实可谓天才之特殊物也。”(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至于王的命题与席勒的关系,他自己说得明白:“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希尔列尔(席勒——引者)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注:《人问嗜好之研究》。)。
审美直观和艺术的目的是“非功用”的。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专门论证哲学、艺术的独立性,首先提出它们的价值所在:“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王氏在《叔本华与尼采》中引述叔本华的话:“夫美术者,实以静观中所得之实念,寓诸一物焉而再现之。由其所寓之物之区别,而或谓之雕刻,或谓之绘画,或谓之诗歌、音乐,然其惟一之渊源,则存于实念之知识,而又以传播此知识为其惟一之目的也。”“实念”即是“理念”,这是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在他的哲学里,意志是世界的本质,理念是其直接的客体化,意志是通过理念才间接地客体化为作为世界存在方式的各种表象的。也就是说,理念是意志和表象的中介。意志就像康德的物自体一样作为终极的存在,是无法认识的,只有作为其客体化的理念才能被认识。而“艺术的唯一源泉就是对理念的认识,它唯一的目标就是传达这一认识。”(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258页。)。这正是艺术天才的任务。王国维除了早期的个别文章外,没有再袭用“理念”一词,表明了他努力啄破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外壳,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的自觉。文学以表现真理为旨归,所以追求利的“餟餔的文学”与追求名的“文绣的文学”一样决非真正的文学。(注:《文学小言》。)
总而言之,审美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是对真理的纯粹直观,而审美直观是为艺术天才所能胜任的工作,艺术是天才的游戏的事业。那么,审美直观与“美在形式”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王国维有一段话涉及到这个问题:“美之对象,非特别之我,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夫空间时间,既为吾人直观之形式;物之现于空间皆并立,现于时间皆相续,故现于空间时间者,皆特别之物也。既视为特别之物矣,则此物与我利害之关系,欲其不生于心,不可得也。若不视此物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观其物,则此物已非特别之物,而代表其物之全种。叔氏谓之曰‘实念’。故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这里面的关键词是“种类之形式”、“物之全种”、“特别之物”,前两者与后者存在着二元对立式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审美的对象非现于时间、空间中的具体之物(特别之物),不会使人产生利害之心,执着于具体的物,所观照的形式是“代表其物之全种”的普遍的有意味的形式(“种类之形式”),也即是实念或者说真理的所在。叔本华的哲学没有谈到审美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的区分,王国维显然是想把康德的美在形式说与叔本华的审美直观说结合起来,只是尚欠融会贯通。
功利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要传统。对文艺的功用,孔子有“兴观群怨”与“事父”、“事君”之说(注:《论语·阳货》。),即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汉代在先秦儒家“诗教”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正统的文艺观。《毛诗序》要求诗歌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提出诗歌的“美刺”作用:“美盛德之形容”,“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但又必须遵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唐宋文人、道学家又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明确把文章视为宣道的工具。余波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初的桐城派等文学流派,可谓经久不衰。注重政治教化作用成为延续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学观念,对历代作家和文类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晚清,由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在传统注重政治教化作用的文学精神的制约下,文学又被要求成为开通民智的工具。
王国维的“非功利”的文学功用观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中以儒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以及晚清文坛以文学为新民之道的主流文学观念。《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以主要的篇幅批判了中国“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以哲学、艺术为“道德政治之手段”——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娼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娼优蓄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他还把是否把文学当作工具看成是文学盛衰的原因:“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个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注:《文学小言》。)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攻击晚清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工具论倾向,并指斥把文学视为政治、教育的手段:“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
王国维坚决反对功利主义,正是为了倡导自己的以功利主义为对立面的文学观。他相信一个基本的文学命题: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在《红楼梦评论》中他就说:“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又说:“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他声明这是“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其实王氏私淑的叔本华也说过:“我们要求的,不论是诗是画,都是生活的、人类的、世界的反映。”(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349页。)反对文学上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正是为表现人生开辟广阔的道路。
那么,怎样才能表现好人生呢?这就要做到“真”与“自然”。“真”与“自然”是贯穿王国维文论的基本概念,其中心要求是真切地表现真切的人生经验。这种文学主张今天看来似乎稀松平常,但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相对于种种为功利主义所障蔽的文学观念,还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的。“真”是目的,“自然”是实现“真”的方式方法。在王早期的论文中,“自然”往往指的是自然界,与它作为文论的概念不同。在表达“真”的诉求时,他常常与功利主义的东西相对照。因为在后文的论述中,将有大量的材料能够说明王氏对“真”的诉求,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自然”的涵义。“自然”包括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表达两方面的意思。他在谈元曲时说:“元曲之佳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注:《宋元戏曲史》十二,《王国维遗书》十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版。)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解除了种种主观的障蔽,从而反映生活的真实,抒发真情实感,即实现“真”。元曲“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注:《宋元戏曲史》十二,《王国维遗书》十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版。)可见他并不反对写政治等内容,关键在于不能以功利的“政治家之眼”,而应以解除了主观障蔽的“诗人之眼”来写。(注:《人间词话删稿》三七则。)他又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习,故能真切如此。”(注:《人间词话》五二则。)前一个“自然”指解除了主观障蔽,“自然之眼”即“诗人之眼”,后一个是就表达而言的,指的是表达上的真切。用王国维译的叔本华的话来说,“自然”就是要“解自然嗫嚅之言而代言之”(注:见《红楼梦评论》。)。那么,前一个“自然”是“解自然嗫嚅之言”,后一个是“代言之”。纳兰容若之所以能做到“自然”,是因为他没有受到汉族功名利禄的思想观念的束缚。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五七则中写到:“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其中的要求显然包括了作家心态和艺术表达两个方面。他在词话中多处表示反对“隶事”,要求“不隔”。(注:《人间词话》三十六则、三十九则、四十则、四十一则。)
对于诗词来说,真切的人生经验即真情。他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诗经》里的一些诗句道:“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把“感自己之之感,言自己之言”看作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这些文学天才人格和文章的独特标志。在《人间词话》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注:《人间词话》一六则。)又如:“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注:《人间词话》一七则。)王氏强调真情,与晚清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人不同,在他那里,真情具有本体的意义,而龚自珍等人提倡真情只是具有一定的个性解放和文学革新的意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经世致用为鹄的的。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里说过:“诗之外有事”。
其意境说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真切地表达真切的人生经验。所以王国维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也。”(注:《人间词话》六则。)或许他在《宋元戏曲史》里对意境的解说更清楚一些:“元剧……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也。元曲亦然。”(注:《宋元戏曲史》十二。)这是对文学作品的本质性规定,尽管对诗词这样的抒情性文类还需有具体的规定性。正因为如此,王国维才说他所拈出的“境界”或者说“意境”比严羽的“兴趣”、王士禛的“神韵”为更探本之说。(注:《人间词话》九则。)所以,在对“意境”众说纷纭的解释中,我同意叶嘉莹的观点:“《人间词话》中所标举的‘境界’,其涵义应该乃是说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193页。)
王国维不遗余力地反功功利主义,大力倡导“真”与“自然”,但我们不应误认为他不承认文艺的功用。即便在康德那里,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他否定文艺的社会作用。为了分析的方便,康德把审美当作独立的抽象的心理功能,而与利害、概念、目的等内容意义剥离开来,从而追寻纯粹的美的本质。然而这样以来,审美判断也就远离了现实中丰富多彩的具体的美,于是康德在谈到“美的理想”时又表明,纯粹美毕竟带有假想性质,很少的美能符合它的标准,因此理想美只能是依存美。提出“美的理想”不在于自由美,而在于依存美,这与康德对美的本质的分析是矛盾的。这个矛盾康德无法解决,它来自其基本的思想方法。(注:以上对康德的评述依据《判断力批判》上卷的第一部分第一章“美的分析”,同时参考了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十二章。)王国维是一个文学家和美学家,对文艺的功用比康德有更具体而充分的认识。王并非否定文艺之用,他和功利论者的区别在于文艺之用的内涵及实现方式上。他的文艺功用观用他自己用过的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无用之用”(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国学丛刊序》。),这个来自《老子》的词语本身即巧妙地寓示着“用”与“不用”的辩证关系。他所说的“无用”之“用”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指的是现实政治层面上的“当世之用”或者说经世致用。
王氏认为,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慰藉人生的痛苦,这是艺术的认识论的价值在伦理学上的体现。这种艺术价值观直接来自叔本华的哲学,在《红楼梦评论》中有集中的表述。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这是人的生活意志的表现。有欲望则求满足,而欲望无厌,总难得到满足,所以人得不到最终的慰藉。即使欲望得到完全的满足,厌倦之情又会乘之而起。“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只有艺术能当此重任,作为天才的艺术家“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王认为:“《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叔本华说:“人之意志,于男女之欲,其发现也为最著。”《红楼梦》中的青年男女多为男女之欲所苦,而主人公贾宝玉能迷途知返,拒绝意志,削发为僧,真正实现了自我解脱。所以,“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他又说:“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在他看来,政治家给予国民的是物质上的利益,文学家贡献出的是精神上的利益,而物质上的利益是一时的,精神上的利益永久的,所以他才会得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的结论。(注:《文学与教育》(《教育杂感》四则之四)。)
在慰藉说的基础上,王国维又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美育构想。慰藉说和古雅说是他的美育理论的两个理论支点。从他的《人类嗜好之研究》、《去毒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慰藉说走向美育的思想路径。人因为有空虚的苦痛,所以需要慰藉,于是就有了各种嗜好。嗜好有高尚、卑劣之分,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高尚的嗜好和趣味。而能慰藉国民感情的是宗教和文艺,前者适合于“下流社会”,后者适合于“上流社会”,可以说艺术是“上流社会”的宗教。在艺术的慰藉中,文学的最大,因为文学作品普遍、便利,非其它艺术门类可及。
问题是,既然艺术是天才的作品,远离芸芸众生,那么美育如何成为可能呢?王的古雅说是架设在慰籍说的其美育思想之间的桥梁。真正的艺术作品固然是天才的创作,但世间又有虽非真正的艺术品,但决非实用品的可以称之为“古雅”的作品。相对于优美、壮美这两种“形式”,古雅可谓“第二之形式”。通俗地说,古雅是能通过修养获得的艺术技巧方面的因素。古雅具有美育的价值:“至论其实践之方面,则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虽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创造优美及宏壮之物者,亦得由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又虽不能喻优美及宏壮之价值者,亦得于优美宏壮中之古雅之原质,或于古雅之制作物中得其直接之慰藉。故古雅之价值,自美学上观之诚不能及优美及宏壮,然自其教育众庶之效言之,则虽谓其范围较大成效较著可也。”(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所以,古雅又是架在天才和大众之间的桥梁,为两者所共喻,使美育成为可能。
王国维以“非功利”为旗帜的具有潜在体系的美学思想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因为中国有着二元论的思想传统,感性生命与道德理性始终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中国向来有情礼、理欲之辨),挣脱了传统政治教化的羁绊,强调审美独立性的美学和文学观念,就必然会要求文艺话语更充分地表达个体的感性诉求,从而证明感性生命的合理性,为文艺表现人生开拓广阔的空间。我认为,这是王氏文学观念的现代性的根本所在。
应该看到,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中,王国维的文学观是带有明显的局限的。自从封闭已久的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建立一个现代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国人梦寐以求、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文学当然不应自处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活动之外。王国维过于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和文学的独立价值,没有解决好“用”与“不用”的关系问题,其文学主张回应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并与主流文学观念相龃龉。
王国维当时即位于文坛的边缘,辛亥革命之后,他告别了文学研究,在文学上就声名沉寂了。无论是在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王氏文学思想中事实上被重视的只有他的更多地被看成是传统文论总结的意境说。
对王国维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价值重估得益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知识状况。在文学研究上,继1985年的“方法年”之后又有1986年的观念年,伴随着对主流文学观念的反思,人们开始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人们似乎发现了王国维。之后,有关的研究论著大幅度增加。王氏在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得到高度的评价,一些文学批评史教材把王国维放在了现代性的起点了(注:如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一章即“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非功利”文学观念的合理性受到重视。王国维的美学和文学思想终于完整地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
王国维是一个抡开山斧的人物,他从文学功用观的角度,对中国几千年的功利主义文学大加挞伐,从而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可谓找准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关键,因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肯定文学的独立价值,把它建设成为一个以自主性为首要特征的社会活动领域都是文学现代性的中心任务。在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都处于一个未成熟的状态,王国维也只是迈开了一步,揭示了一种可能。不过,把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历程与他的文学观联系起来加以审视,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我们警醒的东西。
标签:王国维论文;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宋元戏曲史论文; 现代性论文; 读书论文; 人间词话论文; 康德论文; 美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叔本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