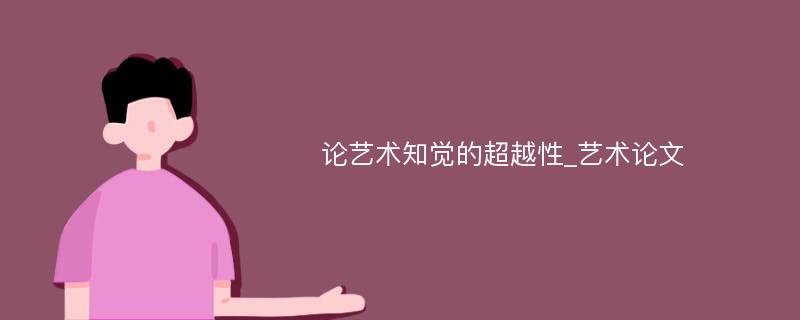
论艺术知觉的超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觉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9-0054-04
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在知觉中怎样从“物质性关联”转化为“诗性关联”的关键,在于知觉改造。这种改造不是在知觉形成结论以后,而是在知觉过程之中进行的。知觉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在摄取客观世界的刹那间,就在自身所依存的主体的全部精神内容的参与下,迎遇客体投射过来的信息,并既是客观地同时也是创造性地构成心灵的感受。那些没经科学研究意图和艺术创作欲望支配,每时每刻随意发生的目之所见(视觉)耳之所闻(听觉),舌之所尝(味觉),鼻子所嗅(嗅觉),体之所动(动觉)等感觉基础上形成的知觉,在类别上可称为日常感知觉。对这些日常感知觉再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构成要素中,客观物质属性的映象是最基本的原生状态。如直觉黄果树瀑布的表象收获。这种表象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黄果树瀑布的客观景象。再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日常感知觉中含蓄着科学知觉和艺术知觉的基因。它的客观真实性可以发展成为科学知觉,主观选择性又可以发展成为艺术知觉。关键是看知觉主体是以什么样的心理值(莱格所使用的用来衡量分配某一种特殊的心理要素的心理能量的计量尺度)为主导。由于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心理值不同,他们从日常感知觉中所获取、所建构的东西就大为不同。
一、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的弱化与消解
当我们知觉一个对象时,对象的许多信息传入大脑并促成我们对这一对象的了解和把握。这时,一种可称之为知识性的认识随之而展开。因而,知识性认识是知觉又一显著特征。比如法国西南部出土的“蒙特加特指挥棒”,上面所刻绘的海豹、蛇、鲑鱼等形象是动物季节发情的符号。这就是原始人在反复知觉季节变化后,对每次季节转到春天动物就会发情的现象所作的知识性认知结果。知识性认识是知觉直接了当最普遍的精神现象。人在知觉中,能由表及里地进行深入的认识活动。比方说,当天我们看到天边雷声不绝,狂风大作,知觉马上就在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这是大雨将临的迹象。
由于知识性认识是知觉最普遍的精神过程,它既为科学思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艺术思维奠定了了解把握认识客体的基础。但是,对艺术思维而言,在知识性认识这一过程中,主体又必须及时消解或弱化知觉中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超越物质对象自身严密的规律性“陷阱”,摆脱对象知识性结构所可能对主观情感意志等个性化内容产生否定、排斥的强大引力,否则,艺术思维的翅膀就不能凌空腾越。例如,我们身处草原,知觉到草的生长情况,如果,此时,我们的心理值是求解大自然的规律,那么知觉就会对草原一岁一枯荣的现象作知识性认识。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迷恋沉浸在草这类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生态习性之中,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变成生态学家,植物学家。我们对草的知觉模式中,就会塞满草的规律性习性。艺术在这种知觉中便不可能产生。但是如果我们在知觉中,并不迷恋关注草的本质属性,我们在知觉中消解或弱化知性要求,或者穿越它们把主体在草的枯荣与人生的境况,与个人的命运、感悟结合起来,人与草的关系就不再是物质性关联,而是一种诗性关联。在这一基础上,才会产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篇。
从西方绘画史的发展过程看,知觉在处理人与客体的关联时,有一条越来越明显的在知觉中不断加大对对象作知识性的客观描述手法的超越。具有写实主义开山大师之称的佛罗伦萨的菲力波·布鲁涅列斯奇(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创造的透视理论,对美术有极重要的价值。他利用数学,得出一条线性透视公式:各条线后退会聚于一点之上,在这之上它们仿佛消失掉了。透视理论是三维绘画空间的重要基石。应该说,这是对客观对象在空间中的一种知识性认识。利用这种理论,知觉对象时,对象的各部位在空间中的位置就会如同客观真实一模一样被复制为表象。但即或是受过良好透视理论熏陶的观察主体进行艺术思维时,知觉也依然时时要超越知识性认识,而实现主观要求。美术史家萨拉·柯耐尔认为“布鲁涅列斯奇的透视理论,使早期文艺复兴的美术家能在一个场景内强调对心理上关系的某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的确立,它时时在消减或弱化着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在西方美术史的进展中,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要更多地表现或传达主体的认识感受,艺术知觉对客体的物质属性的超越一步步强烈。到当代的莫奈、凡·高、蒙克、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艺术家那里,知觉被主观因素自由地驾驭着,以至于以他们的作品中已找不到或很难找到与现实的相同的对应物来。
对感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的弱化或消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一种特性。特别表现在老庄和道家思维形式之中,庄子提出了几个重要范畴,如“心斋”(《庄子·人世间》)“坐忘”(《大宗师》)“丧我”(《齐物论》)“无己”(《逍遥游》),就极重视对感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的消解。从一般表面意义看,“心斋”、“坐忘”、“丧我”、“无己”好象非但不是强调“人”,强调主体精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否定“人”并趋向于“物”。其实深研进去,就会发觉“丧我”、“无己”并非是把主体的人消除掉,而是要清除主体中“为物所物”的那部分东西,要排除主体的“物化”功能,使主体对客体的知觉和把握获得一种自由的精神主体性。“绝圣去智”是老子的最高口号,在庄子这儿发扬光大。他强调“丧我”、“无己”就是要“丧”去我之中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一种物利。人只要有物利、就会为“物所物”。“物利”会逼使人在知觉中,过份关注客体的物质规定性,因而知觉也就会为客体的规律、本质所含蓄,最后深深陷入到知识性认识之中而不能超拔出来。比方说,巴尔扎克作品之中的高老头,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他的观念中,金钱、财产等同于生命,他的知觉自然就“为物所物”。他只关注那些怎么能保证金钱不贬值并不断增值的方法手段。生命本身的意义被金钱异化了。这类人的知觉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建立什么“诗性关联”的,艺术也不可能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长养出来。庄子的“丧我”、“无己”,实为护“我”而有“己”。这就是对知觉物化属性的消解方式。他的“心斋”、“坐忘”的主旨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大宗师》)。其实也就是通过铲除生理欲望,罢黜对世界的知识性认识,从而达到对物化属性的消解,成为“至人”。这种生命哲学极近似于艺术思维,它在知觉领域建构了与客体的“诗性关联”。青源惟信禅师有段著名的语录,揭示了一般日常感知觉和艺术感知觉的巨大差异:
老僧三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第一次“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一般日常感知觉的结果,是对对象的客观真实的知觉记录。但在主观值大量地投入下,也就是说主体在与山水熟识过程中,个人的人生际遇与这里的山水发生关系,主体心理值趋向把自身的主观情愫投入到对象上去。这里再知觉这山这水时,知觉的“内在图式”发生了变化,主体消解了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比如山是否是喀斯特地貌等的认识),超越了日常感知觉层面,迅速建构起艺术的知觉世界。所以,此时的“山”“水”不再是一种物质属性的东西,它是承载主体精神情感内容的符号。它所引起的知觉表象就不是在知性结构中产生识别,分析作用的那种表象,而是凝聚着与主体生命历程紧密关联着的人和事以及附着其上的喜怒哀乐等现象。因之,“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次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知觉结果,告诉我们,这种知觉与第一次的全客观描述不同,与第二次纯主观感受也不同,它是在参禅的至境中,将对人生更深层次的体悟,对生命的自然形态,也就是对“禅境”的体悟转化为更高皈依,把“天”“地”“人”紧密地融汇在一起,复归自然之道。因而才“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山这水是自然之道,是生命之貌。青源惟信大师对山水的三次知觉过程,极生动地说明了在消解知觉知性成分和物质属性后,知觉将人与客体的关系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一种“诗性关联”。
二、精神主体和人化属性的建构
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的消解与精神主体和人化属性的建构是同步进行的。为着分析的需要,专门分开加以阐述。
精神主体作为能充分体现主体自由本质的精神能量,能够在较大范围内超越世界的物质性樊篱,冲破各种物质的规定性。它是艺术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本质体现。因而,在艺术领域内,思维一旦启动,精神主体类似“内在图式”的功能一样,积极主动甚至是霸气十足地支配着知觉活动。“这一个”主体的全部人生经验和审美态度被投放到知觉之中,使知觉不再是那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知识性结构。例如大雁,作为候鸟,对鸟类学家来说,秋去春来是极自然的现象。他们对大雁的知觉绝对排除个人的人生体验,而专注于大雁为生存择地而居的规律。艺术家则不然,他们知觉大雁南来北往的现象时,精神主体将“自我”的人生体验投入进去,消解对象“物”的规定性,以主体全部精神背景建构着这一知觉。于是,大雁那种与人毫不相干的,因气候原因北飞南迁的生存状态被赋予了“人”的意韵,获得了艺术品质。惟其如此,才有李清照“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的人生喟叹。正因为艺术知觉是精神主体对客观事物的“霸权性”干预的结果,客观对象的非艺术性品质才能转化为艺术性品质,才能构成艺术,才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萧瑟秋风中的一片落叶,皓首百发中的一根青丝、深刻变革中的冲突,塞外边关的画角……“,生活中的林林总总全都有它们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它们固的的物质性品质,有它们自己的运动形式和规律,有自己的走向和意义,与艺术本是没有太多的关联。但在精神主体的干预下,经由主体个人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态度建构起来的知觉观照中,“万物皆备于我”。它们无不被主体赋予全新意义而获得艺术品质。
科学知觉中心理能量的投入不能超过对象的规定,否则对象就可能变得“面目全非”。艺术知觉则相反,主体投入的心理能量时时在消解着知觉中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而且随主体意愿的霸权性投入,对象被扭曲变形……。俄国著名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反常化)。这个很有影响的理论。这一概念的本意是“反常化”,只因什克洛夫斯笔误少写一个字母,而被误读作“陌生化”。什氏的意见是指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不是故事,而是使之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这种东西。他在研究大量的作品后,发现造成“文学性”的主要原因是作家对描写对象采取了一种反常化描写方法。这种方法最主要的作用之一是把取自现实中的各种材料进行变形处理,使之“违背”或“偏离”现实或超越一般感觉,而成为艺术的新的构成元素。“陌生化”理论只是从形式上说明了文学性建构的方法。其实这一方法的本质就是我所确立的“人化思维”。在这一步法中,思维主体的心理能量以绝对优势压制着客观实在能量,思维是“人化”而不是“物化”的。因此,真正的艺术精神,并不是要去实现我们长期奉为圭臬的“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再现事物”,而是在艺术创造中完成自我表现。当然我并不反对人化思维在艺术中再现事物的客观形象,而是反对把“再现事物”作为艺术之所以艺术的必要前提,它不可能成为必要前提,只能是目标之一。否则艺术与科学就没有本质区别了。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感知觉中就投入了较多的主体心理能量,使“陌生化”效果蔓延在整个字里行间。请看:“日炽的阳光……晒着父亲棱岸的肩膀和两只崎岖的大脚”。(《爆炸》)有人认为以棱岸修饰肩,崎岖修饰脚不规范,因而拙劣。其实这正是莫言在感知觉中以主体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对象进行的审美歪曲。从一般感知觉看,脚只有大小之差,无崎岖顺畅之别。但在莫言的主观图式中,投入了父子两辈人的全部艰难的辛酸。他对父亲那两只在土上蹭。石上磨、沙上蹈、水中趟的双脚的认识,早已超越了脚的具体形状。崎岖的人生之路的崎岖性质,被对象化地积淀在他父亲崎岖跋涉的大脚之上。因此,崎岖修饰脚已不是语言学上的修辞学问题,是主体对对象的超越性认识,是主体在个人人生际遇中所体验的主观认识和情感,对对象进行“歪曲”式的“陌生化”处理。
“陌生化”作为主体心理能量的一种表现力,本质上就是精神主体和人化思维的一种运作方式。因此,精神主体性和人化属性和人化思维的一种运作方式。因此,精神主体化和人化属性的建构对艺术而言,是必要前提。无此,客观万物就只能冰凉地存在于它们自足的体系之中。精神主体性的“霸权”建构,是改变客观物质属性的关键、经它处理的万象世界就被赋予了“人化”属性。华兹华斯认为:
“物象的影响力的来源并非来自固有的物性,亦非来自本身之所使然,而是来自与外物相交往受的外物所感染的智心所赋出的。所以诗……应该由人的灵魂出发,将其创造力传达给外在世界的意象。”
那些认为在艺术中将自己完全隐藏起来,或如意象诗人庞德和威廉斯那样,“完全”按自然原状加以描写:“找出明澈的一面,呈露它,不要加以解脱”(庞德)。“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随后追加的意念强烈地感应和观看事物,体现实有”(威廉斯)等观点实际上是忽略了诗人(艺术家)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时,主体知觉对对象已做过的“人化”处理。这时主体已不自觉地在“解脱”或“先入为主”地感应和观看事物的。西方意象派诗人宣称,他们从中国山水诗中找到一种完全抛弃主观因素,能够揭示出自足自化的客体世界的无穷魅力的方法来,仿佛客观物象本身是艺术,只是将它们拼合过程中,千万要将主体可能进行的侵蚀消除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威廉斯的《楠塔基特》(Nantucket)。
透窗的花朵/淡紫与黄/被白色的帷幕改变——/干净的呼息——/午后的阳光——/在玻璃的盘子上/一个玻璃杯壶杯子/倒放、旁边/一根横放的锁匙一和那/全然干净的白色的床
表面上看,这的确仿佛是纯客观的描画,仿佛主体心理内容被剔除殆尽。但是稍加领悟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纯客观”的背后有一双主观投注的视线。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诗的意象。从色彩上讲这首诗给我们一种明亮甚至有点明媚和绚的感觉:紫黄的花朵、白色的帷幕、床、透明的玻璃杯和银色的锁匙,在这些色调上再投上午后的阳光,以此烘映出浅色中的温暖,冷调中的洁净,静态中的漫温。静物的组合构成触发了一种愉快的、开朗的、温馨的心境。这果真就是客体自化自足的奉献吗?我们可以设想几个推论,(1)假如诗人此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处在这些物象之前,他不可能对此产生观注和描写的欲望。(2)就算诗人此时正与所描写的物象之间处于一种“同情”状态,视野中一定还有其他物象(如窗户、桌子等等)被诗人剔除掉了,那么是什么导致诗人“顾此而失彼”呢?(3)可以肯定地说诗人触目所及的色彩中一定还有白色基调之外的色彩,它们都被什么蒸发掉了?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了诗人知觉中的主观内容并非沉睡。它们在暗中积极地进行选择,排列和组合。正如萨特所讲:“在原先没有秩序的地方引进程序,并把精神的统一性强加给于物的多样性,于是我就意识到自己生产了它们”。威廉斯的《Nantucket》只能说是以一种纯客观的形式,表现了作者从大千万象世界中摘取一静谧空间来宣喻主体心境的一首意象诗作。主体内容被较深地埋藏在意象的结构之中。
大千万象世界只有在精神主体性的烛照中,才能从物质性结构向艺术品质转化。没有这种烛照和建构,淡紫的花、白色的帷幕、午后的阳光,都只在自身的物质性结构中具有意义,它们充其量只是好看的物质而已。但在精神主体性的灌注下,它们就不再只是一种物质、或一种物质的运动状态,它们可能就是一种心境、一种情调、一个故事、一种可以不加名义限定的情感、一种可以煽诱起无限想象力的“物”
在艺术的世界里,知觉的霸权主义是艺术思维的本质特征。它以主体的“这一个”的全部精神内容,撞击客观物象的现存结构,使之在知觉这个艺术生成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重新描述、组织和诠释了对象。没有这种描述、组织和诠释,“星星就还是那颗星星”,客观对象就只能在自身的本质规定性上,与艺术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收稿日期]2000-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