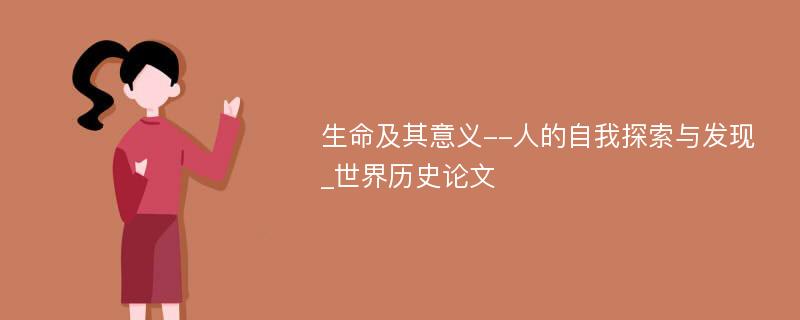
生命及其意义——人的自我寻找与发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自我论文,生命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是人的最高的自我意识,因此,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肯认哲学的人学实质,无疑表明了我国的哲学研究正在走向自觉。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人学研究迄今尚未对人的生命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有意识的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人最可宝贵的东西;并且,为当代人所看重的人生意义就生发于人的生命活动中。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是要靠人自己寻找和发现的;而人寻找和发现自己生命及其意义的过程,也正是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得以生成和觉解的过程。在行将告别充满血与火的20世纪的当今,从人的生命深处生发出来的哲学不应再像黑格尔当年所批评的那样“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理应“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注:黑格尔:《小逻辑》,柏林大学开讲辞31页,商务印书馆,1980。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哲学“原有的家园”就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哲学只有真正地回归到这个家园并倾心地观照她,我们才有可能这样地期待向我们迎面走来的21世纪:人的生命的充盈和意义的澄明。
1
人的历史无疑是人的生命活动史,因而,打开历史我们即可解读人的生命。
古埃及人认为人类历史到他们生活的时期依次经历了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历史哲学的创始人维柯认同古埃及人的这一看法并对这三个时代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注: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通过历史研究,论证了“神”的时代是人类相信“万物有灵”的原始社会早期阶段;“英雄”时代则是各民族为“天神的儿子”——“英雄”(酋长)所统治的时代;“人”的时代则相当于后来摩尔根所说的“文明”时代。)我们借用“三个时代”的说法而扩展其涵义和时限,以“神”的时代指称整个原始社会,以“英雄”时代指称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社会,以“人”的时代指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社会。如所周知,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其原始社会都经历过将某种现象或力量神秘化拟人化并受其控制的阶段,具体表现为各种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的产生;各种神话传说也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至于英雄时代,我们并不陌生,因为那是我们告别不久的时代。那么,在“神”和“英雄”的时代,人对自己的生命有多大的领悟和重视呢?
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神的时代,个人只能匍匐于神灵的脚下,甚至和动物一起被作为祭神的牺牲;而在英雄时代,芸芸众生往往成为英雄豪杰的铺路石和成就其霸业的工具,诸如“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诗句更是形象地道出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大将军们的功名是由无数兵士和民众的生命砌成的。而另一方面,在神的时代,人们崇奉的神灵非但不外在于人的生命,而且就是人的生命的创造者和维系者。无论是宙斯、亚当夏娃,还是中国的盘古、女娲和三皇五帝,这些神话中的人物都曾被认为是某一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生命和生活的源头,作为图腾的自然物同样被先民们奉为自己族群的生命起源和佐护者,其中的生殖崇拜更是直观地表明先民们对人的生命的重视。至于英雄时代的英雄,不仅自己富有生命活力,且是他所在民族的领袖或“救星”,对其民族的生存有着拓荒开道或拯救提升之功。上述这一矛盾的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人最初觉悟和重视的并非个人一己之生命,而是族类生命的存活与延续。个人的生命固然也有其价值,但那价值仅在于对所属族群生存所做的贡献。谁的贡献最大,谁就会被尊为英雄并从而成为该族群的生命象征,当然这里面也不乏凭世袭和强力而执掌权柄、称王称霸的。普通个人的生命意义则仅在于他充当了其血缘群体或民族生命长链上的一个环节,除此之外,他的生命并没有多少特别的价值。这一点,我们从中国众多农民至今仍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且以其家族的生生不息为终极关怀这一事实即可了解。
显然,只是到了每个个人都能以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独立生存、平等交往的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对个人生命及其意义的重视才成为一种被社会认可的普遍的价值取向。我们说市场经济社会当属“人”的时代,不是说人们的能力和作为没有什么差异,而是说每个人的生存都无须仰承于某个特定的群体或个人并受其操控,某些重要的社会角色和职务也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利品;原来“各领风骚五百年”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今也大大改观,变成“各领风骚三五天”了。
哲学的历史同样反映出人类自身的这一变化。就西方哲学而言,尽管苏格拉底早就将古希腊阿波罗神殿上镌刻的神喻“认识你自己”接受为哲学律令,但哲学从正面把握人并取得较系统完整成果则已晚至康德。西方哲学主流所经历的先是自然本体论阶段,次是认识论阶段。本体论阶段的“本体”不外乎水、火、气、土之类的自然物象,似乎与人的生命全不相干,但这些自然物象却是被作为世界和人的生命的“本源”、“始因”乃至基本“元素”看待的。到了认识论阶段,哲学所重视的是人的理性思维和感性经验,虽然还未中生命肯綮,但毕竟已是人的生命自身的机能。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理性和感性已分别被把握为理性之人和感性之人。到了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人的“生命”才从哲学中呼啸而出,使世人为之大大一震。但人的生命既然被归结为“强力”、“意志”,其社会文化意蕴和理性被遗忘或剥除,它就不能不误入非理性主义的歧途。当代西方哲学垂青语言特别是自然语言和诗性语言,视语言为人的存在之家,诚然有其独到之处(试想“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诗言志”等我国箴言),但所见终归只是人的生命自我显现和自我确证的一种形式和这一种形式所能容纳的有限意义。
中国哲学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关于人生的学问甚至是生命哲学,《易经》明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老子看重人的生命本色、长生久视;庄子看重人的精神自由、个性独立;孔孟荀则以仁义道德、内圣外王为圆满的“中庸”人格或人的最高的生命形态;法家和墨家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强调“力”、“利”。应该说,综合先秦思想家们的这些思想,原则上是能够较全面地把握人的生命和人生意义的,这些思想对后世中国人的人生也的确发挥了很大的塑造和范导作用。然而,随着儒家在汉朝被定于一尊,伦理道德逐渐排斥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其他方面并与人的肉体生命相疏离;至宋明,理学家们鼓吹的“存理灭欲”之说成为官方推行的礼教的重要行为规范,人的社会文化生命遂与人的生理肉体生命陷入势不两立之中,形成了类似欧洲中世纪神性贬黜人性的历史境况,维护并强化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华民族生命活力的禁锢和阉割,儒学遂终于在近现代遭到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而来自于西方的申说“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达尔文主义的赫胥黎、斯宾塞学说以及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则一度受到中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
在近现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和学说中,最后惟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借助武器的批判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就马克思哲学本身而言,她无疑是非常重视人的生命活动、重视人的生命异化的克服和生命潜能的发挥的。但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尼采、柏格森一类生命哲学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社会生活过程,而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和牺牲是社会问题,它只能通过社会的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为世界上许多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所服膺的根本原因所在。即使在今天,我们看待和解决人的生死、苦乐问题,也仍然应当有社会的观点。然而,我们也应当意识到,人的生命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个体性,其生命问题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问题,因为这里还有属于每个个人的心理和精神问题。所以对人的生命问题的解决,除了社会的途径和手段之外,还需要用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对于某些人来说还有宗教——等给予观照和化解。并且,即使属于社会方面的问题,它在历史上和在当今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甚至很大的不同,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需要相应变化,如人们对“交往”的重视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如果我们悉心地研究和领悟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那么,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虽然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并把人的问题归结为社会问题,但“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可以无批判地加以肯定的东西,相反,马克思认为“社会”是在人的劳动、实践中变化着的历史概念,即在人的劳动、实践中不断地生成和扬弃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作为主体存在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社会”而是从事着劳动、实践活动的“人”。马克思所期待于人类历史的,不是作为某种社会关系“人格化”的“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57页,人民出版社,1972。),恰恰相反,正是人本身的发展的终极目的性亦即“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人民出版社,1979。)。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如果说社会的本质是人的劳动实践,那么,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则是人的劳动实践的目的和真理。我国哲学研究中的人学转向以及“实践人学”的提出,表明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旨趣有一定的理解,但我们却忽略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观点,未能从这一观点出发彰显出马克思的生命人学的思想底蕴,因而也未能真正地关注和阐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问题。看来,只有在理论上弄清人的生命和人的劳动实践的关系,才能为人对其生命及其意义的寻找与发现扫清道路。
2
生命与非生命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生命进行着合目的的活动。所谓合目的,就是合乎生命在特定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的需要。生命的合目的活动,一方面具有受动性,因为这是生命在环境选择压力下不得不采取特定方式进行的活动;另一方面具有能动性,因为它是体现着生命的内在活力的自为的活动。因而,生命的合目的活动既要指向体外,适应外部环境;又要指向自身,自成目的、自足自适。但是,由于一般生物的合目的活动之“目的”并非自觉目的而属本能范畴,生物与其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并因而与特定的生存环境直接同一,所以生物的生命活动之“他适”与“自适”也是同一的。由此决定了生物的生命及其生存状态的自在性、既定性和平面性,这里没有自我和非我、为我和为他之分,也没有现在和未来、现实与理想之别。生物有生命却没有生命的觉悟和体验,所以也不存在生命意义的问题。
人则不同。一般生物活动的合目的性在人这里发展成为自觉目的,而自觉目的的出现意味着人与他的生命活动不再直接同一,人的生命活动可以成为自己意识和意志的对象;凭借对自己生命活动的自主支配,人不仅使自己的意识和意志获得了主体性和自由,也能够使这一主体性和自由体现于感性的生命活动并进而实现于生命活动的对象之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断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 所以,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0~51页,人民出版社,1979。)人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外部自然界,创造一个对象世界,也就是创造一个贯注和体现着人的生命力量和信念的属人世界。这个属人世界显然就是人的社会和文化世界。在这个社会和文化世界中,人不仅可以直观自身,亦即感觉和欣赏自己的生命机能,而且能够重塑自身,亦即发展和创造自己新的生命。这样,生物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在人这里变成了外部环境对人的适应;生物对特定环境的依赖变成了人对任何环境的超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固定不变的关系变成了人和属人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向着理想状态不断地拓展和生成。于是,人由此而摆脱了生物生存的自在性、既定性和平面性,使自己的生命存在具有了自由性、开放性和立体性。人的这一神奇的生命就是作为肉体和精神、生理和心理高度统一的人的个体生命以及依托于个体生命的人的社会文化生命:政治生命、艺术生命、学术生命等等。可见,人的生命有着动物的生命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不仅有着可以无限伸展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能够达到非凡的张力与和谐,这也就有了人的生命的自我觉解和内在体验,有了生命意义的无穷生发。
何谓生命“意义”?德国历史和文化哲学家同时也是生命哲学奠基人的狄尔泰认为,意义就是生命的体验。其实,意义应当是生命充盈、发挥和表现自身的自足感自由感,是生命向死亡痛苦向一切摧残伤害自己的力量抗争的不屈感悲壮感,总之,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克服一切障碍、创造属人世界中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马克思说得好: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成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包括人的“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和“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在内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的形成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史的产物;而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感觉到的“对象的意义”,归根到底是人所体验到的生命自身的意义;而人所体验到的生命自身的意义又是和生命本质力量的全部丰富性的生成一起生成的。
可见,人的生命及其感觉和体验能力的生成基于人的生命活动永无止境的展开,人对其生命意义的寻找与发现也必定是一个无尽的过程。人的生命是凭借其活动逐步提高其活力、丰富其内涵而由脆弱走向强健、由贫乏走向丰满、由蒙昧走向文明、由自在走向自由的。因而,在人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人所感受、体验到的生命意义必定是很不相同的。在原始时期,个体生命极其弱小贫乏,只有他须臾不可离开的血缘群体仿佛才共有一个强大圆满的生命,因而个体所能体会到的生命意义必定在群体的存活和延续之中(或作为群体生命象征的神灵之中);进入文明时代,个人开始有了人格意识和角色意识,但只要他仍然处在对群体直接的依赖关系中,他的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也就只能生发于对所属群体生命长河的归属感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了一定独立性的个人才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生命意义的体验:个人的成就感自主感以及为市场的自发性所摆布而产生的孤独感和漂泊感。而只有超越了私有制的逻辑,才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种情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5页,人民出版社,1979。)人们才会产生自由而友好地交往的需要并将其视为生活目的。“从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聚会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人们实行结合的手段,也不再是进行联络的手段。交往、聚会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从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粗犷的容貌上向我们放射出人的高贵精神的光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3~94页,人民出版社,1979。)个人生命在与所有其他人生命的共在、共鸣、共舞中获得了无限的惬意与幸福,并使生命自身得到升华。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人的生命的生成、展现和自我理解不仅呈现为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随时随地都有陷入误区乃至走向异化的可能。这是人寻找和发现自己的生命及其意义之所以非常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或症结所在。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人与其生命活动并不直接同一,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识和意志的对象。而这既是人的生命活动走向自觉自由的关键所在,也使人的意识和意志与他的生命活动的疏离具有了可能性。作为肉体和精神、理性和非理性之统一的人的生命,已然先天地置入了肉体和精神、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矛盾,可以使生命走向具有必要张力的和谐,否则,生命本身也会陷入自我分裂自我反对的悲剧之中。
只重视肉体生命或者认为生命的本质就在于肉体感受性,就会只关注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与之适应的实用功利,推崇人的生物本能和利己之心,甚至为此而主张放浪形骸、醉生梦死。这样,人的生命的道德、审美、信仰、思想活动及其意义就会被消解掉,人就会失去精神的丰富性高雅性和超越的自由向度,人的生存就会变得极其庸俗和粗鄙,其生命体验也会变得十分浅薄和狭隘:仿佛人生在世全部的意义就是追逐钱财和满足物欲。以此为人生的价值取向,人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为钱财所拘所役,成为钱财的人格化,甚至走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可悲境地,到头来使生命肉体也遭到否定。那么,只看重人的精神生命或者把人的生命归结为精神又会怎么样呢?我认为,如果说动物的生命就在于它的肉体的话,那么,人的生命则体现于他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而精神更能体现人的生命的本质: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的自由取向。因而精神是人的整个生命机体的主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精神和肉体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意味着人的肉体及其物质需要是低级的动物性的东西。其实,“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只是在将其与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人类生活惟一的终极目的的情况下,它们才“具有动物的性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48页,人民出版社,1979。)。而过去在这方面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认为只有精神才赋有人性乃至神性,肉体则只有物性乃至兽性,从而在推崇精神的同时鄙薄乃至否定人的肉体需要,甚至由此而否定人的经济活动、科学技术活动对于人类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结果,不单束缚弱化了人的正常需要和生命活力,还使精神本身走向空洞虚妄,到头来毁掉了人的精神生命的健康充实和对人的生命活动合理的引导作用。
与此相关,人的生命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导致生命的自相分裂、自相反对。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是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共识,这一共识表明了人把自己提升于动物之上的自我觉醒,意义十分重大,笔者在此无须赘言。然而,理性在人的生活中一旦发展到理性主义并主宰一切,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等等遭到蔑视和封杀,人的生命的活生生的感性特征就将不复存在,人就会异化为干瘪的木乃伊。这无疑是对人的生命的极大戕害。在欧洲中世纪和以“存理灭欲”为天经地义的戒律的中国宋明时期,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各种非理性思潮和观念的崛起也就势在必然并具有很大的正当性了。当然,如果非彼即此,以非理性为人的生命本质,一味地鼓吹生命本能的“冲力”而拒斥理性贯注和范导的必要,人的生命活动就会失之盲目。总之,如果不能全面地把握和妥善地处理人的生命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人的生命及其现实生活就将成为悲剧。这样,人寻找和发现自己生命意义的努力,自然就会变得极其曲折和艰难。
事实上,人对自己生命要素和机能的全面把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又只能是人类生命自身的发展和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对人的“异化劳动”的分析对我们颇有启迪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真正的“生命活动”,因而也是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却变成了“外在的东西”,变成了“异化劳动”,亦即“自我活动表现为为别人的活动,并且似乎就是别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6页,人民出版社,1979。);“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贯注到对象里去,但因此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对象了。”(注: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45页,人民出版社,1979。)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劳动何以走向“异化”并使人的生命也成为“异化的生命”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先后给予深入探讨并指出:一方面,人的劳动作为人的谋生手段本身就具有“受动性”和“消极方面”,另外,“自然形成”而非出于人的自愿的劳动和社会分工则使劳动由异化的可能变成了现实。因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9页,人民出版社,1988。)人凭借劳动超出了动物所不可逾越的特定的自然范围,却又因为分工而被囿于特定的社会范围。但是如果进一步问,这种导致了劳动异化的“分工”难道是在人的生命活动之外偶然地产生出来并外在地施加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上的吗?其实非但不是如此,倒恰恰是从人的生命活动自身的性质和要求中生发出来的。劳动分工从根本上说源于人的生命对自己活动的“效率”、“效益”的追求。只有不断地提高活动的效率效益,亦即不断地提高生命活动的能力特别是体力和智力,人的生命以及生命联合体才能变得足够强大、优越,才能卓有成效地对付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和人类内部的“生存斗争”,人才能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并余出更多的“自由时间”来显示和发展自己的“天性”。“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15页,人民出版社,1979。)。可见, 人的生命自身在其发展过程中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全面的发展则必然以片面的发展为前提。所以,当人的生命的某一方面的机能突出地得到发挥和强化时,往往会遮蔽乃至妨害生命其他机能的发育和进化。例如,对生命活动效率的一味追求,就会遮蔽和妨害生命个体相互之间的怜悯心、同情心亦即道德情感的生发和以人性为内核的人文精神的树立。同样,人的生命的社会文化表现及其形式在培育和提升人的生命力量和意蕴的同时,也往往会使人的生命的某些方面受到某种程度的遮蔽或局限,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成为人的生命发展的障碍或桎梏。包括经济、法律、政治在内的社会制度和包括语言、人文、科学在内的文化形式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看,人类只有通过生产和交往活动的充分展开,成为休戚相关祸福与共的高度一体化的类存在,人类内部的生存斗争和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才能由恶性转变为良性,人的生命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成为展示“自由自觉”的类特性的美的创作和鉴赏活动。从哲学维度说,人们只有本着“回到事物本身”的精神回到自己生命深处达到对生命的觉解,人才不致于在包括社会文化活动在内的自己的一切生命活动中迷失“自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生命的价值、体验生命的意义。
3
每个人生来就有一条命,就像动物生来就有生命一样自然,这反而不为人所特别看重了。生命似乎只是人生的一个自然前提,它被归结为身体,身体则被视为做一切事的“本钱”。本钱固然重要,但它却不是目的,而只是赚取“红利”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红利”即各种事功(功名利禄)的“价值”。事功的价值具有了目的性,它反转来成为衡量人的尺度,所以人也有了“价值”。谁创造的事功的价值大,谁的价值就大;反之,价值则小。在发生天灾人祸的年代,人的生命甚至成为最“不值钱”的“废物”。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现代商品社会,人似乎“值钱”得多了,但“人的世界”远远比不上“物的世界”升值升得那么快。而当人们外骛于物的世界并竭力享有它时,又难免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注:《老子·十二章》。)人在生命能量得到释放的同时也会感到心灵放逐自我丢失,及至败北失意或身心交瘁时,则又会不无矫情地把一切事功视为“身外之物”,生命及其意义被重新归结为身体的存活或身心的闲适。原来认为“轰轰烈烈才是真”,现在又说“平平淡淡才是真”了。如此的颠来倒去,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人们是否已经有了生命的充分觉悟?但是,既然我们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那么,我们就到了充分地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开发人的生命潜能、增强人的生命活力、提升人的生命境界,让生命之光把世界和人自身照得更亮的时候了。作为人的最高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既然已被我们肯认为人学,那就意味着人的自我寻找与发现业已逼近自己的“生命及其意义”这个根本所在了。在今天关注和研究生命及其意义这个主题,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并从而具有三重意义。
首先,只有以人的生命及其意义为研究对象,才能真正重视并深入把握人类个体,在个体、群体、族类三者之间建立合乎时代要求的关系;突破哲学人学研究的传统思路和框架,为哲学人学研究开辟出一个新天地。“人”在我们过去的哲学中其实仅仅作为“类”存在。类是无数生命个体在无限时空上的集合,因而几近于超生死、一天地、齐是非的“神”,所以过去的哲学对人的生死苦乐总是漠然置之,一任历史去解决。要真正关注个人,就必须关注生命,因为生命不仅是个体性的,而且是个人最可宝贵的。源远流长、久兴不衰的宗教正是生发、维系于个人生死苦乐一类问题的。个体生命既是两性结合即人的类活动的产物,又是其必备条件;个体生命的精神、心理要素或机能是人的社会文化活动的内化,而社会文化则是人的生命的共在形式和非人格表现。个体生命在其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展开和延伸便形成了人的社会文化生命。对人的生命的研究单凭外在实证显然是不行的,它同时还要靠个人的内在体验和直觉,只有方法论上的内外结合,哲学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人生的普遍性与深刻性、现实性与可能性,成为真正属于每个特殊个人的哲学。
其次,只有重视对人的生命及其意义的研究,才能跟上人类自身发展的步伐并满足人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需要,也才能为解决当代人的“意义危机”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思路。在现有的哲学论著中,人生意义问题被归结为人生价值问题,讲的是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他人与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与尊重。但是,严格讲来,人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是等同的。价值固然是属人的,而以价值为人的尺度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人的生命及其人格毕竟是无价的。且人生意义虽然生发于人对其价值创造活动的体验,却并不等于价值本身。价值总是为他的社会客观概念,意义则是自为的社会主观概念,它更属于社会的个人,因为归根到底意义是人的生命在其活动中的自我确证感和自我实现感。人在生活中从追求价值到寻找意义的变化,正反映了人在更高程度上的自我生成和自我觉解。但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又是在二律背反中实现的,由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学和工业的“祛魅”作用,由于市场经济日益强化了人的个体性和人的感官化(把人生归结为感官刺激),而激烈的竞争和难料的前途更加重了人的孤独感、漂泊感和宿命感,人生意义问题遂出现了危机,人在神经和精神方面的病症愈来愈多。而器官移植、安乐死、克隆人(虽然还只是可能)等问题更涉及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伦理关系。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单靠哲学固然不行,但哲学若从人的有意识的生命这个根本入手,深入地探究和阐发生死、灵肉、理欲、苦乐、得失、人己等关系及生命意义,对于帮助人们启蒙解蔽、自我超脱和自我把握,是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
最后,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入手进行哲学人学研究,还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内部和人类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树立现代的生命观和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根本上确立敬重天地万物、守护人类家园的意识。生命是自生自长、自为因果的宇宙的菁华,而人的自觉自为的生命又是其最高发展和自觉体现,对此,我们毋庸置疑。但惟其是最高发展和自觉体现,所以人也就负有关怀、保护整个大自然的责任,而决不意味着人被给予了随意地处置和破坏自然万物的特权。诚然,人与外部自然始终有着矛盾的一面,人是在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并在改造外部自然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不能不以包括某些生物在内的自然资源为生;甚至人类内部也长期存在今天也依然存在着相当严峻的“生存斗争”。这表明人的生命个体之间和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确有相克相生乃至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关系。然而,所有的生命又构成一个互依互补的生态系统,从根本和长远上说,它们是共损共荣的。而人既然是有自觉意识、有理想追求的生命,她就应当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肯认并体现出宇宙的生生不息之道和生命的进化之道,厚德载物、民胞物与,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潜能、显示生命的真谛并澄明生命的意义。
除以上三点之外,关于生命、肉体和精神(心灵)的关系,关于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关系,关于生命、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也都需要我们做出深入的研究。在哲学上研究人的生命及其意义,也正是人的自我寻找与发现的最自觉努力。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当今研究生命哲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思想性和时代性上是一定能够超越本世纪初兴起的西方生命哲学的,也完全可以与当代西方哲学进行平等对话。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