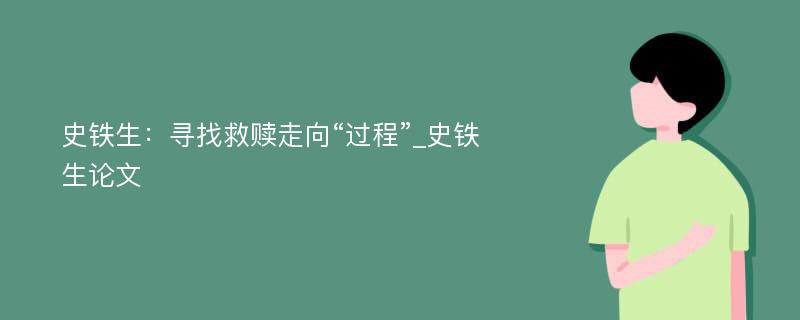
史铁生:寻找救赎与走向“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过程论文,史铁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4-0047-07
一 沉重的肉身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潜心于宗教,从宗教的角度进入宇宙世界,勘悟人生真相,追问生命终极意义,寻找灵魂救赎之路,史铁生的意义显然是别的作家担当不了的。这当然与史铁生自身躯体的残疾有关。不过史铁生其人其文的意义,已远远地超出了身体残疾的本身,也已远远地超出了“史铁生”具体的“这一个”。刘小枫曾把看似不相干的《圣灵降临的叙事》① 一文作为一份“精神礼物”献给史铁生五十岁的生日,人们对此难免有些困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为思想家的刘小枫是在把作为作家的史铁生视为精神信仰上的知己。刘小枫是在把史铁生定位为“思想型的作家”。把史铁生与当年俄罗斯的梅烈日柯夫斯基(Dimitrij Sergeevic Mereskovskij,1866-1941)相提并论不一定合适,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在前后相关联的两个世纪末,在两个民族精神思想的转型时期,在“民族的和西方的思想基础上深入到现代性问题引致的人类精神困境深处”,[1] 116史铁生之于汉语民族的意义,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不应该忽视的。这样说,并非要把史铁生神化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救世主”;在这样一个精神无所皈依,灵魂无处安置的世纪转型时期,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救世主”,现在谁也担当不了。但史铁生对人生真相与生命终极意义的悟证,能让我们远离日益放纵的肉身与不断下滑的精神,却是无疑的。在遭遇价值颠覆的个体精神“无家可归”的当下,不应排除作为“思想型作家”的史铁生给我们带来启示的可能性。
在关于1990年代“散文革命”检讨的对话中,笔者与贾平凹曾有过如下问答:
曾令存:在今年(2002年——笔者)5月份于北京大学“中国散文论坛”的讲演中,您讲到散文内容表现中的现代意识问题,强调散文对生命深度的表现。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作品境界的高下却从此分流。我想您的强调应是有所指的,它并不针对某一个作家,甚至不仅是对九十年代的散文而言。由此而论,您认为包括史铁生等在内的一些作家的散文在九十年代有代表性吗?
贾平凹:史铁生的散文是好的,他的散文没有旧的框式。在突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后,个人的力量就突出了,史铁生是这样,余秋雨是这样。给我的印象里,史铁生是竖着写的,余秋雨是横着写的,都写得极致,应该是大家了。②
——这“横”“竖”的概括很见筋骨。“横”是“面”,追求的是一种历史感与文化意识,而“竖”该是“线”,追求的是一种关于人生与生命极致的拷诘。贾平凹认为史铁生“作品中的宗教感很强,这其中有他灵魂中的东西,也有身体方面的事情,他的宁静和沉思是一般人难得的”。
残疾(残缺)——圆满,苦难——赎罪,宗教——神性,在虚无中寻找意义,等等,是人们在谈论史铁生作品时说得最多的话题。这也是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平素思想得最多并导引他走向生命更深处的问题。在史铁生构筑的纷纭的文学意象世界中,裹挟的几乎都是以上这些脱离俗身的超验问题。上帝在给予史铁生残疾(残缺)躯体的同时,顺便保证着其精神灵魂的健康健全。
如果说刘小枫基督神学的认信与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论的论证与思辨,为我们精神救赎之路的建筑提供了一种智性的思想维度的话,那么作为“思想型作家”的史铁生,他在创作中对苦难的直逼,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对精神救赎之路的寻找,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残疾(残缺)的生命,一个苦难苦弱的灵魂是如何在绝望中寻找救赎,最后走向精神坦途,走向圆满的(不过这“圆满”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富于意义的“过程”。所以与其说是“走向圆满”,或许还不如说是“走向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进一步展开)。前者从理性的思想出发,后者从沉重的肉身开始,最后在神性光芒的照耀下,汇合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怀问题上。
二 人的根本处境
《宿命的写作》中史铁生谈到自己在读了刘小枫的《一片秋天枯叶的湿润经脉》③ 之后,又一次明白了“写作永远可以生存的根据”。
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早年让我感到荒唐透顶,后来慢慢明白,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这处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学以及任何办法可以改变的,而是必然逼迫着你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回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关心社会正义,而是说,人的处境远远大于社会,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2]
不再呼天抢地地诉求,也不再自怜自艾地抱怨。“接受苦难。接受残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关注人的处境。这是一个对苦难人生破执、了解生命真相之后的史铁生。
明白这一切之时,是在双腿残废的三十年之后,在灵魂走出沉重的肉体之后。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介绍波兰著名电影艺术家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的电影作品《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时曾经这么说过:
个体出世后,身体与自己的影子——身体之灵或灵的身体——通常是一体的。身体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就像眼睛看不到眼睛。除非在一种特别的光亮照射下,影子才会与自己的身体分开,我才可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还得看我站在什么位置,与光处于什么关系。一个人要站到可以让自己身体的影子显露出来的有光的地方,不是因为身不由己,就是由于忘乎其形(身体)。[3] 114
有意思的是,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也有类似这样的神来之笔:
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影子。[4] 8
后来在《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想念地坛》等作品中,我们几乎可以似曾相识地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和游离于轮椅上的史铁生,看到史铁生(作为物质和肉身的史铁生)和史铁生的影子(作为精神和灵魂的史铁生)在对话的情形。④
很显然,史铁生所说的“影子”在本质上与刘小枫所谓的“影子”并没有什么差别,都可以指是一种寄托于肉身的“精神”或者“灵魂”。
《宿命的写作》的那段话,恰是史铁生身体与自己的影子分离的结果。影子与身体之所以分离,在史铁生,无疑的是由于“身不由己”而终于“忘乎其形(身体)”,因为身体的残疾而最终“忘乎”残疾,“在一种特别的光亮照射下”。——“特别的光亮”,在这具体语境中,依我的理解,应该是一种宗教神性的光芒。
但即便如此,人们仍难免要问:这其中究竟经历了多少曲折与艰难?心灵之路是如何从苦难与绝望的荆棘丛中踩出来的?
谁能想象?用尺度量?以时计算?
其实,这种“分离”,这其中的曲折与艰难,人间俗世众生的任何尺度都是无法权衡的。只有走进宗教神性的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比较满意的答复。
在两条腿残疾后的最初几年里,在那座荒芜的废园里,史铁生说“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5] 8“要不要去死”?“为什么要活”?“怎么活”?——这些问题是问题吗?对一些人来说,这些问题根本不足以成为“问题”。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却是回旋不去,“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的问题,比如“史铁生们”。《墙下短记》曾写到自己在“失魂落魄的那些岁月里”,摇着轮椅来到那座荒芜的古园:
四处无人,寂静悠久,寂静的我和寂静的墙之间,膨胀和盛开着冤屈。我用拳头打墙,用石头砍它,对着它落泪、喃喃咒骂,但是它轻轻掉落一点儿灰尘再无所动。[5] 148
这文字读来几乎让人哀怜、无奈、绝望。引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起史铁生在其他文章中(比如《病隙碎笔1·十二》,又比如《想念地坛》)反复讲述的恺撒大帝涕泪横流仰面苍天哀求上帝为他治好他唯一心爱的女人,但上帝还是一无所动没有答应任他心爱的女人死去的情形。这个富于悲剧而不失悲壮的故事被史铁生讲述得很震撼,也很深刻,这显然与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有关。叙述主体的经验直接参与着叙述过程。当史铁生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恺撒大帝就是史铁生,史铁生就是恺撒大帝。在巨大的苦难面前,恺撒大帝和史铁生一样,都是区区一个苦弱无助的孤独者。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对史铁生(或者恺撒大帝)而言,作为一个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一种隐喻,疾病这苦难,包括最大的“苦难”——死亡,正如他在前面所说,并“没有现实的敌人”,“甚至无冤可鸣”,“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在这里,史铁生其实是想借自己或者恺撒大帝的遭遇来阐释一个问题:人的根本处境是什么?有一天,当他在荒芜残败的废园里终于悟通到这一点,悟通到“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悟通到“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为什么要出生——笔者)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之时,[5] 8便仿佛觉得“在精神苍穹之上有一颗‘光明的晨星’正在升起,在远方,从那‘不灭之光’的殿堂中心传来祈祷的钟声”,[6] 6终于豁然开朗,认识到包括残疾、苦难、死亡等在内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广大同类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健全的还是残疾的,尊贵的还是卑贱的同类。比如自己曾经在荒芜的古园里遇到的那个漂亮而弱智的小女孩(《我与地坛》),在莽莽苍苍的群山中走着的两个相依为命的瞎子(《命若琴弦》),还有那个对未来充满梦想却遭遇车祸的青年(《原罪·宿命》),一出生便发现患有先天性软骨组织发育不健全的小女孩(《来到人间》),终生坐在轮椅上的C,那个当年在升学考试中“以大大高出录取线的分数”最终却被流放到西北边陲的WR(《务虚笔记》),又比如荒芜废园中戏耍弱智小女孩的那几个躯体健全的人(《我与地坛》),《务虚笔记》中女教师O,医生F,诗人L,女导演N,画家Z,还有约翰逊,那个因为服用兴奋剂而跑出了九秒七九的短跑飞人(《我的梦想》)……
人的本性倾向福音。但人的根本处境是苦难,或者是残疾。[7] 290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碍。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碍,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8] 72
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9]
残疾一般是指身体器官上的,残缺,那是指人,按着基督的说法人有罪行,罪行,其实我觉得就是残缺。不光是那个不满意的残缺,不单是这种残缺。[2]
这就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处境:残疾,残缺,苦难,以及包括这些在内而又远远大于这些的“罪行”(这“罪行”并不简单或者说根本不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主要或者从根本上说还是指宗教意义上的。关于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还会作进一层的阐释)。这一切,即便是躯体健康健全的人也难以逃脱。躯体健康健全的人虽然没有躯体残疾者面临的不幸与苦难,但“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他们精神心魂上的残疾与残缺所带来的痛苦常常并不轻于后者。而凡人皆有与人同在的所谓的“罪行”,它给人类所带来的苦痛,更是难以言说。“按着基督的说法人有罪行,罪行,其实我觉得就是残缺。不光是那个不满意的残缺”,比如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形象的隐喻便是人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对智慧禁果的摘吃。生为人类,残疾、残缺、苦难,乃至罪行,无处不在。这才是生命的真相,才是上帝给人类在悟证人生与思考生命终极意义时候设下的一个“槛”。只有跨过了这个“槛”,认知与接受了人类这“存在的根本处境”与“生命的真相”,所谓的悟证与思考才可能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对于世界与人的由来与存在意义的认识才是完整和现实的。只有如此,你才能体悟到这追问的深刻:
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崇高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是否是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5] 24
你能想像有一种没有疾病的现在吗?你想像过那样的存在吗,没有疾病,没有困苦、丑陋、怯懦、卑贱、抛弃和蔑视、屈辱和仇恨、孤单和孤独……总之没有差别,那会是什么你想过吗?[7] 383
谁能想象这假设的一切若都成为现实,“思想”与“精神”于“肉身”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人们还会去追问所谓“意义”与“价值”为何物?又有谁能想象关注与思考这“意义”与“价值”哲学神学因此还有存在的必要?
残疾(残缺),苦难,以及包括这些在内而又远远大于这些的“罪行”,是人的根本处境,世界与人类的真实存在,同时也是维系世界与人类平衡的必要。史铁生从自身个体的遭遇与经验念想到广大的同类,并由此对生命的本相发出更深入的追问,这一切之所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追问”本身,而展露出一种“舍我”的宗教情怀。
三 走向“过程”
既然如此,既然“人的本性倾向福音。但人的根本处境是苦难,或者是残疾”,既然这假设的一切都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拯救苦难与残疾的出路在哪里?——用《我与地坛》中的话说就是:“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福音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呢?人生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圆满?这圆满是指什么?如何走向圆满?这样的疑问,从二十一岁那年开始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史铁生的思想现场。但最终答案——让自己满意、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的找到,却是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阅历了无数的生死劫难,生命渐入晚境之后。——这里有形象的描述:“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母亲早已弃“我”而去(“她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那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我”亦从一个货真价实的青年进入了中年(《我与地坛》)。有一天(谁能说出这“有一天”的到来经历了怎样的漫长?),“我记得突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想念地坛》)。——那是“破执”之后的“放弃”,用苦难的生命孕育出来的智慧与悟性在引领着“我”走出自己的沉重肉身之后对广大同类心怀慈悲的“轻魂”。
但,“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想念地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又怎能显示出这智慧和悟性的珍贵呢?
由此引出的一个致命的质疑是,“圆满是一种结果”吗?
既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轻易获得这智慧和悟性,找到救赎之路,抵达“圆满”,那么,就不能肯定“圆满是一种结果”。既然不能肯定,那么,“回头是岸”,直面现实,正视“过程”,也许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其实正是“智慧和悟性”的另一种显现形式,一种“过程”的“智慧和悟性”。因此,与其说圆满是一种结果,还不如说是一种希望(或者说是“用过程来实现”的“理想”,是“爱”,一种期愿),一个过程,一个寻找救赎苦难之路的过程——救赎苦难之路其实也在此“过程”之中。对“圆满”的省思与重新定位是对人生态度的重新调较,对命运与生命意义的重新解读。这些消息,散布在觉悟之后的史铁生文字之中:“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病隙碎笔1·三十八》);“仰望”,不光意味心魂凝望,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告诉我们这其中所包含的距离,那无法逾越的心路历程,那从人世出发“到”天堂,其中不可能有终结的过程。“理想,没法在一个具体的时空中去实现。它不是能这样实现的,它是靠一条路去实现的,它是靠一个没有终结的一个过程来实现的”(《“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理想”在“过程”中,一旦成为现实,即已不再是“理想”。在好几篇文章中他都不掩饰自己对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生命的意义》中一句话的欣赏:“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如《病隙碎笔2·四十》,《宿命的写作》等)。“提出”本身不是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思想与体验的过程。
“过程”,这才是上帝最初对众生的许诺,只不过由于“人的本性倾向福音”,看重“目的”和“结果”,而常常忽视“过程”,省略“过程”,不愿意面对充满苦难的“过程”,更不愿意接受苦难的“过程”,因而能够领悟到上帝这一意图的人寥若辰星,能够获得“过程”的智慧与悟性的永远都总是那么几个。便是虔诚的约伯对上帝这一许诺最后的醒悟,也是在接连不断的苦难(撒旦的控告、神的惩罚,……)甚至在一度动摇的信心恢复之后。更何况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史铁生。而恰恰如此,史铁生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的地位方才显得更加无法替代,其思想的深刻性方才显得更加凸出。“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好运设计》)“过程”的认定引领着史铁生健康健全的思想竭力冲出残疾残缺的躯体,浇灌着其轻灵美丽的精神之花盛开在沉重的肉身之上:
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找,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之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10] 96
神之在,源于人的不足和迷惑,是人之残缺的完美比照。[11] 148
精神,当其仅限于个体生命之时,便更像是生理的一种机能,肉身的附属,甚至累赘(……)。但当他联通了那无限之在(比如无限的人群和困苦,无限的可能和希望),追随了那绝对价值(比如对终极意义的寻找与建立),他就会因自身的局限而谦逊,因人性的丑陋而忏悔,视固有的困苦为锤炼,看琳琅的美物为道具,既知不断地超越自身才是目的,又知这样的超越乃是永远的过程。[12] 157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痛苦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却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到处在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巧妙的设计。[4] 48
圆满,是在对生命终极意义不断的追问过程之中,在对救赎苦难之路的寻找过程之中。而救赎的希望,也在“过程”中。
其实,人在世所有“罪行”的救赎希望,均在此“过程”中。当然,史铁生这里所谓的“罪行”,如前所言,并不简单是(或者说根本不是)指法律意义上触犯的“罪行”,也不简单是指我们日常意义上所谓的“坏事”;它主要还是指在思想精神与灵魂方面那些难于为理想的人性或者说是圣洁神性所接受与认可的不健康或者是不应该有的东西,躯体的残疾,疾病在这里并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还是指那种精神的苦难,心魂的恶劣和卑下,抛弃和蔑视,屈辱和仇恨,还有那“不光是那个不满意的残缺”,以及所谓的“贪、嗔、痴”,无穷尽的欲望,等等。“罪行”在这里是宗教神学意义上的。这些“罪行”的救赎,法律是无能为力的,而只能靠信仰,靠那“永远的过程”。
一切都在于“过程”。上帝的本意如此。不过在这里我们更感兴趣的,或许还是史铁生对上帝的本意何以作如此个性化的解读与阐述,何以如此强调这“过程”。这其中当然不能排除他自身的遭遇与经验,——比如残疾,而且可以说这可能是最主要的。但仅仅如此吗?在那篇“对话”中,对王尧所说“一个人在今天所能达到的境界或者高度,有种种的原因。譬如您的状态与残疾的关系”的情形,史铁生以为,其实“同样的原因,并不注定会有同样的效果。同样的残疾,在人生的路上并不一定起同样的作用”,“残疾,一般来说肯定会改变你的生活,但终于改变到哪里去,却不一定”。从其构筑的整体的文学意象世界看,史铁生从自身的遭遇与经验出发对苦难与人生等终极问题所作的思考,其实早已经超出了自身而含藏着一种广大的宗教精神,“因明了物之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过程”。“宗教精神的根本,正是爱的理想。”[2] 宗教精神,或者说是宗教情怀,并非为健全人所有,但也并不等于说残疾人就都会有这种精神或者情怀。人有没有荒谬感?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病”意味着什么?“死”呢?诸如这些超越个体、普遍存在于广大同类中,带有终极性质的问题,不仅是残疾人,即便是一般健康的人,重病临死的时候,都难免为其纠缠。“我呢”,史铁生说,“这个提问开始得比较早,一般二十岁的人还没有涉及到,这是秋天的事。”(《“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这就是史铁生的独特之处。
四 “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
从沉重的肉身出发,探诘人的根本处境,从寻找救赎苦难的人生之路,终于走向永远的“过程”,作为“影子的史铁生”,已不仅仅为“肉身的史铁生”所拥有。有限的躯体已无法再容纳下从中升腾起来的思想与精神。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常常看着自己的影子带着自己沉重的肉身不能解答的疑难,渐行渐远,飞越人间,叩问天国,拷诘地狱,“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回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寻找让自己能够接受,同时尽可能适合人世众生的答案。
比如欲望。欲望是什么?那是人对差别的一种不满,对平等的一种寻求。人该不该有欲望?人是否能够消灭欲望?在史铁生看来,提出这问题是多余的。因为,“也许,人就是歧途”(《随笔十三》),生而为人,本身便是欲望的化身。没有欲望也就没有人,“消灭欲望绝不是普度众生,而只是消灭众生”(《一封家书》);消灭欲望同时也就是消灭人性。但是,“如果欲望纷纭为真,又为什么要控制,为什么不允许纷纭的幻想变为纷纭的现实?”(《务虚笔记》)其实这很简单,如果“纷纭的幻想变为纷纭的现实”,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那将如前所言,“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人有欲望,人不能够消灭欲望。剩下的问题是:人应该如何面对欲望?对此,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提出两点:一,是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我听见园神告诉我: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坐得离舞台太近了。[5] 29
既不能靠得太近,纵身其中,为欲望所奴役,否则人将成为欲望无畏的祭品,成为“欲望”的人质;又不能离得太远,逍遥其外,以为与自己无关,否则人会觉得很“乏味”,无意义于人世。这是个二难选择,但恰恰是这一二难选择反映出一个人的智慧。二,——对欲望的另一种态度,史铁生认为,归根结底,是要把它转化成为“过程”。
只是应该把欲望引向过程,永远对过程(努力的过程、创造的过程、总之生命的一切过程)感兴趣,而看轻对目的的占有,……[5] 126
过程。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过程”。“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我与地坛》),“永恒(的过程)”方才是本质。“只是为了引导出一个美丽的过程,人才设置一个美丽的目的,或理想。理想原就不是为了实现,而只是为了引出过程罢了。”(《一封家书》)从“过程”这种意义上说,“理想”既可从“圆满”角度看,也可从“欲望”角度看。欲望包含着理想的成分,但它远远大于理想。理想,作为欲望的一种替代,其引导出来的“过程”,便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欲望的最好注释。
又比如忏悔。忏悔是什么?它仅仅是指人对自我过失的一种否定或者谴责吗?当然不仅仅是。“忏悔,有它的确定的定义,我说的意思是比忏悔还要大,就是说,它要往里头深思,向内心、向根本追问。”[13] 这“深思”和“追问”,当然指向外在具体的言行,但这还不够。直逼看不见的内在的精神和心魂,才是最重要的。人为什么要忏悔?“人之初,性本善”在这一问题的追问之下很可能成为一种善意的假设。“按着基督的说法人有罪行”;“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而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病隙碎笔1·十六》);“罪,既然普遍存在于人的心中,那么,忏悔对于每一个人就都是必要。”(《病隙碎笔3·二十八》)“事实上我们都需要忏悔,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不怀有歧视的人并不多。”(《给李健鸣的三封信》)在与王尧的对话中,史铁生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法制与信仰两者均不可或缺。这是两种管制人干坏事的办法,“一个是外在的——法律,这事你干了就要处罚你;一种是内在的——要求,因为外在的你不可能管全,剩下的事情要归信仰”(《“有了一种精神对应苦难时,你就复活了”》),要通过忏悔,通过内在的自律、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办法来加以管制。看来,于社会于个体,忏悔都是必要的。不过归根结底还是于个体更为必要,因为没有个体的社会终究是空虚的社会。
与欲望一样,忏悔同样追求“过程”,注重“过程”,而看轻直接的结果。
在对人性恶的觉察中,在人的意识忏悔里,神显现。在人性去接近完美却发现永无终途的路上,才有神圣的朝拜。[14] 29
人间总是喧嚣,因而佛陀领导清静。人间总有污浊,所以上帝主张清洁。那是一条路呵!皈依无处。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在路上。[15] 49-50
人们就像在呆板的实际生活中渴望虚构的艺术那样,在这无奈的现实中梦想一片净土、一种完美的时间。这就是宗教精神把。在这样的境界中,在沉思默坐向着神圣皈依的时间里,尘世的一切标准才被扫荡,于是看见一切众生都是苦弱,歧视与隔离惟使这苦弱深重。那一刻,人摆脱了尘世附加的一切高低贵贱,重新成为赤裸的亚当、夏娃。[16] 114
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关怀可以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5] 201
忏悔的意义便在“永远的过程”中。这是一个灵魂的历程。这个“往里头深思,向内心、向根本追问”的“过程”最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改变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所谓精神品格的提升,主要的还是在这忏悔的过程中。刘小枫有一本书叫《这一代人的爱和怕》,⑤ 史铁生对这书名颇为欣赏:“我们现在糟糕的就是,那种既无怕也无爱,既无对神的畏惧也无对人的怜爱”。[13] 无所畏惧自然无所不为。没有了“约束”,没有了“管制”,没有了“内在的要求”,人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这里,人作为“人”的品格将要因此大大降低。
在那篇对话中,当王尧谈到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国人若接受史铁生的方式(当然不仅仅指对“欲望”的态度,“忏悔”,还包括那种更广大的“宗教精神”),它会“威胁”(另一种说法叫“改变”)中国人面对世界的生存方式的时候,史铁生回答极为深刻:
信仰,对神的看法,在这个民族的上空飘摇,在地上的这些政治是要受到影响的。我不是说要用所有的宽容去对待政治,这点该枪毙的还是枪毙,但是该枪毙的还要枪毙的时候,它的上空要是飘缭着的慈悲、爱愿,和仅仅是仇恨,这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当枪毙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的仅仅仇恨,和你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慈悲和爱愿在向你发出更深的质问,那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就有未来的新路。那么这个东西,这个飘缭的慈悲和爱愿,虽然是虚的,底下该枪毙的还枪毙了,可上面飘缭的东西不一样,决定了底下这还是不一样,虽然同样还是枪毙。[13]
在世纪的转型时期,在整个汉语民族精神的转型时期,史铁生的这一番辨析太具有“挑战”性了——也很能启人深思。“政治”(包括“科技”,确切些,这应该是一种比拟)能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枪毙一个人,但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根本的人性的问题,触及灵魂深处的问题。比如你在枪毙一个人的时候不仅仅看到仇恨,“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慈悲和爱愿在向你发出更深的质问”,看到被枪毙的那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人”(所谓的“坏人”),同时也是一个“苦弱的生命”。这对“政治”来说是根本不允许的,但恰恰在这不被允许的“看到”里我们看到了脱离“政治”的另一面的人性。“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而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这是一种心魂的内在要求。这样的问题政治不能解决,而只能通过信仰,通过忏悔。精神新生的希望,或许就在这里。精神“未来的新路”,不在于向外寻找,而是向内建筑。“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不仅仅是“苦难”,其实还应包括所谓的“罪行”。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与民族也是如此。“慈悲和爱愿”在这里其实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比拟罢了,它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远远大于此的一种精神品格,一种远离仇恨、歧视等心魂“罪行”,富于宗教神性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的获得,不靠给予,而只能通过“往里头深思,向内心、向根本追问”的忏悔去取得。这“取得”是一个“过程”,一个赎罪的过程,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
由此看来,中国人若因为接受了史铁生的这种方式而改变了面对世界的生存方式,未必是件坏事,未必不是一条精神“未来的新路”。我们当下的精神状况究竟怎样?我们缺少什么?“政治”吗?政治能解决这些很深的精神困境吗?还是在那篇对话中,在谈到现今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表达自己“良知”的时候,史铁生对此作过精辟深入的论说,认为只有具有“关怀这个东西的人才算是知识分子,他与多高的文凭无关”;史铁生认为,在高等学府,“人文精神可能是最重要的”;但现在的大学生,“知识越来越多”“思想却越来越少”,“人文关怀甚至就很淡薄”。高等学府思想工作的加强与大学生人文关怀意识“很淡薄”之间这种悖论性的存在,证明“很深的精神困境”的解决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甚至连“政治”(“思想工作”)也可能鞭长莫及。
1999年底,《跨文化对话》编委就“世纪之交谈精神信仰”在香港城市大学马会楼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在“关注未来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提升问题”的背景下,汉语思想界、汉语民族21世纪的精神走向问题,再次成为“圆桌会议”的关注焦点。⑥
《中国新闻周刊》200期纪念特刊曾以“重构中国精神”为题,对中国人的精神下滑进行反思,认为“中国人的精神陷入虚无”,一方面是因为贯穿于20世纪的“反传统掏空了中国人的心灵”,另一方面,文章认为,则是“全能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侵蚀了人们的精神空间,妨碍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自发性发育”;文章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具体体现者”的知识分子,信仰、道德、伦理在他们那里“崩溃”“最为彻底”,“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观念陷入混乱,他们集体率先堕落,并为社会普遍的神崩溃提供理论支持”。⑦“政治”不仅不能解决“精神”的问题,反而妨碍着它的“自发性发育”,更遑论对它进行“提升”。
如果把考察的视野再拓宽些,我们还可看到王岳川的《肉体沉重而灵魂轻飘》。面对“肉体成为了最流通的话语”的新世纪,面对由此反映出来的世界人类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状况,文章作了一番深刻的透析:
如今打着精神解放的旗帜解放了身体,更解放了肉体中火山喷发般的欲望,身体不再是承载精神的地基,而是否定精神的平台;凝视身体使得内在欲望徜徉于世,并获得世俗化的阵阵喝彩;力比多终于成功地冲破社会规范,而活跃在无思想或反思想的文化前沿。⑧
王岳川指出,“人的本体论”“从最早的自然本体论(金、木、水、土、火构成宇宙的元素),到中世纪神性本体论(上帝、神),到17、18世纪的‘理性’本体论,再到19世纪的‘意志’本体论,到20世纪的‘欲望’本体论”,“不管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还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都说明了一点,下半身写作肯定会在当代人的鼓动下走向世界性前台,人类将在获得肉身解放的同时告别神性和理性,成为精神溃败后的欲望张扬和肉身满足的‘新新人类’”。⑨ 我们不应该以这一切都是世界人类在面临的问题作为自己开脱的理由,而应该以此为起点来清洗自己的精神灵魂。
法国现代派剧作家尤金·尤内斯库在其《注释与反注:戏剧论集》曾如是说:
没有哪个社会能够根除人的忧伤;没有哪个政治体系能够使我们从生存之痛中、从死亡恐惧中、从对绝对之渴求中解脱出来。⑩——以此种种去反观史铁生提倡的“生存方式”,不是更能够启引我们深思么?
“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我们有这种“精神(信仰)”吗?世纪转型时期的我们,“复活”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存方式中究竟缺少了什么?为什么会缺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注释:
①该文收集于刘小枫2003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圣灵降临的叙事》一书。
②贾平凹,曾令存:《九十年代“散文革命”检讨——关于散文创作的对话》,《东方文化》2003年第3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12期全文转载。
③该文后来收在华夏出版2004年出版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一书中。
④比如在《想念地坛》中:“我常常看那个轮椅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
⑤该书199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⑥有关这次讨论的情况可参考2000年5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对话》(第4辑)。
⑦参看《中国人需要重建精神》,《文汇读书周报》,第1026期,2004年10月22日。
⑧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⑨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⑩转引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