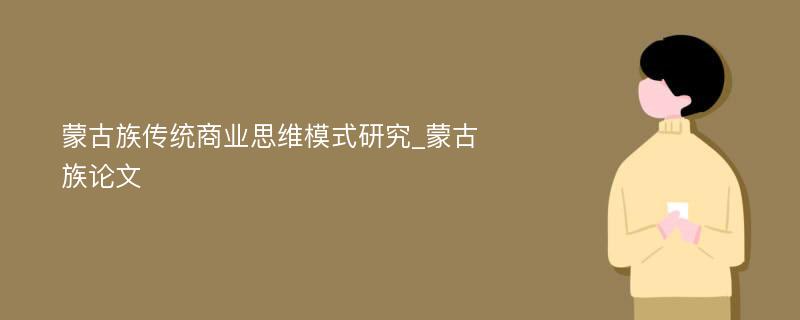
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思维方式论文,传统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13)05-0028-04
关于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的研究,是蒙古族传统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研究的空白。特别涉及交叉领域的研究,难度比较大。但与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研究相关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方式)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者先后出版了《蒙古族经济发展史》[1]、《蒙古族经济思想史》[2]、《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3],并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在哲学(思维方式)领域,研究者出版了《蒙古族传统理论思维》(蒙古文)[4]。另外,笔者就蒙古族传统思维方式、法制、经济、文学以及哲学思维方式等方面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上述研究成果为开展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研究打下了一定理论基础。此外,研究蒙古传统商业思维方式要立足于蒙古族世代生息、繁衍的蒙古高原,要认识到从匈奴、拓跋鲜卑、回鹘、契丹到蒙古族,蒙古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培育了不同民族的游牧经济形态,并影响着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特别在与中原农耕经济相伴生的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共生发展、相互资生的农牧经济形态。从十二世纪蒙古族主宰草原以来,与蒙古族游牧经济共同成长的蒙古族商业经济,特别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交流中,战争掠夺与商业经济共同发展,形成了以游牧经济为主导,以农业经济为滋养,以商业经济为润滑的社会经济形态,并伴随着蒙古族政权演变而发生着变化,逐步形成了具有蒙古族特点的商业思维形式。
一、蒙古族商业思维的形成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形成了蒙古族共同体。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武力扩张使传统蒙古族游牧经济通过战争催生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商业经济成为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从灭西夏,到西征花剌子模为始,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蒙古族游牧经济的供应短缺,常常是通过战争“掠夺”来解决。在这一时期,蒙古族对外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延伸和政治国家的完成,更是蒙古族的商业需要和商业需求战争化,战争成为商业行为的工具,或者说,商业经济是战争的内在本质。因此,在战争过程中,直接掠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各种工匠人是蒙古族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武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5]通过战争建立的蒙古帝国不仅完成了蒙古社会的基本建制,也形成了政治集权制下的蒙古族游牧经济和商业经济,特别是作为与战争共性的财富掠夺政策,形成了蒙古族商业经济发展中的战争掠夺经济,并成为传统蒙古族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补充。
为了满足蒙古族生活需求和实现战争的目的,成吉思汗在《大扎撒》中规定“凡进入他的国土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送到大汗那里。”[6]他积极要求将领和他们的子女,学习经商之道,规定“军队的将领们……并让他们像坚毅的商人那样地掌握他们所知道的本领”。[7]特别是成吉思汗购买三名不花剌商人商品的故事体现了蒙古族在商品交换中遵循的诚实、公平交易的原则。
1218年,蒙古汗国第一次组建“阿演京”的商队去西方交易,却被花剌子模国王下令杀害,成吉思汗说“撒儿塔兀勒切断了我们的‘黄金绳索’,还能饶他吗?给兀忽纳等100名使臣报仇雪恨……”。[8]这是蒙古族西征的开始,同时也是蒙古族传统商业思维方式的初始。在西征过程中,“他们虏掠了那些优秀工匠,使他们从事各种工作,”[9]并明确规定工匠免死,“惟工匠四百及童男女若干得免死为奴,余尽被杀。”[10]这些人“分赏其诸子、诸妻、诸将”,这些工匠为蒙古大军制造了战争所需的箭、弓、云梯与筑路造桥等工艺,同时也生产了大量蒙古族需要的日常用品,为以后的蒙古王国的手工业生产打下基础。“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全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们都向那里进发。”[6]123在西征中建立的蒙古帝国,彼此商业往来十分频繁,为东西方商业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蒙古人西征的起点是商业复仇,过程是蒙古帝国的形成,结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深化。
通过战争建立的蒙古族政权实行政商合一经济管理模式。在商业贸易中,蒙古族是商业经营的拥有者,却不是商业经营的主体。国家商业领导权掌握在蒙古帝王和贵族手中,他们运用政治地位,以权力交易的方式,以“翰脱克商业”收取“翰脱克钱”。从成吉思汗伊始,商人成为蒙古帝国的政治官僚,诸如:回鹘富商镇海、阿合马、桑哥及汉族卢世荣等人均为商人出身,控制不同时期蒙古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大权。这种商业官办、政商合一的经济模式主导着蒙古帝国的商业发展。“上至皇亲国戚、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喇嘛僧人都成为特殊阶层,依靠其权威和财富,通过政府的法规、命令、措施,保护自己的商业行为,从而形成了包括减免商业税在内的各种优惠的条件。尤其封建皇帝、王妃、官吏等都是高利贷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向回回等商人转移现金,从而吃高利。这就是元朝商业的一个重要特征。”[11]基于官商一致的格局,商业贵族拥有诸多的商业特权。在商业贸易中,如果商人出现亏本、遭遇意外,如劫掠等等重大损失,要由附近的居民赔偿。商人到达的地方,要求提供饮食,派遣士兵保护。严令保护商人的财产,禁止“拘雇商车”等,对于“封建贵族和大商人阶层,他们归降于蒙古征服者,获得了各种优待和特权。”[7]77
为了鼓励商业行为,对于商人,减免赋税。窝阔台时期的商业税是三十分之一,到了1283年(至元二十年),元朝规定,“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9月,又规定“徒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12]元朝对商业的税收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发展。对中原地区商人来上都做生意,政府规定“置而不征”的免税待遇。对于封建贵族和大商人阶层,归降蒙古的,能够获得各种优待和特权。
与中原地区传统的贱商政策不同,蒙古统治者鼓励商业发展。从元朝的社会发展看,商业经济不仅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也促进农业、畜牧等经济的发展,全国上下出现了经济繁荣的社会景象。如贯通全国的驿站,不仅提供军事保障,还是商业经营的重要中转站,是商业流通的枢纽。和商业贸易发展相一致,蒙古族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向城镇建设方向发展,在窝阔台时期,哈剌和林成为当时蒙古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商业贸易的中心。[13]
元朝立国后,蒙古贵族鼓励商业贸易。至元以后,国家仅盐税每年就有200万锭,“相当于国家一岁钞币所入(税粮未计入)的一半以上。”[14]忽必烈坚持“理财助国”的国策,“网罗天下大利”者,诸如阿合马之徒,“以功得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并“授以政柄,言无不从”。[7]69这些贪婪之徒做官后,“理算天下钱粮。已征数百万,未征犹数千万,名曰‘理算’其实暴敛无艺。州县置狱株逮,故家破产,十、九逃亡入山。吏发兵蒐捕,因相梃拒命。两河涧盗有众数万。”[15]前往上都的商人、车辆、骆驼等十分繁忙,夜晚篝火成片,人行不断。另外,元朝对金、银、盐等实施专营,严格控制了国内外贸易,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但也造成了平民的贫困,“十倍官钱,州敷县家,县敷编户,鬻庐逃亡,货妻折估。苍天!苍天!悲愤难言。”[7]263
二、北元时期蒙古族商业思维走向
自1368年妥欢帖睦尔败走大都后,北元蒙古族与中原地区再度陷入对峙状态,明朝政府通过军事打击、经济封锁等策略,使蒙古族经济处于瘫痪状态,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生锅破坏,百计补漏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16]从十四世纪末开始,蒙古族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主要采取了战争掠夺的传统方式,迫使明王朝以小规模边境贸易形式满足自己的需要。“蒙古人需要汉族文化成果主要包括食品、纺织品、铁器而开展的抢掠、侵犯,促使建立了明朝的商业贸易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蒙古人生活中存在着重大矛盾。即一方面他们企图通过抢掠、侵犯方法,从明朝获得所需东西;另一方面希望与汉人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通过派使者送礼获得边境贸易权。这个矛盾对蒙古人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北元蒙古族除了战争掠夺外,与中原地区的商业贸易主要通过“通贡”和“互市”的方式,恢复了典型的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交往的形式。
蒙汉通贡贸易是一种带有政治前提的贸易形式,它以蒙古族对明朝的政治臣服为条件,接受封赐的蒙古贵族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向明廷供奉物产,明廷则按照朝贡者的地位和贡品的数量,回赐相应的彩缎、生活用品等。到了也先时代,通贡贸易达到了高潮。蒙古使者“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人数最多时,一个使团有数千人,在1447年,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率领2472人来朝,贡马4162匹,貂鼠、银鼠、青鼠皮12300张。也先时期是蒙古族与明朝之间关系发展的新时期,贸易发展活跃,以“土木堡战争”为标志,以也先为代表的瓦剌蒙古商业思维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也先继承了传统的蒙古商业思维,倚重军事征服,对于蒙古百姓相关的经济发展关注不多,特别在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通过掠夺或进贡贸易来应付蒙古的经济需求,依然保持着脆弱的游牧经济特征。
在与明朝通贡贸易中,也先倚重回族商人。明朝时期,回族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汉氏回族商人多为富商、巨商。也先充分利用了回族政治、经济优势,让他们以官府的名义出使明朝,搭起蒙汉之间的贸易桥梁。在1448年组成的贸易使团中,回族商人占了42%。
土木堡战争是也先与明朝之间基于商业贸易的军事冲突,尽管也先在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俘虏明英宗,但出于双边贸易的军事战争并没有使双方走向更深的军事冲突,相反,以遣返英宗皇帝为标志,双方的经济贸易重新回到了正常轨道,通贡贸易快速发展。在也先统治时期,蒙古地区的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与内地的牲畜和皮毛交易每年达到几千万头(张),同时,内地也为蒙古族提供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蒙汉民族关系发展良好。
由于通贡贸易不能满足蒙古社会下层民众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明朝政府在蒙古族的要求下,最早于长城沿线一带指定交易市场,允许双方在指定时间里进行商品交易,以马市、木市交易为主。到明朝后期,随着明朝的衰弱和阿拉坦汗的崛起,蒙汉双方互市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从东起辽东,西至肃州的长城沿线增设了数十个市场,双方交易范围扩大,从最早的马匹、木材,发展到粮食、布、绸缎、马尾、盐、纸张等,甚至包括明朝查禁的兵甲、弓矢、刀剑等。从16世纪中叶开始,蒙古人的物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以1550年发生的“庚戌之变”事件为标志,阿拉坦汗与明朝确立了和平贸易关系,到1570年明朝册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蒙汉贸易进入到良性的轨道。自与阿拉坦汗和睦通商以来边境消除威胁,城镇平安,这是汉唐以来未曾有过的。
自阿拉坦汗实际控制蒙古草原后,守土拓疆、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他首先发展土默特部经济,积极吸收和鼓励流亡到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群众,开发土默特平川。16世纪后期,土默特聚集了十多万汉族农民,形成了新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商业贸易方面,蒙汉民族交易物种类繁多,蒙古方面输出物品如马、骆驼、骡子、驴、牛、羊、皮革、毡子、皮衣、马鬃、盐碱、薪炭、木材等,输入物品有粮食、布匹、衣服、农具、铁锅、纸张、药、漆、茶叶等日常用品,数量巨大,仅以1571年到1664年的马匹交易为例,通过官方市场进入内地的马匹超过300万匹,年均43万匹。蒙古方面的马匹供应已经成为中原地区马匹的主要来源地。
在贸易交易中,阿拉坦汗总结蒙汉长期贸易的经验教训,与明朝政府各自制定了互市贸易规则,其中阿拉坦汗制定了《规则条约》,明朝政府制定了“市场法五条”,并相互派官员管理市场。在阿拉坦汗时期,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当时贸易规则的制定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在《阿拉坦汗法典》中,不仅继承蒙古族传统的习惯法,还对保护和促进农业发展,发展畜牧业以及发展与明朝贸易等问题作了直接或间接的规定。
北元朝同明朝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北元社会的经济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在结束与明朝一个世纪的对抗后,北元社会逐步走向社会稳定,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特别是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为后来的商业贸易提供了稳定的畜产品来源。北元中后期与明朝的商业贸易发展,结束了传统的蒙古社会以战争掠夺财富的历史,通商解决了战争的根源和冲动。
三、蒙满时期的蒙古族商业思维
自蒙古族归入清朝统治后,蒙古族的商业贸易受到了清政府的严格控制,蒙古民族进入了封闭时期。与盟旗制相适应,旅蒙商的经济形式成为蒙古地区的商业主流。同时,俄国商业开始渗透到准噶尔汗国和喀尔喀蒙古地区,并成为影响清后期蒙古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旅蒙商是清政府对蒙古人的限制与汉族商人追逐利益的产物,也是蒙古族封闭的游牧经济的必然结果。旅蒙商输入的商品以消费品为主,质次价高。在商品交易的过程中,直接物物交换。商人们利用蒙古族百姓天性善良、直率和单纯的特点,采用欺骗、调包、灌酒等方式,以低价值物品换取高价值牲畜,严重损害了蒙古人的利益。特别是通过賖账的方式诈骗蒙古人的牲畜,“旅蒙商人把货物高价賖给,价钱则以羊羔或母羊折算,并设定羔羊一年或几年后都按成年羊以及包括繁殖的后代在内、连本带息地收回,以这种极高的高利贷剥削着牧民。”[18]对于淳朴、善良的蒙古牧民来讲,通过賖账方式购买的商品,让他们陷入了不能自拔的高利贷的圈套。
蒙古地区旅蒙商业的发展,严重损害了蒙古族经济发展,蒙古族的经济命脉被控制在旅蒙商的手中,限制和扭曲了蒙古族的商业经济发展,产生了敌视商业经济的民族心理,并影响至今。
自17世纪下半叶,噶尔丹汗开始与俄国进行贸易往来,主要以农畜产品换取米、面等农作物,直到1755年准噶尔汗国归入清朝版图。在喀尔喀蒙古,俄国根据《尼布楚条约》,通过哈克图关口以及建立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的商业铺子等方式,开展贸易活动,形成了与旅蒙商人共同控制蒙古族地区商业经济的格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和日本对内蒙古地区进行了政治和经济侵略,内蒙古的财富逐步沦为外国殖民者的财富。“因此,如果说近代蒙古地区商业有发展,那么这仅仅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腐败的清朝政府各种政策以及蒙古王公、喇嘛们与汉族流动商贩相互勾结,掠夺蒙古民族经济资源导致的畸形发展。这种商业贸易很快把蒙古地区变成了土产品销、畜产品、工业原料的基础。”[11]259
四、回回人与蒙古族商业发展
蒙古西征前,回回商人已活跃于蒙古和华北地区,成吉思汗对中亚的通商贸易主要依靠回回商人。西征后,打通了东西交往的通道,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蒙古军队作为工匠、军士带入中国,编入“探马赤军”,成为蒙古军征占全国各地,统一全国的重要力量,这些人也是后来回回人的主要组成部分。东来的回回人承担屯戌任务和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多居住在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为了在儒教文化根深蒂固的异乡生存下去,除了在维护自身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汉文化,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其在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发展为后来的回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到元朝时期,回回人已正式编入国家户籍。
在国内和海外贸易中,蒙古贵族大量地使用色目人(主体是回回人),随蒙古军进入中国的还有许多回回贵族、官宦、学术人士,以及来中国经商的回回商人。根据许多历史的记载,当时回回商人大量的来中国,更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元朝的“例献”与“关税”收入,很多是依靠回回商人。最初,回回商人对政府不纳税,一些人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形成了官商一体的经商局面。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向政府承包了盐课等税收,称为“扑买”,大肆搜刮财富,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元朝的商业发展。
元朝对包括回回人在内的色目人给予较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地位,更加促进了西北回回商人在中国的商业贸易,“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19]回回商人来往中原,常常是几十到数百人组成商队,带着大量西域产品,诸如珠宝、犀角、象牙、玉器、香料等,用这些商品换取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麝香、大黄等,长时间的往来,也使得古西北丝绸之路上的城镇再现繁荣。
元朝初期,回回有“屯聚牧养”的地方主要在甘肃河西、宁夏、河南、山东和河北一带,以及云南等地。以肃州为例,据记载,东关内“自东至西大街一条,长一里半;自南至北横街一条,长一里;其余小市僻巷不一,肆中贩粥,不拘时辰,朝市暮散,富庶与城内土孚。惟番回居大半。”[20]
随着元朝统治的稳定,回回商人的活动主要在一些较大的城市,诸如大都、杭州、泉州、昆明、兴元、甘州、凉州、广州、和林、上都等。在大都,回回商人数目不少,颇有经济势力,相当活跃。到1263年(中统四年),在大都的回回人有2953户。在云南昆明,据拉施特《史集》记载,当时该城共有两所清真寺,一个在城南门内,一个在鱼市街。回回商人居住在东门外一个叫金牛街的地方。在广州、泉州等地,回回商人更是人数众多,主要以经商为主,生活富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回回团体。
回回商人借助于元朝政府的支持,在元代商业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影响着蒙古族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蒙古族商业经济随着蒙古国家的演变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是战争、政权、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对应者,是蒙古族商业发展史的写照,是认识和理解蒙古族历史的经济之门和便捷之途,意义重大。
标签:蒙古族论文; 商业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商业经济论文; 蒙古帝国论文; 元朝论文; 明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