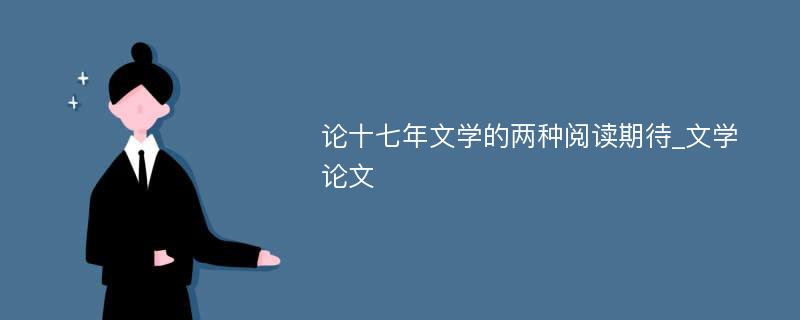
论十七年文学的两种阅读期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期待论文,文学论文,论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03)05-0039-05
十七年文学一个极其突出的现象,是题材的集中,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 几乎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半壁江山。在这两种题材类型的选择后面,当然有一个时代文 学观念的特殊作用。但除此之外,从读者的角度,还可以看到特定的社会心理对十七年 文学阅读兴趣、阅读动机和阅读目的的左右,其中尤以对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题材的阅 读期待引人注目。因此,剖析这种社会心理;以及由这种社会心理支撑的对革命历史题 材与农村题材的两种阅读期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
一、对“革命”的历史叙事的阅读期待
在文学的意义上,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是20世纪中叶一个巨大的“事件”,它 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全世界对“事件”传奇性的双重关注,即不仅关注冥冥中那个操纵 个人、民族、国家命运的神秘力量,而且关注短短28年中国共产党如何成长为时代巨人 的历史,这应该是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特别发达的原因之一。十七年之所以是 “激情燃烧的岁月”,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阅读体验之所以是一种激情体验,应 该都与这个“事件”密切相关,因为正是它改变了整整一代读者进入历史、阅读历史的 方式。在此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以《子夜》为代表的 以阶级性与典型性相结合,通过人物的阶级关系来展示社会面貌的模式;二是以《死水 微澜》为代表的以多元视觉鸟瞰社会变迁的叙事模式;三是以《财主的女儿们》为代表 的以个人心理历程反映时代发展的模式。[1]这三种模式由于都没有1949年改变个人、 民族、国家命运的巨大“事件”作依托,读者对它们的阅读期待只是一种个别的审美期 待,读者进入历史的方式因而也是个人的、分散的理解和认知活动。而十七年革命历史 题材文学的文本创作由于有了一个新的历史动因,有了一个新的聚焦点,所以它不仅需 要重建历史叙事,而且需要将读者进入历史、阅读历史的角度和方式从个人的、分散的 转换成社会的、集中的。
我们知道,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国统区、解放区划地而治的局面,但实现“胜利大 会师”之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心态仍有很明显的差异。对国统区(周恩来在第一次文 代会的报告中回避了这个提法,他称之为新解放地区)来说,新中国的胜利对大多数人 还有点始料不及,共产党成立不过28年,竟然奇迹般成长为时代巨人,这也太具有传奇 色彩了,于是在国统区的社会心理中,就多了些震撼、惊奇、神秘。同时,在巨大成就 的挤压面前,国统区社会对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对自己固有的人 生观产生了自卑感,他们不仅想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奇叙事,而且也想从现实生活中 ,从文学艺术作品中来理解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想从身边这些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的英 雄身上汲取营养,以重新拾掇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而对解放区来说,建立新中国一 直是一个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取得巨大成 功的时刻,那种自豪感、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对新中国即将翻开的那一页,他们的激 动、兴奋、期盼甚至急切、狂热都可以理解,为了这一天,他们毕竟流了太多的鲜血, 现在,他们不仅渴望对自己丰功伟绩的叙述,而且也愿意听到赞美和歌颂。这是跨入十 七年之前解放区社会的一种心理预设。这两种心态的差别,在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和周扬 分别代表国统区、解放区所作的报告中均有清晰的表述。茅盾在报告中作了很多检讨, 而且特别强调了与解放区的差距以及差距产生的原因。周扬的报告则比较理直气壮、斩 钉截铁,他特别强调了解放区文艺的正确性及未来的方向性。[2]
但正是这两种看似迥异的社会心理,却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对历史巨变的崇 敬乃至膜拜。在它的作用下,产生出一个强大的社会心理场,社会群体中个体的感情、 意志、动机统统臣服于主导历史巨变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训诫,个体的心理差异减 少了,群体思想和观念的统摄力、凝聚力增加了。正是这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催生了随 之而来的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阅读期待,这种期待视界与认识论意义的“前理 解”、与接受美学大师尧斯说的“审美经验期待视野”[3]不完全相同。认识论意义的 “前理解”强调的是认识发生前主体已存在的心理结构,皮亚杰称其为“图式”,[4] 海德格尔称其为“前结构”。[5]正是这种“图式”或“前结构”构成了人的历史存在 ,人接受、拥有语言之时,就是他接受历史和传统之日,离开了历史与传统在语言中的 延续,人的理解将成为不可能之事。“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则指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 的积累,乔纳森·卡勒把它叫做“文学能力”。[6]中国学者朱立元先生看到了“审美 经验期待视野”的理论残缺,曾对它作过世界观、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 养的补充,[7]但仍不能用来解释或替代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文学阅读的期待视界。
可以肯定地说;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文学阅读的期待视界既不强调文化传统和语言方 式的继承性,也不强调文学阅读的知识与经验储备。它是一种普遍的、由巨大的历史事 件造成的全社会的心理预期,是对意识形态近乎宗教情绪的仰慕。它也不同于普通的政 治文化心理,因为它几乎被净化到了没有世俗功利成份的程度,它对冥冥中改变了个人 、民族、国家的力量突然之间近在咫尺而感到窒息,必须屏住呼吸聆听其教诲。于是, 在它恭敬、虔诚的膜拜之下,“事件”本身也就被意识形态化了,表现在人们以想象的 形式去再现“事件”与他们自身存在之间的关系。由于事先已知道了“事件”的结果, 因而这种期待视界的阅读兴趣现在主要集中在“事件”的传奇性过程上。它造成了一个 阅读的兴奋点,读者迫切希望了解共产党人的成长历史,迫切希望解开历史传奇的谜团 。这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目的,在这种阅读心理的作用下,作家们开 始着手重建历史叙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切入这段历史,用不同的艺术形 式共同去表现共和国如何在历史风云中诞生这一时代的母题。[8]
这突出表现在题材选择上。革命历史当然是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 成立这段历史,它在党史上是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也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共四个历史阶段来划分的。细心研究一下,我们 会发现,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反映得最多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周扬 1960年7月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提到的11部小说为例;除《三家巷》、《红旗谱》、 《青春之歌》之外,其余的8部(《红日》、《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 黎明的河边》、《铁道游击队》、《草原烽火》、《战斗的幸福》)全是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题材。其他类型的文学创作;如戏剧、电影等等,情况也大体如此。为什么会是 这样?难道秋收起义、井岗山斗争、五次反“围剿”、长征都不算“革命历史”?当然不 是。我以为这其中有一个意识形态指向,而且它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的阅读兴趣、阅 读动机、阅读目的密切相关,从中可以捕捉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信息。我的意思 是说,中国共产党28年的成长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28年的斗争历史;以19 37年的抗战爆发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16年和后12年。前16年中国共产党一度不能成为 历史发展的正面主体,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只有22年,革命力量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其间还有“左”倾、右倾的多次失误。后12年则是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从弱到强的历 史,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这部“成长”的历史“象一个人一 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9]毛泽东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就曾坦 言: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到 了新的发展机会并最终夺取了政权。[10]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确有传奇色彩、确有奇 迹因素的话,主要也是发生在这后12年以及这12年中的后4年。这是一个关于发展壮大 的传奇叙事,冥冥中改变了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神秘力量,在12年的时间里呼啸 而至,几乎是在一刹那间就将历史定格了,这是多么神奇!多么让人神往!与此相关,在 读者的期待视界上就出现了一个关于成长和壮大的心理预设:不仅要求文本中“事件” 过程要有一条从弱到强不断发展、不断走向成功的叙述主线,而且要求人物的成长经历 也要有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从个人体验向宏大叙事的转变。以这个总的趋向作前提 ,这种阅读期待特别关注时代风暴席卷之下特定地区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人物的成长 历史,它的眼光或者集中在一个地区群众组织发动的经过;或者战役的过程;或者人物 的经历,特别不能允许在“成长”的主体叙事之外,容纳其他的社会生活内容。十七年 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正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开始自身的历史叙事重建的,不仅事件一 个比一个有意义,一个比一个有价值,一个比一个有传奇色彩,而且从普通农民朱老忠 们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们,也都从这一个模式走向了一个共同的意 识形态目的地。
当然,在1921年至1949年这个时限之外,还有一个被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 史区间,对这个历史区间的当代叙事显然不属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但 若仔细阅读这些文本,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它的历史叙事的价值取向竟与革命历史题材 毫无二致,同样指向了那个共同的意识形态目的。无论从话剧《茶馆》、电影《林则徐 》、《甲午风云》当中;还是从小说《大波》、《六十年的变迁》当中,我们都能够发 现它们与革命历史题材相同的意识形态联系,那就是以否定的形式为1921年之后的革命 张目,它讲述了革命的起源神话,从“发生学”的意义上,为1921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提 供历史必然性,为革命历史题材“成长壮大”的历史叙事作铺垫。阅读这类文本,完全 可以从中剥离出形式主义批评所说的母题或母题构成,[11]即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艺术布 局,它与革命历史题材有着相同的、不可分割的、最小的主题单元,是同一个主题和题 材的不同方式的联系和延续,区别只在一个采用了肯定的形式,而另一个采用了否定的 形式。因此,读者进入这个历史区间的方式与革命历史题材并无根本的区别。
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文学想像的阅读期待
建国之初,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开始着手将新中国的蓝图付诸实施,其中最为关涉全局 的即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涉 及面最广。它的实质是要让中国人告别几千年世代因袭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按理说, 这个“事件”的震憾力和冲击力,丝毫不亚于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然而,中国人相对 平静地接受乃至进入了这个现实语境。是什么力量如此神奇?竟然能够将如此惊天动地 的“事件”消解得悄无声息?
问题又得回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个话题上去。不过这一回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学想 象起决定作用的主要不再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那两种社会心态,不再是由那两种心态造 成的“前理解”结构。而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权威力 。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首先面临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legitimacy;一译义理性)问题。在社会民众眼中,政治权力只有在具备了较高的认同 率之后,权力才能变成权威,服从才会变成义务,政治权力才具备合法性。在西方,政 治权力的合法性经历了一个从“超越合法性”向“世俗合法性”演进的历程。所谓“超 越合法性”;就是以宗教、上帝来论证权力的合法性,以神性淹没理性,这就是通常说 的“君权神授”。所谓“世俗合法性”,是在文艺复兴后,理性抬头的背景下,以“社 会契约论”为核心;或以“体制合理”为内容认同权力的合法性。在中国,皇权更替的 合法性则以是否“正统”来衡量。[12]在权力合法性理论看来;政治权力的合法与否, 关键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形而下的体制合理,二是形而上的价值本源(意识形态)。比 如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似乎解决了形而下的体制合理问题,但在形而上的价值本源上 ,它最终还要回到上帝那里去。
新中国政权的体制合理与价值本源(意识形态)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一举获得确认 的。从前者来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历史的必然 选择,因为从鸦片战争起,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人的强国梦一 个一个都破灭了,“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现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 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13],这 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从后者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本源,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它裹挟着摧毁 旧的政治制度、改朝换代的雄风,一开始就以强势社会意识的姿态,造成了一种巨大的 历史惯性,这在当时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也无法与之抗衡的,它没有对手,不仅万众瞩 目,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分析和质询。一个有着激动人心的丰功伟绩和广泛基础的新政 体,再辅之以如此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权力合法性;它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权威 力,还能容有哪怕是半点置疑吗?
新中国农村的建设蓝图于是就这样不容置疑地实施了,这其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就是农 村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土改好说,那毕竟是分田分地,是让贫苦农民获得生活 资料和生产资料,当然一片欢声笑语,这场历史大变革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前只涉及北方 农村约一亿六千万人口,还有约三亿一千万人口在1950年秋季以后才开始土改,[14]但 它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1948年就已经由丁玲和周立波分别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暴风骤雨》中作了几近完美的描述,作为一座文学矿藏,它已经被先行者挖掘得所剩 无几了,加上随后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取代了土改在农村的聚集点位置,建国后 便鲜有人再去关注土地改革了。
都说农业合作化是十七年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场深刻变革,这是对的。但深刻在哪里 呢?一般的说法是:它要求农民放弃几千年世代因袭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因此是一场 革命。但我以为这样说还不够。在我看来,农业合作化之深刻,还在于它的意识形态属 性。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观念论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特拉西1801年提出 来的,它曾一度声名狼藉,孔德把它限定为虚假意识,曼海姆认为它与科学不相容。马 克思早年也多在否定意义上使用它,晚年才将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平台进行辩证分析, 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意识形态批判学说。半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理论 研究继续推向深入,比如在意识形态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原理和差异上,法国结构主义马 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就有过许多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意识形态是表象(观念、神 话、概念等等)的体系,具有特定的认识功能。意识形态是人类生存所不可欠缺的条件 ,没有意识形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从个人的一面来看,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动物,“ 人‘生活’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却全然不知是在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而是在人类‘世 界’的一个客体、人类‘世界’本身中生活的”。[15]所谓生活在人类世界本身中,就 是想象地生活在人类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人类的生存条件)中。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将人 类自身与现实的世界关系转换成想象的关系,人类才能在现实的世界中生活。在这个意 义上,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称为“关系的关系”,“第二层关系”。
农业合作化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关系的关系”,它在要求农民放弃世代因袭的私有 制和私有观念的同时,还要求农民以“想像的形式”去体验和再现自身存在与客观现实 的关系,并为这种“想像”作出了终极承诺。正是这种“想像”和终极承诺,它引导着 中国农民一步一步走出放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精神痛苦,引导他们产 生一种“向前看”的心理预设。由于刚刚经历过土改分田分地的欢乐晕眩,刚刚树立起 对恩人和救星的崇敬和仰慕,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走进这个“意识形态陷阱”,他们相 信党不会错,他们愿意“向前看”,愿意相信农业合作化是唯一明智的选择。尤为深刻 的是;当时不仅中国农民处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笼罩浸淫中,决策阶层也同样处在同一个 意识形态的重重包围中。意识形态使得决策阶层也把它对世界所体验的依附关系作为真 实的和合理的关系而接受了,这说明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的无意识结构。
至此,十七年文学的第二种阅读期待就已具备了刍形,那不仅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成 果的期待,也是对农村未来社会的远景想象。在这种远景想象中,还能够派生出对整个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变革成就的一种崇仰和期盼,即渴望在现实社会的经济变革中,再度 出现象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那样的奇迹,因此这种崇仰和期盼本身就极具浓厚的意识形 态色彩,大家都把幻象当作了真实,并投之以极大的热情,要求文学超前地反映这场本 身尚处于实验阶段的革命运动,于是,从创作和阅读两方面就共同创造了此类题材的一 个个意识形态神话。
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农民在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之后,集体经济到底能不 能担负起他们的生活责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上被所有的文本忽略了!也就是说; 意识形态的终极承诺是否兑现、怎样兑现、何时兑现已再无人顾及,文学的兴趣集中在 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创业史》);在合作社发展的规模之争;速度之争(《三里 湾》);在合作社的巩固与否之争(《山乡巨变》);在劳动态度之争(《锻炼锻炼》), 一句话,意识形态幻象成了文学的材料,在文本中被定形并获得了特殊形式和结构的是 精神,是被想象加工过的意识形态经验,而经济层面、物质层面的意义是缺席的,农业 社的社员吃得饱还是“吃不饱”;是否因吃不饱而“小腿疼”,[16]这没有人关心,即 使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也多半作了不切实际的展望。作家们热衷于从贫困落后的农村现 实中去搜寻未来社会的影子,构建出一个个理想的世界图景。而读者们也乐意把这种虚 幻的真实当作生活的主流和本质,并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它、赞美它。对比实行新的经 济政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再看看陈奂生作“漏斗户” 的凄清,看看李顺大造屋的悲怆,我们这才得出结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本用 意识形态幻象全部替代了严峻的生活逻辑!
但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恰恰也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可以认定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新人”被意识形态戴上了一幅“人格面具”,所以他们的言 行举止完全符合时代逻辑。我们可以评价他虚假、不真实,但绝对不可以否认他的真诚 。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相比,后者是已经凝固的历史,“事件”也有一个现成的 、圆满的结果,所以它的人物塑造、人物关系有丰富的资源,读者对它的阅读期待主要 集中在对革命过程的了解上。而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现在进行时”,要把握的是动向 、苗头、趋势,它的资源只能来自意识形态,所以读者的阅读期待只能寄寓在文学的想 象上。另一方面,在私有制、私有观念与集体化的冲突中,由于集体化是一种虚拟的、 想象的关系,而私有制、私有观念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所以对它的依 恋有助于我们对文化传统的认识,而这一部分大家都公认描绘得比集体化精彩,作家写 得得心应手,读者读得畅快淋漓。
再者说;在阅读体验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不关心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究意是幻象还是 现实,即是说我们可以不关心“真”与“伪”,那只是“想象”与现实的接近程度问题 ,我们应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实践本身,以及它对人的认识主体的限制 。即使在今天,十七年文学的现实语境阅读仍然没有、也不可能走出意识形态的限制, 当我们指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乃至其他现实题材追求的是一种“伪意识”时,那也 并不是相对于某种客观存在的“真意识”而言的。我们今天对十七年文学的反思性、分 析性阅读本身也还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它或许在向着“真相”、“真意识”逼近, 但结果却不可能寻求到终极真理。现在我们说它“伪”,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所构建的 体验自身与现实的“想象”关系距离太大,但由于我们同样不能超出自身所处的意识形 态,从一个至少目前并不存在的、完全客观的立场来对十七年文学作科学分析,所以我 们不可能宣称自己已把握了完全不可能把握的真理。[1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 由说今天的十七年文学阅读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体验,它的意义只不过在为历史的发展 提供“思想资料”而已。
收稿日期:2003-0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