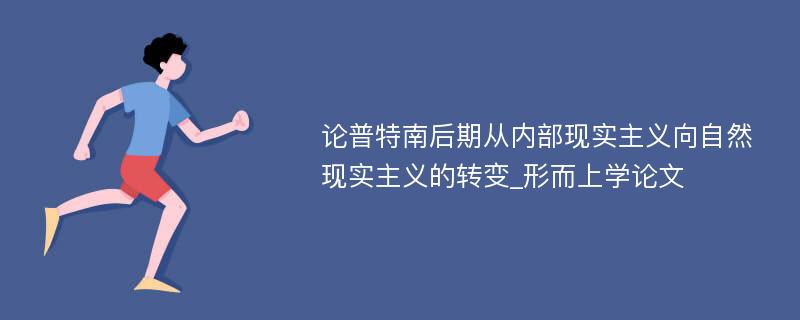
论普特南后期由内在实在论向自然实在论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在论论文,后期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当普特南放弃科学实在论而创立内在实在论学说时,英美哲学界反响强烈。然而十多年后,普特南又出人意料地否定内在实在论的基本立场,转向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视野。对于普特南的这一新转变,西方学术界至今尚未给予充分的重视,这或许与普特南后期轻视理论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有关。然而本文试图表明,普特南的这一转变值得关注,因为这一转变不仅在学理层面上比内在实在论更进了一步,而且整个改变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世界观,在元哲学的层面上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内在实在论的困境
在创立内在实在论之初,普特南的矛头所指是近现代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即形而上学实在论(包括他自己原先主张的科学实在论)。针对形而上学实在论所坚持的外部世界对象决定命题真值的观点,他认为:“构成世界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在某个理论或某种描述之内提出,才有意义。……‘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而不是我们的信念同不依赖于心灵或不依赖于话语的事态之间的符合”(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这就是普特南著名的关于实在论的“内部主义”观点。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只能在我们的语言(文化)框架内实现,真理实际上取决于信念内部的融贯而不是与外在世界的对应。这里的相对主义意味显然可见,正因为如此,普特南的观点受到罗蒂的高度评价。
然而普特南不能容忍由自己的学说中推出相对主义的结论。他宣称:“相对主义是自我否定的”(同上,第128页);“一个陈述可能一时是合理的可接受的,但却并不是真的。在我对合理性概念的说明中,我将为这个实在论的直觉保留一席之地”(同上,第2页)。普特南仍然要坚持语义外在论,坚持除“合理的可接受性”之外,还有一种超时空的真理概念。
普特南坦承,内在实在论在理论上确实还有很大的困难。他在20世纪90年代反省道:“一个诠释我们语词的世界,一个似乎存在着一种从外延伸到我们大脑之中的‘理智射线’的世界,是……一个幻想的世界。我不可能明白那幻想是怎样有意义的,但同时我又不可能明白除非那幻想有意义否则指称是怎样可能的。所以我感到我面临着一种真正的困境。我早期关于内在实在论的阐述是解决这一困境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尝试”(H.Putnam:Threefold Cord Mind,Body and Worl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17);“现在看来,这个方案从总体上说是有致命缺陷的”(H.Putnam:"A Half Century of Philosophy,Viewed From Wit-hin",Daedalu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Winter,1997,p.199)。
内在实在论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真正克服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降,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即在我们和世界之间设置一种分界面(interface),认识只能达到分界面。在分界面之内,认识是确定的,但在分界面之外(外部世界),则是认识无能为力的领域。我们和这个领域或许可有一种自然的关系如因果关系,但这不等于认知关系,我们不能直接达到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尽管现代西方哲学派别林立,但大多数哲学家仍然继承了这一思路,即便像罗蒂这样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也没有真正摆脱这一窠臼。
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同样陷入了这一覆辙。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图画仍然停留在认知者和‘外部’所有事物之间有一分界面这一基本前提下,……这种构想最终总是一定会使我们面对那看上去不可解决的问题。”(H.Putnam:Threefold Cord Mind,Body and World,p.18)“分界面”这一概念是二元分裂思维方式的产物。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下,对于问题的回答只能有两种:要么走当代唯物主义者如福德尔(J.Fo-dor)、戴维特(M.Devitt)的路,用外部世界对于我们的因果作用解释语言的意义,但这显然属于普特南内在实在论所摈弃的科学实在论的思路,是普特南所不愿采纳的;要么走反实在论者如古德曼、罗蒂、达美特的路,把语言的意义看作是共同体的概念框架所决定的。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倾向于这条路,但又不愿意承认这条路,这样,自我矛盾便是唯一的结局了。
二、清除分界面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普特南意识到了清除分界面的重要性。他从亚里士多德、詹姆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以及同时代的麦克道尔(J.McDowell)等人那里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近代哲学传统的新思路。经过几年的探索,普特南终于在1994年的“杜威讲座”中明确地将这一思路提升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论,这就是他目前仍在倡导的“自然实在论”。
普特南在他的自然实在论中着重对近代哲学的几个关键概念做了重新诠释。在他看来,近代哲学包括当代哲学之所以在分界面的泥淖中苦苦不能解脱,和哲学家们对诸如心灵、感觉、实在这几个关键概念的错误理解有直接的关联。心灵、感觉、实在在经过二元分裂式的凹凸镜过滤之后,失去了它们在前反思状态下的真实色彩。正确的方法是回到生活,回到常识的观点上来,以未分割的没有分界面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些传统概念,这样我们便能获得一种崭新的视角。在这一新视角下,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意图受到了同情的理解,而形而上学实在论试图为日常信念提供基础的做法则完全被抛弃。
1.改造“心灵”
“心灵”是个很不确定的概念。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多半倾向于把心灵理解为与外在物质世界相对立的内在领域,一种“内在影院”(塞拉斯语),其对象是观念、印象。哲学要探讨的是心灵的观念究竟怎样与世界沟通的。
普特南在内在实在论阶段已经开始否定这种孤立于外部世界、孤立于他人的心灵。不论是他的语义外在论学说,还是缸中之脑论证,都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只存在于心灵中的心理事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心理事件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心理事件并没有实际所指,它们不过是一些有待解释的心理记号而已,对于一切人类而言都是共同的。广义的心理事件则是在狭义的心理记号的基础上加上了社会、环境的内容,使原本无指称的记号有了指称,从而有了意义。在不同的人那里,狭义的心理事件可以相同,但广义的心理事件则是不同的。(见H.Put-nam:"Meaning of'meaning'",Mind,Language and Reality,Philosoph-ical Papers,Vo1.2,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75)
然而,普特南还没有真正摆脱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因为他毕竟设想存在着狭义的心理事件,认为它们是心灵的直接对象,只不过其本身没有意义罢了。实际上,普特南所谓的狭义的心理事件和近代哲学的“观念”一样,成了我们和世界的分界面。只不过和传统哲学不同,在普特南那里,心灵实际上被还原为人的大脑,对于狭义心理事件的研究可以由科学对于大脑的研究来完成,大脑成了“内在影院”,尽管它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麦克道尔的影响下,普特南改变了自己原先对于“心灵”的理解,不再把心灵看作内在独立的领域,而是把心灵看作一种能力系统。他指出:“心灵既不是一种物质的也不是一种非物质的器官,而是一种由多种能力构成的系统。”(H.Putnam:Words and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92,n.6)“关于心灵的谈论不是关于我们的某个非物质部分的谈论,而毋宁是以一种方式描述关于我们所拥有的某些能力的运用,这些能力伴随着我们大脑的活动并伴随着我们与环境的各种交互作用而产生,但是它们不必以还原的方式用物理学的或生物学的词汇,或甚至用计算机科学的词汇来解释。”(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 Mind,Body and World,p.37)
心灵不过是人在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地、自然地生长出的一些能力的集合,就像动物在与自然打交道时会生长出各种能力一样。人会思考,鸟会飞翔,其区别只不过是与环境打交道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们不会因为某动物具有某种特殊的与环境打交道的能力而把它与环境分割开来,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人具有某种与环境打交道的能力而将这种能力看作是一种内在的与环境对峙的实体。它们分别是人与动物的自然史的一部分,这里根本没有“内在”的问题。心灵首先应该被理解为动词,它意味着诸如回忆、筹划、注意、担心等一系列活动或活动能力。不应该把心灵当作实体,似乎它上演了回忆、筹划等一系列活动,而应该就把心灵等同于这些活动或活动能力。其实杜威早已提出过这一思想,普特南的新思路不过是回到了实用主义而已。
一旦我们把心灵理解为独立的内在实体(不论它存在何处),就必然难逃“分界面”的结局。因为只要心灵被当作内在实体,那么在它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只能是内在地为它所有,这些为它所有的东西何以能突破内在的界限而与外部世界挂钩,一定是一个令人不解的难题。如果设想它们与世界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认知关系,那就等于设想心灵有一种直接抓住外物的神秘的力量。由于反对这种神秘力量的设想,罗蒂和内在实在论时期的普特南都否定了直接表象世界的可能,在我们和世界之间设置了分界面。普特南现在意识到,只有改变我们对心灵的看法,消除它那独立的内在的特性,才有可能克服我们与世界的分离。
2.改造“感觉”
感觉是心灵最重要的内容,近代哲学家们往往将感觉(perception)等同于心灵的观念,它是我们的认识所能达到的最终界限。感觉成了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分界面。尽管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多数哲学家不再谈论心灵和感觉,但近代哲学的分界面思想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哲学家们或许不再把“我”理解为心灵,或许不再关注感觉而只谈语言,但不论如何,“我”与世界,语词与世界之间仍然需要分界面。哲学家们可能在分界面的处所问题上有分歧:在罗素、艾耶尔那里,扮演分界面角色的是感觉材料;在奎因那里,是我们身体表面的神经末梢;在罗蒂那里,是“记号和声音”;而在福德尔那里,则是我们的“心灵语言”(ment-alese),但有一个分界面横在我们与世界之间充当中介角色,从而割开我们与世界的直接联系,这一点对于上述哲学家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普特南自己也曾经是这一思维方式的追随者,他的内在实在论所坚持的正是一条笛卡尔式的路线。这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他还保留着感觉、感觉材料这一近代哲学的遗物。例如,在他的内在实在论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模型与实在》一文中,他曾说:“尽管哲学家约·奥斯汀和心理学家弗·斯金纳都想把感觉材料逐出存在的领域,但对于我来说,似乎大多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存在着像感觉或qualia(可感特性)这样的东西。”(H.Putnam:Realism and Reason,Philosophical Papers,Vo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5)而在他的内在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作《理性、真理与历史》中,普特南也仍然说:“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自然主义的描述是一个正确的描述,根据这种描述,思想形式、映象、感觉等等,是具有功能特点的物理事件。”(第86页)第二,正因为近代感觉分界面的思维方式没有得到纠正,导致他在谈论语言指称时表现出了强烈的罗蒂式的腔调,即“内部主义”腔调,认为语言的意义来自语言(文化)共同体内部,语言作为记号,并不直接对应于世界,它与世界只有一种因果联系(世界引起感觉,语言文化共同体对感觉做出语义的解释)。
普特南后来意识到,感觉分界面的思想是他在内在实在论失败的关键。在重读詹姆斯、奥斯汀以及麦克道尔等人的著作之后,他摈弃了这种主张,并分析了这一主张的失误所在:
首先,普特南指出,分界面是基础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感觉分界面的倡导者们认为,知识必定有一基础,这一基础必须是直接的不可更改的(即不可错的)。他们的推论是:“直接的”一定就是“不可错的”;我们在感知外部世界时会出错,因此我们的感觉直接感知的不可能是外部世界;感觉只能是内在的观念,因为只有这样,它才是“不可更改的”、“不可错的”。这种将“直接”与“不可错”相等同的做法已经受到来自詹姆斯、奥斯汀和斯特劳逊的驳难,普特南加入了他们的阵营,认为这种等同是没有根据的,他指出:“我们可以直接感知外部事物,但是我们不是不可更改地感知它们。直接性不等于不可变更性。”(H.Putnam: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42)“直接的当然不意味着不可错。所以常识实在论的世界概念并没有和感觉材料相关的理论特征。”(引自普特南1994年3月1日在哈佛大学所做的题为“一种关于真理的‘发生学’理论”的讲座)
根据普特南的观点,知识的直接出发点并不是纯净不染的感觉,而是渗透着文化传统、价值态度以及思维方式等等的具体实践生活。感觉作为这种实践生活的产物,作为它的一部分,是客观的(当然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对于外物的感觉,同时也是“可错的”。
其次,普特南指出,分界面是“句法描述”的产物。持分界面主张的哲学家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句法描述”的错误。这些哲学家们,可能会在分界面到底是心理的还是物理的这一点上有分歧,但他们都主张:这些分界面是可以撇开内容加以描述的,“它们被理解为具有我们可以称作纯句法描述性质的东西。”(引自普特南1994年4月21日至26日在哈佛大学所做的题为“知觉与概念”的讲座)比如,持感觉材料说的哲学家们认为,感觉材料是可以描述的,就像一幅图画是可以描述的一样。一幅图画可以简单地用数字化表象的方式来对它进行描述,而根本不用涉及它的内容,即不用涉及这幅图画是关于什么的图画。我们可以把齐白石的“虾”图用“某某颜色在X,Y,Z,某某颜色X',Y',Z'等等”的方式予以描述,这幅图一旦被如此描述之后,它本身似乎并不指虾,而是在加上某种解释之后,它才指虾。
感觉观念或感觉材料在这种描述之下,本身无所指,它只是借助于其他关系才有了表象的功能。这样,认知者与世界便被隔离了。普特南认为,用“句法描述”的方式来谈论感觉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精神图画不同于物理图画,我们不可能像描述物理图画那样,撇开内容来描述精神图画,我们所具有的感觉观念,所听到的、想到的、看到的句子等,内在地就指称它们所谈论的东西,这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或听到的“符号和声音”(罗蒂语)内在地具有意义,而是因为使用中的句子根本就不是一丛“符号和声音”。
按照普特南这一新的思路,“看见一个对象不应该被认为是两个部分的事情:作为第一个部分的是在对象、光线和眼睛之间的一种‘非认知的’交互作用,而伴随它的则是大脑中的‘认知’过程。整个事情就是认知的;大脑中的事件是我的认知的和感觉的能力的一部分,这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生物,伴随着某种正常的环境,并且伴随着个体和种族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历史”(H.Putnam:Words and Life,p.289)。
感觉不再是隔开我们和环境的分界面,而是我们和环境交互作用的诸多能力中的一种。如此改造之后,我们便仍然能谈论感觉,谈论我们关于世界的表象。不能因为近代以来的许多哲学家们的错误感觉理论,便像罗蒂那样否认表象、感觉本身,要把我们实际从事的表象活动和关于表象的理论区别开来。“放弃作为一种需要‘语义学’的分界面的表象不等于放弃整个表象的观念”。(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 Mind,Body and World,p.59)
三、回归生活实践的实在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普特南曾数次表示,他在80年代对于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否定是“令人后悔的”。(H.Putnam:"A Half Century of Philosophy,Viewed From Within")他现在认为,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动机是好的,目标也是正确的,错误只在于它的论证方式。它原本是想捍卫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一致性,由于恐惧实证主义的驳难,便设定了一个外在的基础作为保证,然而由此一来,它便要对这种基础做出说明,从而给自己揽上了一种解释的负担。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回到生活中来,不用超经验的东西来解释经验的认识,因为“经验的陈述已经对世界做出了断言——关于世界的许多不同种类的断言——不论它们是否用了‘是真的’这样的词”(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 Mind,Body and World,pp.55-56)。
经过传统哲学的长期熏陶,“实在”概念仿佛天然就有一种不同于常识的形而上学意味,哲学家们说的“实在”必定是普通人所不能窥见的真正的存在。普特南现在要告诉我们,这是本末倒置了,哲学家们对“实在”概念的理解非但没有高出普通人的理解的特权,相反,它是造作的,是应该得到改造的;实在论只能是基于常识的实在论。
如果传统哲学对于“实在”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那么常识的实在论便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普特南要坚持常识的实在论,首先必须否定关于“实在”概念的传统解释。他认为,我们既不能接受形而上学实在论关于实在的界定,也不能像一些相对主义者那样,干脆抛弃“实在”这个词:生活既要求我们承认实在,又要求我们去掉实在头上的形而上的光环。
传统实在论之所以要预设“世界本身”,是因为它担心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我们的概念(conception)的污染、歪曲,但在普特南看来,没有受到概念污染的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实在,因为它是我们无法谈论、甚至无法想象的实在。这一点早在内在实在论时期便已明确,现在普特南更进一步认识到,概念并不是所谓对于世界本身的外在的附加物,它是人类自然史的一部分,它和世界的融合是“无意识的”,我们只能在理论上把它们分为两者来谈,而在生活实践中,它们根本是不可分的。世界是充满意义的世界,我们应该认识到:“接近常识的实在并不是要求接近某种前概念的东西”(H.Putnam:Pragmatism:An Open Question,Blackwell Publishers Ltd.,Oxford,1995,p.21)。
我们所面临的是概念化的世界,但同时也是真实的世界、实在的世界。这里的关键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不把概念看作是由主观的人发明的整理世界的工具,而是将它看作在人类实践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世界的一部分。
新的实在论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它和传统实在论(包括内在实在论)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实在论预设了纯净的人和自在的世界,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外在的,哲学所要探讨的就是主观的人是怎样认识客观世界的。而新的实在论继承了实用主义路线,根本反对传统实在论的预设,主张人和世界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彼此依赖、彼此渗透的一体。没有传统实在论所预设的主观的“人”,心灵无非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能力系统;没有传统实在论所预设的“世界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传统实在论所预设的“世界本身”是个空洞无意义的概念,世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世界。
从普特南的角度说,当心灵不再是一种与世界对峙的独立的内在领域,当感觉不再是隔开我们和世界的分界面而是我们对于世界的直接表象,当实在和我们的概念、诠释等溶为一体,和人类客观的生活实践溶为一体时,重谈真理符合论便有了可能。我们既无需给真理背上与“世界本身相对应”的包袱,也不用因不能对这种对应做出满意的说明而仿效罗蒂,放弃真理的谈论。他指出:“充分肯定这样一个原则,即:把一个命题叫作真也就等于断言那个命题……而又不承诺[真理]取消主义者的错误,我在维特根斯坦的著述中所看到的这一可能性,是在意识到常识实在论与精致的形而上学实在论之间巨大差异时保留我们的常识实在论的条件。”(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 Mind,Body and Wo-rld,p.68)
普特南的真理观在此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先他不满意塔斯基的真理论述,认为它只是提示了真理定义的同义反复性质,没有实际意义,在关于真理的哲学讨论中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它并没有涉及实在的问题。现在他意识到,要“充分肯定我所说的‘塔斯基的洞见’”(同上)。这么说,并不是要取消真理的哲学谈论,而是要表明,由于人和世界的交互作用,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参与了确定事实的过程;而事实与实在并不是经验与超验的对立,它们在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完全合而为一。一个命题被我们认可,无非是对应了我们所断言的事实,这些事实就是实在之所是。所以,对应于事实与对应于实在其实就是一码事。
真理不是命题之外决定命题的一种形而上的性质,不能用形而上学实在论所说的“真理”来解释命题;真理不是没有立足点的,真理的概念和命题的概念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能说一个是另一个的基础。“我们对什么是真理的理解,在任何具体的场合……,都是由我们对命题的理解给出的,它取决于我们对于‘语言游戏’的掌握”。(同上书,p.67)命题的真假当然要受制于实在,但反过来,实在也受命题的渗透。这里确有一种循环,然而这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循环,而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同义反复。
这样,普特南就既捍卫了常识意义上的真理符合论,又避免了罗蒂式的相对主义。真理是认识与实在的符合,但这里所谓的实在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实在,一切超越生活、想以某种形而上的基础作根据以决定我们的认识是不是真理的企图,都是一种幻觉;而一切试图用达不到这一基础为理由以坚持相对主义的做法,也同样是一种幻觉。超越形而上学实在论与相对主义两难的秘诀在于:回到生活实践中来。
由科学实在论到内在实在论再到自然实在论,普特南思想演变的轨迹正好构成了一个正反合。自然实在论纠正了内在实在论的反实在论色彩,重新恢复早先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追求,重提真理符合论;然而它又继承了内在实在论对于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批判,祛除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超验前提,在常识而非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在论的信念。
对于普特南的转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喜爱“硬技术”的读者或许会对普特南感到失望:他的论证显然不像早期那样细腻,那样锋利,那样富有逻辑的力量。和罗蒂相似,他也大量借助了他人的观点和论证;与早期相比,理论明显不那么周密,有时甚至让人感到粗糙和零乱。但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普特南后期哲学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在其论证,而在其眼光,因为他的这一转变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哲学的出发点到底应该是“旁观者”还是“当事人”?西方哲学主流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哲学,这主要表现为两点:“我”是世界的旁观者;“我”是“我”和世界关系的旁观者。主客二元对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等,无不与此相关。普特南后期的转变就是要把“旁观者”变为“当事人”,从“我”和世界在实践生活的交互作用中去理解“我”,理解“世界”。以此既铲除二元分裂式的思维方式,又化解在知识领域中的基础主义,为困境中的以二元分裂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哲学找到一条出路。视野更多是黑格尔式的而不是康德式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探索,它不仅可能预示着西方哲学的未来,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新思路。
第二,哲学的重心到底应该是知识论还是伦理学?知识论关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伦理学则关注人类的幸福和繁荣,人类的生活和实践。西方哲学传统自近代以来,注重知识论,注重从知识的角度解释世界、解释生活,由此导致事实与价值的割裂,导致对于客观性的崇拜。普特南的后期哲学立场与此相反,试图从伦理学的角度去看知识,把人类的生活实践理解为一个整体,知识只是其中的一环,它受制于人类对于自身幸福和繁荣的理解。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普特南作为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转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伦理学不再只是知识论的具体应用,而是哲学思考的重心所在。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普特南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