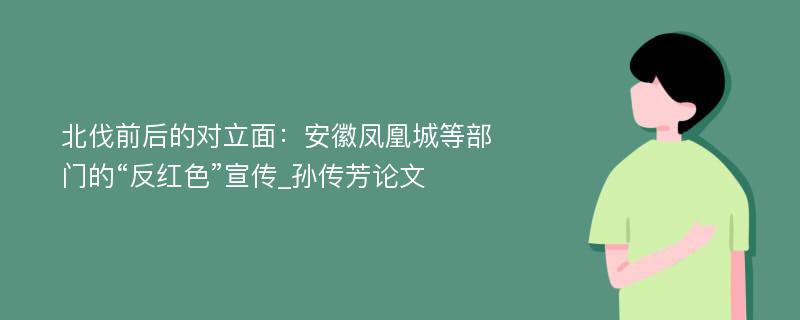
北伐前后的另一面相:奉、皖等系的“反赤化”宣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面相论文,反赤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2-0134-08
近年来,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即北伐不只是一场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领域的综合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大变动,而且北伐的胜败也不只取决于军事战场。① “政治宣传”与“军事行动”相结合是北伐战争区别于以往军阀混战的显著特征。在北伐的进程当中,始终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在军事上刀光剑影的背后,始终隐藏着政治上的高下判断。宣传作为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在此时已经受到国人的关注并开始在战场内外得到比较娴熟地运用。无论对于南方的国共两党,还是以奉、直、皖等系为代表的北洋集团,都试图利用多个“载体”,运用各种形式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
在南方,国共两党通过对“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的广泛宣传与利用,建构了一套有利于自身行为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并由此将其作为发动“北伐”的内在逻辑之一。而作为北伐的客体,奉、直、皖等系军阀也意识到树立政治旗帜的必要性,逐渐形成“反赤化”口号为自身的军事行动正名,以此对抗南方的政治宣传。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也是南北双方在政治宣传方面相互较量的过程,战争的胜负不只取决于军事战场。不过,双方的这种政治宣传究竟对于实际的胜负有多大的影响,还应具体分析。
一
“赤化”的符号最初指向改组前后的国民党。在1924年初,随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以及“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反对派纷纷指责国民党已“赤化”,这是国内“赤化”说法兴起的重要源头,但此时这种声音影响范围有限,基本上只限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斗。
五卅运动时期,英日等国纷纷指责国共两党以及苏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五卅运动贴上了“过激”、“赤化”的标签。“赤化”说法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反赤”的气氛开始局部出现。列强的这种指责在当时发生了一定效力。《国闻周报》记者胡政之描述:“自五卅惨案以来,英国之宣传政策与外交手段,亦已大著威力。其先盛传中国排外暴动赤化之说于各国,使外人对中国怀抱恶感,然后则利用此恐罹厌恶之心理,诱各国于一致行动之境地。”② 中共后来也承认,由于帝国主义者反赤运动的成功,使得“五卅”后一年多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变成全中国的反赤运动,由此导致了“赤”与“反赤”两条战线的尖锐对抗。③
1925年底,原属奉系的李景林部在攻打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中对“赤化”这一符号加以利用,树起“反赤”旗帜为自身的军事行动正名。这年12月4日,李景林发表讨冯通电,攻击冯“愚弄部下,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而李本人则“荷戈卫国,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坠落”,其间并有“不问敌不敌,只问赤不赤”之语。④ 此后,“反赤”的名义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伐的军事战场之中⑤。
在双方的争夺中,李景林部受到重创,国民一军攻占了天津、直隶,与河南的国民二军以及察、绥、陕、甘的国民军势力连成一片。同时,段祺瑞的执政府也处于国民军的完全控制之下,基本上形成国民军独占中央政局发言权的局面。不过,虽然国民军取得了胜利,但这种局面只能暂时维持,李景林余部入鲁境内与张宗昌形成直鲁联军,伺机反攻国民军。同时,国民军的这种胜利重新调整了当时直奉两系军阀的关系,为他们重新联合提供了契机。
吴佩孚曾因冯玉祥倒戈,在北京政变之后元气大伤。郭松龄倒戈张氏之后,吴氏以“同病相怜”的姿态,联络张作霖,谋求共同对抗冯玉祥,鲁省将领张宗昌也极力拉拢吴张合作。1926年1月5日,张氏致电吴表示谅解。1926年1月10日,奉直联盟在汉口建立,作出了“双方共同以冯玉祥为敌,合力消灭冯和国民党”的决定。⑥ 至此,两个曾经的对手结成了联盟。1926年1月20日前后,国民军与奉直联军的战争分别在山海关、山东、河南等地展开。战事对国民军逐渐不利,冯氏自知不敌,主动退却并取消国民军的番号。1926年4月中旬,国民军被迫撤离北京,退守南口,段祺瑞执政府旋即倒台,奉直势力联合执掌中央政权。
奉直两系占据北京之后,虽在中央政府的组建形式上发生分歧,但在军事行动的计划方面意见大致相同,齐燮元在京对中外记者演说直奉妥协的政策就是“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以期施行全国之刷新”。⑦ 4月底,奉、直、晋、鲁各军在北京居仁堂召开军事会议指出:“国事糜烂,民彝陵替,实由国际共产党之图赤化我中国也,以言义战,首当讨赤”⑧。决定计划兵分三路攻打国民军:奉军进攻热河,吴军进攻南口,阎锡山的晋军进攻绥远,推吴佩孚为“反赤”联军总司令。1926年5月10日,直、奉、晋等各方曾在北京成立了“讨赤各军联合办事处”,除奉直军阀要人出席外,阎锡山、刘镇华、孔繁锦、张兆钾等晋陕甘地方军阀均派代表参加,“共谋军事上之统一,以期彻底的讨伐赤化”。⑨ 奉直联盟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北洋体系在“反赤”旗帜下实现重新整合。
二
直奉等军阀以“反赤”名义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也采取一些政治手段打击“赤化”势力,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社会范围内取缔“赤化”宣传并制造“反赤”舆论。
1926年4月,直奉联军打败冯玉祥国民军进入北京之后,张作霖立即以“宣传赤化”为名查封《京报》报馆,枪杀社长邵飘萍。4月28日,李大钊等19位国共两党的重要干部在北京被张氏处决。不久之后,鲁系张宗昌也以“赤化”罪名处死《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申报》报道,北京卫戍司令部奉令检查各处来往邮件,发现宣传赤化者,一律扣留。同时,对北方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书籍严格控制。⑩ 5月,靳云鹏在表扬负责维护京津治安的王怀庆的同时,对于“赤化”予以指责,表示将以“礼义廉耻”与“孝悌忠信”为根本,与张作霖同心“讨赤”。(11) 此时,张宗昌也通电各报馆:
比年邪说朋兴,赤化滋蔓,偕窃名义,号令天下,阴结叛徒,犯上作乱,纲纪灭绝,伦常乖谬。我张吴两帅痛国基之将顷,惧正义之垂尽,遂乃命将出师,联合声讨。至赤氛未靖,残敌尚存,尤顾同心协力,彻底肃清。总之此次讨赤救国,宗旨光明,以义始决不敢以利终,南山可移,此志不渝。(12)
在京、津、鲁等境内,反赤一方大力搜捕所谓“赤党”。《申报》报道:“张宗昌委洪锡华为密探处长,募密探二百名,编两支队,专查赤党及捣乱分子。”(13) 王怀庆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后,在京津间大肆搜捕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并先后派人到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检查,但并未搜到赤化文件。王怀庆还颁布治安办法,规定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14)
“反赤”军阀的这些做法在北京的知识界、学界引起了极度的恐慌,“枪毙邵飘萍后,北京报界之一部分,乃大起恐慌,有迅速躲避者,而北京学界之恐惧,亦达于极点。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及师范、中俄、法制等各大学教授、学生中之共产党员,均已避匿。北京大学已焚烧过激之书籍文书。……奉直将领商定检查国立九校赤化分子,北大教员学生请假甚多”。(15) 在这种气氛中,北京高校的许多教师纷纷南下,以致形成一股潮流,其中不乏鲁迅这样具有相当名望与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晨报》评价这些人“思想较新不见容于旧社会”(16)。此处所谓的旧社会当指当时“反赤”军阀控制的区域,大体指北方。
在奉系一方,其“反赤”宣传的内容主要认为“赤化”不适合中国且危害深远。张作霖在1926年12月6日发出的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的通电中指责:“我国野心狡猾之匪徒,拾人唾余,宣传赤化,借不适用之共产学说,利用多数贫民,及下流社会之心理,鼓励青年学子,激烈暴徒,以乱我国家,以饱其欲壑。……夫政治本无绝对利害之可言,惟视是否适合时宜为断。吾国为四千余年盛名文物之邦,未有治国之要素,何必取此不合国情之说而效之,何必取此世界一致反对者而行之。”(17) 同时,张氏也认为“赤化”就是“卖国”,“反赤”就是“救国”:“比者共产分子归附苏联,宣传赤化,甘心卖国,贻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逐,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18)
但张作霖的这种自我标榜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也没有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环境。由于对“赤化”宣传的极力控制,北京与南方的舆论氛围差别明显。中国青年党人士李璜在1926年深秋从北京到了广州之后才第一次看到《新青年》(此《新青年》为中共不定期机关刊物,并非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与《向导》,它们都和普通刊物一样公开陈列,而封面上用大字印着“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字样的书籍充斥广州书店的柜面。而在北方,这些是需要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放低了声音才敢提起这些名词的”。(19) 几乎在同一时期,留在北京的张慰慈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也称北京舆论“不健全”,“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一些刊物经常被删去文章,“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所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他还指出,北京的这种局面已经类似于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20) 国民党人黄郛的妻子沈亦云回忆在北伐期间,北方社会大家都视“容共”为洪水猛兽,对于“赤化”、“共产党”等话题“恐惧而不敢讨论”。(21) 大批文化人的南移以及他们对北京的这种观感也表明了知识界对待直奉军阀的态度,其存在的“道义”基础已经开始瓦解。
三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各地的势力就已经开始重视“宣传”在战争中的作用,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打“电报战”。一场战争只进行几天便可分出胜负,而之前双方的“电报战”往往要持续数日之久。一些军事派系或直接创办报社、通讯社,或“资助”一些这样的组织,从而控制舆论导向,吹捧自己,攻击对手,此时,舆论的力量已渐渐被认识。
北伐开始之后,南北双方的“宣传战”、“舆论战”更加激烈,政治宣传被更多地应用到了战争当中。《大公报》报道,“此次党军作战,盛用宣传。孙传芳作战,于宣传上亦大下功夫,以资抵制。联军宣传部除每日公表战事情报外,并间以时评社论之类,投寄各报馆”。(22)
在南方,“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的提出以及相关的大量宣传工作,不仅使国民革命军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一种“有主义”的军队的形象,而且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民众动员的社会效果。《大公报》就认为北伐军不仅善于打仗,而且善于宣传,且效果很好,“盖蒋军前此之节节顺利,固由北军在湘鄂太伤民众感情,亦由民党宣传力异常强大所致”。(23) “国民党人习闻宣传之法,稍稍用之,颇奏奇效”(24)。北方奉、皖等系受到此种影响,纷纷照搬这种做法。《新申报》报道:直鲁联军鉴于“赤党唯一的工作,乃为宣传”,于是在“用兵之始,先之以宣传,使一般社会,皆知赤化之为害与赤党之不得不讨”。(25) 孙传芳由于与南方接触最多,感受也更深:“党军作战,巧为宣传,所到之处有老百姓为之帮忙,直有防不胜防之势,本人此次,受亏不少。”于是,“运用政治手腕与宣传作用”,“双管齐下,等量并重”。(26) 正是认识到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影响力,孙传芳也曾标榜“三爱主义”与之对抗。
早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孙传芳就已经有意识地控制“赤化”思想的传播。以上海为例,一向为孙氏的重要基地,且为“通商巨埠,华洋荟萃之区”,“工厂林立,工人巨万,最易煽惑”,自从五卅之后,所谓的“赤化”风潮一直没有停歇,孙传芳下令凇沪警察厅对此严加防范。1925年12月,孙传芳在上海与租界当局接洽,主张对“赤化”严格取缔,维护公共安宁,并得到了租界的赞同。(27)
此外,孙传芳还下令严查“赤党书籍”,“以杜乱源”。(28) 并命东南各省检查厅“公布取缔过激思想之法规,凡宣传无政府主义者,处以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之徒刑,以金钱及权势诱惑他人,使有过激思想者,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徒刑”。在此情境之下,沪邮电局派员从严检查往来广州、长沙、莫斯科等共产党宣传物件。孙传芳甚至通电:“在赤祸未靖以前,决不容有其他之主义,惟有唯一之讨赤主义。”(29)
北伐开始之后,孙传芳更加重视对“宣传战”的应用。其在南京总部“特设宣传机关,日以印刷文件,传播各省”。在其辖区各县,均设有“讨赤”宣传委员,专司宣传之责。(30) 《申报》报道:“淞沪警察厅接奉南京孙总司令训令,略谓据报粤东近日密派青年党人,由粤分批乘轮来沪,宣传赤化,煽惑工人,希图扰乱,令饬严查防范,以维治安。严厅长奉令后,特派侦缉队副队长挑选精通粤语之侦探数名,前往南北各码头,认真调查。”(31) 据《晨报》报道,孙传芳“一面对于自粤潜入之宣传员,严加警戒。一面组织反赤宣传队,派赴苏徐沪杭等地宣传”(32)。“孙传芳前函请徐鼎康于苏省候选人员中,挑选三十人,分赴各省担任讨赤宣讲委员,每员担任二县,以两个月竣事,每月给薪金六十元,川资四十元”(33)。法捕探长率领通班侦探,轮流至界内各大旅馆严行搜查,“如有来路不明,形似可疑者,均须详询来历,其外如各轮船码头及各学校亦谕令全体侦探一体注意,一经查处,即行拘解捕房询究”。(34) 如下这则报道最为具体:
此次联军出师讨赤,对于宣传一事,亦极注意。除于本月六日出版联军日报外,更由训练参谋二处,逐日将前敌所得之战讯,及胜利消息,及各项军报,用铅印或油印,分发各机关团体。同时更拟选各项讨赤文字,粘贴于各通衢大道,使人民览阅无遗。此外更刊印各项标语,如“赤化为灭国忘种之导火线”,“党军部下之五月份军饷尚未发”,“到处强用不兑现之军用票”,“党军利用工人学生及男女青年,打先锋惨不忍闻”,“党军强迫人民纳捐”,“党军任意没收人民财产”等语,异常之多。骤视之有如爱国运动然。宣传之努力亦可见其大概。(35)
“反赤”一方所进行的宣传规模很大,奉军的宣传部,人员多达数百人。张宗昌也因为“赤军利用宣传,鼓惑青年”,于是命专人负责主持宣传事务,并组织顾问参议等百余人,分赴长江各省及闽粤等地,宣传反赤。(36) 《申报》报道:“张宗昌委何海鸣为讨赤联军宣讲队司令,就鲁境召集中学生二千余名编为三队,俟到苏后,再于上海召集苏皖赣浙闽五省学生,充宣讲队,分发各省。”(37) 奉军进入郑州之后,宣传队随之同来,《大公报》报道:“各马路,各街巷,车站近处,城门洞里,满贴黄白绿色之反赤传单,种种口号,如‘认贼作父之靳云鹏,媚外卖国之蒋介石’,‘保存旧礼教旧道德’等,不一而足。”“传单皆用黄白绿色印就,绝无红色,可见用意之深也。”(38)
同时,直鲁联军总司令部宣传处还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征求反赤文字,“不论撰作,译述之论文及小说、杂录,均所欢迎,长篇巨制,尤所需要”,“但有佳作,不吝重酬”。(39) 至于宣传方式,主要是利用演说、标语、漫画、游行等方式进行“普及”性质的“反赤”宣传。“北军的宣传之术至为夥颐,或颁发小册子,或张贴告谕,……惟简单标语,附以图画,读之者既易了解,尤易感动,洵为宣传最良工具。自直鲁宣传队南下,讨赤文字遍于通衢。”(40) 在宣传的方式方面,南北两方并无二致。
四
“反赤”是北方军阀树起的一面政治旗帜,但所反之“赤”到底指什么?为何反赤?赤化的主要危害是什么?这些都是反赤一方所要解决的问题。奉直等军阀的“反赤”宣传主要服务于其军事行动,由于面对的是最基层的普通民众,在当时社会识字率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这种宣传十分强调其鼓动作用,淡化理论色彩,讲究浅显易懂,因此缺少学理上的支撑,无法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更无法上升到政治思想的高度。其“反赤”宣传主要是应用通俗的语言,渲染赤化的恐怖与危害,夸大赤党对群众安全的威胁,他们并未曾致力于对此口号进行严密、系统的理论阐释。如《直鲁联军宣讲队之标语》称:你们第一要晓得蒋介石是害人贼;赤党要来抢你财产了,大家赶快起来挡着他;无父无兄与共产共妻,试想世界上行得通吗;你的财产,你愿被共产贼党用强抢的手段共了去吗?你的妻女,你愿被共产贼党掳掠了去,作他们的公妻吗;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走狗。(41) 孙传芳也在“防赤”布告中称:“南方赤党,竟敢师出无名,共产公妻主义,强迫湖南实行,强夺商民财产,利权划归党人。”(42) 一直倾向奉系的《晨报》也报道:凡共党所至,焚掠屠杀,无所不用其极,其残暴凶恶,莫不令闻者动色叱舌。(43)
北伐期间,南北双方都控制自己的宣传机器,报道有利于自己的消息,隐瞒对己方不利的消息,甚至捏造一些假消息力图对普通民众施加心理影响。淞沪警察厅严春畅厅长就通告市民:“近因时局不靖,粤来赤党,潜匿沪埠,散布谣言,刊行一种印刷品,雇用小贩,沿途喊售,伪称某处失守,某帅伤亡,考其实际,完全出于捏造,摇惑人心,莫此为甚,亟应严行查禁,以维治安。”因此他下令出动各警“对于前项印刷品,如某处战报,某报号外,以及传单、图画等项,一律禁止在华界喊售,并不准携入境内,以保公安”。(44) 《九江日报》因刊登有关东南联军的行动信息而被勒令停版。“孙传芳命印大批反赤示文,张贴各街,解释其地位。”(45) 此时,舆论界成为政治家们竞争政治权力时必须借助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将军事力量、政治宣传以及敌后的颠覆活动结合在了一起。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舆论的注意与谴责。《大公报》就指出:“时局混沌,各方消息歧出。因为大家都讲宣传,把真相隐蔽起来,反使人对任何方面报告,都带几分不敢相信。”(46) 以“赤化”与“反革命”这样一组罪名为例,由于“在北则不欲官场以外有消息”,“在南则不欲党的宣传而外有其他宣传”,以至“在讨赤军范围内而所载事实有不利于讨赤军者,辄以赤化目之。而同时在粤军范围内所载事实有不利于粤军者,则以反革命目之。甚至同一地点之同一报纸,当北军掌权,则受赤化之嫌;及南军到来,又蒙反革命之祸”(47)。另一篇社评对此则概括为“抗之于北者,犯讨赤之禁,违之于南者,触反革命之刑”(48)。这种相互抵牾的现象在北伐时期非常普遍。
至于“反赤”宣传的效果如何?这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奉、皖等系的“反赤”宣传一方面源于其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一旗帜的策略性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赤化”的拒斥,但这种宣传是否对奉、皖等系在军事战场上有所帮助,还需具体分析。
对于当时的许多军阀而言,他们大多出身草莽,在军事作战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在掌握思想动态方面相当欠缺。详解当时各系军阀的“反赤”宣传,充斥着“仁义”、“廉耻”、“孝悌”、“伦常”等充满浓厚道义色彩的词汇,与当时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渐行渐远,以至于许多社会舆论都不约而同将“南北”与“新旧”等同起来,从而使得北方军阀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49) 同时,北方军阀对“赤化”、“过激”思想与行为的防范又过于简单,只重硬性手段,如禁止思想的自由讨论,大力钳制言论,无法从理论上真正打击对手,因此遭致舆论界的严厉批评。
以直奉等为代表的北方军阀势力对于“赤化”的态度主要集于“反”与“讨”,只注意外部“反赤”,忽视内部“建设”,其自身缺乏能被社会广泛认同的理论与主张,这是其受舆论界广泛诟病之主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许仕廉指出,战争虽以“讨赤”为名,“实在建设的目的我们都不明白”。(50) 《大公报》批评反赤者“不宣布具体的政治主张,并禁智识阶级之自由讨论”(51),“尝察北方病根,只能号召反赤反共,而本身积极的无设施无表现,譬云反某某不好也,然则必有好者在,好者为何,未使国民见也”(52)。连一度倾向北方军阀的《晨报》也抨击道:“今之所谓讨共者,大抵只用外科手术,而忽略内部治疗。……内部治疗者,简言之,即首停战争,清明政治,废除苛税,增加生产而已。”(53)
宣传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宣传的对象所决定的。奉、皖等系军阀一方面在其所能掌管的报纸上进行“反赤化”宣传,另一方面主要是派出宣传队,利用演说、标语、漫画、游行等方式进行宣传,这些对于有一定识字能力的人确能产生一些影响,但对于广大底层民众而言,限于当时的教育水平与接受能力,很难起到真正的发动作用。
或许是认识到“讨赤”这一旗帜的缺陷,当1926年11月张作霖在天津会议上被北洋各派拥为“全国讨赤联合军总司令”时,其重要谋士杨宇霆认为“讨赤”两字范围太狭,建议改称“安国”,得到了与会各方的认可。《大公报》评论奉系“已视讨赤两字为有伸缩余地”(54)。《顺天时报》此时则直言,“讨赤”的口号已经不再适用,“奉张对于南方战事,依然以讨赤之标语一括之是也,……赤化之意义,暧昧空虚,吾人已迭论之。……而北方欲以讨赤一语,支配民心,岂非儿戏耶?”(55) 不过,“讨赤”的名义并未被完全放弃,仍时时见于日后的文电当中。
“反赤”一方的政治宣传越来越呈现名实不符的情况。奉、直等系只重“反赤”名义,不重研究事实,虽高举“反赤”旗帜,但所“反”之“赤”是否为“真赤”尚存疑问。《大公报》对此批评:“如北方骂赤化,最显著者为共妻共产一语,究竟广东国民党有无共妻共产一事,则不欲深考。”(56) 《京报》记者邵飘萍则认为,“赤化”从本质讲是“经济上之一种特殊制度”,而广州以及冯玉祥国民军的行为“不过最低调之整理地方主义”,并非“赤化”,因此,北方的“反赤”宣传并不成立。(57)
此外,奉、皖等系虽然大力进行“反赤”宣传,但对于“赤化”、“共产”的真正含义,社会上一直没有形成系统认识,陈独秀在1926年3月就曾指出:“此时所谓赤化、所谓反赤这些名词,在社会上很流行,几乎演剧上广告上都要用做材料以惹人注意;可是究竟什么是赤,大半还不甚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无意识的随声附和,或有意识的拿做攻击敌人之武器罢了。”(58) 同年8月,中共的刊物《中国青年》刊发了读者来信,指出社会上对于“赤化”的确切含义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59) 几乎在同一时期,《国闻周报》记者胡政之也描述到,当时国内虽然流行一种新标语,曰“打赤化”,但对赤化之含义则知者甚少,普通人心目中所了解者不过共产公妻之说。(60) 当时,多数人对“赤化”、“反赤”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表面而显得肤浅。虽然如此,这并不影响对“赤化”这一说法的使用,对于奉、皖等系军阀而言,“反赤”主要是一面“旗帜”,一种“名义”,“赤化”作为一项罪名已经成为杀人的利器,而对其真实含义的探讨已并非必要。
而且,在许多舆论者的眼中,“反赤”一方的政治宣传与其自身的行为出入越来越大,《大公报》就指出:“考其实际,彼据有名义之人,所作所为,固未尝有一次与名义相符。往往护法之人,亦即为破坏国内法纪之重要分子。其作恶殃民之程度,亦未必即不如所讨之贼,而唱道和平之人,更常为弄兵黩武之辈。至反赤名义,为近日最显赫之招牌。然其所谓赤者,固未必即诚属赤,而非赤之军队,其为害于人民,或且尤甚于被指为赤之师旅焉。”(61)
对于这种局面,《国闻周报》在北伐刚刚开始时即有预测:“从前尚可以借口于民意与法律而创造事实,今则事实赫然具在将欲比附名义。”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国人已经意识到,“事实问题,惟事实可以解决之”,“假迳名义”的行为已经失效。(62) 1927年7月,《大公报》发表社评,认为纯粹的宣传并不能起到效果,百姓需要的是“现钱现货”,即实际的利益,“空头支票,谁都不受”。至于将来,“不拘何派,非货真价实,断不能得国民之信仰,因为老百姓本身利害便是个试金石,他倒不管你是讨赤或反共,但有残民害众的行为,任你再会宣传,也不能长掩天下耳目”。(63)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时期的宣传战可以在短期内产生效果,但从较长的时间段看,效果有限,且危害长远。1927年年中,《大公报》评论:“近顷宣传之说盛行,虽偶尔收暂时之效,然流弊之中于国家社会与个人者迨不可以预测,此种利害,不可不辩。……滥用宣传之结果,不特于事实无裨,反致误人误己。”(64) 到了这年年底,《大公报》的社评指出:“空头支票,信用早亡,虚伪宣传,徒增厌恶。”(65) 随着北伐的临近结束,《大公报》指出,不仅北方的“反赤”口号,而且包括南方的“革命”宣传,两者都开始逐渐失去效力:“而自国民一般言,变迁尤甚。昔仅憧憬空名,今则必问实际。是以革命美名,不必遽能助人,而讨赤空言,亦难充分号召。所以然者,人民之实在需要,为法治与民主,苟背于斯,皆所反对。”(66) 此时,政治宣传的本质已经逐渐为社会所认识。
五
北伐战争与以往的军阀混战相比,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军事争夺中渗入了更多的政治元素,交战各方不再如以往那样赤裸裸地争权夺利,而是将自身的行动赋予鲜明的政治色彩,纷纷标举各种“旗帜”或“主义”,从而确立“合法性”与“正当性”。国共合作状态下的国民革命军高举“反帝”、“反军阀”等旗帜,通过在军队中设置政工人员,宣传自身的“主义”。而通常被视为比较落后的以奉、皖、直等系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也不甘其后,顺应时代潮流,以“反赤”的名义,一方面应对南方的政治宣传,一方面为自身的军事政治行动正名。
概言之,北伐前后的“反赤”声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奉、皖等系军阀以“反赤”名义所进行的军事讨伐,另一种主要以章太炎以及国家主义者为代表的知识阶级的“反赤”思想。(67) 知识阶级的“反赤”言论更多源于与“赤化”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冲突,主要是基于一种学理上对“赤化”的排拒。因此,他们是从理论体系上对“赤化”现象给予剖析,从一党专政、阶级革命等角度探讨“赤化”的重要特征,阐述中国不能实行“赤化”的理由。(68) 而奉、皖等系军阀的“反赤”虽也有双方理念上的冲突,但更多的是借“反赤”做政治招牌,是对这一旗号的策略性运用,其主要是使用通俗、浅显的语言宣传“赤化”的社会危害,基本限于社会普及层面,缺乏学理上的阐释与支撑。《时事新报》即将“反赤”势力分为“政客之反共产派”和“学者之反共产派”,并指出前者纯为自身利害关系,后者“太偏于学理上的争辩”。(69)
同时,军阀将“反赤”的重点放在“反”与“讨”上,自身军队的政治建设极其失败,“反赤”只重名义,不重事实,其有效性常常受到质疑,具体的方式也遭致社会舆论的普遍批评。此外,“反赤”行为本身也对当时的社会以及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有舆论甚至称“赤化”的根源正在于“反赤”战事,“反赤”的危害已大于“赤化”本身。加之各派军阀之间利害关系复杂,无法采取统一的行动,可以说“反赤”旗帜从其树立之日起,就有其自身所难以克服的困境与难局。
注释: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台北,《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李云汉:《北伐史的面面观》,载《近代中国》(台北),第113期,1996年6月;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3)。
② 政之:《宣传战与外交战》,载《国闻周报》,第2卷,第23期,1925-06-21。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向导》,第155期,1926-05-30。
④ 《李景林讨冯通电》,载《时报》,1925-12-05,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第319—320页,武汉出版社,1991。
⑤ 后来,《大公报》也指出:“溯讨赤之称,倡自李景林。”见《“不见棺材不落泪”》,载《大公报》,1927-06-14。
⑥ 孟星魁:《直系军阀大联合的酝酿和失败经过》,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99—10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⑦ 《申报》,1926-04-28。
⑧ 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18页,第8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⑨ 《申报》,1926-05-12。
⑩ 《军警严查赤化》,载《申报》,1926-09-03。
(11) 《靳云鹏赞扬王怀庆办法》,载《申报》,1926-05-13。
(12) 《申报》,1926-05-25。
(13) 《申报》,1926-04-22。
(14) 《申报》,1926-05-10。
(15) 《申报》,1926-04-29。
(16) 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载《晨报副刊》,1926-10-05。
(17) 《张作霖发表讨赤宣言》,载《晨报》,1926-12-08。
(18) 政之:《北京改制记》,载《国闻周报》第4卷,第24期,1927-06-26。
(19) 李璜:《学纯室回忆录》,第2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20) 《张慰慈致胡适》(1927年1月16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1) 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9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22) 《孙军宣传部之和平宣传》,载《大公报》,1926-10-14。
(23) 天马:《孙蒋战事前途之推测》,载《大公报》,1926-10-03。
(24) 《宣传与革命》,载《大公报》,1927-06-13。
(25) 遵严:《讨赤宣传》,载《新申报》,1927-01-23。
(26) 《坚壁清野》,载《大公报》,1926-11-26。
(27) 《孙传芳与租界当局接洽,共同取缔赤化运动》,载《申报》,1925-12-21。
(28) 《孙传芳查禁赤党书籍》,载《申报》,1926-06-02。
(29) 《申报》,1926-08-13。
(30) 《东南时局感言》,载《国闻周报》,1926-11-04。
(31) 《警厅严防粤来青年党》,载《申报》,1926-08-21。
(32) 《反赤宣传队》,载《晨报》,1926-10-01。
(33) 《孙传芳亦注意宣传》,载《晨报》,1927-02-01。
(34) 《法捕房严查共产党》,载《申报》,1926-09-03。
(35) 《党联军激战中之宁垣》,载《晨报》,1926-10-04。
(36) 《鲁军已动员南下》,载《申报》,1926-11-27。
(37) 《鲁军南下续志》,载《申报》,1926-11-28。
(38) 雄:《纪郑州反赤游行》,载《大公报》,1927-04-22。
(39) 《申报》,1926-07-16。
(40) 遵严:《讨赤宣传》,载《新申报》,1927-01-23。
(41) 《直鲁联军宣讲队之标语》,载《新申报》,1927-01-17。以上三段来自《新申报》的材料都转引自王奇生《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3)。王文以北伐时期南北两方的宣传漫画为例,探讨了这一时期双方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另一条战线的角力,对本文多有启发。
(42) 《孙总司令之防赤布告》,载《申报》,1926-09-10。
(43) 《共产党残暴的心理》,载《晨报》,1928-02-16。
(44) 《申报》,1926-09-05。
(45) 《申报》,1926-09-19。
(46) 《假定下之一种时局判断》,载《大公报》,1927-07-28。
(47) 以上两段均引自《赤化与反革命》,载《大公报》,1926-09-17。
(48) 《天津与上海之预言》,载《大公报》,1927-04-27。
(49) 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载《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要舆论对于北方的失望并不必然转化为对于南方的支持,而且这种舆论中认知的所谓“新”与“旧”也并不必然转化为胜利与失败。
(50) 许仕廉:《四论武力与吴张会议》,载《晨报副镌》,1926-07-06。
(51) 《时局杂感》,载《大公报》,1926-09-12。
(52) 《时局杂感》,载《大公报》,1927-04-17。
(53) 《中国之癌》,载《晨报》,1928-01-17。
(54) 《妥协欤战争欤?》,载《大公报》,1927-02-02。
(55) 《顺天时报》,1927-02-10。
(56) 《赤化与反革命》,载《大公报》,1926-09-17。
(57) 飘萍:《中国今后之趋势》,载《京报》,1926-02-18。
(58) 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载《向导》,第146期,1926-03-17。
(59) 这位读者如此解释其之所以有这种想法的原因:“因为名词的好坏,无关事实,只要是他的主义对,不管他是甚么样子的名词,也要加入队伍,同心协力帮他成功;那么反过来说,他的主义不对呢,也不管他的名词怎么样天花乱坠的好听也只有掩耳朵跑罢了。至于更进一层的各主义信仰的目下安危关系,更不曾计较的了。”参见《读济之先生的我们怕“赤化”吗?》,载《中国青年》,第131、132期,1926-08-31。
(60) 政之:《国民之两种恐怖心理》,载《国闻周报》,第3卷,第36期,1926-09-19。
(61) 子宽:《还是假借名义》,载《国闻周报》,第3卷,15期,1926-04-25。
(62) 政之:《事实问题惟事实可以解决之》,载《国闻周报》,第3卷,第24期,1926-06-27。
(63) 《混沌与变化》,载《大公报》,1927-07-24。
(64) 《宣传与革命》,载《大公报》,1927-06-13。
(65) 《赈灾与造灾》,载《大公报》,1927-12-17。
(66) 《南北统一纪念日》,载《大公报》,1928-02-12。
(67) 陈独秀就指出当时中国主张“反赤”的有两种人:一是军阀中之反动派,如奉系之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粤系之陈炯明、魏邦平等;一是知识者及政客中之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安福派、中和党及老民党分子章太炎、冯自由、马素等(陈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载《向导》,第146期,1926-03-17)。
(68) 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可参考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载《历史研究》,1997(6)。
(69) 张镜予:《赤色帝国主义与中国》,载《时事新报》,1925-10-02。
标签:孙传芳论文; 奉系军阀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大公报论文; 申报论文; 新青年论文; 北伐论文; 九·一八事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