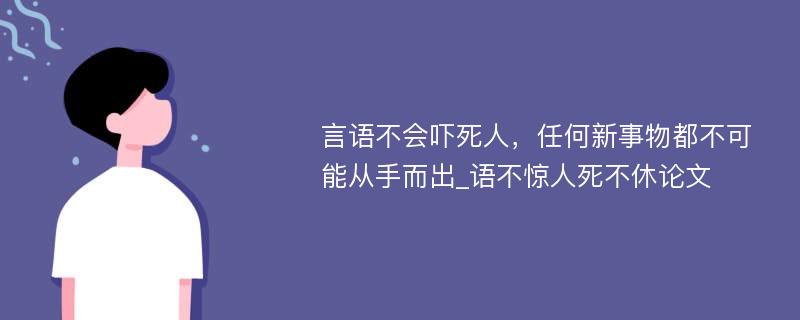
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不惊人死不休论文,新意论文,出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在您的青少年时期,我国曾有一个相对贫穷、动荡的年代,请给我们讲述几个您那段时期课余时间读书的故事。
梁:那个时期的书籍、报刊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我虽生长在一个干部家庭里,但还是没有多少钱买书。我印象最深的是趴在书店柜台前读书,那个时候书店的服务态度非常好,你可以看一天,不买一本书。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柜台的服务员就像一个善良的农家妇女,看着一群麻雀吃她院里的麦子,却也不管”。我在这个书店柜台读久了,终于用零花钱买了我平生买的第一本书——秦牧的《艺海拾贝》。这算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可说的,是向邻居借书。我的邻居是一个“小作家”,现在想来他的书也不多,只有一个普通书架,但我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我从小学开始在他那里借书,一直到初中毕业,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的书,还有一些文学理论书,都是在那里看的。后来我也成了作家,已经五十来岁了,在公众场合还是叫他“叔叔”,他很高兴,还为我的作品写过评论。
第三个故事,是我如何从追求文采而转入追求思想的。有一次上历史课,课本上有影印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章,我不好好听课,却去辨认芝麻大的影印字,有这样一段我至今还能记得:“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突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这一段十分生动的文字,一下子吸引了我,便回到家里找到父亲的“毛选”,想不到这就是我读政治书籍的开始。这件事情对我以后影响很大。我一直认为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章一定要写得文采飞扬,才有人读,这也是我后来坚持写作政治美文的原因。
第四个故事是在乡下读书。1968年底,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先在农村劳动,很少能够找到可读的书。当时有北京知青是军队干部子弟,带来一大包军史、战史方面的书,使我大饱眼福。从此养成了读军事书的习惯。还有一次,在农家的一个灶台上,看到一本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已被烧掉了几页,我拿回去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后来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文革后,我很快又买到了它的再版本,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第五个故事,不是读书而是有关读报的。我的业余知识,特别是文学知识,可以说一多半是来源于报纸的副刊。那时候,家里订有一份《人民日报》,大人看新闻,我每天必读的是第八版的副刊。后来我刚参加工作时,在宣传部新闻处工作,正是粉碎“四人帮”前,社会上还是没有什么书可看。机关里订有全国各地的报纸,每天报纸一到,我就把所有的副刊找来读一遍,并且还分门别类剪贴了许多本。这也影响了我以后的写作,我以后发表的几篇成名作品,如《晋祠》《跨越百年的美丽》《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红毛线、蓝毛线》等都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前两篇还选入了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教材。
记:您认为哪些书对您青少年时期的影响最大?是否有些书今天已经有点过时了?
梁:我青少年时期读的古今小说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志向影响巨大,像《水浒》《林海雪原》《红旗谱》等这些除暴安民的英雄主义,以及描写我们党的地下工作、基层工作的一批小说,所宣传的牺牲精神,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都深深地影响了我。这对后来我当记者,表现出的注重基层,联系实际,为老百姓说话以及报效国家的志向,还有当领导后,始终保持的平民意识,都很有关系。对我的感情培养影响较大的是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当时郭小川、贺敬之的诗,还有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朗诵诗选》《革命烈士诗抄》等,都给予我旺盛的激情,一批优秀的古典诗歌像唐诗宋词也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写诗。对我的写作影响较大的还有年轻时背了一大批古今散文的名篇,特别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朱自清、徐志摩等人的文章。古文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史记》。我一直认为,有志写作的人,乘少年时要多背一点名篇,这将受益无穷。我直到大学毕业后当记者,在外采访时书包里还装一本可背的书。现代作家杨朔、魏巍长达三五千字的文章,我都背过。我认为青少年志气的养成与读好小说有关,因为小说里有人物形象,那是一种偶像;情感的培养不能不读诗,不懂诗,甚至可以说没有写过诗的人,性格是不健全的;文采的训练一定要背一些散文名篇,文章作法不靠肚子里装很多模式,是无法自创出新的。有一些小说,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有兴趣再去读了;当时曾经激动人心的一些诗歌,也很难再激动现在的年轻人。时代呼唤着新作品的出现。但能够经过历史考验,有思想艺术价值的名篇将永远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记:有人说,文学作品是“写”出来的,而不是“读”出来的,那么,您认为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哪个对写作更重要?
梁:我认为前者更重要。学生刚开始写作,主要靠的是丰富的知识。古人讲“读书破万卷”,我们以短暂的人生所体验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前人的知识积累,古代许多大文人、大诗人的作品,明显地接受了前人的传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创出了新高度的。甚至许多文人的生活圈子就是书房,但作品也很有名。王勃才二十多岁就死了,能有多少生活体验,但《滕王阁序》写得多好。读书本身就能增加人生体验。作为学生和刚从事创作的青年人,首先要把书读够,打好知识积累的根基,然后加上自己的体验,才可能有所成就。
记:如果让你年轻四十岁,回到宝贵的青少年时期,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梁:我最想做的是:一是把外语学好。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外语成了起码的交流和治学工具。在我的文学知识中,外国文学这一块就相对弱一点。二是把古代史学好。虽然曾读了许多古文,但是很多经典,都没来得及通读,特别是几部通史,应该补上这一课,这对整个学术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三是有时间一定要练一下书法。我后来长期当记者,常在炕头地边采访,在采访本上写字只图快,把字都写坏了,看到别人漂亮的书法,总有一点遗憾。
记: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都有人推荐,也都有人称其为“经典”,你心目中的“经典”是什么?
梁:我认为:一、中国的四部古典小说要读。二、唐诗宋词要读,特别是其中爱国主义的篇章,如陆游、辛弃疾的作品。三、《史记》《古文观止》,明清笔记要读,如《浮生六记》、张岱等人的小品。四、上世纪30年代鲁迅的文章、朱自清的散文要读。社会上关于散文的选本很多,可以选一些来。比如我用得最顺手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古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散文》。今人小说和诗歌,我一时还开不出单子。
记:有的同学刚开始写作文。就一写几万字。被称为“少年作家”,还有的同学是每次只能写几百字,当时你属于哪一种?
梁:当时我属于后一种。就是现在我的写作也不算高产。一般来说一年只写一篇分量稍重点的散文,有时一篇文章要构思写作好多年。比如现在选人高中课本的《觅渡,觅渡,渡何处》,前后写了6年;《大无大有周恩来》从积累到写作20年。我是主张写作一定要求精,我的座右铭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所谓少年作家一写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一般来讲不可取,对以后的成长未必是好事。
2002年11月25日
链接阅读
壶口瀑布
壶口在晋陕两省边境上,我曾两次到过那里。
第一次是雨季,临出发时有人告诫:“这个时节看壶口最危险,千万不要到河滩里去,赶巧上游下雨,一个洪峰下来,根本来不及上岸。”果然,车还在半山腰就听见涛声隐隐如雷,河谷里雾气弥漫,我们大着胆子下到滩里,那河就像一锅正沸着的水。壶口瀑布不是从高处落下,让人们仰观垂空的水幕,而是由平地向更低的沟里跌去,人们只能俯视被急急吸去的水流。其时,正是雨季,那沟已被灌得浪沫横溢,但上面的水还是一股劲地冲进去,冲进去……我在雾中想寻找想象中的飞瀑,但水浸沟岸,雾罩乱石,除了扑面而来的水汽,震耳欲聋的涛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个可怕的警觉:仿佛突然就要出现一个洪峰将我们吞没。于是,只急慌慌地扫了几眼,我便匆匆逃离,到了岸上回望那团白烟,心还在不住地跳……
第二次我专选了个枯水季节。春寒刚过,山还未青,谷底显得异常开阔。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到沟底,这时的黄河像是一张极大的石床,上面铺了一层软软的细沙,踏上去坚实而又松软。我一直走到河心,原来河心还有一条河,是突然回下去的一条深沟,当地人叫“龙槽”,槽头入水处深不可测,这便是“壶口”。我依在一块大石头上向上游看去,这龙槽顶着宽宽的河面,正好形成一个丁字。河水从五百米宽的河道上排排涌来,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拥,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山是青冷的灰,天是寂寂的蓝,宇宙间仿佛只有这水的存在。当河水正这般畅畅快快地驰骋着时,突然脚下出现一条四十多米宽的深沟,它们还来不及想一下,便一齐跌了进去,更涌、更挤、更急。沟底飞转着一个个漩涡,当地人说,曾有一头黑猪掉进去,再漂上来时,浑身的毛竟被拔得一根不剩。我听了不觉打了个寒噤。
黄河在这里由宽而窄,由高到低,只见那平坦如席的大水像是被一个无形的大洞吸着,顿然拢成一束,向龙槽里隆隆冲去,先跌在石上,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一川大水硬是这样被跌得粉碎,碎成点,碎成雾。从沟底升起一道彩虹,横跨龙槽,穿过雾霭,消失在远山青色的背景中。当然这么窄的壶口一时容不下这么多的水,于是洪流便向两边涌去,沿着龙槽的边沿轰然而下,平平的,大大的,浑厚庄重如一卷飞毯从空抖落。不,简直如一卷钢板出轧,的确有那种凝重,那种猛烈。尽管这样,壶口还是不能尽收这一川黄浪,于是又有一些各自夺路而走的,乘隙而进的,折返迂回的,他们在龙槽两边的滩壁上散开来,或钻石觅缝,汩汩如泉;或淌过石板,潺潺成溪;或被夹在石间,哀哀打漩。还有那顺壁挂下的,亮晶晶的如丝如缕……而这一切都隐在湿漉漉的水雾中,罩在七色彩虹中,像一曲交响乐,一幅写意画。我突然陷入沉思,眼前这个小小的壶口,怎么一下子集纳了海、河、瀑、泉、雾所有水的形态,兼容了喜、怒、哀、怨、愁人的各种感情。造物者难道是要在这壶口中浓缩一个世界吗?
看罢水,我再细观脚下的石。这些如钢似铁的顽物竟被水凿得窟窟窍窍,如蜂窝杂陈,更有一些地方被漩出一个个光溜溜的大坑,而整个龙槽就是这样被水齐齐地切下去,切出一道深沟。人常以柔情比水,但至柔至和的水一旦被压迫竟会这样怒不可遏。原来这柔和之中只有宽厚绝无软弱,当她忍耐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力相较,奋力抗争。据徐霞客游记中所载,当年壶口的位置还在这下游一千五百米处。你看,日夜不止,这柔和的水硬将铁硬的石寸寸地剁去。
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挟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正像一个人,经了许多磨难便有了自己的个性;黄河被两岸的山,地下的石逼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也就铸成了自己伟大的性格。这伟大只在冲过壶口的一刹那才闪现出来被我们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