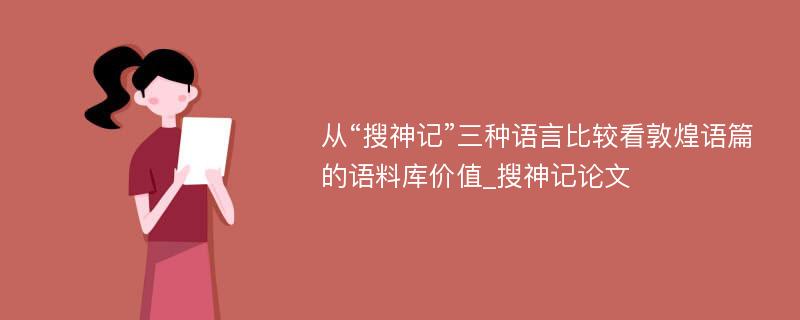
从三种《搜神记》的语言比较看敦煌本的语料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语料论文,三种论文,语言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4)04-0045-07
一
《搜神记》目前可以看到四种本子,即二十卷本、八卷本(《稗海》本)、敦煌本(简称“敦煌本”)、一卷本(《无一是斋丛钞》、《魏晋百家小说丛钞》所收)。据考,一卷本是选自稗海本和二十卷本的刻本,所以我们用以比较的本子选取前三个(以下标示出处时分别简称“廿”、“八”和“句”,(注:本文采用的各本《搜神记》的版本:二十卷本,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敦煌本,句道兴撰《搜神记》,收入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八卷本,即《稗海》本,收入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附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敦煌文献《搜神记》残卷S.525、S.2022、S.2072、P.2656、P.5545。))。关于这三种《搜神记》的成书时代及其彼此间的关系,前修时贤已有较深入的论述。鲁迅[1]、余嘉锡[2]、范宁[3]、张锡厚[4]、江蓝生[5]、汪维辉[6][7]、李建国[8]等都已论及(注:鲁迅(参考文献[1])认为,二十卷本搜神记“亦非本书”,“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余嘉锡(参考文献[2]):“余谓此书(二十卷本,引者按)似出后人缀辑,但十之八九出于干宝原书。”范宁(参考文献[3])认为,二十卷本已经不是干宝原书,也不是传世古本,很可能是明代胡元瑞辑录的。八卷本是后人误提或嫁名作伪,实非干宝所作。张锡厚(参考文献[4])认为,敦煌本是五代时期至迟也是北宋初年的手抄写本,比较接近干宝原作,因而敦煌本的发现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他还推测敦煌本的产生过程:“敦煌本并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有它的渊源所在,极有可能是从干宝《搜神记》原书中择其所需,选编成册,才题曰‘句道兴撰《搜神记》一卷’。”总之,张文认为敦煌本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高于二十卷本和八卷本。张文引述:日本的内田道夫先生认为敦煌本、八卷本、二十卷本可能出自同一古本,敦煌本是由古本派生出来的民众写本,有很强的通俗性。江蓝生(参考文献[5])认为,八卷本《搜神记》在语言上有很多反映唐五代以后特点的现象,肯定不是晋干宝所作,有可能出自晚唐五代或北宋人之手。江先生还说:“这三种本子的《搜神记》事实上是两个系统:二十卷本是一个系统,敦煌本和八卷本内容相近,说明八卷本自有所本,是另一系统。”从语言史的角度看,二十卷本文句古朴,与魏晋六朝时期的文献基本一致;敦煌本、八卷本具有早期白话的一些特点,其原书出世要远远晚于干宝原书。“分属两个系统的《搜神记》,内容不同,语言的历史层次也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八卷本应比敦煌本晚出”。敦煌本“很有可能就是唐五代时期的作品”。汪维辉(参考文献[6]、[7])在江先生的基础上补证:八卷本《搜神记》绝不可能是晋代干宝所作,应该成书于北宋。李建国(参考文献[8])认为,二十卷本是个很不可靠的辑录本,八卷本肯定是宋以后人杂采包括《搜神记》在内的诸书编纂而成的。至于八卷本和敦煌本的关系李先生基本同意内田道夫的意见,八卷本比敦煌本晚出。他说:“句道兴是唐初下层文人,他可能出于对干宝《搜神记》的仰慕,故而也纂集一本《搜神记》。此书以抄本流行于民间和寺院,而且流传很广,所以在敦煌文献中有多个写本。它虽然发现于敦煌,但实际并未消失,大约在宋代有佛徒对此书的某一种已经残缺的写本进行增订补缀,这便是八卷本了。”)。综合各家论述可以得出四点:1.三种本子的《搜神记》皆非干宝原书。2.三种本子出书的确切年代尚难确知。二十卷本可能是明代的辑本,敦煌本应该是唐代的手抄写本,由唐代下层文人句道兴编撰,八卷本是北宋乃至宋以后的编纂本。3.三个本子是否属于一个系统,尚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同出于一个古本;另一种意见认为,属于两个系统,即二十卷本是一个系统,八卷本和敦煌本是另一个系统。4.敦煌本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很高。关于1、2,学界的意见比较一致,特别是八卷本成书的大致时代,江蓝生先生和汪维辉先生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关于3,目前人们的意见还不一致,三本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还需深入讨论。关于4,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敦煌本的语料价值方面的成果还不多。从语言的角度论及敦煌本《搜神记》的看法散见于内田道夫[9]、洪诚[10]、张锡厚[4]、江蓝生[5]等人的文章(注:内田道夫说:“句道兴撰的《搜神记》和其他本相比较,有很强的通俗性。”(据张锡厚转引)洪诚(参考文献[10])说:“今存《汉魏丛书》本《搜神记》内容与句道兴的《搜神记》只要是同有的故事,情节都是相同的,文句有文言与白话之异。疑句道兴所据乃是隋唐志所著录的原书。”江蓝生(参考文献[5])说:“从语言上看,敦煌本文字风格比较一致。”“敦煌本、八卷本具有早期白话的一些特点”。),但都未见作具体而深入的分析。由于敦煌本《搜神记》是《搜神记》各本中现在所能见到的出书时代最早的古AI写作本,所以对这个本子的语言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以便能更好地利用这份珍贵的语料。上述三种本子的《搜神记》交叉互同的条目本事基本相同,但行文语言常有差别。我们拟从这些条目中选取相关语句,在其要表达的语意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词汇、语法的比较,以便认识敦煌本《搜神记》的语料价值。
我们统计出三种《搜神记》交叉互同(“同”指本事或故事同)的条目,分类列表于下。表中第一类为廿、句同而不见于八的3条;第二类为廿、八同而不见于句的4条;第三类为句、八同而不见于廿的8条;第四类为三本互同的7条。表中的数字为各本所收条目的序号(注:二十卷本共464条,敦煌本共35条(原未编号),八卷本共40条。由表可见,二十卷本与敦煌本同10条,二十卷本与八卷本同11条,敦煌本与八卷本同15条。张锡厚将二十卷本后附的佚文“丁兰”条与敦煌本的丁兰事视同计入,得11条,我们不计入;将二十卷本的“狗”与八卷本的张司空事视同计入,得12条,我们发现两条之间本事几无相同之处,因此不计入。)。下面依类举例进行比较分析。
二十卷本敦煌本八卷本
第
354 23
一
283 25
类28 27
第
341 15
二
415 16
类
421 17
380 20
第54
76
三85
132
类
159
1811
2114
22 8
280 1 28
第54 6 1
395 9 3
四
359 1610
447 1913
类
457 2029
453 3412
二
这一节分析第一类和第二类。
先看第一类。二十卷本第28条和敦煌本第27条同记董永事,但词汇、语法等语言情况有较大的差别:二十卷本使用单音词,敦煌本往往使用双音词;二十卷本不用介词处,敦煌本用;二十卷本判断句不用判断词“是”,而敦煌本用。如:
1.父亡,无以葬。(廿,28)
2.其父亡殁,无物以葬送。(句,27)
3.鹿车载自随。(廿,28)
4.与鹿车推父於田头树荫下与人客作。(句,27)
5.我,天之织女也。(廿,28)
6.我是天女。(句,27)
另两条也有相似之处。表意意图基本相同,而两本的词汇选择乃至句法选择有别。如:
7.乃於野凿地,欲埋儿。(廿,283)
8.巨身掘地,拟欲埋之。(句,25)
9.匍匐往(廿,354)
10.匍匐而前往(句,23)
11.衣而飞去。(廿,354)
12.其天女著衣讫,即腾空从屋窗而出。(句,23)
廿本的7、9、11中加点词的使用及句法构造与上古逼似。敦煌本“拟欲”、“前往”、“著衣”的使用使两本之间的语言差别画然。特别是11的“衣而飞去”的连动短语在12中变成了各以两个动词为重心的小句。这些说明了两个时期的说话人的语言有了较大的差别。敦煌本的语言比二十卷本通俗,大致反映了唐代的口语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再看第二类。经过这一类的语言比较,我们发现,八卷本和二十卷本关系很密,一些条目本事虽差不多,但人名地名有别,一些细节的描述此详彼略。如廿第341条与八第15条同记盘瓠事,第341条说“戎吴强盛,数侵边境”,第15条说“有房王作乱”。第341条仅记“后盘瓠衔得一头”,而第15条从失犬到犬走投房王,取得房王信任伺机咬得王首,共敷衍出76字。似可看出两本都参考了古本《搜神记》,只是成书时加工的程度不同而致相异。然而因八卷本可能是文人的编辑之作,语言上未必比接近干宝原书的二十卷本通俗。如:
13.“盘瓠咬王首而还”(八,15)
14.“后盘瓠衔得一头”(廿,341)
头部义的“首”在上古占绝对优势,用“头”则很少见。至中古“头”的使用渐渐多起来,在口语性比较强的文本中渐渐占有优势,当然在史书等较书面的文本中“首”的使用仍占有优势。如《三国志》中“首”的出现频率大约是“头”的两倍,但在二十卷本《搜神记》中“头”已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出现次数约为“首”的5倍,八卷本“头”也占有优势,但出现次数大约只为“首”的两倍。
这一类中,值得提出的是廿第421条和八第17条,自“孔章曰”以下两本几乎全同,只有个别词句小异。汪绍楹先生已经指出,这是明人在纂辑二十卷本时掺入了八卷本的内容,“应该移正”。两条中不同部分所叙述的情节差距很大,语言方面几乎没有比较点,我们仅检得一对例子似可比勘:
15.张司空之才难可比也,若去,非但丧汝二躯,我亦遭累。(八,17)
16.但张公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廿,421)
从这一对例子似乎可以看出,两本在语体上比较接近,难以看出孰俗孰雅,但语气上略有差别,16比15略显委婉,如用“智度”不用“才难可比”,用“子”不用“汝”,用“老表”(“老表”为墓前华表的自称)不用“我”,这些似乎透出了一点明代文人对此条进行精工制作的一些消息。
经过以上三本交叉互同共7条的语言比较,可以初步看出,八卷本一些条目的语言未必比二十卷本更通俗,而敦煌本的通俗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用以比较的样本还是太少,得出的结论未必允当,下面将重点比较第三类和第四类。
三
本节分析第三类。我们这一类8个条目中选取了语意最接近的语句进行比勘,发现敦煌本无论在词汇还是语法上都比八卷本更有口语风格。如:
17.广于后更闻刘安曰:“是何灾异也?”曰:“无他,公堂舍西头壁下深三尺有三个石龙。今日灾祸已过,慎莫发看,发看必令人贫矣。若不发看,后克富贵,此是神龙也。”而广不用刘安之言,遂发看之。有一赤物,大如屋椽,冲突出去上天,其后广家大贫困。(句,5)
18.重问:“此灾何有?”安曰:“堂屋西壁下深三尺,当有三个石柱。今灾已过,慎勿发看。若视之,必大贫。若不看,必大富贵。此神龙也。”后广不依,即掘看之,验其虚实。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飞出他去。后广大贫,一如其言也。(八,4)
17中的“是何灾异也”与18中的“此灾何有?”相比,后者更有书面语风格。“西头”是新兴的方位结构,而18不用。表禁止的副词“莫”也比“勿”后起。“此是神龙也”与“此神龙也”,前者当然后起。
19.不经旬日,秦缓到来,遂与景公候脉,良久,语景公曰:“病不可治也……”(句,7)
20.旬日医至,察其容,候其脉,良久叹曰:“此病不可疗也……”(八,6)
“到来”与“至”、“与景公候脉”和“候其脉”、“治”与“疗”都是前者更接近口语。“治疗”之意上古用“疗”而不用“治”,“治理”意的“治”至中古发展出了“治疗”的新义。如《风俗通义·石贤士神》:“石人能治病,愈来者谢之”,《论衡·率性》:“古贵良医者,能知笃剧之病所以生起,而以针药治而已之。”敦煌本表现出于这个新发展,而八卷本存古。
21.女父母路还家,迎丧灵还家坟葬。
在冢中发出棺木,里得金钗无数,并金铤、绢两匹。其父母惊愕怪之。(句,13)
22.其父母发取女尸于祖父茔内安葬,开冢出棺改敛,见铜钱无数,并有金钗子一只、金镊子一枚、细绢二匹,甚异之。(八,2,(注:八卷本第2条与敦煌本第13条本事相同,但敦煌本残缺而八卷本文本整饬,前后照应颇有章法,显系后人据事改编而成。语言风格上确如江蓝生先生所言,敦煌本文风比较一致,而八卷本文白夹杂。))
“发出”这种动补结构应是中古新兴的语法现象,22中“出”的用法自上古而然,仍然是对上古这种带有方向性的动词的沿用。
23.雍州刺史梁元纬以帝连婚,倚恃形势,见真马好,遂索真马。真曰:“此马已老不堪,又是父所乘之马,不忍舍离,不敢辄奉使君。”赐厅而坐。纬恨嫌,即私遣人言道真取物,付狱禁身,不听家人往看。(句,15)
24.雍州刺史梁纬,与帝连婚,时恃形势,见孝直马好,每索之。直答云:“亡考所乘之马,不忍舍之,不敢辄奉,伏愿使君照悉。”粱纬因此致恨,密构孝直取受赃事,乃教下狱,不令家人通往。(八,9,(注:八卷本此条文句典雅,尤其段孝直在殿前所读表文,乃属精心制作。此条与敦煌本本事全同,而文句雅俗之别判然。说明虽是晚出之作,但语料价值并不高。))
“父”与“亡考”二词语体上的差别甚明。允许义动词“听”在上古典籍中少见,中古常见,而“令”在上古常见,所以敦煌本“听”之“允许、听凭、让”的意义应该反映了语言发展中语义引申偏移的现象,因而反映语言的变化比八卷本快。
25.刺史今为此马,欲杀我,恨汝等幼小,未解官府,汝等但买细好纸三百张,笔五管,墨十挺,埋我之时著于我前头,我自申论。(句,15)
26.刺史阴谋欲夺我马,私捏人诉,意欲杀我,必死矣。嗟汝等幼冲,未解申雪。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将取纸三百张,笔十管,墨五挺,安我墓里,我自申理。(八,9)
安放义的“著”似是中古产生的,而“安”则自上古沿用至今。26用“安”而不用“著”,说明八卷本的编辑者使用的文字比较典雅。“前头”与“墓里”这两个方位结构相比,前者更加后起。《齐民要术》中“N里”这种结构已经很多,如“粟初熟出壳,即于屋里埋着湿土中”(种粟第38),而“N头”这种典型格式尚未见到。即使有类似的搭配,其中“头”仍有实义,如“以肉薄之,空下头,令手捉,炙之”(炙法第80)中的“头”此处仍指竹筒的端部,“下头”即下边那一端。可以看出,敦煌本反映的语言现象较新。
敦煌本和八卷本中还很多类似的例证,我们选取一些附在附注中(注:王知之大怒曰:“我是万乘之主,纵枉杀三五人,有何罪过?”遂杀之。(句,18)王曰:“我是万乘君王,枉杀三五个之类,何有患乎?”乃戮之。(八,11)/见杜伯前后侍从鬼兵队仗,乘赤马,朱衣(8)笼冠,赫奕,手执弓箭,当路向王射之。(句,18)忽见杜伯著朱衣,乘白马,冠盖,前后鬼兵数百,当道而来,弯弓执矢射王。(八,11)/(李信)夜中梦见伺命鬼来取,将信向阎罗王前过。(句,21)(李信)忽夜梦司命使鬼使取信至阎罗王殿前。(八,14)/信即烦恼,语其妻曰:“卿识我语声否?”(句,21)(李信)悲啼懊恼,语其妻曰:“如识我语音否?”(八,14)/其妻即依夫语,捉被覆之而去。(句,21)其妻依言,以被覆之。(八,14)/先生是陈留信义人也。(句,22)孝先,陈留信义人也。(八,8)/有一鬼变作生人。(句,22)续有一鬼,化为生人。(八,8)/言未绝之间,其人即来。玄即指示子珍,“此人是也,宜好射之。我须向衙头判事去,不得在此久住,他人怪我。”(句,22)言语之间,其冤家果至。玄石目曰:“是此矣,宜审射之。我须入衙决判事,在此他人有疑。”(八,8)/珍答曰:“父母以珍学问浅薄,故遣我向定州边先生处入学,更无余事。”(句,22)子珍曰:“父母以子珍寡学,遣於定州边孝先先生处学业,余无事。”(八,8)/其家大小闻哭声,并悉惊怖,一时走出往看。(句,5)广家中大小,一时走出,惊怕看之。(八,4)/太守不知是鬼,乃问之曰:“女能作衣以否,我家雇作衣。”女子曰:“善能作衣也。”(句,13)子元不疑是鬼,又问曰:“既无依倚,还善制衣否?”女子对:“善制衣。”(八,2)),以供参考。
四
这一节分析第四类。我们选取了三种《搜神记》中语意最接近的语句进行比勘,经过词汇和语法的比较更加清楚地显示出八卷本与二十卷本的语言比较接近,语言比较文,而与敦煌本的通俗有不小的距离。如:
27.乃取笔挑上,语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颜拜而回。(廿,54)
28.乃取笔挑上。颜顾,喜之。乃语颜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颜闻而喜不自胜,拜而回家。(八,1)
29.把笔颠倒句著,语颜子曰:“你合寿年十九即死,今放你九十合终也。”……回到家,见管辂。(句,6)
27和28都用拿取义动词“取”,而29用“把”。“取”的用法上古多用,“把”则很少见,偶见使用也只是“握”义,如“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孟子·告子章句上》)。27和28的“挑上”的“上”有实义,指“上面”;29的“句著”的“著”明显有虚化为表完成的体标记的趋势,29中的“回到家”中的“到”已经是典型的补语,而27、28只用“回”隐含了这种语法意义。特别是前二例用“汝”,第三例用“你”,明显表示出敦煌本反映了唐代第二人称代词的基本情况。柳士镇说:“‘你’字唐代开始流行,并且一直沿用至今。”[11]
30.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寝。(廿,280)
31.僚欲呼医师针灸,恐母痛难忍,自以口於母肿上徐吮之,其肿自熟,血流出,迨夜即得安寝。(八,28)
32.寮欲唤师针灸,恐痛,与口於母肿上吮之,即得小差。以脓血数口流出,其母至夜,便得眠卧安稳。(句,1)
31、32中的“迨”本为“赶得上”的意思,表示“等到、达及”的意义大约是晋代才出现,如“迨良期於风柔,竞悲飒於叶落”(陆云《牛责季友》),但这种用法后来不占主流,还是慢慢地被最常用的“至”取代。可以看出敦煌本的语言趋俗,而二十卷本和八卷本都有弃常见义不用的嫌疑。“安”前两例用“安寝”,而第三例用“眠卧安稳”,这样不仅“寝”、“安”都被双音词替代,而且语序和语法关系也有改变。“安寝”是状中短语,“眠卧安稳”是动补短语。我们知道,语法史上状中关系比动补关系的历史古老得多,动补关系在上古还只是零星的语法现象,至中古才慢慢地发展起来。看来,敦煌本在表示同样的语义关系时与其他两本的句法选择是不同的。
33.忽一日,於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於草中。(廿,457)
34.忽一日,於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草中。(八,29)
35.后纯妇(注:《敦煌变文集》作“妇”,疑误,当为“归”。又,此句“家”后当逗。)家饮酒醉,乃在路前野田草中倒卧。(句,20)
33用“卧於草中”,34用“卧草中”而不加介词“於”,35表示处所的成分以介词“在”带领移至动词前。在唐五代时期表处所的介词结构已大量前移,“在”对“於”的竞争力量也在急速增加。张赪[12]的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於”引进的表处所的介词结构在非佛经类文献中仍以居VP后者为多,而“在”引进的就以居前者多了,至唐五代时期,不仅“在”字介词短语保持前期的居前势头,“於”字介词短语随着介词结构前移的大潮也大多跑到前面去了。所以33、34例的处所成分的位置明确表示它们反映语言变化的滞后性。如果说33还大致与晋代的语言实际相符合的话,成书于宋代前后的八卷本语法反应力就较弱了。35符合唐代的语言实际,适时地反映了语言的发展面貌。
36.此是我真女婿也。(廿,395)
37.此是我真女婿也。(八,3)
38.真是我女夫(注:此例S.525“真”作“直”,敦煌手抄写本常有这种情况,如S.6022“段孝真”作“段孝直”。)。(句,9)
“真是我女夫”中情态副词“真”与判断动词“是”的搭配大致到唐代才真正形成,用于感叹句中。上古载籍中很少见到,《史记》中有5例作副词用的“真”,但4例不用在“是”字句中,用于“是”字句中的仅一例。《史记·外戚世家》:“尹夫人望见之,曰:‘此真是也。’”句中的“是”是不是判断词尚难定夺,疑为形容词。《三国志》中副词“真”6见,不用在“是”字句中。口语性较强的中古文献《世说新语》也未见到这样的句式。迟至敦煌变文和寒山诗中,方见其例:“实为五运之尊,真是兆民之主”[13],“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14]。或许这种句式到唐代才真正在口语中使用。
同样语境中各本表现出词汇选择的差异,我们再给出一些例证。如:
39.乃遣人发冢,启柩视之,原葬悉在,惟不见金枕。(廿,395)
40.乃遣人发冢,启柩观之,原葬诸物悉在,惟不见金枕。(八,3)
41.遂遣兵士开墓发棺看之。送葬之物,事事总在,惟少金枕。(句,9)
42.视其金枕在怀,乃无异变。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廿,395)
43.视其金枕,怀乃无异。徧寻至秦国,既以枕於市货之(注:此例中“徧”疑为“变”之音近之讹,当作“变”,属前。)。(八,3)
44.看之,怀中金枕仍在。遂将诣〔秦〕市卖之(注:此例S.525号为:“看怀中金枕宛在,遂诣秦市卖之”。)。(句,9)
41中的“总”是中古新兴的副词,而39、40仍用“悉”。以上6例都用了视觉动词,敦煌本用“看”而二十卷本、八卷本用“视”或“观”。汉语词汇史上“看”对“视”或“观”替代的事实是很清楚的。汪维辉经过研究发现,“看”在上古罕见,仅《韩非子》中有一例[15]。至三国时代人们的口语中早已在说“看”而不说“视”了,晋代以后不仅在口语中而且在文学语言中“看”也取代了“视”。像这样表现出新词新义的产生或显示词汇兴替的例子敦煌本中还有不少。如:
45.今日君来,愿为夫妇。(廿,395)
(46)今日君来,愿为夫妇,君意若何?(八,3)
47.今乃与君相逢,希为夫妇,情意如何?(句,9)
48.女与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廿,359)
49.与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八,10)(50)其女先与王凭志重,不肯改嫁。(句,16)
51.僚将归奉其母,病即愈,寿至一百三十三岁。(廿,280)
52.将归与母食之,其疾即愈,延寿一百三十三岁。(八,28)
53.将归与母食之,乃哺之于疮上,即得差矣。命得长远,延年益寿,乃得一百一十而终也。(句,樊寮,1)
五
以上通过对三种《搜神记》交叉互同条目语言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些条目中八卷本与二十卷本的关系很近,而与敦煌本的关系较远,但是八卷本与敦煌本相同的条目竟有15条之多,两者又明显有承继关系。如何解释?我们初步认为八卷本不一定“从敦煌本出”(注:本文采用的各本《搜神记》的版本:二十卷本,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敦煌本,句道兴撰《搜神记》,收入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八卷本,即《稗海》本,收入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附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敦煌文献《搜神记》残卷S.525、S.2022、S.2072、P.2656、P.5545。),它与敦煌本、二十卷本一样,成书过程中都参考或依据了同一古本《搜神记》。
散见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法苑珠林》等类书中的古本《搜神记》条目应该没有经过太大的变更。如果要变更也只会比古本更简从而使语言更加简雅。纂辑者(可能是胡元瑞)纂辑二十卷本时,对绝大部分条目应该未作大的变动,前述第421条是比较少见的,因而二十卷本的语言比较“古朴”[5]。
八卷本的编辑者在编辑该书时,古本《搜神记》应该还没有散佚,这可能就是它有些条目在语言上与二十卷本接近的原因。该书编辑时可能也参考了敦煌本《搜神记》,这从它的编写体例中可以略见端倪。敦煌本的编撰者句道兴在编撰《搜神记》时应该是有明确的编撰体例的,有两事可见。一是卷首题有“行孝第一”,可以看出敦煌本应该不止现在所见的一卷,而且每卷应有卷名;二是卷内每条的首句讲究体例统一,基本上都以“昔+姓名+者”开篇。八卷本参考了这第二条体例,因为全书40条中12条冠以“昔”字开篇,其中6条刚好与敦煌本故事相同,这应该不是巧合。这似乎可以看出为何它与敦煌本同条目有15条之多的现象。八卷本在编辑时,可能还有自撰的条目。江蓝生先生、汪维辉先生考察的40来条用以判定八卷本语言时代的鉴别词,大半在二十卷本、敦煌本未见的条目中,说明这些条目是编者自撰的可能性很大。这40来条词语中还有一些词语所在的条目与二十卷本或敦煌本同,但这些词语均不见以其义用于二十卷本,却有一些出现于敦煌本的关系条目或以相似的词语形式见于《搜神记》敦煌残卷中,如“却(表转折)”、“合眼”、“阿婆”见于敦煌本,“歇”和“要紧”,S.525分另作“歇息”和“要当”等。这样看来,八卷本既参考了《搜神记》古本,又参考了敦煌本,再杂以对前两本的改动和自撰,因而形成了其语言风格不一致的现象。江蓝生先生说:“与敦煌本相比,八卷本各条的语言风格则很不一致,有的几为文言,有的则白话程度颇高。”[5]原因或许在此。所以八卷本的语料价值远远不如敦煌本。
由于敦煌本是唐人句道兴依据古本编撰的,加上他注意用当时的语言写作,反映了当时语言状况。它的语言比二十卷本通俗,也比八卷本的部分条目通俗。与八卷本相比,更显示了它语言内部风格的统一性,因而语料价值较高,是研究汉语史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
收稿日期:2003-0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