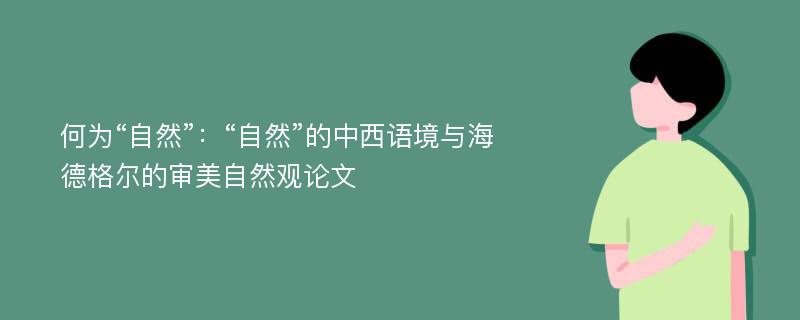
何为 “自然 ”?:“自然 ”的中西语境与 海德格尔的审美自然观 *
张海涛
内容提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近代哲学强调内在自然的外化,中国庄禅哲学强调外在自然的内化。两者都忽视了自然的“存在”意义。海德格尔则自始在历史时间内厘定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自然的“存在”意义。一度被技术所遮蔽的自然的在世性和历史性在艺术的审美呈现中变得显豁。审美世界的开启提供了重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现象学视角。由此,海德格尔的自然观可以称之为审美自然观。
关键词 自然 中西语境 海德格尔 审美自然观
“自然”概念的现代释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国古典的自然观,另一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自然观。中国古典的自然观侧重事情自生自发的样子,“自然而然”;西方近代哲学的自然观以“nature”为基础,“与表示规范的nomos(‘normality’)和表示人为手段的techne(‘art’)是相对而言的,分别代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注] 陈嘉映:《人还会有自然的生活吗?》,《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2期。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的现代释义都还是一种对自然的“现成”把握方式。对“自然”的释义不应脱离生存时间及历史时间。
“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1]的《牡丹亭还魂记》,主要依据《杜丽娘慕色还魂》改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魏晋志怪、唐人传奇对《牡丹亭》创作的影响,人们常常估计不足。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明明白白写道:
一 、西方近代哲学中的 “自然 ”
以“nature”为基础,西方近代哲学的自然观可以细分为三种:原始主义的自然观、有机主义的自然观和非理性主义的自然观。
原始主义的自然观在卢梭“回到自然”的口号中表露得极为鲜明。“回到自然”所回归的不仅是未经人化的大自然,更是未受文明浸染的儿童和野蛮民族所具有的纯朴心灵。卢梭的《爱弥儿》认为要对儿童进行适应其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以使人不至失去质朴的自然本性。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高声赞扬那勇敢、剽悍、未经开化的野蛮族群——阿尔巴尼亚山民。小施勒格尔干脆宣称:自然是生命、原始的生命。可见,所谓原始主义的自然,就是人与自然的未分化状态。
有机主义的自然观按照著名思想史家诺夫乔依在《作为美学范畴的“自然”》一文中的归纳即是“从规则、习惯、传统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自由与习惯的对立)。”[注] A.O.Lovejoy,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48,pp.170~173.转引自罗钢:《一个词的战争——重读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这种自然观的形成源自西方近代知识型的生物学模式,即将世界上的一切都看作一种生物式的有机存在。由此,人的生存、成长就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自然生长。这样,所谓理性的约制、习俗的规范、传统的承继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碍着人的自然生长。有机主义的自然观实际上提请出的乃是先天与后天、天生与培养、浑朴与雕琢、天成与技艺之间的对立。庄子言: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庶几与此意相同。在这种有机自然观的影响下,近代西方哲学催生出一种“自然天才”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禀赋)。由于这种才能作为艺术家天生的创造性能力本身是属于自然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ingenium),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注]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康德这种将“天才”看作艺术家天生禀赋的观点即是一种典型的“自然天才”观。质言之,有机主义的自然所说的方是有机生命的生物性存在。
在元认知策略方面,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差别明显。在制定计划、自我评估、自我检查和选择性分配注意力方面,好学生都比差学生强。这说明了好学生能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词汇学习,并在词汇学习的过程中运用自我评估、自我检查和选择性分配注意力来有效地学习。
在庄禅哲学中,人的“性本”自然不是明确的理性或非理性而是规避了生命感觉意向的空寂,是无动于衷的木然、无所住心的安然,实际上就是外在自然的内置。所以,在庄禅哲学中,“只有当内在自然的‘性本’确立之后,外在自然(山丘、园田、虚室)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注]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这样,庄禅哲学中的“自然”实际上力求排除西方语境中“nature”的人性意涵,以便使人与自然间的通达变得了无扦格。
西方从浪漫哲学时期形成的三种自然观基本上没有走出“性本”自然的范畴,而庄禅哲学的自然观又质朴地指向自在的外在自然。“性本”自然观催生了非理性主体的诞生,自在自然观消解了价值主体的生长。一个回归生命本然的冲动,一个回归自然原始的宁寂;一个建立在知觉意向统摄的基础上,一个建立在人不断外在自然化的过程中。无论进程从人出发还是从自然肇端,其目的都无非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原初同一。在这一诉求的推动下,人的在世性无论如何是要被勾销掉的。因为“人的本质基于在世”。[注] [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熊伟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第393、371页。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生存在内容方面的意思无非就是“站出来站到存在的真理中去。”[注] [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熊伟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第393、371页。 人惟有从自然状态跃身而出、出位在世,才成其为人。因此,人向自然的归退必要以取消人的生存性、在世性为前提。如此一来,人从在世的澄明复又回到了自然的锁闭,人与自然固然就此融合为一,但也就此沉入了原始的茫茫黑暗。
二 、中国庄禅哲学中的 “自然 ”
“昆北”阳平声字“双”的唱调(《南柯记·瑶台》【梁州第七】“臂鞲双抬”,765),该单字唱调的过腔是。其中的是第一个乐汇型级音性过腔,是第二个乐汇型级音性过腔,是第三个乐汇型级音性过腔。这个过腔也是由“级音+级音+级音”同一种音乐材料组成的多节型过腔。
在老庄那里,向自然的退守意味着人的“出世”。陶渊明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间,与自然相对的“樊笼”也就是历史社会的在世状态。因此,“回到自然”实际上意味着从历史时间返回自然时间,从价值状态返回虚无处境。此种情形下,人的性本自然势必要排除任何意向性的冲动,达到一种“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说到底,道家哲学所设想的那个人与自然“兴来如答,情往似赠”的玄妙状态,惟有在人外在自然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因此,在向自然的退守中,人要非我、无情、澄怀、“坐忘”,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正所谓“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即是说,无论“万物复情”还是“与物为春”,总是要达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和合之境。然而如此一来,物犹为物,人却已非人。因为人的主体性已就此消散为植物性、生物性。人的主体性一旦被摈弃,人的在世性也就一并被勾销掉了。道家的悖论在于,人的生命感觉惟有当人从自然状态中绽出时才能获得。海德格尔说此在总是带着情绪的此在就是这个意思。由此,人对现世之恶的体会,对人生无常的感喟总还是基于“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一实情。既如此,人的在世也就是人返归自然的前提。然而,问题是,在世既已是人之为人不能更易的事实,那么已然从自然状态中到场到人又如何能做到完全出世?而且对现世苦厄的领会、对生存的出世“筹划”,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本就是此在(人)在世的一种展开方式。惟有在人的在世展开中(情绪、领会、话语),“回归自然”才作为一种生存路向被标示出来。没有已经在世界中的在世,也就无所谓退守自然的出世。这样,若要做到与自然的原初为一就必得勾销在世,而一旦勾销了在世,人与自然的原初为一也就失去了依据。老庄无法绕出这一悖论,人与自然的完全同化也就难免是一种虚构。
非理性主义的自然观按照诺夫乔依的总结即是:“无意识的自我表现,从深思熟虑中摆脱出来,否定技巧的因素。”[注] A.O.Lovejoy,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48,pp.170~173;转引自罗钢:《一个词的战争——重读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实际上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巧若拙”,苏东坡所说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注] 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轼文集·卷49》,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8页。 石涛《画语录》中所说的“无法之法是为至法”。[注] 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也就是一种无斧凿之痕、非刻意求工的表现方式。因此,非理性主义的自然实际上乃是“自然而然”。这种自然观在现代西方哲学、诗学中体现为叔本华将艺术看作直观的知识,且只有直观的知识能通达真理的非理性真理观,以及克罗齐“直觉即表现,表现即艺术”的非理性艺术观。这种自然观的更深层次的阐发则意味着对世界本质以及人的本质的非理性把捉。这在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乃至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所以,在现代哲学中,非理性的自然多数情况下所指谓的乃是人的欲望、意志、知觉等非理性层面的性本自然,也就是与外在自然相对的人的内在自然。
文人直冒酸味,名士酒气熏天;文人如河边的垂柳,名士如利剑出鞘;文人是追梦者,名士是逐风的人。李白是文人中的名士,他曾立志报效国家,仗剑走天下,得意时酒是胆,可以藐视权贵;失意时,酒中透着忧伤。李白每次醉的不同,这是他的宿命。
在海德格尔这里,实际上没有历史时间与自然时间之分,时间作为此在绽出的维度和此在存在的意义只能是且仅仅是历史时间。因为时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无论柏格森的“绵延”还是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无论“客观时间”还是“主观时间”,只要时间的同质性没有改变,时间就仅仅是自然时间。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却是“此在的结构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之条件,是此在作为整体的存在样式。”[注] 张汝伦:《德国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所以,时间根本不是一物,不是存在者,而是此在的存在本身。传统的时间概念囿于自然时间的视野将时间看作是永恒的序列,而实际上,源始的时间并非无远弗届而是“有终的”。 “回到自然”不是从历史时间抽身而出回到自然时间,而是人与自然在历史时间内部的相遇。
三 、海德格尔的审美自然观
总结来说,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自然观,无论是将自然看作人类的质朴心灵,还是看作人的天然禀赋、欲望、意志、知觉,其所表达的实际上都是一种内在的自然意识。而中国古典哲学、诗学所表现出的自然观则是一种外在的自然意识,即在中国先哲那里,自然就是作为宇宙、丘山、田园、草木的自在自然。只不过在与这种自在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哲学追求对外在自然的探究、认识乃至于改造、褫夺,而中国哲学尤其庄禅哲学则追求与外在自然的亲善、应答乃至于融洽、合一。刘小枫说:“归隐生命的感觉有两个返回的对象,一是自然宇宙(山丘、田园、虚室);一是人的‘性本’。这两个生命感觉对象统称为自然。”[注]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西方近现代哲学大体上是在人的“性本”层面上来谈论自然,而中国的庄禅哲学则多从自然宇宙层面来谈论自然。
实际上,海德格尔从未主张过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回到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原初同一。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回到那个完好无损的自然。与我们相遇的自然本已置身在由此在的到场所敞开的世界中。因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厘定并不能以剥夺人的在世性为前提。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提醒人们,在现代技术世界我们顶多可以将技术对自然的损毁保持在可容忍的限度内,而不可能以牺牲技术来保全自然。这样,人与自然在历史时间内部的相遇就须先控制作为手段的技术。然而海德格尔却又告诫我们,在现代技术社会,技术在本质上已从人类可以控制的工具变成了人类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绝不只是单纯的人类行为。”[注]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7页。 海德格尔断言:现代技术在本质上乃是一种作为促
比之老庄道学,禅宗哲学已不再拘执于向自在自然的退守,却仍然保留了老庄对性本自然的规范。即是说,禅宗已不再着意于老庄对在世、出世的分立,只要“自性清净”,在世与出世已殊无分别。所谓“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等等”。[注] 郭齐勇:《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佛教的当代意义之蠡测》,《江汉论坛》1995年第7期。 在此种禅法的引导下,尘浊与净土、在世与出世并无差别。临济义玄说:“佛法无用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穿衣吃饭,困来即眠。”[注] [宋]赜藏编:《古尊宿语录·上》卷5,中华书局,1994年,第377页。 《居士传》中言:“若心常清静,离诸取著,于有差别境中能常人无差别定,则酒肆淫房,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波若。”[注] [清]彭绍升:《居士传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413页。 龙树说得更分明:涅槃与世间无别,两边皆空。这种不弃现世而求涅槃的“理论”,实际上说的仍是一种“自然”。只不过此“自然”已不再是作为丘山、园田的自在自然,而成了日常生活的“自然而然”。求佛之路即是“饥来即食,困来即眠”,即是“热即取凉,寒即向火”。寻常意思成了佛法大义,世俗世界也就是佛国净土了。“人在随顺自然时的挥手举足、扬眉瞬目之间便显示的是生活真谛,在心识流转、意马心猿中也可以有心灵自由,人生的顿悟不再由‘知’的追踪寻绎而只是由‘心’的自然流露。”[注]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说到底,禅宗佛学仍然主张人向性本自然的回归。只不过此性本自然是了不动心的空寂、八风不动的慧定。此一意义上的性本自然,究其实,与庄子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并无实质差别。因此,禅宗佛学虽然不再像老庄那样执意于外在自然,但其对性本自然的规定仍不过是一种外在自然的内置,主张的仍然是人的外在自然化。只不过在禅宗这里,人之性本的外在自然化并非为了达到与自在自然的原始同一,而是达到日常的随顺、平常的适意。老庄将人的主体性消解到自然的浑融中,禅宗则将人的主体性消解到生活世界的包围中。禅宗虽然未曾勾销人的在世性,但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既然在心性上与木石无别,在世也就与出世无异。既如此,禅宗也就仍然无法绕出老庄的悖论。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明确表示,人和自然都只是在此在的在世生存中才成其为自身,“自然本身就需要一个世界才能来照面。”[注]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6、138~139页。 他断言:把自然现成化,使之脱离此在在世,“周围世界变成了自然世界”,导致“空间性失去了因缘性质”;“上手者的合世界异世界化了”,从而导致“单质的自然空间才显现出来”。[注]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6、138~139页。 这就是说,自然实际上是伴随着此在的出位、到场来照面的,自然之为自然只有在此在在世的前提下才绽露出来。在1929-1930年冬季学期的演讲中(题为《形而上学的基础概念》)中,海德格尔明确说到:“自然仅在与包容于其中的我们相呼应当中,才能同我们相遇。”[注] [德]奥特·波格勒:《东西方对话:海德格尔与老子》,[德]莱因哈德·梅依:《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张志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8、200、200页。 由此看来,海德格尔在《思的经验》中所提到的“自然的自然性”绝非一种与人的在世性相对立的、脱离开人的社会历史处境而存在的自在自然。陶渊明挣脱“樊笼”复回到的“自然”在海德格尔看来其实自始即在“樊笼”里,因为如若没有“樊笼”,“自然”也就无所谓自然了。因此,奥特·波格勒说,海德格尔实际上呼唤的是一种“由哥白尼的世界观所象征的自然向‘自然的自然性’的回归。”[注] [德]奥特·波格勒:《东西方对话:海德格尔与老子》,[德]莱因哈德·梅依:《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张志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8、200、200页。 而“这种自然性无疑被视为一种历史性的东西。”[注] [德]奥特·波格勒:《东西方对话:海德格尔与老子》,[德]莱因哈德·梅依:《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张志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8、200、200页。 即是说,自然之进入人类的视野本就根植于人类自身的历史性嬗变,自然绝非那个等待上到手头的“一物之自然”(nature as a thing),而是人类历史性易变的产物。黑尔德说得不错:“生活世界与大自然向来关系密切,根本无须附加理智的连接。生活世界本身就是‘自发地’发生的、具有‘大自然’特征的显现过程。”[注] [德]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2页。
逼的解蔽。[注]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7页。【海德格尔后来将其称之为“集置”(Ge-stell)】 从前农民在大地上耕耘,并没有被促逼着耕地。他将种子交给自然的生长之力,为它企盼大地回春、甘霖普降,为它迎候晨昏变换、时令更迭。他守护着种子的发育,呵护着种子的成长,静待种子的成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那时候,‘耕作’(bestellen)还意味着:关心和照料。”[注]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13、16、35页。 而现在,轰隆的机器蛮横地打破了大地的安宁,它催促着作物的成熟,它急切地将成熟的果实变成食物。于是,“耕作农业成了机械化的食物工业”,于是,“就连田地的耕作也已经沦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摆置着自然的订造的漩涡中了。”[注]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13、16、35页。 此种情形下,现代技术实际上“在促逼意义上摆置着自然”。而所谓“摆置”则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开采,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它通过“开发和摆出”进行开采。在现代技术的摆置下,自然从其自然性中被剥离出来。自然就此开始了被侵夺、被改变、被贮藏、被分配,又重被转换的历程。如此之后,自然的自然性在订造着的解蔽中被异化为非自然的东西。
更为严重的是,技术的摆置还将人本身也收归麾下,人成了被促逼的、被订造的、有待开发的资源。海德格尔举例:“在树林中丈量木材、并且看起来就像其祖辈那样以同样步态行走在相同的林中路上的护林人,在今天已经为木材应用工业所订造——不论这个护林人是否知道这一点。”[注]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13、16、35页。 现代技术通过对人的摆置,在逼使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的同时也把人聚集入了订造之中。如此一来,自然的自然性、人的人性就都被异化为了对象的实体性。“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自身贯彻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注] [德]海德格尔:《诗人何为?》,《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06、310、310页。 人与自然在技术的摆置中双双走了样。好在还有“艺术”。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之本质现身之日也正是救渡之可能升起之时。“救渡乃根植并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注] [德]海德格尔:《诗人何为?》,《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06、310、310页。 而作为技术本质现身之物的“解蔽之命运”却自始便允诺人的参与。因此,海德格尔又说:“拯救必须从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攸关处而来。”[注] [德]海德格尔:《诗人何为?》,《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06、310、310页。 人只有从被技术摆置的命运中解脱出来去“守护在其生长中的救渡”,救渡才有可能。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作为并不能全然祛除技术统治的危险,但人类的沉思却可以思考:“一切救渡都必然像受危害的东西那样,具有更高的、但同时也相近的本质。”[注]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13、16、35页。 由此,海德格尔提醒人们注意技术之本质的高度模棱两可性。因为在古希腊时代,不只是技术冠有τεχνη之名,τεχνη也指美的艺术的创造。海德格尔认为对技术本质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必须在一个与技术之本质有着深切亲缘关系而又与技术之本质根本不同的领域进行。这个领域就是“艺术”。《技术的追问》的最后,海德格尔援引荷尔德林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来说明:现时代,人向其本质的最高尊严的回归、自然向自然性的回归惟有在艺术(审美)中才有实现之可能。[注] 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认为“解蔽之本有”需要人对解蔽的参与。因此,被遣送到解蔽之中的人本身即意味着救渡。因为这种救渡“让人观入他的本质的最高尊严并且逗留于其中。”而这种最高尊严,在海德格尔看来,即在于:“人守护着无蔽状态,并且与之相随地,向来首先守护着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的遮蔽状态。”[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3页。
做好施工后的质量管理工作,可以有效的促进水利工程的完美竣工。因此,当水利工程施工后,相关人员就应及时的审核竣工资料,不仅要对相关质量检验报告进行有效审核,而且还应对技术性文件进行审核,这样才能确保工程的竣工能够符合相关工程竣工的要求和标准。企业还应实行一定的保修制度,为工程后期的服务提供一定的保障。
在《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还对“自然”概念进行了一番考证。通过考证,海德格尔向我们揭示到:希腊文中的“自然”指的乃是存在本身。在拉丁文中“自然”的意涵则转变成了“出生”“诞生”。海德格尔认为,拉丁文的“自然”译名实际上“已经减损了φυσιδ(自然)在希腊文中的源初内容,毁坏了它本来的哲学的命名力量。”[注]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页。 而且,这种情形不仅存在于希腊文向拉丁文的转译中,也同样存在于所有其他从希腊语到罗曼语的哲学翻译中。罗曼语对希腊文“自然”的转译后来在基督教及中世纪被权威化,并在近代哲学的概念体系中被确定下来。自此,我们现在仍在流行的自然概念被创造了出来。这样,“自然”概念实际上一直处在一种畸变和沦落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自然的源初意涵几被损毁殆尽。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只有在源初的意义上澄清了“自然”概念的意涵,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才能被昭明。因此,海德格尔跳过自然概念的整个畸变过程,在源初的意义上,将自然定义为“既绽开又持留的强力。”海德格尔的原话是:“φυσιδ这个词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自身绽开(例如,玫瑰花开放),说的是揭开自身的开展,说的是在如此开展中进入现象,保持并持留于现象中。简略地说,φυσιδ就是既绽开又持留的强力。”[注]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16页。 海德格尔继而解释说,自然作为“绽开”是随处可以经历到的——月之阴晴圆缺、海之潮涨潮落、天空之明灭可睹、细雨湿衣之不见、闲花落地之无声。但是,自然作为“绽开着的强力”却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些我们今天还称之为“自然”的过程。因为“自然”在源始意义上并不是指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这一φυσιδ是在本身,赖此在本身,在者才成为并保留为可被观察到的。”[注]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16页。 1939年在题为《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如当节日的时候……”》的演讲中,海德格尔对φυσιδ的作为“出现和涌现”的意义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φυσιδ乃是出现和涌现,是自行开启,它有所出现同时又回到出现过程中,并因此在一向赋予某个在场者以在场的那个东西中自行锁闭。”[注] [德]海德格尔:《如当节日的时候……》,《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5页。 1946年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借里尔克的一首无题诗再次强调了他的这一自然观。在那里,他说道,自然乃是我们惯常所说的“狭义的自然”的基础,是人与动、植物共同展开其存在的根基。因此,自然作为“芸芸众生”的基础,指的实际上就是“存在者整体意义上的存在。”[注] [德]海德格尔:《诗人何为?》,《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91~292页。 随后,在1950年写作的《技术的追问》中通过对技艺、艺术的绽出方式与自然的绽出方式的对比,海德格尔又进一步将自然的本质揭示为“涌现着(φυσει)的在场者在它本身之中(εν εαυτω)具有产出之显突(Aufbruch)”[注] [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页。 的最高意义上的“绽出”。
结语
西方近代哲学的“性本”自然和中国庄禅哲学的自在自然,一个把自然设定为主体内在的“性本”,一个把自然还原为原始的混沌,自然要么以一种人之本质的形象深入到主体内部,要么以一种对象的姿态坐落在客体的位置上。在这两种观念中,人们对自然的把握,实际上都还是一种现成的观照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只要我们还以一种现成的方式来谈论人与自然,那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便永远无法避开形而上学的局限。海德格尔的逻辑是:此在的在世披露了自然的属人性(撇开人的生存时间和历史时间谈论“自然”没有意义),自然的属人性催生了技术的诞生,而正是技术的摆置取消了人及自然的神秘性;限制技术的办法是现象学地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回到人与自然关系的“事情本身”,而人与自然关系的“事情本身”,只有在作为语言本质的“诗”中才如其所是地显现。实际上,惟有在语言所构筑的人的意义世界中“自然”才得以彰显其价值。哈贝马斯说:“使我们摆脱自然的唯一事物是语言。”[注] Habe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 trans. by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p.314.而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注]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因此,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将人的“世界”与象征自然的“大地”的统一安放在诗中。在《诗人何为?》中,人与动、植物在源始自然中达到一致的过程,亦自始在里尔克的无题诗中展开。海德格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审,对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破解是借助于诗的显现功能完成的。可以说,惟有通过审美之维的开启,人与自然关系的“事情本身”才得以显现。
〔中图分类号 〕B51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9)03-0084-06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美学研究”(15CZX062)
作者单位 :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魏策策
标签:自然论文; 中西语境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审美自然观论文; 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