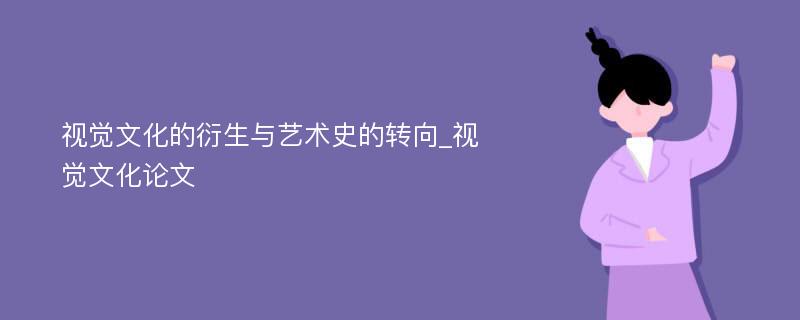
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觉论文,艺术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视觉文化”或“视觉研究”?它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个转瞬即逝的跨学科漩流,还是一个研究主题,或者是文化研究、媒介研究、修辞和传播学、艺术史或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是否拥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抑或只是那些受人尊崇和业已成熟的学科残余问题的集成或混杂?如果它是一个研究领域,那么它的边界和相对固定的定义是什么①?如果不是,那么其研究的对象是否尚处在难以确定的形成过程之中,作为一个学科的建制远未达到成熟?迪克维斯特卡亚在《文化转向之后的视觉研究》一书中提出,视觉研究尽管在过去十几年的英美学院中不断繁衍扩展,但对于它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定义以及方法等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共识②。没有共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只是在视觉文化研究发展可能性的方向上还存在着各种尖锐对立的不同倾向与观点。面对这样的窘境,我们与其追求给视觉文化或视觉研究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不如回溯它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自身发展的历史;在辨清其源流和谱系的基础上,或许有可能找到其发展兴盛的契机。
一、视觉文化与“文化”的多种含义
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视觉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个时期,艺术史、人类学、电影研究、语言学以及比较文学等学科遭遇到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冲击。后结构主义批评家认为,学院式的人文学科如同作为人工制品的语言一样,它们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产物。在此情形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成了文化研究探究的对象。这个“人类学定义”的文化概念,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非常宽泛的活动,它包括构成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流行音乐、印刷媒介、艺术和文学,也包括体育、烹饪、驾驶、人际关系和血缘等。这个人类学的总体性概念,不仅包括了“精英的”或“高雅的”艺术和文化,而且也把“文化”术语与流行或大众文化的理念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先前“精英的”或“高雅的”文化就不再拥有任何特权③。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文化”概念复杂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这个与“文明”概念紧密相连的术语开始出现在18世纪晚期,指个体或社会智识和精神教化过程,到了19世纪,它已被看作是一个物质性术语,包括艺术作品、诗歌、哲学文本、文学等诸如此类的教化产品。不过很清楚的是,在这个与“野蛮”相对的观念之中存在着明显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在西方思想中,文化一直作为评价和等级概念而发挥效用。在这里,“文明”是指文雅化、教养化过程,“野蛮”是指自然的原初状态,或按字面意思指“生活在丛林中”④。这种文化观念在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中表现相当明显。在阿诺德看来,文化指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层面,它源于对完美的热爱,探究、追寻和谐普遍的完美,它是甜美,是光明,是“世界上所思与所知东西的精华”,从根本上是非功利的,它在于不断转化成长而非拥有什么,在于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而非外部的环境条件,内在于人类的心灵,又为整个社群所共享,是美和人性的一切构造力量的一种和谐⑤。不过,阿诺德并没有暗示这种文化只能被贵族或上流阶层所拥有。但他领会到他所看重的开化的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别,他认为后者追求享乐主义,处于不成熟和无政府主义状态。
阿诺德的文化精英论调在随后的利维斯、格林伯格和麦克唐纳的著作中得以延续。列维斯也把那些具备恰当的文化趣味和判断力的人作为文明社会的卫道士。正是这些精英群体从西方艺术和文学经典中提升出来的文化智慧和敏感,让社会能有希望保持一定的道德和审美判断力。他察觉到日益兴盛的流行娱乐(特别是好莱坞电影)和大众报纸杂志对这种文化判断力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些流行娱乐只是为了商业性目的,对公众的文化教育没承担起任何责任。而在各种大众文化商业性危害的威胁之下,让有教养的少数人保持着文化的趣味和判断力是必要的。格林伯格也认为,低级黄色小说、流行音乐、杂志和好莱坞电影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一种易于接近的、商业化的和不需要高智力的畸趣文化,主要是为了满足拥有足够收入的工人阶级和较低级的中产阶级,它们以各种形式提供了一些不需要琢磨的娱乐形式,既能给观众带来轻松的愉悦,又不需要他们在上面花费过多的智力或判断力。从这些观点中不难看出评价大众文化的共同背景。对他们而言,大众文化是低级的,远离文化的真实源头,同时以大量平庸和无聊的内容威胁着人类文化的伟大成就。正如麦克唐纳所认为的,“大众文化是非常非常民主的:它完全拒绝歧视任何物或人,或它们两者。对磨粉机而言它们都是谷粒(它们都是制作工厂的养料),并且都生产出实实在在磨碎的精细产品”⑥。他认为大众文化是高雅文化的低俗形式,“是高层的强制,它由商人雇佣的技术加工而成;它的受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局限于是买还是不买的选择”⑦。哈利·波特小说和电影被当作流行娱乐,斯蒂文森的诗歌被当作严肃的文学。这种等级划分或价值评判常导致关于文化的最为基本的争论。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这样一个被反复申说的观点,即电视看多了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对儿童来说。但没有人会不断建议要注意艺术博物馆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效果。这说明人们思想中广泛存在一个习惯,即认为“高雅”文化能够提升观众智识和审美上的素养,而没有这些方面能力的文化实践活动则在等级上被贬低。
但随着媒介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在“二战”后电视逐步进入日常生活,开始挑战文字和印刷术的主导地位,产生了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谓的“图像革命”⑧。后来米歇尔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为“图像转向”。当代文化的“图像转向”意味着图像不再是表征外在现实或内在情感的工具或载体,而转变为当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即所谓视觉化或图像化生存。对于长期浸泡在电视中的当代读者而言,那种精英化的文化论调似乎让人难以接受。媒介环境学视野中的“文化”不再对一种文化实践的道德、智力和审美的品质进行任何评判,而变成一个纯粹描述性的、没有价值等级的中性概念。事实上,这种与品性评价相区分的“文化”定义早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尔德那里就初步形成了。对赫尔德而言,文化是特定社群的生活方式,它包括日常的风俗与习惯、信仰以及传统,伴随着与文明相连的伟大艺术性和智慧性的纪念物⑨。换句话说,一种文化不是参照一些从别处借来的人为强加的标准而成长起来的,而是通过源于自身的动力。赫尔德常被视为文化相对主义第一人;他倡导社会多元性的观念,每一个社会必须通过它自身文化的价值进行理解。赫尔德对文化的人类学界定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它反对一元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另一方面挑战了某些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这样一个长久以来的假设或前提。没有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文化,而且在当下毋庸置疑的是,文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使社会变得日益多元。因此,要使一大堆庞杂的文本被所有人认可、进而形成一个共享的文化传统,这样的事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实际的情形是,“所有的文化,以及所有这些文化所生产出来的文本,是多元、混杂、异质性、不均衡发展的,它们拥有多样的历史轨迹、节奏和时间”⑩。
二、视觉文化与艺术史
视觉文化概念的兴起就是关于如何界定文化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的进一步体现。它被不同的使用者用来反对传统学院关注高雅文化的精英主义(11)。这一新领域质疑传统艺术史“进步”的历史叙述方法,并潜在地打破了把欧洲假定为标准文化并视为意义的唯一源头的中心主义。与其他文化彼此依存的视觉文化倡导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强调在分化、相关性和连接等系统性原则的基础上,任何单一社区或世界的某个部分,不管其经济力量或政治权力如何,都没有认知上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视觉图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成为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一个正当其时的策略(12)。夏普林指出,在艺术史领域首先系统性地探究视觉文化观念的是英国艺术史家巴克迪莱(Michael Baxandall)。他在《15世纪意大利绘画与经验》一书中,虽然仍运用传统的艺术史方法来阐释艺术作品之间的关联以及画家或雕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明确提出,为了理解15世纪的意大利绘画,我们必须超越文艺复兴艺术和高雅文化的范围,不能限于传统学院式分析。例如,他认为布鲁内莱斯基在15世纪早期发明的沉迷于数学比例的透视法,必须与那个时代商业交易中实用数学占主导联系起来考虑,因为在那个时期,从事复杂的计算是商人从事日常事务的必要基础。在发明二进制登录账簿的社会中,一种对数学式数量和比例的偏好倾向自然也影响到视觉经验,包括图像表现。巴克迪莱还将绘画中的人物表现与同时期的舞蹈指南进行对比。显然,巴克迪莱试图改变艺术品呈现的语境。他不再只聚焦于高雅艺术和书本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介绍文化生活中同样影响艺术图像制作的其他方面。他试图表明,当我们尝试去理解那个时代的艺术时,其他一些明显微小和边缘的文化活动是如何重要(13)。
事实上,潘诺夫斯基几乎同时在从事着相近的研究工作,他在出版于1955年的《视觉艺术的含义》一书提出了“图像学”(iconology)研究方法。这是一种从分析中发展起来的解释性方法,它力图弄清楚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或内容,而这种被凝缩在作品中的含义或内容能够反映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阶级、一种宗教或哲学信仰之基本态度或根本原则。例如,我们不能局限于认为达·芬奇那幅描绘了十三个围着餐桌的人的著名壁画再现的是“最后的晚餐”,而应该超越作品本身,试图把它当作关于达·芬奇个性的记录、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文明或某种宗教态度的文献。这样一来,艺术品的构图和图像志(iconography)特色就成了更为广大的文化内容的征兆了。图像学就是试图去发现并解释这些征兆性的价值,这些价值艺术家往往并不知道,甚至与他打算表达的东西大相径庭(14)。
巴克迪莱、潘诺夫斯基等人虽然已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但艺术品仍然是关注的中心,对视觉文化广泛语境的探究只是为了更好地阐明对个人绘画或艺术家的理解。比如巴克迪莱逾越艺术的范围,去关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那些绘画领域富有的生产商与消费者的信仰、观念和价值等文化层面的内容,是为了达成对绘画作品更好的欣赏与理解。在这些视觉文化研究先驱者这里,艺术品仍然享有特权,是一种文化中比其他图像类型更为重要的表达。但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生产出来的影像遍布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在所谓“图像革命”的年代里,大多数形象散布于杂志摄影、广告栏、电影、电视以及其他大众生产和复制的技术,包括个人假日照片和更为常见的数码摄像,传统的艺术品被新兴的图像技术大量复制、改编,甚至戏仿、篡改,成为了大众媒介的“殖民”产品。我们业已“生活在由图像、视觉类像、脸谱、幻觉、拷贝、复制、模仿和幻想所宰控的文化中”(15)。如此一来,传统的艺术已不再是文化身份最重要的视觉表达形式。在此情势下,追随巴克迪莱、潘诺夫斯基等艺术史研究方法的视觉文化倡导者,认为有必要打破艺术史只限于研究那些“高雅”或“精英化”传统艺术的做法,转而认可日常生活领域几乎无所不在的形象,把这些视觉表达形式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由于形象“构成了迥异于印刷的一种媒体,一种以不同方式传播、以不同方式达到完美效果的媒体”(16),传统的艺术史学科就转变为跨学科的视觉文化研究。
对于视觉文化与艺术史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大体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是艺术史的一种合理延伸;第二种则认为,作为独立于艺术史的一个新聚焦点,它更适合于采用与数字化、虚拟化时代相关的视觉技术来进行研究;最后一种观点认为,视觉文化研究是对传统艺术史学科的威胁和自觉的挑战。”(17)这些观点集中表现了视觉文化研究的各种倾向。不管我们对上述观点是否赞成,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或多或少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相关联。
如果我们赞成第一种观点,那么,视觉文化和艺术史之间的差异是否只是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变化?但事实上,随着研究对象的拓展,通过现代视觉技术制作出来的大量图像或影像与传统图像艺术大不相同,因此在方法上显然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而必须吸收媒介学、传播学、符号学、哲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多种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传统艺术史,找到视觉文化研究的新对象和新方法,进而为创建一门新兴学科打下坚实基础。因此,视觉文化研究者只有形成与艺术史相区别的自觉意识,才能找到与现代视觉技术制作出来的图像相契合的研究方法,进而把视觉文化研究从艺术史中独立出来。
三、视觉文化与新艺术史
扫视一下视觉研究最先兴盛的欧陆和拉美地区就会发现,视觉文化课程更多地被设置在新媒介、符号学、哲学、视觉传播以及人类学等系科中。艾尔克斯(James Elkins)经过考察后指出,北美和英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视觉文化沿着他们熟悉的路线扩展,也就是说,从艺术史、文学和电影研究中衍生出来,而对于欧陆和拉美学者来说,视觉文化的主导性模型更多地衍生于符号学、视觉传播和哲学等。他进一步指出,视觉文化研究大抵存在着“三种谱系:在美国,视觉研究系从艺术史系中生长独立出来;在英国和东南亚,视觉研究更多地与文化研究相近;而在欧洲大陆,视觉研究与符号学和传播理论联接在一起”(18)。由此可见,视觉文化研究有艺术史、文化研究与传播学三种研究路径,分别关注视觉图像不同的属性与功能:艺术史取向关注图像的文化属性与功能,文化研究方法力图揭示图像的政治属性及其意识形态功效,至于图像的消费问题即其经济属性则是传播学研究思路的聚焦点。它们分别从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达成对图像全方位的扫视,令图像的本质特征和内涵得以彰显,并把观看图像变成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一个需要弄清楚的神秘之物,也就是去“展示看本身”(19)。
从艺术史传统衍生出来的视觉研究,也被称为“新艺术史”,这种发端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对传统艺术史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了自觉的反省。以英国艺术史家布列逊为代表,新艺术史批评瓦萨里以来的历史主义、进步论艺术史观,认为这种将艺术视为一个趋近完美的历程的“瓦萨里艺术模式”是机械论史观。同时,这种被布列逊称之为“普林尼—瓦萨里—贡布里希结构体系”的艺术模式,将艺术史研究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公元前600年到罗马帝国征服欧洲大陆之间的希腊艺术,以及公元1000年到1900年的西欧艺术这两个狭窄的历史时期,而且往往聚焦于前一时期的雕塑和后一时期的绘画,并将古典主义理想美的规范作为艺术史评判的唯一标准。贡布里希著名的“图式—矫正”理论是这种旧艺术史模式的主导性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所展现的艺术史就是“在新要求的压力之下,制像的传统的图式化程式逐渐得到矫正”的过程(20)。在这些艺术史家看来,艺术家尝试某种样式或图式,其目的是制造一种令人满意的传达视觉事实的表现方式;对照那些事实来检验图式,并对与事实不尽相符的图式做出某些调整,于是一种容量更大的图式、比以往更富表现力的视觉场被开拓了。这样一来,“相互联系的图式(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整个系列就形成了一个历史链……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外在于这个历史链的事物能够影响链索的内部发展和演变。而历史的更大领域——隐藏在链索本身后面的历史进程——只能通过外在性对后者产生影响”(21)。
显然,这种旧艺术史模式是非历史、非社会的。布列逊对此指出,在这种艺术规范中,图式基本上被看作一种视觉形体、一种格式塔、一种模板或模具,基本被假设为一种独有的光学上的结构,或者说,视觉再现的产物仅仅认为是光学的或仅仅是作用于视网膜的。这种将视觉排除在一切文化现象之外的做法,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错误。布列逊所倡导的新艺术史认为,视觉再现不是孤立的艺术玩家在与世隔绝的美学空间中熟练处理规范化形式的产物,而是作为社会和话语施动者的产物。因此,当主体观看时,他不仅见到了形式、光、色彩和光学结构,还有社会在大量的、复调结构层面上组构的意义。主体感觉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视觉场,还是一个存在高度微妙差别和被编码的环境。因此,新艺术史主张用意指来取代图式,要从光学转移到社会背景上来。这样一来,在视觉的基点上,应该确立的不是视网膜,而是社会的、历史的世界;不是“视觉的金字塔”,而是社会权力的结构;不是一个永恒的认知心理学的孤立主体,而是其成分不断为社会势力所影响的主体。视觉主体性作为一个被组成的空间,在其中是有一大群视觉代码混合着和碰撞着的(22)。实际上,新艺术史是想建立一门真正历史性的艺术史学科,它试图将绘画作为符号的艺术而非知觉的艺术来看待,由此揭示图像的社会性及其作为符号的现实。因此,这是政治、经济和意指活动之间相当复杂的互动模式。在布列逊看来,“一旦视觉是跟诠释而非知觉相关联,一旦艺术史又承认自身领域研究中的暂时性或不完备性,那么一门新的学科的基础就有可能,或者说,就被奠定下来了”(23)。
从某种意义上说,富有创造性、持怀疑和批判立场的新艺术史,不仅自身构成了视觉研究的家族谱系,而且凭借其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主要以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符号学为代表)上的多元和开放性,奠定了一门新的学科,令艺术史改头换面,同时对视觉研究的另外两条路径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艺术史与视觉研究处于一种交叉重叠关系,一方面视觉研究直接衍生于艺术史的转向,但它在兴盛崛起过程中又产生了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符号学等路径;另一方面受视觉研究新方法的影响,艺术史也发生了重要转型。虽然新艺术史仍然以图像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重心已发生了较大偏移。如果说传统艺术史侧重探究的是这些图像的形式、构图、色彩等审美内涵,那么,以巴克迪莱、潘诺夫斯基等人为先声、以布列逊为代表的新艺术史,已从一种关注形式和光的作用的解释理论转移到“一个充满着社会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多元性(plurality)和骚乱(commotion)的那种社会空间的叫嚷和吵闹中”(24)。新旧艺术史的一个根本差别在于对审美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对于旧艺术史家而言,审美通常指称关于感知美或丑的哲学观念,他们把美视为一个与判断力或主体性相分离的范畴,并相信在自然和艺术中可以发现纯粹的美,它是一个普遍的而不是只在特定文化或个体符号之中的特殊范畴。但新艺术史家不再持有美是寄寓在一个特定对象或图像之中的信念,也不再把美视为具有可被普遍接受的特性。他们认为区分哪些是美的和哪些不是美的不同标准是建立在趣味——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具有文化特定性的——基础之上(25)。这意味着,审美不再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一个普遍性范畴,而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它与审美主体所处的阶层、文化的背景、所受的教育以及身份等息息相关。在这样一种审美理念指导下,趣味的观念取代了普遍性审美概念,因而对艺术品的鉴赏往往被这样的问题所取代:为什么要欣赏这样的艺术品?这样的艺术品代表了一种怎样的趣味?而鉴赏主体这样的趣味又是如何通过社会和文化体制形成的?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我们在传统的审美活动中,往往以为观者对艺术图像的欣赏是一种“纯粹的凝视”,但在现实的观看中,任何观看的活动都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进行。在他看来,“纯粹的凝视”是艺术场域走向自主化的产物,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观看方式,是对大众的普通的观看习惯、艺术观念的拒绝,“纯粹的凝视暗含着同看待世界的一般态度的决裂,这种决裂给定了它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也是一种社会分离。加西特在这一点上是可信的:他认为系统地排斥所有那些‘人’的东西,即那些一般的、普通的——与出众或超凡脱俗相反的——一切,也就是‘寻常’之人在其‘寻常’生活中投入的诸种情欲、情绪及情感,这是由现代艺术造成的”(26)。这种建立在真正历史主义基础上的新艺术史,实际上跃出了传统艺术史研究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已转变成为对视觉图像文化内涵的分析。
这种带有浓厚社会学色彩的考察方式无疑与文化研究相通。它从跨学科立场出发,立足于对视觉文化现象进行意识形态剖析,具有实践性品格、政治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这种视觉研究的一个基本内核就是视觉性,“即组织看的行为的一整套的视界整体,包括看与被看的关系,图像或目光与主体位置的关系,以及观看者、被看者、视觉机器、空间、建制等的权力配置,等等”(27)。总而言之,就是对看的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性审视,从而揭示观者身份认同之中性别、阶级、文化和种族等权力纠葛与各种错综关系。传播学取向的视觉研究把视觉图像置入生产与消费的经济活动之中,把观者的心理品质与经济活动的商品属性结合起来。因此,这种视觉研究的重心在于利用视觉图像不同于印刷文字的特点来吸引受众,在以图像为主导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声音、文字等其他媒介形式对商品的形象进行炫目的展示,也就是最大可能地抓住受众的眼球,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这种对视像经济属性与功能的关注,其实也就是探讨如何促成图像意义和快感的实现,因此,从传播学和符号学角度来阐明视觉说服机制,是这种视觉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视觉研究上述的历史谱系我们不难看出,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已非文化的精英部分,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以及它们视觉表达的多种方式。这样一来,视觉文化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也包括其他种类的视觉形象,而与20世纪相关的视觉形象应该包括诸如电影、电视、广告以及图表设计、连环漫画册或摄影等(28)。在通达社会信仰和价值的方面,这些流行的视觉形象提供了与传统高雅艺术同样重要的线索,对于理解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与功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初步总结:所谓视觉文化,是一个主要研究艺术、媒介和日常生活中视像的文化建构的新领域,在那里,视觉图像是某种文化语境中意义得以生成的关键性要素(29)。这个初步的论断实际上与这样一个观念紧密相连,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
注释:
①(10)(12)(19)Nicholas Mirzoeff(ed.),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5,p.86,p.37,p.55,p.86.
②③(17)(29)Margaret Dikovitskaya,The Study of the Visual after the Cultural Turn,New York:The MIT Press,2005,p.2,pp.1-2,p.3,p.1.
④⑦⑨(11)(13)(28)Matthew Rampley(ed.),Exploring Visual Culture,Scotland: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p.5-6,p.7,p.10,p.11,pp.11-12,pp.12-13.
⑤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
⑥Gordon Lynch,Understanding The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pp.6-7.
⑧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14)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5)(16)W.J.T.Mitchell,Picture Theory,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2,p.1.
(18)James Elkins,Visual studies:A Skeptical Introduc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3,p.10.
(20)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第二版序言》,林夕等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21)(22)(23)(24)布列逊:《视觉与绘画·中文版序》,郭杨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第15页,第26页,第15页。
(25)Marita Sturken & Lisa Cartwright,Practices of Looking: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Oxford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8.
(26)布尔迪厄:《〈区分〉导言》,黄伟、郭于华译,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7页。
(27)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吴琼、杜予编《形象的修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