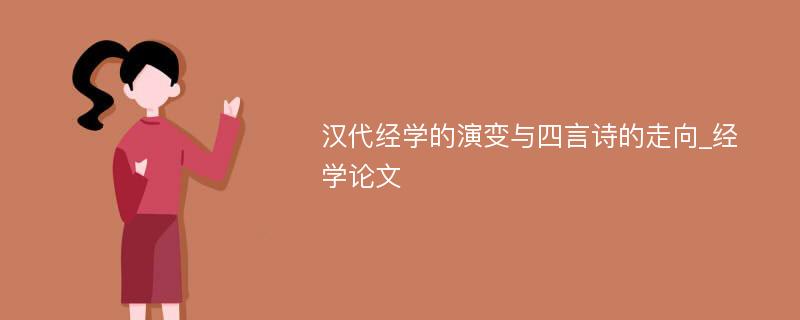
汉代经学的演变与四言诗的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汉代论文,走势论文,四言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123-04
汉初百余年的时段中,四言诗履经了一条看似风光无限而实则险象环生的尴尬历程。究其原因,除了五言诗的产生和赋体文学的强势兴起外,经学与文学的互动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这一点切入,既能发现汉代四言诗附庸于经学后的高雅形态,又能看到汉代四言诗因患“文学贫血症”而引发的边缘化现象,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
一、经学初创期的主流层面四言诗
从高祖到景帝年间,思想相对比较活跃,以黄老为主,以儒家为辅,处于一个兼收并蓄的开明期,儒家经学尚在发轫阶段。《史记·儒林传》记载:“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文帝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1](P2353)这段话表明,在汉承秦祚的最初六七十年间,经学在孝文帝时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总体上还处于初创期。对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将“经学流传时代”的下线划定在汉武帝之前,是比较合理的。言外之意,这个时期的经学和昌盛期的经学有显著区别,远未在政治文化上确立起它的话语权威。
与经学处于初创期相应,文学创作活动也呈现出相对自由的局面。汉初主流层面的四言诗,在赓续《诗经》四言诗传统的同时,亦兼有对楚地歌谣等艺术形式的吸收和借鉴。当时,上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及其贵妃,下到刘氏宗室成员及担任官职的文人,都直接参与了四言诗的创作。创作主体的多样性与创作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相伴随。
汉初主流层面的四言诗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种:
首先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诗。如《安世房中歌》中的十三首四言祭祀诗歌,就继承了《诗经》中《雅》和《颂》的传统。如曰:“大孝备矣,休德昭清。”[2](P145)让人直接联想到《诗经·大雅·卷阿》中的诗句:“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3](P281)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如此高规格的庙堂之乐,也并非一味地模仿《诗经》之《雅》、《颂》,而是有新的艺术元素融入于其中。如“都荔遂芳,窗窊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2](P146)。在这首诗里,有都荔、桂花、日月、羽旌诸多物象,宛若《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中所描绘的那个缤纷多彩的世界。
其次,表达个体情感的诗作。如刘邦的《鸿鹄》,抒发的是开国天子的无可奈何之情,是失望心态的真实呈现。刘邦在文学史上一共只流传下两首诗作,除了这首外,另一首是《大风歌》,采用的是楚辞体。史载刘邦喜好楚声,那么为什么如此青睐楚声的一位君王会选择用四言诗来写《鸿鹄》呢?对此,有人不顾《史记》等文献以四言体形式记载这一诗歌的事实,认为这首诗本身就是含有兮字的楚声,这是不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这首诗的内容上找答案。其诗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1](P1593)在这首诗里,刘邦一方面想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这种情感的表达,楚声和四言诗在功能上都具备。但更重要的是刘邦又需借此来表达自己不能更立太子的意志,劝诫戚夫人不宜纠缠于此事,可以说温情之余是一种残酷的命令。这就是以抒情见长的楚声所不具备的,因而必须借助于典重庄严的四言诗来表达。这种内容对形式的选择范式在此处仅是初露端倪,在经学昌盛期有更进一步的体现。
再次,反映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四言诗。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都在思想方面承继了《诗经》的讽谏传统,被刘勰的《明诗》篇评为:“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4](P58)韦孟的诗作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因子,如在篇章结构上明显变长,且摒弃了《诗经》回环复沓的表现手法。明代徐师曾评价云:“是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自互文,以致反复嗟叹咏歌之趣者居多。迨汉韦孟制长篇,而古诗之体稍变矣。”[5](P99)
二、经学昌盛期四言诗文人的双重身份和地理分布
从汉武帝到东汉明、章帝期间,一般认为是两汉经学的昌盛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6](P41)经学的话语效力开始迎来它如日中天的鼎盛期。对此,侯外庐先生指出:“学术既然定于一尊,经学遂成了利禄的捷径,学术的正宗与政权的正统互相利用,搅在一起了。”[7](P313)当治经学成为人们步入仕途和攫取利禄的手段和工具时,它的影响就会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与之相应,文学创作活动也表现出“世道既变,文必因之”的发展规律。具体到这一时期的四言诗上,呈现出经学化程度高、抒情成分严重缺失的特征。那么,这种特征是如何形成和体现的呢?
首先,这种作品特征的成型导源于经学文化氛围影响下的作家群体。在宗经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体,是这一时期主流四言诗的创作者与影响源。如韦玄成、刘向、扬雄、班固等多位著名的汉代四言诗作家都和经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一方面是声名卓著的文学家,另一方面又是出类拔萃的经学家。如韦玄成,属于诗经中的“鲁诗派”[8](P212),有着厚重的家学渊源。其先祖为治鲁诗的韦孟,是楚元王傅,其父韦贤亦因治鲁诗闻名而被昭帝任命为“鲁诗”博士。像这样世代奉守经学且获高官厚禄的家族,在两汉全盛时期成为了一种思想和价值的风向标,邹鲁之地的后人就为之谚云:“遗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2](P238)
其次,从地理分布上看,这一时期主流四言诗的创作者大多都是出自经学昌明之地。两汉经学昌明的地域大致分布在今天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古多属中原、燕赵之地。在兼有经师和文人双重角色的作者中,韦玄成是邹人(今属山东),焦延寿是梁人(今属河南开封),刘向、班固生于西汉都城长安,都是出自经学昌明之地。只有扬雄出自蜀地。就经学昌盛期的作者地望而言,可以说浸染上了浓厚的经学色彩。
三、经学昌盛期主流层面四言诗的特征
从文学创作活动的另一端,即作品的内容与风格来看,这个时期的主流四言诗整体上与经学紧密相连,抒情作品极少,风格典雅,继承了雅颂的传统,门类繁多而取向归附于经学。以其和经学关系的紧密程度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直接为解经而作的《焦氏易林》,该书四千多则诗歌几乎全部由四言构成。对于《焦氏易林》的归属问题,在学术界有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以宋人黄伯思,明人杨慎、钟惺、谭元春,清人王士禛,近人钱钟书、陈良运等为代表,认为其是优秀的四言诗篇。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写道:“盖《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蠖焉。”[9](P813)一派以清人冯班、章学诚,近人逯钦立等为代表,拒绝将这类作品视为四言诗。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中曰:“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10](P79)时至今日,这种争论还远未停止。相较之下,占主流意见的是后者,这就使得《焦氏易林》常常脱离出四言诗研究者的视野,遭遇到归属难定的尴尬:一方面沦为经学的附属品,成为解经之作,实现了意义上的经学化;另一方面,又因其具有占卜的属性,从诗的领域中被剥离开去,排除在汉代的四言诗之外。
二是与弘扬经学相关联的四言诗作,以汉武帝时期祭祀型四言诗歌和班固的《明堂》、《辟雍》、《灵堂》等为代表。在经学至上的笼罩下,这类诗作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突出四言诗体的权威性,使四言诗形式和内容上的典雅厚重同时得到彰显。通过对比同类题材的诗体选择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点。试以汉武帝时的十九首《郊祀歌》为例,其中六首为三言,依次是:《练时日》、《華爗爗》、《五神》、《朝陇首》、《象载瑜》、《赤蛟》;五首为杂言,依次是:《天地》、《日出入》、《天马》、《天门》、《宝鼎歌》;八首为四言,依次是:《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太元》、《芝房歌》、《后皇》。相较之下,于诗体的选择上,在庄重典雅的祭祀场合,四言诗较之其他诗体明显居于优势。从内容上看,八首四言诗的祭祀对象分别为《帝临》中的黄帝;《青阳》中的青帝,配春天;《朱明》中的赤帝,配夏天;《西颢》中的白帝,配秋天;《玄冥》中的玄帝,配冬天;以及《惟太元》中的太一神。只有一首例外,即《芝房歌》,为祭祀祥瑞之物灵芝而作。而三言与杂言的祭祀对象,《赤蛟》中的龙、《宝鼎歌》中的宝鼎等,相对来说缺乏神圣性。可见,当祭祀至尊的帝王和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天神时,运用的都是四言诗体,既弘扬了汉代经学的阴阳五行观,又彰显了四言诗体的权威性。
三是思想内容方面与经学相契合的四言诗,以韦玄成的《自劾诗》和《戒子孙》诗为代表。作品多秉承《诗经》“二雅”的诗教宗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将希望寄托于明王贤君等。如在《戒子孙》诗中直接呼吁:“嗟我后人,命其靡常。靖享尔位,瞻仰靡荒。慎尔会同,戒尔车服。无惰尔仪,以保尔域。尔无我视,不慎不整。我之此复,惟禄之幸。於戏后人,惟肃惟栗。无忝显祖,以蕃汉室。”[2](P114-115)这种呼吁的背后是对敦厚的诗教传统的一种虔诚式承继,对此,明人许学夷一针见血地指出:“雅流而为汉韦孟、韦玄成。”[11](P44)又说:“韦孟四言《讽谏》,韦玄成《自劾》等诗,其体全出大雅。”[11](P55)与此一脉相承的还有傅毅的《迪志诗》,其以“惧我世烈,自兹以坠”为己任,想着奋发成才。这跟韦玄成的《戒子孙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体上仍不失为表达经学思想的典范。诚如胡应麟所评:“唐山后东平《武德歌》,韦孟后傅毅《励志诗》,皆典实不浮,差可绍响。然高古浑噩,大弗如也。”[12](P8)
经学昌盛期还出现一大批无诗之名而实为四言诗的作品,主要有以下四类:
一是以“颂”名称出现的四言诗。颂在《毛诗序》中表述为:“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3](P272)刘勰在《颂赞》篇亦曰:“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4](P84)两者都阐明“颂”具有美盛德的功能。这类作品有扬雄的《赵充国颂》、史孝山的《出师颂》、《列女传》中的四言颂诗等,均和颂扬有密切的联系。如《有虞二妃》之颂:“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14](P4)极力称赞两位传主的美好品德。四言颂诗,庄重典雅,韵律和谐,和《雅》、《颂》的歌功颂德传统联系紧密,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篇总结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4](P30)另外,刘勰在《颂赞》篇中亦指出汉代的其他“颂”在创作上也大都借鉴《诗经》:“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駉》、《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荣,典章一也。”[4](P86)刘勰提到的这些以颂命名的作品不全是四言诗,但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汉代颂诗的经学化特征都是非常明显的。
二是以“铭”形式出现的四言诗。刘勰在《铭箴》篇中曰:“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4](P101)铭的用途或在于给人以警戒,或是宣扬美好的德行,四言诗的体制往往以其雅正典重与铭的思想内容相契合。如班固的《高祖泗水亭碑铭》,崔駰的《车右铭》、《车左铭》、《车后铭》等。
三是以“箴”名称出现的四言诗。刘勰在《铭箴》篇中写道:“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4](P104)这类四言诗和上面的铭类诗作虽在名称上有区别,但实际功用是一致的。如扬雄的《十二州箴》、《百官箴》,崔駰、胡广的《百官箴》等,都以四言的形式对担当相应职务的官员加以警戒,勉励他们恪尽职守。
四是作为文章总结、断语出现的赞类四言诗。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篇》曰:“赞者,明也,助也。夕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史迁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4](P88)这表明赞本是一种祭祀时的赞誉之歌。发展到汉代,这类赞辞往往不是独立的四言诗,而是依附于其他文体而存在,并且多出现在文章或著作的最后。于史传文学作品中比较常见。代表作如班固的《叙传》篇,相当于《后汉书》中的赞,其中为每篇的写作意图作总结时,都采用了四言韵语的形式,如《叙平纪第十二》云:“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丧我四海。”[15](P4240)四言结构简短而精要,起到总结和评价的功能,彰显了四言诗体的权威性。所以刘勰总结这一文体为:“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于四字之句。”[4](P89)
除去以上这七类四言诗外,另还有一些四言诗错杂在辞赋体和碑、诔等应用型作品中,种类繁多,此不赘述。就上述几种而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和经学保持了一致性,刘勰《宗经》篇称:“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4](P30)这些名称各异的四言诗都具有浓厚的经学化趋向。另外,就数量和质量上看,经学昌盛期的文人四言诗创作,虽在数量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在质量上能被后人所认可的却寥寥无几。问题的症结在于:受经学氛围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四言诗走上了一条内容选择形式、形式完全依附于内容的僵化道路。四言诗体仿佛是一个坚硬的外壳,只能把经学作为内核。而经学对于诗体的选择,则是非四言莫属。思想内容上的经学化,使得四言诗体俨然成了一具生硬的木偶,偏离了“诗缘情”的轨道,从而导致抒情言志方面的整体匮乏,语言文字古奥,因此文学性大为减弱。仍以武帝的《郊祀歌》为例来看,其由于雅颂化、经学化程度加强,变得“多侈陈乐舞声歌之盛,文字亦多古奥难通”[16](P46)。如《朱明》篇:“朱明盛长,甫与万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诎。敷华就实,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尝。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2](P148-149)这些文字多的是典奥,少的是生气。萧涤非先生评价云:“《郊祀歌》大部皆无文学价值,其对于后世之影响,亦只限于贵族乐章。”[16](P47)这种文学观赏性的降低,最终使得四言诗遭遇到了文体边缘化的尴尬。
四、经学衰落期主流层面的四言诗
从东汉安帝到灵帝末年,汉代社会由盛转衰,经学也进入衰落期。正如皮锡瑞所论:“至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讲。……是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6](P114)与经学的由盛入衰密切相关,各种文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新变。文人四言诗开始退去经学的外衣,出现了带有向西汉初期回归的新气象。据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这个阶段所作并流传下来的文人四言诗有二十二首,其中既有与经学紧密联系的四言诗,如李尤的《井铭》等,同时,言志抒情的诗歌呈现出激增的状况。这个阶段的诗歌总体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气象。
首先是抒写个人情怀的四言诗涌现,以张衡、朱穆、秦嘉等为代表。这类诗作大都能一反经学昌盛期四言诗的僵硬面容,写得清丽婉转、轻快活泼。如张衡的诗《歌》之一:“天地烟煴,百卉含蘤。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实多。”[2](P47)全诗有比兴的手法,有花、鹤、雎鸠等意象,抒发的是缠绵的情思。另一首《怨诗》,同样写得清丽纯真、脉脉情深,完全摆脱了经学昌盛期那种古板生硬的程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赞叹道:“张衡《怨》篇,清典可味。”[4](P58)秦嘉的《述婚诗》与《赠妇诗》,则在诗歌题材上脱离了经学的樊篱,以四言诗抒写婚姻爱情,为四言诗开创了一种新局面。
其次是品评个人才华德行之作的兴起,以桓麟、应季先、蔡邕、刘珍等为代表。这种题材四言诗的出现和经学的衰落以及“经学家法的废弛”[17](P146)密不可分。人们重视人物品评,赞扬人的个性才华,或以此来为自己延誉,或以此来获取仕途晋升。这类诗作有时以赠答等形式出现,如桓麟的《答客诗》:“邈矣甘罗,超等绝伦。伊彼杨乌,命世称贤。嗟予蠢弱,殊才伟年。仰惭二子,俯愧过言。”[2](P184)有时以碑文的形式出现,如蔡邕的《酸枣令刘熊碑诗》:“清和穆铄,实惟乾巛。惟岳降灵,笃生我君。服骨睿圣,允钟厥醇。诞生歧嶷,言协典坟。懿德震耀,孝行通神。”[2](P194)这类品评人物题材的作品开启了魏晋以诗品人的先风。
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文人四言诗歌选材开始与经学相疏离,迎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种情况和西汉早期的情况有形似之处,带有某种历史回归的性质。
五、两汉民间层面的四言诗
民间四言诗是下层人民智慧的结晶,以汉末最多。
从内容上看,民间歌谣很少和经学发生直接的联系,它们多是直接对下层社会生活的反映,保持了民间歌谣直指坊间的传统。从整体上看,在经学衰落期,创作上出现了一拨小高潮,有对忠贞贤良的歌颂,如《顺阳吏民为刘陶歌》。有对社会黑暗的直接控诉,如《汉末江淮间童谣》:“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于金。”[2](P226-227)亦有对朝廷迫害忠良的谴责,如《蒋横遘祸时童谣》:“君用谗慝,忠烈是殛。鬼怨神怒,妖气充塞。”[2](P229)这类作品总体上虽然文学成就不高,语言接近于直白,但体现了“诗缘情”的本质,在经学日益衰落时期,丰富了汉代四言诗的内容。
两汉时期的四言诗演变和经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经学的起伏盛衰,都在四言诗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但就四言诗本身的走势而言,则与经学的发展呈现反比例关系。经学越是昌明,四言诗就越是僵化;经学越是衰落,四言诗则越是清新活泼。四言诗与经学的联系越是紧密,四言诗就越缺少自由和生机;而一旦与经学疏离,反倒是这种诗体得以健康发展的契机。四言诗与经学的结缘,在意识形态层面使这种诗体成为主流话语的组成部分,在文学层面则使得四言诗边缘化。四言诗与经学脱钩后,不再是主流话语的表达工具,在文学上却是向自身回归。
收稿日期:2012-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