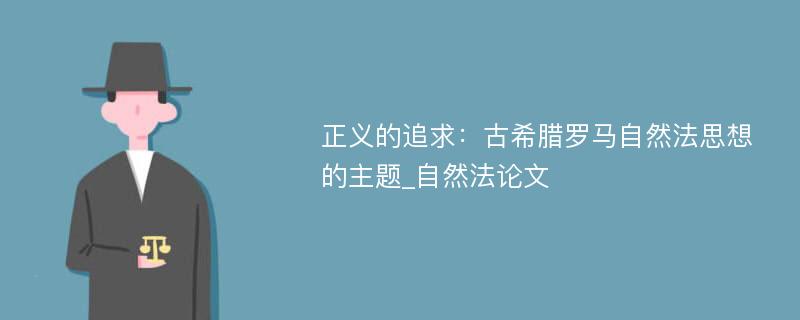
追寻正义:古希腊罗马自然法思想的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自然法论文,罗马论文,正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019-07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法的观念从萌芽到最终形成,虽几经嬗变,对正义的追寻始终是其永恒的主题。这一论域代表着人类心灵的一种固有期望,也即希求一种超越人类法律和权威之上并构成其最终依据的正义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先于经验世界的先验法律秩序,它们提供了验证实在法“正当性”的标准和尺度,探讨实在法是否具有法的资格。但是,由于自然法学家们都是将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渗透到正义观念中,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有着极为复杂的理论谱系。基于此,本文试对古希腊罗马自然法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以追踪他们探寻正义的思想轨迹。
一、从神话到逻各斯的思维革命
“自然法的学说与哲学一样古老。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好奇是哲学的开端一样,自然法学说的开端也是好奇。”①正是基于他们的好奇,希腊人开始了自己的哲学探索,进而将之据为自己的理性思维而与他们的先辈所营造的神话氛围相对抗,由此引发了一场从神话到哲学的革命,而自然法观念的萌生也就脱胎于这一历程。
与其他民族一样,从古希腊人那里,我们也能看到其道德规范和法律秩序的神圣源头。②在希腊神话中,我们能够感知到初始时期希腊人的政治、法律观念:宇宙中存在一种超自然和人类的法律,该法律就是神的秩序和正义,诸神正是藉此规定着自然和人类的秩序。虽然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神的法律是人的任何法令所不能改变的,但这种将“神之法”和“人之法”相对立的二元法律观,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人们从自然秩序中去挖掘人类社会的生活秩序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不过,我们却并不能由此就认为在希腊神话中形成了自然法的观念。正如美国学者欧文所言,“荷马的世界观并不包括自然的或神圣的规律,这些规律意指特定的预测(例如,如果有一场自然灾害,那就是某位神衹在惩罚你)。”③在《荷马史诗》中,希腊诸神并不代表自然,也不是自然的神化,自然只是诸神控制人的意志的体现,其本身并不构成人类应当遵循的最高法则。
人类自己颁布的法令的根基,只是存在于人格化神的意志中,这种神话学的法律图景,最终将古希腊人置于与自身之外的自然事件相对立的无助境地中,④这就使得他们开始惊诧于自然本身的秩序与法则,并试图将其引入人类社会,从而完成了“从神话(Mythos)到逻各斯(Logos)”的思维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哲学开始尝试着揭开笼罩在人们理性之上的神话面纱,要求不再通过超验的法则去解释经验世界。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的好奇,希腊人很快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在研究政治之前先研究自然。人们不再是想当然地将法的权威安身于“一个主神的威力、他的个人统治或‘王权’之上,而是建立在宇宙的内在规律和分配法则之上”。⑤
在最初的自然哲学家那里,“自然(physis)”一词乃是从事物的“所是”上加以理解的,它首要的是与Nomos相对立的,后者指涉的是特殊的法规、习俗、约定、同意以及权威的意见等。⑥这种二元思维方式乃是新的法律图景的主要特征,并且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得到了完整的表达。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⑦它并不为任何神或人所创造,而是通过确定秩序的理性,也即逻各斯所支配而发生着。在此,自然就在哲学上第一次与法则联系了起来。“‘自然’的最简单和最古远的意义,正就是从作为一条原则的表现的角度来看的物质宇宙。”⑧宇宙本身就存在着一条理性和自然之道,正是这条自然之道孕育着人类的法律秩序。因此,人类道德行为的初始规范,就是要让个人和社会的生活合乎并服从宇宙的一般法则。基于这样的认识,赫拉克利特指出,人的一切法律都是以神圣的、足以支持一切的唯一自然法则为基础,它们最终都只是人类为了实现这一神圣法则而做出的努力。人的“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⑨为此,赫拉克利特主张,既然城邦的法律只不过是自然的神圣法则的具体体现,人民就不应抵制自己城邦的法律,对城邦法律的遵守就是最好地遵守了自然的法则。“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像为城垣而战斗一样。”⑩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自然”和“习俗”的关系乃是其哲学中“一”和“多”的问题在政治、伦理领域的表现。在城邦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中(而非之外),隐藏着一种关于自然的永恒法则,这一法则使得各种人定法彼此和谐一致。这样,希腊神话思维中的自然和习俗之间的模糊界限就得到了第一次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表明了自然法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首次出现。“经由赫拉克利特……自然法作为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法则,而所有人法均由其获得力量的观念,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1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赫拉克利特对自然和习俗给予了明确的区分,但二者在他那里乃是处于永恒的和谐而非对立之中。社会秩序和自然的法则被认为是一体的,人类的法律因其为自然的法则所孕育而拥有最高的权威,应当为所有人所遵守。这一思想后来被毕达哥拉斯应用于数的原则,他从几何学的比例与和谐中发现了正义的基础,而这就为柏拉图关于城邦与正义的理论铺设了道路。
然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自然与习俗处于永恒的和谐中”这一思想虽然强调了人类法律的价值及其约束力,但希腊神话中将人类法和正义加以区分的问题并未受到重视。如果所有的人间法律都被认为是正义的而必须加以服从,这将给经验的政治运作带来困惑。“当赫拉克利特声称所有的法律都是由一个神圣规律所孕育时,他假设这样神圣的规律公正。但是难以同意所有的成文法都是公正的,所以,也难以同意赫拉克利特对法律不加批判的支持。他可能将成文法和自然规律相区分(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而将自然规律与神的正义等同起来;但是就更加难以声称每一成文法都是依据自然规律的,或者所有的成文法都应当接受。”(12)
二、自然与习俗的二元对立及其困境
赫拉克利特关于自然与习俗处于永恒的和谐而非对立的思想,在公元前5世纪首先遭到了希腊悲剧作家的挑战。在剧作家那里,宇宙间存在着一个由“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律条”,(13)这一律条体现着永恒的正义,并引领人们去追寻着正义,人类自己制定的法律都应符合自然的法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定法就如赫拉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都是由自然的神圣规律或法则所孕育而天然具有正义性。随着人类自身立法活动的开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法律和规范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并开始意识到为城邦人民所共同拥有的法律和道德制度的多样性,以及自己城邦与临近城邦或部落制度上明显的差异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变化,人们开始反思:我们的法律和习俗是否都只是人造的,并因而都只是人为的和任意的?如果是,那我们是否具有遵守它们的自然义务?与此同时,那些将自然看作是“最终的统一原则”的人们也会问道:在这些多样性的法律和习俗之上是否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法律?我们能否在事实上将那些彼此冲突的法律规范的依据都归之为永恒的自然法则?
上述这些问题得到了智者学派的回应,并被归之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是否有任何事情每时每地都是正当的?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智者学派遵循了自然哲学家之前关于事物的恒的性质与事物的表象二者间所作的对比,(14)以此类推,当他们将目光从外在的对象投向人自身、进而追问:“从对诸神的礼拜直到在自由人与奴隶,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差别,所有这些制度和传统风俗习惯是否以自然(physis)为基础?并因此就是神圣不可侵犯,还是能够变更和改进?”(15)这样,他们就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挑明了“自然”(本性)与“习俗”(法律)之间的对立,并使这一对立最终构成雅典政治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结构”。正如柏拉图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在智者学派那里,“真实的和天然可敬的事物是一回事,按习俗可敬的事物是另一回事,至于正义,根本不存在绝对真实和自然的正义”。(16)这样,“自然”与“法律和习俗”就无法简单地划上等号。
在智者们的眼中,人定的法律并不是依据永恒而不可改变的神授命令、或者是依据某种永恒的法则而颁布的,它完全是一种人为创造的或由参与者共同约定的东西,而且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而改变,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与自然的法则有着本质的差别。“法律的规则是依据契约制定的,自然的规则却是自然而然产生的。”(17)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智者学派内部对自然与习俗二者的关系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形成了颇不一致的意见。
立足于“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原则,以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为代表的智者们赋予“自然”以新的含义。在他们那里,自然不再是指宇宙或逻各斯所揭示的给予人类的永恒自然秩序,而是指作为自然的人的本性或自然状态。法律的意义就在于,它将人引入某种正确的生活方式,从而把人从与野兽无别的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国家设立的法律是古代优秀立法家的发明,法律迫使公民依法统治和被统治,无论谁逾越了界限,法律就实施惩罚。”(18)由此,他们否认自然法的存在,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着规范人类政治生活的自然正义,单是人定的法律或习俗就能构成正义的标准,法律较之自然具有更高的地位。(19)
与之相反,另外一些智者尽管也将自然归之于人性,但他们从现实的城邦法律中认识到,人定法仅仅是立法者的技艺和习俗的产物,具有易变性和暂时性的特征,因而缺乏使人普遍服从的自然效力。这样,在成文的城邦法律之上,还应存在着某些不成文的自然法,这些法是人依据自然(本性)的要求而自由规定着的法律,它本身构成自然正义的基础,因而对所有的人都有效。智者西庇亚对雅典的民众这样说过:“先生们,我把你们都当作我的亲友和同胞,这是根据本性来说的,而非依据习俗。依据本性,那么同类相聚。但习俗是人类的僭主,会对本性施加暴力。”(20)通过对自然的诉求,西庇亚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彰显了一种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对他来说,现有的民主政体所主张的平等太过有限,因为它仅仅对那些有着平等公民权和来自同一城邦的自由民有效,而他所要做的就是要根据自然,也即人的本性将这种平等和血缘关系扩展到全人类。显然,在他这里,“本性(自然)”被赋予了高于“习俗(法律)”的地位,正义并不存在于人类习俗的道德和法律之中,而是存在于由自然推导出来的人性之中。由此,自然法不再是自然哲学家那里的非伦理形式,而是开始“发展出了道德的维度”。(21)
应当看到,尽管智者学派对待自然法和人定法的态度迥异,但他们关于自然法和人定法相对立的思维路径,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永远加以思考的问题:法的正当性。正如文德尔班所说:“在智者学派以前,无一人曾想到过检验一下法律,问一问法律自称的合法权力究竟基于什么。”(22)在寻求对自然的人性解释的同时,智者们也寻求着对法律的自然解释,自然正义既是自由、平等的法律原则的根源,同时又被看成是审视和抨击现有城邦法律的依据,这就对后世自然法学说的成熟有着重大的影响。
但是,挑明“自然”与“习俗”或“法律”之间的对立,对于那些旨趣在于辩论技巧(23)和现实批判的智者们来说,无疑存在着相当的危险。一方面,将正义同人定法统一起来,认为正义体现在人类制定的法律之中,进而否认世界上存在一个先验的自然法与自然正义,“这种观点意味着,除了人为的法律或惯例所规定的以外,人不能诉诸更高的东西”。(24)如果正义等同于人定法,那么正义最终就只能是根源于立法者的意志,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恪守城邦的法律或正义并不必然有益于被统治者,甚至还会有害他们。显然,这与智者们自己最初的出发点是相违背的。与此同时,将法只是看作由人们协商一致所形成的实证的人法,这种法律实证主义(25)的观点必然会带来在现实中法的相对主义。正义完全成了一种相对的东西,是相对于自己利益而存在的,并不存在超乎利益之外的正义。这样,“正义之事”就会因社会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正义的生活方式不再被看成是“正当的”或“善的”生活方式,也即人们所追寻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非其自然正当。(26)
另一方面,将正义的根据归之为自然,而认为人定法仅仅是某种相互保证的约定俗成,与正义并不相干,这一思想固然表达了智者们以自然法作范本为人类树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秩序,从而得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最终却往往是事与愿违。就自然而论,人应当是平等的,家世与财富与之并不关涉,因此,城邦理应建立在人类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与此同时,智者们又看到,此强彼弱正是自然状态中常见的现象。因此,依据自然就合乎逻辑地演化为依据强力,自然的正义被理解为“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和强者的利益”,而“法是由弱者、大多数人制订的,用来约束强者、‘最优异者’,阻挠最适宜的人取得东西:因此违反了正义的原则。自然权利是强者的权利”。(27)显然,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的生活远非一种“善”或“好”的生活,对于一个城邦社会来说,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权利对公民理应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在智者学派那里,自然与习俗的绝对对立,最终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并由此引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困境,这一点很快就为苏格拉底所觉察。与智者们相同,苏格拉底将一种关于人的本性的理性学说看成是其哲学理论的必要前提,但智者们的基本思想和立场却是他所不能认同的。对于父母之爱、恋人之爱、朋友之爱,我们到底是将其看成是合乎人的自然本性还是理解为只是一种习俗?显然,无论是哪一派智者,其答案要么是消解善和道德的观念,要么就是引导人们对城邦法律的质疑。基于此,苏格拉底认为,智者们从人的本性出发展开的自然与习俗的对立仅仅是提供了产生自然法的必要条件。自然法得以出现,还必须对法律和美德的关系加以澄清,也即要探询: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与人性是吻合因而对人而言是善的”?(28)
三、正义的追寻与自然法的奠基
一种善的(或好的)政治生活如何可能?在苏格拉底看来,这就必须将智者们那里相对立的“自然”与“习俗”重新统一起来。在哲人那里,好的生活方式所依据的“不是习俗,而是自然”,(29)它要求走出“洞穴”,超越人类生活的政治、法律层面,使政治服从于德性。透过“美德就是知识”这一命题,苏格拉底揭示了诸如正义、虔诚、善等可以被认知的客观政治价值的存在。但是,对于一个现实的城邦而言,好的生活方式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哲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言说”或对城邦法律的单纯批判,更为重要的是哲人要下降到“洞穴”中,以期对民众的生活产生影响。“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与城邦生活相联系的;当它对城邦生活作出超越的时候,它也是以城邦作为先决前提的。”(30)这就要求哲人必须将自己当作一个公民来看待城邦,“把人看成完全沐浴在政治生活中”。(31)为了抵制智者学派的批评,苏格拉底将正义理解为“善在和谐着的城邦中的实现”,进而使城邦法律的价值得到应有的尊重。(32)合法性与正义被理解为同一的事情,苏格拉底对自然法理念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通过哲人的“上升”和“下降”,“自然的”和“习俗的”重新得到了统一,善是至上的、永恒的理念,而城邦的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一善的理念。
一如其师,柏拉图全部学说所指向的亦是智者学派及其对世俗城邦具有破坏性的批评。对柏拉图来说,最值得我们去追问的就是善在城邦中的实现,也即是“正义”。与智者学派不同,在柏拉图那里,个体的自由并不居于中心的位置,“一个人不可能去实现不仅无条件实现、而且无法描绘蓝图的事情”。(33)个体唯有通过分享并参与到整体性的自然正当中,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34)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提出,城邦的目的并不是所谓的“保障人们相互抗衡的权利”,抑或为某人或某阶层谋求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这样,依据“自然”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就不仅是智慧的,而且是正义的。正义并不是超越城邦之外,而是安居于城邦之中。因此,要寻求正义,我们所要做的就不是将自然和习俗对立起来,而是要去探寻隐藏于城邦的习俗和法律之中“永恒的理念的法”,并根据这一理念的法去提升习俗和城邦的法律,使其达到对理念的摹仿,从而变得高贵起来。而对于哲人来说,这就是要以正义为神圣基础,通过哲人对民众的教育,让所有成员理解其法律精神,从而将他们提升到一个完美人性的高度。(35)
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也反对智者学派关于自然与习俗的绝对对立,并将其斥之为只是一种修辞上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承认,自然和习俗在事实上是可以区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将正义归之为自然,或者归之为习俗,相反,正义中“还是有些东西是出于自然,有些东西不是出于自然”。(36)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然的正义和习俗的正义,并对二者的关系作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诠释。自然的正义对任何人都具有同等效力,并不取决于人们承认与否;而习俗的正义则产生于多样的现实生活中,它起初并不确定,但一旦立法者颁布了的某种法律,其便具有确定的内容。依据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重新诉诸“自然”,以扭转整个社会的失范。通过将柏拉图的“理念”与自然概念联系起来,他提出,由立法者所颁布的实证法律体系,虽然并不具备苏格拉底那里的绝对有效性,但这种法律上的不完备性是完全可以“借助于实体性正义、通过自然法的内容被克服”。(37)与此同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显然是自然的产物,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38)因此,并不存在超越城邦之外的人的目标,城邦的法律本身就合乎自然的正义和法则。自然的法则并不是作为批判城邦现有法律的根据而提出的,它恰恰是要证明现有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由此,我们看到,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正义”为中心论题的自然法理论,法律和自然都得到了理性的定位,并被认为具有更多的同质性。在智者学派那里自然与习俗的绝对对立被重新统一了起来,城邦恢复了固有的尊严,正义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个体的权利,而是整个城邦的幸福。正如莫里森所指出的,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法“并不意味着自然权利,而是意味着自然的功能、目的和义务”,(39)在此之下,智者们“免于法律的自由”重新为“法律统治下的自由”所取代,单纯个人的自然权利不再认为有其自足性,而是认为必须首先履行一个好的公民的自然义务,也即通过“恰如其分”地履行对整体意义上的城邦的自然义务才能获其正当性。
四、普遍性观念的兴起与自然法的完备形态
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学生亚历山大通过武力摧毁了城邦,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从此以后,人们不再能以一个城邦的公民自视,而必须开始思考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意义。“亚历山大之后,说人是政治动物,不再意味着人与城邦的关系,仅仅意味着一个个体。反之,谈到一个个体,又意味着人也是普遍的。无论个体有什么特征,都肯定地属于作为一个一般物种的人类。”(40)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改变使得人们有必要将城邦的政治价值重塑为适合于世界性的政治共同体,而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观念正是适应这种变化而产生的。
从一种泛神论的宇宙观出发,斯多葛学派主张,宇宙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逻各斯”、“世界理性”、“宇宙灵魂”的存在。此“逻各斯”不仅是普遍的法则,同时也是构成万物的原质。人类之理性乃是受此普遍法则的支配,构成自然秩序中和谐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自然、理性和神被认为是一回事:法律的普遍性被理解为是出于广义的自然,人因其理性而同神有着独一无二的关系,而判断一条法律是否符合自然的表尊就在于其是否获得了理性的同意。(41)
由此,在斯多葛学派那里,所谓自然法,“简单来说,就是‘寻求在我们之中的自然理性并在行为中予以表现’。”(42)人依照自己的理性而生活,就是要在生活中顺从于自然,服从永恒世界的律法,这是每个人不容推辞的责任所在。对此,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里西普给予了经典的揭示:“主要的善就是以一种顺从自然的方式生活,这意思就是顺从一个人自己的本性和顺从普遍的本性;不做人类的共同法律惯常禁止的事情,那共同法律与普及万物的正确理性是同一的。”(43)自然被认为是控制着包括众神在内的所有受造物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法则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以人类整体的一种秩序、一种普遍的伦理规范的面目出现。
普遍性论证的平等观念使得自然法概念在斯多葛学派那里获得了完备的形态,并通过西塞罗将之转移至法和国家的具体现实中而真正展现其重要地位。(44)西塞罗对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概念作了创造性的引介。他指出:“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符合的正确理性,它是普遍适用、不变和永存的,它以其指令召唤履行义务,以其戒律防止作恶。……改变这种法律为上帝所禁止,部分废除它并不允许,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取消它。我们也不可以经由元老院和人民而免除我们对其的义务。”(45)在这里,自然法不只是与个人的正当联系起来,而且还与社会和国家的正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能力知道法律,只要他或她合乎自然地生活。因此,即便是对统治者而言,自然法也有其约束力,我们能根据它来区分人所订立的善法与恶法。基于自然法的目的是自然的正义,人定法的目的也必然是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谋取正义和安全。
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对罗马万民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与早期适用于罗马公民的市民法相比,万民法所体现的理念就是全体人类都具备同样的、放之天下皆准的自然理性。正如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所指出的:“根据自然原因在一切人当中制定的法为所有民众共同体共同遵守,并且称为万民法,就像是一切民族所使用的法。”(46)显然,在永恒性、普遍性和自然理性这些特征上,万民法实际上与自然法是同义语。正是秉承着符合自然的正确理性这一“正确之法”,罗马法学家最终将自然法中所蕴涵的理性、平等、正义等价值理念和精神注入罗马法,并最终得以建构起符合于事物本性、符合于生活的经验事实的法规,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优秀的法律典型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问题始终是自然法学家的中心视野。他们从对宇宙生成变化之理的“自然”追问出发,发现其中所蕴涵的超越人类合法权威之上的自然法则,并将这些法则看成是有待我们追求和实现的善和正义的实践原则和道德标准。这种思维路径构成了西方自然法的传统精神,它为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宪政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建构的道德基础和价值追求。
注释:
①[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页。
②J.P.Mayer,Political Thought:The European Tradition,New York,1939,p.9.
③[美]特伦斯·欧文:《古典思想》,覃方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
④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⑤[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页。
⑥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对“自然”的理解,不再是神话时期的“作为物质之物的运动过程的自然界”,而是指一种“自身绽开”“揭示自身的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指这种绽开着的自然过程所具有的一种集聚力量,也即指“事物之所是”。有时,这一语词在伦理学上是中立的,它意指一种统一的宇宙秩序。但也常常与诸如正义、报复、和谐等政治和道德观念相联系,表示宇宙中统一的道德秩序。习俗一词,则从最早的“动物和人的区分”演变为“祖传的习惯”、“法律和契约”。应当注意的是,希腊人总是将习惯和契约相等同,这一点与我们今天颇为不同。
⑦⑩《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27页。
⑧[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页。
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页。应当注意的是,在行文中,赫拉克利特仍经常用神、神的法律这样的语词,但与希腊神话中的神法所指称的内涵不同,他所说的神法并非神的意志,而是指逻各斯,也即自然的理性和法则。
(11)[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页。
(12)[美]特伦斯·欧文:《古典思想》,覃方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13)《古希腊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14)参见John Burnet,Law and Nature in Greek Eth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Apr.,1897,pp.328-333.
(15)[德]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16)[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1页。
(17)《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页。
(18)(20)[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7、460页。
(19)参见James Luther Adams,The Law of Nature in Greco-Roman Thought,The Journal of Religion,Apr.,1945,p.102.
(21)[爱尔兰]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丁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22)[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3页。
(23)关于智者学派提出自然法的理论动机,法国学者罗斑曾分析过:“智者学派用来使‘矛盾’自动出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自古以来对‘自然’的观点与‘习俗’或‘法律’的观点的区别,这种方法对他们职业上的战术大有帮助:前一种观点有时可以使他们在一种神话的烟幕之下来表现最危险的大胆主张,有时又可以使他们用来维护社会上的保守的原则。他们之所以努力来找出不成文的法律和自然权利,我们也可以怀疑他们的兴趣所在也无非在形式的辩证法的方面。”([法]罗斑:《希腊思想的科学起源》,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74页)
(24)[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西方哲学史》上卷,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25)尽管将这一部分的智者学派归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实证主义并不科学,但我们仍可以在他们那里法律实证主义的源头。正如唐纳德所言,法律实证主义的发端虽远到19世纪,但从其产生和发展历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作为法学史上的一对夙敌,其恩怨滥觞于希腊政治哲学史上的“physis(自然)—nomos(习俗)”之争,并以“事实(facts)—规范(norms)”、“正当性(legitimacy)—合法性(legality)”等问题形式贯穿于整个西方法哲学史甚或知识论传统(参见Donald,R.Kelly,The Human Measure:Social Thought in Western Legal Trad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90,Chapter 1.& 2,pp.1-14,24-28)。
(26)(28)(29)参见Leo Strauss,Nature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108、95、102.
(27)[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
(30)Leo Strauss,Thought on Machiavell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292.
(31)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240.
(32)参见James Luther Adams,The Law of Nature in Greco-Roman Thought,The Journal of Religion,Apr.,1945,p.105.我们看到,正是基于城邦和善之美德二者的这种关系,苏格拉底才将对城邦法律的服从看成是不容商榷的,甚至认为遵守一种有缺陷的法律并不比违背这样的法律更不正义。而在后来,当苏格拉底被希腊城邦判处死刑时,他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其用意乃是通过自己的死亡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
(33)[美]伯纳德特:《施特劳斯的〈城邦与人〉》,张新樟译,载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566页。
(34)正是基于此,斯特劳斯宣称,与其说柏拉图意在宣扬一种高高在上的理想,倒不如说他是在竭力制止那种批判现实城邦的激进的“理想主义”,而《理想国》就是“有史以来设计得最好的治疗各种政治野心的良药”(参见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65)。
(35)参见[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3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9-150页。
(37)[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6页。
(3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39)(40)[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至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54页。
(41)参见James Luther Adams,The Law of Nature in Greco-Roman Thought,The Journal of Religion,Apr.,1945,p.110.
(42)[法]莱昂·罗斑:《希腊世界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休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43)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75页。
(44)参见J.Rufus Fears,Natural Law:The Legacy of Greece and Rome,in Common Truths:New Perspectives on Natural Law,ed Edward McLean,Wilmington,DE:ISI Books,2000,p.20.
(45)Cicero,On the Republic,in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Translations of the Principal Sources with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I,Translation A.Long D.Sedley,Cambridge,1987,pp.432-433.
(46)[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标签:自然法论文; 法律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宇宙起源论文; 古希腊论文; 政治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宇宙法则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