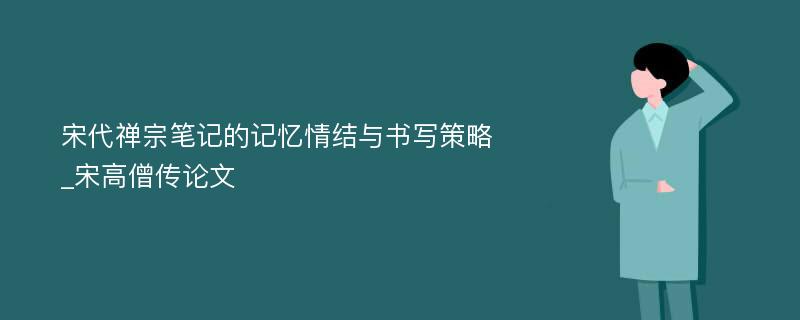
宋代禅林笔记的忆古情结与书写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禅林论文,宋代论文,情结论文,策略论文,笔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忆古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昭示了当下的不圆满,以及回忆者的不安和焦虑。所以我们常常见身处末世、历经战乱的人怀念盛世的富足与和平,而少见与之相反者。宋代禅林笔记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对先贤古德的赞颂与回忆中,惠洪的《林间录》是为证明。此后,宗杲的《宗门武库》、晓莹的《云卧纪谈》、《罗湖野录》、净善的《禅林宝训》、道融的《丛林盛事》、昙秀的(《人天宝鉴》、圆悟的《枯崖漫录》等,无一逃脱回忆的罗网。那么,这一场集体性的忆古暴露出宋代禅林的哪些弊病,呈现出书写者怎样的“盛世”理想,为了描述这样的理想采取了哪些书写策略,其忆古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本文将略陈浅见,求教方家。
一 忆古的起因:末世的焦虑
在宋代禅林笔记中,最常见的一种忆古形式是古今对比,即先忆前辈宗师之德行,后责今日学者之缺失,在颂古呵今的过程中直接指出当下禅林的问题所在。从这最露骨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直观宋代禅林的“不圆满”,并由此寻找忆古情绪滋生的源头。
一直以来,禅门都标榜不与王权政治相往来的孤高气节与淡泊品质,并以此来保证宗门的纯粹性与独立性。然而至北宋中后期,禅门的独立精神逐渐丧失,禅林风气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惠洪最先洞察到了这一变化,并在《林间录》中表达了对于禅林末世的感怀:
谢景温师直守潭州,虚大沩以致之,三辞,弗往。又嘱江西彭汝砺器资请所以不应长沙之意。晦堂曰:“愿见谢公,不愿领大沩也。马祖、百丈已前无住持事,道人相求于空闲寂寞之滨而已。其后虽有住持,王臣尊礼,为人天师。今则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户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耳。岂可复为也!”器资以斯言反命。师直由是致书,愿得一见,不敢以住持相屈,遂往长沙。盖于四方公卿意合,则千里应之。不合,则数舍亦不往也。开法黄龙十二年,退居庵头二十余年,天下指晦堂为道之所在,盖末世宗师之典刑也。①
唐代的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之前,禅风淳朴,“道人相求于空闲寂寞之滨”;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之后,虽设住持之位,但仍以德行赢得世人尊重;然而至北宋晦堂祖心的时代,禅门中却已遍是依附官府、丧失气节之徒。谢景温守潭州,是在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由此可知,禅宗内部的危机在这一时间已经显露无遗。晦堂祖心不愿去长沙住持大沩,是要以此明志,对抗流俗。
由于禅门精神的失落而产生的焦虑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演愈烈。据《丛林盛事》载,归云如本曾作《丛林辨佞》一文,议论当世向达官权贵摇尾乞怜者,圆极彦岑为之作序曰:
然士君子相求于空闲寂寞之滨,拟栖心禅寂、发挥本有而已。后世不见先德楷模,专事谀媚,曲求进显。凡以住持荐名为长老者,往往书刺以称门僧,奉前人为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献佞,识者悯笑而恬不知耻。……吾道之衰极至于此!呜呼!天诛鬼录,万死奚赎其佞者欤!嵩禅师原教有言:“古之高僧者,见天子不名,预制书则曰公、曰师。钟山僧远,銮舆及门而床坐不迎;虎溪慧远,天子临浔阳而诏不出。当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圣人之道振之……”②
古之高僧,不因名利而屈节、不因俗务而坏道,因此受到礼遇和尊重;今之衲子,为求私利而丧德,为夺虚名而失守,因此遭人耻笑和怜悯。古之高僧,修身敬法而格自高,圣人之道所以振,今之衲子,贪名逐利而行自贱,宗门之法所以坏。圆极彦岑的这番议论意在为当下宗门把脉,揭示禅风衰敝的根源。此序作于南宋孝宗淳熙壬寅年(1182),可以看出,这时的禅林已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
对于世俗权力的态度决定了禅门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宋代禅林笔记讨论的焦点。书写者常常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一问题上古今存在的巨大差异,如此后《禅林宝训》载灵源谓佛鉴语③,《人天宝鉴》载隐山与灵空书④,《枯崖漫录》载浙翁佛心禅师语⑤,等等。从其叙述语气中不难看出,“相求于空闲寂寞之滨”的古老禅风已变得遥远而不可企及。
朴素作风的遗落是末世之感产生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林间录》载:
石头和尚庵于南台有年,偶见负米登山者,问之,曰:“送供米也。”明日,即移庵下梁端,遂终于梁端,有塔存焉。百丈寺在绝顶,每日力作以偿其供。有劝止之者,则曰:“我无德以劳人。”众不忍,藏去作具,因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先德率身多如此。故六祖以石坠腰,牛头负粮供众。今少年苾刍擎钵,颦额曰:“吾臂酸。”⑥
荆州福昌善禅师,明教宽公之子,为人敬严,秘重大法。……南禅师与悦公亦在会下。南公曰:“我时病寒服药,须被出汗,遣文悦遍院借之,皆无有。百余人例以纸为之。”今则又不然。重毡之上,以褥覆之,一日三觉,可谓快活时世也。⑦
唐代的禅宗祖师中,石头希迁不忍他人送米之艰辛而移庵梁端,百丈怀海每日劳作以偿还供养,此前的六祖慧能与牛头法融也都勤劳俭朴,堪称表率。而时下比丘稍有劳作便满腹牢骚,毫无吃苦耐劳之精神。福昌惟善,北宋真宗、仁宗时人,偕僧众百余人,皆以纸为被,律己严格;时下比丘却只图饱暖舒适,一味懒惰困睡。谢逸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为《林间录》作序,并称此书耗费十年而成⑧,则《林间录》应始作于哲宗绍圣末年,而惠洪所谓“今”当是称北宋哲宗、徽宗朝。由惠洪之笔,可见北宋末禅风之凋丧。
其后,《云卧纪谈》也有类似记载:
熙宁间,西湖有僧清顺……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过数斗,以瓶贮置几上,日三二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有。……清介贫甚,食仅足而已。几于不足也,然未尝有忧色。老矣,不知尚健不?噫!今吾党以清贫为耻,以厚蓄为荣,及溘然,则不致其徒于缧绁者几希。若使其少慕顺之风,岂至遗臭耶?⑨
《云卧纪谈》作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从文中“老矣,不知尚健不”一句可知,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就已扬名的清顺在此时应至耄耋之年,那么《云卧纪谈》当写于绍兴初年。短短六十年之间,禅林已是物换星移。在对待外物的态度上,清顺只求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连蔬菜也不常吃;至晓莹之时,僧人却已开始大肆敛财,为自己积攒家资。在获取外物的方式上,清顺是接受他人的馈赠,而且只取个人所需的一小部分;至晓莹之时,僧人却已开始巧取豪夺,甚至于因此锒铛入狱。在清顺由青年而老年的时间里,禅林原有的荣辱观和道德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慧宗杲曾指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妙喜曰:“节俭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历观古人,鲜有不节俭放下者。年来衲子游荆楚,买毛褥,过浙右,求纺丝,得不愧古人乎?”⑩
修行的终极目的,是求得心性的自在解脱。如若放不下对外物的执着,如何能得到心灵的自由?因而,节俭就成为修身的根本,习禅的关键。古之修行者,能清贫自守,一心向道;今之修行者,却贪图享受,意志薄弱。类似的感慨在宋代禅林笔记中层出不穷(11),足以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
识见器度的庸俗是末世之感产生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据《林间录》载:
悦禅师妙年奇逸,气压诸方。至雪窦,时壮岁,与之辨论,雪窦常下之。每会茶,必令特榻于其中,以尊异之。于是,悦首座之声价照映东吴。及悦公出世,道大光耀。有兰上座者,自雪窦法窟来,悦公勘诘之,大惊,且誉于众。相从弥年而后去。前辈之推毂后进,其公如此。初,未尝以云门、临济二其心。今则不然,始以名位惑,卒以宗党胶固,如里巷无知之俗。(12)
雪窦重显与云峰文悦是北宋真宗、仁宗时人,分属云门宗与临济宗,然而前者对于后者的欣赏、援引并未因门庭不同而受到影响。云峰文悦则以相同的态度对待来自雪窦门下的兰上座。这与当下禅林中那些诱于名利、党同伐异的人相比,高下自见。“如里巷无知之俗”的言下之意是称扬前辈宗师的卓越见识和非凡胸襟。
《罗湖野录》有:
潭州云盖智和尚,居院之东堂。政和辛卯岁,死心谢事黄龙,由湖南入山奉觐。日已夕矣,侍僧通谒。智曳履且行且语,曰:“将烛来,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绝叫:“把近前来,我要照是真师叔,是假师叔?”智即当胸殴一拳。死心曰:“却是真个。”遂作礼。宾主相得欢甚。及死心复领黄龙,至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五日示寂。……是时智年九十,可谓宗门大老矣。视死心为犹子,闻讣,叹法幢之摧。盖前辈以法道故。今则不然,生誉死毁,与市辈无异,真可羞也。(13)
云盖守智是黄龙慧南的法嗣,死心悟新是晦堂祖心的法嗣,黄龙慧南的法孙。二人是师叔与师侄的关系。虽然后者的名气远盛于前者,但这并未使二人心生芥蒂,因为他们将法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据晓莹称,《罗湖野录序》作于南宋“绍兴乙亥”(14)(1155),距死心示寂的“政和甲午”(1114)不过四十年光景,禅林内部却已经由相互敬重变成了相互诋毁。
《禅林宝训》对于禅林风气的变化进行了总结与剖析:
简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则与人共其道;兴事立业,则与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则与人共其名。所以道无不明,功无不成,名无不荣。今人则不然,专己之道,惟恐人之胜于己,又不能从善务义,以自广也。专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贤与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于蔽,功不免于损,名不免于辱。此三者乃古今学者之大分也。(15)
简堂行机,活动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90)。他认为古今学者的差别在于:古人重道,今人利己,古人修身养性,今人追名逐利;古人胸襟豁达、识见卓荦,今人狭隘自私、目光短浅。所以《禅林宝训》每每感慨古今的“霄壤”(16)之别,并以“末法”(17)来指责当下禅林。
从禅林笔记的写作时间及书中人物的活动时间可以看出,禅宗“末世”的焦虑主要产生于北宋后期、尤其是神宗熙宁、元丰之后。究其原因,当与神宗熙宁元年政府开始大规模地鬻卖度牒、紫衣、师号有直接关系(18)。赐师号、赐紫衣本来是世俗权力给予僧人的最高荣誉,分别始于梁武帝与武则天,唐末五代时渐趋盛行,然而尚未至于可以买卖的地步。大规模地鬻卖度牒早在天宝十四年即已出现,然而时值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实行的时间相当有限,且因手续复杂而不至于泛滥。但至北宋神宗时期,为了弥补国家的财政亏空,僧人的身份、荣誉成为了可以用财富交换的对象,而不再与修行深浅、德行高低有直接关系。神宗的这一举措,潜移默化地起到了“引导僧众向世俗荣典看齐”(19)的作用。在禅林中,对名利的追逐开始取代对内心的探求。禅林原有的荣誉价值观被彻底颠覆,一直以来倡导的精神品格、朴素作风、识见器度也被一一丢弃。这样,禅宗在向世俗力量靠拢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芒。
二 忆古的策略:典范的塑造
1.忆“老成人”,以存“典刑”
不管令忆古者焦虑的问题有多少种类型,归根结底都是“不务守先圣法度”(20),“曲违圣制,大辱宗风”(21),“去古既远,师法益坏”(22)。简单地说,就是对“先圣法度”、“圣制”、“师法”的亵渎和破坏。那么,如何恢复古圣贤之法便成为当务之急。因而,宋代禅林笔记的忆古带有了强烈的追述古法的意味。且看《云卧纪谈》载白云守端事:
白云端和尚,住浔阳能仁。新其堂与厨,略记其实曰:“古之称善知识者,盖专以祖法为务,旦夕坐于方丈间,应诸学者之间而决疑焉。若院之事,则有学者分而集之。故善知识之称,得其实而有尊矣。愚嘉祐丙申孟夏,自圆通应命来继兹席,虽不揆其实而至,且患其法堂、厨舍悉皆颓圮,有风雨不堪之忧,何足以容众而继人之后者哉?已而得州人周氏怀义大新其堂。明年,有慕蔺来者,又新其厨。然后风雨不足忧,而徒众得以安焉。周氏素达于吾教,不欲书以自显。愚谓厨资出诸远近之入,不书之无以嘉其善。乃并以二善刻于厨壁。噫!考于古之称善知识者之义,愚尚有愧焉。己亥九月十七日住持沙门守端述。”石刻既毁,前辈典刑无复见矣。今立根椽片瓦,便彰饰说,邀功归己,欺于后世,安肯自书其愧耶?(23)
白云守端将翻新法堂厨舍的功德归与他人,而言及自己之为善知识则语带愧疚。与此相反,时人著文,只知为自己邀功,不惜以妄语欺骗后世。一谦逊,一骄纵,可见学养之大不同。至晓莹之世,记录守端文字的石刻已不复存在。晓莹凭借记忆搜寻文章之大概,目的是希望时人能够重见“前辈典刑”。
在宋代禅林笔记中,一再提到“典刑”的意义:
天下指晦堂为道之所在,盖末世宗师之典刑也。(24)
绍兴之末,丛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25)
师(资寿妙总)年德虽重,持律甚严,苦节自砺,有前辈典刑。(26)
在这里,“典刑”有着旧法、常规的意味,“老成者”则因保有旧日传统而成为古代法度的象征。也就是说,“老成者”是作为“典刑”的载体而存在的。这一书写方式来源于儒家“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27)的说法。忆古者以追溯“老成人”为手段,意图是为展陈先代的“常事故法”。惠洪,则成为这一书写方式的引领者,详见周裕锴《惠洪文字禅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28)一文,此不赘述。
由此,被追忆的对象不再作为独立的个体显示价值,而是作为古人风范、法度的代表被频频召唤。有文如此:
妙喜亦尝谓元昭有宗师体裁,又称光为禅状元。谅其然乎!以之追踪丹霞、庞老故事,可无愧也。(29)
佛鉴曰:佛眼弟子唯高庵劲挺,不近人情,为人无嗜好,作事无傥援,清严恭谨,始终以名节自立。有古人之风,近世衲子罕有伦比。(31)
西山亮禅师,福州人。枯硬俭约。尝蓄纸被一张,补粘殆遍,寒暑不易……闻者谓其住山有古人风。(31)
“追踪……故事”的方式体现了禅林笔记书写者的基本思路。“故事”在这里已不再是过往旧事的意思,而是与“典刑”一样包含了先法、旧式、古制的涵义。回忆者们将书写对象与古代贤者相比,一方面表达了对古人风范在当代逐渐凋零的惆怅和无奈,另一方面又赋予书写对象以古老、淳朴的光辉。时间的迁逝可以摧毁石碑,磨灭肉体,但是古老的传统却在这样的追忆与描述中得以再次呈现。
当然,对于“宗师体裁”和“古人之风”的礼赞也有着现实的动机。我们在忆古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良苦用心:
湛堂准和尚,兴元府人……平生律身以约,虽领徒弘法,不易在众时。晨兴后架,只取小杓汤洗面,复用濯足。其他受用,率皆类此。才放参罢,方丈行者人力便如路人,扫地煎茶,皆躬为之。有古人风度,真后昆良范也。(32)
明极以大父事宏智,拈提如山涛论兵,暗合孙吴,亦可为丛林榜样。(33)
高庵为人端劲,动静有法,处己虽俭,与人甚丰。闻人有疾,如出诸己。至于苍头厮役,躬往候问,听其所须。及死,不问囊箧有无,尽礼津送。其深慈爱物,真末世之良轨。(34)
湛堂文准担任住持后,依然保持着节俭勤劳的生活习惯,并未因地位的提高而放松对自我的要求;明极慧祚是宏智正觉的法孙,侍奉宏智如同亲生祖父,极尽敬重孝顺之礼,拈举公案则彰显慧性,有如山涛,虽“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35);高庵善悟品质刚正,居处素俭,但对待他人却毫不吝惜。无论德行与才能,这些禅师都堪称典范。对于他们的歌颂赞扬,是要树立“后昆良范”、“丛林榜样”及“末世之良轨”,令禅林学者有法可循。
2.破“户婚体”,以昭精神
净土惟正感慨世异时移时曾说:“古之度人以清机密旨,今殊不然,正以合去老幼、童其颠、褐其身而已。”(36)这道出了宋代丛林衰敝的深层原因,即当下学者徒有僧人的外表,却遗失了禅门的精神。故泐潭洪英谓潘延之曰:“古之学者治心,今之学者治迹,然心与迹相去霄壤矣。”(37)正是为了弥合这霄壤之别,当被回忆者作为古代法度的意义存在时,其精神的典范作用便成为书写者竭力追求的目标。惠洪在《林间录》中有这么一段对于书写方式的探讨:
李肇《国史补》曰:“崔赵公问径山道人法钦:‘弟子出家得否?’钦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为。’赵公叹赏其言。”赞宁作钦传,无虑千言,虽一报晓鸡死且书之,乃不及此。何也?(38)
同样是写法钦,赞宁《宋高僧传》耗费千余字叙其生平事迹,连一只鸡的死都记录在案,人物的表现效果却不如李肇《国史补》中的那两句对白。“报晓鸡死”一事,见《宋高僧传·习禅》:“初,钦在山,猛兽鸷鸟驯狎。有白兔二跪于杖屦之间。又尝养一鸡,不食生类,随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长安,长鸣三日而绝。今鸡冢在山之椒。”(39)僧人与林中禽兽和谐共处的描写在《高僧传》与《续高僧传》的“习禅篇”中经常出现,赞宁不过是继承了传统僧传的写法。然而惠洪认为,这样的书写已经不能适应禅门的需要。当下禅林人物的书写应当如《国史补》那样,以简洁的语言突现人物的精神。惠洪的批评是否客观暂且不论,毕竟《国史补》与《宋高僧传》体例不同,一为笔记,一为传记,写作方式自然有别,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惠洪对于传统僧传的鲜明态度。
在写作《禅林僧宝传》与《僧史》时惠洪更加清晰地表露出对于传统僧传的不满:
禅者精于道,身世两忘,未尝从事于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于讲师之笔。道宣精于律而文词非其所长,作禅者传如户婚按检。赞宁博于学,然其识暗,以永明为兴福,岩头为施身,又聚众碣之文为传,故其书非一体。予甚悼惜之。(40)
僧史自惠皎、道宣、赞宁而下,皆略观矣。然其书与《史记》、两《汉》、《南北史》、《唐传》大异。其文杂烦重,如户婚斗讼按检。(41)
他认为,虽然《高僧传》、《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都有为禅者作传,但其作者大都精于义学而疏于禅学,叙述禅者生平往往枯燥乏味,如同登记户籍和审查案件,难以传达人物的神采风流。传统僧传的作者,一欠缺足够的文学功底,二不具备足够的远见卓识,因此无法把握禅门的精髓,也不可能有效地树立禅门的典范。惠洪要做的,是超越传统僧传“户婚斗讼按检”的方式,以迁、固之笔法、史眼,弘扬禅门之精神气格。
《林间录》的写作便贯穿着这一思想,如:
唐高僧,号懒瓒,隐居衡山之顶石窟中。尝作歌,其略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萝下,块石枕头。”其言宏妙,皆发佛祖之奥。德宗闻其名,遣使驰诏召之。使者即其窟,宣言:“天子有诏,尊者幸起谢恩。”瓒方拨牛粪火,寻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尝答。使者笑之,且劝瓒拭涕。瓒曰:“我岂有工夫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钦叹之。予尝见其像,垂颐瞋目,气韵超然,若不可犯干者。为题其上曰:“粪火但知黄独美,银钩那识紫泥新。尚无心绪收寒涕,岂有工夫问俗人。”(42)
惠洪以两百字的篇幅记录了懒瓒的四言歌与煨芋事,文字全部围绕懒瓒山居乐道的淡泊情怀与不慕名利的高洁品质展开。但在《宋高僧传》中,赞宁用了七百字,言及懒瓒名之由来,与李泌的交往,及开路、驱虎之神功,却未涉及人物的精神世界。
赞宁文中同样有煨芋一事,但却是这样描写的:
相国邺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隐南岳而潜察瓒所为,曰:“非常人也。”……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自赞而拜。瓒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愈加郑重,唯拜而已。瓒正发牛粪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尽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后终居相位,一如瓒之悬记矣。(43)
在赞宁笔下,懒瓒的不同寻常并非出于德行的清懿,而是出于对李泌高升相位的成功预言。这与其后所写懒瓒开路驱虎的事迹一样,代表了传统僧传将书写对象神通化的特点。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详细论述,此处暂不赘言。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以看出,惠洪与赞宁书写人物的侧重判然有别。赞宁着重人物外在行迹的描述和神通法力的展现;惠洪则强调人物内在气质的挖掘,往往以嘉言善行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精神追求。这与二人的写作渊源有着很大关系。赞宁因袭的是传统僧传的写作模式,对于后来兴起的禅宗未能给予充分的理解与阐释;惠洪则是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纪传体史学著作中汲取养料,将书写对象当作有生命的个体,以典型的事例张扬其内在的风采神韵,以时代的背景烘托其生存的独特意义。惠洪将懒瓒画像的题辞置于文末以示称赏,就有效仿“太史公曰”的意图。其《禅林僧宝传》在每传之后有“赞曰”一段,也是如此目的。故宣和六年侯延庆在为《禅林僧宝传》作引时将惠洪与司马迁、班固相提并论(44)。
至于惠洪对于传统僧传的批评,无疑也有以偏概全之嫌。慧皎以“高僧传”的名字取代宝唱的“名僧传”,本身就能说明慧皎对于精神品质的重视(45)。且慧皎、道宣的时代禅宗还未蓬勃发展,对于禅林人物有所疏忽也情有可原。倒是赞宁,入宋后赐紫衣、充僧录,且奉诏作《大宋高僧传》,与君主、权贵往来频繁。陈垣曾评其书:“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不叙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美,致使西山之节,郁而不彰。”(46)因而,惠洪对传统僧传的不满主要是针对赞宁。在《宋高僧传》中,赞宁自称“赐紫臣僧”、“赐紫沙门”,写及其他沙门时,也常常以赐紫为誉(47)。《禅林僧宝传》虽也写及“赐紫”,但往往强调禅师拒绝接受的态度(48)。另外,赞宁与惠洪都曾为玄沙师备立传,赞宁止用了三百字,念念不忘“奏赐紫衣”(49)之事。惠洪用了近两千字,对于“赐紫”却只字未提。可见二人趣旨之不同。
惠洪的书写方式充分说明了时下禅林的缺失以及有识之士对于精神传统的重视。此后的禅林笔记无一例外地追随着惠洪的步伐,如《丛林盛事》载二灵庵主与天童交的毅然绝交(50),《禅林宝训》载佛鉴慧勤忆五祖法演的清心寡欲(51),《人天宝鉴》载真如慕喆与杨岐方会的为法忘躯(52)等。由此,宋代禅林笔记也显现出《世说新语》的风格特点。
3.趋神圣化,以示尊礼
回忆者按照当下禅门的需要来树立古圣贤法度,并由此确定或强调他们对于禅宗传统的认知。而被回忆者由此也失去了他们最本真的面目,被拔高和塑造成书写者心中的理想和典范。他们不再作为历史人物而存在,而是成为一个个文学形象,他们也不再作为某个个体而存在,而是成为一个个神圣的符号和象征。
因而,凡是有损于祖师形象的书写与传闻,惠洪都给予严厉的谴责。如《林间录》卷上“曹溪六祖大师方其韬晦时”一段有:“《大宋高僧传》曰:天子累召,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扬,北人见之必轻法。’是果祖师之言乎?不仁者之言也。”(53)慧能不应帝王之请,在惠洪看来,是禅门高标风范的体现,但在赞宁笔下,却是由于慧能对自我外在形象的不自信。惠洪又考证石头和尚施身食虎、清凉文益书别国主、洞山悟本不认其母、玄沙师备覆舟溺父诸事,并痛斥丛林散布谣言、诬蔑宗师之罪:“此直不情者记之以自藏。安知诬毁先德为罪逆,必有任其咎者,不可不慎也!”(54)二祖慧可雪地断臂,本来是求法心诚的表现,而在道宣笔下却写成遇贼断臂,于是惠洪又感叹:“宣暗于辨是非也!”(55)同样是不赴帝约,同样是禅师断臂,却由于书写者身份、立场和目的的不同造成了书写效果的巨大差异。
从惠洪对赞宁等人的批判和指责中,可以看到禅林笔记对于传统僧传的有意对抗和挑战。传统僧传“习禅篇”中多写禅者降伏猛兽的神通,而在禅林笔记当中,突出表现的是禅师的德高望重和睿智机辩。如《丛林盛事》载:
真净禅师居筠之大愚,太守钱公弋来游,怪禅者骤多。众以师有道德者,奔随而至。钱公即入其室,未有以奇之。翌日命斋,师就席。俄有犬逸出屏帷间,师少避之。钱嘲曰:“大善知识固能降龙伏虎,岂畏犬耶?”师应声曰:“易伏偎岩虎,难降护宅龙。”钱大喜,乃移居圣寿问道焉。(56)
从驯虎到避犬,禅师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源于书写者对于理想禅师的不同想象。慧皎、道宣、赞宁等辈注重外在的异术与神通,而惠洪、道融、晓莹诸人则注重心性的护持与修养。龚隽在比较传统僧传与禅门灯录的禅师书写时说:“可以肯定,灯录在创造理想禅师的形象时,是有意识地消解掉僧传系统中神化性的色彩,把祖师和佛的形象人间化。灯录理想的禅师并不是那种可以呼风唤雨、广施神迹的灵异之士,相反,这些传统僧传所制造出的圣人形象恰恰是灯史所要破除的。”(57)此论敏锐地把握了禅宗人物书写出现的微妙转变。《林间录》中还记载了黄檗希运呵斥神通的故事:
断际禅师尝与异僧游天台,行数日,值江涨不能济,植杖久之。异僧以笠当舟,登之浮去。断际嫚骂曰:“我早知汝,定捶折其胫乃快也。”异僧叹曰:“道人猛利,非我所及。”(58)
龚隽认为这一故事可以看作灯录禅传所提倡的反神通的“典范”(59)。然而,反神通并不代表要消解神异性的书写。同样的故事,同样是禅门内部的书写,更早一些的《祖堂集》则记为“敛衣蹑波而渡”,并于结尾处增加了“言已,忽然而隐”(60)一句。《景德传灯录》为“褰衣蹑波,若履平地”,文末也有“言讫不见”(61)一句。这说明,在品评人物的标准上,禅门内外有所不同,但为了达到各自的书写目的,都不排斥神异变化的手段。当然,这与古人的认知水平有很大关系。本文仅从叙事策略着眼,阐述禅门书写“制造神话”的手段。
在《宗门武库》中记载了这样一起灵异事件:
法云佛照杲禅师,尝退居景德铁罗汉院。殿中有木罗汉数尊,京师苦寒,杲取而烧之,拥炉达旦,次日淘灰中得舍利无数。诸座主辈皆目之为外道。盖佛照乃丹霞辈流,非俗眼所能验也。(62)
法云佛照烧木罗汉而得合利,被视为“外道”,与异僧神奇渡江、被黄檗斥骂的原因是一样的。但是,此处的灵异事件并非用以显示法云佛照的神通能力,而是为了突出他的卓荦不凡。在《五灯会元》的记载中,丹霞天然烧木佛时还尚无合利的踪影(63),而至法云佛照时舍利便神话般地出现了。无舍利,是为表现丹霞天然的机智;有舍利,是为证明法云佛照“非俗眼所能验”的身份。至于真有舍利还是假有舍利,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书写者如何以“合利”为策略去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和典范。类似的例子在宋代禅林笔记中尚有不少,如《罗湖野录》中记潜庵清源言语应验事(64),《云卧纪谈》记大慧宗杲为云峰文悦之后身事(65),《人天宝鉴》中记仰山慧寂得二神之助事(66),等等,都是试图通过神佑、神护来肯定禅师的德行及其宗门的地位。因而可以说,禅林笔记消解掉了传统僧传中的“神化”色彩,使禅师们不再拥有变化莫测的本领,但却通过“神话”的方式制造了神圣光辉的禅门典范,令时人及后人顶礼膜拜。
三 忆古的目的:传统的延续
作为笔记体,记录近代以及前代往事应当是一种通例。然而,这一场不约而同的回忆体现出太多的相似性,比如对当世的批判,对前辈的颂扬,对“典刑”的强调,对精神传统的重视,以及对人物的神圣化等。此时的笔记就不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载体,而成为社会呼声的集结,也不再仅仅是关乎过去,而更多的是要影响当下。
关于“古”的意义,《禅林宝训》有一段记载:
圆悟谓佛鉴曰:“白云师翁动用举措,必稽往古。尝曰:‘事不稽古,谓之不法。予多识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盖今人不足法。’先师每言师翁执古不知时变,师翁曰:‘变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终不为也。’”(67)
圆悟克勤、佛鉴慧勤是杨岐派五祖法演的弟子,白云守端的法孙。二人回忆了五祖法演和白云守端的一段对话。白云守端认为,稽古是因为“前言往行”可资为法,而今人不足为法。今人改变了旧规、常例,也遗失了传统中的精髓。古,意味着“故”、“常”;今,意味着“变”、“易”。古,意味着恒久不变;今,意味着流荡散漫。因而,古的意义在于它将成为今人的“法”。可是在一些后辈眼里,“执古”却代表着不顺应潮流和顽固不化(68)。
“多识前言往行”一语出自于儒家经典。《周易正义》卷三载:“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唐孔颖达疏:“君子则此大畜,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使多闻多见,以畜积己德。”(69)这一说法最早被禅门大量征引是始于惠洪,有文字为证:
若前辈必欲大蓄其德,要多识前言往行,僧史具矣,可取而观。
佛鉴携此书来,请记其本末,而以谓先觉之前言往行,不闻于后世,学者之罪也。闻之而不能以广传,同志之罪也。
《易》曰:“多识前言往行,以大畜其德。”是录也,皆丛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遗风余烈,则古人不难到也。
此一代之博书,先德前言往行具焉。(70)
按辈分,惠洪是黄龙慧南的法孙,也算是白云守端的师侄,但《禅林宝训》的成书是在惠洪辞世半个世纪之后,因而白云守端是真有此语、还是圆悟克勤受惠洪影响如此叙说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是惠洪第一次在禅门著述中这样强调“前言往行”的意义。他征引儒家言论、书写“前言往行”,目的是为增强说服力量,感召后来学者。《僧史》与《禅林僧宝传》的成书时间晚于《林间录》,因而以上言论也可以看作是对《林间录》的理论总结。谢逸称《林间录》“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之余论”,又说“余谓斯文之作,有补于宗教,如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缯纩”(71),可见是领悟了惠洪记录“前言往行”的路数的。惠洪开创了禅林笔记的写作传统,同时也开启了禅林忆古的大门。此后,南宋的宗杲、晓莹、道融、昙秀、圆悟等人纷纷加入禅林笔记的创作队伍,大书特书禅门宗师的前言往行,希图以此拯救当世、鼓舞众生。有序如此说:
有曰:前哲入道机缘,禅书多不备载,其过在当时英俊失于编次,是无卫宗弘法之心而然,遂致有见贤思齐者徒增叹息。细味其语,诚可箴吾辈懒慢之病。因追忆平日在众目见耳闻、前辈近世可行可录之语,共成一编。(72)
噫!古者之行非难行也,人自菲薄以谓古人不可及尔。殊不知古人犹今之人也,能自奋志于其间,则与古人何别?今刊其书,广其说,欲示后世学者,知有前辈典刑,咸至于道而已。(73)
道融以“追忆”的方式,意欲达到“卫宗弘法”、令后人“见贤思齐”之目的。昙秀所言的“前辈典刑”,即指古人法度,用以除恶、防非、劝善,使后世学者向古代贤者看齐。二者忆古的目的,皆是激励今人,振奋志气,追赶古人,从而缩短古今的差距。这与惠洪所说“想其遗风余烈,则古人不难到也”的语气何其相似!不难看出,记录先贤的“前言往行”已成为禅林笔记的基本内容,追忆先贤的“遗风余烈”则是禅林笔记的基本格调,而使今人“自奋志于其间”却是忆古的根本目的,也是禅林笔记的写作目的。
其他禅林笔记都认同并效仿了《林间录》的忆古模式,借以表达相同的禅门诉求。在言及禅林笔记的写作内容时,晓莹称《云卧纪谈》“则以畴昔所见所闻、公卿宿衲遗言逸迹,举而资乎物外谈笑之乐”(74),称《罗湖野录》“追绎畴昔,出处丛林,其所闻见前言往行,不为不多……以所得先后,会粹成编,命曰《罗湖野录》”(75),净善称《禅林宝训》“仍取黄龙下至佛照简堂诸老遗语,节葺类三百篇”(76),北山绍隆称《枯崖漫录》也是“集古成录”(77)。在言及禅林笔记的社会意义时,无著妙总称《罗湖野录》“雄文可以辅宗教,明诲可以警后昆……庶几后世英俊继而为之,使夫佛祖之道光明盛大,其功岂不博哉”(78),净善称《禅林宝训》“大概使学者削势利人我、趋道德仁义而已……实可以助入道之远猷也”(79),北山绍隆称《枯崖漫录》“俾五灯之后,复见一灯光明烛天下”(80)。佛法犹如明灯,照破人间迷暗。禅林笔记的写作就是要以忆古来戒今,从而将佛法的精髓、禅门的传统传递下去。
忆古,是一个古老的情结。孔子便是一个好古的典型,他称自己“信而好古”,是“好古,敏以求之者”(81)。他的好古是由于看到了当下的礼崩乐坏,而欲恢复周礼的传统,于是作《春秋》以追念先王之道。这种忆古的情结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迁逝而改变。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人们总是会怀念比自己更久远的时代,想从过去寻找医治当世弊病的良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82)其《史记》的写作也是一项浩大的忆古工程,目的是以古代来对照当世,从而使今人引以为戒。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有着相同的意图,即“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合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83)。考古事,寓褒贬,别善恶,是为了警醒当下,并在未来臻于郅治。这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条重要思路。宋代禅林笔记的忆古情结正是来自于儒家史书以追索往事来“镜”、“鉴”当下的书写理论。这从惠洪对《史记》等纪传体史书的叹赏与效法中也可见一斑。
南宋圆极彦岑曾这样描述宋代丛林的现状:“佛世之远,正宗淡薄,浇漓风行,无所不至,前辈凋谢,后世无闻,丛林典刑几至扫地。”(84)正是出于对禅门现状的省察和忧虑,惠洪以及晓莹、道融等人开始了忆古的行为,希望通过追述古德先哲的嘉言善行为今人树立典范,从而延续禅门将要中断的优良传统。因而,忆古不仅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振作的信号,它不仅暴露出现实的弊病,还暗示了未来的希望,以及回忆者改革现实的愿望和决心。它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使得禅门的精神得以绵延不绝。《云卧纪谈》中有语:“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耳。”(85)人类的文明正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反思现在、回忆过去中得以传递。
注释:
①《林间录》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599页。
②《丛林盛事》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70页。
③《禅林宝训》卷二:“凡接东山师兄书,未尝言世谛事,唯丁宁忘躯弘道、诱掖后来而已……与忧院门不办,怕官人嫌责,虑声位不扬,恐徒属不盛者,实霄壤矣。”(《大正藏》卷四八,第1023页)
④《人天宝鉴》:“隐山与灵空书曰:‘沙门高尚大圣慈荫之力,后世纷纷者自卑贱之。三三两两出没于泉石间,其气象与天台岩洞无异。频频伛偻王公之前,得不为识者掩口?年来粪火煨芋、不起谢恩之风,固不复见觅一人。如政黄牛、志庵主,大似掘地觅天。”(《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33页)
⑤《枯崖漫录》卷上:“今之踞方丈者,非特括众人钵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将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则剜去搜买珍奇,广作人情,冀迁大刹。只恐他日铁面阎老子与计算哉!”(《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56页)
⑥《林间录》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605页。
⑦《林间录》卷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615页。
⑧《林间录》序,《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585页。
⑨《云卧纪谈》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4页。
⑩《禅林宝训》卷三,《大正藏》卷四八,第1030页。
(11)如《丛林盛事》卷下:“保安封……又有滑稽语,讥后世后生不求淡素,惟务衣装,今并记于此。曰:‘纺丝直裰毛段袄,打扮出来真个(好)。蓦然问着祖师关,却似东村王大嫂。”(《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88页)《禅林宝训》卷二:“高庵闻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叹息久之,曰:‘比丘之法,所贵清俭,岂宜如此?徒与后生辈习轻肥者,增无厌之求,得不愧古人乎?”(《大正藏》卷四八,第1026页)《枯崖漫录》卷上:“今之踞方丈者,非特括众人钵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将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则剜去搜买珍奇,广作人情,冀迁大刹。”(《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56页)
(12)《林间录》卷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638页。
(13)《罗湖野录》卷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二册,第1000页。
(14)《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二册,第961页。
(15)《禅林宝训》卷四,《大正藏》卷四八,第1039页。
(16)《禅林宝训》卷一:“英邵武谓潘延之曰:‘古之学者治心,今之学者治迹,然心与迹相去霄壤矣。’”卷二:“灵源谓佛鉴曰:凡接东山师兄书,未尝言世谛事,唯丁宁忘躯弘道,诱掖后来而已……与忧院门不办、怕官人嫌责,虑声位不扬、恐徒属不盛者,实霄壤矣。”卷三:“古之学者……不系心于声利,不籍名于官府。自魏晋齐梁隋唐以来,始创招提,聚四方学徒,择贤者,规不肖,俾智者,导愚迷……比汲汲为一身之谋者,实霄壤矣。”(《大正藏》卷四八,第1021、1023、1032页)
(17)《禅林宝训》卷一:“英邵武谓晦堂曰:‘凡称善知识,助佛祖扬化,使衲子回心向道,移风易俗,固非浅薄者之所能为。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节义,往往苞苴肮脏,摇尾乞怜,追求声利于权势之门……”卷四:“痛哉,学者之心术坏矣!……然非佛日高明远见,乘悲愿力救末法之弊,则丛林大有可畏者矣。”(《大正藏》卷四八,第1021、1036页)
(18)参郭学勤《北宋佛教政策述评》,《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顾吉辰《关于宋代“度牒”问题的探讨》,《驻马店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第十一章《宋代的紫衣师号》,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444—460页;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第四章《相对平稳和低调——宋英宗、神宗、哲宗时期》、第十四章《荣誉与地位的引导——关于紫衣师号的颁给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212、406—428页。
(19)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29页。
(20)《禅林宝训》卷一,《大正藏》卷四八,第1018页。
(21)《丛林盛事》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70页。
(22)《枯崖漫录》卷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75页。
(23)《云卧纪谈》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0页。
(24)《林间录》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599页。
(25)《禅林宝训》卷四,《大正藏》卷四八,第1038页。
(26)《人天宝鉴》,《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38页。
(27)《毛诗正义》卷一八《大雅·荡》。郑玄笺:“老成人,谓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属,虽无此臣,犹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4页上)
(28)《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29)《罗湖野录》卷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二册,第991页。
(30)《禅林宝训》卷二,《大正藏》卷四八,第1025页。
(31)《枯崖漫录》卷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83页。
(32)《宗门武库》,《大正藏》卷四七,第944—945页。
(33)《枯崖漫录》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50页。
(34)《人天宝鉴》,《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33页。
(35)《世说新语·识鉴》:“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后诸王骄汰,轻构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世说新语校笺》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
(36)《云卧纪谈》卷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29页。
(37)《禅林宝训》卷一,《大正藏》卷四八,第1021页。
(38)《林间录》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586—587页。
(39)《宋高僧传》卷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2页。
(40)《题佛鉴僧宝传》,《石门文字禅》卷二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87页。
(41)《题修僧史》,《石门文字禅》卷二五,第276页。
(42)《林问录》卷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616—617页。
(43)《宋高僧传》卷一九,第492—493页。
(44)《禅林僧宝传引》:“其才则宗门之迁、固也。”(《卍续藏经》第一百三十七册,第440页)
(45)慧皎自序:“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高僧传》卷一四,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5页)
(46)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35页。
(47)《宋高僧传》卷一二:“(鉴宗)道俗归心,恢扬法教。出弟子尤者天童山咸启、敕赐紫衣背山行真、大慈山行满,皆分枝化物。”。(大安)咸通十四年,诏宜号延圣大师,赐紫袈裟一副。”“(文喜)大顺元年,威胜军节使董昌、武肃王同年发表荐论,两赐紫衣。”卷一三:“(光仁)爰奏举,诏赐紫袈裟并师号证空焉。”(第279、282、293、305页)
(48)《禅林僧宝传》卷五:“(石霜庆诸)唐僖宗闻其名,遣使赍赐紫伽梨,诸不受。”卷一七:“(天宁道楷)楷道行卓冠丛林,宜有以褒显之,即赐紫伽梨,号定照禅师。楷焚香谢恩罢,上表辞之。”卷二五:“(云居元祐)徐王闻其名,奏赐紫方袍。佑作偈辞之曰:‘为僧六十鬓先华,无补空门愧出家。愿乞封回礼部牒,免辜庐老衲袈裟。”卷二七:“(明教契嵩)赐紫方袍,号明教。嵩再奏辞让。”(《卍续藏经》第一百三十七册,第462、512、538、546页)
(49)《宋高僧传》卷一三,第306页。
(50)《丛林盛事》卷上:“初与天童交和尚同行,二人禀誓断不出世。后交爽其盟,出尸太白,和遂与其绝交。”(《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74页)
(51)《禅林宝训》卷二:“先师节俭,一钵囊鞋袋,百缀千补犹不忍弃置。尝曰:‘此二物相从出关仅五十年矣,讵肯中道弃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裰,自言得之海外,怨服则温,夏服则凉。先师曰:‘老僧寒有柴炭纸衾,热有松风水石,蓄此奚为?’终却之。”(《大正藏》卷四八,第1025页)
(52)《人天宝鉴》“杨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虑不办,虽冲寒冒暑,未尝急己惰容。自南源终于兴化三十年,总柄纲律,尽慈明一世而后已。真如者,始自束包行脚,逮于应世领徒,为法忘躯,不啻饥渴,造次颠沛,无遽色,无疾言。……嗟于二老,实千载后昆之美范也!”(《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31页)
(53)《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605页。
(54)《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617页。
(55)《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627页。
(56)《丛林盛事》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55页。
(57)龚隽《禅史钩沉》,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57页。此处说“灯录”是指禅宗内部有关禅者行传的资料,包括了语录、灯录、禅林笔记等内容(见该书第343页)。
(58)《林间录》卷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621页。
(59)《禅史钩沉》,第343页下注。
(60)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等点校《祖堂集》卷一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29—730页。
(61)《景德传灯录》卷九,《大正藏》卷五一,第266页。
(62)《大正藏》卷四七,第945页。
(63)《五灯会元》卷五:“(丹霞天然)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2页)
(64)《罗湖野录》卷下:“(潜庵清源)年逾八十而丧明,学者益亲附之。有欲版其语要流通,源设拒曰:‘若吾语深契佛祖,从今百日间目复有明,则副汝请。’如期果愈。缁素赞喜曰:‘得非般若之验欤!’寿九十有六而迁寂。建炎己酉冬,讫后事不数日,虏犯洪城,杀戮无噍类,源不罹斯厄,非道德所致耶!”(《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二册,第993页)
(65)《云卧纪谈》卷上:“与二僧游杯渡庵,有犬逸,怒吠,二僧惧而返。大慧径前,犬则如迎宿客,而庵之主僧延遇特厚。大慧曰:‘某甲晚生,岂足以当盛意?’主僧顾伽蓝土偶而言曰:‘昨宵将三鼓,梦此人告以今日云峰悦禅师来,且戒其为待耳。’大慧谢不敏。及回隐静,询云峰于老宿,有以云峰语录为示,开卷恍然,过目诚诵终不忘。自时丛林传大慧为云峰后身。”(《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5页)
(66)《人天宝鉴》:“沿流而上,有二神迎问曰:‘深山绝险,师自何来?’师曰:‘吾欲寻一庵地。’神曰:‘弟子福庆相遇,愿施此山与师居止。’师曰:‘君既施我,须具广大心,不见僧过,则吾受君施矣。’神曰:‘诺。’神遂指集云峰下曰:‘莫吉于此。’师乃结茅而居,木食涧饮,危坐终日。未几,二神见曰:‘徒众将盛,弟子住处不便,当易之。’至夜,风雷暴作,移庙于堵田三十里,古塑神像巨松皆往。乃会昌三年夏四月也。感异僧乘空而至曰:‘特来东土礼文殊,今日却遇小释迦。’自是沩仰宗风大振于世。”(《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21页)
(67)《禅林宝训》卷二,《大正藏》卷四八,第1025页。
(68)《林间录》卷下:“云峰悦禅师见僧荷笼至,则曰:‘未也,更三十年定乘马行脚。’法云秀禅师闻包腰至者,色动颜面。彼存心于丛林,岂浅浅哉?今少年苾刍见其画像,则指曰:‘这不通方汉也,死耶?’”(《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635页)
(69)《十三经注疏》本,第40页中。
(70)《石门文字禅》卷二五《题修僧史》,卷二六《题佛鉴僧宝传》、《题上人僧宝传》、《题宗上人僧宝传》。周裕锴《惠洪文字禅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一文已揭此条。
(71)《林间录》序,《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585页。
(72)道融《丛林盛事》序,《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52页。
(73)昙秀《人天宝鉴》序,《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97页。
(74)《云卧纪谈》序,《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页。
(75)《罗湖野录》序,《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二册,第961页。
(76)(79)《禅林宝训》序,《大正藏》卷四八,第1016页。
(77)(80)《枯崖漫录》序,《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143页。
(78)《罗湖野录》跋,《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二册,第1103页。
(81)《论语·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1页下,2483页上。
(82)《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8页。
(83)《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8页。
(84)《丛林盛事》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71页。
(85)《云卧纪谈》卷上,《卍续藏经》第一百四十八册,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