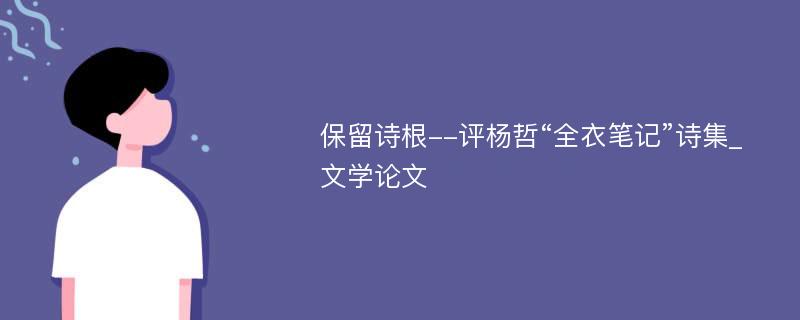
留住诗性的根——评杨兹举诗集《盛装的音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集论文,盛装论文,音符论文,评杨兹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兹举是一位校园诗人出身的学者,在新时期文学的全盛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担任过海南师范学院(现为海南师范大学)红帆诗社的社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琼州大学任教,专治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有不乏思想创见的研究鲁迅和赵树理的专著,在海南文化研究方面亦收获不菲。走上学术之路的杨兹举,诗歌写作似乎成了他治学从教的副业,然而,随着文学品鉴力的不断提高而诗艺日益精进,事实上他一直保持着海南本土优秀的诗人的创作地位,更重要的是,从他的诗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可以看出诗对于这位以文学安身立命的人文学者来说,具有确立其生存与言说价值的根基作用,因为他的诗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种语言事实,而富有在语言背后潜藏着的现代人愈来愈欠缺的诗性。诗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保留着人类对世界的初始经验,结合了心灵与精气,以强旺的感受力与生动的想象力,创造出主客浑融的感性世界,在这一感性世界里,寄寓了类的生存的根本诉求,因而作为思维方式的诗性对人来说具有本体意义。杨兹举的诗集《盛装的音符》,作为感悟、思想和情感的凝聚,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以倾吐或私语的方式留下了诗性这一生命之根。 诗集分为“盛装的音符”“高贵的寂寞”“凝重的沉思”“无声的澎湃”“温热的忆念”等五辑,从标题可以看出书写的心灵性,作为核心词的“音符”“寂寞”“沉思”“澎湃”和“忆念”,都是由外物或活动引起的主体的情感状态,但又不止于情感,因为对于知识人来说,他的情感活动不能不伴随着评价性的思考。情思发而为诗,成为公共性的艺术欣赏对象,但又保留了个人隐秘的信息,后者决定了诗歌表达对象征、隐喻和暗示等手法的运用,而这正是作者思维活动的诗性所在,同时,诗性思维也在生存感悟的表达中获得了用武之地。 杨兹举出生于被称为南溟奇甸的琼北侨乡文昌,生命的文化底色在这片受南洋文化影响的热土上铸就,形成了由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个体文化人格,富有进取精神而又沉稳笃定,具有开放的眼光而又脚踏实地。大学毕业后来到位于五指山民族地区的高校从教治学,耳濡目染于有别于沿海汉区的自然风物与民族风情,感性经验的对冲与本土情怀激起了他的诗思,赋予他的写作以新的在地性,给创作带来了别开生面的题材。“盛装的音符”一辑就是对海南岛南部黎苗生活区域自然与文化现象的观察与反映,是学者诗人的椰岛咏与黎乡情。诗中的常见意象明显带上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南国”“椰岛”“黎乡”“五指山”“橡胶林”“山民”“槟榔树”“木棉树”“凤凰树”“芒果树”“芭蕉叶”“牛铃”“船形屋”“寮房”“筒裙”“山兰酒”“三月三”“竹竿舞”“叶笛”“古俚曲”……从地域范围、具体地名,到人、植物、生产工具、居住与生活方式、民俗节日、审美文化,无不是对曾经以五指山为中心的琼南人文地理的语言刻画。兴许是为自然所赋予的生存条件相对优越,加上位置偏远,故而文化空气相对稀薄,黎苗山区呈现给外来者的更多的就是生命与生存的原生态。正是这样的原生态,激发和唤醒了诗人内心深处的生命感。面对“一片诚实的山野”“一片质朴的泥土”,诗人看到的是“最美丽的风景”“最伟大的风景”。美丽而伟大的“风景”,是自然本身,它的化身是“恣意盛开的木棉花”——“像凌空的焰火飞腾的彩霞/热气腾腾展示着健美的生命”,是“一颗颗饱满的山兰种子”——“贴近热烘烘大地的胸脯/像孩子激动时的心跳/一场甘霖过后禾苗飞扬/满野是荡开的碧绿歌谣”,是“哼唱一曲潺湲的清音”的山泉,“翻阅一迭厚厚的翠绿”的山风,是“在晨光中任性地飘香”的槟榔花,是“在清风里自由自在地摇晃”的芭蕉叶(《诚实的山野》);也是自然之子,是种山兰,也种橡胶,过三月三,跳竹竿舞,穿筒裙,吹叶笛,“把大自然揽进自己的心膛的/了无痕迹的交融中放任着性情/坦露正直也宣泄无羁”的“山野孑民”,竹竿舞里跃动着他们的生命形态——“黎姑娘们舞动着是盛装的音符”,“黎汉们舞动着是稳健的山鹰”。(《竹竿舞》)诗人或许出于某种政治伦理而把脱离狩猎和农耕文化不久的山民的生活诗意化了,但是谁能说更富有自然性的少数民族生民,他们的且耕且乐的生存方式,不是在人类文明进化的途中不经意地保留了生命与生俱来的诗性,即自由与娱乐精神。 如果说,杨兹举在对民族地区生活的体写中,在生命伦理意识的驱使下投射给对象世界以炽烈的诗性情愫,比如常常以性感语汇来表现自然物的生命姿态(如以女性譬写木棉树、橡胶树)的话,那么,在诗集的主体部分“高贵的寂寞”“凝重的沉思”“无声的澎湃”三辑里,无论是情爱心怀的表露,还是在历史遗迹前的沉思,无论是托物言志或以事喻理,还是对社会现象的批判,杨兹举的诗性智慧在自我与世界的对话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抒情诗人的卓越才华。 “高贵的寂寞”一辑所收的,大部分可作情诗观。爱情之为诗歌万古常新的题材,乃因人类的两性之爱具有超越生物需求的情感性,且两性吸引产生的情感具有最强的自我关切性和对象化表诉的迫切性,故而有言语活动就有因异性引起的抒情。杨兹举的情爱诗是他心灵史上的吉光片羽,是抒情主体性格与才情的对象化。有些诗像是青春恋情的告白,如《请求》《南方白梅》《深深的脚印》《野炊》《你把我吸成灰烬》等,在抒情方式上可以看到“朦胧诗”影响的痕迹,可知是他的早期之作,但其中仍然有极富抒情力量和个性的佳作,如《你把我吸成灰烬》,用火柴的燃烧形容失恋的创痛,进而用吸烟喻写恋人离去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以毁灭与消失来表现爱的一往情深的独特方式,最能说明爱恋异性的心灵性和它对于求证自我的生命本体意味。不论爱情事件的结局如何,对于爱的言说是爱的行为的美丽延伸,因为炽热的恋情已借助想象而物化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爱欲能让人走向极端,或者是行为,或者是心理,前者是由于人的自然性占了上风,后者是因为人意识到任何情况下都要有文明的风度。用诗歌来宣泄爱的情感,属于后一种情况,在这样的宣泄里,往往奔涌出决绝的情志,如《请求》的后面两节采用“要么……要么……”的祈使句式,在坚决的祈求里保持着人格的尊严,但是,更能给心灵带来震撼的是“让我纯洁得/像一具殉情的尸体”这样的惊悚表述,它是痴爱者心灵深处严正的悲情所产生出的残酷的诗意。“高贵的寂寞”里的情诗,抒写的不见得都是青春的恋情,如《举杯邀月》《日出》《再见》《蜡烛》《无法推算的一生》《最艰难的》《自挽》《等待》《往事》《痛苦的等待》《小船对港的絮语》诸篇,有些诗只能泛称为情事诗。但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是以近乎执拗的态度表现出情感的强度,这种情感往往圣洁而绝望。例如在活用“蜡烛成灰”这一情诗典故时,诗歌给出的是最违背爱的初衷的结局:“悔也悔不及了/我闪烁鬼火的眼睛/幽成葬丧无辜的坟茔”(《蜡烛》)。类似的以残缺为美、在遗憾中实现的,还有《日出》。诗歌选取“阳台”作为暗传情愫的通道,清晨或黄昏在此“忘情地迎迓”,这里盛满了不为人知的浓情深意——“一棵忘乎所以的恋心/郁绿生长中这样/为你初开的情窦而颤栗/不知道自己只是一盆盆景/向一个灿烂的憧憬/痴迷而盲目地献出微笑/一朵一朵地开/又一朵一朵地闭/走漏了多少心中芬芳的秘密”,原来又是一场单向的暗恋,爱的心声自然不会得到回应,结局照例不会完美。但是唯其残缺,美的对象才更引人遐想,它寓意没有实现的恋爱反而凸显了恋心的可贵与美好。在情感与想象的神奇撞击下,被比喻成爱神及其断臂的阳台,成了“情感的造型”而令人经久难忘。 “凝重的沉思”与“无声的澎湃”两辑里的诗歌,与爱情诗相比更富有社会性,这些作品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的诗性表达。能引起“凝重的沉思”的,有历史的遗迹,如长城石砖、古城墙、古玉、海瑞墓、卢沟桥,也有现实中的事物,如树、旱井、五指山、茅草屋等。诗人显然以现代的视角去看待民族的历史,从民族沉重的历史负担中看出了现实的沉滞或危机。一块从封建的灵柩里出土的古玉,在诗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古王朝的一块遗骨”,让人担心的是,假如它得到超度,则“臣民又要下跪/团城一堆痛苦”。这样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让诗人不得不发出疑问。《一块古玉引起的深思》所传达的对于封建幽灵的警惕性,正是一个具有启蒙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只有保持对封建主义的警觉,才能洞穿隐藏在历史形象背后的现实威胁,这是学者诗人特有的文化敏感性和诗性感觉。它也体现于《长城石砖》以超常的感觉能力感触到凝固在历史遗物里被人反复误读的历史启示:当在“荣耀千古的伟墙”面前,“举世倾听/一曲绵延不绝的昂扬”,长城石砖不动情衷,“如一片镜面/忍受膜拜者的遗忘”,而终于有人读懂了它——“轻轻我贴上/热辣的手掌/未曾惊动睡梦般的沉思/却受到一次强力的反弹/震荡我生命的血脉/体内顿时流遍历史的/苍凉”。以一个动作,表现对沉思的历史生命作出感应的震惊体验,独立苍茫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对只把长城当作景点的历史健忘症不啻是有力的针砭。 对历史的凝重沉思,归根结底是对族群命运的深切关注。《五指山》就是例证。奇妙的诗思,赋予五指山以生命,并用看手相这一推测命相的方式,勘定了祖祖辈辈栖居于此的山民的命运,表达了诗人对少数民族同胞的人生关怀。由“猎筒”和“竹梭”所象征的较为原始的生存方式,表明这个靠山吃山的生存群体仿佛停留在社会的历史进程之外,与人类整体文明的差距使得他们难以抵挡历史生活的风雨,因之作为现代文化载体的诗人无法不为他们的眼泪而叹息。诚然,诗人对于民族生活脚步的迟滞抱有复杂的情感,但诗歌里的价值取向却是确定的,就像《茅草屋》所写,虽说“解读不出茅草屋里的荣辱和悲欣”,但诗人觉得山里人更应面对的是广阔的山外世界的诱惑与招引。所以,茅草屋“作为山民粗犷和质朴的化身”,它所显示的是“缝补缺憾的悲壮和凄美”,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历史阶段并未结束。从诗歌摄取的这些沉默的民族生活历史图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文化人灼热的文明焦虑。 或许,对社会历史和现实保持反思与批判态度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共性,然而,杨兹举在体察生活世界和表达其感触与思虑时,表现出作为诗人学者的独特的致思方式,他总是以别致的感性形式传达自己的问题意识与理性精神。比如他把树比拟为歌星,突出了它在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检讨了我们破坏生态的愚蠢行为(《树的怀念》)。又如用掉进枯井的痛楚来譬写世俗舆论对不幸者的吞噬,批评了社会环境的欠缺人道(《枯井》)。再如用钢铁机器一路挺进,连蝮蛇都无处藏身来形容城市建设,非议了冰冷傲慢的现代化进程(《路道扩建》)。诗人眼中的世界不同于常人所见到的世界,乃因有诗心才有诗的眼睛。诗人的心灵好比最灵敏的天平,恪守着真实、正义和美的法则,只要世界出现任何失衡现象,它就会做出准确的反应,反应的结晶就是诗歌这种情感的形式。同常人一样,诗人的情感有些是个人化甚或是高度私人性的,但这种情感一旦找到客观对应物,“无声的澎湃”就会突破个体心理的阈限,引发更多的心灵事件,恰如充满隐喻性的《河的凝望》那首诗带给我们的阅读效果。坚持伫立原则的山,错失了流经它的河,而只能眼睁睁看着美丽被揉搓,目睹罪恶发生而产生的巨大愤懑,促使一个毁灭性的念头产生——“祈求海水倒逆/从山的脊背呼啸而至”,而绝对性的力量,足以使悲剧现实完全翻转——“一声灭顶巨响/满目闪烁”。从“无声的澎湃”到“满目闪烁”,道出了杨兹举的诗歌发生学,也显示出这位学者诗人的人格力量。 杨兹举教书育人,著文写诗,都充满激情而又十分严肃。他的一些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的诗歌,不乏对正直、有骨气、敬业、有作为的人格期许。《自爱》犹如他的自画像:爱惜自我形象,害怕自己的人生图纸被别人任意涂写,他于是“用一颗自爱心/制成橡皮/细细地辨认/细细地涂改/保持一种庄重的清晰”。《名字》也是自我审视:在他看来在生命这块土地上“名字只不过是/生生灭灭的/草”,但是名字也会因为人的所为而具有另外的意义——“用一生书写坦荡/名字/可以像一把绿火/燃烧/把所有恩怨/焚为肥料”。他咏柳,欣赏它“纤弱里/含有万般不可掐断的固执”(《柳》);他为红叶题诗,相信它“你会把一张发烫的履历/交给大地的”(《履历——题在红叶上的诗》)。《半截粉笔》掂量过半的职业生涯,无怨无悔坚持这一生的选择:“回首校对纯属多余/生命不能重撰一遍/剩下的另半截/就做笔直着一生信念的桅杆吧/总有一些需要摆渡的小叶帆/必须借助它的一往无前”。《死人骨头》更是令人震惊的咏物明志之作,作者从世人感到恐怖的死人头骨上看出了做人的真谛:“人啊假如没有骨头/那么死后/留什么当作他/曾经作为人的证据”。 诗集的最后一辑“温热的忆念”,以乡情诗居多,集中抒发了对于故乡的眷恋之情。在乡土中国,由乡村而城市、由故乡而异地是大多数文化人所经历的人生轨迹,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最初印象和早期的人生经验都来自于乡村,这些印象与经验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中不断发酵,不论何时何地,随时打开都醇香无比。说故乡是游子的生命之根,它的真实性在于对故乡的形象记忆经久不衰,它能够反复将独享回忆的人打动。这就是杨兹举为何会借《悬崖上的小草》来表达对土地的恋情的原因。生长于琼北,客居于琼南,变身为城市人的杨兹举,从未割断同故乡的心理联系。确然,“离别开放了这纯洁的怀念”(《怀念》)。让诗人无法不怀念的,是故乡深深的牛蹄印儿,盘在山村脖颈上的爱打扮的小路;低头沉思的屋檐,举首眺望的炊烟,椰花点染的烟雨;恣意嬉闹的泥香,长不大的童年;浑厚的乡音,儿时伙伴的乳名;纯朴的笑脸,沉重的叮咛;发生在相思园里的没有办法删改的故事;挂在二十岁嫩绿的枝丫上的灿烂而硕红的笑;覆天盖地如霞火,在心头旺旺地烧着温暖的那一声呼唤……这些根植于游子心灵深处的故乡景物、往年情事,在思念之情的浸润中浓稠似蜜,是无根的现代人最好的灵魂滋养剂。而对于杨兹举本人来说,故乡对于他的人生起长远作用的,还是他从这里获得了做人的启示,那就是要像故乡的木麻黄那样,质朴而诚实,有着“贫瘠中不枯萎的情意”,和“风中雨中不折扣的耿直”。(《故乡的木麻黄》) 这些乡情诗,同样体现了杨兹举处理心灵生活的艺术才华,例如一曲《蛙鼓》,就以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传达了乡村情怀的诗性。“蛙鼓”是乡土中国田园记忆里的一个重要的心理符号,它通过听觉记忆沉淀着少小离家者的乡村经验,因而它跟“蝉鸣”一样是文人思乡怀土的一个触媒。这首诗显然是写在异乡听到蛙声而产生思乡之情。读书致仕改变了一代一代乡村出身者的身份,但不论如何发达,这些从乡村里走出来文化人,在心灵里都愿意保留着最初的身份认同。正因为如此,“蛙鼓”对于“村孩子”来说,就是“稔熟的乡音”。在生命的声音记忆里,最重要最美好的又莫过于“摇篮曲”,所以乡音能够“催长思乡的雨季”。乡愁一旦在感觉里唤起,就会既浓且密还宽广,只有南方特有的“雨季”能够形容,“雨季”既用来拟写思乡之情的浓郁宽广无边无际,它本身又是心灵深处的故乡形象。心灵里的故乡,不是眼前的故乡,因而它是朦胧的,但在诗的逻辑里,它是被雨水沾染雨幕阻隔而变得朦胧混沌的。“朦胧”既是状态,又是施动者,因为它是乡愁主体的情感投射,有了这种投射,多情的才是故乡。人与故乡互为主客体,情感相互激发以致不可收拾,浓得化不开的情只有用“潮湿”可以暗示出来:情到深处谁说雨水不是泪水。诗的第一节以“烟雨”这一古典意象结穴,使寄寓情感的自然物象具有了人生况味和文化气韵,同时又以“椰花点染”这一南国特色与之交融,显示出情感表现的当下性。在诗中情感的起伏与意象的衍生是互为表里的,且始终遵循诗的想象逻辑。既然是蛙鼓引起思乡之情,那么,表达情感状态的潮湿的夜晚自然是被蛙鼓敲漏的;思乡之情在夜里更加强烈,被乡愁充斥的心之田野就跟雨季里自然的田野一样,潮湿得无边无际;无边无际的心之田野上长满了密蓬蓬的相思豆(暗用了王维的诗意),相思的对象是故乡,故乡也就成了这个田野上的不眠的夜行人:诗的第二节再一次用移情法把相思之情写得辽阔而深邃。诗人熟稔诗歌语言的本体性,运用顶真的修辞手法,把挥之不去的雨夜思乡之情表达得回环婉转,缠绵悱恻。并且顶真是用在两节诗的粘连处,就更增加了诗歌语言形体和声韵的美感。这首打上了地域印记的宣叙调诗歌,不愧为乡情诗的杰作。 有人说,做一个诗人是幸福的。大概指的是不论外在的物质生活是否给我们以满足与欢愉,诗人都是自满自足自娱自乐的,因为他(她)拥有一个远比外部世界精彩得多的内在世界,这个世界固然是外部世界的投影,且跟诗人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有关,但它更是诗人的情感、思想和想象在语言魔法下的神奇幻化,就像上帝创造了世界并赋予万物以秩序一样,诗人用它的具有原始性的思维创造了充满动感和交互性而又秩序化的意象世界,这一世界同样依傍于永恒的真理,囚禁于肉身的躁动的灵魂,唯有在这个世界里才得以休憩。诗歌不仅自度还能度人,诗人俨然超拔俗世成为指点迷津的灵魂牧师,这也是所有现实中人需要诗歌和社会需要诗人的理由。在这样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关系中,杨兹举是幸运的。他不仅以体悟性强与见解独特的现当代作家研究专著和最受学生欢迎的课堂教学,证明了他是一名有成就的学者、教授,还以《盛装的音符》这部达到相当艺术水准的诗集,证明了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在今天的大学中文系里,可以做文学研究同时又能搞文学创作的兼学者与作家于一身的人并不多见,比起民国时代大学中文系作家云集来,当代中国(台湾地区是个例外)大学文学教育主体强于研究而弱于创作。不少从事文学教学和评论研究的教员,很难说真正有文学兴趣,更谈不上融文学与生命为一体,这些人可能有学问有成果但缺少的却是对一个文学从业者来说最为重要的诗性情怀,他们太学者化而拒绝做一个文学家。它带来的问题已日益严重,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学中文系的师生对教学研究和学习考查对象之外的作家作品几乎不甚关注,文学阅读范围窄,文学鉴赏能力和艺术判断力普遍下降,造成文学审美独特的社会功能难以实现,而为其推波助澜的理论依据则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和文学作品并不存在文学性之说。然而我们不能把问题产生的根源都推到当代教育和学术评价体制上去,起决定作用的应是文学教育主体自身的文化质地,即是不是葆有情感与想象都十分活跃的诗性思维,通过这样的思维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以避免完全迷失于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功利性。学者杨兹举正是用他的诗歌创作,为文学研究主体保留诗的根性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