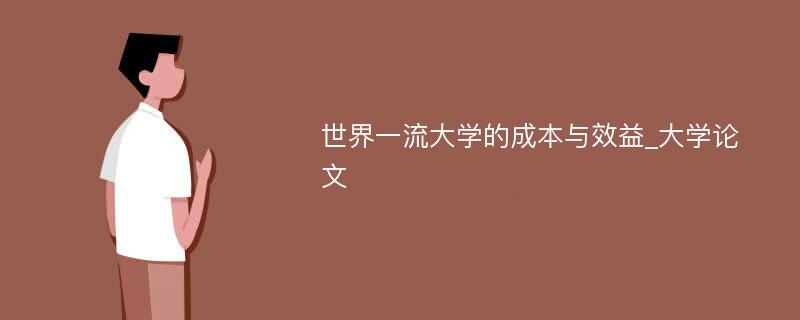
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本与收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益论文,成本论文,世界一流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个人都希望上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一个国家觉得自己可以没有世界一流大学。问题是,人们并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该怎样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大家又经常提到这个词。通过Google搜索,我们发现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词条成千上万,而且很多院校——从位于加拿大中部的相对一般化的学术性大学到新成立的位于波斯湾的学院——都自称为“世界一流”。当今是一个存在着学术炒作现象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大学纷纷声称自己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尊贵地位,但它们通常缺乏有力的理由。那些孜孜不倦地想确认“世界一流大学”的人在这样做时,往往也不知所云。例如《亚洲周刊》(Asiaweek),这份香港出版的、颇有影响的杂志曾经连续好几年对亚洲的大学进行排名,直到它的行为广受非议为止。本文将尝试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界定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并且论证:对大学而言,成为“国家一流”或者“地区一流”是同等重要的,不要去竭力追赶那些最富有的、在许多方面都胜一筹的大学。
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一位在19世纪后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达40年之久的学者,当被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问及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些什么时,他的回答是“5000万美金和200年”。事实证明他错了。在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就只用了20年及稍微多于5000万美金(由洛克菲勒自己捐赠)的资金就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成本又不一样了,不只是因为通货膨胀,而且因为高等院校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费用也极为昂贵,与此同时,当前的竞争也激烈多了。现在,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也许要花费五亿美金的资金,有精明的领导和足够的运气。
世界一流大学并不多见。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多层次、多样化的。这里,我们关注的只是那些为数甚少的、寻求成为国家或国际高等教育系统顶尖大学的高校。在美国,顶尖大学的数量很少。一般被视为精英俱乐部的美国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自20世纪初成立至今,其成员仅仅有节制地增加,到现在也就是50多个会员(其中很多大学并非世界一流)——而全美国则有3500多所高等院校。即便在美国,大学也极少是为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办学的。在别的国家,顶尖院校的数量同样很小,即使在德国政府对大学的预算和任务基本一致对待时也不例外。最精英化的大学只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国家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亚洲华尔街杂志》(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列出了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其中只有四所不在美国,它们分别是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索邦)和东京大学。
当然,是他人的评价使一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院校之列的。但问题是,现在没有人能够设计出一套合适的国际评价体系。在此,我们无意提出这类指标,但是,这样的讨论或许至少是研究发展有关评判依据的第一步。
界定
极少有人试图给世界一流大学下定义。下述各项特征决不会为诸多的专家组合所一致认同——这只是一种建立若干水准基点的努力,它将为研究和讨论奠定基础。在词典里,世界一流的意思是“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达到了国际卓越的标准”。定义够清晰的了,但是在高等教育界,由谁来判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判断一所大学是否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有关必要特征。
科研卓越是世界一流大学概念的核心——必须那些是广为同行认可的、能够推进知识前沿的科研。这些科研可以测评,也可以进行交流。如果说科研是中心因素,一所大学所具备的其他因素对于出色的科研也是必要的。一流的教授群体当然是主要的因素。然而,为了吸引和保有最好的学术人员,还必须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它们包括职业保障的安排——很多国家称其为终身制教职(tenure)——与适当的工资和收益,尽管学术工作者并不一定要求高薪酬。最优秀的教授将他们的工作视为一种“内心倾向”——受知识兴趣的驱使,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
学术自由与知识氛围对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教授和学生必须拥有追求知识——无论这些知识引向何处——的自由;同时,他们还应该可以自由地出版他们的著述而不用担心来自学校或者外部的压力。有些国家给予那些无关政治的硬科学领域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在更为敏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则有所限制。在大多数国家,学术自由扩大到既可以在狭窄的专业领域内也可以就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发表意见。
院校管理也很重要。世界一流大学都有由一些法令、章程保障的重要内部自我管理措施和传统,以确保对这个学术共同体(一般指教授,有时也包括学生)学术生活的核心部分(招生、课程、学位授予标准、选聘新教员与院校工作的基本方向)的控制。
充足的设施对于院校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最前沿、最有创造力的研究和最有革新性的教学都需要有相应的图书馆、实验室,以及互联网和其他电子资源。随着科学与学术的复杂化和扩展,要完全做到如此就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尽管互联网可以节约一定的学术费用,并且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接触到多种知识,但是,它绝对不是一剂万能药。学术设施不只限于图书馆和实验室——教师和学生还必须拥有足够的办公室。
最后,学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有足以支持科研、教学和其他大学职能的资金。维持一所纷繁复杂的高等院校不仅费用高昂,对它的资助还必须是一贯的、长期的。维持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经费在持续增加,因为科学研究越来越复杂,成本也越来越高。由自动化导致的多数教学生产率提高不能使大学受益,因为教与学一般仍然需要师生之间的直接接触。在当前环境下,获得资金构成了一项特别的挑战,因为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缩减高等教育经费。各地都要求高等院校通过收取学杂费、提供咨询服务、出售科研产品以及其他创收活动来支付日益增加的部分预算费用。事实上,任何地方的研究型大学都离不开公共经费。仅仅在美国和日本一小部分地区,才存在最好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而且,美国政府通过政府科研拨款与向学生贷款、拨款等方式给高等教育以有力的支持。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捐赠。美国的税收制度规定,凡是为非营利机构(如大学)捐款都可以不纳税,这种税收制度是美国的世界一流私立大学成长的重要因素。研究型大学有能力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但是持续而充分的公共财政支持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资金,要想建设和维持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告诫
在考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时,需要有一种现实而客观的观点。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即便是那些大国而且相对富裕的国家,也只可能或者说只需要建成一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对许多国家来说,支持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超出了他们能力允许的范围。研究型大学居于一国多样化的院校系统的顶端,这一系统中的剩余部分与这个顶端同样重要。
即使是最好的大学也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例如,哈佛大学工程专业的排名就不在最前列。对很多国家和高等院校来说,集中建设一些世界一流的院系、研究所(特别是在那些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可能更为适宜。例如,马来西亚的高等院校就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和橡胶技术方面的学科,而这些对当地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少数高水平院校是很专门化的。以加州理工学院为例,这是一个主要以科学领域为中心的小型大学,但是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消息,它在美国大学中排名第四。一些专于有限领域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在印度和国际上都受到了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这样的院校还提供了学科领域宽广的受教育机会,使学生能够选择并且获得跨学科工作的机会。
没有人提出了一套学术界认为可以接受或经得起严肃批评的对大学进行国际(甚或只是国内)排名的方法。现在,高校排行榜有很多种——它们一般都强调与研究型大学有关的特征。尽管这样,没有几种排名是由官方组织或者著名研究机构主持完成的。报纸和杂志做了绝大多数排名工作,就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只有少数排名是严肃的。这么说来,我们现在既没有合理的国家大学排名,也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关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以便人们辨认或追求这样的院校。在这里,我想引用一种可能不太恰当的说法,即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关于色情文学的见解:“当我看到它,我就知道了它。”
过分强调
过于强调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可能会损害某一特定的大学或院校系统。这样做有可能使得精力和资源偏离更重要并且可能更实际的目标。它或许会使人们以牺牲大学的入学率与为国家服务为代价,将精力过多地投在了建设研究型大学也就是精英大学上。它也有可能导致提出一些不现实的期望,以致有损教师的信心和工作表现。
世界一流大学理念反映了当前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研究型院校——尤其那些美国和西欧重要国家的大学的规范和价值观。世界一流大学理念源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它在19世纪末成为一种主流大学观,尤其是在这种模式为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接受后。尽管世界各地大学在本质上都是遵循西方传统的,关于研究型大学的世界一流理念还是体现出了这一传统的不同变式。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美国大学正在偏离学术目标和观念的多样化,因为它们在挤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这座“独木桥”,谋求成为像哈佛、伯克利或者其他为数甚少的重点研究型大学。现在,当世界各地大学似乎都把自身定位于这一单一的院校理想时,我们也可以作出与之类似的批评。高等院校,还有国家,在发起一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之前,需仔细考量自己的需求、资源与长远利益。
大学的运转是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世界一流是一种基于全球视野的观念。它意味着,某所大学正在与世界最好院校竞争,并追求成为最杰出的院校和得到公认。国家之间甚至地区之间大学的现实情况是有差异的。它们与当前的社会和经济需求有关,并包括一个对地方社区需求的回应问题。在这些不同的背景下,院校表现和院校角色的性质是各不相同的。指称一所大学为“世界一流”而将其他院校归入学术等级的底端,这种情况可能是难免的,但也是不幸的。将建设一流大学与这些不同的实际联系起来,这并不容易,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
展望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些国家譬如中国,政府和院校规划者就很关注这个话题,这个国家的几所顶尖大学都在自觉地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其他国家如韩国,对这个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英国,这个传统上一些顶尖大学的故乡,现在也在担心要失去其优势地位。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能够带来的一个重要益处就是——它关注学术标准及其改进,关注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高等院校怎样适应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乃至全球学术界。追求卓越并不是一件坏事,竞争也可能会激发进步。然而,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观点,并且要维护公共利益。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概念的模糊与其不现实性相关,就目前来说,最起码,要测评高等院校的质量和成就就很困难。实际上,这样选择可能更加合适一些:高等教育的精力和资源要聚集在更为现实的和可能更为实用的目标上。
致谢: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以下人士的作品和观点: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新加坡管理大学Pang Eng Fong和Linda Lim,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我还受惠于爱德华·希尔斯、马克斯·韦伯和约翰·亨利·纽曼关于大学本质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