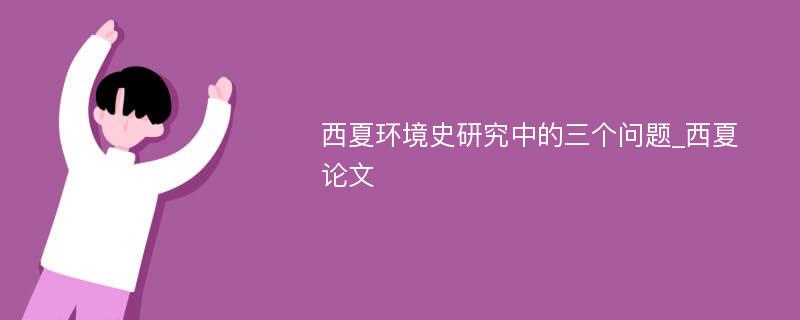
西夏环境史研究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史研究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2-0013-07
一、西夏境内的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是环境状况的指示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的变化幅度远远大于植被的变化。因此,对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的考察不仅可以知晓野生动物本身的种群分布、迁徙状况,而且还可以根据野生动物的分布和规模来推测某一地区的植被、气候等环境状况,以此来丰富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不过,资料的状况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拙文仅就所见资料辑出西夏境内的数种野生动物,同时就西夏境内个别家养动物也一并予以考论。
(一)犛牛 《西夏书事》卷3载:“夏四月,彝兴献犛牛一。犛牛生西羌,似牛而尾甚长……异产也。彝兴得之,遣使以献。”[1] (32)《天盛律令》亦载:“犛牛在燕支山、贺兰山两地中,燕支山土地好,因是犛牛地……贺兰山有犛牛处之数,年年七八月间,前内侍中当派一实信人往视之,已育成之幼犊当依数注册。”[2] (577)犛牛即牦牛。文献明指西夏时期在贺兰山、祁连山地区有犛牛生息,但文献中的犛牛应为人工放养。不过西夏时期也有野牦牛,如《月月乐诗》中讲“在这强大的国家里,到处是潺潺流水,草儿葱绿,人们在山上猎杀野牦牛”[3] (14)。再则,既然贺兰山、祁连山等地适于畜养的牦牛生存,想必当时这里也有野牦牛活动。牦牛的存在,反映了西夏时期贺兰山、祁连山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鹿 《太平寰宇记》卷172载:“河西出齿鹿,足短而形大,如牛,肉千斤。”可见西夏时期河西地区(指河套和河西走廊)有体形庞大的鹿。文献中所谓的“齿鹿”具体为何种属,恕无能奉告。有学者发现中古时期华北(指北方)边缘地带,特别是临近草原地带,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如阴山地区[4] (43)。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卷1中也讲到:“北地产鹿,有倍大于中国(指中原地区)者,鹿角近根实处,刻以为环,肉好相半,内虚可贮物,谓之鹿顶合。”概指宋代中国北方的鹿不仅体形硕大,而且鹿角很有特点。笔者曾注意到,在西夏谚语中频繁地提到鹿,如194条:“犹如五月骆驼命终而倒,犹如十月黑鹿伏劫处逃”;203条:“要藏匿不易,鹿枝角已露出,观赏还可以,敬虎豹皮有愧”;236条:“良男所去狭地树中,黑鹿去,角也不得”;300条:“夜闻鹿鸣天晓,日见鹃啼天晚。”[5] (16-23)西夏文献《月月乐诗》中也有人们追捕鹿群的生动描写。鹿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西夏谚语和宫廷诗中,反映出西夏人不仅对鹿存有一种亲切感,而且相当熟悉,甚至在西夏的生活器皿上也刻有鹿的图案。如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政府附近出土了一件西夏酱釉剔花瓶[6] (925),近底部处刻一鹿,鹿回首做惊惧状,口中喷出一团云雾。鹿刻比例十分恰当,线条流畅,具有写实性①。综合以上信息,笔者认为西夏时期河套、河西走廊等地区应该分布着众多鹿群,反映出这些区域保持着良好的草原生态系统。需要注意的是,上引西夏谚语中出现“黑鹿”。在现代鹿的种属分类里,黑鹿又称水鹿,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西北地区仅青海有零星分布)。西夏文献的黑鹿是否就是现在的水鹿,存疑待考(笔者推测,西夏境内的鹿应多为马鹿)。此外,《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地理典籍中均记载了夏州、庆州、延州等州县需要向朝廷进贡麝,表明当时这里有麝类分布。
(三)虎 《西夏书事》卷3:“继迁善骑射,饶智数。尝从十余骑出猎,有虎突从山阪下,继迁令从骑悉入柏林中,自引弓踞树巅,一发中虎眼,毙之。蕃部由是知名,光睿爱其勇,遂授以官。”[1] (33)李继迁早期活动于河套地区,这条文献很可能就是李氏在河套附近狩猎的记载。在西夏谚语中老虎的出现率极高,如53条:“龙欲青水何时尽,虎奋黑山何时休”;88条:“勇鹰险处抓兔子,老虎情面狐饮酥”;96条:“狼狗一狂乃为群,虎豹降服随路行”;142条:“虎豹威仪,美狐出去,深水苇长,老马憋气”[5] (9-13)等等。西夏谚语是西夏社会面貌的真实反映,其中也包括一些自然界的状况。老虎在西夏谚语中的频繁出现很可能表明西夏境内有老虎活动。上引《圣立义海》中讲到西夏天都山有虎、豹、鹿、獐等野生动物。《金史》卷4《熙宗纪》也记载:“上如东京,壬子,畋于沙河,射虎获之。”沙河地望无考(概为金东京附近),但表明当时老虎时常出没。据笔者在博士论文《西夏地理研究》中初步考证,西夏境内存在三块较大的天然林区:贺兰山(包括贺兰山东麓)、阴山(包括乌拉尔山)、屈吴山和六盘山。这也是古今自然景观差异最大的区域。森林生态系统有维系老虎生存的食物链,因此西夏时期的老虎极有可能分布在上述林区。
(四)骆驼 宋代文献中又称骆驼为橐驼。由于西夏是沙漠王国,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也是西夏重要的运输工具。《西夏书事》卷27云:“(秉常)以遗马、白驼入献(辽朝)。”[1] (312)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白驼了。又宋人张亢言:“陕西民差配之苦,数倍常岁,止如鄜州买骆驼、骡驴、牛羊、红花、紫草、桥瓦……”[7] (卷128,3208)可见骆驼也是宋夏贸易中的商品。《蒙兀儿史记》卷2《成吉思可汗》载:“(蒙古)围力吉里寨,数日,拔而夷之。复下乞邻古撒城,经落思城,大掠人畜,所获畜产,橐驼最多。”力吉里寨、乞邻古撒城、落思城具体地望不详,但大致处于西夏西北部疆土,这一带至今骆驼的数量也很可观。《马可波罗行记》第72章亦载:“(唐古特)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美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唐古特即为西夏,可见西夏境内骆驼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西夏境内是否有野骆驼分布?宋代史籍中确载西北地区有野骆驼活动。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嘉祐本草图经》载:“野骆驼出塞北、河西,今惟西北蕃界有之。”② 文献中“西北蕃界”应该包括西夏地区。由此可见,西夏境内确有野骆驼分布。
需要指出的是,西夏境内人工喂养骆驼的数量十分庞大,分布较为广泛。这一点可以从文献中反映出来。如《宋史》卷334《高永能传》载:“(宋夏)鏖战于无定河,斩首数千级,得马三千,橐驼牛羊万计。”文献讲述的是在今陕北一带有大量的家养骆驼,甚至在宋夏沿边有以骆驼命名的地名,如绥远寨又名骆驼巷,在今陕北吴旗县境内。又《宋会要》兵八之62载:“移灵州城下,先锋遇贼接战,斩首二百七十二级,生擒四十三人,夺马牛羊驼畜万余,粮草五万余。”显然西夏时期的灵州地区亦有大量骆驼。同书又载“李宪引兵至汝遮谷,贼众数万,牛羊驼畜充满川谷。”汝遮谷大致在今天甘肃省的祖厉河谷境内,可见当时这里也有家养骆驼分布。撮要言之,西夏时期东起无定河谷,西到兰州的宋夏沿边地带均有大量家养骆驼。1997年,在甘肃省环县发现一座宋代彩绘砖雕墓,其中有两块牵骆驼砖雕,即为以男子手握缰绳牵引骆驼的形象。此外还有静卧或者站立骆驼的砖雕[8]。古人有“事死如视生”的信念,该墓中画像砖所反映的内容应为墓主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宋夏沿边骆驼的普遍。当然,黑水城以及河西走廊地区也应有家养甚至野生骆驼。西夏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是否也有野骆驼或者家养骆驼,由于史籍阙载,难以定论。不过从无定河谷有骆驼分布的事实推测,鄂尔多斯也应有骆驼分布,因为鄂尔多斯干草原更具有骆驼生存的自然环境。由此可见,骆驼是西夏境内十分普及的动物。相比之下,现在西北地区骆驼的分布范围则主要退缩至贺兰山以西地区了。
西夏家养骆驼的用途是什么呢?笔者分析,除了食用、皮毛等功用外,西夏家养骆驼的主要目的恐怕是为了负载运输,是当时主要的畜力工具③。北宋边臣赵卨曾奏:“乞兑经略司封椿钱十万缗,就河东近便州军收籴军储,用骆驼转至延州。比本路籴价甚有余息,可速施行。”[7] (卷250,6097)正是由于骆驼在西夏的交通运输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西夏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对骆驼的畜养、宰杀作出了种种规定。例如不能擅自屠杀骆驼;由于各种原因致骆驼死亡后,主人当告知相关部门等等[2] (154)。有趣的是,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有一人手牵骆驼穿行于东京城内的情景,画中的骆驼究竟来自西域、西夏还是辽朝已不得而知,但反映出当时骆驼作为畜力工具的普遍性。
(五)野马 野马与家马相类似,具有头大、耳小、鬣毛短而直立、额毛较短等体质特点。历史时期野马曾经十分广泛地分布于中国北方地区。西北地区也曾是野马的重要活动范围。《北史》卷58《周宗室诸王传》载:“(宇文贵)从(宇文)宪猎于盐州,一围中手射野马一十有五。”由此可知北周时期在今天陕西定边、宁夏盐池一带有野马群活动,数量十分可观。不过文献讲的是公元6世纪的情况。西夏时期的状况如何呢?西夏谚语第278条曰:“愚童讼权贵,野马制于索。”[5] (22)宁夏及其周边地区有野马分布的状况至少延续到明清时期,因为《嘉靖宁夏新志》确载:“灵州贡红蓝、甘草、苁蓉……麝、野马、鹿。”[9] (26)在《乾隆宁夏府志》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在古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生产力水平等因素,自然生态的演进相对缓慢,西夏时期上述地区亦有数量可观的野马就不足为奇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时期野驴的分布范围与野马大致相同,唐代宁夏也曾是野驴的重要产地。18世纪以后,野马、野驴的分布范围开始急剧退缩[10]。西夏境内是否有野驴分布,史籍无载,今人就不得而知了。
(六)狼 《金史》卷23《五行志》载:“秦、陕狼害人。”西夏谚语中有关狼的条目也较多,如90条:“老狼啼哭不掉泪,大鸟咬物没有牙”;115条:“苦蕖根须籽九苦,豺狼小崽小又腥”;119条:“引鸽翅膀遮远山,老狼足迹遍山谷”[5] (11)。直到解放前西北许多地方还有野狼出没。不难理解,西夏境内的狼应较为常见。
(七)鹦鹉 宋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卷17中讲到:“有关中商得鹦鹉于陇山,能人言,商爱之。”又《太平寰宇记》卷31“陇州”条下载:“土产,龙须席、鹦鹉、山丹等。”宋代的陇山不仅指今陕西陇县、千阳境内的山脉(今天之陇山,实为六盘山之余脉),而且还包括了今天的六盘山区,范围比今天的陇山大得多。上述文献表明,宋代在今天宁夏南部六盘山区一带有鹦鹉分布,而宁夏北部的贺兰山也一直是鹦鹉产地。《乾隆宁夏府志》卷4“物产”条下载有“鹦鹉”、“鸬鹚”等禽类[11] (114)。事实上,清代西北史籍中对鹦鹉多有记载,如《西宁府新志》《兰州府志》《皋兰县志》等等,反映出清时鹦鹉是西北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禽类。学术界一般认为贺兰山是文献记载中我国鹦鹉分布的最北地区,即为北纬39°附近[12]。可以想见,西夏境内不仅有大量的鹦鹉,其他禽类的数量也蔚为可观。
此外,西夏谚语中出现有黄羊、狐狸等野生动物,如164条:“空中鸟飞,叫鸣两种,谷境黄羊,顺弛一返”;204条:“草间鹌鹑学大雁叫,口破裂,草中兔子学黄羊跳,腰闪折”;114条:“狐叫起来气欲绝,狗蹲下来尾巴夹”;220条:“宁为危境虎噬,不为沟中狐食我”等等[5] (12-18)。《蕃汉合时掌中珠》《文海》等西夏文献中也载有虎、豹、狼、鹿、黄羊、野狐等野生动物,同时还记载了捕捉、网套、圈套、烟熏等狩猎方法,反映了西夏境内分布有丰富的野生动物。篇幅所限,恕不一一详解。
以上就资料所见的西夏野生动物枚举数例,事实上西夏境内的野生动物远远不止于此。一些野生动物在今西北地区已经绝迹,如老虎;其余的种群数量也在急剧减少,如鹿、麝、野马、黄羊等等。这种状况反映了这些动物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二、西夏时期自然环境遭受破坏之表现
某一历史时期对自然环境的人为破坏方式主要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如进入工业时代,工业污染就成为十分突出的环境问题;而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大规模的垦殖、战争是人为破坏自然环境的主要形式。就西夏而言,战争、垦殖、修筑城寨以及樵采是对自然环境有着较大影响的几种活动。
(一)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讲,西夏是带有军事色彩的民族政权。纵观西夏历史,大大小小的战事首尾不绝,自然给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西夏大举南下时,就有烧杀掳掠的的行为。“(西夏)分攻柔远寨,烧屈乞等三村,栅段木岭,势甚张。”“去秋(西夏)乃复入叩大顺,围迫城寨,焚烧村落,抗敌官兵,边奏屡闻,人情共愤。”[1] (244)西夏甚至采取焚烧大片草地的办法来阻止辽军的南下。如在夏辽河套之役中,“囊霄(元昊)以未得成,言退三十里候之。凡三退,将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马无食,因许和”[1] (203)。焚烧草地,断其粮草,确为抽薪之举。明朝在防御鞑靼时也曾使用过此类“战术”。当然,战争使得民众逃亡,土地撂荒,间接地对生态与植被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垦殖 宋夏双方在边界集结大量军队,为保证粮食供给,双方(尤其是北宋)在沿边大肆垦殖,从而导致林地或草地面积减少。史载:“诸监以草地充屯田,遣卒种艺,所入不充其费。”[7] (卷67,1490)明确指出利用草地进行垦殖。又泾原路经略司言:“本路弓箭手阙地九千七百顷,以渭州、陇山一带山原坡地四千余顷,可募弓箭手二千人,诸佃户或不愿应募。”[7] (卷312,7573)可见宋夏沿边的垦殖活动开始面向山地,而这些山地很可能就是疏林地带。事实上,在城寨密集的宋夏沿边地带,每一个城寨基本上就是一个屯垦的据点。如范仲淹言:“臣观今之边寨,皆可使弓(箭)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7] (卷134,3202)有人估计仅北宋时期陕西沿边垦殖的土地就不下十万余顷[13]。垦殖对草地和林木的破坏便可想而知了。宋夏沿边的垦殖活动还对黄河泛滥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修筑城寨 宋朝没有修筑长城,但宋夏双方在缘边修筑城寨及烽燧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宋夏双方通过修筑堡寨的方式筑起一道防御对方进犯的“长城”。初步估算,北宋在宋夏沿边修筑的城寨数量近三百座(不包括西夏境内的城寨)。修筑这些城寨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需要许多木材,沿边地带的林木就成了砍伐的对象。陕西宣抚使韩琦言:“其土功自以为百万计,仍须采山林以修敌栅、战楼、廨舍、军营及防城器用。”[7] (卷145,3512)修筑城寨的一部分木材是由军士们自己砍伐,有一些则通过购买沿边民户的木材。“元祐中给赐城寨,唯鄜延路米脂、浮图未曾修筑,将来秋冬,西贼万一困弱,可乘机便,次第修复,预计材植防城楼橹并版筑之具。况见今修葺沿边城寨及楼橹之类,若以此为名,选将佐量带兵甲领役兵于边界采木及优立价值,召蕃汉人户于沿边城寨中卖应用,免致于近里计置搬运。”[14] (7628)蕃汉人户的材木从何而得呢?恐怕只能从就近的山林中砍伐。如果修筑一座城寨需要100棵成树的话,300座城寨就需要3万棵成材的树木,对于基本为疏林、土山的宋夏沿边地区而言,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不仅如此,在战事中所用的器械、工具、道路的修筑等也需要砍伐沿边树木。史载:“凡出兵深入贼境,其济渡之备,军中自有过索,浑脱(羊皮筏子)之类……令种谔如将及河造筏,贼界屋并可毁拆,或斩林木相兼用之,如更不足,以至枪排皆可济渡。”[7] (卷316,7643)可见在战争中,北宋军士连沿边民众的房屋都不放过,更何况沿边的林木。当然,就修筑城寨这一点而言,北宋应比西夏负有更多的生态责任。
(四)樵采 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北宋时期居民开始生活用煤,但应该说,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煤还是奢侈品,樵采是他们获得御寒燃料的主要方式。宋夏沿边戍边军士的状况恐怕亦是如此。宋臣范仲淹言:“陕西虽有兵近二十万,戍城寨二百余处,所留极少。”[7] (卷132,3130)“环庆一路四州,共二十六寨,将佐十人,兵马五万。”[7] (卷143,3457)北宋在宋夏缘边布置的军队大约为30万左右;沿边蕃汉民众的人口数量也十分可观:“自环庆低于泾原,沿边属户,逾数十万。”[7] (卷133,3176)环庆、泾原路缘边属户为10万,以每户5人计算为50万人。横山地区的属户数目不详,文献中有这里“民众繁庶”的记载④。考虑到这里地区没有环庆、泾原路广阔,保守估计其属户为环庆、泾原路之一半,即以5万户计算,也有25万户民众分布在这里。这样,宋夏沿边地区至少有100多万人。
大规模人口的生活用薪就很成问题,沿边的山林、草地便成为掠取的对象。《西夏书事》卷28载:“元祐二年九月,(保忠)令军士四散樵采,焚庐舍,毁冢墓。”[1] (320)宋人张舜民在《西征途中二绝》中讲到:“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虽然作者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沿边官军、民众砍伐林木来充薪无疑是历史事实⑤。由于樵采是当时生活用薪的主要手段,北宋政府专门过问宋辽边界的樵采情况:“北人有无侵越旧界,及边人有无侵北界地樵采,具图以闻。”[7] (卷315,7621)河东路提点刑狱黄廉言:“准朝旨往代州定验有无人侵北界地采薪……内有道近铺屋及密抵林木,委是人迹往还,本铺守卒朝夕采薪,舍远就近,不能无之,及有避远取直过往,虽非采薪,亦不当直过。”[7] (卷319,7705)可见樵采在当时不仅十分普遍,还是边境军士重点防范的事情。
除上述几种人为破坏环境的方式外,西夏统治者在天都山、贺兰山等地修筑了规模宏伟的离宫,这些建筑也需要砍伐大量的优质木材。西夏政府甚至还成立了“木材租院”[2] (534),是为砍伐木材的“配套机构”。此外,修筑陵墓、西夏民众的取暖用材等等都需要砍伐树木,西夏民众的捕猎行为、过重的草场载畜量等均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当然,自然因素也是诱发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如连续的干旱加速了土地沙化的过程,暴雨会使坡度较陡的植被受到破坏。还需提及的是,在灭火技术甚低的古代社会,森林火灾是使森林毁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清末贺兰山曾发生11次以上森林火灾。清末苏峪口内、黄渠口内的林火亦曾延烧数月[15] (270)。
三、西夏人朴素的环保和生态意识
史籍中无西夏环境保护意识的明确记载,更无圣贤鸿儒有关此问题的直接记述。因此,很难讲西夏已经具备了保护环境的意识,更难以上升到思想史的层面。拙文讨论的有关环保意识无非是通过西夏政府的一些法律条文、出土文书等资料所反映的西夏民众对环境保护的一些行为和态度。西夏政府和民众是否在主观上具有了环境保护的思想,不得而知,但其一些做法在客观上对保护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天盛律令》中有关保护环境的措施 《天盛律令》记载了不少保护环境的措施,如关于植树以及对毁坏树木处罚的规定。《天盛律令·地水杂罪门》载:“沿唐徕、汉延诸官渠等租户、官私家主地方至处,当沿所属渠种植柳、柏、杨、榆及其他种种树,令其成材,与原先种下的树木一同监护,除依时节剪枝条及伐而另植以外,不许诸人伐之。”“沿渠干官植树中,不许剥皮及以斧斤斫刻等。若违律时,与树全伐同样判断。”[2] (505)西夏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在水渠边上植树:“渠水巡检、渠主沿所属渠干不紧紧指挥租户家主,沿官渠不令植树时,渠主十三杖,渠水十杖,并令植树”[2] (506)等等。可见西夏人已知道用生物方法来加固渠道和进行绿化,并且注意到所植树木的多样性。种植树木的多样性不仅能够制造美景,同时也有利于病虫害的防治。上述西夏法律条文颇具“植树法”味道,对于今天宁夏平原渠道的管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西夏还设立专门的机构对贺兰山等地的林地与草场进行管护。《天盛律令·事过问典迟门》载有:“贺兰山等护林场、养草滩等护院”[2] (319),虽然该书未明载这些机构的具体职能,但从名称可以判断出应是对贺兰山等林地、草地进行维护和管理的机构。此外,《天盛律令》还有针对动物的专门规定。如《天盛律令·盗杀牛骆驼马门》中规定:“诸人杀自属牛、骆驼、马时,不论大小,杀一头徒四年,杀两头徒五年,杀三头以上一律徒六年”[2] (154)。甚至对普通的猪、狗等动物都不能随便射杀:“诸人刺射、斫杀羖羊、狗、猪等,则有官罚五缗,庶人十杖。”[2] (391)对伤害动物的处罚最高可达徒10年。
(二)西夏民众对植树造林的重视 除了前引《天盛律令》中有一些关于植树造林的规定外,一些文献也反映出西夏普通民众植树造林的信息。《圣立义海》载:“树本土生,扩林植山。诸鸟夜宿,诸兽昼隐。夏日阴凉,冬时庇暖。”“(劈旺)秀山:载种种树,亦有果树。鹿、獐居。”[3] (60)西北大部分地区缺林少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西夏先民们懂得通过栽种树木来改善生存环境,并且意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对气候的调节作用。黑水城出土的一件文书(F257:W6)讲到:“各家园内栽□□,倘若依例每丁栽树二十株,却缘本处地土多系硝碱沙漠石川,不宜种。”[16] (101)由于原件残缺,不能准确完整地判读文书的内容,但可以看出政府有每个丁必须植树的规定,有似于今天义务植树的规定。综合这些信息分析,西夏不仅在京畿附近植树,而且要求其他地区的民众植树造林,甚至在西夏谚语中能找到植树和保护树木的信息,如92条:“铺石高下谁察度,植树长短谁度察。”不仅有民众植树,似乎还有人检查植树的效果。101条:“瑞树草上勿研毒,白(米)柏上勿涂朱。”[5] (11)由于西北地区少见林木,北宋政府或戍疆边臣也意识到在宋夏沿边植树造林的必要性。史载:“定难军赵德明官告回言鄜延州保安军绝少林木,可降谕逐处令以时栽植。”[14] (7255)又《宋史》卷277《郑文宝传》载:“(郑文宝)又募民以榆槐杂树及猫狗鸦鸟至者,厚给其直。地舄卤,树皆立枯。”可见在环庆路进行植树的不易与艰辛。
(三)西夏谚语透露出西夏民众对大自然的和谐感与敬畏感 西夏谚语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创作的心得,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和普及性。从西夏谚语中不仅可以捕捉到西夏时期自然环境的相关信息,而且还透露出西夏民众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文献缺略的情况下,通过对西夏谚语的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西夏民众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了解西夏民众朴素的生态观与环境观。
就现存的西夏谚语而言,其中的六成涉及到自然界,我们可以将之粗略地分为天象、动物、植物以及山川地理等四大类,并且可以将之概括为“自然类”谚语。从内容上看,这些“自然类”谚语中的一些是表现、赞美大自然的,如168条:“多风,大山不动是山高;众水,大海不盈是海深”;222条:“大喉白鸟蹲地上,心欲吃蛙目一斜;云间垂鹫亦望影,地上老虎喜相见”[5] (14-19)。另一些“自然类”谚语则是通过自然景物来对民众进行教育,例如59条:“秋驹奔驰需母引,日月虽高浮于天”;138条:“是非语快如鸟有翼,利害意传如马善弛”;157条:“泽边蛙,脸上没有羞;夏蜣螂,皮下没有血”;195条:“老马无用,我不欲卖,知情形;瘦羊干瘪,我不欲吃,熟人情”[5] (9-16)。西夏人将熟知的动物编入谚语中,以企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这说明他们对这些动物有很深刻的了解,间接地反映出西夏人能够与动植物和谐相处的自然观和生态观。
对山川、河流心存一种深深的敬畏感是古代许多民族的共性,党项民族亦是如此。西夏文文献《圣立义海·山之名义》载:“河水在东,山有神宰,宿儒山名,善恶能隐。”[3] (60)显然,在党项民族眼里,一座座山不仅仅是壮美的自然奇观,同时也是具有灵性与神性的膜拜与敬畏的对象。西夏仁宗时期的《黑水建桥敕碑》亦载:“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神等,咸听朕命……”[17] 可见西夏民众对自然山水的崇拜与敬畏。虽然这种崇拜与敬畏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所引发的,但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种诠释:敬畏就意味着另一种方式的保护。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古人对自然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思考。
注释:
①在宁夏海原县境内的一城址(疑西夏临羌寨)内也发现了许多刻有鹿纹的花瓶。参见李进兴《临羌寨考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5—158页。虽然这些文物无明确的考古学地层依据,但形制、釉色、装饰手法等与先前出土的西夏同类器物一致,当属西夏时期的器物。
②转引自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野骆驼分布变迁初步研究》,载《湘潭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年第1期。该书已佚,宋人唐慎微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收录部分该书内容。
③骆驼还是西夏运输军需物资的主要工具。如《宋史》卷486《夏国传下》载:“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缘边与贼界相接人民繁庶,每来入寇,则科率粮糗,多出期间。”
⑤事实上,为了抵御北方的严冬,盗伐林木御寒恐怕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宋人庄绰在《鸡肋编》卷上记载:“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而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为害甚大。”
标签:西夏论文; 贺兰山论文; 宋夏战争论文; 动物论文; 太平寰宇记论文; 鹦鹉论文; 宋史论文; 骆驼论文; 宋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