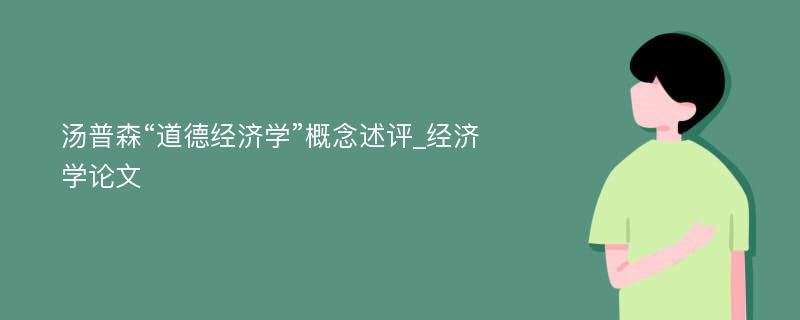
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概念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道德论文,概念论文,普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P.汤普森是一位以理论建树而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除了举世闻名的“阶级形成理论”外,他还于1971年系统提出了“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概念(注:对于“the moral economy”,国内也有“道义经济学”、“道义经济”的译法与用法,本文根据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认为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是一种价值观念,所以统一翻译成“道德经济学”。)。这一概念最初是针对英国18世纪的粮食骚动提出的,但不久就被其他学者用来分析、解释其他地区、时段和领域的民众抗议,成为有关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围绕着道德经济学这一概念,学术界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出现了一批相关论文与专著,举行了一场以此为主题的国际学术演讨会。(注:会议于1992年在伯明翰大学举行,与会人员主要来自英国、欧洲与北美,会议的主要内容已编辑成《道德经济学与民众抗议》一书。)道德经济学概念的国际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但在国内,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概念却长期鲜为人知,更不用说评介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钱乘旦、沈汉等学者才开始提及、评介这一概念。(注:沈汉、王觉非教授在《评爱德华·汤普森的新作〈民众的习惯〉》(《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与《史学巨擘杰出一生——悼念爱德华·汤普逊》(《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中,开始提到了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概念;1995年,钱乘旦教授首次对道德经济学概念给予简要评论,称其是“社会转型中一个尚未被人注意的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很普遍而又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转型社会中的平民百姓——读E.P·汤普森〈乡规民俗〉》,《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总第28期,第64页)。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沈汉教授与王加丰教授已将载有两篇汤普森道德经济学论文的《共有的习惯》一书翻译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但这一概念更多地为国人所知,可能要归功于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注: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对于书中的道德经济学概念,国内以下学者都做过简要评论。他们分别是:吴英:《评斯科特的“小农道德经济”说》,《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刘金源:《农民的生存伦理》,《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6期;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读书》2002年第5期。)一书。可由于作者在该书中没有明确交代这一概念源于汤普森(注:斯科特在应用道德(义)经济学这一概念时,只是在几个注释中提到了E.P.汤普森1971年发表的《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一文。),因而给国内个别学者造成一种错觉,使他们误认为道德经济学这一概念“上溯至前苏联的社会农学研究者恰亚诺夫”(注: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读书》2002年第5期。)。由此可见,对学术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并不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事。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道德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过程、学术反响予以梳理,并进而对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予以阐发。
一
“道德经济学”这一概念虽然在名称上与经济学、伦理学有直接关联,但其提出、发展与完善却不是经济学界、伦理学界的功劳,而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张关注下层、强调“从下往上看”的新社会史的兴起有密切联系,是史学界对英国社会转型时期民众粮食骚动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
粮食骚动是英国18世纪与19世纪初期的一种最普遍、最常见的民众抗议,是当时最典型的一种社会抗议形式。史蒂文森曾评述说,“最持久、最普遍的是与粮食相关的那些骚动,据统计,18世纪的骚动中有2/3是这种类型。”(注:R.Quinault and John Stevenson,eds.,Popular Protest and Public Order:Six Studies in British History 1790-1920,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5,p.33.)1700年之后,英国发生粮食骚动的年份主要是1709-1710、1727-1729、1739-1740、1756-1757、1766-1768、1772-1773、1783、1795-1796、1799-1801、1810-1813、1816-1818年(注:John Stevenson,Popular Disturbance in England,1700-1870,New York:Longman,1979,p.91.),其中,18世纪下半期,尤其是1766年、1795年和1800年,是粮食骚动爆发最频繁的时期(注:John Walton and David Seddon,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Massachusetts:Blackwell,1994,p.25.)。
但英国这一时期的粮食骚动,像同期的征兵骚动、反圈地骚动、宗教骚动一样,在之后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中,一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这一研究状况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改变。二战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把注意力转向“隐藏在冰山顶尖之下”的社会下层,主张“从下往上看”,不再把民众抗议仅看作是对社会结构转型的被动反应,而是让抗议中的民众作为主体出场,赋予他们更多主动的含义,使粮食骚动等民众抗议第一次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道德经济学概念的出现就是这种史学研究转向的反映和体现。
具体而言,道德经济学概念是对粮食骚动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对于民众为什么进行粮食骚动,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外在的经济因素,认为是民众对粮食供给不足与粮价过高所做出的一种被动反应。如贝洛夫在《公共秩序与民众骚动》一书中认为,粮食骚动的爆发是由于失业和粮价过高造成的(注:Max Beloff,Public Order and Popular Disturbance,1660-1714,London:Frank Cass & Co Ltd.,1963,p.75.);阿什顿在《18世纪英国的煤炭工业》一书中则认为粮食骚动是“肚皮造反”(注:R.B.Rose,"Eighteenth-Century Price Riots and Public Policy In England",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No.6,1961,p.278.);与上述观点相类似,威尔逊在《英国的学徒期:1603-1763年》一书中认为,18世纪上半期的一些粮食骚动是与失业、工资季节性变动、由收成与战争导致的短期粮价波动有关(注:Charles Wilson,England's Apprenticeship:1603-1763,London:Longman,1979,pp.35-36.)。
应当承认,上述对粮食骚动的经济解释是有事实依据的。据史蒂文森对温莎的个案统计,市场上的粮食供给不足及其粮价飞涨,与粮食骚动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注:资料来源:J.Stevenson,Popular Disturbance in England 1700-1870,p.92.)至于粮食供给不足及其粮价飞涨的原因,也的确与自然灾害、战争灾难、粮食歉收有关。1709年,冬季严寒,第二年夏天又异常炎热,致使每夸特小麦的价格在18个月内从27先令3便士涨到81先令9便士。1740年,粮食歉收,紧接着冬季严寒,牛津的小麦价格随之上涨,两年之内从每夸特20先令2便士上涨到59先令。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军需粮食剧增,紧接着粮食歉收,随之到1757年年中,小麦价格从几个月前的22至26先令上涨到67至72先令。(注:George Rude,The Crowd in History,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81,p.36.)正因为自然灾害、战争灾难、粮食歉收对粮食供给与粮价有如此大的制约关系,所以在自然灾害与粮食歉收的年份,也一般是粮食骚动的多发之年。
但上述这种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解释模式有一个严重的不足,就是严重低估了非经济因素在粮食骚动中所起的作用。市场上的粮食供给不足与粮价上涨只是民众进行粮食骚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民众所以进行粮食骚动,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粮食供给不足及粮价上涨的认识。粮食骚动作为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抗议方式,既取决于粮食匮乏或粮价过高这些外在因素,更取决于民众对这些外在因素的认识,取决于他们的认识结构。
基于这种认识,另外一些学者改从民众观念角度对粮食骚动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正是这种从非经济因素探讨粮食骚动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道德经济学的概念。
1963年,E.P.汤普森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该书虽然主要探讨1780-1830年间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但书中有一段关于粮食骚动的重要论述。汤普森认为英国18世纪有两种不同的骚动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某种程度上由大众自发的行动,这不是骚动一词可以概括的,但这种形式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方面最常见的例子是粮食或价格骚动。粮食骚动很少只是表现为不受约束的抢劫行为,骚动者的抗议行动被古老的道德经济学赋予一种合法性,认为哄抬粮食价格或谋取暴利都是不道德的。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人们最后竭尽全力恢复旧的家长制道德经济学,以对抗自由市场经济学。(注: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61页;另见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London:Penguin Books,1968,pp.67-73.)正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道德经济学这一术语第一次被用来说明粮食骚动。(注: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提出道德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也不是汤普森。汤普森本人认为这一术语源于18世纪晚期,可他已无法找到文献证实。他能找到的文献记载都始于19世纪30年代,如宪章派的一位成员就在1837年反对政治经济学的评论中提到过道德经济学。但汤普森是第一次用道德经济学这一术语来解释粮食骚动的学者。)但此时汤普森并没有对道德经济学做出细致界定。1964年,鲁德在《历史上的民众》一书中指出,粮食骚动是一种有自我约束与高度仪式化的抗议,在骚动中,民众是按他们认为的“公平”或“合理”价格买粮,大都遵循一套很固定的价值观念。(注:George Rude,The Crowd In History,pp.33-65.)但民众抗议背后的这套观念是什么,鲁德并没有做出明确说明,更没有将这套观念概括成道德经济学。
直到70年代初,道德经济学才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系统提出。1971年,汤普森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18世纪民众的道德经济学》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汤普森对民众粮食骚动的行为方式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认为粮食骚动有它自己的一套“秩序”与“规则”,大都遵循一套固定的仪式,其抗议的目标是传统的权利与习惯,而这些传统的权利与习惯源于都铎时期有关市场如何运作的家长制法律模式:粮食应运往市场交易;让穷人在商人批量购买粮食前优先廉价购买;严惩倒买倒卖、囤积居奇行为等。在这样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汤普森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道德经济学”概念:“粮食骚动虽然是由粮价上涨、商人的不法做法或饥饿所引发,但这些不满是在一个关于销售、磨面、做面包等做法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的民众共识中发挥作用。而这又依据一套与社会规范与义务、共同体内各方经济职责相关的长期沿续下来的传统观念,可以说这一切构成了贫民的道德经济学。”对这些道德观念的伤害,同实际剥夺完全一样,是粮食骚动的直接动因。(注:E.P.Thompson,Customs in Common,p.188.)
二
汤普森提出的民众“道德经济学”概念,为粮食骚动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引发了很多赞同、质疑与挑战,形成了一场国际大辩论。
一方面,道德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与肯定,成为他们分析粮食骚动及其他类似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一些学者把道德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应用于工业领域与农业领域,如兰德尔用“工业中的道德经济学”来描述格洛斯特郡的纺织工人抗议(注:Adrian Randall & Andrew Charlesworth,eds.,Moral Economy and Popular Protest,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p.21-22.),斯内尔则认为,民众对居住权、对济贫法和年租金的态度反映了一套长期沿续下来的道德经济学观念(注:K.D.M.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00.)
道德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除从原来的粮食市场领域扩展到工业、农业领域外,还从最初的英国扩展到整个世界,成为适用全球类似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用道德经济学概念来分析东南亚农民在市场资本主义冲击下的反叛原因,认为“对农民的日益严重的剥削很可能是反叛的必要原因,但远不是充分原因……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剥削引致反叛的可能性最小”。他认为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与精英以互惠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这才是造成农民抗议的主要原因。农民“拿起武器的目的,更经常的不是为了打倒精英,而是强迫他们履行其道德义务”(注: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第248、242-243、246页(对于斯科特与E.P.汤普森运用的道德经济学概念的关系,可以通过两人的记述得以说明。汤普森认为斯科特用的道德经济学术语源于他的论文,但已被应用于农民研究领域,用来证实关于社会正义、权利与义务及互惠关系的农民观念。斯科特则在一篇论文中对他运用道德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前前后后做了如下说明:在1973年和1974年,他专心从事30年代缅甸和越南两次农民起义的研究,并以此为主题写完了书的草稿,他当时曾初步拟定了两个书名,其中之一是“生存伦理的政治经济学:东南亚农民起义”,后来当他读到汤普森1971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民众的道德经济学》一文后,他觉得道德经济学这一术语更为确切,就把他的书名定为《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但他又同时指出,他所界定的道德经济学与E.P.汤普森有很大不同。参见:E.P.Thompson,Customs in Common,pp.341-342;Adrian Randall and Andrew Charlesworth,eds.,Moral Economy and Popular Protest,pp.187-188).)。
对于道德经济学应用范围的扩展,汤普森本人并不完全赞同。他在《道德经济学再论》一文中指出,他所用的道德经济学,通常限定在市场上购粮权利的对抗。它不仅指在粮食匮乏时民众对市场应如何买卖所持有的一套共同信念,而且包括:民众由匮乏激起的感情冲动,在这些危机中对当局的要求以及在生死攸关时居然有人谋取暴利而产生的愤怒,上述这一切共同组成了他所理解的道德经济学。如果把这一概念应用到其他语境中去,那必须予以重新界定。(注:E.P.Thompson,Customs in Common,pp.337-338.)
另一方面,道德经济学概念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威廉姆斯在《道德、市场与1766年的英国民众》一文中指出,道德经济学概念的分析框架有三个不足:第一,用道德经济学来解释1776年粮食骚动的爆发是不充分的;第二,道德经济学忽视了另外一支参与力量(中产阶级);第三,道德经济学低估了骚动的一个主要的制度性原因,即市场经济。(注:Dale Edward Williams,"Morals,Markets and the English Crowd In 1776",Past and Present,No.104,1984,p.73.)夏普在研究了16、17世纪的粮食骚动后指出,早期的粮食骚动行为中并没有多少为道德经济学所驱使的迹象……对民众道德经济学的过分强调很容易导致看待贫民生活与行为时出现太情感化的观点,会掩盖他们在粮食匮乏与不足时的痛苦、绝望与愤怒的现实。(注:John Walton,and David Seddon,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p.32.)
三
道德经济学虽然至今还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但它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道德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冲破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把粮食骚动中的民众观念置于应有的主体地位,为民众抗议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以往学界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忽视甚至抹杀了作为历史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选择性,从而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尽管恩格斯晚年曾对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做法进行了批评,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6页。)。但非经济因素对历史的反作用一直没有给予一个恰当的定位。而道德经济学的分析模式鲜明提出,观念因素有时比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更为直接,这一定位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重大发展。
其次,道德经济学概念的提出,也从方法论上克服了传统实证主义研究的局限,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历史研究的文化解释范式。传统史学主要是一种实证分析,这种实证做法虽然使史学有了坚实的客观基础,但在具体分析民众抗议时却有其无法解决的局限。这表现在有关民众抗议的史料主要是统治者记载的,如果让史料自己讲话,研究者就很难跳出史料记述者原有的认识框架。道德经济学概念的提出虽然依旧离不开史料,但同传统的实证分析相比更注重解读史料,是对民众抗议行为与抗议语言进行文化解释的结果。这种文化解释既表现在通过抗议行为中的仪式、规则去分析这些行为模式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挖掘其中蕴含的民众观念;也表现在通过骚动者的语言去剖析话语背后的文化逻辑,揭示话语背后的民众思维方式与价值倾向。道德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民众抗议研究中文化解释的成功典范,是对史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贡献。
最后,道德经济学概念的提出,还成功运用了“从下往上看”的研究视角,提出了社会转型时期民众抗议的一定合理性问题,为深入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的民间立场。道德经济学作为“一套与社会规范与义务、共同体内各方经济职责相关的长期沿续下来的传统观念”,从形式上与当时市场走向自由放任的时代潮流相悖,但在民众看来,政府与商人对这一观念的恪守,却能够给他们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在粮食饥馑时买到廉价粮食,比自由放任的粮食市场规则更有人性。因此,如果关注各阶层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和感受,就不能断言民众所恪守的传统价值观念劣于以经济人为核心的新兴价值观。因为任何价值观都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价值观的优或劣、先进或落后,首先应由持有这一价值观的主体来判断。脱离某一主体所处的语境,简单地用现代价值观念来评判他们当时的观念,很容易遮盖传统价值观念的合理性,抹杀掉它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可见,道德经济学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深入认识和评价社会转型中的民众传统观念提供了一种超越现代性的批判立场,而这是其他概念所无法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