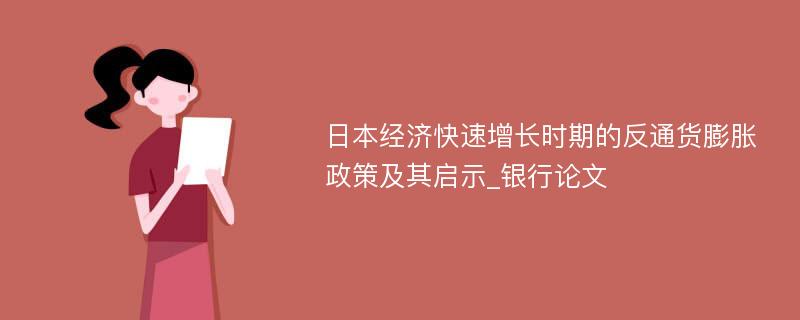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日本经济论文,启示论文,时期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在1956~1973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之所以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反通货膨胀政策所造成的良好经济环境。然而在我国每逢经济高速增长,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又不得不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其中总是把调控的着力点放在速度上,从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鉴于此,本文想通过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加以分析,以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1、造就发展生产,增加供给的经济机制。
日本政府当局认为,引致通货膨胀的原因虽然在于供需失衡,然而,根治通货膨胀的关键却是发展生产,增加总供给。为了增加生产,日本政府采取了下列对策:(1)以重化工业化政策作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使其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有较高比重。此外,以当时世界上现代化和先进化的产业部门作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使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化、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化方向发展。这种重化工业化政策,造成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推动了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出口产品高档化。1957~1972年,日本出口产品的构成中,重化工业产品的比重从40.5%增加到77.1%。这种出口产品的高档化,打开了国际市场,使贸易收支逐步转向顺差。(2)降低对基础产业部门的贷款利率,增加对这些部门的投入。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全国银行的平均放款利率,从1955年的8.98%降至1970年的7.66%。而对重点产业的放款利率更低,例如,1961年10月,日本开发银行的标准放款利率为8.7%,但对电力、海运、特定机械工业部门的利率仅为6.5%,这有利于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入。对重点基础产业降低贷款利率的同时,财政部门也增加了对这些部门的财政支出。1955~1970年,日本政府资本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1970年,美国为8.4%,英国为13.1%,西德为12%,法国为9%,而日本则为38%,比这些国家高出2~4倍。这样便消除了瓶颈产业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制约因素。
2、运用窗口指导,进行宏观金融调控。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企业自有资金率比较低,仅占同期筹资总额的25%左右(同期西方其他主要国家平均达50~60%),证券市场又不发达,因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几乎只能靠银行贷款来解决。为了满足企业对资金的旺盛需求,日本银行不得不扩大信贷总量,以致贷款总量远远超出其实际吸收的存款,甚至连本来应当提取的存款准备金部分,也只得依靠日本银行的信用来创造。由于日本政府一直推行低利率政策,使得银行利率明显低于市场的实际利率,这就刺激了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并迫使各银行加大了对日本银行的信用依赖。
毫无疑问,这种低利率超贷款的政策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日本政府便以窗口指导方法来控制资金的流向,即在各个银行来到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贷款“窗口”时,中央银行以各种非正式的指示要求它们贷给那些政府指定要发展的或效率高的产业和企业,这样,日本的低利率超贷款政策既满足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又未导致对经济有害的通货膨胀。另外,日本银行还充分发挥利率的功能,对每一银行分配制定了一定的货款额度,超出这一额度则运用惩罚性利率,这就使日本银行在积极创造信用,提供过多基础货币的同时,又能不断地对各银行造成一种控制信用的压力。
3、减轻企业负担,保持较小的财政规模。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直接减轻了企业的利息负担,使企业有可能吸纳大量的成本低廉的资金,来保证企业在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等方面对资金的旺盛需求。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实行减税政策,国民的租税负担,特别是企业的租税负担比较轻。1955~1970年,国税负担率从18.1%仅增加到18.9%。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租税负担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减轻租税负担,可以加快企业资本积累,增强企业实力,促进整个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实行低利率和减税政策,财政规模扩大缓慢,1955~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7.2倍,然而中央财政的支出决算净额仅增加了5.3倍,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24.5%降至18.8%。日本财政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1970年,美国为33%,英国为37.7%,西德为35.8%,法国为35.8%,而日本只占22.2%。由于财政规模扩大缓慢,因而政府的消费支出在1955~1970年之间只增加了5.7倍,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0.2%降至8.3%。政府消费支出减少,避免了财政赤字。财政规模小,意味着社会资金用于无偿支出的部分相应减少,这对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是颇有益处的。
4、以间接金融为主。
所谓间接金融,就是资金的最初提供者和资金的最终需要者都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的调剂资金余缺的融资方式。与间接金融相对应的是直接金融,即资金的融通不经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而是资金的最初提供者与资金的最终需求者之间直接融通资金。
日本企业从外部筹措资金的情况表
年份
银行贷款(%)
有价证券(%)
外债(%)
1956~1960
72.3 12.7
4.9
1961~1965
75.0 9.25.7
1966~1970
85.5 10.24.4
1971~1975
89.5 10.24.4
1971~1975
89.5 10.9 0.8
资料业源:《现代日本经济》,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32页。由上表可以看出,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银行贷款占企业所筹外部资金的72.3~89.5%,而以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筹措的资金至多不过12.7%。日本这种以间接金融为主,以直接金融为辅的融资体制,对其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是有利的。
二
我国目前正处在与日本经济起飞前期大体相同的阶段,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对我国目前抑制通货膨胀很有借鉴作用。
1、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不是放慢经济的发展速度,而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增加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使中国跻身于先进行列。我国从80年代至今有三次经济高速增长,一次是1983年至1985年,另一次是1987年至1988年,这两次经济增长持续时间只有二、三年,原因在于这两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最后不得不把速度降下来。第三次经济高速增长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至今,已有3年时间了,这次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高通货膨胀率更甚于前两次,个别月份通胀率高达27%。之所以会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走的一直是一条片面追求产值的路子,其结果必然是高投入、低产出和低效益。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所以能持续18年且平均增长率高达10.2%,其原因在于,日本重在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不是产值的增长速度。
我们不妨和日本相比一下:从5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产值增长速度高于日本,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却超过了中国。1960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为495亿美元,日本只有386亿美元,中国领先于日本。日本从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10年倍增计划,到1965年国民收入达到776亿美元,五年翻了一番,而中国1965年只增加到563亿美元。1970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又翻了一番,达到1701亿美元,中国为782亿美元。到1975年,日本国民收入又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4286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016亿美元。15年中,日本的国民收入由少于中国的109亿美元,提高为中国的4倍以上,即日本增长了10.1倍,而中国仅增长了1.05倍。1953~1981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约为14.2%,而中国只有4.4%。由此可见,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远远低于产值增长速度。日本在60年代也曾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日本的生产率特别高,使得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所以比较好地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我国现在要治理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我国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国民经济保持均衡发展,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存在过高的问题,而是越高越好。
2、保持适度财政规模,加大对瓶颈产业的投入。
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为了加快企业资本积累,增强企业实力,实行减税政策,因而财政规模比较小。这一方面,减轻了企业的租税负担,加快了企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会成为抑制行政机构膨胀,迫使其节检执政的客观约束条件,从而有利于避免财政赤字。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几乎年年有赤字。财政赤字的根本原因用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的话说就是,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是引起财政赤字,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目前全国干部队伍总数已接近3400万人,每年经费开支10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如果将机关行政事业干部减少400万,每年就节约近200个亿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消灭赤字,又可以减少办事拖拉、扯皮等腐败现象。
我国改革以来,伴随着经济加快增长,往往出现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加工工业过度发展。与此同时,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则严重滞后,供给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产业。按照GNP年平均增长7%计算,至2000年,约需原煤16~17亿吨,钢1.4亿吨,铁路货运量19~20亿吨。而按照“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到2000年,原煤只能达到14亿吨,钢8000万吨以上,铁路货运量19亿吨。这就是说,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业这种供给状况不可能支持GNP7%的增长速度,更何况目前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了。每逢经济高速增长,过旺的投资需求,首先将拉动因供不应求的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品价格上涨,进而由成本推动导致社会众多的价格涨势。这就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高速增长时期必须降低对基础产业的贷款利率,加大对其投入,以消除瓶颈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3、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使中央银行相对独立化,专业银行商业化。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日本银行相对独立于政府,各都市银行都是商业性银行,这样,专业银行就成为中央银行的直接调控对象,中央银行较好地起到了窗口指导的作用。由于各都市银行都是商业性银行,贷款必然以盈利为目的,不是高效率的企业就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这就促使企业更加注意改善经营,提高投资效益,创造高效率。这是日本经济高速又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直属于政府,是国务院的直属职能部门,各省分行也拉入了省政府系列,因而其相对独立性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对各级政府的功利化行为,在资金力量上很难形成约束,因而也就很难真正独立地执行宏观货币政策,实现金融宏观调控的任务。当然,中央银行相对独立化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换。
我国从1979年起分设专业银行,但经过15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专业银行经营机制并未实现转换,信贷资金供给制向借贷制的转化远未真正实现。目前专业银行仍然一身二任,既要微观经营,又要参与金融宏观调控;既要追求社会经济效益,承担政策性业务,又要追求自身经济效益。专业银行若不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金融企业,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就失去了可资发挥作用的直接对象。因此,必须加快专业银行商业化的进程,努力转换其自身的经营机制,净化其性质、职能,明确其利润经营目标,还其经营货币企业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专业银行才能形成自我约束机制,才能为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构造起坚实的微观基础。
4、资金融通以间接为主。
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资金融通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为辅的。这一点颇值得我们借鉴。资金融通以间接为主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控制社会资金总量。在间接金融方式占绝对优势的融资体制下,企业筹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银行遇有资金不足则主要依靠中央银行贴现(或再贴现)。这就能使中央银行的各项金融措施得以奏效。如果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其他银行的利率便会随之上升,从而提高企业的筹资成本,起到限制企业投资需求的作用;如果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率,各个银行的信贷规模就会相应缩小,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控制住了,社会总需求的规模便能够有效地控制住。
(2)有利于把握资金流向,帮助产业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转变的背后是资金流向的转变,在间接金融占绝对优势的融资体制下,中央银行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资金流向,主动配合产业政策的实施。例如,中央银行在进行票据贴现或再贴现时,优先选取那些符合政策目标的产业或企业的票据,可以引导资金流向,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
(3)有利于抑制利率上升,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较好的金融环境。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一直存在着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果任利率随供求关系变动,势必形成高利率。利率升高会提高企业的筹资成本,导致产品价格升高,抑制需求,进而抑制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一直坚持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在实际上起着鼓励间接金融活动,抑制直接金融市场发展的作用,防止了由于股票、债券的大量发行而抬高利率的倾向,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金融环境。
标签:银行论文; 央行论文; 日本银行论文;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利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