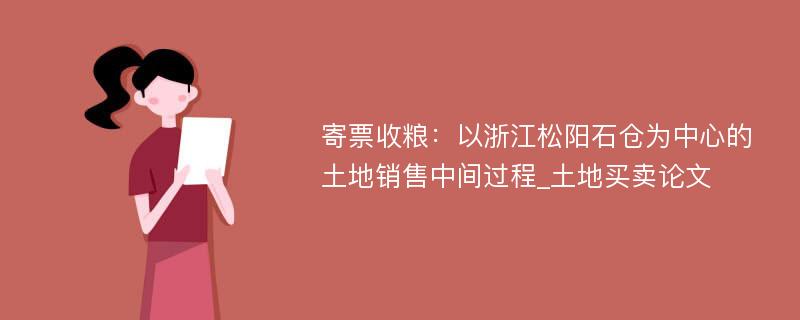
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松阳论文,浙江论文,土地论文,过程论文,买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杨国桢先生在一篇关于清代浙江田契的论文中,讨论了浙江绝卖契的格式。他提到,除了印刷的“绝卖文契”外,还有相当多的手写契约。如下引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一月浙江会稽或江阴县的一份卖地契(为节省版面,内容及签名有所删节。下同,不一一说明)。
立永卖契王诗章,今因遥远不便,情愿将父遗下官田壹所,坐落土名湖豆塘,系七亩塘外量斗田贰亩正……情愿出永卖与五福会众卓厚荣等为业,面议田价钱壹拾陆仟文。其钱当日随契收足,其田自永卖之后,任从出钱众人营业布种收花,并开割过户输粮,并无兄弟阻执等情。此系两想[相]情愿,各不翻悔,恐后无凭,立此永卖契为照。
即日立除票,廿三都贰庄今将王诗章户内下官田贰亩,情愿出除于本都本庄卓厚荣等收户输粮,并照。
该契文由于涉及“官田”,故杨国桢对此有较多讨论。本文将讨论重点放在契文之后的加引注文上。从抄引的格式上看,王诗章所立之“除票”是以契内加批的形式,写在这份“永卖契”上的,杨国桢将这份“除票”认定为土地买卖过程中,卖者履行过户即“过割”手续的证明,即将原业粮户,改过现业都图之下。其具体手续是,买主将契输税交官用印,取得“税契”手续,随即推收过户。杨国桢引雍正十年(1732)诸暨县知县崔龙云《申严顺庄滚催实革里书永禁碑》文如下:
永定推收之法:凡典卖产业于成交税契时,随即推收过户,不许卖主掯勒。因顺庄初行各县,多有只将田粮数目彼此开除,未有田亩字号付庄书,借此掯勒横索,是以今届大造之年,暂定各图有田殷户一人情愿认充者管理册籍,推收完峻,交□归农……嗣后民间典卖产业,即将字号推付过户,则逐年推收。①
关于“除票”的原件,杨国桢称“没有发现此种据单的实物”,但他引用一份晚清时的“推户据”,以此类推清代浙江的“除票”。光绪年间的这份“推户据”是这样的:
立推户据△△△,为因将己产坐落△邑△保△区△图第△号内△△△粮户名下△田△△亩,契卖与△△△为业,应凭业主照数过户,办赋以明年为始,所有今年△△均由原主输纳,恐后无凭,立此推户据为证。
光绪△△年△△月△△日立推户据△△△
光绪年间的“推户据”即是清代中期或清代早期之“除票”。在浙江省松阳县石仓,偶尔也有写在地契上的此类“除票”,但更多、更常见的则是以单据形式出现的。只不过,在石仓,此类单据称为“送票”、“送户票”而非“除票”。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将其称为“送户票”。
我们经手过的石仓送户票多达数百张。在松阳县的其它村庄,也有大量送户票被发现。在我们所购徽州契约中,此类送户票也不少见,且时间可以上溯至明末或清初。
根据我们对石仓契约的统计,从土地买卖双方订立契约到办理“契尾”,间隔时间一般在2-8年,一年以内及8年以外的情况比较少见。也就是说,土地买卖完成之后,田主并没有立即办理土地产权的过户手续,所以,将“除票”或“过户票”称为土地出售之后即办理土地产权过户手续的凭证,是不妥当的。或有人问,尽管办理契尾与出售土地存在一个时间差,但“除票”仍然是卖主同意过割产权的凭据。本文将证明,这一观点也是不成立的。
在石仓,除了送户票之外,还有一种“收粮字”,以及名称不同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各种单据。这些单据反映的是土地买卖契约订立之后至过户手续办理之前一系列复杂的契约形式。也就是说,由于土地买卖双方订立契约与办理产权过割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其间的土地权益就需要设计一系列制度来加以划分与明晰。这就引发本文有关土地买卖中间过程之讨论。
本文主要利用在浙江石仓及其周边乡村发现的各种送户票与收粮字等单据,讨论在土地买卖契约订立之后至产权过户之前的几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买卖双方是如何处理土地赋税及其它相关问题的。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一复杂而有趣的过程显然被人忽略。
二 税责转移而非地权过户
先讨论杨国桢引王诗章卖田契。契中注文所称“收户输粮”,其实不是指王诗章将所卖之田的“田底权”转移到买家卓厚荣手中,而是指王氏将土地的税粮转移到卓氏手中。我们将此称为税责之转移,并不是“田底”之过户。
在石仓乃至中国的东南地区,土地买卖通常分为“活卖”与“绝卖”。一般说来,“活卖”的土地只出卖“田面权”,并不出卖“田底权”,“绝卖”的土地才出售“田底权”。“活卖”的本质是土地信贷,“绝卖”的本质才是土地买卖。关于“田面”与“田底”,本文最后部分有详细的解释。
确定一块土地到底是“活卖”还是“绝卖”,不能仅凭契文上是否有“绝卖”或如“日后并无找价取赎”之类的字样。也就是说,即便是写明“绝卖”的土地,或即便是写明“日后并无找价取赎”字样的土地,也有可能是“活卖”——可能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后,卖主索要“找价”。在浙江松阳石仓,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初五,石仓村民刘廷贤、刘元松兄弟将祖田四亩卖给阙其兴。卖方与买方订立契约如下:
立卖田契人刘廷贤、刘元松,今因钱粮无办,自情愿将到祖遗下民田壹处,土名坐落廿一都夫人庙庄茶排门首上下,共田大小捌丘,计额肆亩正,今俱四至分明,托中送与阙其兴入首承买,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值价纹银叁拾玖两正,其银即日随契两相交讫明白,不欠分文,其田自卖之日为始,任凭买主俱耕管业栽种,卖人不得异言争执,其田所买所卖,二比情愿甘肯,两无逼勒,并无债货之故,委系正行交易,不是准折,其田易[亦]不曾重复典当他人,如有来历不明,皆系卖人一力承(当)②,不涉买主之事,其与上下伯叔人等并无干碍,其田自卖,永远子孙不得取赎再找之理,今后二家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卖田契永远为照。
这份卖田契与契尾相联,契中及骑缝处加盖官印,契尾办理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九月。这实际上意味着,刘廷贤等将“田底权”转移到阙其兴名下,是在土地卖出的8年后完成的。在这份卖田契中,有“其田自卖之日为始,任凭买主俱耕管业栽种”一句,并非转让“田底权”。真正的“田底”之转让,只能以契尾订立的时间为准。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契尾所载亩额只有一亩五分,交易价格只有10.5两,与契中价格不符。这一情节,容后解释。
就在订立卖田契的当天,即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五日,卖方立出一张送户票,内容如下:
立送户票人刘廷贤、元松,原与阙其兴交易民田四亩正,与刘光普户下二亩五分,刘廷贤户下壹亩五分正,不得丢漏,恐口无(凭),立送票为照。
票中将契中所交易的4亩民田,分解为刘光普户下的2.5亩和刘廷贤户下的1.5亩,就令人猜测契尾中的1.5亩,只是全部交易的一部分,即来自刘廷贤自己户下的1.5亩,不包括刘光普户下之2.5亩。也就是说,这一契尾,只是转移成交田亩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将来源于两个户下的田地一次性出售,实不多见。一般情况则是每次只出售一个户名下的田地。或者为一个户名下田地的全部,或者为一个户名下田地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此份送户票另一诡异之处,在于其讲清了售田的由来,却忘记了交待送户票的功能。一般的送户票可见下例:
立送票人戴天云,与阙其兴边交易民田壹亩正,户坐天恩户下,任凭阙边收拾过户完粮,戴边不敢异言执留之理,恐口难信,故立送票为据。
乾隆十七年正月廿九日 立送票人 戴天云
代笔 魏芝元
戴天云将天恩户下的一亩田售给阙其兴,送户票中的“任凭阙边收拾过户完粮”,指的是税责转移,而不是“田底”过户。回到刘廷贤卖田契中来,刘廷贤送户票,显然不是为8年以后的“田底”过户而准备的。严格地说,在出卖土地的乾隆十八年,买卖双方并不知道他们将在何时进行“田底”的过户。
之所以将送户票中所称“任凭某边收拾过户完粮”一句理解为税责转移,是可以找到证明的。仍以刘廷贤送户票为例,我们就找到两份相关的产户执照,可以证明税责转移已经完成。
特授松阳县正堂纪录二次黄为严饬推收事,遵奉宪行,随买随收,今将廿一都夫人庙庄刘廷贤将户下田地壹亩伍分正,外山○,收入本都茶排庄的名阙有兴户下入册办粮,合给印单执照,须至单者。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 日 经 推收
特授松阳县正堂纪录二次黄为严饬推收事,遵奉宪行,随买随收,今据廿一都夫人庙庄刘光普户下田地贰亩伍分柒厘,外山肆亩正,收入本都茶排庄的名阙有兴户下入册办粮,合给印单执照,须至单者。
乾隆十八年十二月 日 经 推收
与刘廷贤送户票比较,刘廷贤户下1.5亩,刘光普户下2.5亩,可以完全对应。一次性地卖出4亩土地,由于涉及两个户名,则必须办理两个过户手续。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过户”,指的是税责过户。只不过,刘光普户下不仅卖出2.5亩田地,还卖出4亩山场,这是上引卖田契中所不见的。当然,刘光普有可能将卖出的山场另立他契出售,而这份卖山场契,则不为我们所查获。
另外,与刘廷贤卖田契对照,买者为阙有兴,而不是阙其兴。两者其实为一人。石仓“一户多名”现象相当普遍,我们有专文论述③,此处从略。
刘廷贤卖田契中另有一句,“其田自卖,永远子孙不得取赎再找之理”,其实也不能当真。就在乾隆十八年,即出卖土地的当年四月二十一日,买卖双方订立“找契”一份:
立找契人刘廷贤、刘元松原与阙其兴边交易民田肆亩正,其田前价足讫,今因钱粮无办,再托原中转俭[捡]业主找契外纹银贰拾壹两正,其银即日收足,不欠分文,其田自找之后,永远割藤断根,并无再找取赎之理,恐口无凭,立找契为照。
还需要强调的是,在石仓,由于所有的送户票都是与卖契同一天订立,而卖契却没有一张与契尾同时订立,所以,无论是“绝卖”还是“活卖”,其送户票的意义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更换田主,而是转移税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买卖双方何时办理契尾即完成“田底”过户是不重要的,保证税额不被丢失才是关键所在。买卖双方持卖契及送户票,至县政府设于村庄上的田赋征收处办理相关手续,经办人在一份印刷的“产户执照”上填写卖主姓名、买主姓名、各自所在的都图村庄以及田亩额、签署时间,即告完成。在上引刘廷贤例中,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五日订立卖契与送户票,十二月某日办理的“产户执照”,办理过程也不用支付费用。在一般情况下,订立送户票与办理产户执照往往只相隔十几天,最多数月。税责转移的法律过程一般在本季度完成,否则影响税之征收。在住地田赋征收处办理田赋改征手续,是相当便捷的。刘廷贤案中办理“产户执照”的时间偏长,也不是特例,推测买卖双方对于当年的税粮交纳还有一个另外的约定。
总之,在“卖契”订立之后,土地买卖的全部完成一般还需要有以下三个步骤:税粮过户、找价、办理契尾。如果没有找价,或没有办理契尾,土地的出售还只是“田面”的出售,“田底”主人保留回赎的权利。
三 如果卖方不肯转让税责
有些土地卖方不愿意将税责转移给买方,可能是担心随着税责转移而导致“田底权”流失。所以,相当多的土地卖方最终选择自己承担税责。尽管格式文本的标准写法似乎是一定要进行税责转移,但聪明的卖家可以在文本中订立专门的约定。详见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初十吴文祖卖田契:
立卖契吴文祖,今因缺用,愿将自己民田,坐落二十一都茶排庄安着,计额亩贰亩,共贰处,壹处土名叶山边,大小肆丘……凭中出契卖与阙天有边为业,即日得受九七圆丝银贰拾壹两正,其银随契收足,其田自卖之后,任凭阙边推收过户,纳粮管业,吴边不得执留,此系自己物业……倘有此弊,不涉阙边之事,吴边自行支当,两相情愿,各无返悔,今欲有凭,立卖契为照。
一批其田,不拘年近年远,原价取赎,内注一字,倘取赎时,外加花字酒席,再照。
在卖田契订立的当天,双方订立的送户票内容如下:
立出户票吴文祖,今将自己户内吴茂远名下额田贰亩,拔过阙天有边户内承纳,不致漏落,立出户票为据。
一批四年过若未取赎,方阙边推收过户,此四年阙边备银,吴边代完,再据。
卖田契中的“不拘年近年远”,在送户票批文中改为“四年过若未取赎”,买方阙边才可以推收过户。其契尾订立于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即卖田契订立的8年之后,远远超过双方议定的4年期限,可知在卖方无力或放弃回赎之后,买方办理了契尾,完成田底过户手续。不过,此送户票中“批”文中的“方阙边推收过户”,还不能说是田底过户,因为,4年之后,吴边仍可能开一张送户票,转移税责,由于没有发现吴的“产户执照”,所以此点没法证明。
如果卖方不肯转移税责,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卖方将土地出卖之后,土地的收入全部归于土地买方,卖方用什么支付田赋?在吴文祖卖田以后,田底还没有过户的4年中,吴文祖的田赋由谁来交纳?按照送户票“批”文中的规定,是由买方阙边准备好银子,交由吴边来交纳。因为,在官府的纳粮册上,吴氏仍然是户主。吴文祖卖田契中所称:“其田自卖之后,任凭阙边推收过户,纳粮管业,吴边不得执留”之规定,不过是一纸虚文。送户票的规定才是真实有效的。
再看一份订立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严永德卖田契,干脆注明“卖人自己完纳”税粮,节录如下:
立卖田契严永德,今因钱粮无办,自愿将自手置有水田,坐落松邑弍拾壹都五合圩庄,小土名上潘屋后,安着水田壹处……既卖之后,任从买主起耕改佃,完粮收租管业,面言不拘年限,任从严姓备办原契价钱取赎,阙姓无执,愿卖愿受,并无逼抑之理,今欲有凭,立卖田契付与阙边存照。
一批每年钱粮,卖人自己完纳,再照。
契文中虽有“任从买主起耕改佃,完粮收租管业”,但批文中规定“每年钱粮,卖人自己完纳”,契文中的规定不如批文中的规定,前者只是例行套语,后者才是有效的约定。
一份订立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十九日的林长淳卖田契之批文则明白约定“粮税无得过户”,其契文节录如下:
立卖田契人林长淳,今因钱粮无办,自情愿将祖父遗下兄弟均分自值服内民田,共叁处……自愿托中亲立文契,出卖与王启进亲边入受承买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言断,时值田价洋银陆拾元正……其田自卖,任凭业主入册完粮,收租管业,卖人不得异言阻执……其田日后备办契内原价,有赎无找……
一批花押洋银壹元正。一批当中面言,粮税无德[得]过户,出卖人自己完纳,再照。
也是批文中的约定比契文更为重要。此批也可再次证明送户票是转移税责,而不是转移地权——既不是田底权,也不是田面权。
回到乾隆三十四年吴文祖卖田契的讨论上来。由于没有转移税责,每年吴文祖可以从阙天有处获得其交来之税粮,再交纳给官府。当吴氏收到税粮后,出具收据,交与阙天有。这类收据可以称为“收税粮票”,一份嘉庆七年(1802)的收税粮票或收钱粮票格式如下:
立收钱粮票人张光辉,今来收过阙天贵亲边本年钱粮陆亩正,并及杂费一足收清,并无欠少分文。恐口无凭,立收字存照。
在此契中,阙天贵将嘉庆七年六亩土地应交之赋及杂费,交给张光辉。张光辉负责向官府交纳当年田赋及杂费。这一有钱的买方向缺钱的卖方交纳钱粮的怪事,其实是与土地买卖过程中,卖方不愿转让税责有关。有一些此类票据写作“立收水粮字”,揣测其意,当为此类粮食,如同流水,左手收入,右手交纳。当然,也可能是将“税粮”误为“水粮”。
从理论上讲,那些没有获得税责的买家,每年都必须向卖家交纳田赋,卖家都必须签一张收据。也就是说,每一张不能过户纳粮的送户票,都有一张或几张“收税粮票”与之相配合。例如:
立收粮票人万元胜,今收过黄立万边门前上粮五分,又收寮子边粮三分,今收过十七年起[至]廿六年,共立收票壹纸,上年一并收足,不得再收,所收是实,故立收票为据。
乾隆廿六年十月廿五日 立收票人 万元胜
见收代笔人 吴旭万
立送户票人邓海松,今将本户推出贰亩正,收入阙玉磬户内入册,不得丢漏分厘,恐口难信,故立送户票字为据。
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九 立送户票人 邓海松
代笔 阙玉山
立收税粮字人邓海松,今因收过同治十二年、十三年、光绪元年,共三年,收过阙玉磬税粮铜钱壹千贰百(文),一应状[收]清足乞[讫]。
光绪二年三月初九 立收税粮字人 邓海松
代笔 阙玉山
万元胜收粮票的性质与邓海松收税粮字相同,不仅收一年之粮税,而且收多年之粮税。不同的是,一个在乾隆年间,一个在光绪年间。由此可见,收粮字的传统由来已久。不仅如此,邓海松与阙玉磬成交的这块土地,其“正契”订立的时间与送户票订立的时间相同,“找契”的时间则晚了10天。成交于光绪元年(1875)的土地买卖契约,要补足同治十二年与同治十三年的税粮,可见卖主经济窘迫。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邓海松仍不愿意将田产断卖,送户票称“收入阙玉磬户内入册”,只是转移光绪二年以后的税粮而已。直到民国年间,这一制度依旧,限于篇幅,兹不举例。
买家收到送户票以后,会出具一张收据,表明自己收到送户票。例如下:
玖都一户阙德璁,一收本都张登寿户田三亩伍分正。
道光拾三年正月 日收单 张登寿
居住在廿一都茶排的阙德璁,成了“九都”的户主。这个“九都”,是云和县的九都,与石仓相邻。道光初年,阙德璁在这一区域有大量的购地活动,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契约。
由买方向卖方每年交纳税粮的办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当麻烦。不仅每年要将粮食挑来挑去,而且往往在交粮时候,还要请中人作证,或请代笔者出具收据。于是,有买家向卖家一次性付出一笔钱,称为“贴粮银”,作为税额。例如以下出粮字:
立出粮额字人林长淳,原因上手祖父遗下民粮无德[得]过户,自愿向与王启进亲边付出贴粮洋银壹元正,其洋银即日收清,当日面断,洋银无得起利,以作粮亩完纳,两家不敢异言,如有日后自赎之日,其洋本归还银主,不得执留,此出两家心愿,各无反悔,口言无凭,故立出粮字为据。
光绪拾陆年十二月十九日 立出粮字人 林长淳
代笔 林万鹤
很显然,此“出粮字”是送户票的变种。由于卖方不愿转让税责,于是买方向卖方另外付出一笔税金。类似情况相当普遍,有例如下:
今得徐昌喜户此粮分厘未有,当中面言,贴出英洋壹元五角正,以作完粮,日后如有此粮,的[得]归徐边,不干阙边之事,恐口难信,故立贴粮字为据。
光绪叁拾叁年五月拾五日 徐木有
依口代笔 张景斋
有的干脆就在契外加批,注明贴过卖主银元数。例如民国十一年(1922)十二月初九黄用财订立的一份卖田契:
立卖断截田契字人黄用财,今因无钱应用,自情愿将父手遗下分己阄内民田,坐落松邑廿二都南坑源白坛庄,安着田壹丘,计燥租五桶,计额三分正,其田上下左右至俱买主自己田为界,今具四至分明,自愿托中立字,出卖与阙起适入受承买为业,当日凭中面断,目值时价英洋弍拾五元,其洋即日交付清乞[讫];不少分厘,其田自卖之后,任凭买主过户完粮,收租管业,契明价足,一卖千休,永远无找无赎,此出两相情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故立卖断截田契字为据。
一批契外贴过卖主英洋壹元正,其每年之粮,卖人自己完纳,此照。
如果真的“卖断”,也就不用卖人自己完纳每年之粮了。由此可见,所谓“卖断”,实为不断。总之,“田底”既然没有“过户”,就意味着土地买卖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意味着卖家有可能回赎土地,就意味着田赋由卖主交纳还是买主交纳,仍是一个问题。这一税责与地权分离的制度安排,为地权的逐渐脱离设置了一个过程。
四 卖主租田:地主即佃农
细读上引民国十一年黄用财卖田契,可知其出售之三分水田本来并非自耕,而是一块出租地。土地出卖给阙起适后,五桶租谷也自然转给了阙起适。类似的例子还有,如民国八年(1919)阙起顺将一亩土地出卖给阙起芳,详见下文:
立卖田契字人阙起顺,今因无钱应用,自情愿将上手遗下分己股内民田,坐落松邑廿壹都茶排庄水缸湾,安着田壹大丘……合共计粮额壹亩正,自愿托兄弟凭中劝说立契,出卖与阙起芳承买为业,当日三面言断,时值价英洋柒拾伍元正,其洋即日收清,不少分文,其田自卖之后,任凭受主过户完粮,归收租谷弍拾肆桶,卖人无得异言……故立卖田契字为据。
一批日后卖人备办原价,对期之日,任凭赎回,此照。
一批契外付过大洋壹元,其利息以作卖人每年完粮之用,此照。
一批付过花押洋弍元正。
在本案中,阙起顺之一亩土地卖价为75元英洋,一年可收租谷24桶。这块土地是活卖,不是绝卖。对期之日,即卖地后的每个周年之日,可以原价赎回。买主在付出75元英洋的土地卖价之后,再付1元,以年利20%计,每亩水田之田赋大约只有0.2元。
这样一来,阙起顺卖出的这1亩水田,可以分解为三种权利。一种是“田底权”,阙起顺承担本块土地每年的田赋,他仍然是这块水田法律意义上的拥有者,此权有“契尾”为证。一种是“田面权”,阙起顺卖出的田面权,市场价格为75元英洋,买主所得年报酬为租谷24桶。由于“桶”的意义不详,不作申论④。这一权利,有“土地执照”或“粮户执照”为证。一种是永佃权,尽管田面权在不同的人手中转让,但本块土地的佃耕者没变。我们推测这位佃耕者拥有某种“永佃”的权利。
还有许多证据,可以确实证明土地的田底权、田面权与永佃权的同时存在。最有趣的事实是,当卖方卖出其田面权后,又向买方租来同一块土地耕种。这时,地主与佃农合而为一,田底权与永佃权集一人之身。有例如下:
立卖田契人阙玉柯,今因粮食无办,自愿将祖父遗下自己股内民田,坐落松邑廿壹都茶排庄,小土名叶山边,自己住屋上手围墙内安着,上至围墙,下至鱼塘余地,外至围墙,内至水圳为界,共田弍丘,计额柒分正,今具肆至分明,自愿托中立契,出卖与阙起柱侄边入受承买为业,当日面断,时价英洋念玖元正,其洋即日交讫,不少分厘,其田自卖之后,任凭买主起耕改佃,永远收租管业,卖人无得异言阻执,与内外子侄人等无涉,日后对期如备办原价,任凭取赎,愿卖愿买,各无反悔,恐口难信,故立卖田契付与买主永远为据。
光绪弍拾陆年五月初壹日 立卖田契人 阙玉柯
一批付过花押洋伍角正。在见 阙起东
代笔 阙玉腾
由于可以备办原价取赎,所以,阙玉柯出卖的是田面权。出卖田面的田主有两个选择,或转让税责,或不转让税责。本案有“收水粮字”证明卖方的税责并未转移,其文如下:
立出水粮字人阙玉柯,原因日先与起柱侄边交易民田壹契,坐落松邑廿一都茶排庄,土名叶山边围墙内,安着田弍丘,计额柒分,今收过水粮洋壹元正,日及取赎之后,其洋付还买主,两无收割是实。
光绪廿六年五月初一日 立出水粮字 阙玉柯
代笔 阙玉腾
阙玉柯未将税责转给买主阙起柱,而是要买方交纳水粮银壹元正作纳税之资。一旦取赎,水粮银一元也将付还买主。很显然卖方是以水粮银之利息来纳税的。关于这一点,前引相关契约已有说明。
接着,卖主阙玉柯向阙起柱讨过刚刚卖出的田面用来耕种。与卖田契及收水粮字相互对照,可以确定阙玉柯同一天中所卖、所收及所讨之田,本来就是同一块田。
立讨田札字人阙玉柯,今因无田耕种,自愿向问到阙起柱侄边讨过民田弍丘正,坐落松邑廿一都茶排庄,小土名叶山边,安着自己住屋上手田弍丘正,计水租谷拾肆桶正,其谷每年八月秋收之日充纳,每年不敢拖欠,如有欠少,任凭田主起耕改佃,种人无得异言阻执,恐口难信,故立讨田札字为照。
光绪廿六年五月初一日 立讨田札字 阙玉柯
在见 阙起东
代笔 阙玉腾
这样一来,作为田底权拥有者的阙玉柯,既是地主,又是佃农。这样的佃农,本来就与其所耕作的土地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他们所拥有的佃耕权只能是永佃权。正如上文所说,即便他们在卖田契中称:“其田自卖之后,任凭买主起耕改佃,永远收租管业,卖人无得异言阻执。”但是,当卖人暨田底权人就是佃人时,“改佃”只是一句格式用语,而不是其他。
卖主在将田地断卖之后,也有可能向买主将田讨来耕种,嘉庆十九年(1814)十一月二十九日,邓元荣立卖田契如下。
立卖田契人邓元荣,今因钱粮无办,自情愿将父手遗下民田壹处,土名坐落廿一都百步庄,小土名百步兰排上,民田大小陆丘……共计额钱粮贰分正,自托中人立契送与本都林新应叔边入手承买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言断,时值田价铜钱叁拾千文正,其钱即日收清完足,其田自卖之后,任凭买主执契管业,过户完粮,起耕改佃……自卖之后,永远为业,不敢(异)言找赎,两家情愿,凭[并]无反悔,恐口难信,故立卖契为据。
虽然契中规定“不敢异言找赎”,其实还是发生找契一纸,时间为嘉庆二十年二月初三,其文如下:
立找断截田契人邓元荣,原与林新应叔边交易民田壹契,土名坐落松邑廿一都百步庄,小土名百步兰排上,亩分界至正契载明,今托原中相劝业主找出契外铜钱贰拾捌千文正,其钱即日两相交付足讫明白,其田自找之后,一找断绝,永不敢异言另生枝节找赎等情,如违甘受叠骗之罪,恐口无凭,立找田契付与林边子孙永远为照。
找契除了增加邓元荣的弟弟邓元得之外,4个中人完全相同。找契与卖契之间相差的两个多月,其实是人为编造的。本找契最为怪异之处,还在于其找价铜钱28千文,与卖价30千文几无差别。在石仓,一般情况下,找价只有卖价的一半。
就在邓元荣卖出土地的当天,即嘉庆二十年二月初三,邓元荣向买方讨来卖出之地用来耕种,有契如下:
立租田札人邓元荣,今因无田耕种,自情问到林新应叔公户内租出民田一处,土名坐落廿一都百步庄,小土名百步兰排上,并屋后田大小九丘,即日三面言断,每年充纳燥谷叁担壹箩正,其谷的至秋收之日交量清楚,不敢欠少桶斗,如有欠少,任凭田主起耕易佃,邓边不得异言执留,恐口难信,故立租札为据。
在本案中,虽然不见办理契尾,但由于石仓基本没有二次找价,所以可以认定,此田已经断卖。卖方已将田底、田面全部售出。邓元荣,从以前的田主,沦落为纯粹之佃农。如不欠租,邓氏可以永佃此田。于是,在田底、田面权失去之后,邓氏拥有的只有永佃权了。
五 “田面”的流转
按照格式,土地卖契只要写明土地四至,而不需写明原户主姓名,送户票则不然,为了完成税粮过户,送户票必须将土地的原户主姓名写得清清楚楚。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原户名,指的是税粮之户名,而非契尾之户名。也就是说,所谓原户名,指的是田面之户名,当然,如果某块土地的田底、田面没有分化,就也有可能是田底之户名。有例如下:
立推迁字人赖登达,日先与王日福交易赎契一纸,推收过户,目今赎出契纸,将赖荣太户内伍亩正,推与阙天贵、培入户完纳,不敢推多少割,恐口无凭,立推迁字是实。
嘉庆拾六年三月初十日 立推迁 赖登达
见字 王日福
代笔 林登发
另有同日配套的收钱粮字:
立收钱粮字人赖登达,今来收到阙天贵粮亩伍亩正,一应顶项收足,立收字为据。
从契中可见,赖登达出售的土地,其户名为赖荣太。赖荣太可能为赖登达父,亦可能为其祖父。“日先”赖登达将赖荣太户下五亩水田,与王日福交易,并转让税责。现在赖登达将契纸赎回,转将五亩水田卖给阙天贵与阙天培,即阙其兴之子,亦并转让税责。不过,由于在转让税责之后,赖登达又要收取阙天贵的税粮钱。“推迁字”中称为“推与阙天贵、培入户完纳”似乎也成了一句虚词。
又有一例相同性质的土地买卖,只是立契人不是卖主,而是买家。
立定字阙天有,买得孙永元田壹处,原系倪士良出卖,契载回赎,如若投税,阙边之事,不涉倪边之事,恐口难凭,立定字存照。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见 承荣
代笔 蓝永和
阙天有买了孙永元的一块田,但这块田之田底却不是孙永元的,而是倪士良出卖给孙永元的。倪给孙的卖田契上写明可以回赎,表明倪是田底权人。现在,倪将此田从孙边抽出,卖与阙天有,由阙天有交税。也就是说,阙天有代替了孙永元,成为这块土地田面权的持有者。
以上两例都是卖方将田面转卖,实际生活中,也有买方将田面转卖之事。详见下引三例,时间分别为乾隆、嘉庆和道光。
立过户票人曹兆龙,今有冯元琳户下民田壹亩九分五厘正,送与本都本乡阙天开户内入册完粮,不得丢漏分厘,立送户票是实。
乾隆四十七年拾月廿三日 立过户票人 曹兆龙
代笔 王宗桂
立送户票人阙发宗,今将云邑伍都徐河庄赖永祯户下民田叁亩正,送入本都本庄阙天开户下入册办粮,不得丢漏分厘,空口难凭,立送户票为用。
嘉庆拾年拾月初四日 立送户票 阙发宗
见送票 阙发保
代笔 李天福
立送户票人阙新魁,今将傅于户内起出粮额柒分正,推入茶排庄本家天开兄边户内入册完粮,不得丢漏分厘,恐口无凭,立送粮票为据。
道光拾叁年十弍月初六日 立送户票人 新魁
代笔 献奎
曹兆龙将冯元琳户下的田面送给阙天开户下。阙发宗送出的田面,户名居然为云和县五都之赖永桢。阙新魁推出的七分土地,本来就是傅于户下的田面。曹兆龙、阙发宗和阙新魁将田面卖给新的主人之后,均将税责转移给他们。这表明,田面是可以脱离田底进行交易的。
由于田面的转手太多,转让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差错,有案例如下。共同立契人及中人人数太多,抄引时删节。
立缴册字人王日福原(于)与旧岁,(将)坐落云邑九都江山源庄,小土名回树潭神坛前槽礁下水坝边民田壹处,托中出卖与阙天贵、天培身边为业,丘段界至,立契载明清楚,契内载有老额陆亩伍分正,徐于乾隆四拾六年将回树潭老田补额折实贰亩零,当日凭中并不知因情,因补额该属界内田项完粮,今再托原中将界内补税之册,遂将王接兴户内粮贰亩有零,情愿缴于阙天贵、天培买主收割完粮,当日三面言断,贴与王接兴边册费铜钱陆仟文正,其钱即日亲收足讫,不少分文,自缴册以后,自送立推签过户,任凭买主收额割户完粮,王边永不敢另生滋事,恐口无凭,立缴册字存据。
嘉庆拾七年伍月初二日 立缴字人 王日福
代笔 林登发
在此契之前,应当还有一份王日福出售6.5亩老额的卖田契,即为正契。由于王日福并非这块田地的田底权人,他不知这块田地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补了二亩零的税额,所以在再次出卖时,需要补足差额,合计则成为一块8.5亩零的土地。在接下来的找契中,这块土地的面积是按照官府备案的全部数值计算的。
立找断截契人王日福,日前有民田一项与阙天贵、天培交易,土名坐落云邑九都江山源庄,小土名回树潭水田壹处,上至山为界,下至溪为界,内至溪与山为界,外湖内大石丘田塍外高坎为界,四址分明,大小不载丘数,共计实额捌亩伍分零正,只因家口缺乏,再请托原中向前相劝主阙边找出契外铜钱壹拾壹仟文正,其钱即日随契当中交讫,不短分文,其田自找之后,永为阙边子孙血业,年深日久,并不敢言称找赎等情,如有此情,自愿甘受叠骗之罪,愿找愿出,今欲有凭,立找断截契付与业主永远为照。
嘉庆拾柒年六月廿一日 立找截契人 王日福
代笔 林登发
由于田面与田底脱离,辗转出售的田面很难保证不在转让的过程中发生错讹。好在石仓的土地总是卖而不断,卖而不绝,所以,还有可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在研究中时常会面对契约书写中的各种错误,觉得不可思议:契约也会出错?但转而释然:在一个熟人社会中,明显的书写错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是很容易得到纠正的。
六 讨论
回到本文开篇时的提问中来。杨国桢先生在引用了相关契约与碑文后,还引嘉庆手抄本《钱谷必读》的有关记载,其文如下:
立契成交之后,原主同现业赍带契纸推字赴庄书处。如原业田粮,本庄一都二图,现业住在二都三图,则应过入二都三图册内。一都一图之庄书,查收卖主推字,将粮于册内注除出应过亩分数目之条,交于二都三图之庄书,照数科则,添于册内。
杨国桢先生解释说:“‘过’是改入新业主所在地的册籍上,以便输粮。‘割’是在原业主所在地的册籍上,除去卖出亩分数目和应输之粮。”⑤这一解释完全正确。因为《钱谷必读》所述与石仓的情况可以吻合。依石仓之例一,就是土地卖方在卖出土地后,开出送户票(亦即“卖主推字”),将税责转让给土地买方。
不过,在石仓,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卖主不愿转让税责,他们不但没有为买方开具送户票,反而接收买方交来的“税粮字”或“水粮字”,自己完纳田赋。或者,由买方在土地价格之外,再多交一份贴银钱,以作卖家交纳田赋之资。由此看来,由于《钱谷必读》等叙述乡村土地买卖的具体过程,不够细致,所以,另一种不转让税责的土地买卖为其忽略,于是,乡村土地产权的复杂性也就长期为研究者所忽略。
这种不转让税责的土地买卖,在明代是相当普遍的。杨国桢征引万历十三年(1585)刊刻的《四民利观翰府锦囊》中契约格式,其中关于“推收”的文字如下:“自卖之后,请买主一任前去管业……此系正行交易,甘愿自卖,其田该载产米若干,候在大造黄册之年,自用收割产亩□户当差,递年津贴粮役与出产人,了纳粮差,不致留难,向后再无异说执僭之理。”⑥文意并不完全清楚,但“递年津贴粮役与出产人,了纳粮差”一句,却是明白表明,在完成田底过户之前,需要补贴粮役给卖方,交纳粮差。
栾成显先生在研究了一批明代中后期的徽州“推单”后也指出:“在推单之中,多有‘税粮自卖年起至造册年止并收足讫’的说法,这是由于交易之际并非大造之年,税粮尚不能过割,田土虽已卖出,但税粮仍需由卖方交纳的缘故。”⑦明代的“推单”当然不会说明,卖方交纳的税粮由谁来提供,而石仓的收粮字却表明,这是买方而非卖方的责任。由此看来,石仓的送户票与收粮字制度由来历久,明清时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田赋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石仓的送户票与收粮字所反映的土地交易中间过程,证明了浙南山区地权之分化。虽然当地并无“田底”、“田面”或“田骨”、“田皮”之称谓,却有“田底”与“田面”分化之事实。田面之出卖,本质是抵押。由此而推论,只要存在土地的信贷市场,就一定存在田底与田面之分化。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对于中国乡村地权分化及其相关问题,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田底权还是田面权,指的都是土地的所有权。具体而言,土地所有权可以分解为三种权利: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当田底与田面分开,即一块土地已经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产权人时,所谓田底权人,只拥有部分收益权和部分转让权,所谓田面权人,在不转租的情况下,拥有全部使用权、部分收益权和部分转让权⑧。需要说明的是,石仓的田面权指的是那种地租率较高,不可能转佃收取小租的“相对的田面权”,其理由是,我们在石仓尚未发现那种可以转佃收取小租的“公认的田面权”⑨。行文至此,窃以为长久缠绕学界的土地产权之争论,似乎可以尘埃落定了。
注释:
①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0—253页。
②( )表示漏字,[ ]表示错字,下同,另外,一些民间通行的错别字依原文。不一一说明。
③单丽、曹树基:《从石仓文书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④石仓的“桶”一般有两种,一种为大桶,每桶20斤;一种为小桶,每桶2斤。村民称民国时期的桶一般为20斤。如果此数据为真,24桶折合480斤,几乎为亩产的全部。地租不可能多至如此。如果为每桶2斤,24桶合计为48斤,作为一亩水田的租谷,则太少。暂且存疑。
⑤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253页。
⑥同上书,第24页。
⑦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再往上溯,杨国桢引元代泰定元年(1324)刊刻的《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记载了元代的契文格式,关于推收,则有下文:“从立契后,仰本主一任前去给佃管业,永为己物。去后子孙更执占收赎之理,所有上手朱契,一并缴连赴官印押,前件产豕仰就某户下改割供输,应当差发”(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29页)。由于从土地出售至地权过户之间似乎没有时间差,所以也就不存在何人交纳税粮之问题。从这一点看,元末的契约格式与明代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⑧参见曹树基、李楠、龚启圣:《“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1728-1949)》,《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8—131页。
⑨参见曹树基:《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8—121页。
标签:土地买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