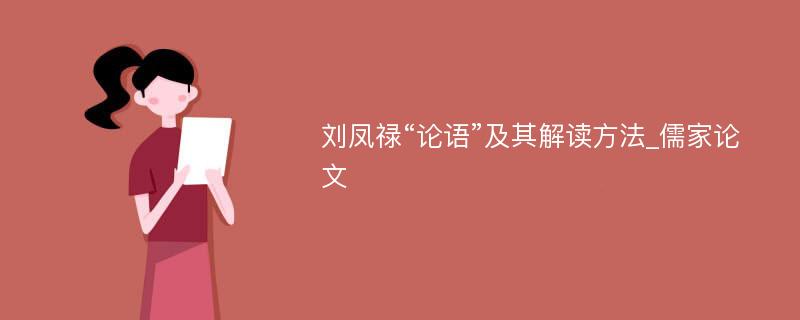
刘逢禄《论语述何》及其解经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其解论文,方法论文,刘逢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逢禄所箸《论语述何》二卷,现存有两个版本:一是《清经解》本,二是《刘礼部集》本。二者主旨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是:《清经解》本解《论语》条目多于后者,所多者,大都与公羊春秋无直接相关。再者是语言组织上在某些条目略有不同,但不影响大意之相同。《刘礼部集》是魏源所辑刘逢禄遗书,《清经解》本应是在遗书基础之上有所增订。在体例上,《刘礼部集》本基本上是取《论语》诸条目中某一句进行发问:“何谓也?”、“何也?”,再做出回答。从其行文对问题的贴近,更能发现其解《论语》的思路,《清经解》本虽然也是就某句作解,但无此种方便。基于此,本文的讨论主要以《刘礼部集》本为据。
一、《论语述何》的主旨
据刘逢禄自述,《论语述何》是因劭公《论语注》久佚,抉取《解诂》、《繁露》之说,存其大凡之作。(注:刘逢禄《论语述何》自叙有,“今追述何氏解诂之义,参以董子之说,拾遗补阙,冀以存其大……”。参见《刘礼部集》,清光绪十八年(1892)延晖乘庆堂重刊本。)由此可知两点信息:一是所谓“述何”实则是述汉代公羊家(何休作《解诂》,董仲舒作《繁露》),二是刘逢禄之意不在解释《论语》,而在“述何”,是对何休《论语注》久佚而做的恢复性工作。何休是东汉公羊家,阮元编的《十三经注疏》中有何休解诂、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而刘逢禄正是以《春秋公羊传何氏释例》奠定了他作为清代最有成就公羊家的地位。《论语述何》即是借《论语》来讲说公羊学,下文即可表明此种旨归,这开启了一条与传统通常解读《论语》不同的路子。(注:一般认为刘逢禄是清代以公羊学集中解《论语》的肇始者,这种做法除了受何休《论语注》久佚的启发,还受庄存与的影响,如张广庆先生即认为庄存与乃是发群经大义公羊化之端者。(参见张广庆“清代经今文学群经大义之《公羊》化”《经学研究论丛》第一辑,台北圣环图书公司,1994年,页259)另据郑卜五先生考察,孔广森对刘逢禄的影响更大,孔广森虽与庄存与一样未集中以公羊学诠释某部经典,但在《春秋公羊通义》中,已有将公羊学同《孟子》、《论语》、礼学相会通之做法,从刘逢禄《春秋论》等处对孔广森的推崇看,孔广森确对刘逢禄《论语》大义公羊化的做法有相当大的影响。(参见郑卜五“常州公羊学派‘经典释义公羊化’学风探源”《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上,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经学研究丛刊6,民国九十二年)本文主题与张、郑二先生不同者,在于贴近《论语述何》文本,从方法角度对刘逢禄解《论语》作较详的分析。)
通过归纳,《论语述何》的主旨大致可分为:孔子作《春秋》;《春秋》的一般特点;《春秋》微言;《春秋》大义几个部分。主旨在作者的解释趣向中体现出来,而解释趣向又与解释方法相伴。现择有代表性之例,并对照朱熹的注,表明刘逢禄的解释趣向,同时为后面对方法的讨论作个铺垫。
(1)孔子作《春秋》
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作《春秋》,孔子于是成了《春秋》大义与春秋时代现实联系的中介,读《春秋》其实也就是重塑历史情境的精神体验过程,以孔子之心为心,达到一种“视界融合”。或许是基于此种原因,今古文经学家都重视经典的作者。周予同先生整理今古文异同,在所列十三条之中,有五条是关于作者—孔子。(注: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9。)在《论语述何》中,刘逢禄即是将孔子作为《论语》大义公羊化的枢纽,表明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遂成为其主要工作之一:
(为政第二:4)(注:《论语述何》并未注出《论语》出处,为方便查考,特注出,下同。)五十而知天命何谓也?夫子受命制作,垂教万世。书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知天命之谓也。
刘逢禄与朱熹在解释《论语》时,因注意所指的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内容。朱熹注“五十而知天命”为:“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朱子所注,重在阐发天道性命。刘逢禄则重在“五十”、“中身”上,“五十”只是一个年龄数字而已,他却援引《周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遂将“知天命”引申为“受命”,于是得出“夫子受命制作,垂教万世”,从公羊学的语境看,制作即是制作《春秋》。
(述而第七:19)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何谓也?上章言易诗书礼,此谓作《春秋》也。吴楚猾夏,乱贼接踵,所以发愤著书也。《春秋》成而乐尧舜之知我,盖又在暮年矣。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朱熹注为“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然深味之,则见其全体至极,纯亦不已之妙,有非圣人不能及者。盖凡夫子之自言类如此,学者宜致思焉。”《论语》中并未明言“发愤”等状态所指向的行为,朱子认为是指向“学习”。刘逢禄则以之为发愤著《春秋》。
(述而第七:24)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何谓也?曰《易》本乎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不足以至隐者,不书也。故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春秋》之义,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无行不与。
朱熹注“二三子”一节,将“吾无隐乎尔”解为:“圣人作、止、语、默无非教也”。刘逢禄则解为“《春秋》推见至隐”,且引《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页3297)为据,从而将“无行不与”与《春秋》见诸行事之“行”结合,于是“无行不与”的结果巧妙地成了二三子皆身通《春秋》之义了。此时,孔子作《春秋》是问题的核心。
(子罕第九:5)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何谓也?曰,《春秋》宪章文王,《传》曰,王者孰谓,文王也。礼乐制度损益三代,文王之法也。
刘逢禄对不同条目的解释时简时繁,此处解释甚简,只表明了《春秋》以文王之法为根本。在公羊学里,文王就是孔子理想文明的象征,如《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之“王”就解释为“文王”。朱熹未解释文王,他解释了后面的“文”:“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兹,此也,孔子自谓。”同是看重孔子,在朱熹那里孔子是有谦谦君子之象的圣人,在刘逢禄那里孔子则是作《春秋》、行天子之事的“素王”。如:
(述而第七:23)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何谓也?曰: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将受命制作,素王万世也。
孔子与《春秋》关系之讨论在公羊学中尤其重要,何休解诂《春秋公羊传》集早期公羊学大成,并作为后世公羊学的蓝本。他所认为的“三科九旨”都立足于孔子,如第一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注:徐彦说:“故何氏《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参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195。)不只关乎“三统”之义,而且同“素王”说一道,显明了《春秋》一经的性质,即《春秋》是一部针砭时弊的法典,含有改旧制立新制的义理。此性质需要借助某位圣人表明出来,也就是说,若无孔子修(作)《春秋》,则公羊学中重要的判断“以《春秋》当新王”、“素王”之说便无有着落处。第二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第三科“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表明了这样一个立足点。(注:第三科除表明空间之外,还同文明与否的行为有关。)《孟子》、《公羊传》、《春秋繁露》、《史记》都曾明言孔子作《春秋》,(注:《孟子》、《春秋繁露》、《史记》多处言及孔子作《春秋》,兹不赘引。今本《公羊传》唯有昭十二年说:“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是—条明证。另外,(清)臧琳引晋人孔舒元(著有《春秋公羊传集解》,见《隋志》)哀十四年传有“为孔子之作《春秋》也”(今本无)。(参见阮芝生《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民国五十八年,页40))刘逢禄即是对此公羊学学统的继承。
(2)《春秋》的一般特点:
刘逢禄有言:
(述而第七:8)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何谓也?曰圣人之言皆举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约而旨无穷。董子说《春秋》云:不能察寂若无,深察之无物不在,谓所不书多于所书也。
《论语》此句完整是:“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可知朱子是在普遍意义上的教与学处作解。刘逢禄则引用董仲舒之说,给出了孔子此说的语境,认为孔子因《春秋》不书多于所书而出此言。
(卫灵公第十五:24)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何谓也?《春秋》不虚美,不隐恶,褒贬予夺,悉本三代之法,无虚加之辞也。故曰:《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刘逢禄因“毁誉”这样的字眼,便念及《春秋》之褒贬;看到“三代”便念及《春秋》复古的理想,所谓“悉本三代之法”,最终得出“《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与《春秋繁露》都有此说)。“三代之法”本来是指三代的王法,即一套礼法秩序,刘逢禄是基于对“斯民”理解,来表明孔子复古的政治理想。朱熹则以毁誉的本意作解,其言“毁者,称人之恶而损其真;誉者,扬人之善而过其实。夫子无是也”,对“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的解释,也只是说三代之民善其善、恶其恶而无有私心,并以此说明孔子对毁誉的慎重。需要说明的是,刘逢禄并没有录入《论语》之“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一句,朱熹解之为“则必尝有以试之,而知其将然矣”,如果将“试”解为在接触中考察某人是否值得赞誉,才决定是否赞誉,则刘逢禄的解读便不合适。如果将“试”解为通过历史知识中的某人行事来决定是否赞誉某人,则刘逢禄的解释有道理。他没录入这句话,也没有对此做出说明,是否他也是认同第一种理解,出于他的解读目的而故意省去?
上述刘逢禄说《春秋》“兼采列国史文”“择善而从”、“不书多于所书”、“不虚美,不隐恶,褒贬予夺,悉本三代之法”,都表明《春秋》的一般特点,这是《论语》中所未明言的。
(3)《春秋》微言
《春秋公羊传》里的“微言”大致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在于曲折表达的方法,基于孔子布衣的身份不能直接表达褒贬态度,或者因为时代远近不同而有用情的不同(董仲舒所言“与情俱也”即是)等等,最终指向的是对礼法秩序的维护,与大义相关,但在过程上却是隐微的。另一为改立法制以致太平的隐微之言,其内容是改旧制立新制,如质、文之变。
在《论语述何》中,刘逢禄对“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的申明对应着第一个层面的微言:
(为政第二:18)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何谓也?多闻如《春秋》采百二十国宝书,于史文阙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慎之至也。多见,谓所见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辞,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
此是孔子对于张学干禄的教导,其言不必然指向《春秋》的写作谨严,以及隐微书写的原因。刘逢禄在此通过“多闻阙疑”与“多见阙殆”,表明了《春秋》“三世”之义。
(八佾第三:5)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何谓也?曰《春秋》之义,诸夏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卫劫天子之使,则书戎,邾牟葛三国朝鲁桓,则贬称人之类是也。潞子婴儿之离子夷狄,虽亡犹进爵书子,所谓夷狄进于诸夏则诸夏之也。与其为卫邾之有君,不如为潞子之亡,何也?《春秋》书灭者亡国之善辞,言王者当兴之也。
朱熹、刘逢禄二人对此句的解释有较大的分歧,关键在对“如”训诂上。朱熹注为:“吴氏曰:‘亡,古无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伤时之乱而叹之也。亡,非实亡也,虽有之,不能尽其道尔。’”朱子承程子等人之言,训“如”为“象”,意思是夷狄尚且有君,不象诸夏没有君。如此训“如”,确如尹氏所言,是孔子感伤之叹。而在刘逢禄那里,“如”是“及”之意,整句的意思变成了“夷狄虽有君,比不上诸夏没有君”,即是:“与其为卫邾之有君,不如为潞子之亡”,本来被认为是夷狄的潞子,在刘逢禄的解释中直接成了诸夏,因此比朱熹的解释多了一层含义:诸夏与夷狄的区别不是固定的,而是依据其行为是否合于孔子的理想而区分的,这也是《公羊传》中夷夏之辨的核心思想。
另一层微言指改立法制之隐微,如三统说:
(八佾第三:4)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何谓也?曰此以见《春秋》变周之文,用夏殷之忠质也。忠质亦以为中也。如俟其物穷自变,矫枉过直,则为秦人之纵肆,晋人之高放,三代之治泯如矣。
朱熹注说:“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是对孔子之言的正确理解。刘逢禄进一步同公羊学“变周之文,用夏殷之忠质”联系起来:孔子在《论语》中强调“质”,正与董仲舒、何休等人之“三统说”相合。这其实是刘逢禄公羊学“三统说”的背景使然。如《论语述何》另一处说:
(为政第二:23)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何谓也?曰殷受夏,周受殷,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故春秋立百王之制,通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故告颜子为邦,兼用夏殷周之制。仲尼以万世为土(疑有误),何但十世哉?(注:《清经解》本对此的解释是:“继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则治,不循则乱,故云可知。”同前者虽语言组织不同,内容则一致。)
(4)《春秋》大义
皮锡瑞认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以戒后世。(《经学通论》)《公羊传》虽无明言“义”字,但汉代公羊家多有对《春秋》之义的彰明,如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云:“《春秋》之义,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地之礼也。”(《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92年,页404)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页3298)等等。由此可见,皮氏所谓《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关注的是《春秋》中所含的一套礼法秩序,乃是古已有之。刘逢禄在《论语述何》中亦有对此的申明:
(子路第十三:7)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何谓也?曰鲁无君臣,卫无父子,政本皆失,故夫子正之于《春秋》而复叹之。
朱熹注为:“鲁,周公之后,卫,康叔之后,本兄弟之国,而是时衰乱,政亦相似,故孔子叹之。”杨伯峻译文只言及鲁卫两国政治如兄弟一般,(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页136。)刘逢禄则在此强调了鲁无君臣,卫无父子。从内容上,刘逢禄更为具体,意思更为明确:鲁国三桓当政,是为无君臣之礼,而对于卫无父子,刘逢禄在《论语述何》另一处说:
(述而第七:15)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问而出曰:夫子不为也。而公羊许拒蒯聩立辄,何谓也?曰《春秋》绝蒯聩之出奔,又不与其入卫。而先齐国,复以明伯讨,许石曼姑以强王,义非许卫辄也。辄固不得拒父,然受命于灵公,亦不得背祖而私逊父以其位。故为辄之义,止当不为丧主避位以谢父而已。为石曼姑之义,止当于蒯聩入则守义以拒之,若辄避位则援郢立之而已。其祸启于灵公不立公子郢而立辄,故夫子于《春秋》绝蒯聩,于《论语》不为辄,以为于义皆非也。
《公羊传》哀公三年对卫无父子之史事有说明,卫灵公因世子蒯瞆“无道”,而将其逐出国门,灵公死后,大臣曼姑受命于灵公立蒯瞆之子辄为卫君。后蒯瞆在晋国赵鞅的帮助下回国,大臣曼姑于是帅师讨伐蒯瞆。考何休解诂的意思是,虽然辄在王法上应该遵从其祖父灵公之命成为卫君,但“非义之高者也”,义之高当怎样,他没有明确说明,而是引用了《论语》此节。(注:参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页2346。)刘逢禄则明白说明了辄虽然未违反王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公羊传》)——承其祖父之位,但为其父亲蒯聩之故则应当避位,这样才既守王法又能显出父子之义。辄未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春秋》绝蒯聩、《论语》不为辄。总之是因为孔子心中有高义在,而卫无父子之义是肯定的。朱熹注此指出了“卫无父子”的关键:“若卫辄之据国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语(按,相对于伯夷、叔齐)明矣。”
(颜渊第十二:9)哀公问年饥,用不足。有若曰盖徹乎。何谓也?曰,鲁之不足,由于三家四分公室,故季氏富于周公而君贫,宣公不治其本而税亩于公田之外,复用徹法,春秋讥之。后乃复古,书大有年,见天人相与之际。今哀公因年饥而欲用田赋,是敺民而归之三家也。故有若风其收民心以强公室,岂徒为迂论而已。
朱熹注《论语》,于此节所着重发挥者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所谓“君民一体之意”。刘逢禄则将重心移至“强公室”而“弱三家”,强调上下尊卑之义。
(子路第十三:30)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何谓也?曰礼比年简徒谓之蒐,三年筒车谓之大阅,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讥罕也。郑元言用不习之民使之攻战必破败,是谓弃之,公羊疏谓何郑意别实不别也。
桓公六年《公羊传》有:“大阅者何?简车徒也。何以书?盖以罕书也。”昭公时也有类似说法。刘逢禄在此明确抬出“礼”,《春秋》讥罕乃是礼的要求,并指出此礼在义理上的根据: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朱熹在此注为:“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朱子在此是直接解释字面的意思。刘逢禄则以军礼为中介,引向《春秋》“重民”之义。
(卫灵公第十五:14)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何谓也?曰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举,罪与三家者同。春秋于庄公二十八年书臧孙辰告粜于齐,讥其为国不知礼也。自后大乱三世,臧文仲执政若罔闻。知历庄、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书其卒。馀事曾不见于策,盖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贤病国之臣,不若遄死之为愈尔。
朱熹注的意思是,臧文仲知贤而不举,是不称其位。刘逢禄则贴近《春秋》,指出臧文仲历春秋四世,本当有诸多事迹可见于策,可见是孔子削了他的事迹。刘逢禄指出臧文仲妨贤病国、素餐尸位之不仁,突出《春秋》“举贤良”之义。
此时,不妨对朱熹与刘逢禄二人在《论语》内容上的解释旨趣作一简单对比:刘逢禄以孔子为“素王”,认为孔子作《春秋》,并且《春秋》中有“微言大义”,显然这些都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而朱熹则认为孔子是圣人,并立足于“德性教化”解《论语》,其逻辑是孔子体认到“天理”,并以“圣人作、止、语、默无非教也”来言传身教。从朱熹的“天理”到刘逢禄的“天命”,孔子在二人的解释系统中都是作为天与现实的中介存在的。所不同的是,在朱熹那里,孔子的言传身教都是天理的发动流行。在刘逢禄这里,孔子虽承天命作《春秋》,在具体内容上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且有在礼乐制度上损益三代的自主性。二人学术背景的不同使他们对《论语》的解释不同。
二、刘逢禄解《论语》的前提与方法
(1)前提
刘逢禄作为公羊学者,与何休、董仲舒一脉相承,认为公羊学是在彰明孔子微言大义。刘氏在《论语》“我爱其礼”一条下说:“《论语》与《春秋》相表里者,皆圣人口授之微言”,另在《谷梁废疾申何·叙》中说:“《春秋》微言大义,《鲁论》诸子皆得闻之,……其不可显言者,属于夏口授之,公羊氏五传始著竹帛也。”(《刘礼部集》)在孔子、《春秋》、《论语》这个三角结构中,孔子与《春秋》之关系(作《春秋》)在今文经学中甚为明确,而孔子与《论语》的关系在传统中也得到一致的认定。这使得刘逢禄可以将《春秋》与《论语》互释,对此《论语述何》中有例可明显证之:
(季氏第十六:1)季氏伐颛臾,不书于《春秋》,何也?曰,封内兵不録,或闻夫子言而止也。成王以大田附庸锡之鲁公,故在邦域之中。董子述附庸之制,称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颛臾不见于《春秋》,其小大则未之详。
刘逢禄自问“季氏伐颛臾,不书于《春秋》,何也?”之时,已然认定《论语》与《春秋》同出于孔子矣。又如:
(述而第七:21)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于《春秋》有当乎?曰,《春秋》外离会不书者,言不足别善恶,此其义也。
由此可见刘逢禄解论语的前提:有两个文本,一是面前的《论语》,一是心中的公羊学,二者同源是其“先见”。当前者用辞或义理与后者相遇之时,便取后者以注说前者。
(2)方法
考察《论语述何》所涉及的《论语》的原始语义和语境,发现《论语》与公羊学之间呈现出三种关系:一是《论语》本身明确与公羊相合;二是《论语》暗示出与公羊相合;三是《论语》本身明确与公羊无关。在这三种情况下,刘逢禄都将之做了公羊化解读。下面在表明这三种关系的同时,讨论刘逢禄公羊化《论语》的方法。
第一、《论语》本身明确与《春秋》相合者。
在此,“明确与《春秋》相合”的意思是,《论语》在语义上与公羊学相合,而语境上又未排斥这一点。如:
(述而第七:1)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夫《诗》、《书》、《礼》皆述古,《易系辞》、《春秋》则夫子所作,不纯乎述,何也?曰: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其义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尔。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本身与《春秋》“复古”的精神核心一致。所以刘逢禄以《春秋》“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其义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尔”,来解释“述而不作”。
又如前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条,《论语》中本就含有《春秋》之义:感叹中原诸国礼崩乐坏,欲使之回复到三代盛世。刘逢禄的解释则进一步表明了《春秋》在夷夏之辨中的隐微处:夷狄与诸夏并非固定,依行为是否文明而定。
再如《论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条,以及针对“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刘逢禄说:“子夏言学必以行为本,《春秋》损文用忠之义也,世有仅明小学而不知大学者,子夏所谓未学之人也。”也与《公羊春秋》损周之“文”,益夏殷之“忠”、“质”相一致。(注:马一孚在其“《论语》大义(《春秋》教)”里用了不少篇幅,讨论《论语》里所含有的《春秋》改制的内容。参见《复性书院讲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另外,“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条,是《论语》中所含有的“举贤良”之义,刘逢禄结合春秋历史给出了《论语》此条的具体背景。其它还有多处,如《论语》讥季氏八佾与《春秋》之礼相合,等等。
所相合者,其实都是儒家的普遍追求。在此点上,不惟《公羊春秋》与《论语》相合,儒家其它经典中都包括了类似的价值取向。只是刘逢禄特意地使之与公羊学联系起来了,使用的方法是将主题深化或具体化。
第二、《论语》暗示与公羊相合者
此所谓“暗示”,是指《论语》在语义上并不一定指向公羊学,但在上下文之间又没有表明与《公羊春秋》必然无关,且某些地方的确又易令人产生朝向公羊学的联想。对此情形,刘逢禄在他的理解背景中用类比引申的方法将之与公羊学相联系。
如:“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条,其中的“发愤”表明一种行为状况,可以指向任何事,朱熹填上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学”,而刘逢禄填上的是“著《春秋》”。在这种情形下,所填越具体,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刘逢禄何以如此认定是“著《春秋》”?我们看一下他下面的解释当可明白:“《春秋》成而乐尧舜之知我,盖又在暮年矣。”原来是因为《论语》中这个“乐”字使然,《春秋公羊传》哀十四年传有:“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显然,刘逢禄认为《论语》中“乐而忘忧”之“乐”与《公羊传》之“乐”是一体的。
另外,如前所举以“木铎”为“素王”;“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以毁誉类比褒贬,引申出公羊学通过“褒贬”来传达政治理想;“鲁卫之政,兄弟也”,由其中“兄弟”一语,与鲁卫两国政治败乱联系一起,引申出了公羊学君臣、父子之义。等等都属类比引申。
还有一种在解释上跨度较大情形:
(阳货第十七:19)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圣人之文天文也。天道至教,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春秋》之文,日月详略不书者,胜于书,使人沉思而自省悟。不待事而万事毕具,无传而明,不言而著,子贡知之,故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刘逢禄以类比之法,基于天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牵引到《春秋》,以《春秋》为天文,日月详略不书者,胜于书,使人沉思而自省悟。在这里突出的是解释者的知识背景,不同于其它处,其它处突出的是《论语》自身朝向《春秋》的暗示。虽都不免于刘逢禄作为解释者的领受,此处所表现的《论语》与《春秋》之间的距离较远。这种因《论语》对天的讨论而类比《春秋》特点,在朱熹那里丝毫无有迹象,朱子注说:“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
与此相似,前举:“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一条,则是将一种教学特征与《春秋》的“文约而旨无穷”、“所不书多于所书”相类比,也是一种跨度比较大的解释。可见,解释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文本暗示与解释者共同参与的结果,且在《论语述何》中,时有解释者参与意识过强的表现,下面一种情况尤其体现出此点。
第三、《论语》本身与公羊无关者
《论语》与公羊无关者,是指通过其上下文来看,《论语》某些条目传达的主要意思一定不是刘逢禄所发挥的内容。然而刘逢禄却以“断章取义”的方法将之引向了公羊学。
如前所举“春秋微言”部分的:“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论语》此条完整的是:“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从整个语境看,此条主题是“求俸禄”。刘逢禄只就其中某句解释,完全不考虑上下文,甚至认为“多见”是“所见世”。如果加上对主题的考虑,孔子于《春秋》慎言,似乎不再是避害容身,而是为了俸禄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再如:
(述而第七:28)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何谓也?不知而作,谓不阙疑也。多闻者,兼采列国史文,择善而从,取其可征以寓王心。多见谓所见世,识其行事不著其说也。
朱熹说:“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识,记也。所从不可不择,记则善恶皆当存之,以备参考,如此者虽未能实知其理,亦可以次于知之者也。”其言“未能实知其理”,可知朱子未将《论语》此节与孔子作《春秋》相连,因为朱子对《春秋》“微言大义”的认识与公羊家相契合,(注:皮锡瑞“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经学通论》《春秋》部分,中华书局,1954年。)必不会以为孔子作《春秋》是“未能实知其理”。刘逢禄则将“择善”与“王心”相连,解“多见”为“所见世”,表明孔子作《春秋》的原则。但刘逢禄置《论语》“知之次也”不录,表明他知道《论语》本意,但为了与公羊学相联系,故意略去了一些解读上的障碍。
从“论语述何”这个句式来看,如果主词是《论语》,要求会严格得多,既要求本《论语》原意,又要“述何”。如果所暗含的主词是“刘逢禄”,那么即是刘逢禄通过《论语》来“述何”,在解释上便可以不那么严格。换言之,只要能“述何”,是否遵循《论语》原意则不甚重要。通过上面三种情况尤其从刘逢禄断章取义的解读来看,可以肯定,“论语述何”的主词并非《论语》,而是隐藏在后面的解读者“刘逢禄”,解读者的主动性在几种方法里展露无遗。
三、结语
刘逢禄是以公羊家面貌出现在儒学史上的,有人(如蒋庆先生)将儒学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形而上基础已由当代新儒家给出,政治儒学形而上基础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公羊学是政治儒学的主要内容。显然,这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当我们读《清经解》本《论语述何》时就会发现,在众多的条目中,刘逢禄也强调心性上的修养。这当然与《论语》文本本身有关,但也可以看出来公羊学者未尝不重视心性,(注:公羊家对“心”、“志”的重视在董仲舒那里就有所体现,如在《春秋繁露》“玉杯第二”中提出“徐而味之”、“察视其外,可以知其内也”的解读《公羊传》之法,可见一斑。)只是在儒学体系上侧重“治”、“平”的理解。如客观看待《论语》,会发现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在为学、做人、制度诸方面,可以概括为两个向度:朝外的与朝内的。从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春秋公羊传》基本就是感于春秋时代的衰乱,而传达出对周代宗法制度的怀念,或说对一套礼制的尊崇。这是《论语》朝外向度与公羊学相合之处。朝内的向度如《论语》所强调的“仁”,与公羊学变周之“文”而从殷之“质”之说相合。所谓质,基本就是指《论语》中的“仁”,是礼的根据,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本真的道德情操。在“朝外”与“朝内”之间,“朝外”是孔子基本的关怀,这是由孔子生在春秋乱世的背景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朝内的向度应是朝外向度的辅冀。但朝内的向度又有其自足的意义,从孟子到宋明儒对心性的张扬即是以此为基础。刘逢禄和朱熹各自着重发挥了《论语》中所含的两种“元素”,至于朱熹的“天理发见流行”是他那个时代的学术旨趣。而朝外的向度始终与社会现实关系甚紧,其在汉代的兴盛是由于经学升至国家的正统地位之故,在清代公羊学兴起之初是受经学复古思潮的影响。晚清则是由于时势与经典的关怀相妙合,即使没有庄存与等人重新兴起公羊学,也难保康有为不会有记公羊学之古来改制的举措。
回到刘逢禄这里。大凡一个人在解读某文本之时,会将文本语义往其既定的思想框架中引接,如牟宗三先生认为孔子将“天”推远了,而有基督教背景的人则会认为孔子始终以“天”作为其根据。没有人能判定二者孰“真”,但我们可以从其引述的材料中判断哪一方更为合理。对刘逢禄《论语述何》也当如此看,其将《论语》与公羊学比附有一定的根据:一,春秋时代背景一致,如《清经解》本中,刘逢禄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学”为“学谓删定六经也”,对通常解读为“学习”作了具体限定;二,孔子复古大义一致。这两点罩在《论语》具体表述上,基本不会让人有不适之感。但有些地方为迁就公羊学而对《论语》断章取义,则是因为其个人背景太过强烈或“述何”的目的使然。刘逢禄之后,宋翔凤、陈立、戴望、康有为等相继沿此路说《论语》,形成了清代晚期《论语》大义公羊化之学风。因公羊学本来就切近于人事,此学风根本上或与现实历史情境相关,康有为《论语注》尤可体现此点。从表面看,《论语》大义公羊化这种类似“讬古改制”的解读确有一时之效,但其中含有的“过度”解释在经过澄清之后,其效果则有可能恰恰相反,然则此学风于勘落传统公羊学局限在胡毋生、何休条例做法之时,却为公羊学带来了些许新的气象。
标签:儒家论文; 论语论文; 刘逢禄论文; 十三经注疏论文; 史记论文; 公羊传论文; 朱熹论文; 春秋繁露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