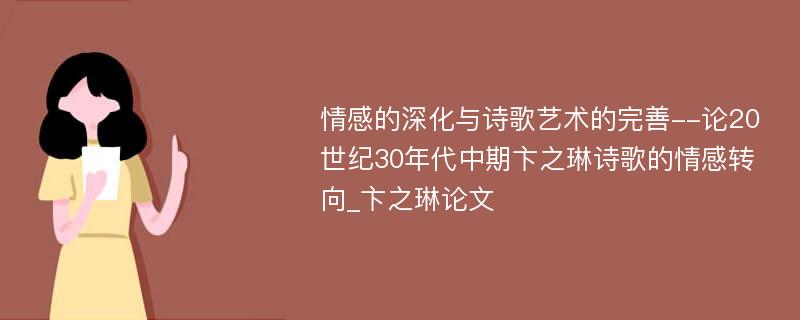
情思的深化,诗艺的提升——浅论卞之琳三十年代中期诗歌的情感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艺论文,情思论文,三十年论文,诗歌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3)02-0131-05
卞之琳是一位不愿张扬,喜欢思考的诗人。诗如其人,他的诗歌世界里充满了平和恬静的气息,朦胧含混的意象。对于他诗歌的解读,历来都是评论界头痛的难题。除了词义含混、意象朦胧之外,卞之琳诗歌中所隐匿的感情倾向是最难捕捉的。就连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在解读卞之琳的时候也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因此卞之琳的诗历来都被读者认为是:“谜一样”(注:亦门:《诗与现实(第二册)·<内容一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11月初版,第100页)的诗。晦涩而不易领悟作者创作之要义。这主要因为:一、作者自身对于诗歌创作的严格要求:“我写诗,而且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规格本来不大,我又偏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1](p1);二、作者写诗不仅抒发情怀,而且表现他那份独到的人生体验。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卞诗看作是晦涩难懂的诗,而应该注重诗歌所暗含的具有卞之琳特色的那份情感淘洗和体验。
以1935年卞之琳在日本创作的诗歌《在异国的警署》为界,我认为卞之琳诗歌此前和此后暗自流淌着两种大的情感流向。一是在这首诗之前的茫然、苦闷、孤独的情思;二是在这首诗之后的充满理趣的情感体验。本文试以《在异国的警署》为分界线,探讨上述两种情感流向,并对三十年代中期卞之琳诗风的转变作一梳理。
一、
诗人产生诗歌创作的冲动,往往都是他们心中情感的积蓄所致。这种情感不是充满激情,就是愁楚满怀。尽管刚刚步入诗坛的卞之琳还是一个没有走进社会,生活在校园里的大学生(卞之琳步入诗坛,是偶然机缘所致)(注:卞之琳在《雕虫纪历(增订版)·自序》中回忆他自己走上诗歌创作道路时写到:“不料他(徐志摩)把这些诗带到上海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居然大受赞赏,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分交给一些刊物发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姓名。这使我惊讶,却总诗是不小的鼓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第2页)),但是,促使他写作诗歌的原动力仍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颗关心国家危亡命运的赤子之心。“旧社会所谓出身‘清寒’的,面临飘零身世,我当然也是要改变现状的,由小到大,由内到外,听说到北伐战争,也就关心,也为了它的进展而感到欢欣。我从乡下转学到上海,正逢‘四·一二’事件以后的当年秋天,悲愤之余,也抱了幻灭感。当时有政治觉醒的学生进一步投入现实斗争;太不懂事的‘天真’小青年,也会不安于现实,若不问政治,也总会有所向往。我对北行的兴趣,好象是矛盾的。一方面因为那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一方面又因为那里是破旧的故都;实际上也是统一的,对二者都像是一种凭吊,一种寄怀。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的埋头读书,我终于安定不下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1](p1-2)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这样回忆他写诗的路程。
动荡的国事,激变的时代风云,震撼了卞之琳那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爱国情怀。这时的卞之琳,一方面不满于黑暗丑恶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茫然于如何改变这现实境况。因此,他的诗歌里充盈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
(一)、难以改变现实的无奈情怀
作为一个空有一腔爱国心,却又没有能力改变既定现实的诗人,卞之琳无奈而又痛苦。《西长安街》[2](p17)这首诗的第一节,作者用“长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枯树”、“老人”、“晚照”、“冬天”等意象勾勒出一个荒凉黯淡的世界。“我”虽然与老人走得很近,可是一路上“我们却一声不响”,只是“跟着各人的影子”。与此同时,“红墙”把蓝天隔绝在墙外。在这个冷漠而隔膜的世界里,“我们”就这样无望的沿着长长的道儿“走着,走着”,却不注意两旁的事物,也不相互谈话。如果说第一节作为回忆。那么,第二节应该有所改变。时间流逝,世界变样。可是,虽然换了“黄衣兵”,“不见旧日的老人”,这世界还是一如既往的死气沉沉:“黄衣兵站在一个大门前,\(这是司令部?从前的什么府?)\他们象墓碑直立在那里,\不作声,不谈话,还思念乡土”对于时间的流动,时代的变化,士兵同老人一样僵硬、麻木而没有觉察。然而,他们的心是动的——思念乡土。这有什么用处呢。虽然士兵自己手中握有钢枪,却只能眼见着敌人侵占家乡,而无能为力。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悲哀呀。时代变了,先进了:“多‘摩登’,多舒服!尽管威风\可哪儿比得上从前的大旗”。但是街上仍旧荒凉:“那三座大红门,如今怅望着\秋阳了。”整首诗,作者对“老人”、“黄衣兵”的麻木是失去希望和无可奈何的。那么,真的就只有在夕阳下怅然若失吗?真的这世界,这社会就没有希望吗?作者将希望寄托于“一个老朋友,他是在一所更古老的城里”。希望朋友不要学那荒街上的老人,要留意长安的印象。改变不了别人,只能自我改变。这是作者对远方朋友的希冀。但是,现实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作者没有把握——“我身边仿佛有你的影子”。《春城》也属于这种心境的表现。“题为《春城》,寄忧国忧时的心情于冷嘲热讽北平人(包括我自己,也代表全国一般市民)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在‘善邻’兵临故都城下以后的苟安局面中无可奈何的心态。”[5](p138)在肮脏、昏暗、麻木的故都,“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2](p33),尽管没有了线的牵引,但是“碰到了怎能不依恋柳梢头”。对祖国的爱与恨,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命运、改变现实的那份无奈心绪,全都融进这一句诗中。
(二)、怀古伤今,抒苦闷迷茫之情
历代中国诗人喜欢通过对古物风习的凭吊,来抒发自己怀旧伤感的情绪。诗人所具有的这份独特的敏感气质,使身处动荡社会的卞之琳也不能平静。在《登城》里,“我”和朋友“走上了长满乱草的城台”[2](p121)。在这个秋阳西下的傍晚,面对一派荒凉景象,朋友不愿“揭开老兵怀里的长历史”。“我”也感到茫然,且不知往哪里去。过往不忍回首,现实满目疮痍,未来则更是迷茫不知路在何方。这是怎样的苦闷与忧伤啊!自古以来,中国诗人就经常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使用“傍晚”和“夕阳”作为表现自己哀伤、忧郁心情的意象符号。特别是在国家处于衰落危亡之际,那些爱国的热血志士们面对“傍晚”和“夕阳”,总会发出:“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辛弃疾《摸鱼儿》)的悲慨。面对日渐衰微的国家,卞之琳的心绪不曾平静。夕阳,在卞之琳眼里如此颓败“倚着西山的夕阳,\站着要倒的庙墙,\对望着:想要说什么呢?\怎又不说呢?”[2](p4)古老的历史不堪回首。现实的衰败令人无法评说。说了又怎样?能改变得了吗?“西山的夕阳”与“要倒的庙墙”也只能互相无言地对望。“驮着老汉的瘦驴\匆忙的赶回家去,\脚蹄儿敲打着道儿—\枯涩的调儿!”一心回家的“老汉”和“驮着老汉的瘦驴”,对于如此哀伤的景象丝毫未予关心,可见他们已麻木到极点。“半空里哇的一声,\一只乌鸦从树顶\飞起来,可是没有话了,\依旧息下了。”“孤鸟”的意象在古诗中也屡见不鲜,晋人陶渊明《饮酒诗》:“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来去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脱身己得所,千载不相违。”诗人通过失群的孤鸟,来自喻空有一腔抱负却无从发挥的失意之情。但是,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而不气馁、不颓唐。中唐诗人杜牧《登乐游原》:“长空淡淡孤鸟没,万古消沈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诗人通过“鸦背夕阳”这一特殊的意象符号,抒发自己对初唐盛世的眷恋和对国家衰微命运的无奈心情。诗人接受了中兴以成一梦的现实,从中体认到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傍晚》中“乌鸦”的意象除去含有这层深意外,还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乌鸦”从树顶“飞起来”,它“哇”的叫声打破了枯涩的沉寂。可是当它看到这衰败的晚景,听到那枯涩的调儿时,没有了语言,又栖息回树上。“乌鸦”的这一段起落动作表现了觉醒者无力抗争,只能又回到沉默状态的悲哀。我认为卞之琳用这一意象,抒发了其苦闷的心悸。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失意与凄凉的心境。同样的心绪,在《群鸦》中也有体现。“啊,冷北风里的群鸦,\活该!你们领着\惨淡的冬天来干吗?”[2](p112)惨淡寒冷的冬天,只有乌鸦在空中飞。抵御严寒需要很大的勇气,应该受到赞扬。然而,“群鸦”不但没有得到理解,反而受到叱责。“啊,冷北风里的群鸦,\飘远了,一点点\消失在苍茫的天涯。”群鸦远去了,留下的只有“苍茫的天涯”而已。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卞之琳在创作这一类诗中出现的这种苦闷迷茫之情,乃是这时他对于麻木的人民失去信心,以及他意识到社会国家需要变革,但是又找不到变革之路的心理状态的曲折反应。1
诗人的诗作,往往是诗人自己心灵历程的表现。卞之琳的诗作也不例外。随着诗人对人生、社会的认识不断变化,在诗里所表现的情感倾向也有所不同。
二
应该说1933——1935年是卞之琳诗歌创作逐步臻于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卞之琳“开始在学院与文坛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了……”[1](p5)并且为了生计他的行踪也流动了。随着生活圈子的扩大、人生经历的不断丰富,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也有了变化。特别是1935年,对于卞之琳来说可谓是“收获年”和“创作转向年”。这一年,“他所写的那几首诗,可以看作他诗作成就的顶点”[3](p97)。1933——1934年间,卞之琳的诗作就预示出一个新气象的到来:《古镇的梦》,世俗生命荒谬地存在于时间和梦幻中;《古城的心》,在衰老沈睡的古城的微弱心跳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异乡客的沦落哀伤;《烟蒂头》,热闹中的寂寞体验;《水成岩》,流水的无情,时间的冷漠,“积下了层叠的悲哀”[2](p133),带走了不能再来的青春与记忆。《春城》,表现了面对敌人的侵略,北平人苟安的状态。等等。1935年,诗人的声音与以往有了些许不同。《距离的组织》,在一觉醒来偶得的“心情或意境”[2](p37)中,使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存在与觉识”有了新的体验;《旧元夜遐思》,则表现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魄。但是,在独醒者心中仍然充满着不能改变现实和唤醒梦中人的无奈与痛苦;《在异国的警署》,直抒诗人受到无端审问的愤怒心情;《尺八》,哀叹祖国的衰微命运;《圆宝盒》、《航海》和《音尘》通过诗人对时间的独特体验,我们感受到了在时空间人与历史的特殊关系。
在这些诗中,几乎从未被诗人和读者提到的就是《在异国的警署》一诗。这首诗感情直白而缺乏可读性。它在卞之琳众多诗作中,应该算作是不很成功的一篇。但是,该诗字里行间所充斥的排山倒海的气势是以往卞之琳所不具有的。而且,在它之后的卞诗又有了与以往更加不同的声音与情感。因此,我认为这首不算很成功的诗——《在异国的警署》——是卞之琳诗歌情感转向的分界标志。“是他不久登上新的高峰的起点”[4](p208)。
1935年,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并蓄谋侵占整个中国。这年卞之琳为了完成国内特约译书,跨海东渡日本,在京都住了5个月。然而,刚踏上东瀛土地,卞之琳便经历了一次非常不愉快的审问。对于这段经历卞之琳在一篇序言中写到:“其实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控制下的情报部门,如果还有点文化知识,也自有理由对我前去客居,会另眼相看……我在1934年春天,写了一首诗,题为《春城》……这就使人家有理由视我为并非等闲之辈,对我的旅日一行,妄自多心。”[5](p138)加之这时溥仪访日,日本警察又过分敏感。于是卞之琳也被作为“重要人物”受到了盘查。在极其愤慨的情况下,卞之琳写下了《在异国的警署》一诗。
一对对神经过敏的眼睛 看多少不相识手底下传递的细软、
像无数紧张的探海灯 不相识知好的信札、相片,
照给我一身神秘的鳞光, 驰骋我海阔天空的遐思。
我如今是一个出海的妖精。
但凝此刻我居然是什么大妖孽
重叠的近视眼镜藏了不测的奥妙?其力量足与富士比——
一枚怪贝壳是兴风作浪的法宝?一转身震动全岛?
手册里的洋书名是信息的暗码?敌对、威吓、惊讶、哄骗的潮浪
亲友的通讯簿是徒党的名单?……在我的周围起伏、环绕
我倒想当一名港口的检查员
专翻异邦旅客的行李、 可怜可笑我本是倦途的驯羊。
在诗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位善良且带着旅途倦意的异国游客莫名其妙地被当作“妖精”似的,无端受到警察的搜查、传询、厉审。“手册里的洋书名是信息的暗码?\亲友的通讯簿是党徒的名单?……”日本警察那可憎可笑的敏感和无知便跃然纸上。因此,这首直接抒发诗人突发情感的诗歌并不难懂,也没有以往卞诗的那种耐人回味的诗意。此诗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从创作方法上讲,都不是卞之琳的优秀之作。甚至,如若在不知作者的情况下读它,也不会认为是卞氏所作。对于这首诗,卞之琳自己的态度很矛盾。
一方面,卞之琳对其有特殊的感情。这首诗,原是以“阮竽”署名,发表在1935年5月10日发地的《水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而且,卞之琳还将它收进了1937年2月出版的第三版《鱼目集》,把它作为“另外一首”放在最后。因为,诗人对其有特殊感情。其原因在于这首诗代表了卞之琳一次特殊的心路历程。虽然,刚到日本就发生了这不愉快的一幕,但是,卞之琳认为此次旅日之行对他很有益处。因为这次异国之行扩大了他的眼界。
另一方面,从这首诗的艺术性角度讲,卞之琳自知此诗水平不高:“后来我就写了一首纪实抒情诗《在异国的警署》。这首诗我自己从艺术性考虑,认为写得太差,不耐读,不想留存,就像我有关这首诗的可笑的不愉快的经历,想最好忘却一样。我乐意秋吉教授没有注意到这首诗或者出于善意,存心不选这首诗。”[5](p138)并且,1979年卞之琳在编《雕虫纪历》时没有收入这首诗。1982年《雕虫纪历》再版时,也没有它。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卞之琳不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卞之琳的诗一向讲究“艺术性”、“耐读性”。同时,卞氏主张“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6](p8)并且,将其贯之于自己的创作中。但是,这首诗不但没有体现卞诗的主张,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大大放纵了诗人自己的情感,却不是“逃避情感”。那么,卞之琳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不成功的作品,还曾把它拿出去发表呢?我认为,卞之琳能写出这首诗并非一蹴而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有一个积蓄渐变的过程。那就是从《西长安街》、《傍晚》、《群鸦》、《春城》的苦闷迷惘和难以改变现实的无奈情怀到《旧元夜遐思》中独醒者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魄。但是,在独醒者心中仍然充满着不能改变现实和唤醒梦中人的无奈与痛苦。因此,我们在卞诗中读到的是: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对于麻木人民的痛心、对独醒者的孤独与无奈的感伤。而1935年恰是其心中所积蓄的力量将要爆发之际,加之身在异国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诗人找到了一个发泄情感的突破口,利用《在异国的警署》一诗,把郁闷心中久已的情绪如山洪般爆发在他的诗里。尽管这首诗不是卞之琳诗作中的精品,但是它的意义不在于诗歌的形式,也不在于诗歌的内容,却是诗歌所展露的心灵与情感的震撼。在这一首用“自由体”写成的诗中,贯穿着一股愤怒的力量。无辜被当作“妖精”的“我”实际上是“倦途的驯羊”。“驯羊”本性温顺,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到日本只是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顺便领略一下异国风物。但是,在“一对对神经过敏的眼睛”里,“我”却成为“其力量足与富士比——\一转身震动全岛”的“大妖孽”。面对着“在我的周围起伏、环绕”的“敌对、威吓、惊讶、哄骗的潮浪”,那个一向讲究情感克制的诗人不存在了。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我”发出了铿锵有利的抗议和质问“重叠的近视眼镜藏了不测的奥妙?\一枚怪贝壳是兴风作浪的法宝?\手册里的洋书名是信息的暗码?亲友的通讯簿是徒党的名单?”出行日本的不幸遭遇使他此前的认识加深,关怀变得更加宽广。“人家越是要用炮火欺压过来,我越是想转过人家后边去看看。结果我切身体会到军国主义国家的警察、特务的可憎可笑、法西斯重压下普通老百姓的可怜可亲。当然,多见识一点异国风物,本身也就可以扩大眼界。”[1](p5)《在异国的警署》当是其这种加深、加广之情感的原始形态的暴露,因而是其思想与诗风双重转变的重要标志。
三
异国的经历使卞之琳清醒的认识到国家衰微的根源所在。这段经历促使他更深刻的思索人生。“这些都影响我在这个阶段的诗思、诗风的趋于复杂化。”“一方面忧思中有时候增强了悲观的深度,一方面惆怅中有时候出现了开朗以致喜悦的苗头。”[1](p5)从这以后,卞之琳诗歌里的这两个倾向更加明显。
一方面,卞诗中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和对个人命运的独特感悟更显得深沉而又凝重。《尺八》应该属于这一方面的变化。在《尺八》里明显有一种“对祖国式微的哀愁”。[2](p39)但是,这哀愁不象《在异国的警署》那样直露地表现:“我只是觉得单纯的尽八象一条钥匙,能为我,自然是无意的,开启一个忘却的故乡,悠长的声音象在旧小说书里面梦者曲曲从窗外插到床上人头边的梦之根——谁把它象无线电耳机似的引到了我的枕上了?这条根就是所谓象征吧?”[7](p4)于是,我们在卞之琳精心营造的象征世界里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那“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生活在异乡的日本,听到凄凉的尺八音,动了乡愁。尺八是唐朝时候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为了寻访“尺八”的源起,“海西客”穿越时空,到繁华的唐朝“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这最后一句别有深意。唐朝时候繁荣的国势已不再来,现在祖国面临着被瓜分、被侵略的危机。卞之琳身处异邦又受到歧视,更感到祖国式微的哀伤。“尺八”原本从中国传入日本,但随时间推移,它已经在日本落户生根。难道中日两国之间就不能像“尺八”那样结出友谊的“花草”?诗人心中的淡淡哀愁是通过“即景即事”的抒情,混杂在字里行间突现出来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感时伤国的心绪比起《在异国的警署》来,显得柔和自然而不生硬呆板。唐朝盛事一去不复返,只能存在于诗人的记忆之中。现在祖国面临被侵占的危机,那繁荣的国势何时才能再一次出现呢。诗中所表现的不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上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情感。“此刻无端来了这个哀音,说是盛世的哀音,可以,说是预兆未来的乱世吧,也未尝不可。要知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哀音是交替的,或者是同在的,如一物的两面,有哀乐即有生命力。回望故土,仿佛一般人都没有乐了,而也没有哀了,是哭笑不得,也是日渐麻木。想到这里,虽然明知道自己正和朋友在一起,我感到‘大我’的寂寞,乃说了一句及简单的话:‘C,我悲哀。’”[7](p4)再如在《候鸟的问题》中,诗人自况为候鸟,苦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南北迁移,没有定所。“抽陀螺挽你,放风筝牵你”[2](p46),表现的是一种被动性。但候鸟只是被动地随季节变换而迁移,而“我”对于这样的生活,却并不是麻木的适应:“我的思绪象小蜘蛛起的游丝\系我是我是足以飘我。我要走。”“我”要由“我”自己来支配“我”的生活,而不由生活来支配“我”,这是诗人的抗争。“我岂能长如绝望的无线电\空在屋顶上伸着两臂\抓不到想要的远方的音波!”诗人不安于这样的生活,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然而生命的这种不确定性,有时却无法摆脱。这真是人生的一种悲哀。卞之琳运用戏剧化的写作方式加深了诗歌的内蕴,表现了诗人对生命的深切体验。
另一方面,卞诗里对人生哲理的透彻体验也越发带有理趣的哲思。《断章》应属于第二方面变化的优秀诗作。整首诗只由四句组成,却蕴涵着无限深意。“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2](p40)短短四句,利用空间的拓展、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意象(“桥”、“月”、“窗子”、“梦”)、“你”的不确指性,丰富了诗的情思。“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里的“你”可以是“我”,也可以指“他”。这种在人称上的不确指增加了诗的客观化,隐藏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从而加深了诗的趣味。“你”是看风景的主体,但是却又是被看的客体。“桥”和“楼”的空间转换更增强了主客对调的立体感。其实在人生这条风景线上,我们每一个个体不都是即充当主体角色,又充当客体角色吗。“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我们刚顺着诗人的视角观看室外的“风景”。又被这两句拉回到了室内的空间。“明月”装饰“窗子”是实景。“别人的梦”是虚设。在虚实之间诗人又带领我们进行了一次人生体验。即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看作为一首惆怅的情诗。自然景物在“你”眼中是美丽的风景。“你”在爱你的人眼中也是美丽的 风景。当月光射进窗子的时候,独在异地的“你”开始思念远方的家乡和那个还在家乡的人儿。与此同时,“你”已进入一个人的梦中。这个人也许是远方的那个人儿,也许是一个暗地里喜欢“你”的人。独在异地的“你”孤单寂寞,可谓是一种不幸。但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却进入别人的梦中,这说明还是有人惦记着“你”,又可谓是一种幸福。人生就是这样,永远处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爱与被爱之间。再如其《鱼化石(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也表现出这种风格:“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你我都远了乃有鱼化石。”[2](p138)如果我们把这首诗理解成爱情诗的话。那么在“女子”向自己情人倾诉的绵绵衷肠里,我们体会到她对爱情的执着。如果我们把这首诗看作是“鱼”对水的依恋之语。那么,在鱼的赞美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生生不绝的运动过程。整首诗通过“水”和“鱼化石”的意象框定了时间的永恒和万物的恒生。在这首诗里,我们较深刻地体验到诗人对时间的那种特殊感悟。
我认为从这时开始,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不仅加深了内在情思,而且诗艺也不断提升,并日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主要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冷静的智性。这种智性往往又通过诗人有意营造的“意境”表现出来。李怡师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中也提到了卞诗的这一特色:“诗人不仅关心那条情感如何流出,更注意把它淌回来,……它不叫你顺着情感溜下去,而是请你‘进入’,进入到那个空旷的氤氲的场所中去,有时候甚至并不试图说明什么、思索什么,仅仅再现一种诗人自己也说不清的“心情”、“情调”,这就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理想——意境。从现代西方的人生观、哲学观来读解卞之琳的一些诗作,也许会于一位其中包含着无尽的悲哀、玄妙的哲理,但卞之琳却断然否认了这一点,他曾解释说,这不过就是一种‘意境’罢了.”[8](p120)
收稿日期:2003-01-20
